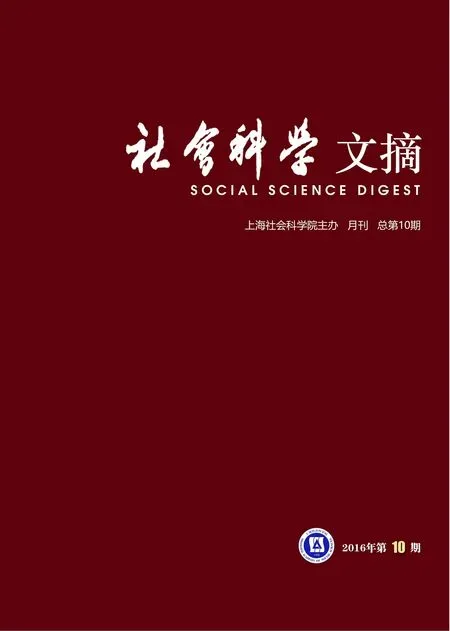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
文/杨光斌
合法性概念的滥用与重述
文/杨光斌
我们迫切需要对社会科学中的基本概念(如政体、合法性、自由、民主、宪政)进行重新解释以达成新的认知,否则就必然是概念滥用。社会科学是人们基于特定国家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定经验的观念化工作,在本体论意义上属于地方知识。但是,在作为意识形态战争的冷战中,很多地方知识被“普遍主义化”,现在流行的很多概念如本文中的合法性,就是“冷战学”的产物。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的观念化概念,已经深深嵌入中国思想界,以意涵不明的或充满张力的合法性概念来度量中国政治,造成了许多误读。由这一问题意识出发,本文基于对合法性概念的知识论上的重述,试图对合法性的构成维度作一个总结。
合法性概念的知识脉络
合法性概念的滥用只是中国社会科学令人难以置信的落后性的一个缩影。“无选举授权就没有合法性”已经是很多中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的政治表达。然而,它在合法性概念体系中的地位如何?
合法性理论的“立法者”马克思·韦伯首先提出合法性命题,强调合法性体现为政权的合法律性和有效性;半个世纪之后的冷战时期,为了配合熊彼特对民主概念的颠覆性改造,美国政治学家李普塞特复活并建构了合法性概念,将选举式民主纳入合法性理论,即所谓的合法性来自选举授权。但是,选举授权不仅未能避免20世纪60~70年代西方政治危机,第三世界国家更因此出现政治衰败。为此,亨廷顿响亮地提出不能进行有效治理(统治)的政府不但不具有合法性,还是不道德的。自由主义者罗尔斯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哈贝马斯在20世纪70年代初相继出版了影响世界的研究西方政治合法性的著作。提倡“反思平衡”的罗尔斯不但论证了西方政治自由主义的合法性问题,还为非西方社会的合法性政治提出一个“良序合宜政体”。
这是思想市场上的巨大反讽,当罗尔斯反复强调不能依据西方社会条件而判断非西方国家政权的合理性、合法性时,中国学者依然在依据那个为西方定制的理论而评判中国政治的合法性。从上述西方知识脉络上看,合法性不仅仅是一个因时因地发生变化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包含了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义性等多种维度的概念体系。
合法性的“因时因地”性质
合法性是一个“因时因地的哲学”,“因时因地的哲学”(“positional philosophy”)是亨廷顿用来定位保守主义的说法,也特别适应于合法性概念的性质。正如同“因时因地的哲学”并不否认保守主义的基本要素一样,其也不会否认合法性的基本要素或者现代性政治的共同基础。
第一,合法性概念的时代性。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合法性、正当性的观念,且不说前资本主义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标准和来源的不同,就是在现代性政治中,从韦伯的官僚制就是合法性,到李普塞特的选举授权合法性,到亨廷顿回到韦伯式的以统治能力为标准的合法性,最后到罗尔斯的以正义原则为标准的良序社会,都是回应大时代的产物。也就是说,以一个产生于特定时代、特定社会经验的概念当作政治标准去度量所有国家的政治的时候,要格外谨慎。
第二,合法性政治的国家性特征。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合法性诉求,这是由国家发展阶段、国家的文化基因禀赋所决定的。在发展阶段上,有的国家最急需的是秩序和经济增长,如果此时冠于选举授权的合法性即追求分配政治的民主合法性,结果就是已经发生的世界性政治衰败。因国家禀赋差异,比如同质化文化与异质化文化的差异,把同质化文化下的合法性工具运用到异质性文化之中,结果非但不是合法性政治,而是灾难性政治,是非道德的无政府状态。中国先人早就有这方面的智慧:“物之不齐,物之情也。”
第三,即使是同一个国家,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有不同的合法性诉求。德国从韦伯式的官僚制合法性,发展到魏玛共和国选举授权合法性并因此回到国家主义的合法性,最后发展到当今的基于“共决制”式的商谈民主的合法性。美国作为国家的合法性,首先来自南北战争之后确立的联邦制而非邦联制的国家,之后建立在因进步主义运动而确立起来的现代政府体制,后来就是熊彼特式民主即李普塞特所谓的选举授权合法性,不久便是三边委员会所建议的“民主的统治能力”的合法性,现在依然是治理能力的危机,即福山所说的“否决型政体”。中国也概莫能外。
合法性之"四维"
世界政治演化到了今天,基于政治实践的各种合法性学说,已经为我们提供了可以抽象的合法性政治的基本要素,包括四个方面: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和正义性。
第一,虽然合法律性是人们都承认的现代性政治原则,但因为法治或者说宪政是“西方性”的基因,非西方国家的法治必然不可能等同于是西方,何况西方国家本身的法治化道路也是不一样的,有英美式的自发秩序,也有法国和德国自上而下的强制性法治,还有新加坡式的“党主立宪”,中国这样的人情文化国家的法治化道路更有别于西方。世界历史和世界政治告诉我们,虽然合法律性是现代政治的基石和闸门,但合法律性并不必然意味着具有正当性,希特勒是靠民主程序上台的,结果是人类的灾难。今天,很多发展中国家也都实行竞争性选举,都有了宪法法院,但并没有因此使社会和国家更好,根据世界正义工程(the World Justice Project)的指标,其法治水平并不比中国高,甚至远远落后于中国。因此,合法律性并不必然意味着正当性(即符合正义原则)。正义性是衡量其他指标的最高原则。
第二,有效性是最没有争议的合法性政治的基石,从韦伯式官僚制的有效性,到李普塞特所说的长期有效性有助于合法性,再到亨廷顿所说的作为有效性的统治能力,以及罗尔斯强调的政府责任的有效性,都是合法性须臾不可缺的要素。在这个意义上,古老的合法性概念其实是基于古老的有效性概念,哪个政治统治不追求有效性呢?也就是说,现代性政治不能代替几千年演化而来的传统性智慧。
第三,比较而言,“人民性”是学界争论最大的要素,这里需要给出具体的说明。可以说,大众政治参与是现代政治合法性的根本来源。自从卢梭呼唤“人民主权”以来,人民性已经成为不容置疑的合法性政治的最重要的来源,所以,鼓励人民参与政治并保障公民政治权利,是政治合法化的必要历程。但是,同样是人民参与,为什么有些国家是有序政治因而才具有合法性,为什么很多国家变成了无序政治、无效治理并因此丧失了合法性呢?思想的成熟和深度体现在逻辑的分层性上,而打包处理的做法即以一个大概念来解释一切,恰恰是思想肤浅的表现。
关于人民性,这里有几个层次的逻辑。
首先,同质化的人民即同一个种族的条件,在这个条件下,在法治政治确定即罗尔斯所说的宪法政治第一的前提下,人民参与范围的扩大并不会动摇政治制度,反而赋予政治制度更大的合法性。李普塞特所说的选举授权合法性就是以美国、英国、瑞典为原型的,甚至还以当时的法国为反面教材。但是,即使是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同质化国家之所以能有序实现政治参与,历史前提也是“大清洗政治”。比方说,在美国即表现为白人对印第安人的种族灭绝式屠杀,亨廷顿说用今天的标准说就是种族清洗,迈克尔·曼(Michael Mann)详细描述了这一种族清洗的残酷过程。英国的同质化民族首先也是有了克伦威尔专政时期对天主教徒的大屠杀,最后是19世纪20年代的宗教和解,才有了从1832年开始之后的一系列选举改革,渐进扩大选举权。
其次,由此衍生的更加复杂化的政治是,在异质化社会,即在存在冲突性种族、宗教和社会阶级的国家,“人民”之间并不存在共识的基础,选举授权结果变成了对各自冲突性利益结构的确认,是对“普力夺社会”或“强社会”的确认,国家因此陷于或分裂、或动荡、或无效治理的境地。也就是说,作为一种现代政治形式的大众选举最终坐实了古老的固有的利益结构,在印度北方邦和菲律宾强化了封建制地主的权力,在非洲强化了军阀和冲突性种族的权力。形同虚设的现代国家即米格代尔所说的“弱国家”,连亨廷顿所说的“统治能力”也丧失了,何来合法性?因此,在运用合法性概念时,正如社会科学的其他概念一样,最忌讳的是“概念拉扯”而导致的概念滥用,必须慎重看待人民主权与合法性之间的关系,尤其要慎重看待人民主权的实现形式。
别说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就是一个城市国家,政治制度也是分层次的,也是多功能的。人民主权有赖于政治制度去实现。政治制度的层次性和功能性意味着,必须采用配套的、相应的方式去实现人民的权利,不可能用一种方式而适用于层次不同、功能不同的政治生活。选举、协商、分权和表达权等民主形式,其适用性取决于其场景性质,试图以一种方式而一劳永逸地解决人民主权问题,结果反而践踏了人民主权。为此,哈贝马斯和罗尔斯才不约而同地都把商谈、审议、协商看作合法性或良序政治的路径;尤其是罗尔斯,他更是明确质疑多数决程序民主对于正义政体的价值。这些洞见已经被正在发生的世界政治所证明,即第三波民主化——“阿拉伯之春”所招致的国家治理能力的丧失和政治衰败。
因此,虽然说现代性政治就是人民性,但即使基本于合法律性的人民性政治,是否必然具有正当性?也要视正义性而定。要知道,不同语境下的“人民”是完全不一样的,即同质化与异质化文化下的人民具有完全不同的意义,从而呈现共识政治或冲突政治的结局。因为语境不一样,以什么样的民主制度而实现、容纳“人民性”,就是政治家最艰难的抉择。即使是自由主义者罗尔斯,也承认万民社会中存在不同的但符合正义原则的合情理的制度形式,承认非西方社会的“合宜的协商等级制”即以协商程序为主的“良序合宜政体”。
第四,正义性。相对于合法律性、有效性和人民性等经验性或工具性的标准,正义是评价合法性的价值标准,也是一套制度标准,因为罗尔斯正义论的主题就是制度正义。虽然,本文中的正义原则是来自自由主义者的论述,但是,他们的正义论主张已经汲取了社会主义关于公正思想的营养。比如,罗尔斯说过财产所有权的民主和自由(民主)社会主义这两个政体才是符合正义原则的,而美国式自由资本主义和自由资本主义的改良版即福利资本主义则有违其正义原则的一些方面。进而,寻求世界和平和全球正义的罗尔斯认为,非西方的很多国家,恰恰因为其政治的协商性质、基于协商的法律保护了人权,是符合非西方语境的正义原则,因而是一种良序社会即“合宜政体”。其实,社会主义政治的“理想描述”包含着公正社会原则,公正更是中国文明的一种古老的政治传统和政治实践。
“合法律性—有效性—人民性—正义性”之间的逻辑是:(1)合法律性是一切现代政治的前提和基础,在此基础上的有效性增进了合法性,韦伯的合法性概念依然没有过时,是所有其他合法性理论的元理论,而且是不能或缺的要素性概念。但合法律性政治并不必然具有正当性。(2 )现代性政治就是人民性政治或者说大众政治,因此没有大众参与的政治就谈不上合法性,但人民性之于合法性的关系是多面向的,既有实质的人民性又有形式的人民性。就前者而言,人民性体现为民生的实现程度而达成的“民心向背”;就后者而言,政治形式并非有了人民性就具有合法性,因为人民性与合法律性和有效性之间都存在着复杂性关系,人民性形式的民粹主义破坏着合法律性,人民性形式的党争民主也有可能形成“否决型政体”,即无效治理,法治的破坏和无效治理伤害的都是合法性。正义性制度(宪法政治第一位重要性)不但可以框定人民性,也是衡量合法律性和有效性的标准。合法性四要素之间的关系,有助于理解具体情境中的合法性政治。
作为一种政治秩序观的合法性
合法性知识叙事告诉我们这样一个事实,合法性是特定语境下的政治秩序观。中国与西方分属于两种不同的历史语境,遵从两种政治逻辑。西方历史最悠久的一个政治传统是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对立,而且一直是法律性的程序至上主义。从韦伯式的合法性理论,到李普塞特的合法性理论,尤其是到罗尔斯的正义政体理论,都是基于二元对立之下的社会对国家的衡量,形成自由行动、个体责任传统,并据此而度量国家满足个人利益的合法性信仰。
在现代性政治中,有很多共同的要素已经建制性地存在于世界政治之中,即自由、民主、法治、公正、人权等价值也已经是中国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抹杀或磨灭了各自的政治传统与政治逻辑,更不意味着可以无视自己的政治传统和政治逻辑而用基于完全不同政治逻辑而产生的政治概念衡量中国政治。“文明例外论”,在基督救世文化的普遍主义那里并不受欢迎,但是中华文明确实独特,这是所有涉猎中华文明的作者都特别强调的。
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治理体系,要建设法治化民主,但是这些重大的根本议程的解决,只能在中国语境和中国逻辑里解决,因为政治制度从来不能脱离其文化而有效存在。
正如郝大伟和安乐哲所言,“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和以权利为基础的民主以及自由企业资本主义,都是西方现代性历史发展的具体产物。因此,任何试图将这些东西在各文化中普遍化的做法都可能是愚不可及的。”“把所有这几件起作用的东西照搬到中国去,就会大大改变中国的特性,实际上将整个把中国社会改造成一个外族历史叙事的终端。”现代性意味着政治形式的同一性,很多国家的政治制度在形式上都英国化或美国化了,但是文明基因并不能随着政治的改变而改变,在文化难以改变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外来的政治制度并不能如人所愿,很多情况下甚至更加糟糕。因此,美国孔飞力(Philip Kuhn)教授著作的最后一句话可以拿来作为本文的结束语:中国建制议程的界定所根据的将不是美国的条件,而是中国自己的条件。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系教授、长江学者;摘自《政治学研究》2016年第2期;本文系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项目“国家理论的反思与重建"(10XNL015)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