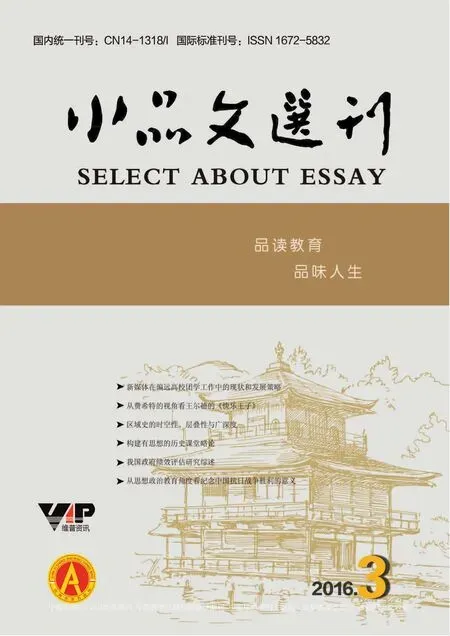古今文《毛诗》浅议
宋丹丹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387)
古今文《毛诗》浅议
宋丹丹
(天津师范大学 天津 300387)
经学史上,素来有“今文经”与“古文经”、“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的说法。由于缺少翔实的证据,关于《毛诗》的今古文之辩历来纷争不断,但总体来看支持《毛诗》为古文经的学者仍占大多数。不过依旧有少数人坚持《毛诗》今文说,力图推翻自古以来的公认。本文针对《毛诗》古今文之说阐述一下自己的观点。
《毛诗》;古文经;今文经
今文经指汉初由儒生口传,并用当时流行的隶书记录下来的经籍;古文经指汉代前期从民间征集或孔子故宅壁间所发现的用先秦古籀文字写成的经籍。四家《诗》中,鲁、齐、韩三家为今文经,毛诗为古文经,为大多数人所认同,然近年来又有人提出异议,认为《毛诗》为古文经缺少文献依据,很有可能亦为今文经,对此,笔者认为值得商榷。
有一种说法认为“汉史文献所记古文经来源主要有:《汉书》之《景十三王传》《楚元王传》《儒林传》《艺文志》、王充《论衡》之《佚文》《案书》《正说》、《史记·儒林列传》、许冲《说文解字序》、《后汉书》之《杜林传》《儒林列传》”,“细审以上文献,并无言《毛诗》为古文经之依据。”[1]相同意见的还有王国维先生,其在《观堂集林》卷七《汉时古文本诸经传考》中提到“《汉书艺文志》《毛诗》二十九卷不言具为古文,《河间献王传》列举其所得古文旧书,亦无毛诗,至后汉始以《毛诗》与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传》并称,其所以并称者,当以三者同为未列学官之学,非以其同为古文也。惟卢子幹言‘古文科斗,近于为实’,而下列举《毛诗》、《左传》、《周礼》三目,盖因《周礼》、《左传》而牵连及之,其实《毛诗》当小毛公、贯长卿之时,已不复有古文本矣”。[2]《汉书》等诸文献中确实没有明确说《毛诗》为古文,但同样没有明确写出其为今文,仅以没提到就断定《毛诗》非古文未免有失公允;至于《景十三王传》(即《河间献王传》)中写道“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繇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3]“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3]其中提到“得书多”“之属”,故不一定详尽列举,仅以《周官》等举例,没提到《毛诗》也并非不可理解。献王好古文,若说其所立《毛氏诗》为今文博士,于情于理均不通。
除了王国维先生提到的这些疑点,有学者认为,“纵观《汉书·艺文志》六艺略的录书结构,可知其是按先古文后今文的模式进行的,若有古文经,则将其列于首位,且称‘某古经’或‘某古文经’。如‘书’类首行为‘《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4]所以认为若《毛诗》为古文经,也应列于“诗”首行而非排在三家之后,且应标明“古”字。拙见以为特写明“古文经”或“古经”,乃是为了区别古今文,倘若不加,古文经和今文经名称相同者,无法辨识。而《毛诗》不同,已有“鲁”、“齐”、“韩”、“毛”做为区分,故而即便不加“古”字也不会和今文经相混淆。正因为《毛诗》没有写“古文经”或“古经”,所以便没有将其放在“诗”类首行。与此相同的还有《左氏传》,此为古文,但同样没有“古”字。
有观点从出土文献的角度提出质疑。其一为解放初,上海市文物保管委会购得两块《熹平石经·诗》残石,这两块《诗》残石,推测应是今文《鲁诗》;其二为1977年出土的安徽阜阳双古堆汉简中也发现西汉早期《诗经》竹简,其文字、篇章顺序与四家《诗》均有不同, 推测是楚国流传下来的另一版本,三家诗现今已有考古发现,而一直保存至今的《毛诗》却还无古文经的原始残存,认为这是推翻古文经《毛诗》的证据之一。虽然目前并没有汉代乃至更早的《毛诗》相关出土文献,但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发现大批《诗经》写本,“据历年研考所知,现藏于英国、俄国、日本的《诗经》卷子,都是《毛诗》残卷,大多是《毛诗故训传笺》,也有白文和晋徐邈《毛诗音》残卷”。[5]此外1930年,在吐鲁番雅尔湖旧城出土了《诗经》残纸一页,有《毛诗·简兮》校记,“传笺双行小字,共九条”。[6]除此,还有诸多和《毛诗》相关的出土文献不再一一赘述。
清末,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一书提出西汉古文经传都是刘歆伪造,其中包括《诗经》,一时轰动士林,影响很大。近年来又有学者提出“刘歆伪造《毛诗》”的说法,“伪造一古文《毛诗》新立官学不仅符合政治上托古改制的要求,也击中了外人无法辨别其真伪的软肋”,[4]《诗经》之今、古文之差异主要在诠释方面,“而诠释的差异,正好成为托古改制的注脚”。[4]对此,钱穆先生称“余读康氏书,深疾其抵牾,欲为疏通证明,因先编《刘向歆父子年谱》”,“要而述之,其不可通者二十有八端”[7]。钱穆先生主要从时间、伪造手法和伪造目的等三个方面进行反驳。
1 时间不通。
刘向卒于成帝绥和元年,刘歆在第二年领校《五经》,如若刘向生前刘歆作伪,刘向怎会不知?若死后作伪,如此短的时间即能伪遍群经?
2 作伪手法不通。
倘若刘歆伪遍诸经,是他一人之手还是群体为之?古时书籍多为竹简,书写笨重繁杂,且杀青不易,恐不能不假借他人之手。若是群手伪作,为何无一人一字提到作伪?况且与刘歆校书者并非一人,尹咸、班斿、苏竟等均为当时的大学问家,刘歆之伪作必不能辨认不出;扬雄校书天禄阁,东汉诸儒班固、崔骃、张衡、蔡伦等,并校书东观,怎会辨识不出伪作?当时通博洽闻之士如桓谭、杜林、师丹、公孙禄、范生等,皆不言刘歆伪作,“然则歆之遍伪诸经,当时知之者谁耶?而言之者又谁耶?”[7]
3 造伪目的不通。
前面提到说刘歆造伪是为王莽政权服务,然而刘歆争立古文诸经,王莽才刚退职,绝无篡汉之迹象;说刘歆伪经媚莽,多就《周官》而言,但《周官》后出,争立诸经之时,《周官》并不包括在内。“莽据《周官》以立政,非歆据莽政造《周官》”,“且当时媚莽助篡者众矣,不独一歆,歆又非其魁率。甄丰为莽校文书,六莞之议,蔽罪鲁匡,此尤其彰著,何以谓伪经者之必歆?”[7]
除此杨宽、饶宗颐和李均明等也做过相关论述,为刘歆正名。由此可见,说刘歆伪作《毛诗》必然也是不成立的。
今古文经仅以字体来划分显然不够严谨,两者的不同不仅在于所书写的字体,而且字句、篇章、篇次、语序、字数均不完全一致,更重要的是对经典内容的阐释也有差异。对此,王葆玹先生曾提出以抄本时间来做为区分依据:“所谓今文经仅限于汉武帝元朔五年或稍迟写定的经书今文写本,除此之外,凡有古文祖本的经书传本,不论是隶体还是古籀,都可能属于古文经的范围”。[8]且不说这样的划分科学与否,但确实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路,帮助我们更好的区别今古文经。
从这个方面来看,认为《毛诗》为古文经也是有根据的。时间上毛诗虽后出,但文字为籀文,即篆文,是六国时的文字,未立于学官,仅在民间广泛流传。除此,解诗方式的不同也是古今文《诗》的区别之一。三家诗解说诗义,常常即事言之,而《毛诗》更重视诗中的美刺与礼义教化内容的发掘,不那么拘泥于具体史实,《毛诗》这种述诗之法直承孔子述作《春秋》之法,有古圣先贤的遗风,谓之“古学”也顺理成章。
今古文经学之争从汉朝持续不断延续至清朝,甚至到近代,历经两千年左右,在学术史上影响重大,周予同先生总结为:“因经今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社会哲学、政治哲学以明,因经古文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文字学、考古学以立,因宋学的产生而后中国的形而上学、伦理学以成”,[9]可谓全面而精准。倘若过分强调两者的对立性,走向极端,于学术研究反而会产生消极影响。正确认识今古文经学,才能整体把握中国学术文化传统的内核。
[1] 梁振杰.《古文<毛诗>质疑》[J].文学遗产,2007(5):122
[2] 王国维.《观堂集林》卷七[M].北京:中华书局,1961:322
[3] 班固.《汉书》卷五十三[M].北京:中华书局,1962:1706
[4] 章琦.《<毛诗>今文说》[M]. 新国学,2010(00):14
[5] 夏传才.《诗经》出土文献和古籍整理[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05,28(1):68
[6] 刘立志.《近百年间出土的<诗经>文献述要》[J].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学报,2009,(2):91
[7] 钱穆.《钱宾四先生全集》卷八[M].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1,3,6
[8] 王葆玹.《今古文经学新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61
[9] 周予同.《经学历史序》[M].北京:中华书局,2004:1
宋丹丹(1989-),女,汉族,河北沧州市人,文学硕士,单位:天津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I207
A
1672-5832(2016)03-0068-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