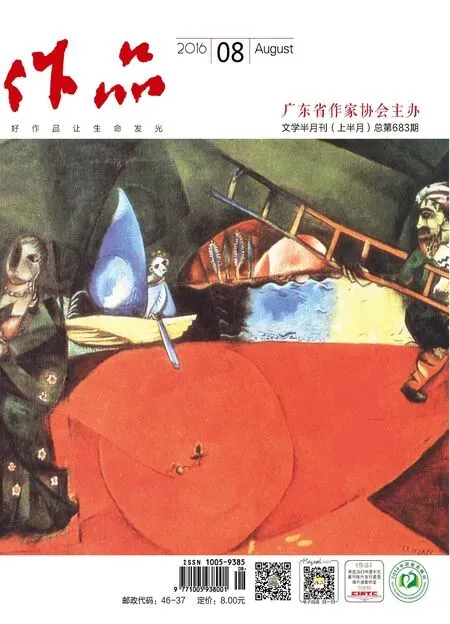春 英
文/叶清河
春 英
文/叶清河
叶清河1980年生,广东清远人,发表作品见《创作与评论》、 《作品》、 《广州文艺》、 《文学界》等,曾获全国青年产业工人文学奖中篇小说奖,有小说被选刊选载。
四婶被荣源鞋厂辞退后,就回到了村里。几天后,我们接到四叔的电话,说四婶病了。
我赶回村里,四婶坐在椅子上,神情漠然,目光迷离。我喊她:四婶。她看我一眼,良久才说,我叫春英,你是谁?我愣了一下,四叔摇着头,说我回来之后,她就这样了,连我她也不认得了。
那几年里,我们也带四婶看过了几个医院,但她的病情一直没有好转。时常地,她会坐在巷子里,看着某一个地方,久久地出神。如果不喊她,她会一直地坐着,如一尊石像,不声不响,直到被夜色所吞没。
我的四婶,她的名字的确叫春英。
二十多年前,那个叫春英的女孩子,跟着四叔来到了蘑菇岭。那一年我刚五岁,那天我在外面玩了回家,发现家里门口站着一个大女孩,脸容娇俏,穿戴鲜亮。我停了一会,那大女孩招手让我过去,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发现她的腔音,夹着轻轻的震颤,听着很特别。我说,我叫小亮,你呢?她笑着,我吗?我叫春英。我挠着头,喊一声,春英姐。她咯咯地笑得更开了,抚着我的头,对,以后就这么喊。
但很快,春英姐就变成了是四婶。喝喜酒的那天,乡里的亲戚都来了,那队伍浩浩荡荡,前头的人来到了村里,后头的人还在他们自己的村子。村里的巷子,摆满了桌子、椅子,村头架起了几口大锅,那木柴可劲地烧,肉菜在锅里翻滚,香气飘上了村子的半空。鞭炮烧了一挂又一挂,从远山又传来回响。村里的男人妇女,都分了工,切菜的、煮饭的、招待的,忙个不停,孩子们则满村地呼朋引伴。宴席上,有大人们爱喝的头曲酒,孩子们喜欢的菠萝啤、美津汽水;晚上,还在村前拉起白布幕,放了电影《大刀王五》、《神鞭》。
我记得,当时新人穿着一件红色对襟裙,戴着耳环、手镯,踩着红鞋子,在家里长媳妇母亲的带领下,端着盘子挨桌子地给敬长辈。这个是大舅父、这个是三姨丈、这个是表姐夫,新人就跟着一个个地喊过去,双手恭敬地递上茶,小心地点上烟。然后,长辈就给新人回利是,说些夫妻美满、早生贵子的话。
那当儿,我在一旁看着,觉得挺好玩的,也嚷嚷着要喝茶。母亲让我别闹,周围的人却哄笑着,新人也笑,端了茶给我喝。身边的人问,该喊什么?我喊,春英姐。母亲纠正了,喊四婶。我环顾四周,又看着面前的新人,总觉得那一转口之间,会有什么丢落了,就呜呜地哭了起来,边哭边喊,四婶。四婶又抚了我的头,给了我一个利是。
喜酒过后,肉菜的香气渐渐飘去,鞭炮的纸屑渐渐吹散,村里的日子又回到了鸡零狗碎。四叔继续外出城里打工,四婶则留下了在村子里,每天,她依然会穿上明亮的衣服,踩着崭新的鞋子。在我,这都是新奇的,总觉得这个婶子与别人不一样。但是这样的做派,在家人那里,尤其是在祖父那里,却犯忌了。
祖父是大家庭里的家长,做农活是一把好手,但也专制,家里的事,都由他做主,祖母、四个媳妇,都由他安排农活。这天,祖父瞥一眼四婶,说喝过粥,你也到田里去!
四婶只是笑,答应了一声。
不过,那时候四婶不喜欢喝粟米粥,她说闻到粟米粥的碱水味道,看到粟米粥的糊状样子,就感到不舒服。她自己煮了米饭,蒸了萝卜丝,皱着眉头吃下了。而这又一次犯了家里的大忌,那时候村里的习俗,是白天喝粟米粥,到了晚上才吃一顿米饭的。
之后,四婶是跟着去田里了,不过身上穿的还是明亮的衣服。正是农忙,田野里都是忙碌的人们,长成的秧苗在风吹过里摆动,蜻蜓和蝴蝶在河边飞舞。田里是汪汪的浊水,四婶挽起了裤管,还是走了下去。然而,站到了水田中,她却有些茫然无措,似乎是过了好久,才明白到是来插秧的。开始插秧了,四婶又顾忌着身上的衣服,双腿站得笔直,腰也梗着弯不下去,那秧苗就不是插在田里,而是扔了下去的。半天下来,她就扔了那么几行秧苗,还东歪西倒的。回头看身后,妯娌们已经离得很远了,插下的一大片秧苗,包围了她。祖父在一旁,骂骂咧咧着,四婶回了一句,祖父就大发雷霆,把一大捆秧苗往田里一摔,泥水溅了四婶一身。很快,村里也风言风语了,说四叔娶了个中看不中用的女人,不能干农活,有个屁用?
那段日子,四婶过得很艰难,她就像是一头贸然闯入村里的野生动物,总让人感到格格不入。祖父每天依然冷脸相对,只是派工,却不教四婶做农活、用农具,家里人也都不敢作声,村里人则只等着看笑话。四婶呢,却还在倔强,每天下田,依然是穿着一身明亮的衣服,只是变得沉默了,不再笑了。
半个月后,四婶就回城里了。
原本,那个叫春英的女孩子,是在东莞的一家玩具厂打工,已经做到了线长,手下管着二十多人。她回到了厂里,找到了经理,经理正为缺个得力的线长犯愁呢,马上就让她归了队。终于,在工友那里,她又做回了春英。只是,才过了几天,四叔就让四婶回家。那时候,村里的习俗,凡是嫁来的媳妇,都留在家里耕种,男人才到外面去打工,形成了“女耕男工”的家庭模式。可是,四婶不肯回家,四叔说她不过,又不敢违抗祖父的命令,心里苦闷极了。过了几天,四叔和四婶就吵了起来,四叔撂了狠话,要是不回去,就离婚。四婶看着四叔,叹口气,你说真的吗?四叔愣一下,还是点了点头。四婶说,那就离吧。四叔看着四婶离去的背影,心里后悔,却又收不回,一时愧疚难当,竟然去了跳河。亏得有路人看见,救回来了。
就那样,四婶又回到了村子里。
很快又到了来年春耕,当四婶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穿的已经不是明亮的衣服,而是干农活的旧衣服了。那个叫春英的女孩子,在四婶身上剥掉了。
开耕的第一件事,是挑农家肥到田地。那些农家肥,是从牛栏、猪栏清理出来的粪便、灶头烧剩的柴灰、稻草、烂菜叶等等,堆放起来积了一整年的。走到粪屋附近,一股浓重的气味传来,四婶挨着墙面,哗啦啦就呕吐了。进了屋里去,又呕吐了一回。这样之后,她才抓起了铁笊,装满了两簸箕农家肥,挑起了担子。那天,她就一直一声不吭地,只管挑了一趟又一趟。直到中午,她累倒在了田里。大家把她扶起来,放到树荫下,这才又发现,她脚板也起了泡,肩头也磨得红肿了。母亲给她搽了药油,她醒过来了,喝了半壶玉米粥,挣扎着爬起来,又去挑担了。渐渐地我们都知道了,四婶这是要与祖父斗,与自己斗。
几天后,祖父又给四婶派了新农活,她得学会犁地。春天里,满山都是绿芽,溪水清莹透澈,新翻的泥土有一股潮湿的气息。祖父阴沉着脸,把牛交给了四婶,就一个人坐在地头抽烟。四婶去套牛枷,那牛犊却欺生,就在原地里转圈,躲着牛枷。好不容易把牛枷套上,挂上了犁具,四婶还没有掌握犁地的窍门,推着那犁具,越推越费劲,只累得满头大汗。可是那牛呢,还故意走得歪歪扭扭的,走了几转,就停住了,怎么吆喝都不走。四婶火上了头,扬起手中的竹枝,就抽在牛背上。那牛一溜烟地往前狂奔,四婶在后面追了一阵,犁具挣脱了她的手。那牛一直跑到了山边,过了一会,兀自吃起了草。四婶坐在地头,却笑了。也许,她本来就不想好好犁地的。
事情的真正转变,是到四婶生下了堂弟。
四婶怀第一胎的时候,家里人并不知道。那时候,正是农忙,农活都是一趟赶一趟的,摘了粟米,紧接着就割稻谷,然后是挖番薯、拔花生、收黄豆。那天收黄豆,七月的太阳向大地喷火,为了赶收成,一连地忙了一整天。到了傍晚收工了,四婶才发现裤管里湿了一滩血水,她流产了。到了第二年,四婶再次怀孕了,祖父不好再安排四婶重活。可是,终究躲不过一些非议,三婶就说,就你矜贵,哪个女人不会怀孩子?谁怀着孩子不照样下地干活?三婶这个人,嘴巴是比较不饶人的,不过她说的也是事实,向来村里的妇女怀孩子,都没有休息的,直忙到要生孩子的那一刻。四婶呢,听不下话,也就较上了劲,干活更加卖力了。结果,又在一次种番薯回来后,孩子流产了。孩子接连流产,流言又起了,说这都是四婶故意的,她赌气般地干活,就是要让孩子从自己身上掉下来,因为那时候,她还不想留在村里的。再过了两年,四婶又怀上了,这一回,祖父也不敢大意了,安排了祖母照管四婶。那时候,祖母每天都会到乡里小墟上买肉,剁碎了给四婶蒸肉饼,每隔两天就会煲一次鸡汤。我想,也就是在那段时间,祖母对四婶的感情悄悄地发生了变化,之后直到她老人家去世,对四婶都一直怜惜。后来,堂弟出生了,四婶也就在村子里落下根了。
又过了两年,父亲四兄弟分了家,四婶有了自己的田地,渐渐熟识了村里所有的农活。她总是凌晨四点就起床,熬粟米粥、煮猪食、喂鸡喂鸭,天亮了就去地里干活。傍晚回来,又忙于淋菜、喂猪、照顾孩子,常常要到八点多才吃晚饭。
那段时间,四婶又做了一件在村里轰动一时的事。
田里插了秧,就要放田水。为了抢田水,人们常常在半夜里出动。那天夜里,四婶先去放了一轮田水,回来睡了个把钟,还是不放心,又再次去了田里,却遇见了隔壁村叫金荣的,把水渠全堵上了,把水全放到他在下家的田里。四婶与金荣吵了起来,金荣欺负四婶是女人,动手把四婶推倒在了田里。四婶爬起来,与金荣扭打在一起。金荣开始时占尽上风,但四婶却憋了不怕死的劲,缠住了金荣,又是抓又是咬,还怪叫着,完全是疯了一般,渐渐地气势上来了,把金荣打倒在了水渠里。这事情,后来就传开了,人们又添油加醋地增加了些内容,说四婶当时骑在金荣身上,每甩一巴掌,就问一句还敢不敢?又说,当时金荣已经跪下了,眼泪鼻涕一起流。不过,那之后,村里人再看四婶时,确实就多了些恭敬了。
渐渐地,四婶成了村里的“熟媳妇”,也成了村里耕种的一把好手。每回村里娶新人,四婶都参与张罗宴席,带新人敬茶。那些新媳妇们,要下田地了,也都悄悄地跟了四婶,施磷肥、施复合肥,喷乐果,喷敌敌畏,亦步亦趋地学着。那时候,祖父也老了,他变得有些懒散,不愿意管事了,可是看着这个媳妇,他感到满意了,在村里人面前,有时候也会不经意地自己夸上两句。
不过,有时候事情一旦好了,也容易招来是非。那天早上,我们刚起床,就听到三婶和四婶在巷子里吵架,听清楚了,原来是三婶说四婶偷了她家的丝瓜,四婶却坚持说那丝瓜是她自己家的。村里的菜园,一家家都是挨在一起的,只用篱笆墙隔开,有时候瓜苗长到了隔壁去,也是有的,因此到底四婶有偷没偷,外人一时也很难判断。三婶和四婶,却越吵越凶,又扯到了偷冬瓜、偷番薯,然后又扯到了两家的孩子打架,然后又扯回了当初分家时谁多了谁少了,整整吵了一个上午。到了下午,四婶就喝了农药。送到了镇上医院,救了两个小时,四婶都没有醒过来。四叔哭得烂泥一般,大家在一边,都悄悄地落泪。突然,三婶扑了进来,趴在了四婶的病床前,痛哭起来。过了些时候,四婶的手脚就奇迹般地动了,最终救了回来。
日子就那样过下来了,村里的光景,就是春天播种、夏天收割、秋天储粮、冬天砍柴,一年复一年,村前的流水般连绵不断。但是,到了最近几年,好像是突然之间的,村里的人家开始少了,先是某户人家,接着是几户人家,然后就一窝蜂般,越来越多的人家都搬迁到了城里,有条件的买房子,没条件的就租房子。一直到了最后,就只剩了四婶一人,还留在村里,继续耕种。
有一回,我带着小敏和孩子,回村里看四婶。沿路所见,大量田地荒弃,晒谷场里野草疯长,菜园的篱笆墙倒了一大片,一盘石磨扔在村口,村子陷入了沉寂。到了家,四婶正在熬粟米粥,我们就搬张矮凳子,在她身边坐下了。
那时候,四婶不但喜欢上了喝粟米粥,熬粟米粥也是顶呱呱的。说起来,这还是得了祖母的真传呢,过去村里人都说,祖母做的粟米粥,粟米粉化在了粥水里,粟米头也熬得爆开了,闻着已经飘香,喝进嘴里,有些糯,却不会滑腻,牙齿、舌头、口腔,都被粟米的香气所充满了。如今四婶熬的粟米粥,也就是当年祖母的那个味道了。
火烧旺了,灶膛里听得见柴草的噼啪声。四婶舀了粟米粉,加了两勺冷水,用筷子搅拌匀了,倒在锅里。又加了几把柴,火烧得更旺了,那火苗红彤彤地往上蹿,又舔到了黑漆漆的锅底。这时候,得用锅铲间歇地搅拌,不然粟米粉容易沉在锅底,烧糊了。等到水重新烧开,浮起一层白色的泡沫,四婶又拿勺子把泡沫掠去。然后,就进入了熬粟米粥的最重要阶段,保持平稳的柴火,熬上一个多小时,最后洒几汤匙“灰水”,粟米粥就算是做好了。
饭桌上,四婶邀我们喝粟米粥,我欢快地喝了,感觉又回到了过去的日子。小敏和孩子,从未喝过粟米粥的,小敏还能皱着眉头喝了一碗,孩子则干脆看一眼就丢下了。四婶看着小敏,笑说,做叶家的媳妇,是一定要学会熬粟米粥的。小敏只好笑,说还得跟四婶学。四婶却认真了,说你真想学,我就教你。小敏就不吭声了。
想想那回,四婶还真是一腔热情的。那天,从粟米粥的话题,四婶又说到了种粟米。她说,蘑菇岭是石灰岩山区,干旱少雨,粟米是最适宜山里的作物,它们耐旱,不需要过多打理,收成高。每年春耕,翻了地,撒下粟米,当春雨过后,满地都是绿苗,你要看到就知道了,那么充满了生机。然后,除草、施肥、培土,当粟米树长得跟上学的孩子高了,就开始结籽,吐出缨丝。到了七八月份,粟米树比人还高,叶子开始枯焦,那就是采摘粟米的时候了。掰开粟米棒的包叶,露出饱满的粟米粒,采摘下来,一袋一袋地拉回家。那样的时候,总有一种无法说出的满足感,那就是自己种下的呀……四婶轻轻笑着,沉浸在她自己所说的世界里。
只是,小敏对这些,到底不感兴趣,听到孩子的呼喊,也就借机走开了。
四婶有些失望,沉默很久。
那时候,对于四婶留在村里,我们也有些担心的。临走时,我还是问了四婶,有没有想过,也搬到城里去?
四婶说,我在这里住惯了。
我说,到了城里,住久了也会惯的。
四婶说,你们回去,路上小心。
我们走了出来,到了巷口,回头看,四婶还依在门口,看着我们。突然,我就记了起来,那年我从外面回家,看见那个叫春英的大女孩,也站在门口,心里阵阵哀伤。
那段时间,四叔却立足了心,要搬到城里来。
那天,四叔从广州回来找我,说他想在清远市区买一所房子,看过几个楼盘了,有一处觉得特别合适,100多平米,三房两厅,首付18万,按揭20年,每月供2500多元。四叔说得流利,看来已经看准了,志在必得了。我知道,那时候四叔承受了很大的压力,他要买房子我应该给他鼓劲,但也正因为他是我四叔,我又不由得替他多想一些。比如,四叔一直都在干体力活,如今他四十五岁,还是青壮之年,当然可以不惜力气,可是,他把自己满打满算,再干20年,一直到六十五岁,这真的说得过去吗?
突然间我发现,四叔和四婶搬来或不搬来城里,原来对于我们这些亲人,都会有所顾虑。因此,我建议他还是多看一看。可是,四叔很坚决,分别时还说,瞅个时间,他就会去交定金了。
过了两天,四婶给我来了电话,问我四叔是不是要在城里买房子了?我一听有些懵了,买房子这么大的事,四叔竟然敢不跟四婶商量了?四婶脾气又上来了,他哪来那么多的钱?有了房子就可以吃风饱吗?我没敢回话,四婶喘着气,说无论如何,你要劝住你四叔。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去找四叔,四叔就回了村里,跟四婶吵起来了。我们又赶回村里,四叔还在气头上,说这个人呀,倔得跟牛一样,说什么就算我买了,她也不会进城去住。我劝说,四婶也是怕你扛不住嘛。四叔说,我都说了,我能扛住……大不了,再借一点,也就凑够了。我心里就忐忑了,说差多少?四叔咬了牙,说一万吧。我说,真是一万?四叔叹口气,那就两万。我来气了,说一万还是两万?四叔说,就两万!我在心里翻滚着,四叔一直忍着没对我开这个口,他是想好了跟谁借了吗?要是他跟我开了口,小敏那里我该怎么说?再看四叔,他坐在门槛上,半缩着脖子,不觉又有些怜惜他。
没办法,我又去劝四婶,四婶正在房里看照片。那是一些黑白的照片,一张是五个女孩子围坐在草地上,脚掌相对成圆形;一张是在海边,风吹过一群女孩子的衣角、头发;一张是在卡拉OK厅,有女孩子正抓着麦克风唱歌。那些照片,原来都是四婶当年打工时照下的,那时候,照片里的女孩子还叫春英。我找了好一阵,到底认出了春英,她扎着个马尾,眉宇间还有些稚气,却总是笑得那么开怀……
叹息一声,四婶说了起来。
那个叫春英的女孩子,出生在一个叫山塘的小镇,她家祖上五代都是捕鱼为生,常年住在北江边的船蓬里,人们称他们为“疍家人”。邻船有个姐姐,是疍家人里最早出门打工的,每次回家来,都穿得花枝招展,操着城市里带回来的腔调。有一回,春英缠着那个姐姐,听她说了很多城里的事情,就也想到城里打工。父母觉得她小,不让她去。后来,春英就偷偷溜出了家,转了几回车,来到了东莞。刚到了城里,什么都是新鲜的,也什么都不会,被工友欺负过,被线长骂过。可是,春英是个要强的女孩子,她埋头学,哭着学,慢慢地跟上来了,后来还做了线长。
偏偏那时候,遇上了四叔。事情不过是,那天在车间,春英突然来月事了。那时候,春英每次月事都觉得特别痛,腹部里如一阵阵的电击,只恨不得在地上打滚。一直挨到了下班,她已差点晕过去,是四叔把她背到了医务室。之后,四叔又几回地为她问医买药,那个叫春英的少女,也就动了心了。
四婶又叹息一声,后来,春英变成了四婶,她离开了工厂,回到村里,还曾经给她的那些工友写过信。开始的时候,她们也回信了,只是到了后来,她们也都像当初那个春英一样,一个个地离开了城市,嫁到了各个地方,联系也就渐渐地断了。
四婶眼里,已经溢满了泪水,这些年来,我的心思都放在这里了,如今让我到城里去,我除了种庄稼,别的什么都不懂,我不会再有机会了。
我看着四婶,心里阵阵忧伤。四婶才四十五岁,可是长年的农村体力活,长年在户外暴晒,她已经过早地衰老,脸上长了褐斑,眼角、脸颊长满了皱纹,头发也已经干枯了……
我离开之后,四叔和四婶还有过怎样的谈话,我并不知道。到了后来,事情却又有了转折,四婶竟然同意了四叔,她可以进城了。只是,四婶提出了一个离奇的条件,得给她做升寿。
在蘑菇岭,很久没有人做过升寿了。所谓“升寿”,就是在老人六十岁寿辰那天,订做一副寿木(棺木),请来阴阳先生作法念经,祈愿老人福长寿长。刚开始听说这个事,大家都觉得很荒唐。可是,四婶执意要做这个升寿,说我不在这里了,那寿木会替我在,我也就放心了。
那回四婶的升寿,着实在村里掀起了一阵热闹。那天,四婶身穿红色对襟衣、藏青色长裤、枣红色布鞋,端坐在厅里,神情肃穆。村头大门口,就摆着那副寿木,那寿木刚刚新上了油漆,红得耀眼,正面是一个白底黑字的“福”,后面则是一个“寿”。阴阳先生头扎红布条,顶着个竹篮子,篮子里插着香,念了一个上午的经,把寿木安放在了村子大门口的棚架。
之后,四婶就离开了村子,到了城里,进了荣源鞋厂。
算起来,四婶这一趟进城打工,前后也就一个多月。那时候,我们几次约四婶来家里吃饭,她都推辞了,说得加班。有一天晚上九点多,我们带了家里做的椰子炖鸡汤去找四婶,在工厂外的石凳上,我们坐了下来。我们问她,在工厂做得还习惯吗?她说,还行,就是坐得久了,屁股疼。我们劝她,不要加太长的班。四婶低下了头,说身边都是年轻的男孩女孩,自己做什么都跟不上,觉得真没用,也许真是老了!
四婶线上的线长,是我们村里一个叫阿美的外嫁女。据阿美说,四婶进厂后,一直比较沉默,但刚开始那几天,工作还算正常。一个多星期后,她突然在线上呕吐了,接连地吐了几回,有一回还吐到了线上的鞋子。之后一段时间,四婶突然又跑厕所勤了,一个上午能跑十几回。阿美关心四婶,问她是不是不舒服,四婶先不说话,阿美再问,四婶终于爆发了,一边扔鞋子一边喊着,跟你说多少回了,不要喊我四婶四婶的,我有名字的,我叫春英,知道吗?阿美一时也吓蒙了,车间里好多人都站起来看。很快,这事就在厂里传开了,四婶最终被辞退了。
就是这样,四婶变得痴傻了。为了照顾四婶,四叔也辞了工,回了村里。城里下定的那套房子,因为没有办理按揭,白白地损失了两万块的定金。
据四叔说,四婶每天还是起得很早,喂鸡喂鸭,扫地打水,忙完这样忙那样。然后,就牵出家里的牛,到地里翻地,种下粟米。渐渐地,村前村后,都种下了粟米。然后,每天又走得远一些,每天都翻几块地。有时候,四叔担心四婶累着了,也劝她不要再种了,已经够多了。可是,四婶坚持要种,四叔没办法,只好由了她。于是,一直到了山边、河岸,那些原本荒芜的地,就都重新翻过,种下了粟米。等到春雨过后,一颗颗的嫩芽吐出来了,绿油油的,连成了一大片一大片。
很快,又到了清明时节,村里人回来了,要给先人拜山。这是一年中村里最热闹的时候,到处是人声,到处是鞭炮声。人们看到地里长成的粟米树,都发出了惊讶,好久没有见过这么大片的粟米地了,春风轻轻拂过,摇曳出一波波绿色的微澜,看着真让人舒服。可是,也有些议论,说这些地是没有经过同意的,怎么就都耕种了?四叔那里,少不得挨家挨户地解释,说等粟米长成了,每家都会送一些去。
那天,我们拜山回来,已经是近傍晚,发现四婶不见了。我们连忙分散去找,一边找一边喊着:
四婶、四婶——
可是,找过了每一条巷子,找过了村前村后,找过了竹林河边,还是没有找到四婶。回到村里,那边传来了另一个叫喊,是四叔的:
春英、春英——
村门口棚架上,那副寿木里探出了头来,看清楚,是四婶。四婶发现了我们,赶紧竖起了食指,喊着:
嘘,说别出声,我在玩捉迷藏呢!
(责编:王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