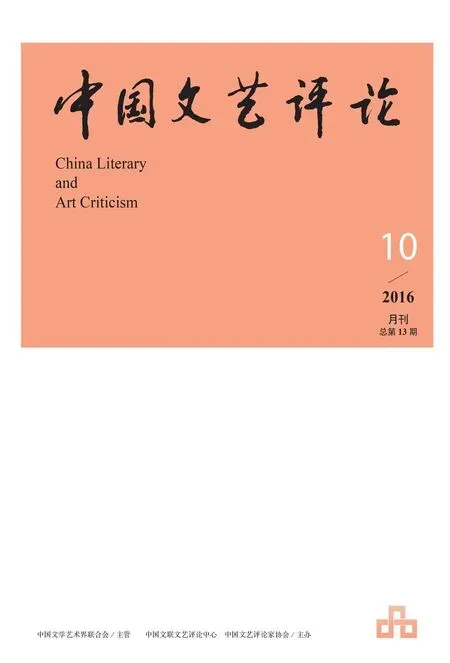大众文化对艺术表达的挑战与应战
杨光祖
大众文化对艺术表达的挑战与应战
杨光祖
一、消费主义盛行,导致艺术精神的丧失
现代化的迅速发展,工业化、都市化的日益强大,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乡村生活的终结,这是人类发展的趋势,谁都挡不住。新的消费意识形态也应运而生,“我消费故我在”的观念,不断深入人心,快乐主义、拜物教、享乐主义成为人们越来越喜欢的文化。丹尼尔·贝尔说:“过去30年里,资本主义的双重矛盾已经帮助竖立起流行时尚的庸俗统治:文化大众的人数倍增,中产阶级的享乐主义盛行,民众对色情的追求十分普遍。时尚本身的这种性质已使文化日趋粗鄙。”[1][美国]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严蓓雯译,三联书店,1? 989年版,第37页。
消费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开始广泛地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艺术家,甚至渗透到他们的骨血里去了。陆扬说:“大规模的现代工业生产技术、大规模的现代消费市场,以及大规模覆盖的现代大众传媒,构成大众文化的三个要素。”[2]陆扬:《后现代文化景观》,新星出版社,2014年,第321页。这话是对的。
多年来,一些“三俗”作品大量诞生,畅行无阻,而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却由于某种原因,比如收视率等原因,很难面世。文艺评奖、文艺节目的这种片面地唯市场论,以收视率、版税为唯一标准的不看社会效益,唯金钱马首是瞻的现象,后果非常严重。已经严重扭曲了我们的文艺评价标准,某种程度上败坏了文艺生态、文化生态。看电视,搞笑搞怪的节目垄断了黄金时段,娱乐至死、消费第一,成为了很多主创人员的座右铭。我曾经撰文说:“这种乱象最后导致的结果是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让普通百姓不知道何者为佳,何者为劣,严重影响了人们的精神生活,某种意义上导致了人们信仰缺失、灵魂空虚、心理焦虑。”[3]杨光祖:《文艺批评就是“剜烂苹果”》,《羊城晚报》2014年11月2日。
这种将严肃文艺与通俗文艺或者通俗文化使用同一评价体系的做法非常可怕。它极大地降低了文艺的高度,让文艺创作越来越走向制作,走向规模生产。如果我们的文艺评论家、评价机构都认同这种机制,那就无法创作出杰出的文艺作品。
由于过度崇拜消费主义,相信市场,于是,文学艺术创作的倾向出现了问题,低俗现象非常普遍。大家都知道,如果过度迷信市场,能吸引读者的眼球的,可以说,感官刺激成了唯一的创作目的,甚至为了吸引读者,不惜胡说八道,用耸人听闻的历史观来刺激读者等。
如今,老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平都有了大幅度的提升,相应地,精神文化消费空间大大增加,对文艺作品的诉求也日益强烈。但遗憾的是文艺工作者、文学报刊、影视机构却没有给他们足够优秀的文艺作品。我们的影视、报业、手机就技术来说,越来越高端、精准,可是,里面承载的内容却有日渐苍白、“三俗”之嫌,真正的严肃文艺,有格调有思想的作品似乎越来越少,这在某种意义上,会对老百姓的精神生活带来负面影响,甚至对构建中华民族的共有的精神家园产生不利的作用。
我们知道,作为严肃的批评家,必须要有一种批判精神,要有运用自己的理性,严肃批评的能力。对那些票房很高,市场很认可,但人文精神严重缺乏的文艺作品,必须指出它们的不足。对一些纯粹娱乐的作品,不能评价过高,要知道,它对消解人们的精神,破坏他们那点稀薄的是非观,颇有杀伤力。我们的文化产品,要既有经济效益,更应该有社会效益,要引领人们往上走,而不是往下降。通过文艺作品,让人们脚踏大地,仰望星空,而不是跟着物质欲望走,跟着感官刺激走。
众所周知,文艺作品既有商品属性,但也有艺术属性,就人类的发展而言,艺术属性更加重要。因此,我们不能将商业规则误当做艺术法则,一定要坚守艺术第一的原则。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是净化人的心灵、陶冶人的情操的伟大力量,倘若没有艺术性,一部作品还有“文艺”可言吗?[1]杨光祖:《文艺批评就是“剜烂苹果”》,《羊城晚报》2014年11月2日。
我们当然需要一些消费主义的文艺作品,满足一些市民的文化诉求。但我们还必须有一些更伟大的文艺作品,拒绝消费主义的普及化。黑格尔说,一个民族要有一些观照天空的人,否则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
二、市场至上,影响了艺术作品的质量
大众文化是为市场而规模化制作出来的,包括了广播、电影、动漫、电视、网络小说等。当下大众文化逐渐趋向标准化、程式化、肤浅化,追求虚假的感官快乐,而忘记了许多值得我们去追求的价值观念。片面追求经济效益的直接后果,就是主旋律弱化了,严肃文学艺术边缘化了,真正优秀的作家艺术家无法生存了。但是,那些低俗的文艺作品、节目,却没有边缘化,它们以“市场”“收视率”的名义走向了中心。我们知道,在欧美那些发达国家,大众娱乐作为文化产业极其发达,日本、美国的通俗文化也非常成熟,但他们的严肃文艺依然有着广大的市场,并不会因为大众文艺而受到排挤。在他们那里,精英文艺和通俗文艺是分开评价、各自发展的,《哈利·波特》永远是《哈利·波特》,没有人认为它可以取代莎士比亚。
完全为市场而创作,导致艺术作品完全商品化,艺术家的想象力受到限制,人文价值、理想、信念都抛诸脑后。于是,生产的作品基本都是满足平均数的通俗化作品,基本就只有一种属性:商品,而它们的艺术性却几乎荡然无存。
所以,我们看今日的小说,大多数似乎都不是小说,而更像是电影或电视的脚本。作家写作的初衷就是奔着电影或电视剧改编去的,至于能不能被人家相中,那倒是另外一回事了。什么时候我们的小说家如此没有自信呢?比如严歌苓的长篇小说,其结构基本上就是电影或电视剧的结构,情节置换也是影视的。这种大众文化对小说的艺术表达之影响太巨大了。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几乎毁灭了小说。
那么戏剧呢?这种舞台艺术以它的现场性,营造了一种和观众水乳交融的感觉,某种意义上给观众的冲击比影视要更大一些。但大众文化的冲击,也使得舞台成了挑战人类伦理底线的所在。茂腔戏《红高粱》,在舞台上直接展现红高粱地里的野合、脱衣、亲热等等,让观众很不好受。
真正的艺术家被认为绝不流俗于商业市场行为。布尔加科夫说,为金钱写作是可耻的。一位作家写作肯定是应该得到经济回报的,这没有什么错。但关键是你的写作必须忠实自己的内心,而不是市场,不是金钱。我曾经说,市场对一位作家的伤害,并不会比别的小。中国当代作家普遍缺乏传统文化的滋养,所以,他们的写作更容易受到市场、金钱的影响。由于作家主体的精神匮乏,于是大众文化对他们的影响就是致命的,市场至上,就成为他们唯一的创作目标。无论作品内容,还是形式,都明显受到了大众文化的影响,日益趋向低俗、媚俗、庸俗,严重破坏了中华审美精神,包括中华审美能力。如今不少大学生受此文化影响,也不愿阅读经典,沉迷于网络游戏、网络小说之中而不能自拔。汉语写作的日益衰微,让很多人不知道什么是好文字,什么是坏文字。
我近几年遇见不少的作家,包括一些知名作家,谈起鲁迅,嗤之以鼻;谈起周作人,更是不屑一顾。至于张爱玲的小说,他们完全排斥。我就说,其实这些所谓的作家,一生都没有真正走进汉字,虽然他们也写了很多东西。其实,散文是老人的文体,应该是越写越好的,所谓人书俱老。可是我们如今的散文家却大都是青年在写作,连中年写作都很难进入,更休谈人书俱老。
就文学作品来说,语言是很重要的,甚至可以说,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但我们发现当代作家的语言大都不过关,而且还不以为然。这一点不要和鲁迅等大师比,就和杨绛先生的文字比,相形逊色太多了。止庵说:“杨绛散文语言具有准确的美,朴素的美和精练的美,这统可归之于一句很古老的话:‘辞达而已矣。’对这句话我们似乎总觉得只是一个起码的要求,其实它是一个最高的要求。”“杨绛散文白描的风格,她的深沉、实在、朴素、含蓄,与此前三四十年间成为时尚的那种虚夸、浮躁、雕饰,是根本对立着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散文美学观念。”[1]止庵编:《杨绛散文选集》,百花文艺出版社,1995年,序言。
当然,能做到这一点,是与她的丰厚学养有关的。她的中西兼通的学问,开阔的视野,极高的品位,深厚的修养,当代作家几人能及?“而且文化在她这儿是‘化’得最纯熟的,丝毫不露痕迹,文化不是作为一项内容而是作为一种底蕴出现在她的文章中,文化也就是她的心态的一部分,这是她高超的地方,也是她平易的地方。”(止庵语)
《洗澡》出版后,施蛰存撰文说:“语文纯洁,本来是读者对作者,或作者自己对作品的最低要求。但在近十年来,却已成为最高要求,在一群三十岁左右的青年作家的作品中,要找一本像《洗澡》那样语文流利纯洁的作品恐怕很不容易了。”他认为杨绛“自是语文高手”。[1]施蛰存:《读杨绛〈洗澡〉》,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第355—356页。
由于一味追求市场,文艺作品的思想内涵就很单薄,甚至很庸俗、低俗。
三、多媒体、高科技的发展下,艺术出现浅俗化、碎片化、技术化现象
大众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全赖强大的传播渠道,即如今备受人关注的新媒体,尤其网络的迅猛发展,博客、微博、微信等的广泛使用,让如今人的文学阅读习惯完全改变了,刷屏成为人们,尤其青年一代的日常习惯,而读书,尤其读经典几乎被他们遗忘了。
视觉文化的发展,使得作家的写作也发生了巨大变化。短平快似乎更多地被作家认同,并成为了习惯的写作方式。长篇小说的写作更加容易了,很多作家一年一部长篇小说,以前那种半生写一部长篇小说的生产模式早就过时了。这种产量让人惊叹,但小说的质量却日益下滑,文章比较粗糙。这么快的产量,哪里有时间精细打磨?而且,这几年的长篇小说,就容量来说,却越来越短篇小说化。人物很少,故事情节也不复杂,很像市场上的注水肉和那种掺了很多水的牛奶。甚至有些小说已经来不及消化时代,完全是将微博等网络的一些东西粘贴到小说里。这种创作模式,导致小说的浅俗、碎片,也没有阅读的艺术美感,就是一个粗糙的工业产品而已。
网络小说的迅猛发展,也值得我们关注。我们阅读那些网络小说,字数似乎越来越多,但内容却很少有厚重的。这种满足网络即时阅读的写作模式,必然带来小说的通俗化,甚至情色化、暴力化,而且还受资本的限制和控制。他们没有多少自由的创作空间,等于就是一个资本的狂欢。他们的写作思路严重受网站负责人的影响。其实,也是一种浅俗、庸俗的写作,不管变化多少花样,也没有几个有文学价值的作品。
高科技带来的技术化、浅俗化,在电影领域更加普遍。美国导演卡梅伦的《泰坦尼克号》《阿凡达》,带给观众的是视觉的盛宴,就艺术性、思想性而言,是非常贫乏的。我曾说,这是技术的胜利。不过,卡梅伦的电影还是有一个过得去的故事,有一种人道主义精神在,对观众还是有一定的教化意义,而当下的一些国产商业影片除了技术的肆意铺展,根本就没有一点人道主义精神,没有张扬人性,而是宣扬暴力,歌颂暴君,历史观、价值观都是错误的。为了市场,为了票房,可以说,商业片完全抛弃了人类情怀,完全成了资本的奴隶。以前的电影和文学是亲戚关系,很多好电影都改编自文学作品。如今的电影越来越改编自电脑游戏。张宗子说:“那时候是文学电影时代,现在是电脑游戏电影和漫画电影时代。”[1]张宗子:《不存在的贝克特》,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242页。
当然,对这种现象,也有学者进行了深入研究,比如南京大学的周宪先生,他认为当代电影是叙事电影向奇观电影的转变,他说:“在当代电影中,这种叙事电影的模式开始衰落了,叙事的力量被另一种力量所取代,那就是画面的视觉奇观性。”[2]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49页。由于视觉文化的日益霸权地位,电影的叙事不那么受欢迎了,尤其3D电影的出现,更是满足了观众的感官刺激需要。其实很多人并不需要深刻,也不需要思想,他们就需要刺激,需要放松,需要娱乐。可以说,大众文化的强势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电影的发展方向。按本雅明的说法,传统的阅读方式是“韵味”的,而电影的观看是“震惊”的。丹尼尔·贝尔说:“(它)产生出一种我称之为‘距离的销蚀’的现象,其目的是为了获得即刻反应、冲撞效果、同步感和煽动性。”[3][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赵一凡、蒲隆、任晓晋译,三联书店,1989年,第31页。那么,什么是奇观呢?周宪说:“所谓奇观,就是非同一般的具有强烈视觉吸引力的影像和画面,或是借助各种高科技电影手段创造出来的奇幻影像和画面及其所产生的独特的视觉效果。”[4]周宪:《视觉文化的转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56页。当然,这种变化与大众文化的发展密不可分。从此,可以看出,社会文化思潮对艺术创作的表达影响巨大。
四、批评精神的弱化
作为一位优秀的文艺批评家,他的天职就是推介优秀的文艺作品,培育良好的文化生态,甚至引领一个时代的美学风尚。作为一位文艺批评家,他的修养和水准,就体现在他面对一件艺术品,有没有感觉,有没有一种审美直觉。他的良知,就是他能否坚持这种审美直觉,而不要被艺术之外的东西所忽悠,背弃自己的艺术感觉说话。作为一名批评家,必须追求真理,指出问题,并敢于对文艺家和文艺作品做出真诚而善意的批评。批评家必须具备一种英国学者利维斯所说的“差别意识”,不能当和事佬。
在当前大众文化一枝独秀的严峻形势下,文艺批评也日渐堕落,无法行使自己的神圣职责。作为艺术家、作家,毕竟也是人,都有一种喜欢听好话、喜欢表扬的虚荣心,你如不识趣去批评,人家就很不高兴。如果是书画、影视等,则牵涉到作品的销售问题,这就是与金钱有了关系,那么你的批评可能会影响人家的市场价格。这时候要敢于批评,就真的很难了。而且这样的场合,人家既然请你,你再要严厉批评,就真是不懂人情世故了,在别人眼里,你就是有错了。于是,红包批评、圈子批评、哥们儿批评、金钱批评,开始占据批评界的主流。这些年,知名批评家也是忙于赶场子,赚了个盆满钵满。其实,某种意义上,批评家已经成为了人家生意链上的一环。所以,批评公信力的丧失,是一个当前必须引起重视的问题。当然,对于红包批评,我个人觉得合理的报酬是应该有的,批评家参加作品研讨会,取得一定的报酬是应该的,但拿了红包,依然要凭艺术良知说话,这才是根本。批评能力或批评精神的丧失,不是因为拿了红包就可以胡说八道。
马克思在《资本论》里说,这是一个资本狂欢的时代。资本的介入给文艺创作带来很复杂的后果,有时是正面作面,有时却是一种庸俗化、低俗化的过程。作为文艺批评家,面对那些背离艺术,只为了金钱的烂俗作品,必须要举起刀子,像剜烂苹果一样,“剜”掉它。否则,精品被排挤,经典被遗忘,一个社会畅销的只是那些文化垃圾,那是多么可怕的景象,值得我们警醒。长此下去,一个社会的艺术判断力和鉴别力就会丧失,艺术感觉就会被污染。
面对这种唯市场、唯金钱的乱象,文艺批评家的责任就是引领和培育,用自己批评家的良知,坚守艺术性第一,商业性第二的标准,披沙拣金,将真正优秀的文艺作品推介出来,而对那些“烂苹果”,坚决地剜掉,否则,就会烂掉整个苹果,乃至整筐苹果。作为批评家,必须用左手指出艺术和艺术家的缺点,甚至严厉批评他们的错误走向,同时还要用右手指出优秀的文艺作品和艺术家,并告诉读者什么才是好作品,好作品的标准在哪里。当然,有人会质疑,你凭什么可以指出标准,你说的就正确吗?当然,每个人都是有局限的,批评家也不是全知全能的,他的话也不一定完全正确。但这不妨碍批评家说出自己的观点。至于它的对错,别人当然也可以反批评。
批评精神的弱化,除了审美直觉的缺乏,拜金教的影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的批评家没有自己的文艺理论。他们没有能力思考,没有思想的穿透力,因而也就没有胆量去批评。
多年来,不少中国从事文学艺术批评的人基本都依靠的是西方文艺理论。而西方的文艺理论是建立在西方的文学艺术创作基础上的,并不一定符合中国的文学艺术创作实际。这几年大家讨论很激烈的强制阐释问题,就是这种现象的一个体现。但可惜的是,我们正好缺乏优秀的批评家。我们多的是西方文艺理论的搬运工,用西方文艺理论削足适履中国文艺创作的所谓批评家。这种批评家对文本没有感觉,面对任何文本,都可以搬来西方理论强制阐释一阵,貌似很有理论,其实是伪理论、假理论。
我们在进行文艺批评时,忘记了本民族的文艺理论。我们应该挖掘本民族的文艺理论,包括对近代中国文艺评论的成就。王德威说,我们可以梳理章太炎、陈寅恪、钱钟书等人的文艺理论贡献,但这何其艰难。中国如果要诞生伟大的批评家,那一定是谙熟中国文艺批评传统的人,同时也不陌生西方的文艺理论。
当今社会,文化多元,价值多元,同时也是消费文化、通俗文化比较发达的时期,在这众声喧哗的时代,亟需批评家的批评精神、批评锋芒,和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文艺理论。
杨光祖:西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吴江涛)
——河北省优秀群众文艺作品巡演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