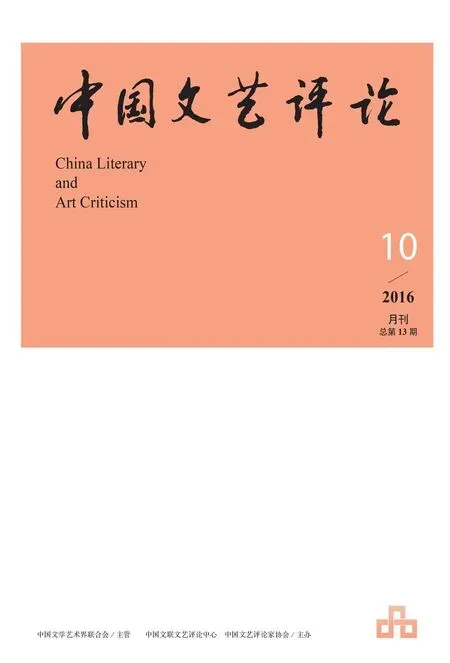倒影中的舞蹈自省——评舞剧《水月》
吴宏兰
倒影中的舞蹈自省——评舞剧《水月》
吴宏兰

云门舞集 《水月》剧照
十多年来一直在给学生们讲编舞家林怀民先生的作品鉴赏,从他早期的舞作《薪传》《白蛇传》到中后期的《行草》等。也曾有一度觉得林先生是否江郎才尽了?还是在自我复制?刻意打造所谓大师风格,迎合已经形成的粉丝观赏群体的需求?但是他自己一句“年轻时做加法,年老时做减法”足以释惑——我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年轻时气盛傲物,总觉得自己要争取更多话语权,话越讲越多,生怕自己的声音被淹没,而成熟后才懂得了倾听,学会慢讲,少说,允许留白,给他人机会。于是,理解并欣然接受了他后来风格的演变,以及某些套路的复写与趋静的舞风流变。
与2007年保利演出的《水月》一别后,再于当下重品他的舞作《水月》,更体味出林怀民后期作品的风韵。在他精心设计的“镜花水月”中恍然映出了当下舞蹈市场的乱象,高下立见,令人反思唏嘘。
一、个体言说中的宏大叙述
选题从来都是舞蹈团体创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其是否能够站稳市场乃至稳定观众群体和抓住资金链的关键。然而,是关注生命的个体言说,还是投入群体生命式的宏大叙述,则需要编导仔细斟酌。其实,个人的际遇又何尝不是一个个家国缩影?我们看到,很多编导强烈地把爱国情怀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情于作品中一舒胸臆,但显然,并不是用一个大的概念冠名就能支撑得起作品,作品也不会因为名目之大而随之宏大起来,其结果更可能是由于编导力所不逮的压迫感和观众强烈的落差感最终给作品画上句号,再无复制的经典性可言。
林怀民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热爱让我们在他由始至终的创作脉络中摸得明晰,看得真切。可是,他并未用家国大概念来冠顶,倒是时常落笔于微,或用某一个古典作品名来古为今用,文为他用,重新释读,如《寒食》《白蛇传》《薪传》《红楼梦》等;或在中国传统精神中提炼物化的名目来寄情,如《竹梦》《松烟》《行草》等;抑或在经典中寻求只言片语的珠玑来“小题大做”,如《水月》《稻禾》《流浪者之歌》等。
作品《水月》只是选择了在“镜花水月”的小点立意上展开舞蹈的文化构思,值得称道。落点虽小,其展现的个体与群体之间的生存感却绝不微小。

云门舞集 《水月》剧照
一个男子刚毅的躯体在空旷的舞台上步入——屹立——舞动,一名女子于静谧空间里纠结——挣扎——抗争……编导关照了这份孤独,在高空悬挂的镜像中给了他和她一个镜像的陪伴。然而,这样的陪伴一如李白的“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孤独被大写化了。没有参照的孤独感似乎是抽象的,而有镜像的自我陪伴的孤独感变得尤为具体。
个体的孤独感,人与人的际遇从偶然到必然,男人与女人的琢磨契合,生命的相聚分离,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终了“大地一片白茫茫真干净”的重叠感……观众不知不觉在生命渺小的嗟叹中感悟了宇宙空间和人类生命长河的宏大。
二、极简美学中的极美造境
林怀民一直被评价为舞蹈大师,实则,他更应该是视觉大师。不论是早期的《薪传》中演员们搬石吆喝的情景介入,还是他自称灵心悟道之作《流浪者之歌》里金黄色稻谷摆成的涡旋式形象的运用,亦或是《行草》里演员舞动与底幕书法的浑然一体,再到近期回归自然、回归土地的舞作《稻禾》,无一不带给观众强烈的视觉冲击。这些创意虽比不上那些耗资上亿作品般大手笔,却仍然不失震撼,且多了几分简素之美,似乎在不经意中迎合了二战以来的极简主义风潮,实实在在地为一个经费局促的舞团赢得了最大化的视觉认同。
近来流行的“极简”概念,不仅仅指的是物质形态的简、数量的减,更是观念上、欲求上的简。于是,生活中的“断舍离”,观念里的简约乐活,无不带出了“少”的美学。“云门”舞作之美即如是。
有人认为,“水月 ”一词的名目应源自佛教偈语 “镜花水月毕竟总成空”。因与佛教的参禅悟道相关,便总想在作品中看到些超凡脱俗的仙气。也有人或因李白的《夏歌》:“镜湖三百里,菡萏发荷花。五月西施采,人看隘若耶。回舟不待月,归去越王家。”企盼在作品中寻找古典的诗韵之美。而更多的老观众则在等待林怀民再一次打造令他们心醉的视觉惊喜。无论用何种心态观舞,显然大家对此次作品都有着高层次的需求和期待。而林怀民只用了地面的斑驳水印、天幕上的一块斜置大镜和底幕时有时无的方形镜幕便成功造就了虚实相间的舞美镜像,可谓是四两拨千斤。加之地面如星云轨迹的白色水纹图于末段静静注入薄薄的流水,令演员原本所在的“实”的层面又加了一层“虚”的景象。虚实如此接近,相印成趣,又互相呼应,观众的视觉无意间多了更多选择:你关注舞者之舞还是关注镜中之舞,又或是关注水影之舞,甚或是舞者与水影、镜影的对应之舞……而这种选择之多、审美之繁、虚实之变正是林怀民作为视觉大师要给观众的:虚枉的顿悟也好,美幻的韵致也罢,都在这桌平面镜像、门平面镜像和悬空的斜置镜像中交互辉映,各种心理期待、各种虚无都被一一应证。
三、西方音乐包裹下的东方灵性身体语言
当林怀民选择用巴赫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来演绎自己的作品时,曾有德国人和华人不禁质疑他的选择,因为这显然有悖于他建立云门之初提出的“中国人作曲,中国人编舞,中国人跳给中国人看”的口号。然而,随着他的文化视野渐渐扩大,文化的全球共通性认知让他逐渐打破了自己的苑囿,终于,把那首在他家“住了二十多年”的德国人(巴赫)的音乐作品用在了华人的舞蹈作品中,并且赢得了东西方的共同认知。

云门舞集 《水月》
最初林怀民开始走这种“走心”的舞蹈思路时总不禁令人联想起韩国“微量主义”的现代舞代表人物洪信子,似有效颦之嫌,可时至今日,当林怀民将内修、太极导引、现代舞等诸多元素打碎了又重塑在他的作品里时,我们看出了他的“中国风”。舞团的太极导引老师曾说他的作品里的导引是不对的,而习惯西方现代舞体系的舞者也会说他的现代是不纯粹的,而事实上,林怀民并不是要复制任何一组动作,而是要消化,要“为我所用”,于是,我们看到了林氏的特有言说。
对于音乐上的“拿来主义”,林怀民在运用上也是极讲究的,对于音乐的动作处理娴熟、老辣。音乐之于舞者的动作关系是很微妙的。好的音乐会帮助作品说话,而过于强势的音乐会让舞蹈变成陪衬,流于伴舞。那何为好的音乐?其实就是合适的音乐。推动主体氛围,带动动作情绪,与动作风格契合即为好,过犹不及。可见在舞蹈中,音乐的运用也是极讲究的,用得不好宁可不用。中国现代舞编导大家王玫老师曾强调过对于音乐的运用:“每一个变化不可以不处理。”但是,她也提出了不能被音乐牵着鼻子走的问题。过于听命于音乐容易变成形式即内容的作品,失去舞蹈的自主。看完林怀民的《水月》后,有观众曾提问,其中的动作是否是演员的即兴?林先生当场给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说:“每一个动作都是精心设计出来的,在什么时候跳什么必须都是设计好的。”事实上,我们所欣赏到的看似演员随性的舞蹈都是与音乐恰到好处地相互映衬:音乐低沉浑厚时,动作随之在趋低空间里以力道诠释;音乐于高音中清丽婉约时,动作激扬于趋高的空间;音乐婉转悱恻时,动作对应由往复感呈现,缠丝扣手自然融于舞蹈语汇之中,却又在人物的连贯情绪里不曾跳脱。难怪音乐顽童马友友在看完《水月》后亦激赞不已。事实上,他也曾有一版自己演奏的巴赫《大提琴无伴奏组曲》的舞蹈演绎,只是同样有着深厚音乐功底的舞蹈编导马克·马瑞斯并不若林怀民一般在解读音乐的同时带入了东方的传统文化,而是以西方唱诗班式的文化背景来展开自己的舞蹈表达。这一版诠释契合音乐,但并不似林氏的解读如此撩拨马友友潜在的血缘文化细胞。
四、不应忽略的细节
回味《水月》,它俘获的是不同年龄段观众的审美认同感。在一场没有中间休息的演出后,观众不仅不着急离席,更是积极参与演后谈,这恐怕与林怀民的诸多小细节相关。

云门舞集创办人林怀民
对于观演礼节的强调,林怀民先生有着自己的执念。在台湾,他是出了名的对观众“有要求”的编导,在大陆,他就曾因观众一意孤行、忽视他演出前专门叮嘱的“不可拍照”的禁令而中断演出。在这个还不够成熟的舞蹈观演市场,大家习惯性隐忍乃至纵容今天泛滥又便捷的随手拍,可是林先生则表示他“忍不了”。一副全然不怕得罪观众的傲骨,换来的是观众对“云门”演出油然而生的庄重感,仪式感,敬畏感。这种敢于和习惯性陋习挑战的勇气难道不值得更多的导演借鉴吗?林怀民觉得演出是艺术作品的呈现,是演员的倾情诠释,这样的一场艺术品的铸就过程是应当被尊重的,而不用不合时宜的方式打断它是首先的尊重。林先生将艺术作品应得到的尊重看得如此之重也唤醒了观众的尊重意识,这是非常宝贵的。正是所谓“人必自重而后人重之”。
身为“云门”的演员是幸福的,不仅在演绎作品时是被尊重的,并且他们的身体也是受到呵护的。曾有报道《水月》中缓缓注满舞台的水是被要求事先烧到40-50℃的,因为只有这样,当演员在水中起舞时,才会让水正好以接近舞者体温的温度与身体接触。这样的细节只有尊重舞者,将舞者作为艺术作品二度创作中的重要元素的编导才会如此用心处理。而云门长期坚持的太极导引的训练也是有效降低舞者身体运动伤害的手段。再侧目业内诸多演出团体,试问又有多少团体能够如此用心去呵护塑造艺术作品的肉身?又有多少演员是在一次演出后,重则终身残疾,轻则落下病根……人们常说舞蹈是“青春饭”,这其中透着多少无奈和苦涩。对于这一言论林怀民显然不买账,他曾说,他要让他的演员五十多岁照样可以跳舞,事实上,他也一直在这么做。
对于《水月》的服装恐怕有不少观众也心生疑虑,现代舞解脱身体束缚不假,不穿足尖鞋和隆重的纱裙礼服也可以理解,但并不至于要简易到用肉色吊带衫这样极简的服装,而《水月》大胆尝试。一眼望去,舞台上的男女性别似是而非,雌雄莫辨。林先生解释说这是经费使然,然而我想,这种性别的模糊处理,人物特殊性的隐藏,恰恰给予了诸多人等自我代入的机会,舞者所舞即是芸芸你我,正如《金刚经》所说:“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
当然,完璧微瑕,《水月》也有些许遗憾之处。稍稍留意的观众不难发现,“云门”的演员基本在《流浪者之歌》后便不再运用脸上的小表情来说话了,而仅仅用身体“大”语言去表达和与观众交流。对于这种交流,观众可能会因为寻找不到一贯生活、表演中的眼神碰撞而产生隔膜感,因为,当你深情望向演员时,总遇上他们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全然一副入定的风骨。遥想邓肯当年,每一个舞段都生动地从她的音频笑貌中传递着情绪性格情境的信息;玛莎·格莱姆的《悲恸》中那份绝望透过噙着泪的空洞双眼把观众一同拽入了伤痛的深渊;再回望林怀民早期的《唐山大兄》,演员的坚毅目光执着望向远方,亦有着《拓荒》般的斗志……也许,林先生希望大家沉浸在作品中时,于这份内省式的自观表达中读出他人到中年趋静的人生参悟吧!可《水月》独舞与双人舞的入世情怀下男人女人的情绪,这个还是可以有的,不是吗?这样的舍“小”就“大”,不啻在观众和演员中人为设置了一个屏障。当然,失去小表情的舞者仍在强烈的身体张力中传达了她或他的情绪和际遇,也传达了支撑他们身体语言背后的大传统。演员在自己的内观中娓娓道来,如此中式的身体在西方的音乐中流淌,运力发力顿挫得宜,我们似是用外视角看着人类生命的种种际遇可能,像看了一部纷繁的史书,如此现世又这般现实,最终有了禅道的参悟。若加之眼神和表情的传达,应该更加事半功倍吧!
林怀民曾说,他的舞团演员要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因为,舞蹈从来都不是大富大贵的行业。今天,在《水月》里我们看得出这一参悟在演员身体上的体现——演员的定力、禅性、静心,也看到了这部作品在慢琢细雕沉淀之后所得到的成功和圆满。可能当初是先生一时的灵感迸发之作,经年抛琢,现在却如镜如鉴,照出虚无,照出多少急功近利。我们当懂得,月之盈需先损之,花之丰必先藏之,时间亦是镜子,太过急进欲速则不达,若成镜花水月,毕竟总要成空。
吴宏兰:北京联合大学师范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陶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