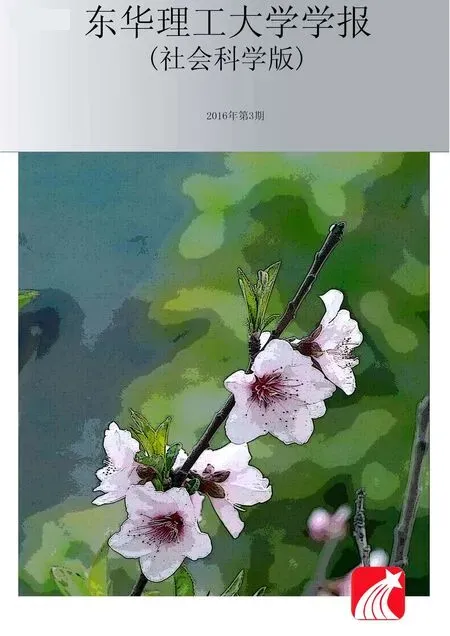《李泌传》与《邯郸记》
——管窥汤显祖的历史意识与时代感受的交互关系
董上德
(中山大学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李泌传》与《邯郸记》
——管窥汤显祖的历史意识与时代感受的交互关系
董上德
(中山大学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广东 广州 510275)
文章由《邯郸记题词》而注意到李泌及《李泌传》,进而得知汤显祖刻意建构出《李泌传》与《枕中记》二者的“相关性”;但问题并非止于此,原来,《李泌传》与《枕中记》存在“错位”关系,这些“错位”却被汤显祖借用了,让他在改编《枕中记》时找到了创作新的故事情节的“抓手”,以此寄寓他对历史、对人生的独特思考。文章认为,汤显祖在万历二十九年撰成《邯郸记》传奇,此剧成为“临川四梦”的“收官”之作,如要研讨其意义,不能局限在“小说—传奇”这种文体转换模式中去寻找,应从汤显祖的历史意识与时代感受的交互关系来看《邯郸记》的特殊意义。
汤显祖;李泌;历史意识;时代感受;邯郸记
董上德.《李泌传》与《邯郸记》——管窥汤显祖的历史意识与时代感受的交互关系[J] .东华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35(3):225-230.
Dong Shang-de.The biography of Li Mi in Tang Dynasty and Handanji written by Tang Xianzu——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Tang Xianzu’s sense of history and feel about his time[J] .Journal of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2016,35(3):225-230.
汤显祖的《邯郸记》(本文引用《邯郸记》原文,均据2016年中华书局出版,朱萍整理的《临川四梦》,随文注明剧本出数,不另出注)涉及唐代历史,他对唐代史料与唐代人物有过一番研究。从其《邯郸记题词》可以知道,汤显祖熟悉唐代著名人物李泌的事迹,故而在题词中扼要叙述了李泌的故事,且与《枕中记》相比附,甚至说:“《枕中》所记,殆(李)泌自谓乎?”[1] 448
其实,汤显祖对此一说法并不自信,因为他知道“(《枕中记》)世传李邺侯泌作,不可知。”其“殆泌自谓”云云,假设之辞而已。可为什么他在题词中特别把李泌的故事凸显出来呢?《李泌传》与《邯郸记》有何内在关系呢?如有关系,我们又如何解读呢?
本文试图选取这一角度,重新研读《邯郸记》,以求对汤显祖的思想与心态有进一步的认识。
1 《李泌传》与《枕中记》的“相关性”
汤显祖熟读《李泌传》,他对李泌一生的主要事迹概述如下:“观察郏、虢,凿山开道至三门集,以便饷漕。又数经理吐蕃西事。元载疾其宠,天子不能庇之,为匿泌于魏少游所。载诛,召泌。”这都是李泌诸多经历中的“大关目”;而且,可以肯定的是,汤显祖读的是《新唐书·李泌传》,他在简述李泌事迹后写道:“唐人高泌于鲁连、范蠡”,此语从《新唐书》中出,原文是:“柳玭称:两京复,泌谋居多,其功乃大于鲁连、范蠡云。”[2] 4638查《旧唐书·李泌传》(第130卷),并无这一评语。汤显祖是否读过《旧唐书》,不得而知,他对《新唐书·李泌传》倒是烂熟于心的。
汤显祖发现,若依照他对李泌生平事迹“简约化”的叙述来加以比附,则李泌的故事与《枕中记》里卢生的故事有着一定程度的“相关性”,这也是他所说的“殆泌自谓”的缘由。为论述方便,且引用《枕中记》的一段文字:

两相比照,可以看出,卢生与李泌的人生经历有某种“重合度”,要而言之,如下四个要素是可以对应的:一是督办过关涉政治与民生的重大工程;二是曾经在边关要塞破敌立功;三是一度遭到权奸的妒忌与陷害;四是历经政坛风波而重新得到重用。
如此相似,难怪汤显祖从卢生的故事联想到李泌,则二者的“相关性”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从历史真实来看,我们找不到卢生与李泌的这种“相关性”的确切依据,汤显祖曾说“(《枕中记》)世传李邺侯泌作,不可知”,既然是“不可知”,则“世传李邺侯泌作”云云只是“传说”而已,不能当真。可问题是,为什么汤显祖在《邯郸记题词》里那么郑重地将“李泌”牵扯进来呢?若只是作简单比附,这样的比附意义不大;宦海风波、官场恶斗,诸如此类,每每常见,历朝历代身在朝廷的张三、李四的不少故事也可以跟卢生相比附,何必将目光单单落在李泌身上呢?我们除了看到卢生与李泌的“相关性”之外,还应进一步思考汤显祖关注李泌的动机是什么。
2 《李泌传》与《枕中记》的“错位”关系
事实上,《李泌传》的内容并不如《邯郸记题词》里所叙述的那么简单,它比《枕中记》要复杂得多。笔者认为,卢生与李泌的“相关性”是汤显祖自己借助《邯郸记题词》而“建构”出来的,但醉翁之意不在酒,他在构思《邯郸记》时,似乎另有考虑,在创作上别有谋划,而不是仅仅着眼于对《枕中记》的改编。
这就要考察历史上的李泌其人,看看他的经历中有何奥妙能够让汤显祖对他另眼相看。可以说,《李泌传》与《枕中记》存在着某种“错位”关系,并非事事“重叠”,样样“对应”;其间的“错位”反而是我们“意会”《邯郸记》深层意蕴的一把钥匙。
李泌历经唐玄宗、唐肃宗、唐代宗、唐德宗四朝,汤显祖历经嘉靖、隆庆、万历三朝。“李泌(所处)的时代”与“汤显祖(所处)的时代”的相关性,倒是一个诱人的题目。
就李泌一生而言,有一件事做得光明磊落却付出了代价,这就是他不依附一度权倾天下的元载。《新唐书·李泌传》称“元载恶(泌)不附己”[2] 4634,元载是知道李泌的才华的,也希望李泌能够依附自己,可李泌眼光独到,他早就看出元载靠把持朝政的李辅国而出人头地,李辅国与元载均喜欢弄权,怀抱野心。而元载其人更为卑鄙,他与李辅国有亲戚关系,又得到李辅国的多次提拔,可是,却参与了谋害李辅国的行动,其内心之阴险狠毒可见一斑。此外,元载为了及时得到皇帝的“密旨”,以重金买通太监董秀,因而“帝有所属,必先知之,探微揣端,无不谐契”[2] 4712,其势力越来越大,以至于独揽大权,排斥异己,只是延揽、重用依附自己的人,在当时的政坛上做到了“非党与不复接”的地步。而李泌心性耿直,不与元载同流合污,结果是得罪了元载,其代价是被元载找了一个借口调离朝廷,出任江西观察使魏少游的僚佐,直到元载被诛,皇帝才把李泌召还。
《枕中记》中的卢生,只是“为时宰所忌”,并非因为不依附权贵而被驱遣出朝廷。被人妒忌与不依附他人,是两回事,这也是《李泌传》与《枕中记》发生“错位”的显著地方。可是,在《邯郸记》里,卢生一而再、再而三地被宇文融找到“题目”去作践自己,原因十分明白,是因为卢生不依附宇文融(《枕中记》并无提及宇文融其人,这是汤显祖故意添加的),剧中宇文融有一段宾白说道:
自家宇文融,当朝首相。数年前,状元卢生不肯拜我门下,心常恨之。寻了一个开河的题目处置他,他倒奏了功,开河三百里;俺只得又寻个西番征战的题目处置他,他又奏了功,开边一千里,圣上封为定西侯,加太子太保,兼兵部尚书,还朝同平章军国事。到如今再没有第三个题目了。沉吟数日,潜遣腹心之人,访辑他阴事,说他贿赂番将,佯输卖阵,虚作军功;到得天山地方,雁足之上,开了番将私书,自言自语,即刻收兵,不行追赶。(笑介)此非通番卖国之明验乎?把这一个题目下落他,再动不得手了。我已草下奏稿在此。(第十九出)
汤显祖将卢生的三次“宦海风波”均纳入“状元卢生不肯拜我门下,心常恨之”的缘由之下,这是非常值得注意的,他以这样的系列情节来展示一个朝廷官员在不依附权贵的情形之下会出现什么样的“后果”,这不是《枕中记》原有的题旨,倒是《李泌传》启发了他,他将李泌特定的经历“移植”到《邯郸记》里卢生的故事之中了。
据《新唐书·宇文融传》记载,此人确如汤显祖笔下所写的那样,是一个势利小人。张九龄对他的评语是“辩给多诈”[2] 4558,并力劝另一政治人物张说要对宇文融严加防范。而张说与宇文融多次交锋,长期交恶;宇文融权势更大,与他人联手终于罢了张说的“宰相”职务,可以说十分霸道。不过,宇文融又是一个能人,《新唐书》本传说:“融明辩,长于吏治”,深得唐玄宗的信任,尤其是“玄宗以融为覆田劝农使”,政绩突出,因而“擢兵部员外郎,兼侍御史”,是“开元时代”的风云人物。有趣的是,既然汤显祖注意到李泌的奇特人生,又认为李泌与卢生有“相似”的遭遇,那么,在《邯郸记》中,为何没有让与李泌有“交集”的元载露面,反而让与李泌似无“交集”的宇文融登场呢?依史书的描述,元载基本上是一个否定性的人物,而宇文融不是,他既有“坏”的一面,也有精明干练的一面。汤显祖以他做为《邯郸记》里的反面人物,做为卢生的对立面,他决定着卢生在人生重要关口的命运,显然是有意为之,而《邯郸记》的字里行间又隐藏着汤显祖对宇文融这类人物的憎恶与痛恨,更是值得深思。
我们知道,汤显祖本人就有不依附权贵的经历。《邯郸记》里的卢生不依附宇文融,导致接二连三的“厄运”;而在“万历时代”,尤其是在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汤显祖可说是“运气极坏”,原因是他不愿意依附权贵。邹迪光《临川汤先生传》记载:
公虽一孝廉乎,而名蔽天壤,海内人以得见汤义仍为幸。丁丑会试,江陵公(张居正)属其私人啖以巍甲而不应。庚辰,江陵子懋修与其乡之人王篆来结纳,复啖以巍甲而亦不应。曰:“吾不敢从处女子失身也。”公虽一老孝廉乎,而名益鹊起,海内之人益以得望见汤先生为幸。至癸未举进士,而江陵物故矣[4] 1511。
丁丑,即万历五年;庚辰,万历八年;癸未,万历十一年。换言之,直到万历十一年即张居正刚刚“物故”之后,汤显祖才有机会“举进士”。而万历元年至万历十年,正是张居正权倾天下的“江陵时代”。张居正以精明干练著称,是一位很有政绩的权贵,在其生前,得到神宗皇帝的信任与倚重。就这一点而言,张居正与宇文融并非没有可比性。汤显祖没有拜在张居正的门下,与卢生没有拜在宇文融的门下,也并非没有可比性。由李泌的不依附元载,转化为《邯郸记》的卢生不依附宇文融,再联系汤显祖在长达十年的“江陵时代”而不依附张居正,并表达过十分自觉的意识:“假令予以依附起,不以依附败乎?”(邹光迪《临川汤先生传》)如果我们借用法官判案时可以使用的“自由心证”,能说汤显祖的《邯郸记》所描述的宇文融跟卢生的关系,与汤显祖本人的人生经历没有一定的关联吗?在此,我们是否可以“意会”出汤显祖改编《枕中记》时不易被人发现的用心呢?
汤显祖借用《李泌传》与《枕中记》的“错位”关系来构思《邯郸记》,还有一个实例,就是《邯郸记》里的萧嵩形象。在剧中,萧嵩无比机智,与宇文融周旋,如第十九出,宇文融诬陷卢生“通番卖国”,写了一份奏章,落款时加署萧嵩之名,要萧嵩在其奏章上“押花字”;萧嵩知道这是无中生有的陷害之举,不愿意署名,宇文融以“通同卖国”的罪名胁迫萧嵩就范,萧嵩无奈,想出一个“妙招”:“下官表字一忠,平时奏本花押,草作‘一忠’二字,今日使些智术,于花押上‘一’字之下,加他两点,做个‘不忠’二字,向后可以相机而行。”在第二十四出,萧嵩为卢生辩冤,宇文融在皇帝面前说萧嵩曾在奏章上“花押”,萧嵩辩称:“此非臣之真正花押”,并说:“臣嵩表字一忠,平日奏事,花押草作‘一忠’二字。及构陷卢生事情,宇文融预先造下连名奏本,协同臣进。臣出无奈,押此一花,暗于‘一’字之下,‘忠’字之上,加了两点,是个‘不忠’二字。见得宇文此奏,大为不忠,非臣本意。”皇帝这才知晓事件本末,召还卢生,惩办宇文融。这是萧嵩“用智”的故事。可是,查史书,开元时代的萧嵩,其本传见《新唐书》第101卷,他于“开元初,擢中书舍人”;“(开元)十四年,以兵部尚书领朔方节度使”;开元十七年,接任张说被罢官后空出来的宰相职位[2] 3953。
本传没有提及他“用智”的故事,却说他在政坛上极为谨慎,而谨慎之人一般不会冒险,不会像《邯郸记》里的萧嵩那样竟然在奏章上“做手脚”。可是,我们读《李泌传》,可以看到,李泌一生机智,是一位擅于“用智”的高手,故此,史书说:“泌出入中禁,事四君,数为权倖所疾,常以智免。”[2] 4638可以想见,“事四君”已经够不容易了,还要对付这前后“四君”身边为数众多的小人,该有多大的智慧才能够身历一次又一次的“惊涛骇浪”而不倒。汤显祖受到《李泌传》的启发,将李泌的机智经历“嫁接”到萧嵩身上了。
可见,汤显祖在创作《邯郸记》时,只是借取《枕中记》的情节框架(《枕中记》的叙事形态是“粗陈梗概”,为汤显祖留下很大的创作空间),剧本的不少内容为《枕中记》所没有,相较而言,得自《李泌传》的启发而转化为剧本情节者,更值得关注和研究。
我们由《邯郸记题词》而注意到李泌及《李泌传》,进而得知汤显祖刻意建构出《李泌传》与《枕中记》的“相关性”,再进而发现《李泌传》与《枕中记》的“错位”关系,这些“错位”却被汤显祖借用了,让他在改编《枕中记》时找到了“抓手”,以此寄寓汤显祖本人对历史、对人生的独特思考。其实,汤显祖撰成《邯郸记》传奇,此剧成为“临川四梦”的“收官”之作,如要研讨其意义,不能局限在“小说—传奇”这种文体转换模式中去寻找,更应从汤显祖的历史意识与时代感受的交互关系来看《邯郸记》的特殊意义。
3 从《李泌传》到《邯郸记》:管窥汤显祖的历史意识与时代感受的交互关系
汤显祖虽以诗人、剧作家闻名于世,其实,他也是一位对历史研究很感兴趣的学者。他曾经在给吕玉绳的信里说自己“有意嘉、隆事”,即很想研究嘉靖、隆庆间的人物与历史,没想到此种兴趣被一位和尚泼了一瓢冷水,“忽一奇僧唾弟曰:严、徐、高、张,陈死人也,以笔缀之,如以帚聚尘”,换言之,严嵩、徐阶、高拱、张居正诸人,都是“垃圾”,研究他们干什么?汤显祖听到这番言辞后,“弟感其言,不复厝意”。可是,他研究历史的兴趣并没有减退,转而研治宋史:“赵宋事,芜不可理;近芟之,《纪》《传》而已,《志》无可如何也。”从汤显祖的历史研究的成绩看,他是很有“史识”的人,连清代大史学家全祖望也对他的见识十分肯定,推崇备至,这可是史学“圈内”的意见,不能等闲视之。*徐朔方笺校《汤显祖诗文集》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32页。徐朔方先生在笺释文字中指出,信中提及的和尚“当是僧真可,字达观”;并引全祖望《答临川先生问汤氏宋史帖子》一文,认定汤显祖在研治《宋史》方面颇有成绩,如在体例上“合《道学》于《儒林》”,即取消了《道学传》,将相关人物的传记并入《儒林传》,全祖望称汤显祖的见地乃是“百世不易之论”,徐先生亦说“汤显祖长于史学,此为一例。”又,俞越为清陆心源《宋史翼》作序,称陆氏编撰此书有一个特点:“其有《儒林传》而无《道学传》,自有微意。”汤显祖的做法早于陆心源,这也是值得注意的。参见陆氏《宋史翼》(吴伯雄点校本),浙江古籍出版社,2016年,第2页。汤显祖关注嘉靖、隆庆历史,是意识到于他而言的这一段“近现代史”在整个明代历史进程中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但是,他的研究“对象”不一定是他所喜欢的人物,有些人甚至是他所十分鄙视且痛恨的,故此,那位和尚泼他冷水,他就“不复厝意”,也是“事出有因”的。不过,其实也不尽然,他只是没有像研究宋史那样“正儿八经”地做而已,他对于嘉靖、隆庆以至于万历的历史,没有忘情,时时关注,并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表达他的思考与倾向。如《邯郸记》的创作,似乎可作如是观。
这就涉及到汤显祖的历史意识与时代感受的交互关系问题。
已经有学者注意到汤显祖的时代感受。吴梅先生在研读《邯郸记》时指出:“记中备述人世险诈之情,是明季宦途习气,足以考万历年间仕宦况味。勿粗鲁读过。”[4] 1574黄芝冈先生注意到汤显祖为《枕中记》写的评语,而推测其写作《邯郸记》的意图:“汤校点《虞初志》,在《枕中记》的评语里说:‘举世方熟邯郸一梦,予故演付伶人以歌舞之。’他说明自己写《邯郸记》是为了讽刺当时的显贵。汤写《南柯记》虽同是写显贵的一生,但其主旨却在写佛家思想,因此不曾大量反映当时显贵们的施为,……《邯郸记》的悲欢离合,无头无绪,虽真像一场大梦,但实按这场梦境的所有情节,却全是当时显贵们的现形丑剧……《南柯记》和《邯郸记》虽同具佛、道的逃世思想,但对《邯郸记》究竟应当另作估价。因为它反映了当时显贵们演出的种种活剧,具有充足的现实性。”[5] 185笔者认为,上述意见,均很有见地,且相当精辟。读《南柯记》与读《邯郸记》,我们会有不同的感受,尽管两部作品似乎很相近,其实,绝对不是简单的“同题”重复,上引黄芝冈先生的意见,值得格外重视。
可是,学者们忽略了或者说尚未深究一个事实,即汤显祖在《邯郸记题词》里将李泌与卢生来比附,这到底有何用意?不少学者注意到《邯郸记》带有汤显祖的“时代感受”,却没有关注到汤显祖的时代感受与其历史意识的“交互”关系。
从《李泌传》到《邯郸记》,其间隐藏着一个话题:汤显祖相当关注“李泌的时代”,也就是唐代的开元至贞元时期。《邯郸记》里的宇文融、萧嵩、裴光庭等,都是活跃于上述时期的政治家;而李泌,更是著名的“四朝元老”。如果说,《邯郸记》的故事蓝本《枕中记》展示“富贵荣华”的极致,那么,本来最为“著名”又可以“比附”的人物非郭子仪莫属,为何汤显祖不关注郭子仪而青眼于李泌呢?原因可能是,李泌与“李泌的时代”更有政治意味,而郭子仪尽管与李泌大致是同时期的人物,但其身上的政治意味不如李泌那么特殊和复杂,后者毕竟在当时的历史舞台上主要是一位战将,而非政坛上的权臣。
其实,在汤显祖看来,李泌这个人物更容易触动他的历史意识与时代感受,并引发这二者的交互关系。
汤显祖先后生活在嘉靖、隆庆和万历年间,我们姑且称之为“汤显祖(所处)的时代”,它与“李泌(所处)的时代”在几个要点上存在可以类比的关系:其一,权臣把持朝政,且十分强势,在历史上都具有“标签”意义;其二,曾经出现“太子废立”的“难题”;其三,朝廷十分重视“边事”。如果只挑出其中的某一点来观察和比对,在古代中国,不少时期都会有这样或那样同类的“要点”,单一的比对意义不大;可是,若将这三点同时“打包”来比对,那么,“李泌的时代”与“汤显祖的时代”的“同构性”就显露出来了。在“李泌的时代”,像李辅国、元载、宇文融等,都是权臣,臭名昭著又能量极大的李林甫、杨国忠等更是以弄权留下千古骂名,是具有“标签性”的人物;而在“汤显祖的时代”,严嵩(汤显祖出生于嘉靖二十九年,严嵩于嘉靖四十五年尚然在世)、徐阶、高拱、张居正、申时行等,同样是叱咤风云的权臣,这些人物或足以流芳百世,或将会遗臭万年,他们在“强势”二字上可与李林甫、杨国忠等相比,也是具有“标签性”的人物。在“李泌的时代”,有的皇帝如唐玄宗,热衷“开边”,故而“边事”很多,人所熟知;*唐玄宗热衷“边功”,参见范文澜著《中国通史》第三册,人民出版社,1978年,第155-163页。在“汤显祖的时代”,有的皇帝如神宗,也是将很大的心力投入到“边事”之中,故有“万历三大征”的政绩。*关于“万历三大征”,参见樊树志著《万历传》,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227-255页。为节省篇幅,且不复多说,我们不妨看看“太子废立”这个共同的“难题”。
对于汤显祖而言,太子废立的话题或许是他关注李泌的不大不小的“触媒”之一。李泌在唐德宗的太子的废立问题上曾经扮演过不可忽视的角色。据《新唐书·李泌传》记载,德宗不喜欢已立的东宫,而赏识另一个“儿子”舒王,“(李)泌揣帝有废立意”,力图劝阻德宗不要改立;他知道舒王不是德宗亲生的,为德宗之弟所出,这个要紧的“秘密”还是德宗私下告诉他的,李泌说:“陛下有一子而疑之,乃欲立弟之子,臣不敢以古事争。且十宅诸叔,陛下奉之若何?”德宗听后很不高兴,说:“卿违朕意,不顾家族耶?”李泌据理力争:“臣衰老,位宰相,以谏而诛,分也;使太子废,他日陛下悔曰‘我惟一子杀之,泌不吾谏,吾亦杀尔子’,则臣绝嗣矣。”说毕,痛哭流涕,颇动感情。可德宗不是那么容易说服的,李泌苦口婆心,“争执数十,意益坚;帝寤,太子乃得安。”[2] 4636对于一个王朝而言,王储问题关系重大,不能不慎重,更不可儿戏。“立嫡立长”,是宗法制度的规矩。德宗曾经动念想不守这一规矩,李泌煞费苦心加以阻止。同样的情形,也出现在万历时期。在立东宫的问题上,神宗的态度是十分暧昧的。据《明通鉴》记载,在张居正去世后,申时行等于万历十四年提议神宗册立东宫,“上以皇长子幼弱,稍俟之。时(郑)贵妃有殊宠,甫生子即进封;而恭妃王氏,生皇长子已五岁,不益封。中外藉藉,疑上将立爱。”[2] 2733请注意“中外藉藉”四字,说明“立东宫”自万历十四年起就已经成为一个朝里朝外的“公共话题”,不再是朝中的“秘密事情”。而汤显祖本人,于万历十二年,不接受内阁大臣申时行、张四维的延揽,出为南京太常寺博士,正七品,不管如何,已经进入了仕途,他对此后的“立东宫”一事,不会没有耳闻。我们不一定要说汤显祖会如何关注这件事,可就一个人的“时代感受”而言,这肯定也是构成其“时代感受”的不大不小的因素。况且,“立东宫”一事,从万历十四年起一直延宕了好多年,乃至于到万历二十一年,依然没有明确的决定,神宗只是提出“三王并封”;而圣意一出,舆论哗然,不少大臣纷纷上疏,表示反对,要求皇帝赶紧“立嫡”。当时,身为“元辅”的王锡爵,揣摩上意,有意附和神宗;而庶吉士李腾芳写信给王锡爵,提醒他如果“三王并封”,册立太子的大典会变得遥遥无期,对国家不利,对王锡爵及其子孙也不利。王锡爵回应李腾芳说:这是“权宜之计”,并以古人张良、李泌为例,说他们是“皆以权胜”的典范,自己也要学习学习[7] 4692-4693。请注意,王锡爵竟然也留心李泌!将李泌与张良相提并论,可知在王锡爵的心目中,李泌也像张良一样,是一位以“智谋”闻名的人物。有趣的是,唐代的李泌分别出现在王锡爵与汤显祖的视野之中,他们对李泌的观察角度可能不大一样,但李泌作为唐代政治人物,其在明代政坛上的“知名度”绝对不低,这也是我们观察万历时代的一个“细节”。
从万历十四年申时行提议册立东宫起,直到万历二十九年十月,东宫才正式确定下来,前后耗时长达十五年;而在此“历史语境”之下,汤显祖先后做了两件与朝政有关的事情,一件事情轰动政坛,即万历十九年上奏《论辅臣科臣疏》,此事还惹得神宗大怒,导致汤显祖被贬往广东徐闻;另一件事情惊动剧坛,即万历二十九年八月写完了影射明代朝政的传奇《邯郸记》,而《邯郸记》写成之后两个月,明神宗的皇长子才被册立为“皇太子”。提及这一事实,我们无意说,《邯郸记》的写作与太子废立问题有多大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或许没有关系,可是,汤显祖在“太子废立”问题尚未解决的“历史语境”里写出了《邯郸记》,也是事实。他在此语境之下想到了唐代的李泌,身为“元辅”的王锡爵曾几何时也想起了李泌,而李泌与德宗时期的太子废立问题又有关联,大家可能对这个困扰明代政坛十多年的难题有共同的关注,恐怕也不一定是“巧合”。
鉴于太子废立、边事频发、权臣当政这三点在“李泌的时代”与“汤显祖的时代”具有“同构性”,汤显祖的历史意识与时代感受才会产生“交互”关系。说“交互”关系,是想强调,它是超越“对应关系”的,即上述两个“时代”既有某种程度的“同构性”,也有明显的“历史错位”,而“同构性”与“历史错位”均为汤显祖创作《邯郸记》提供“灵感”,并产生“交互”作用。比如,剧中的卢生与李泌的经历不无“重合”之处,也有明显的不同:卢生在考试时行贿,且在晚年还热衷于“采战”,诸如此类,都是李泌的故事里不具备的。*龚重谟先生认为“(《邯郸记》中)宇文融便是明代张居正、申时行等一班权臣化身……卢生还朝任宰相穷奢极欲,是张居正等一班权臣荒淫无耻生活的写照。”可备一说。龚重谟著《汤显祖大传》,北京燕山出版社,2014年,第196-197页。然而,不管如何,唐代的历史在德宗时期已经全面地走向衰败,明代的历史在神宗时期也全面地走向衰败,这是不争的历史事实。汤显祖的历史意识,或许就建基于此。
我们不必对汤显祖与李泌之间的“因缘”做出过度解读,这两个人物很不对等。李泌作为“古人”,受到汤显祖的注意,这对于博览古今的汤显祖而言无非也是“平常事”而已。不过,经过如上分析,“李泌的时代”与“汤显祖的时代”存在着某种历史上的“可比性”,则是构成了一种“历史的张力”。我们是否也可以借助“汤显祖与李泌”这个话题,借助“李泌的时代”与“汤显祖的时代”的某些对应关系和非对应关系,来认知《邯郸记》里丰富而复杂的内涵并进一步认知汤显祖的内心世界呢?
《李泌传》与《邯郸记》,是汤显祖有意为我们“预设”的话题。在与汤显祖“对话”的时候,是需要了解这个话题的,否则,我们会在汤显祖的“面前”显得“失语”。这是笔者撰写拙稿的动因,也是一种尝试。敬请方家赐教。
[1] 汤显祖.临川四梦[M] .朱萍,整理.北京:中华书局,2016.
[2] 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 .北京:中华书局,1987.
[3] 徐士年.唐代小说选[M] .郑州:中州书画社,1982.
[4] 汤显祖诗文集[M] .徐朔方,笺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5] 黄芝冈.汤显祖编年评传[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4.
[6] 夏燮.明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2013.
[7] 谈迁.国榷[M] .北京:中华书局,1988.The Biography of Li Mi in Tang Dynasty and Handanji Written by Tang Xianzu——The Interactive Relation between Tang Xianzu’ Sense of History and Feel about His Time
DONG Shang-de
(InstituteofChineseIntangibleCulturalHeritage,SunYat-senUniversity,Guangzhou510275,China)
Tang Xianzu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Li Mi, a famous statesman in Tang Dynasty, in his foreword of Han Dan Ji.In his opinion, the story of the hero of Handanji and the story of Li Mi are somewhat similar.This paper is written to discuss why Tang Xianzu paid close attention to Li Mi as well as to reveal the relations between Tang’s outlook of history and his life experiences.
Tang Xianzu; Li Mi; the outlook of history; life experiences; Handanji
2016-08-10
董上德(1959—),男,广东顺德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戏曲史、小说史研究。
J805
A
1674-3512(2016)03-0225-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