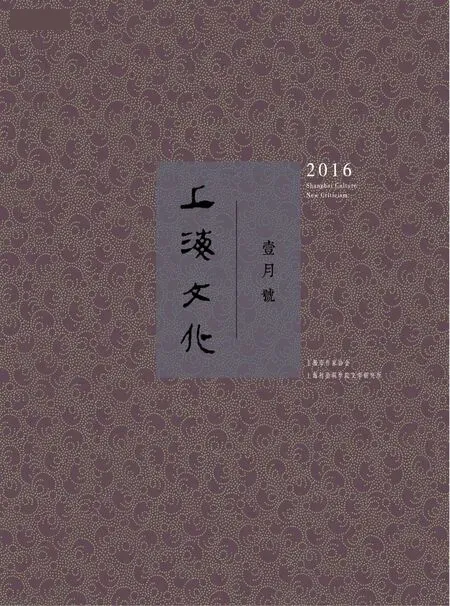我不知道谁比柏拉图说得更好
吴雅凌 黄德海
我不知道谁比柏拉图说得更好
吴雅凌黄德海
黄德海:从我们七八年前认识开始,陆续看到你翻译和写作的《俄耳甫斯教辑语》、《俄耳甫斯教祷歌》,赫西俄德《神谱笺释》、《劳作与时日笺释》,卢梭《文学与道德杂篇》、《致博蒙书》等,觉得你的主要精力在西方古典学问。但很多次交谈让我意识到,你在倾心古典学问之前,应该有一段很长的精神成长期,这个时期更多是关注文学的。
吴雅凌:你说得很对。我在学校里一直学的是文学,兴趣也是文学的。在法国念书受的是所谓“比较文学”的方法训练,认知的视野停留在20世纪,往前至远到16世纪。后来因机缘巧合开始接触一些西方文明源头的东西,始知学问尚有深浅。不过,即便在努力尝试亲近你提到的这些经典作品的过程中,我想我也没有跨出文学的界限。
黄德海:从你自己能深入阅读法语作品开始,在这个语言打开的世界中,看到了哪些异质的精神性因素?这些因素哪些是在单纯的汉语中是绝难看到的?它们在你的精神构成中起了怎样的作用?
吴雅凌:我是在心智迈向成熟的年龄接触到一种新的语言,一种迥异的思考和生活方式。作为一个年少无知的外乡人,我想我首先收获的是美的敏感。那种颠覆是根本性的。在很长时间里,我看欧洲就如一个不懂画的人赞叹一幅画,不知深浅,却不影响为之着迷。在不自知中模仿它的美的各种表象,从文字绘画电影戏剧诸种形式的叙事细节中的感动,到日常公共生活行为规范的切身教训,从语言的呼吸顿挫、眉目传神,到一顿阳光下的露天午餐的面包和酒。我身在其中而不知这美的深浅,包括在索邦楼里听过的那些课,遇见的那些人,借过读过的那些书。我在离开以后几乎又花了同样多的时间才慢慢理解这一切。按照柏拉图的说法,随着时光,我们慢慢为自己争取到年长的有情人的资格,慢慢看清当年那个“心爱的少年”的模样。
:如果我的理解没错,我觉得你所说的文学,更像是带有原初意味的“秘索思”(mythos)——“内容是虚构的,展开的氛围是假设的,表述的方式是诗意的,指对的接收‘机制’是人的想象和宗教热情,而非分析、判断和高精度的抽象”,其表现载体则是诗、神话、寓言、故事等等。你翻译和写作的大宗,我觉得都跟这个秘索思有关,除了俄尔甫斯教祷歌、辑语以及赫西俄德的作品,你翻译的《赫西俄德:神话之艺》、《柏拉图与神话之镜:从黄金时代到大西岛》,甚至西蒙娜·薇依的《柏拉图对话中的神》,以及你刚刚编定的新书《黑暗中的女人——作为古典肃剧英雄的女人类型》,都跟这个秘索思有关,或者更确切地说,跟神话有关。
吴雅凌:在西文词源里,文学衍生自文字,比如法语中Littérature(文学)与Lettre(文字)同根。文学一开始指与文字相关的认知的整体,不妨说,文学相当于各种文明里的经典,18世纪以来,文学则专指与审美有关的书写、认知乃至言行,逐渐也就形成现代学科划分里的所谓狭义的文学。我与文学的相遇恰好是从狭义向广义、从今向古的过程。这个初遇如刚才所说与美的敏感有关。此外,我们大多数人在今天一开始接触文学时没有机会获得某种广义的古典的视野。我想这不是个人的事,而是一个时代问题,否则也不值得我们在这里讨论。
在文学的路上,我很有幸在某个时刻遇见神话。我从翻译整理神话开始,慢慢以神话作为某种思考的参照点,尝试理解古希腊诗歌(包括最早的神话诗和稍后的悲剧)、柏拉图对话乃至后世的作者作品。我对西方文明史上不同时代的人们如何看待神话总是充满兴趣。这就如一个以文学为名的认知过程,柏拉图在《会饮》中提到六个“美的阶梯”:一个美的身体、两个美的身体、所有美的身体、美的生活方式、各种美的知识、美本身的知识。打个也许不太恰当的比方,神话以其贯穿古今的存在和变幻让我大开眼界,帮助我理解何谓“从美的身体到美的生活方式的追求”。
:你的翻译和写作范围,除了古典和神话,还有近世以来的不少文学作品,像《卡米耶·克洛代尔书信》,菲利普·勒吉尤《卢瓦河畔的午餐》等。这些作品,也贯穿着从美的身体到美的生活方式的追求。
吴雅凌:这两本小书在我拿在手上的第一时间都深深吸引了我。一个与雕塑技艺的现代性转折有关,另一个与超现实主义运动有关。这是往大里说,其实着眼点都极其细微,一些书信,一次拜访,我们从中得以亲近生活在那段历史中的人。我想有一点是共通的,这两本小书分别置身于我们刚才谈到的欧洲文明的美的传统之中。这美是活的,用各种可能上身的方式向你扑面而来,只要你是准备好的。欧洲文明几乎没有断裂,所以迄今依稀有少年的模样。当然,美人迟暮是不争的事实。这愈发让人心里疼惜。虽然就文明秩序而言这似乎是某种必然。但我愿意在心里保留这疼惜感,前提是不像从前那样不知深浅。
黄德海:在这扑面而来之中,最让人心动的部分是什么?
吴雅凌:美的惊鸿一现。这最动人,也最要命。每次去奥赛美术馆,我总会去看一幅挂在角落里的不起眼的画。它名叫《经过者》,即便在画家维亚尔(Edouard Vuillard)本人的作品里也不算起眼。画中的约纳河水静静流淌,岸边一丛杨树,秋日金子般的光照,水中的倒影完美无缺。有个男人划舟经过,放下摇撸,点一支烟,被眼前的美景吸引。他忍不住多看了一眼。就在转头多看一眼的瞬间,他已经过神样的风景。里尔克有句诗:“神才有这能力,但请告诉我,人如何通过狭窄的竖琴跟他走?”诗里借用的是古诗人俄耳甫斯的神话譬喻。属人的,如何永久居住在彼岸的美景中?这个问题从古至今困扰我们。就像画中人,在遭遇世界之美的同时也远离这份美。
黄德海:那些必然遭遇和远离这美,让人留恋徘徊。而已经遭遇的这些,对现在的你来说,是如灯下对古人,口不能言,心下快活自省,还是你一直在尝试用你的文字,来慢慢表达这美?
吴雅凌:严格说来,我想我也只是看到一些“美的表象”。这里头的最大魅力就是无法分享。就像那画中人所经历的。在那样的瞬间,有可能遭遇柏拉图在《斐德若》中所描绘的“灵魂遭遇美的阵痛”,并且那个过程必然是孤身一人的。那幅画为古典精神在人性与神性之间的挣扎做出精确的诠释。正因为这样,它令人在感动之余心生一丝莫名而真切的疼痛。基于同样的原因,这个无法分享的过程在某些时刻又不是没有释怀的可能,比如在阅读经典收获感动和疼痛的时时刻刻,比如我们由此展开的谈话。
黄德海:是不是因为你看到了日常之下那些黄金的质地,才有这疼惜感?这疼惜感是我们作为有朽的人的必然吧?我觉得这疼惜感,也表现在你对各种作品的分析中,通过对这些作品的分析,你把你的疼惜感写得分明。有了这样的传达,我们才会对古典的也好,现代的也好,对那些卓越的心灵创造的一切充满爱意,也才给我们一些温暖的对世界的善意。这个无法释怀,是否也是你愿意写作和谈论某些事情的初衷?
吴雅凌:柏拉图在谈爱欲时说,灵魂一旦遇见美就会惊颤,折了的翅膀就要重新发芽,长出羽毛。整个过程刺痛难耐,让人癫狂。生而为人大都有过类似体会。爱欲的滋润让人在极度苦楚中品尝纯粹的欢乐。我一直在引用柏拉图,因为在这些问题上我不知道还有谁比他说得更好。美的认知必然引发爱的问题。作为起步,疼痛是不可或缺的。只不过,我们似乎有一个认知误区,就是把疼痛当成终极结果。所谓苦难的光环,因此而遮蔽认知本身,这从某种程度而言也是一种现代性疾病吧。
黄德海:这个疾病的根源,或许来自人的僭越,也即人自我定义了超越和抵达,只在这中间加上了苦难的光环,并把自我定义的光环作为苦难本身。人大概自负到忘记了,“首先,人类在门前无论做何种努力都是徒然。其次,门不会因人的意愿而开,门内的世界也不以人的意愿为转移”。在你关于薇依《门》的文章里,有某种决绝,一种生而为人的卓绝向上努力的决绝,却并不因此企求高于人自身的某种报偿。
吴雅凌:自负和僭越是属人的本性,古希腊文学提供了最好的范例,英雄的受难经历无不是在反思属人的僭越和界限。他们切身体会并见证“如何通过狭窄的竖琴跟随神”这个问句里的困难。所以我想我们还是有必要区分,这里说的疾病并不在古希腊文学本身。薇依是这方面的解释高手。你说到决绝,让我想到她在解释洞穴神话时说过的一句话:“再微小的贪恋也会妨碍灵魂的转变。”
黄德海:你说疼痛是爱的起步,让我想起薇依的一段话:
有一种让事情变容易的做法。如果那个解除禁锢的人讲述外面的世界的种种奇观,植被、树木、天空、太阳,囚徒只需保持一动不动,闭上双眼,想象自己爬出洞穴,亲眼看见所有这些景象。他还可以想象自己在这次旅行中遭遇了一些磨难,好让想象更加生动逼真。
这个做法会让人生舒适无比,自尊得到极大满足,不费吹飞之力就拥有一切。
每当人们以为皈依产生,却没有伴随一些最起码的暴力和苦楚,那只能说皈依还没有真的产生。禁锢解除了,人却依旧静止,移动只是虚拟。
爱跟这里说到的皈依有某些相似之处。是不是可以认为,没有伴随疼痛的爱未经检验,没有苦楚伴随的皈依,也未经反省,因而也经不起推敲。
吴雅凌:就我所能够的理解,这是一个有关认知过程的譬喻。柏拉图的用语是洞穴或爱欲,薇依则说是秘仪或皈依。殊途同归。你提到的这段引文是薇依给我的许多警醒之一。我想,作为与智识打交道的人群,我们恰恰最容易犯类似自以为是的错误,不是吗?首先,我们很可能混淆真实与似真并以此影响自己和他人。其次,我们很可能在不自觉中过分轻易地思考和谈论我们并不置身其中的苦难。我觉得有必要提醒自己,特别是当我们从事与公开言说有关的行业的时时刻刻。
黄德海:这几年,我身边的很多朋友被薇依吸引,不少人在不同的场合提起她,我们也非常集中地谈论过。我觉得你在某种意义上是沉浸在薇依的世界里的。
吴雅凌:作为一名早慧的作者,薇依没有留下什么完整作品。她似乎总在匆忙中写作,留下一段段笔记和残篇,就如她进工厂在流水线上制作一个个待加工的零部件。单是这样的写作者身份,我想就很有趣。进一步说,这种写作样貌与她本人的思想品性契合。在压力下写作,没有时间地写作,在头痛时写作,饥饿地写作。但凡写作者难免有留下作品传世的执念,而她自愿站在一无所有的人的阵营。再进一步说,这些看似残缺的作品在她去世后持续激发着活水般的思想流动。到目前为止,这是一位时时带给我惊奇的作者。所有表面看似不可解的矛盾都是认知的机缘。同样的,在她的言说里出现的那些看似矛盾的“缺口”也都是机缘,有可能帮助我们探究我们还不知道的领域。
黄德海:对我来说,那个我们还不知道的领域,才是最珍贵的。我觉得你最近翻译的薇依《被拯救的威尼斯》,就是一部写出了我们还不知道的东西的作品,光彩熠熠。你引薇依笔记中的话,“加斐尔。在戏中某个时候要让他感觉,善才是不正常的。事实上,在现实世界本亦如此。人们没有意识到而已。艺术要呈现这一点”。或许,要表达那不可表达的,只能用戏剧(文学)的方式。
吴雅凌:在我的理解里,这是她对文学提出的一个终极挑战。文学若是成功的,必然为它所呈现的世界戴上某种光环。成功的文学如索福克勒斯悲剧,必然令我们在光环中看俄狄浦斯,成功的文学如福音书中的耶稣受难叙事同样如此,以至屈辱不成其为屈辱,苦难不成其为苦难。薇依在《被拯救的威尼斯》里做的,就是剥掉英雄的光环,去除正义的声名。她想要呈现某种没有贪恋的真相。她指出文学的要害,或者说哲人把诗人赶出城邦的理由。我想应该把柏拉图的努力理解为一种进行时态,通过一种戏剧对话形式来表达对诗歌之美的爱和对美人迟暮的疼惜。薇依的悲剧尝试也是如此,通过某种反古希腊悲剧的方式去重拾悲剧传统。我想有一点值得反复强调,就是这里头的去舍是很复杂微妙的,非如此不足以形成一种“争战”。这是给予对手最高级别的敬意。柏拉图对诗歌的态度也许能够给予我们某种努力方向的启示,通过古典学问让我们今天对文学有类似的感情。
黄德海:现代人要承接古典,或者与那些过往的伟大心灵有关,其实已经没有一条可以模仿(重复)他们的路走了,而是只好通过某种反(不同于)古典的方式来重拾这传统。薇依如此,你讨论的写《安提戈涅》的阿努依也如此。
吴雅凌:在索福克勒斯的安提戈涅身上已然集中体现了那个时代与其传统的挣扎和张力。阿努依的回归是还原张力本身。在认知过程中与一种精神遥相呼应,而不是简单重复某个古代世界,那既不可能也无意义。又比如,薇依认为,柏拉图做的没有别的,就是在遵循某种比他更古远的传统。
黄德海:如果从单纯还原的方向去做,永远不可能,因为再好的模仿,都是仿制品,在这个时代状况下,人只能尽这个时代的力,做这个时代的事,用这个时代的样式写作。而所谓精神的遥相呼应,其实是一种感召,进而言之,是一种竞争——用创造力和敬意完成的竞争。柏拉图对诗歌,就是这样一种用创造力和敬意进行的竞争。而你希望通过古典学问让我们对现今文学有类似的感情,就是让我们一起用竞争性的方式“回忆”(柏拉图意义上的)起整个古典世界。
吴雅凌:就我个人而言,好文学与古典学问是两个并行不悖的说法,并且不仅仅适用于某个特定时期的作品。你提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问题,是不是就如我们已经说过,一开始我是不知深浅的,而这似乎不只是个别现象?我是指我念“比较文学”的阶段,那时接触的全是现代意义的文学,后来有了所谓“古典学问”的参照,这并没有让我把以前知道的摒弃在外,而是让我明白以前知道的是多么有限范畴里的东西。
黄德海:这个并行不悖你怎么理解的?不止适用于某个特定时期的作品,是不是适应于一切好作品?这些好作品的范围是什么?你的大部分翻译和写作,看起来是站在古学一边的。这些作品给阅读者提供了很好的借鉴,免得人们只知道自己站立的这块土地,自己所处的这个时代。一个跟随而来的问题是,你是否反省过自己的古学立场?
吴雅凌:我倾向于避免轻易地谈论立场,这是基于我本人无论古学今学都一样浅薄这个事实。不过我想,一部好作品的必备条件之一不就是以自身的纷繁性呼应真相之难以言说吗?比起坚定不移的理念和宣言,更多强调求真过程中自身的困惑和限度,从某种程度而言,这也许更好地呼应古典精神里的均衡特质。此外我想,但凡具有诸如古今问题意识这样的相对丰盈的认知视域的,并且,就我们刚才说到的洞穴譬喻而言,不是在自身没有付出任何疼痛代价的前提下就公然提供示范的,都有可能是好作品。
黄德海:谈到付出疼痛代价,其实就遇到一个问题,即写作与信的关系——这里的信,可以不是宗教意义上的,但也不跟宗教意义上的信完全区别——我们写下的一切,自己信吗?进而言之,我们是否会根据自己写下的,校正自己的身心和日常?
吴雅凌:作者比作品高明的情况假设存在也只能被历史湮没无从考证。问题也许不在于信不信,而在于有没有能力把信不信书写下来。这也是为什么,柏拉图从苏格拉底的对话术发展出一种戏剧方式的书写。人的思想如海潮般,单个声音的言说总是有限,只能抓住一朵浪花,多种声音的交织才有可能容纳变幻无穷的浪花。基尓克果的假名写作与此遥相呼应。不同文明里的古老文本都不约而同采用类似的书写方式。论语如此。旧约里的先知书如此。福音书同样如此。我想,好文学有上身附体的力量,能够影响人的日常。
黄德海:我觉得,你在对待薇依上,就是这种信的表现。你翻译俄尔甫斯祷歌,绎读的赫西俄德,卢梭……是否也表现出这种信?
吴雅凌:我自以为是信的,或者努力走在信的路上。如果不看出他们的好并努力让这些好变成自己的,在这个过程中获取一些无法和别人分享的自得其乐的瞬间,我们大概会丧失这份微不足道的工作的最后一点意义。
黄德海:我们对这份微不足道的工作的坚持,大概也是因为这个。那么,在上面三者中,有哪些让你觉得特别振奋的地方?从赫西俄德开始吧。
吴雅凌:如果你每天醒来只面对一个作者的十行诗,除此以外没有别的,甚至没有心神再去翻开别的任何一本书。如此几年,朝夕相处,这个作者哪怕是三千年前的古人,也会变成亲人。我从赫西俄德那里开始理解神话。他最早定义希腊古人眼里的诸神世界,赫拉克利特称他为“众人的教师”,古希腊的小孩子通过诵读《神谱》学习认识他们的神。我还从赫西俄德那里体味世故人情。他最早告诉我们辛苦是生活的真相,并且言传身教不对诸种虚妄妥协。你刚才说到信的问题,我想至少有一点我们不得不信,他说的“宙斯的公正”历经三千年不变,只是换了不同的称谓,比如我们也说“天地无情”。
黄德海:天地无情的表现方式,是兴致勃勃的活力。在你关于赫西俄德的文章里,我能看到一种显而易见的活力,我觉得他自身的技艺,以及他要传达的东西,经你之手,来到了我们置身的当下。这个活力,正是从这位逝去了两千多年的亲人身上体味出来的。或者,他们其实一直不曾老去,只是因为我们过于轻易地遗忘,才把他们归入了逝者的行列。
吴雅凌:他们都留下了不死的东西,这是毋庸置疑的,这个东西自有生命力,只要有机会就能附体托生,焕发动人的光彩。这个东西只有在写作过程中才与写者有交集。过去了就不属于写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写作是一个等待的过程,当然要有相应的各种准备,但是文字涌现的时刻不由我们决定。
黄德海:的确,写作是一个等待的过程。这也让我想到了某种虔敬,就像你较早翻译的《俄尔甫斯教祷歌》还是《俄尔甫斯教辑语》中有人引的West的话:“某一个私人文化团体的成员夜聚屋内,借着烛火,在八种焚香的气息萦绕中向他们想到的神祷告,唱这些祷歌。”这种气氛,让我觉得像你刚才说的这个等待过程,也像是你说的不由我们决定的时刻,仿佛是属神的。你当时怎么决定翻译这些零篇散章的?在翻译这些的过程中,你自己的收获又是什么?
吴雅凌:我很想说不是我找到它们,而是它们来找我。但事实是我很幸运一直有高明的人指点,使我少走弯路,在不自知时就已受益。翻译俄耳甫斯教诗文(正如赫西俄德诗文)让我认识神话,而神话又帮助我完善对我所置身其中的这个世界的看法。如果是今天做俄耳甫斯教文献,可能会有点不同。比如说,那些祷歌在今天会让我想起泉州乡下的祭神,那些弥漫在空气中和脑海里的香火。我可能会多添入一点活泼和世故的质感。
黄德海:卢梭呢?这个让人觉得熟悉又陌生的哲人,你如何接近的?容易吗?
吴雅凌:你的描述很准确。就纷繁性而言,卢梭确乎是最让人赞叹的例子。因为语言更亲近的原因,我能够比较清晰地看见他的模样。但是,和卢梭相处的过程并不总是愉快的。有些作者让我们无比亲近,乃至在某些时刻把自我假想为他或她。但卢梭有如此强大的存在感,让人永远只能把他视为大写的他者。另外一个层面则是,卢梭问题远远不只是个人求索的问题。这方面尚有大量的工作有待努力。
黄德海:非个人求索的部分,是指对社会整体的思考吗?是不是对你来说,更关注的是某种对个人更有启发的东西,而不是社会或政制问题?
吴雅凌:恐怕这两方面是无法脱离开的。事实上,两者之间的张力不也是各种值得关注的问题的根本所在吗?
黄德海:谈到这个问题,有我一个私人的疑惑在里面。说到古典学,尤其是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古典学,我始终有个疑问,即,他们在讨论完苏格拉底的转向之后,自身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对施特劳斯来说,他如何安顿这个有朽的人身?后来看到他的一段话,暂时缓解了我的疑惑——“我的座右铭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伊本·卢德(阿威洛伊)的名言:我的灵魂一朝死去,也如众哲人之死。”在我看来,如苏格拉底式的认知灵魂的方式,大概可以安顿自己的身心。
吴雅凌:我倾向于认为,问学过程就是努力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蒙田的思考开端语是:“从事哲学就是学习死亡。”在柏拉图传世的三十几篇对话中,我们看到一个完整的苏格拉底传,其中心思想不就是在关注灵魂的安顿吗?《会饮》和《斐德若》谈论灵魂的德性问题,《斐多》谈论死亡,《理想国》作为一种譬喻,既适用于外在的城邦共同体,也适用于个人教养。
黄德海:蒙田的这句话,恐怕就是化自《斐多》中苏格拉底的话:“那些真正献身哲学的人所学的无非是赴死和死亡。”嗯,现在的情势下,大概得强调一下,苏格拉底明确反对自杀。既然探索学术问题的过程就是努力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也就是,对你来说,阅读和写作本身就是解决自身问题的过程,而你一直对创作的问题着迷,《黑暗中的女人》中很多地方也涉及了创作或灵魂的“孕生”问题。
吴雅凌:灵魂的孕生问题包含在第俄提玛给予苏格拉底的最高教诲之中。《会饮》比较了两种生育。一种是身体方面的,即女人受孕繁衍,通过传承血脉实现永生。一种是灵魂方面的孕生,通过生成美好的作品、法律和德性,实现精神的不死。这两种孕生模仿神的创世行为,因而让人最有可能与神接近。美的认知引发爱欲问题,爱的追寻引发生育问题,这是属人的可能,从古有之。其实我们的讨论不也是围绕这个话题吗?它让人着迷,因为它贯穿人的历史,无处不在,从高古的神话到眼前的日常生活。里尔克曾经在青年时代尝试在罗丹和塞尚身上寻找“神样的创作者”原型,他写下评论这两位艺术家的动人文字,他本人后来也成就为某一类型的写作者神话。
黄德海:这个灵魂孕生的过程,虽然艰难,却是写作被给予的好报偿——在辛勤的劳作里过去的每一个时日,让我们不致绝望。
吴雅凌:这是魅力所在。过分轻松的完成过程本身是一种欠缺。在创世记里,神一连做了六日造物的工,第七日才停歇。六分辛劳对应一分闲暇。这里头含带着一种张弛和均衡。罗丹说过一句话。雕塑时不要让泥土闲着,泥土若有知觉,要让它们感觉疲累不堪(Fatigez la terre)。
黄德海:这个孕生的过程,是对身体限度的挑战,也是对心灵承受度的挑战,对女性来说,或许有更多、更复杂的意味。你在一篇文章中说过,“如果我们没有错解柏拉图的话,那么赫西俄德不是一味轻视女人,而是拒斥女人所代表的繁衍方式的有效性”,并且认为,“赫西俄德和尼采笔下的女人神话,目的不在于追究女人与男人的关系,而在于探讨‘灵魂的孕育者’,也就是诗人的身份问题。诗人孕育自身的灵魂之树,也是在孕育着流传后世、属于所有人的果实”。灵魂孕生问题是不是也在跟你一起完成对女性的认知,“帮助我们带着与生俱来的心病尽可能走得更远”?
吴雅凌:所有的认知最终归向“认识你自己”。女性兼具两种孕生可能。在传统分配与启蒙以后的诉求之间必然有所撕裂。孕生是一种说法,归根到底是一整套共同体内的政治生活方式。我们从古希腊三大悲剧诗人笔下的女人群落就看得很分明。我
一直很感兴趣那些在不同时代把创作(灵魂孕生)视为自我完成过程的女性。她们很像索福克勒斯笔下的女人类型。启蒙从他开始,撕裂也从他开始。女人身份与创作者身份的撕裂,归根到底是身体本能(沉重下坠)与灵魂诉求(向上攀升)的撕裂,这样一种人性的、太人性的存在之难反过来也远远超越了女性问题。
黄德海:这撕裂是一条不能弥合的缝隙。这条缝隙,或许透露出人的某种迫不得已却又不可替代的东西,也让写作在某种意义上引领着我们走上属人的上升之路。或者,这也就是人通过狭窄的竖琴跟随“他”的方式。
吴雅凌:这条缝隙就是身为写作者的全部生存空间,进一步说是每个人的洞穴。有趣的是,里尔克在那首诗里紧接着也是在说属人的撕裂,“在两条心路的交汇处没有阿波罗神庙”。古代神谕设在岔路口,为迷途者指点迷津。通神者即是最早的诗人。“在真实中歌唱”。文学早早地在那里了,也包括在每个古今交会的岔路口。
编辑/张定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