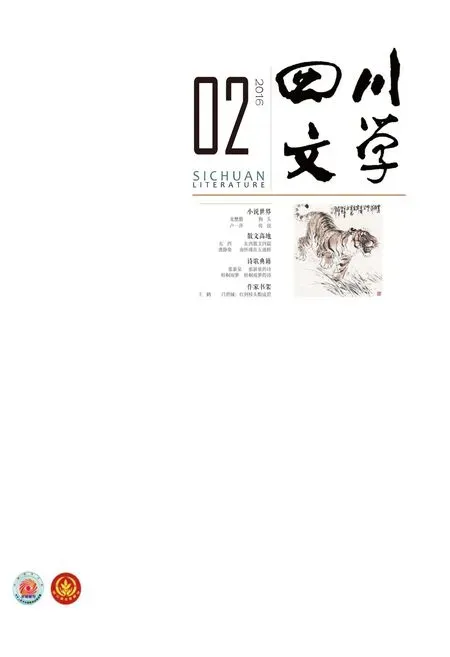从灌县到都江堰
李忆莙
从灌县到都江堰
李忆莙
1
明代太遥远。当时在中国旅行的那些人,他们眼中的元代是怎样的?那时的社会结构,那时的官宦人家与一般平民之间的悬殊有多大?对于那时的风土人情,他们做了怎样的描述?除了《马可波罗游记》中的一些散章,我至今还没看过这一方面的结集。比较具体的倒是写在一百多年前的《长江流域旅行记》(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和《一个博物学家在华西》(A Naturalist in Western)二书。作者同是英国人,他们在四川进行了比较长时间的游历和考察,据说他们的记述都偏重于四川西北部的山川景色和风土人情。
元代距今七百余年,确实是有点远了,而一百多年前,最远不过是清末。而我既有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之行,何不把这两本书找来看看。也许跟随着他们的足迹,可以重新再走一次同样的路线呢。有着这样的想法,我一到成都,就在下榻的宾馆附近的书店找这两本书,但都没找到,都说要找这么旧版的书,得花点时间哪。后来有朋友告诉我,几年前,四川民族出版社曾出过一本叫《伊莎贝拉在阿坝》的书,并说此间大家都认同这是一本外国人眼中所记录下来的最没有偏见的书;从这本书中你不但可以看到作者的胸襟,同时也感受到作者那纯粹为了亲历一个无拘无束的、可挥洒生命、可呼吸自由空气的人间净土,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的激情。而这样的一本书,竟然出自一个女性之手,而且还是在一百多年前!这意味着书中所记述的有关阿坝的人与事,都已过去了一百多年。换句话说,书中所描绘的人文状况、民俗风物、山川景色,俱为百余年前有烟云矣。
然而,从古至今,文学就是为历史开追悼会的。文学的跌宕起伏,没有历史铺垫,便不能今昔对比,更衬托不出今非昔比或今不如昔。
当然,一百多年前与一百多年后,即使山川不变,风土人情不改,世界也无可避免地起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比如新中国的成立。
然而,直至到我出发去马尔康,还是没找到《伊莎贝拉在阿坝》这本书。无缘带上一起去旅行,也就无从“今昔对比”了。
2
当我从马尔康回到成都,省作协文学交流中心的梁曌,捎来好消息:终于在网上搜到《伊莎贝拉在阿坝》了 — 是川大小书店里惟一的“孤本”,已经着人去买回来了。
原来伊莎贝拉除了是作家同时也是旅行家。1831年出生在英国。22岁开始旅行,足迹遍布北美许多国家。她曾穿越北美洲,翻越洛基山脉,到过波斯、库尔德斯坦等地。她去过的亚洲国家包括中国、朝鲜、日本等。她是在1896年来到中国的。《伊莎贝拉在阿坝》,其实是选自她的游记《长江流域旅行记》里的第二十八章至第三十四章编译而成,字数不多,大约十一万字左右。
《长江流域旅行记》是伊莎贝拉在中国旅行的沿途所见、所思、所闻的记录。在她的记述里,不时会著墨于一些当时的衙门,村寨,以及官吏,官差等。她的笔触非常细腻,人物描写生动,并且对当时的社会、时局、官署,以及民疾有相当程度的揭示。她的阿坝之行从灌县(今都江堰)出发,经汶川(绵箎)、威州(汶川)、杂谷脑(理县),再翻过鷓鸪山,到达位于今马尔康境内的梭磨土司官寨 。
伊莎贝拉的勇气与毅力,着实令我肃然起敬,震惊地想:一百多年前啊,在那广袤的荒凉大地上,远处是迷迷濛濛带看寒意的雪山,前面是大峡谷,周围被长满了云杉和幽暗松树的森林所包围着。面对如此境况,心中能不怀疑:前面有路可行吗?真的,走到水穷处,就只能背靠陡峭崖壁横着身子移步,而脚下,是万丈深渊,深渊下面是湍急的河水,水流忽然来个急转弯,冲打在岩石上,激起千层浪,却都被雾气所笼罩,什么都看不见了,只听得震耳欲聋的咆哮声。这并非想像,而是岷江主流与无数支流以及大峡谷的真实状况。
而伊莎贝拉,在那个除了坐轿子或骑马或徒步以外就没有其他交通工具的年代,她翻山越岭,跟风雪搏斗,从成都到梭磨,再从梭磨回到成都。900英里,她跋涉了3个月。
《长江流域旅行记》于1899年,首次在英国伦敦出版。而我所读到的这本《伊莎贝拉在阿坝》的出版缘起,必须追溯到一百多年后的2004年。四川民族学学者红音女士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期间,在东亚图书馆无意中发现了一本百多年前记述自己家乡的书—《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有了这偶遇的前因,后来才结出翻译成汉文出版的果 。
《长江流域旅行记》的写作时间大概是在1897至1898年之间。伊莎贝拉1896年抵达中国后,从上海逆长江而上。那时的中国,已经是晚清时期了,清王朝沉浸在一片暮色苍茫之中。
3
《伊莎贝拉在阿坝》的第一章是:灌县与成都。
灌县是今都江堰的旧称。根据伊莎贝拉的描述,她说灌县是个不怎么起眼的城镇,街道狭窄,而且很肮脏,有着一种偏远山区的闭塞气息。由于闭塞,那里的人见识少,看到外国人会围上来观看,一面指手划脚,一面说:“看,又来了一个吃小孩的。”
那时是1896年,灌县的人口大约是22000左右,可却没有多少人气,而且相当贫穷。她看到的都是一些毫无生气的小店。在市郊也没看到多少富人的大宅。
于是伊莎贝拉作了上述的结论。但很快她又作出了调整,坦言只说对了一半,另外的一半在于两个方面其一,这里有最古老的水利工程— 都江堰,因而使得灌县享有很高的知名度。
其二,灌县是一个贸易中心,这里的人长期与来自北方的藏人进行贸易。特别是在冬季,有将近500藏人带着他们的货物以及牦牛和马匹驻扎在城墙外(现在城墙还在吗?)所交易的货品种类繁多;藏人带来的是皮革、羊毛、麝香、鹿角和药材等。而汉人的货品则是茶叶、棉布、丝绸、铜、铁器等。其中最大宗的货品交易是茶叶。藏人喝茶等同汉人吃饭一样,是每天必须的,因此茶叶的需求量非常大,他们几乎把所有的货品都换成茶叶。汉人则把从藏人那里换来的皮革、羊毛、麝香、鹿角,尤其是名贵药材,销往内地去能赚取成本的好几倍。
当然,伊莎贝拉所描述的场景,我们今天是看不到了,只能靠想像。
但是都江堰,这世上最古老的水利工程,两千多年来,一直造福着成都平原的百姓,仍然一如既往地“旱涝保收,五谷丰登”。若从古迹或文物的意义来说,二千多年的历史,也的确足够在中华民族乃至全人类的心灵里涓滴成永恒的化石。
所以,一百多年的时光流淌,对都江堰而言真的算不了什么。在今时,如果你把都江堰看成是古迹,是历史意义的,那么,它就是一个活的文物;若你把它看作是一项水利工程,那它就是当前世界上硕果仅存的惟一仍然在操作中的最古老机械。
伊莎贝拉写都江堰,倒是没花上多少笔墨,只是大致介绍了一下都江堰排沙泄洪,引流灌溉的功能。而对于都江堰这伟大工程的设计和修建者李冰和他的儿子的介绍,相对用了比较多的篇幅。对李冰的“深淘滩,低作堰”的治水理念钦佩不已。
她认为如果“深淘滩,低作堰”能够被广泛利用到应对大江大河的水患问题上,那么世上将会减少许多灾难。因此她把崇敬的目光投向二王庙,用很细致的笔触,一笔一笔地慢慢地描绘。
首先是写二王庙的位置,对于坐落在高峭崖壁上的选址十分赞赏。在她的审美观感上,寺庙在层层茂密的丛林覆盖中,露出泛着微光的绿色琉璃瓦,其间点缀着整齐的日本柳杉等一些异域植物,这种衬托是最迷人、最美妙绝伦的景致。然后她走进二王庙的院落,告诉你她所看见的:“院中有一株柚树竟达18英尺。这些庄严肃穆的庙宇,雅致的庭院,精美的亭台楼阁,以及庙后耸入悬崖的塔顶全部隐藏在茂密的柳杉中。这里的建筑风格实现了优雅魅力与壮丽威严的完美结合,是我在远东见过的最美丽的建筑群……”
我一边读着这些文字,一边努力地回想,她所说的那株18英尺的柚树我看到了吗?似乎一点印象也没有。当读至“清澈的山泉从大石雕刻的蛇口汩汩流出,厚厚的石阶通往寺庙大门”,我的心里立即有一丝温柔的牵动— 呀,这石阶我走过— 她到过的,我也来了;她踩过的,我也走过。
二王庙,一座纪念李冰的庙,它是灌县的荣耀。
伊莎贝拉是这样认为的。她说二王庙里有30个道士是专门掌管神殿前的灯柱的,他们必须确保香火常年不灭。每年皇帝都会派遣钦差送来御赐的供品朝拜二王。
她在殿外看到黄色的锦旗迎风飞舞,那是皇帝的御赐— 这确实是灌县的荣耀,因为李冰。
我忽然想:这些锦旗是哪个皇帝御赐的呢?一百多年前的1896年,慈禧还在清廷里掌握大权,但她“只是”皇太后而不是皇帝。她的掌权时代自丈夫咸丰皇帝死后开始,而后经历过两个皇帝,即同治和光绪。临死前钦定溥仪继位。
所以,根据年分推算,伊莎贝拉所看到的锦旗应该是光绪皇帝御赐的。因而让我在阅读伊莎贝拉的著作的同时平添了不少乐趣。我跟随着她的足迹,继续在二王庙的建筑群里穿梭游览。
她看得很仔细,几乎每个角落都走遍了。她不单赞叹寺庙的整体之美,大殿的金碧辉煌,还注意到窗花的图案,顶柱的精雕细刻与美丽的彩绘,她的专注与细腻令我汗颜。我三到都江堰,每次都去二王庙,每次都仅是“到此一游”。在匆匆的步履中,游是游了,可并没有留下太多深刻的印象。或许,我不够细腻,细节注意得不多。回想起来,我觉得我对二王庙的“关注”是停驻在外观上的,喜欢远远地眺望它。
因为伊莎贝拉的细腻,让我懂得了放慢脚步;脚步慢了人生会变得更美丽,这种感觉真好。
“二王庙给我的印象是自然与艺术完美结合所产生的美丽与雄伟的效果。寺庙门外,一些精美的建筑被参天大树繁茂的枝叶遮盖,溪水汩汩,灌木上盛开的鲜花使潮湿的空气中漂浮着浓浓的花香…… ”她的描述是那么地令人神往,令人心醉。也只有放慢脚步你才能觉出闲处的恬适与韵味。在这里,光阴流得很慢很慢,因此也无所谓沧海变桑田。
其实,当年伊莎贝拉所看的二王庙是重建的。换句话说,是新的二王庙。而我们现在所见到的也并非是同一建筑群。二王庙初建于南北朝,一千多年来,经历过多少次兴废已无可追考,反正历朝历代均有修葺或重建。在这意义上说,二王庙给世人传下来的只是一个名字,是一页兴废相交更替的历史。晚清时的二王庙,是在明代的基础上,于同治、光绪年间相继重建的。明代末期张献忠剿四川,二王庙毁于大火。因此有理由相信,伊莎贝拉极为赞赏的建筑主体,大部分为清代所建。民国十四年(1925年),二王庙又一次遭受浩劫,被大火焚毁。之后再由当时的住持李云岩募资重建。这就意味着1925年之后的二王庙已不是伊莎贝拉所记述的那座建筑群了。“文革”期间,二王庙又遭受到灾劫,为红卫兵所破坏,将李冰和二郎的塑像捣毁。
我三到都江堰,时间分别是1993年、1999年及2014年。这也就是说,我无缘见到伊莎贝拉眼中“自然与艺术完美结合所产生的美丽与雄伟的效果”的二王庙,因为它已不是原来的了,而是李云岩在1925年募资重建的。更教人不胜歔欷的是在短短的二十年间,我所看到的二王庙竟然不是同一座!
2008年5月12日汶川大地震,二王庙严重损毁。过后根据文物局方面的资料显示,严重损毁面积4000多平方米,部分损毁面积7000多平方米,总体损毁程度达九成。如此数据,二王庙等于是毁于一旦!
在当时,所有目睹了在废墟中变为一片殘坦断壁的二王庙的人,都无不认定二王庙从此走进历史,永远消失了— 这么严重的损毁是没有可能修复的。
然而不到三年的时间,即2011年的4月21日,二王庙整体对外开放(在较早前,已将修葺好的部分先行开放)二王庙的修复工程,并不单是修复,还包括了文物抢救和保护各方面的工作,因此获得了国家授予的“优秀文物保护工程特别奖”。这简直是一个有如阿拉丁神灯般的奇迹。而这奇迹的缔造者,并非单方面的,而是结合了投资1.1亿元的 “灾后文物重建1号工程”,以及相关的部门,如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故宫博物院、清华大学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文化遗产保护研究所等8 个部门单位的专家学者们的专业支援成果。这集体智慧的结晶既有建筑学的高超技术,也积聚了深厚的文化内涵,这才是二王庙得以在废墟中重生,缔造奇迹的真道理。
对于都江堰,你很难分清是古是今。在时间上,它无疑是古,但在实用上,它却是今。而二王庙,它屡兴屡废,相交更替,始终去古未远;在不古不今,亦古亦今的时光中历尽人间的风雨,教人不忍细说。然而,它始终是中国人努力建造的圣殿,永远挂满秀丽的书法、荣耀的牌匾,特别是李冰的治水名言:“深淘滩,低作堰 ”,那是千古流传的前人智慧,是四川人心中的暖流,是永世的感恩与铭记。
【我与《四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