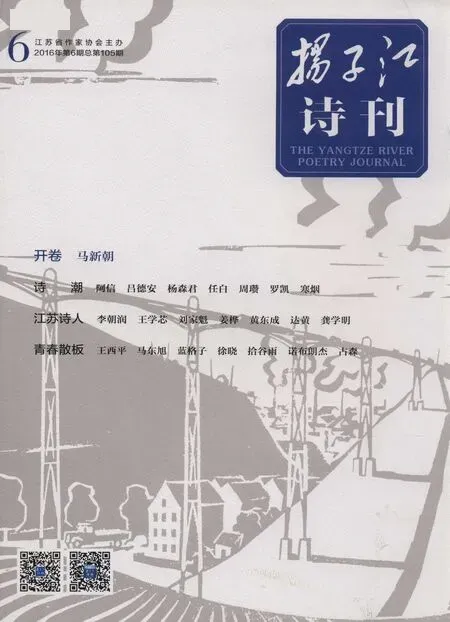杨森君的诗
杨森君
杨森君的诗
杨森君
月亮山
高处仍然很冰凉
坐在石头上的人,未必是为了
看到更远的地方,秋天能留下来的
恐怕只剩下这些枝桠了
无序的枝桠
接近边缘
流水载着落叶
滑下石崖
一些红色的植物
我还叫不上它们的名字
叫不上名字的喜欢
让我在此逗留
是时候了
连最微小的事物
都默许了
黄昏到来前
白昼的寂静
在月亮山,前世长于今生
沿着一条石径拾级而上,两侧的树木
看似比石头还古老
在月亮山
见过世面的人
常常都会弯下身
像年幼的孩童一样
喃喃自语
瘤 子
肩膀一侧的瘤子终于被取出来了
七两重的一只瘤子寄生在我的身体上
居然幸运地被我抚摸、搓洗
一次误诊让我开始怀疑某医生
“别管它,不碍事儿”
我就一直任其滋生、变大
几乎压迫到我的颈椎、神经
我不能轻易地把头痛归罪于它
但也没有理由证明我头痛不是因为它
看着血糊糊的瘤子
装在塑料袋里
我说,扔掉它,赶快扔掉它
我把它理解为一种惩罚来抵消我对它的厌恶
此瘤已不存,但愿某罪已抵消
阿拉善之夜
昔日的王爷府
也只有一个月亮
它照过的草丛也不会因此茂盛
我一度把它想象成一只盛满羊奶的木桶
一位穿红袍的僧人
坐在台阶上
他看见我从营盘山上下来
如果他有寂寞,我与他的一定不同
白昼热闹的赛马场上空
偶尔会有流星滑落,它们变成灰烬之前
从没有自己的名字
它们的消失,只是一瞬
其余的星辰正向西方流去
一根灯柱接着一根灯柱的尽头
是阿拉善小镇,在它曾经还是一片沙漠的时候
附近是一座古老的骆驼牧场
冬 雾
雾从对面弥漫而来。如果此时不是暮色四合
如果此时看见的是别的,而不是镇北堡
我不会像现在这样忧伤
我也不会把草木的悲哀戴在脸上
我无权知道蝴蝶的下落
是的,当他们说到这里曾经蝴蝶成群
我却绝口不提。我只是默默地踮起脚尖
摘下一枚枚枯枝上起毛的浆果
没有为什么,就别问为什么
就像汹涌的雾气,在镇北堡以南的旷野上
一会儿攀上树梢,一会儿落进凹地
偶尔会从雾中传来一阵隐隐的回响
那是事物表面上的声音,灰白的声音
它符合树木现在的情形:
因为过于干燥,所以要裂开缝隙
腾格里
你们看不见
青草如何被窒息
月亮在缓缓下沉
它所有的光线正在搜刮着干枯的地皮
有伤的一面
下午分外开阔
原野到处是已经谢幕的红蒿
日复一日,黄昏都要
在此停下几分钟
将光线一直伸过另一座山头
我还不能说秋天有多残忍
即使它以最快的速度
销毁有伤的一面
即使山坡上的马匹
开始像一坨坨红锈垂下长鬃
我是爱着完美的人
在多事的九月,这么容易忍受
落日看起来也像是在回应我
我不便将它描述得过于盛大
秋 日
任何一个人的推演都不过是一种经验
包括荒凉的常识,清晨窗玻璃上的白霜
我不能轻率地将一座裂缝逐渐扩大的榆树林
描述为废墟,它是现成的,它只是循环至此
四十年前,我就看到过它,一片榆林
在一个村子的北侧,在鸟群盘旋的下方
我怀有不明确的向往,对它,对它轮回的绿
与形似死亡的灰色枝条
有一些已经不存在了,我从没有认真察觉
我借用过某棵树冠的荫凉,坐在地上
我把一只缓缓爬向荫凉的甲壳虫一次又一次
弹了回去,让太阳狠狠地晒着它黑颜色的脊背
我只是记住了一些渺小之物,其余的
我已永远想不起来,但我不憎恨遗忘
就像这个秋日,也像一种遗忘:树叶开始飘落
枝杈即将光秃,大部分鸟巢都显形在外
天葬台
郎木寺南行数里,便是天葬台
据说,这里是亡魂升天之地
对此,我一直半信半疑
多么空旷的一块地方
生杂草,也开一种
似乎永远也长不大的白色花朵
如果不是事先知道
这里是天葬台
我可能在走累的途中停下来
卧草而眠
或者观赏一会儿
神似寂寞的蝴蝶
再上路
我来的不是时候
没有看到秃鹫,也没有看到天葬师
石板、铁锤、刀斧
随意扔在地上,看似很久没有用过
暗红的土质,让我联想到一具具尸体的消失过程
我当然感到恐惧
天堂不过是一个好听的词
没有人愿意下地狱
也不会有人主动上天堂
扎尕那
一匹马,应该属于草原,属于鬃毛飞扬的狂奔。
在扎尕那的一面山坡上,
环状的云彩在取下午的光。
一匹马被一根磨细的麻绳拴在木桩上。
沟沿上的青草,需要伸长脖子才能啃到。
它 是一匹仅供游客花五十元钱骑一程再返回原地的马。
我没有骑它。
看到一匹马的命运,我的心就软了下来。
我低着头仔细打量了一会儿它的眼睛。
失去自由之后的呆滞与羞怯,
放进它的大眼睛里是我想到的
最恰当的词。
我不骑并不能改变它的命运,
它的主人刚刚接下了下一位游客的五十元人民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