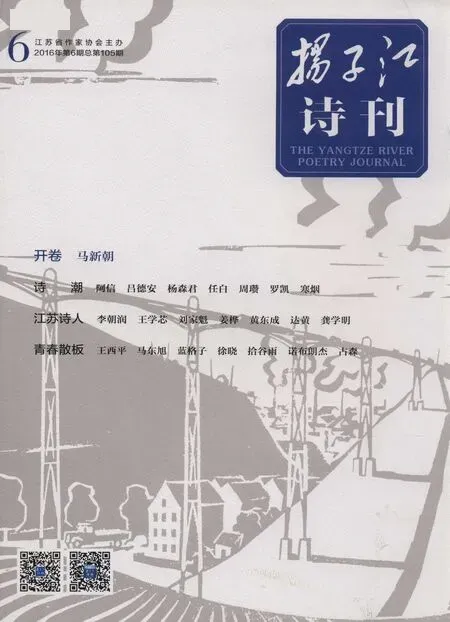窗花之忆(组诗)
阿 信
窗花之忆(组诗)
阿 信
我们没法从一场春天的游戏中退出来
瞎子看不见杏树在开花。
兔唇的孩子,也有在山岗上高声呐喊的冲动。
我们搬开石头,露出粘附虫卵的骨头。直到
我们中间的一个,被她的母亲喊回。另一个
脸上长满痘疱的男孩,被早早淘汰出局……
我们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尽管参与者,
已经所剩无几。
雨
落向村庄的雨,洗净榆树和那里住着的
两大一小三只麻燕的脸。那最小的一只
满脸透出惊奇!
用我们的手稳稳接住,别让它们
掉入泥淖。
落向村庄的雨,要密密地裹住
这些气息。
我 的母亲和姐姐在里面哭,我的哥哥患上了肺病。
不让远在青海的父亲,
雨中听见。
七个夜晚
七个夜晚从深井打捞残星。
七个夜晚在一株白杨树干上刻下月光。七个夜晚
把散落的羊只一一找回圈中。一生中最长的夜啊!
家族中的老人,盘坐一地。嗯嗯,啊啊,吔吔。
而死亡借一匹麻布的竖琴唱歌。
七个夜晚秘密刻录的信息,被九天之外逡巡的
一颗流星捕捉,被童年清凉的泪水收藏。
取 水
梨花一树一树。
苦涩的甜味渗入四月的空气。
梨花深处,泉水清冽。
叫不出名字的蝴蝶恋爱着这里尘土的清新。
我们老远就闻见刺鼻的硫磺气息——
不是来自地下,而是来自
记忆的清贫期。
群 鸦
群鸦乱舞。群鸦在空中
不会掉下来,即使冲它们大喊。
树枝上面是空的、灰白天空。
群鸦划出的线条,交叉、纠缠
清晰又凌乱,无法描摹。
树枝下面是粗硬树干,是北方
厚厚的积雪。群鸦
逆风盘旋,发出尖叫;又沿着
看不见的海浪的锋面
收缩翅膀,斜刺而下
像一群
踩板冲浪的少年。
我一会儿兀自担心,一会儿
又在内心,暗暗替它们喝彩。
雨夜,惊怖的梦
时常梦见
一个被蛛网缠绕的灰烬般的院落——
门楣上红字滴血,半掩的门扉深不可测,
没有呼叫从里面传出来。那里
艾蒿高过腰部,虫豸搬动瓦砾。
那里,一度发生的事情,像真相
被岁月和积尘遮蔽。
梦醒后我听见窗外有哭泣的雨声。在梦里
月色从云隙间窥见
伏在墙头的那个孩子,
紧张恐惧的眼神。
也许,只有在北方冬天下雪的时候,
我才能得到真正的安宁。
给父亲
死亡是一种自然,我已接受很多。
但这一次,是一次痛苦接受。
没进行对话和沟通,没有预谋和妥协。
单方面决定,一意孤行,甚至
起码的告别都被取消。
睡眠和死亡如何划界?什么样的存在
才配修炼通往冥界的穿越术?什么样的传唤
如此峻急和迫切?不可能再有答案。
一次散步,走出太远。
一次晚餐,突然多出一副碗筷。
只有接受。只有寄望于
羁绊一生的愁苦、劳累、哮喘、伤病……
不再跟随你。带给你生之安慰的
田园、水井、鸡舍、犬、骡子……
都随你而去。
愿生活继续。梨花如期
开遍故乡的山岗。兄长们在梨树下劳作,
种植瓜果和菜蔬。我重新上路
带着你早年买给我的那把
上海牌口琴。我要在长路上再一次把它吹响。
河 滩
河滩保留着洪水拖曳而过的痕迹,
现在是平静的正午时分。
一个背背篓的女人来到这里。然后是
两 个孩子,来到乱石和树枝之中。来到注视之中。
天空低伏,村庄退隐——
裸露的河滩,仿若油画般空旷、阒寂。
只有背背篓的女人,和她的两个孩子
在乱石和树枝之间,弯腰、捡拾、偶尔抬头。
泪水就这样无声地涌出——
我 奔回她身边,重新成为两个孩子当中的一个。
星 空
再贫穷的村庄,也会有羊圈、碾盘、水井
和先人们的坟;
再 荒僻的村庄,也会有鸡鸣、犬吠、婴儿的啼哭
夜晚繁密的星空——
离乡三十年的人梦见的那一片星空。
黄雀记——给三哥
欲求黄雀,从辞章入手,必不可得。
少年属意于绳锯和斧斤。用一个春天,
早早备下:皮筋、竹片、钢针和木棍——
用于发明一台打孔的手钻。这个想法
让他整夜颤抖。白天
面色发白,牙关紧咬,混迹人群。
多少伟业发端于脸色阴郁、鼻涕清亮的少年。
从手钻出发,经过一片
象征的竹林——拆开一把弃置屋角的
秃扫帚。那精心挑选的,是否拥有
少年天真和鲜为人知的屈辱?
手钻旋转。竹条
在掌心跳动。痛切又轻快。
失怙的孩子,要给自己当父亲。
一架黄金鸟笼。一部
暗设机关的捕鸟器。这是他奖赏给自己
黯淡的少年时代唯一值得安慰的礼物。
新麦大熟,诸事俱备。通往
一只黄雀的道路,让少年提前长成。
隔着无数六月,我看见
在一个薄雾的清晨,少年手提鸟笼,
带着媒鸟,离开村庄。我甚至
听见滚过他胸口的那首灼烫的
歌曲:“黄雀,黄雀!
不入吾笼中,欲入何地?”
从此,世上再无黄雀。
从此,世上更无热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