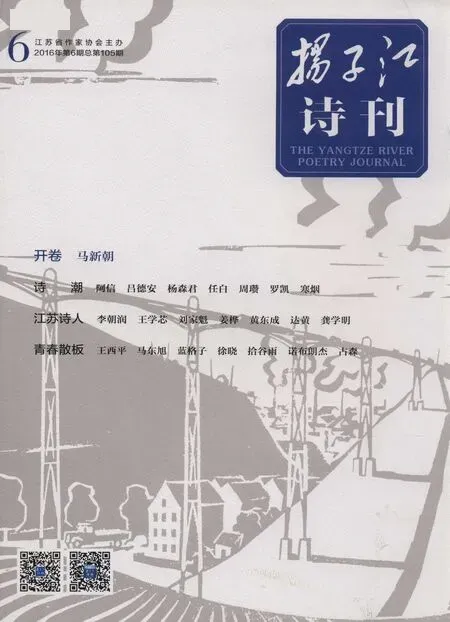新诗写作中的中国乡村经验
马新朝
新诗写作中的中国乡村经验
马新朝
中国新诗100年来,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不容否定。
中国新诗打破了旧有的锁链,可以自由地表达新生活。并把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和精神元素以诗的方式融入到了全球化的诗意语境中。
100年来,中华民族经历了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以及当下的农村、农民大流转,这都是人类历史上重大的或者是绝无仅有的大事件,大动荡,大变化,大变革,大悲痛。新诗在表现这些大事件中虽然还没有产生伟大的作品,或是与这些大事件相匹配的作品,然而,新诗已经找到了书写这些大事件的路径和精神基因,已经找到了书写这些大事件背景下人的命运和个体存在的语言方式。
在当下这场农村、农民大流转中,中国新诗如何表现呢?
这对中国新诗人来说,既是严峻的挑战,又是一次难得的机遇。诗人们已经具备了充分的条件写出可以与这场大变革相匹配的伟大诗歌。这种伟大的诗歌应该是世界的,也是中国的;是现代的,也是历史的。诗人们既要使用自由的、开放的、全人类的视角来看待这场变改,不受民族的、疆域的限制,又要继承传统的优良因子。
乡土,是一个贫困的、受辱的词;乡土诗则是一个被污染了的词,一个当下的诗人们竭力避开的词。诗当然不能分类,更不能像过去那样以题材划分,诗就是诗,诗是一团,是一个生命的整体。然而,为了叙述方便,本文仍然使用乡土诗这一个词来命名。
在当下诗歌写作中,有不少诗人的诗歌写作就像他们那些仍然生活在乡村里的兄弟姐妹们那样迅速地逃离乡村,从而向往着都市生活繁华和奢靡,但他们仍然是一个生活在都市里的乡下人。一些诗人认为乡村是一个过于落后的词,太土气,写乡村诗,别人会说你不先锋。况且中国的现实不同于西方,诗人们从西方诗歌中很难找到中国乡村生活和意识的对应物,这对于一些唯新是好的诗人,因此会感到失落。对于乡村诗歌写作的规避,这是因为大变革所导致的迷茫。然而,仍然有不少优秀诗人在写着乡村。
考察整个中国诗歌史,新诗对于中国乡村现实的写作还是有突破性贡献的,可以说是尚没有得到批评界认可或是忽略的伟大贡献。新诗百年的各个时期,一些优秀的诗人们左冲右突,反复探索,冲破前人的桎梏和封锁,使用不同的语言和审美趋向。为新诗真实地表现乡土中国写出了创造性的作品。
成名对一些人来说是惊喜,对一些人来说是预谋,对于朦胧来说却是突发情况。成名后他有点儿诚惶诚恐:“那种感觉是一下子多了很多人在看我,很害怕自己做得不够好。”《太子妃升职记》一夜爆红的时候,于朦胧也被推到了大众视野的正中央。他不是没有慌张过,只是学会了一点一点去适应,这个过程就是把他自己个性里那些容易被干扰到的部分想办法安抚好,给自己的心找一处舒服的位置,安顿下来。
中国所有的重大变革,几乎都离不开乡村。
中国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国,几千年来农业文明不仅一直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也融入我们每一个中国人的性格和血液中。农业文明的各种特征是我们每个人的心灵底色和诗歌语言的背景。作为一个中国诗人,你是无法脱离自己的生存背景的。我们的祖先几乎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者,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艰难地生存着,不仅抵御着自然的灾害,也抵御着统治者的各种盘剥、压迫,还有战争,饥饿,伤痛,种种苦难。
然而,面对这样一个农业文明古国,数千年来,在浩如烟海的古典诗歌中却很难找到与之匹配的反映乡村题材和农民苦难的伟大作品。中国古典诗歌对于反映乡土、乡村生活大多是以观光式的、赞美式的、隐逸式的,以及感叹稼穑艰难,昼永夜长,与农人的实际生活相去甚远,很难看到有反映乡村农民现实生活和苦难的作品。
中国是一个诗歌的国度,在明清以前,诗歌一直是我们文学的主流,但数千年来乡村的真相和乡村现实,诗歌却不能给予充分的表现。这些庞大的、整齐的、唯美的、以及格律严谨、对仗工整的诗词海洋,遮蔽了这个农业大国农民的苦难、眼泪、鲜血,以及活生生的个体生活。
乡村苦难在古典诗词中的缺席,造成了民族的集体失忆。
五四以后,新的思想和新的文学观念在中国大地上蔓延。新诗草创期,诗人们开始反思中国的诗歌观念和价值取向,开始关注乡村现实。从乡土诗的先驱者刘半农、刘大白开始用直白的语言反映农村现实,一直持续到1949年,新诗写作出现了很多反映中国乡村现实的优秀诗人。
这时的诗人们敢于直面乡村,把笔触伸入到乡村的各个角落,饱含同情地写出了乡村的疼痛和无奈。比如臧克家的《难民》,写一群逃难的农民,傍晚时分来到异乡的一个村庄里的遭遇,却不被收留,忍着饥饿和寒冷又向另一个村庄走去,读罢令人心颤,虽是一首短诗,却是那个战乱年代的真实写照。艾青的《在北方》《大堰河,我的保姆》等诗,无论从内容到写作手法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在北方》写得老辣,深刻,有力,仅仅几个细节,让人过目不忘,这几个细节已经成为那个时代的典型细节,保姆的形象也就是吃苦耐劳的中国农民的形象,这些表现乡村的形象和细节在过去的文学史中是极少见的。
在这里,我还要说说中原诗人徐玉诺和苏金伞,他们二人对于中国乡土诗的贡献是划时代的,只是还没有得到评论家们应有的评价。战乱和黄河泛滥,几千年来给中原人民带来了无穷的灾难,中国有多少苦难,中原就有多少苦难。诗人苏金伞和徐玉诺在五四的精神感召下,第一次诗意地展现出了中原地区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现实图景和农民的命运以及存在的真实。他们使用中原乡村最为朴实的语言甚至是方言俗语在现代主义的光照下捕捉那些带血的细节,正面的、全景式的来表现中原农村和农民,而不是浮光掠影。苏金伞在《跟妈妈说》一诗中写道:“有一条黑狗/在野地里扒坑/都说这是老八婆家的狗/老八婆已经死了三天/才被人发觉/——这狗是替主人挖墓穴哩/大前天/她还跟我一起挖野菜/她的肋巴疼/弯不下腰来/她说她没有一个亲人”。
闻一多则认为中原诗人徐玉诺的“《将来之花园》在其种类中要算佳品,它或可以与《繁星》并肩……《夜声》《踏梦》是超等的作品”。茅盾和叶圣陶认为:他的诗歌真切地描述农民生活的惨烈,风格刚劲,带点原始性的粗犷。徐玉诺和苏金伞的诗歌,来自中原土地深处,又具有现代感,是一个时代的真实纪录。
评论家单占生先生说:“古代诗人笔下的乡村田园,多是清风明月、曲溪跃鱼的人间仙境,这与中国文人仁山智水的审美趋向有关,是中国知识分子隐逸思想的一面镜像,而真正书写农民命运的诗作并不多见。正因为是这样,我们才把杜甫笔下的乡村哀境视作诗中珍品。”
从新诗的草创期到1949年,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洗礼,逐渐具备了现代人文意识的中国新诗人,开始真正用心书写中国农民命运。代表诗人有:艾青、臧克家、徐玉诺、苏金伞等人。单占生先生又说:“对中国乡村的重新发现,尤其是乡村苦难的重新发现,对中国农民命运的强烈关注,正是中国新诗人对中国诗歌历史的巨大贡献。”正是艾青、苏金伞等人用新诗的形式终结了中国诗歌数千年来对于乡村生活的“轻”式描写,关注民生疾苦,从而使诗歌“沉”下来。他们的这些艺术贡献不仅属于诗歌,也影响到了整个艺术领域。
1949年以前乡土诗写作,艾青和苏金伞们已经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遗憾的是,解放后以及“文革”中的若干年,因为政治、运动、观念等原因,乡土诗大多变成了政治的传声筒,标语口号太多,我们暂且不论。
进入上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的这场大变革,数亿人打工进城,大离散,大拆迁,古今中外都没有。面对新的变化,新的境遇,一批新诗人迅速崛起。
这批新诗人阵容巨大,年龄跨度也很大,几乎涵盖了新时期的众多诗人群。这些新诗人与他们的前辈诗人有着很大的反差,不仅诗歌观念有差异,表现手法也更加多元,丰富。他们经过了八九十年代以来现代主义以及后现代主义的洗礼,经过了上世纪80年代以来众多艺术实践和探索,能够以全新的视角看待中国的现实和农村、农民。他们不仅抛弃了中国古代文人那种观光式的、隐逸式的、休闲式的、赞美式的乡村写作观。当下的乡村诗歌写作你已经看不到旧有的风花雪月、旧有的闲情逸致、旧有的写作观念。新诗人们也不再满足于艾青、臧克家、苏金伞们那种对于中国乡村生活的既定写作方式,以及对于农民生存的苦难与无奈的展示,从而诗意地上升为对于人的生命的终极关怀。这是一群有着开阔视野和现代意识的诗人,然而,他们的诗中却很少能看到爱恨情仇。面对伤痛的中国乡村,大变改的中国乡村,诗人们的视野变得更为开阔和广大,诗人从自身入手,用自己的内心去体悟世界,自己不再是局外人,而是带着一种温和的爱,显得自由,从容,不时地对诗人自身进行着深刻而又痛彻的反思。
这些诗人的乡村生活写作比起他们的前辈来,变得更为复杂、更为多彩,内容更为斑驳,也不再是单线条。他们改变了过去那种城市和乡村二元对立的写作观,也就是对抗“城市病”的写法,不再矫情和煽情。诗歌中有时既有乡村,也有城市的影子,有时城市和乡村纠结在一起,难以分清彼此。因为乡村和城市的界限正在变为模糊。中世纪式的安谧,宁静,已为另一种繁复、混杂的景观所代替。他们把乡村不再作为他者,而是作为自己内心的一部分,甚至是作为自己身体的一部分来抒写。这些诗表面看起来异常平静,没有激辩,没有大词,没有说理,只是娓娓道来,像是在叙家常。然而,在这平静的叙述语调背后,乡村不仅只是乡村,农民不仅仅只是农民,他们首先一个人,完整的人,一个去掉了农民工头衔和农村户口的具有普遍意义的人。
因此,他们的诗歌视野宽了,突破了以往乡村诗的狭窄地域,从而使乡土写作具有了立体感和文化意味与内涵。村前的泥泞小路不仅是属于乡村的,也是属于诗人的,也是属于全人类的,村头上那个老人的疼,不只是一个农民的疼,更是一个正常的人的疼。我们不能把这些诗人冠以乡土诗人,因为他们的诗歌不只是属于乡土,他们在处理乡土题材时,并没有把它们做为传统意义上的乡土诗来写,只是作为诗来写,只是作为人来写,作为一个大写的人来写。
比如:杨克的诗《人民》,他的诗思飞翔于当下诗歌的烂泥之上,大胸怀,大制作,大悲悯,写得结实而柔软,成为一个时代的写照,句句敲击着人的心灵,并给那些卑微的人们以诗意的抚爱。雷平阳的诗《杀狗的过程》,一个平常的杀狗事件,一般人会因为见得多而表现麻木。但经诗人道出,却是那样惊心动魄。诗人说出的事件已经大于事件本身。那血口高悬着,也许就是我们自己,就是那个“回乡奔丧的游子”。从而道出人类身上普遍的疼痛。比如我的诗《复合的人》:这首诗写的是一个农民工到城市打工,城市的繁华,造成他内心的迷茫。诗中并没有写他打工的艰辛,那是一种老旧的写法。而是以我心写他心,写他内心世界,一个农民工的内心世界,也就是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无助和迷茫。在这首诗中,你看不到城市和乡村的界限,看不到农民与市民的界限,界限消除了,只剩下一个活生生的个体的人。他以人的视角来感受城市这个陌生的世界。
1980年以后的中国乡村诗,特别是新世纪以来的乡村诗,它们除了受现代诗的影响外,也继承了五四以后中国新诗的优良品质。艾青和苏金伞们像丰碑一样立在那里,我们每一回头都能看到,我们之间的气息仍然贯通。
艺术不是进化论,并不是新的诗人就一定会比老的诗人写得好。然而,在乡村诗这个特定题材的处理上,近30年来所涌现出来的一些诗人,他们艺术成就的确超越和突破了他们的前人,也许是因为艺术观念的不同或是表现手法的差异,他们的乡村诗歌写作来得更为从容、温润、宽广,更具有人性化和现代感。
新诗100年来,经过诗人们艰苦的探索和写作实践,基本解决了新诗是什么,和怎么写的问题。我们现在的诗歌技艺,已经可以和世界接轨,不逊于任何国家和地区。放眼当下的中国诗歌,可以说唯美的、精致的、技艺的、充满才情的诗歌满眼皆是,才子诗人很多,我们的诗歌写得过于聪明。然而,我们仍然缺少大师和伟大的诗歌,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诗歌呈现出的是大面积集体的贫血,精神强力不够。
诗歌是民族的触角和精神的强力,只有精神的强力之光才能点亮诗歌之光。中国当下的诗歌需要像美国惠特曼那样精神强力的诗人,需要像李白、杜甫那样精神强力的诗人。诗人需要补钙,整个中国文学都需要补钙。
在中国乡村伟大的变革时期,应该出现伟大的诗歌和伟大诗人。
也许曙光就在前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