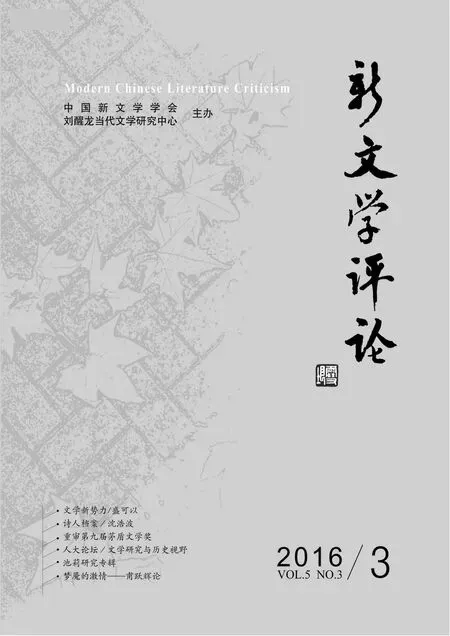贡纸、人物与文化的意义
——评孙红旗长篇小说《国楮》
◆ 王学海
贡纸、人物与文化的意义
——评孙红旗长篇小说《国楮》
◆ 王学海
中国现当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区分,主要在于近百年以白话写作的新文学为开端。但若再追溯历史,则先秦与唐宋,也是一个古代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区别,若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唐宋传奇与话本小说等。只是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由朦胧诗及现代主义、意识流等国外文学的引入,中国的文学(特别是小说诗歌),又有了一个大的改观。但毋庸争辩的是,中国白话小说的现代文学,从一开始起,就是既继承自明以来的古典话本小说的传统,又汲取了西方大量被翻译进来的翻译小说的写作手法。但不管怎么说,中国当代小说的刷新与发展,正是在中国传统古典小说基础上成长发展的。当然,中国小说发展到了今天,已经越来越西化,有的小说甚至除了还用中国文字,一切全是西化了。然小说发展到这一地步,也旋即陷入了瓶颈。由此,不少睿智的小说家,为了能突破这瓶颈状态,在作品的叙事中,嵌入了不少属于传统文化的东西,有的甚至还以传统文化为中心叙事,企望结构与书写出一篇与当下浮世的小说不同的作品来。可见,中国小说发展到今天这个状况,自传统文化汲取营养,是一个必然的趋势。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我们读到了孙红旗先生的《国楮》,这部以现代汉语为书写语言,注重古代白话的现代书写之穿插运用,并以此“双重”语言来体现小说中人物的生命体验,去凸显人的内心世界及自由追求精神,自有一番与众不同的特殊情趣。
毋庸讳言,《国楮》作者在小说创作中首先存在当代语言与历史话语及书写的对接问题。它首先让我们在读惯了新文学之后的小说后,又以此文本为我们置换了一个独特的阅读空间,即用古代白话为基调的现代汉语写作,使我们阅读的审美指针一下逆转到了具有《红楼梦》成书年代的那种历史韵味。并从中建立起一个重新认识中国古代与近代白话小说共融的审美境界。《国楮》的小说语言,作为文学语言(而非日常交际语言),注重语言的思想本体性,即在作品中让“语言说”,具体就在于古代汉语的现代运用的巧妙穿插。在一定的意义上,人选择语言是由时代所决定的,但作为作家,他在使用语言时就由创作思想去决定语言的运用,所以在文本中,作者试图由语言的角度、方向这两个层面上去伸展它自身的魔力——作为文学的“语言说”,《国楮》试图去做的,是古代汉语在现代汉语叙述中的“历史运用”,从而让小说更具中国性。有研究已证明,中国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之区别,根本上就是古代汉语被转换成现代汉语的写作,然《国楮》的可贵之处,竟在于证明这个转换不是唯一的、铁定的,这是因为古代汉语的语言思想性是可以在现代汉语书写中延续的。在改革开放半个世纪以来,国外的文化哲学思潮,连同文学的新名词,正像当年“五四”新文化运动那样,新名词新思想爆炸似地响彻并迅速统领了中国文学的前行。但这一热过后,文学创作重新回到常态化时,随着国学热的掀起,不少作家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创作路向,即全面西化的小说创作既让中国小说掉进了一个怪圈,又严峻地向具有思想的中国作家提出了照搬西化方式的小说家创作是否有本土意义这样尖锐的反思性问题。因为我们毕竟是中国,中国应该有自己本土特色的小说,而不是借着与世界接轨,小说完全成为西方的小说,好像中国古代没有小说一样。而且若把这些小说翻译到国外就一点也看不到“中国味道”。为此,《国楮》这一古代汉语在现代汉语写作中的穿插运用,我把它概括为“历史运用”,从中国小说自身发展的趋势看,是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中国的小说,汉魏六朝就已大量涌现,如《搜神记》、《幽明录》、《拾遗记》、《世说新语》等,至唐代传奇小说是一个顶峰。实际上,至明代,话本小说“三言二拍”均是古代的白话小说,而至《聊斋》及后来的四大名著,语言上的运用更是如此。所以,以现代汉语写作,间杂回到古代白话小说,“美声与民族唱法的混搭”,这样的创作方法在当下,不失为一种新的寻根小说。
此外,《国楮》虽洋洋38万字,但在语言运用上尚知“节俭”。如讲绍熙贡纸、开阳古城,作者并没有通过史料和地方志,把大量的材料罗列于小说之中而造成大肆的语言铺张之趋,这又是值得肯定的一个方面。
《国楮》开首即以连四纸以价廉物美的后赶趋势纷纷抢占绍熙纸原有的生意地盘,并以绍熙纸的掌门人延誉的长子元煦因与玉蝶儿的私情而被土匪黄金洪砸匾的两大情节的同时展开,为我们翻开了往昔国纸——开阳绍熙贡纸很不平常的生存与成长的近代史实。自然,每一部小说总归有一个或几个故事,然每一部小说,怎样去结构故事,却总是这部小说成败甚至优劣的关键。所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国楮》的故事叙述,并非古典小说传统意义上的具有惊险加噱头的说书般的叙述,而是以某些人物的突兀出现,故意打乱故事线性的铺陈,让我们在散乱中拾起更多的体验。譬如元煦与玉蝶儿的私情,原来是中国文学作品中才子佳人相约青楼的一种惯例,但从中突然闹出个乃香来,似疯非疯,似侠非侠,一样地痴情但又非比常性地出格,这样的搅局,便给小说增加了无穷的可塑性。又如开阳绍熙纸行延誉是一个主角,接棒的元煦是B角,猛然间又弄出元靖来,这个不温不火、沉闷偏傻相的二子,一忽儿语言结巴,一忽儿身弱易病,然一忽儿又聪明绝顶,一忽儿竟身怀侦探大智,这样的附加角色,无疑是故意不让故事顺势衔接,它故意撞坏了传统中国小说环环相扣的陈式,其荡开的无限性中,正是现代小说理念在试用传统白话小说构成中的一种气质性的显现,是诡谲引发细节的生成性作业。
《国楮》的另一个特色是它以故事的发展推动着扩张着小说的表现力。前面谈到开首的连四纸在纸张制造上简化工艺,降低成本,抢占市场,予绍熙纸巨大压力,紧接着好端端又由元煦交友及其扯出邸抄,共同营造了又一个绍熙贡纸绝处逢生的新转机及惊天大案。因为邸抄,绍熙贡纸一下又有了新的更大的市场,因为邸抄的被阴谋[将两篇悖论之文置于一刊(王锡候案与乾隆帝诏罗藏书)],元熙给徐府带来了灭顶之灾——整个徐府上上下下全被押进了牢房,并有满门抄斩之祸。但也正是这节外生枝、波澜起伏的惊险故事,小说的顺势故事情节被其打乱。而在这乱中,作者恰恰又可借势从中营造更大的气场。这就像音乐中的二重奏三重奏甚至四重奏一样,一个故事被打乱,另一个故事竟又会砍劈出一个更为生动宽广的场景,并从中又让读者去费力寻找可能的联系,从而能让读者的视野在树干枝蔓、杂草乱沟中作着与小说双向互动的大胆想象与审美判断。这里面又不得不提到《芥子园画传》与砸匾的故事。一个原本平常的传统的才子佳人青楼红粉的故事,由于《芥子园画传》这个开阳绍熙贡纸珍本与粗蛮杀人土匪首先在故事中形成了巨大的反差,接着恰由这个粗人土匪意外从《芥子园画传》上,以逻辑的推理寻找出了被自己梳拢的女人养着的小白脸是绍熙纸行的元煦,并发展出惊悚的故事情节:一白面书生,一杀人土匪在红粉佳人卧室中的正面冲突,引出了更加出乎人意料之外的结局,即原本要由土匪杀夺人所爱的死对头的刀,改由土匪自己剌自己一刀而收场,这不啻是一种现代性的构成在中国式传统文化故事中的闪现,这样的处理,无疑更具有阅读的意义。
再回到邸抄,正因为元煦看到了邸抄的绍熙纸的市场生机,所以他不惜奔波于京杭之间又准备说服父亲大肆推行制造适合邸抄独用的绍熙市场纸而非贡纸。正因邸抄,让竞争对手有了图谋欲加之罪的诡计。自然,我们很快就会看出来,这不是追求数量的长篇之故事凑故事,而是故事中连环式扩张,是情节与细节有机的滑伸。我们知道,小说里的故事,并非民间故事里的故事,小说里的故事,是小说结构的重要部分,也是营铸小说品质的元素。我非常警觉地注意到,作者孙红旗先生在故事这一结构的运作上,他似乎正在考虑避免现代性小说彻底把故事打乱,而导致故事游弋得不知所云而逃离了读者的现状,所以他在《国楮》中既以现代小说写作手法实验之,又避免任性意与扩大化,所以他的故事既有突破传统小说常规的实验,又不完全依照现代、后现代、实验小说等非常西化的小说写作手法去照搬照写。所以你说他的《国楮》里有故事,确实是一个连着一个,从连四纸与绍熙贡纸之争,到元煦与三个女人的故事;从元靖与放鸽子,元靖与月婷读书,到元靖赶考先头名后失头名;从邸抄到爆出商场的生机,到徐府的灭门之灾,故事确是一个连着一个。然这些故事的组合与排列,这些故事的顺小说之势的开讲,又非完全按照传统白话小说的写作手法。它一会儿顺势沿进,一忽儿被打散遁影。一忽儿高潮迭起,险象环生,一忽儿又游弋无际,支离无架,并且,细细研读,我们又会发现,孙红旗先生在处理这些环环相扣与细节时,往往或双事共向呈现,或单事乱头转向,或故事刚要出局又新象滋生,或新出悬念瞬间把故事的澄明又一次搅浑。这一切,当然也显示了孙红旗先生创作小说的能力。并且,由于作者创作时的动机是刻意让现代小说回到传统白话小说的纯中国品性中去,所以,在小说结构的故事引伸或延宕处,作者往往别出心裁地以大量的押韵古诗作为故事行进或称小说结构的环链,这样,既避免了陷于太传统的习惯性陈旧纠缠泥淖之中,又开凿了浓浓的中国文化新意的诗意创作。这应是《国楮》的第三个特色。我国的四大名著,《西游记》之所以脍炙人口,是因为在游戏之中劝学谈禅,识恶护善,神话之下又食人间之烟火。《三国演义》或云天下黎民,或汉室宗亲,智慧奸诈,讲道护法,无一不在天理人情之中。然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一把羽扇借得长江东风,凡此种种,亦在《国楮》中有所体现。书中人物朱筠、方戬节以“从简牍到缣帛,从蔡侯纸到‘三坟五典’、‘八素九上’,这一切都有懒于传承”为中心话题,以吟诗答对重新开创中国小说的文学生态,以仕女变魔魅勾勒出小说铺陈的人世惊变。此种手法,宛如明清之交文人流行的“游幕”方式,于徐渭、方文、朱彝尊们的种种,借书中的或吟诗诵读,或落笔生画,把商场竞争、官场互庇、家事衣食、人间情事演绎得既古色古香,又生态鲜溢。且从中频添了中华传统中之优秀文化的遗香,这兴许是《国楮》的又一特色。是作者叙述方式——将故事散杂化再回归传统的一大创新。
《国楮》中有两个人物,其出格的魔力,当是长篇的又一亮点。首先是元靖,这个人物在他与月婷一起成长学习及其说话结巴,嘴角常淌涎水时,我还以为这个人物是生硬的刻意为之,似乎故意给书中添加一点胡椒似的,倒少了感觉不对味,倒多了又呛气管。一句话,生硬之中呈现着做与制的不良感觉。直到某一天元靖连考三场顺利夺魁,而到最关键的省考一场因身体素质与月婷突然夭折带来的心灵打击等诸多原因,原本聪明绝顶、天生夺魁的元靖,只拿了个增生。之后,他仅只把全副精力与聪慧天资全部用于继承和复兴绍熙贡纸上,我们才对元靖这个人物的看法有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而也只在到这时候(份上),我们才真正认识(认可)这个“被生硬”的人物,原来是一个隐喻极深的文化人物——他有极高天赋进入传统文化,并以古代名贤之痴呆怪相出现在小说之中。每当生活起有风波,或者日常须待理性时,他总是以其不起眼之势力,爆出冷门,彰显国学。又以潜行的方式,出现于大众日常生活之中,故于书香门第是不极品的宠儿,于普通人群是不入俗流的病相,如此形相,实有嵇康阮籍之玩,八大张旭之癫,而又自成一个元靖。他不是道德的判官,却是伦理的严格践行者;他不是国学的专门导师,却是个满腹经纶的谦谦君子;他不是侠士快捕,却是个嫉恶如仇的汉子勇士。并且我更看重的是这个人物的背后:在这个人物的背后,是作者重新诠释传统文化的灵魂,是传统文化令他激动,令他神往也令他颤慄的那种澎湃的心绪。是作者内心神往的中华传统文化的深深庭园的缩影。
《国楮》还有一个是以行动来强化说话的奇特形象人物,那就是乃香。不要以为她只是看戏、嗑瓜子、偷汉子又不顾家庭死活的放荡女人的典型,她可是一个敢说敢做又敢担当的侠义心肠的奇女子,她对元煦之爱的大胆与疯狂,她处理父亲去徐府大闹即将出人命时石破天惊的意外方式,她酷爱艺术的单纯与痴迷,她悄悄离家行走江湖的侠骨柔心与无畏精神,给了作者笔下这位人物许多僭越式的魔力,无论是她的姑娘身份,她的知识修养,她的家庭处境,还是她的相同于常人的日后生活处境,看似平常乃至有点平庸,读时觉得一般却又有点意外。她是在作者别出心裁的创作心理中强势成长的。如果说玉蝶儿是个写实的人物,那么,乃香就是个写意的人物。她的饱满,在于几个特殊的细节,她的深度,在于几个出格的场景。其实,乃香和许多年轻姑娘一样,有爱美的天性和幸福的理想,只不过因为不能做家务活,结婚仅一个月就被一纸休书赶出了家门,所以,乃香首先是一个受害者,遇到了元煦,她不仅压抑的心灵得到了释放,那种追求纯真的精神,非常强烈地投射在了她的简笔式的言行之中。她仿佛要在新的生活起航中证明,自己别无所求地铲除庸俗,更在于能用自己的力量得到一份真诚的爱,并以此证明自己的不可被奴役性。为此,她可以不顾唾骂依然我行我素,她也可以在紧要关头、众目睽睽之下,不顾私利而断然于明智。在《国楮》中,作者予乃香最为绝妙的两笔,一是她在调停父亲与徐家正面冲突时,说了一个“一奇女,衣毛为飞鸟,脱毛为女人,此女便是女岐了”的故事,和她求方戬节打胎时说梦见自己在金龙潭洗澡,遇一僧人的荒诞奇遇。一是她在前一日还是端正坐着看戏,放开嗓子学戏,后一日竟悄无声息地隐遁而去。这种现代魔幻主义的小说写作手法,无疑给《国楮》中的人物,增添了与其他小说人物各别有殊的差别。乃香与元煦,这一段孽缘,在本质上其实就是一种虚幻,但乃香这个人物却使这虚幻之中另生出一种真诚地追求真实之可能与可行。故乃香的消失,其实是无常的毁灭,但在这无常的毁灭之中,也可说在人海茫茫的冥冥之中,它又是一种生命的不朽,是个我与社会挣扎与抗争之中的独特的闪光。
这是《国楮》在人物塑造上的特色。
最后,《国楮》另一个闪光点,是作者写家乡。在青石板走去的孔埠驿站,我们仿佛可以依旧闻到历史扬起的尘埃;在开阳城夜晚的荷花塘畔,卧佛山下,我们可以乘着月色尽享清丽幽静与禅意秋深;在清晨棒槌声四起的西渠,我们可以想象到农妇村姑大户丫环们比早的身影与叫碎一天晨曦的甜脆的声音;在三十五都的七个古村落中,我们可以充分领略开阳城乡旧时的繁华和商业经济的兴盛;在开阳绍熙贡纸特殊的配方与精细的工序里,我们读的是一本走不到边的历史——皇家的用纸与中国第一纸的身份确立与历史沿革;阅读凤凰山文塔的那些许诗性的描述,作者对开化县城美丽的山川风光、人文历史的美文书写,还有待于审美的眼光去不断探测,不断去发现……这是作者的文学关怀,也是家乡情结;是历史主义的艺术显现,现实状态下的历史追怀;是作者家乡情景空灵曼妙的审美,记忆与遥望的真切情怀;是作者对家乡历史积淀与未来建设的深情释怀,美丽胜迹的情感寄托与理性梳理。所以,与其说是作者在《国楮》中写家乡,应该正确地说是作为家乡人的作家,进行的当下背景与家乡历史文化的对话,这是乡土意识与文学创作心态的一次思想碰撞与原创性的互动,它在追怀中滋生新的生态,是反思中情感与理想的呈现。
此外,不得不提的是书中不能让人遗漏的一个人物,那就是作者不露声色地刻画的地方官王维鼎,有了他,被打乱打散的故事可以重新开始梳理,有了他,一些难以支撑挺进的情节可以自然地开合。尤其是面对徐延誉要用明代砚滴行贿王维鼎时,王维鼎说:“我当着徐先生的面,把这尊砚滴给砸了。”表现得正义凛然,随后徐延誉与方戬节谈论乾隆不断尚廉,惩处贪官,将索典案牵出一大批原本多多少少对朝廷有过贡献的官员绳之以法,这样的前后呼应,使王维鼎这个陪衬人物亦有饱满的状态和铺陈的力量。
在阅读《国楮》行将结束的时候,我突然想起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小说家哈金(Ha Jin)这个深受中国小说影响,又试着要创建伟大的美国小说的作家,曾经说过这么一段话:“一部关于中国人经验的长篇小说,其中对人物和生活的描述如此深刻、丰富、真确,富有同情心,使得每一个有感情、有文化的中国人都能在故事中找到认同感。”这份感受与我阅读孙红旗先生的长篇《国楮》是那样地吻合。《国楮》以小说的形式,向我们传递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譬若邸抄的兴起与官方内刊与报纸的历史渊源,绍熙贡纸与中国古代珍本及《四库全书》的重要作用,清皇朝期间,特别是乾隆执政期间,大力推行廉政治吏的法不容情的事例,绍熙贡纸与其他亦有名有质地的纸张的特色与区别,及以朱筠、方戬节为代表的人物传递的国学、中医药方面的传统文化,并以月婷之死,玉蝶儿以绍熙贡纸捻搓成线上吊而亡的故事,给我们带来恰似重温四大名著与“三言二拍”、《新序》、《说苑》等带给我们的中国小说的启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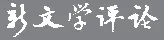
湖南理工学院,浙江海宁文联《文学地图》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