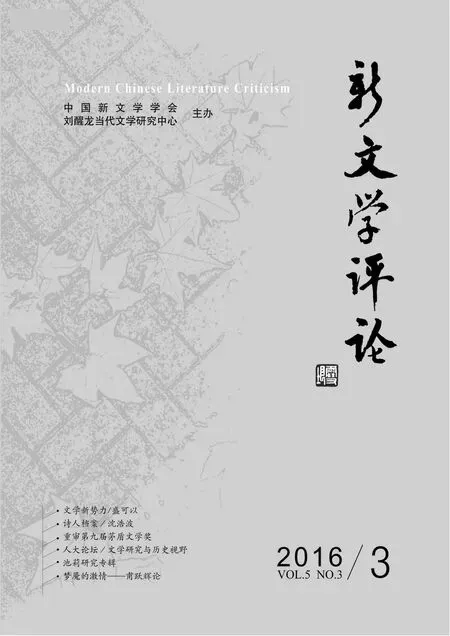梦魇的激情
——甫跃辉论
◆ 宋夜雨
梦魇的激情
——甫跃辉论
◆ 宋夜雨
甫跃辉笔下的人物似乎总爱做梦,少年梦,成年梦,从彩云之南到上海外滩,梦境不断被访问。梦成了甫跃辉小说内在装置的重要一环,成为甫跃辉作为风格标识的写作技巧的一个侧面。梦,甚至成了甫跃辉小说表达的特殊嗜好。甫跃辉的人物离不开梦,梦成了他们生活中难以割舍的一部分。甫跃辉的小说有着类似于卡夫卡“梦与真实的混合”①的元素。就像甫跃辉自己说的:“这些梦是我生活的一部分。他们和我在白天里的生活,构成了某种微妙的呼应或者互补。”②事实上,生活可不就是一个梦吗?
如果说梦作为一种写作元素在少数文本中的零星出现可以视作作家小说文本处理时的偶然性选择的话,那么梦的文本延续性在甫跃辉的小说中事实上已经形成了一条鲜明的情感脉络,进一步说,形成了一种自足的文本传统。这样说来,梦既是甫跃辉写作的一种既定局面,也是我们反观甫跃辉小说内里的一把钥匙。这就涉及我们该如何对一个作家尤其是那些相对年轻并且尚未取得某种写作权威性的作家进行审美经验的判断。作为文学参与主体的作家,从哪里来,又往何处去?他能带给我们怎样的文学经验,以及这种经验中能够传递出怎样的“惊奇”效果?
对一个作家的判断,首先要从小说文本的限度中剥离出作家站立的位置,即作家的“写作之夜”。作家与作家的区别,正是在于这一观看世相的角度不同。要想了解一个作家作品的意义,必须先去寻找作家内在世界的规则和秩序。位置的特定决定了作家回溯往事的路径,感知当下的“此时此刻”的准确性,以及憧憬未来的想象可能性。从时间上来看,1984年生的甫跃辉已经过了而立之年,他已经具备了在“岁月的遗照”中“追忆似水年华”的能力;从空间来看,在云南、上海的地域流转中,甫跃辉完成了生存境遇的一次迁徙。几千公里的路途不仅是怀乡的距离障碍,更为重要的是地域性同时也意味着差异性,意味着一个人思想、意识、认知、生活习性在两种生存境遇遭遇碰撞时的巨大调整与适应,而在这种边乡—都市的生活差异的比照摩擦中,作家就会对生命经验进行回溯与内化,从而形成重构世界的个人化角度,形成表达自我的自觉意识。就此而言,甫跃辉全部的写作历史呈现出了自主鲜明的分类场域,一类是以时间距离为分寸的边乡背景小说,一类是以内心距离为倚重的都市背景小说。边乡是甫跃辉梦境缘起的故土家园,都市是甫跃辉梦境成魇的此在时空。
一、 梦境的故土
处女作《少年游》(《山花》2006年第9期)是甫跃辉“访问梦境”的开始。小说是以乡村小镇(柳浪镇)为背景,故事是从“我”的一次离家出走开始的,但离家并非出于年少无知的任性,而是出于“我”想象世界的某种“清醒”,想象的起飞某种程度上就是梦开始的时候,一个人开始做梦也就是开始成长。在以世界为想象对象的内力驱动下,小说实际关涉的是人的成长以及在少年的成长语境中与世界、他人遭遇的内在反应。小说中,父亲与“我”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亲情对话关系,父亲的威严实际上成了“我”想象世界的巨大障碍,此时想象于“我”而言意味着突围与冲决。所以,在承受父亲的“一顿老拳”之后,我意识到“必须反抗”、“必须成为一个大人”,而成人与孩童的落差其实是人的独立性、自由度的限度问题。那么,走向成人的第一步首先就是摆脱对家庭的依附,对自己的选择作出独立的决断,以便寻求更加独立的自由,由此,“我”在“离家出走”与“成人地位”之间预设了一种单纯的必然性,“一门心思认定离家出走能为我争取到大人的地位”。然而,“我”的少年梦并不是美好的。除却父亲的威严这种外在压力,那些走进“我”内心深处、“我”却无法挽留最终又不断离去的人在生活与我之间构置了更大的障碍。实际上,这才是小说纠缠扭结的张力所在。“我”和舟舟、大有,悠悠、小木头和“我”这两重关系网把“我”紧紧裹挟着,置身其中,“我”无法抽离。大有强奸了舟舟,舟舟外嫁远方,这些事件在成长之路上不断割伤“我”,而“我”无能为力。小木头、悠悠的接连远走更让“我”陷入孤绝封闭的处境,“我”渐渐意识到世界的飘忽,长大是一件多么让人惴惴不安难以把握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我怕什么,就是觉得不安全”。生活既实有又虚存,看不见摸不着,而我们又确确实实深陷其中。我们所理解的生活,或者说,我们内心想要的生活,其实是对生活的把握诉求,而我们生活的形式其实就是与他者的交流关系的纠缠编织。所以,小说与其说是把握生活,不如说是把握那些与我们不断遭遇又不断远去的人。时间就像一把盐,不停地在“我”受伤的胸口播撒、消融。成长是一件多么荒谬的事啊,开始我们寻求把握世界的方式,长大了才发现世界根本就无从把握,而人“唯一具备的把握便是无把握的智慧”③。我们与世界遭遇,又擦肩而过,我们只有在时间的不断流逝中不断失去,让失去的东西沉淀为记忆与岁月。小说更加警醒我们的是,一个人在与世界初次遭遇之后,他认知世界的态度、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初具形态了,而这种形态从人的整个生命而言是悲剧的。从这里,我们可以从甫跃辉的小说历史中辨识出某种内在的连贯性。《少年游》中的“我”与甫跃辉似乎存在一种同步的精神比照,“我”的成长与甫跃辉的小说写作存在一种内含的对话关系。《少年游》作为处女作毫无疑问可以视为甫跃辉小说写作成长的开始,是小说梦的开始,而《少年游》小说本身也是关涉成长本身,两相比照,小说本身的重量与给人的踏实感的文本形象清晰可辨。
《少年游》之后,甫跃辉逐渐养成了边乡叙事的自觉。《鱼王》(中篇小说集,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3年12月出版)、《散佚的族谱》(安徽文艺出版社2014年1月出版)、《刻舟记》(长篇小说,文汇出版社2013年2月出版)三部集子所收录的小说全都以边乡为叙事背景,这足以见得边乡作为一种血肉相连的根脉在甫跃辉写作心理上的重量。当然,相当数量的边乡小说并不仅仅是甫跃辉怀乡病的一次喷发,我想这种叙事的自觉很大程度上源于甫跃辉对自我生命来路的深刻体认。一个人所经历的岁月并不完全就是他自己的,时间流逝中的生命经验有赖于人的记忆不断回望、不断咀嚼、不断沉淀。记忆既是一种写作体认的路径方式,也是写作的能量与源泉,要知道“一切文学最终都来源于历史的回忆”④。而另一方面,在记忆中观望,也是我们此在的调整与面向未来的选择。《散佚的族谱》所收《收获日》、《庸常岁月》、《八月》、《暖雪》、《我的莲花盛开的村庄》俱可称为乡村传奇,然而甫跃辉所铸力的并不在于这些小说的故事性、传奇性本身,而是力图在庸常的乡村日常性中把握相对自足的乡村形态、乡村伦理,用自己的生存体验展开乡村的生存逻辑想象,尤其是对有血有肉的乡村人命运的把握和呈现。
《收获日》也是从一个梦开始的:“睡在另一张床上的儿子同样感到了光的刺激,但他固执地抱住梦境,很不乐意地翻了个身,背对灯光,试图重温灯光打断的好梦:一个大青皮雪梨,一间敞亮的房间,且房间里只有他一个人。他毫不客气地在雪梨丰硕的腹部咬了一口,饱满的汁液涌出来,甜甜的,触到舌尖的一刹那几乎令他晕眩……灯光一照,硕大的雪梨倏然飘远,消逝成一个淡淡的点。他认出那是窗外的月光,很懊恼地闭上眼睛,努力回味舌尖的感觉。”刘瑞明一个简单纯净的梦无意间却说出了乡村最为本质的秘密——贫乏。贫乏的不是外在的生活形态,贫乏的实际上是乡村人面对生活选择时的内在驱动力。小说描摹了云南一座小乡村人的生存境遇,通过张成军娶亲、乔老太出殡、老黑杀猪、李惠文割稻等一系列事件勾连起一个完整的乡村生活图景。在这里,甫跃辉始终警醒自己的叙事节奏与乡村的生活形态保持一致,那就是在各个叙事层面不刻意突出某一方面,通过各个叙事层面的平行运动、相互缠绕来获取对乡村生活的经验判断。每一篇小说都有作家最想表达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其实也是小说的灵魂,它有可能是一句话,也有可能并不是文字的实有,而是一种看不见摸不着却能感觉得到的一种气氛、味道,一种态度。具体到《收获日》,甫跃辉最想说出的那句话可能就是 “这日子怎么过?”小说的题目饶有兴味,我们不禁要问,“收获日”收获的到底是什么呢?甫跃辉的乡村叙事不着力于乡村伦理、乡村秩序的形态重构,他所关注的是乡村男女的生存命运以及在生存境遇的动乱之中那些乡村男女的深刻心理变化。而他所收获的正是乡村男女在生存命运中的无能为力、与生活的和解、与命运的和解,收获正是对命运和解的深刻体认。赵翠兰跟丈夫张年生生活了一辈子,却毫无夫妻情感的内在互动,无法理解、无从沟通,夫妻对于他们而言已经最大限度地简省为一种必要的生活形式。“大半辈子了,她仍旧不知道跟自己的丈夫有什么好说的,除却生活上的事。大半辈子了,真真除了油盐柴米酱醋茶,她跟他再没说过什么。没事可说的时候,他们之间就只剩下沉默,长久的沉默。她熟悉他无语的喘息,他也该熟悉她无语的喘息。无语的喘息弥漫在他们之间,她嘴里呼出的空气,他又吸进嘴里;他嘴里呼出的空气,她也吸进嘴里。他熟悉她的气味,她也熟悉他的气味。大半辈子了!他们在彼此的气味中喘息着过活着,这多少让她有些感动,却也让她感到悲哀。”夫妻最熟悉的是彼此的生活习性而不是内在人格的对话交流,岁月的共同经历与共享成为两个人唯一可以相互抚慰的夫妻情谊。赵翠兰感到悲哀,可又能怎样呢?与岁月的无情相比,命运的扭转毫无可能性而言,赵翠兰只能接受命运,与自我和解,寻求生活下去的动力,在迷惘的生活中,时间既是消耗生命的无可挽回的力量,又是人委身其中获取安慰的一种希望。乔老太被两个儿子抛弃,处于饥饿的边缘,但她仍然顽强地活着,而当她延请小阿炳为自己挑选一块风水宝地以求荫蔽自己的曾孙拾来后,她放心地死去了。拾来成为乔老太活着的唯一希望,在生命即将终结的边缘时刻,乔老太的生活希望却并未同步走向幻灭,相反,它仍在承续。丈夫早逝,儿子不孝,作为一个女人,在岁月的漫长等待中,乔老太怎能不绝望?所以,当李惠文询问乔老太那个安慰了她半生的白马的故事的时候,她才会咬牙切齿地说出那句“都是狗屁”。一句“狗屁”既道出了生活的虚无本质,又表现出人置身其中无法抽离的矛盾性、无力感。可绝望的获取并不代表生命意义的终结,绝望只是生命的一次确证。如果说生命是有意义的话,那么意义就在于人在生活绝望的心理认知下,是否能够重拾继续生活的勇气。就此而言,拾来就是乔老太重拾的“勇气”。一个人有了牵挂就有生活的热情,所以无论不孝的儿子多么残酷,乔老太都能承受。而乔老太对孙辈的寄望在某种程度上也完成了家族内部的命运承续,而家族传递也正是乡村伦理形构的一种方式。李惠文对这个村子从一开始就显得格格不入,因为她不是顺从自己的意愿嫁到这里,她的出嫁完全出于难言之隐。她始终“生活在别处”,丈夫儿子对她而言不是生活的安慰,而是生活的障碍,她的心属于那个叫吴作栋的人。可当她真正见到日思夜想的吴作栋的时候,猛然发现物是人非,人已经不是那个人了。此时,世界对于李惠文而言简直已经轰毁了,所有的念想、牵挂、希望都落空了,她感叹“今年的月亮没去年的圆”,可“人活一辈子,哪个能不带残疾不带疤?”越是执念,人越是痛苦,要重新生活就要首先放下执念与自我和解。王副官的生活道出了乡村人最为深刻的悲哀。自己在前线打仗,断臂回家发现自己老婆怀了别人的孩子。这对于男人而言是莫大的耻辱与伤害,更可悲的是考虑到妻子的身体,还得把孩子生养下来。最后,当王副官准备报仇的时候,妻子的劝慰又再次让他收手了,他只是对着墙放了一枪。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受到莫大屈辱的王副官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妥协呢?是软弱吗?还是生活本身就存在一种和解的引诱?我想,当王知非喊出那句“爹,我们回家吧”的时候,王副官的心肯定碎裂了。他面临着一次选择,是执念于旧恨,还是完全放下嫌隙接纳这个家庭,重归生活秩序。乡村人似乎被一种悖论式的命运世代折磨着,“可是没有瞎话,这日子还怎么过?可是为了瞎话过日子,这日子又有什么滋味?”小说的深刻性,正是在于将人置于命运无常的两难境地,以及在两难之中人究竟如何回应、如何抉择。《八月》有着相似的困惑。柳叶的儿子小龙不幸溺水,无辜死去,柳叶当着众人的面质问王大庆的儿子兴旺,可当兴旺做出一种模棱两可的回应之后,柳叶却说“算了”,“柳叶回头定定地望着兴旺的眼睛,很虚弱,又似乎很失望、很温柔地说,不是他,不是”。无疑,此时的柳叶内心是异常复杂的。她既痛苦,儿子无辜死去,死因不明;又要抑制痛苦的冲击,她要保持清醒,讨回一个公道。那“算了”是什么意思?是宽宥还是容忍还是绝望?一句“算了”足以见得柳叶是个好女人。兴旺作为一个涉世未深的孩子,在众人面前被质问,是说出真相还是维护自我,他的内心经历着多种力量的对冲,“眼角明亮地一闪,一种类似愧悔、乞求或者幸福的东西也随之一闪。——他几乎点头。”他的灵魂正在经受着作为人最为根本的是非观念、道德伦理的拷打。对此,柳叶是感知得到的,从这个角度而言,柳叶的“算了”是对一个无知的孩子的灵魂宽宥。然而,不仅此也,在经历漫长的等待仍然得不到兴旺正面的回答之后,柳叶已经失望了,甚至是绝望。柳叶绝望的是人自私自利的本性,这让人无可奈何、无能为力。柳叶是伤害的直接承受者,并且她又面临着是否继续逼迫、伤害兴旺的选择,换言之,就是是否以牙还牙反过来再从自身的伤害中对兴旺追加更多的伤害?庆幸又可悲的是,她没有这么做。诚然,柳叶的内心也经历过一次天翻地覆的和解。“算了”,就是和解,但和解绝不是对命运的自甘与妥协,进退维谷,人总要生活下去吧。小说不仅在拷打兴旺、拷问柳叶的灵魂,生活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兴旺、不是柳叶呢?小说开头,可以说兴旺与柳叶的母子关系是近乎诗意近乎亲情的,可当悲剧发生之时,这种关系共同体瞬间瓦解,这才是让人警醒、让人虚汗直冒的地方。就像昆德拉说的,“在现代世界,丑陋无处不在,它被习惯仁慈地遮掩了,但却在所有不幸的时刻突然出现”⑤。我们不仅要从审美经验出发观看小说的丰富性,更要从小说的内里反观深处现代性矛盾中的人性的复杂性。《庸常岁月》正如标题本身,小说叙述的就是乡村庸碌的日常形态,无非是家庭的生存境遇、生活琐事,但,甫跃辉专注的其实是庸常岁月里女人的生存状态与命运变迁。齐玉秀从县城边嫁到这个小山村,开始了一个乡村妇女的生活模式。然而,甫跃辉并未让玉秀落入相夫教子的生活俗套中,而是突出玉秀在一系列的家庭变故中的个人主体性,表现玉秀对生活的主动回应以及在与丈夫、婆婆、孩子、丈夫的旧情人、邻里这些多重关系的碰撞中鲜活的内心情感与真实的生活行动,从而完成一个乡村妇女对命运进行深刻体认的血肉形象的塑造。小说一开头,玉秀就做起了“回春”梦,“鲜红的石榴花是微微绽开的年轻的嘴唇”,可玉秀突然又意识到“自己的嘴唇已经四十五岁了,四十五岁的嘴唇还有一点点鲜红吗?”玉秀的一问不禁让人心头一震,让人不得不怀疑。女人,究竟是什么呢?女人,真的就是那个被过分地填充了社会的、文化的、道德的、伦理的、历史的、性别的多样元素的女人吗?“女人”,这个词,似乎经不起玉秀这么略带伤感的一问。可以说,玉秀的一问让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深处历史成规之中的“女人”的真实内含。我们需要在历史、文化、社会语境中进行剥离辨析,还原“女人”的真实面孔,而玉秀是我们进行小说探险的引路人。在玉秀的身上,存在着一种鲜明的个性特点——清醒。在与李桂芬的“明争暗斗”下、在与丈夫曹万川的夫妻矛盾中、在与婆婆小姑子的家庭纷扰中、在与孩子的母子关系中,玉秀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生命感知力,她能敏感地捕捉到与他人关系碰撞遭遇之后的自己内心深处暗涌的心理状态。清醒对于生活而言是必需的,而过分的清醒是可怕的。因为清醒既让人拥有把握生活的能力,同时也不可避免地让人具备洞察人性黑暗的可能。玉秀的清醒是可怕的。在跟丈夫合影之后,“玉秀的手指久久停留在相片里女人的脸上,心想,那一个我到哪儿去了”;在姑婆知道自己一直忙碌照相的事之后,“玉秀不说什么,心里却禁不住有些委屈,被他们误会、被他们骂时也没感觉委屈,怎么这会儿反倒委屈了?玉秀想,自己是不是真的很贱”;当看到村口给孩子喂奶的女人之后,“玉秀心里说不出的厌恶,厌恶中又有点恐惧,自己会不会也变成这样一个女人?是不是在曹万川眼里,自己已经跟这个女人差不多了?”玉秀是孤独的,她的孤独在于在人性复杂关系的碰撞中获得一种意识的自觉,那就是自我只能固守在自我的全部之中,自我不可能与他者实现沟通理解的彻底性永恒性,不可能从生活的别处寻求解脱之道。玉秀的孤独是在生活的表层下内心深处那种难以言说的人的根本性的孤独。人越是清醒,越是孤独。玉秀看得太清了,因而她柔弱的身体里总是氤氲着一种淡淡的感伤,这种感伤相似于子君的伤逝式的感伤。而感伤之余,玉秀丝毫没有沉沦下去,她在挣扎,她在维护自己身为女人的尊严。那么,什么是女人的尊严呢?在女人的世界,男人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无情的时间,是漫长的时间中人的平庸,是美的不再与消逝。女人的尊严既有作为人所要求的尊严的普遍性,又有女性特有的对于美的追求与热爱。而美总会流逝,当时间的永逝成为生命的内在意识觉醒的时候,人便是悲剧的。容颜并不只是容颜,容颜更是一个女人在人世之中活过一回的见证,是女人绽放又凋零的生命镜像,是女人骄傲的感伤。大概,每个女人都要经历一次由容颜触及生命的失落,只有经历生命的失落,女人才会明白到底什么才是女人。正如小说的结尾,“可说到底,女人是什么?玉秀忽然就莫名其妙地想,女人是由血到血的过程。由血开始,由血结束。”经历、明白其实就是豁然,当一个人的眼睛变得豁然,她生活的道路才会变得宽阔,她才能在失落之余继续走下去。“二十五年漫长的光阴消逝以后,玉秀想,再见,就是永不再见,就是开始一段新的行程。是强烈的悲伤,却也是强烈的欢喜。”
梦境对应着两种现实,历史与当下,或者说,记忆与生活。边乡是甫跃辉的记忆之由,一方面,梦境成了甫跃辉回溯生命来路、触摸故土家园、展开记忆想象的内在方式与途径;另一方面,梦境也成了甫跃辉处理小说肌理的必要手段。由于时间与空间作为距离的存在,事实上,边乡故土本身已经构成了缀连着甫跃辉个人生命的一个梦,此时此在,边乡就是一个梦境。回望边乡不仅仅是对乡土人情的描摹与再现、对乡村伦理秩序的考察与重构,更重要的是回望的主体性明确了甫跃辉与故土、与乡村伦理秩序中的人的生存意义、人的命运悲剧的对话互动关系。故土不仅是曾经外在的生存空间,更是我们在生存的困境之中能够反身其中寻求力量与安慰的内在空间。事实上,在边乡小说抒写中,梦境并不直接关涉小说的脉络走向进而成为影响小说内在主体精神的话语成分,梦境多数是边乡人庸常生活之中的一个点缀,它无关乎人物的生存命运,但却不经意间说出了边乡人的某种非一般性、某种向上的力量。一个爱做梦的人至少是一个对生活抱有幻想的人,生活不是幻想,但生活恰恰需要幻想,甚至一些时候,生活的意义就在于幻想。生活的难度某种程度上在于人是否能够忍受生活的庸常与沉重以及人面对生活所具有的多大耐性,而耐性除了被动地承受,还需要人对生活所给与的积极回应,而梦实际上就是边乡人生活态度的一个表情,梦成了边乡人在生活的屏障中打通去路的一个途径。在现代化的今天,边乡与都市天然存在着生存秩序的距离,但这并不能忽视边乡人生存的权利、活着的意义的合理性。梦在小说中的频繁介入,正是折射处于弱势地位和庸常社会境遇的边乡人同样共享着生存的权利和活着的意义。甫跃辉告诉我们,边乡人同样拥有做梦的权利,正是这种权利在小说中的合法性抒写,让生活的意义、生命的价值在边乡人身上得到彰显。甫跃辉赋予了边乡人作为人存在的某种在历史中曾经失去的平等位置。从这个层面而言,梦对于甫跃辉的写作具有特殊的意义,梦的文本参与足以见得甫跃辉在面对读者的时候所表现出的生活倾向性、选择性,在甫跃辉的写作中,梦成了生活的两难中一口新鲜的空气。而这正是甫跃辉边乡小说的价值所在。
二、 梦魇的都市
伴随着从边乡到都市的生存境遇的迁徙,“做梦”仍然在继续,“梦境”继续被访问。但与此前边乡之梦的从容、温暖不同,都市的梦似乎不再那么纯净。假如说记忆是黄色的,那么都市此时此刻的梦境就是黑色的。都市的梦,是魇。那么,我们不禁要问,缘于何种原因从边乡到都市的地域流转就能让梦变成魇呢?前面说到,梦境对应着两种现实,历史与当下,或者说,记忆与生活。换言之,一个人的梦境与一个人的生存境遇、生存状态存在莫大的关联。同样,一个作家的写作与他的个人生活经历也存在或多或少的牵涉关联。甫跃辉笔下的大多数都市青年与他共有着相似的生命路径,从边乡来到都市,求学、恋爱、工作,就像李敬泽说的,“他本人很像是从他的小说里走出来的”⑥。边乡到都市,表面上看是地理位置的迁移,实际上是人生活道路的变向,从云南到上海,路越走越远,也越走越窄。两种生存空间的正面遭遇,不仅要承受这种遭遇所带来的外在的生存空间与内在心理空间的挤压,更要在二者之间作出生活方向的选择和判断。而事实上,也毫无选择的余地可言,求学的命运决定了他们只能投向都市巨大的生活洪流之中,涉身其中就要对自我的生存心理进行调整从而适应都市的生活变奏。而吊诡的是,边乡、都市天然存在的生存差距又在拖拽着他们艰难前行的脚步,边乡是柔软的,而都市的大厦高楼却散发着结结实实的坚硬冷漠的气息。都市作为他们美好的愿景既是作为生活路途上前行的探照,同时又不可避免地成为迈步的巨大障碍,两种力量的交叉摩擦,人便困厄沦陷住了。可以说,这些移民青年的根本困厄正是由来于此,他们身处边乡、都市天然存在的生存差距中,又渴求依靠自身的力量缩减这种差距的长度,以求摆脱这种生存差距所先天赋予他们的面对都市生活的障碍,从山里人变为都市人。但我认为这种变化不在于身份的表层,更在于那种自卑、压抑的生存心理的常态化。所以,至关重要的仍然是他们面对都市的诱惑作出何种回应。
小说《静夜思》(《小说界》2013年第1期)简直就是一部惊悚片,梦魇贯穿始终。小说中的“他”深夜值班,单位房子里闹鬼的传说让“他”内心难安,梦接踵而至。小说的精巧之处在于梦魇与“他”的生活之间构成了一种互动比照关系,也就是说,此在与彼时存在一种对照关联。房子主人的妻妾是两姐妹,她们先后吊死在壁橱里。而“他”的梦魇某种程度上正是出于对她们死亡的幻想,而梦魇的发生又让“他”反观起了自己的生活以及自己曾经伤害的两个女人。让人惊悸的不仅是梦魇可怖的内容,更可怕的是梦魇一个接着一个的毫不停歇的节奏,好像梦对于“他”而言成了一种瘾,既害怕又充满激情和快感。由梦到魇的变化,实际上是人的内心变化,人在魇中的怕出于人内心的不安与悸动,而内心正是行为主体与现实互动的内在沉淀,内心的问题实质上是生活出了问题。“他”的问题是对两个女人的伤害,而这仅仅是问题的表面,更为深层的是这个伤害触及了“他”最为隐秘的人性黑暗,从而引发“他”对内心的道德准则、生活现状、生活方向的怀疑与迷惘。“他道歉过,可过不了多久,又会给她们增添新的伤疤。他也认为他忏悔过,可忏悔了为什么并不影响他继续砍斫她们呢?他实在不能明白。”小说的深刻之处正在于此,它说出了人性之中那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忏悔真的能得救吗?忏悔只能针对一时一事从而获取内心的暂时安稳,拯救,与其说是宗教意义上的罪恶终结与灵魂飞升的时刻,不如说是滚动巨石的西西弗斯在山顶的一次短暂停歇,因为生活所给予的伤害是无法预料的,而伤害的无以复加在我们无法承受的时候,我们只能通过伤害别人来转嫁内心的隐痛。“他没有办法面对任何人,只有变得刻毒,再刻毒。他又能怎么办呢?”尽管如此,我们似乎觉得“他”还是可以原谅的。至少,“他”没有挫败,没有因伤害和因伤害带来的混乱而麻木、委顿、毁灭。至少,“他”在“静夜思”,梦魇的接连上演让“他”想起过往、思考过往,可以说,此时的回忆就是忏悔,“他”对生活还是有感知的自主意识的。“他”深知,自己是罪魁祸首。救赎并不在结果,而在于是否能够真诚地面对曾经施于他人的伤害,并且能够在这一痛苦的回溯过程之中反躬自我人性的残缺,继而警醒继续的生活。
如果说《静夜思》里的梦是忏悔现实罪恶的一个中介物的话,那么,《巨象》(《花城》2011年第3期)里的梦则是一个直接的惩戒者角色。在这里,李生是直接的伤害施予者。李生在火车上偶遇小彦,生活中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了,按照常理,他们的关系在火车上就已经结束了。但事实相反,他们见面、约会,一次,两次……这就很奇怪,相较而言,已经在城市站稳脚跟的李生为什么要喜欢一个既不漂亮又没有城市生活资本的小彦呢?而实际上,李生根本就不喜欢小彦,如果男女之间不是因为喜欢在一起,那就只有一种解释,为了性。而性在李生看来不是纵欲享乐,而是征服。李生对于小彦每一次的主动靠近都不是出于本意,而是出于在女友身上、在这个城市中的一次次挫败,因而他需要在比自己更柔弱的生命身上找到成就感和存在感,转嫁自己的挫败与伤害。“女友在他心中不知不觉已成为这个城市的象征,和女友在一起,就等于真正进入了城市。女友的离开,被他下意识地理解为进入城市的失败。我终究是个‘山里人’,他忧伤地想。而她和他一样是外地人,他凭借早先进入城市的优势,很容易就会把她弄到手。她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弥补他的失落,又让他怜悯和厌恶自己。”小彦对李生的爱是一种错位的爱,她爱李生,而李生的全部回应只是性,他把她当作玩物,当作征服的对象,当作能够凸显自己在这个城市优势地位的配角。他丝毫没有考虑到这些,甚至当怀疑自己是否还是一个好人的时候,他坚定地回答自己“不,我还是个好人”。当一个人想作恶破坏的时候,他肯定想不到之后因果报应之类的可能,他的全部力量都聚集在那个作恶的念头上,就像昆德拉说的,“力量的侵略性是完全无利害关系、无理由的;它想要的只是它的意愿,它是纯粹的非理性”⑦。然而,当李生一次次伤害小彦的时候,巨象也神秘地在他的梦中走来。巨象不仅是一个庞大的梦,更是一种庞大的生存压力。尽管李生在制造伤害,可反过来看,他自己也是受伤的人,渴望进入城市的愿望与山里人的挫败感让他的内心扭曲,巨象来了。错位的爱势必以一方的毁灭为代价,这一切以李生的结婚为结束。有了归宿,李生自然不再需要小彦,甚至连巨象也被李生抛弃了。可李生的生活真的就安稳了吗?小说的结尾可以说精彩之极,精彩到不仅让李生不寒而栗,甚至让读者后背发麻。小彦假装成哥哥打电话向李生哭诉,说小彦死了,当李生听出小彦的声音之后坠楼身亡,而这只不过是一个梦,李生做的又一个梦而已。可接下去,真的像梦境一样,电话响了。小说故意设计了梦境与现实的逻辑反转,按照常理,现实中发生的事可能在梦境中再次上演,现实与梦境应该存在一种模糊的逻辑顺序,而在这里,梦境似乎反过来成了一种引发现实的实体。在这种逻辑措置中,可想而知的是做梦的人内心的恐惧与折磨,梦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惩戒者。伤害是无法弥合的,但这不代表伤害的施与者就会心安理得,伤害其实是双向的,就像一个皮球,当我们伤害别人的同时,其实伤害本身也在反弹我们自己,而伤口更深、更痛。而痛的不仅仅是李生,更是小说之外的我们自己。
当梦构成一个人生活的绝大部分的时候,他的生活一定轻之又轻;而当梦魇成为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的时候,那么他的生活必然重之又重,那是另一种痛。《饲鼠》(《大家》2013年第5期)中的顾零洲过的就是这种梦魇的生活,因为梦魇总是“一夜又一夜”,以至于让人觉得它“太真实了,太不像梦了”。生活的形式变成了“梦与真实的混合”。梦魇似乎成了生活现实的注解。顾零洲依然从乡村来到城市,求学,毕业,工作。生活的内容和形式都很匮乏,顾零洲隐忍着。而隐忍事实上意味着一个人面对生活压力的两种内在力量的冲撞,既想冲破网罗,又无可奈何束手无策,既是肯定,又无时无刻地怀疑、否定。可想而知,顾零洲内心的角力之痛。而稍有安慰的是对面高楼的陌生女人,然而高楼的存在既提供了一种想象生活的角度,又确确实实设置了难以逾越的边界障碍。高楼与顾零洲的距离就像生活划开的一道伤口,过分地越界,伤口就会阵痛不止。既然获取人性温暖无望,那么顾零洲只能从动物身上寻求替代的快感。先是蟑螂,“他选好角度,一泡热尿滋过去,它脚下趔趄,调头从白瓷砖上摔下,摇头晃脑地试图爬起,他赶紧调过枪头,对准了又来上一炮,它哪里抵抗得过,终于晕头晕脑跌入尿坑,黑黑的一个小点儿,在水尿混合的淡黄液体表面簌簌挣扎,他再一次调过枪头,痛打落水狗!它上下浮沉,呛了一肚皮水。他遂有些欣欣然,拉动水箱绳子,轰隆隆一连声响,大水迅速冲过,那小小的黑点便永远消失了。他的笑意在法令纹里隐隐浮现。这是他在夏夜里的隐秘快乐”。生活已经毫无快乐可言,本应无聊的事,现在已经成了顾零洲最“隐秘”的快乐。“无聊”还在其后,顾零洲开始煞有介事地捉起了老鼠,甚至这已经成了他乐此不疲的“事业”,一桩未了的心事。当然,他不满足于捉,他还要“捅”,“反反,复复”,他还要用水“冲”,“反反,复复”,他甚至还把它当作宠物饲养起来,可是它还是死了。顾零洲的生活已经变异了,肮脏的老鼠竟然成了寻求快乐的源泉。而生活的异化实质上反映的是人内心的异化,如果一个人的内心异化了,还有什么样的事是不可能的?更为可怕的是内心的异化某种程度上是人生活热情的消退,一个人没有了生活热情,一切的可能性也就无从谈起了。人的无聊,由来于此,而“人到无聊,便什么都可怕,因为这是从自己发生的,不大有药可救”⑧。饲鼠是一种无聊,更是一种危险的信号。对于顾零洲而言,老鼠的死不仅是生活的失落,更是人性深处的失落、人性尊严的凋落。尊严就是对人之为人的权利的维护和持存,老鼠的死,既意味着一种伤害,又意味着一种失去,而这种失去可能是一去不返的。而当“脱”那个字说出口的时候,我们知道这种失去的确一去不返了,人的尊严、人的道德律一去不返了,而“没有比失去忠诚和道德上被削弱更难以恢复”⑨。小说带给我们的其实是一种选择,在生命枯竭、无聊之时,该何去何从?是在无聊之中冷漠无情还是继续保持对生活的痛感?生活是反讽的,但生命却是生动的。无疑,顾零洲其实选择了一个方向,而且伴随着那种坚定的语气,我们知道“脱”已经成了他生活的目标与方式,而生活方式其实就是一个人的价值判断与选择,这是难以改变的。顾零洲真的变坏了,彻彻底底地成了一个坏男人。大概,一个认真生活的人都会在生命的某个特定阶段坏上那么一回,但顾零洲的坏似乎不大有疗救的希望。梦魇,至少意味着对生活的承受与接纳,意味着一个人对生活的怕,对生活的怀疑,而怀疑从另一个角度看不也是相信吗,没有相信,何来怀疑?顾零洲不再是那个变态、不安、焦虑、贫乏的山里人,他的确从都市压抑的网罗中冲决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只不过这条路是我们不希望看到的。人到中年,他“已然跻身商界精英的行列”,他似乎得到了许多,而人的悖论却是无法规避的,得到越多,失去的必然也一样不会少。
梦魇的有无、来去,既关乎生存的困境,更关乎困境之中人的选择与回应。顾零洲、李生们,他们身处困境,在生活的罅隙中挣扎,都市隐身的竞争压力的挤压,释放了他们内心深处的自私、残暴、怯懦、仇视等等黑暗心理,它们就像一群黑色的小魔鬼,走出内心,伤害他人,也被他人伤害。本应在道德层面被规避掉的人性弱点,在甫跃辉的笔下取得了抒写的合理性与合法性。然而,也只有让那群魔鬼走出内心,我们的内心才能祈获安稳与纯净的可能。顾零洲们在不同的生存境遇下作出不同的生活选择,却始终没有放弃生活的权利。我认为这是甫跃辉小说能给予我们的最大受益——不轻易放弃生活,涉身其中,寻求去路。生活的激情不是来自于物质世界的获取与生存空间的进化,更为根本的还是来自于在梦魇的动荡中对一丝光明的向往与追寻。生活的意义,不正是在于这“梦魇的激情”吗?
三、 梦醒时分
当然,一个人可以生活在别处,却不能始终生活在梦中。梦,作为第三种空间为人暂时提供逃逸的居所,但生活的形式始终是现实的,生活其实就是人与现实的关系,生活的变化是人与现实关系的处理方式的不同所致。所以,人总要从梦中醒来或是惊醒,总之,要去触碰现实,与现实面对面,在生活现实中用心耕作。活着并不代表活过,活过就要用心,要认真,认真地快乐、认真地悲伤、认真地享乐、认真地失去。关于梦,甫跃辉在调整自己,也在调整写作。在《动物园》(《十月》2012年第3期)、《三条命》(《江南》2013年第5期)、《亲爱的》(《长江文艺》2013年第7期)这些小说中,梦几乎不再了。梦醒也是一种选择,是一个人内在精神的成长,是从不安、怀疑、警惕中的清醒,更是一种正面生存现实的态度。可梦醒了,真的看到的就是光明吗?世界并未改变,梦醒了只是表明看待世界、接受生活的姿态变了。而当我们真正睁眼看世界的时候,可能那些最深刻的痛我们才能看到、痛到、感知。正面生存现实,其实就是面对自我的真实。而真正的痛,可能并不是生活施与我们的,而是来自我们自己。每个人只能固守在自己之内,每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个体既意味着差异,同时又意味着难以逾越的边界。个体与个体不可能完全相容,实现沟通的彻底性。
在《动物园》中,此时的顾零洲相对而言已经取得了在城市的生存资本,生活的稳定之下,便是情感的空缺与填充,恋爱、结婚顺理成章。顾零洲和虞丽看起来再合适不过,一个是出版社美编,一个是小学美术老师,又是老乡,身份、地位、生活趣味都大致相当,简直门当户对。而在生活的激情消退中,他们的关系还是出了问题。可问题在哪儿呢?似乎是那个窗户之外的动物园出了问题,虞丽厌恶动物园的气味,而顾零洲却偏偏喜欢开着窗户,于是,“开窗和关窗,是一场漫长的战争”。显然,动物园只是表面,是一个借口。问题还是出在人的内心。动物园只是两人关系互动的中间物,两个人针对动物园不同的行为方式、话语方式的纠缠才是问题关键所在。两个人相处既是体温的靠近与一个新的关系共同体的再生,同时也意味着两个人作为个体的力量的侵入与内在角逐,也可以认为是对一种权力主体的争夺,是谁宰制谁的问题。这样一来,双方势必处于一种强弱动态变化中,也就是说,势必有一方要处于弱势,此时,要么妥协,放弃自我的原则,要么决断,分手。看得出,顾零洲不想分手,他很珍惜虞丽。可嫌隙一旦产生就会要求十倍的努力来弥合,而结果也不一定就会美好如初。恋爱中的人就是这样,当一方觉得另一方不再美好的时候,结局可能就真的不好了。当虞丽三个星期没来之后,顾零洲主动打了电话。之后,他们恢复了关系。可没过多久,虞丽还是提出了分手。其实,虞丽在乎的不是动物园,她想要的是顾零洲能够在她和动物园之间做出一种明确的选择姿态,她想要顾零洲更多的投入与专注,在女人看来,爱有时候就是男人愿意为自己舍弃、牺牲。可顾零洲同时也保持着警惕,他虽然在妥协、在忍让,却没有失去自我。他特别喜欢纪录片《象族》的一句话:“大象的生活充满了庄严、温柔的举止和无尽的时光。”小说的用意何在呢?那可能是顾零洲的一种生活理想、向往,而当一个人有了理想的时候,这个理想就会成为内心隐秘的价值尺度、判断标准、生活原则。只是这种模糊的意识,虞丽会懂吗?其实,矛盾的产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处理矛盾时方式的愚蠢,假若两个人真的能敞开心扉谈论彼此,他们不可能分手。可是,他们都不愿意信任彼此,不愿意在沟通的道路上主动迈出那倾向于对方的一步,不迈步反而意味着退缩。难道他们就愿意如此吗?一段难得的感情就这么放弃?人的复杂性正在于此,面对人性的纠缠,他们既有着模糊的认识,又犹豫、怀疑,不想做出改变和反抗,而是任其发展下去。可是,他们是痛苦的。虞丽走后,当顾零洲在动物园再次看到大象的时候,“那一瞬间,他终于难以自已,感到泪水一再涌满眼眶”。“他莫名地觉得,它们不再是庄严和温柔的,它们赭红色的庞大身躯里,似乎隐藏着同样庞大的痛苦。”痛苦的其实是顾零洲,他深知固守自我的孤独,又无可奈何。而人一定是在失去的痛苦中,才会获得感知幸福的经验和能力。可当他准备回家寻求家的温暖抚慰的时候,却发现“动物园的大门黑沉沉地关着”。他又被困住了,都市的隔离无处不在,生活的烦恼又来了。这是小说的高明之处,也是甫跃辉的成熟之处。它将小说从一个相对封闭的文本空间引向了一个更为开放的生活空间,这个空间既开阔又阻塞,这就是生活的可能性。《三条命》也是男女关系的变奏。只不过,小说一开始顾零洲就面临着分手问题。稍有差异的是,小说的叙述形式是以男女对话的复调形式展开的。对话既是小说的文体形式,又是面临分手的男女双方重新观看彼此、了解彼此的一个契机,当然,更是审视自我的机会。小说也是关涉男女的理解、沟通问题,但这不是关键,通过对话的展开来对两个人沟通中出现的中断与空白进行填充、弥合才是小说的意旨所在。当文本填充实现之后,两个人还是没能在一起。卢丽心很困惑,“我们都经历了那么多,我们在一起就该相互温暖啊,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样?!”可两个人的关系并非是顺向的叠加、积累,爱跟时间并不是成正比的。对话既让两个人深入彼此,又让他们感觉到了那无法打破的距离的存在,顾零洲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痛苦。我有我的痛苦,你也有你的。可是,痛苦能理解痛苦吗?”卢丽心说这是借口,可借口又是什么呢?还不是人心中说不清道不明的魔障?克里玛说:“这个世界上的很多人受困于一种感情,觉得他们的生活中缺少激动人心的时刻,缺少一种更深刻的幸福。”⑩在顾零洲身上,这种“缺少”成了他的“多余”。人有的时候不是缺少爱,而是爱的“多余”。《亲爱的》中,顾零洲就是如此。傅笳已为人妇,顾零洲却与她保持了十年的情人关系。小说其实是在讲一个“度”的问题,十年是一个长度,某种意义上也是爱的深度,小说似乎有意勾连着这二者之间的同构性。可事实是,“两个人再怎么爱,身体上也只能有这么一点儿彼此进入”。这让顾零洲绝望,而绝望的人有两个极端,要么冲决到天,要么沉沦到底。顾零洲选择了后者,他最后感叹“哪有什么深爱?”其实,都是借口而已,给自己沉沦下去做一个坏人的理由罢了。他也深知自己就是那个无耻之徒,可还是要坏下去,索性一坏到底。这些小说的主人公都是顾零洲,顾零洲既可爱又可怜又可恨,这些小说都让人唏嘘哀伤。什么是哀伤,就是这种只有你一个人面对孤独自我的时候、由彼及此的无言的伤痛,它不刺入皮肉,它不挂在脸上,它长在心里,偶尔,让你阵痛不止。顾零洲的个人命运,就像鲁迅所说的,梦醒了却无路可走。梦醒了,世界却并未豁然敞开,希望没有增加,绝望也未减退。顾零洲在彷徨,“他既想看清去路,也在竭力回想来路。”顾零洲的迷惘,又何尝不是甫跃辉的迷惘。从某种程度上,顾零洲就是甫跃辉在小说之中的精神自画像。福楼拜说,包法利夫人就是我。同样,顾零洲就是甫跃辉。小说人物与作家生命路径的同步性是甫跃辉小说的特色,也可以说是风格。事实上,顾零洲已经成为甫跃辉作为写作风格的一个形象标识,反过来,这一形象以文学的形式也为“80后”整体在这个时代立言立传,顾零洲是“80后”作为历史代际产物走入当代小说史的一个重要形象。
一个优秀的作家必定是一个爱做梦的人,小说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人的一个梦,但梦并非仅仅关联着小说的叙事逻辑,梦更是一个作家精神气质的特定显影。梦不仅是一个生理现象,更是关涉生存之境中人的精神深度的一个表象。一个只有真正热爱生活、认真过活的人才有梦可做,有魇可怕。我们所做的一切,包括小说本身,无非是为了生活的品质。甫跃辉深谙此道,他说:“它们(梦)或许可以让小说在现实的泥淖里,喘上一口气。”也正因为如此,他才会乐此不疲地做梦、写梦。无意之间,一条鲜明的想象生活的路径就清晰可辨:梦是小说的“一口气”,而小说又是生活的“一口气”。小说的价值正在于此,那就是“行走在现实泥土之中的人,内心有一种飞翔的愿望”。这样一来,读者很容易误以为甫跃辉小说的生命之轻,但实际上甫跃辉的心思很重,这么说并不是指涉甫跃辉的人格品性,而是说他对人的命运具备了根本性的把握——对人的悲剧性把握,一个只有具备悲剧意识的作家才能深入人性深处,描摹人性的复杂,而“悲剧意识才真正是生命走向终结的觉醒意识,它唤起了所有存在的热情和意志,领会到存在的艰巨性和不可屈服性”。从2006年处女作《少年游》发表至今,甫跃辉已经写了十年,十年是一个总结,更是一个节点。因此,甫跃辉此时的去路至关重要。相比较早期边乡系列小说,甫跃辉都市背景小说似乎更加冷漠、更加异化,而缺少早期那种冷眼看世界的温暖与温情。写了十年,甫跃辉自然收获不少,而收获的同时更应警醒自己那些也随之丢失的部分。就小说与作家的互动关系而言,小说并不应该仅仅作为一种职业、一种写作方式或者说一种生活方式,小说更应该成为作家内在精神的一部分,成为作家作为生命个体反观自我与其他生命个体的一个镜像。作家独立的气象与胸怀直接关系“小说到底能够走多远”这个命题的限度。小说,说到底,根本上还是作家精神品质的凝聚与发散,就像设计房子,假如建筑师的眼光是歪曲的,那房子一定正不了。如果说小说是有灵魂的,那么灵魂正在于此。我想,这也是甫跃辉在面对小说去路的时候不得不思考的问题。
注释:
①米兰·昆德拉著,孟湄译:《小说的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5页。
②甫跃辉:《做梦与写作》,《名作欣赏》2014年第25期。
③米兰·昆德拉著,孟湄译:《小说的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5页。
④吴亮:《文学的选择》,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⑤米兰·昆德拉著,孟湄译:《小说的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131页。
⑥李敬泽:《独在此乡为异客——关于甫跃辉短篇小说集〈动物园〉》,《南方文坛》2013年第5期。
⑦米兰·昆德拉著,孟湄译:《小说的艺术》,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版,第9页。
⑧鲁迅:《两地书 书信》,《鲁迅全集》(第十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88页。⑨克里玛著,崔卫平译:《布拉格精神》,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第21页。
⑩克里玛著,崔卫平译:《布拉格精神》,作家出版社1998年版,25页。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