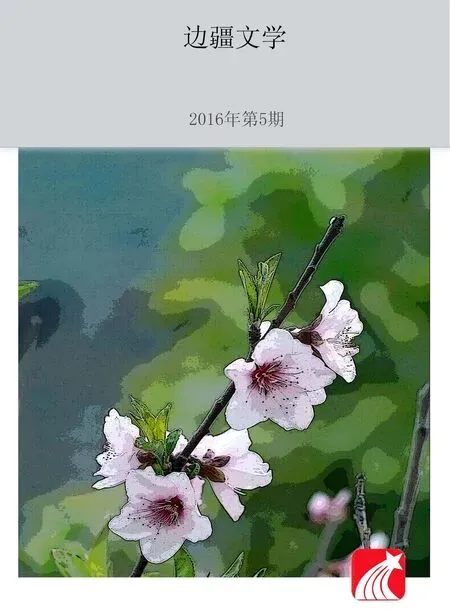雄文未成身先死
——论《神史》的价值和遗憾
◎夏 吟
昭通文学研究
雄文未成身先死
——论《神史》的价值和遗憾
◎夏吟
主持人语:已故昭通作家孙世祥的长篇巨著《神史》,一版再版,在读者中引起较大反响。诗人夏吟的文章《雄文未成身先死——论〈神史〉的价值和遗憾》,既分析了这部长篇小说的正能量价值,也如实地剖析了作品的不足之处,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评论文章。
著名昭通籍作家夏天敏的长篇小说《极地边城》是一部有特色的作品,青年学生崔鑫的文章《〈极地边城〉人物原型考》,通过大量证据,将作品中虚拟的人物形象与历史上的真人进行对比,逐一指出作品中的人物就是历史生活中的某一人物。角度新颖,考据严谨,是一篇有意义的文章。(李骞)
《神史》作者孙世祥英年早逝,使得《神史》成为了昭通文学史中一部谜团般的作品。《神史》的未完成是昭通文学的悲剧,也是我们时代的悲剧。《神史》成为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部奇书,它也必将成为昭通文学的一个里程碑。《神史》的价值是多方面的,将给作家创作带来许多启发,但《神史》因处于未完成状况,它也留下了众多的遗憾,给我们带来许多思考和启发。
一、《神史》在方言的运用上凸显了方言写作的价值,但《神史》在方言书写上的不准确,给书籍留下了许多瑕疵,给读者造成了很大的阅读障碍,也给小说的传播带来了难以弥补的遗憾。
《神史》使用的语言是家常的乡土的巧家法拉方言,这样的看起来土气。但是,《神史》却让我们感受了这样的民间语言里充满着智慧,这种语言是讲述性中带有评价内容的语言,民间依然保留的带有古风的大量的文言句式和植根于农耕文化的滇东北方言土语,有着沉重的泥土气息和古风余韵的语言,如此鲜活生动,它特殊的文化沉积魅力在《神史》中展示出来。
语言专家余世存和全国知名的学者钱理群也被《神史》语言的个性化和地方化所吸引,给予了《神史》高度的评价和荣誉,《神史》一书中也因对汉语言的“见证性”言说功能的发挥,而获得了北京当代汉语研究所2006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在当代汉语贡献的颁奖词里,钱理群先生说:“《神史》在汉语叙述上的意义还在于它的朴素简约及民间语言的传承……孙世祥的著作为卑者传,用简明的汉语言说芸芸众生的生存状态,为写作文本拓展了表达的空间,历史地看,他在汉语的传承上为后人提供了更多的可能。在一个外来语成为时尚的背景下,他写作的价值更具有象征性,为华语世界竖起了一面自信自尊的旗帜。语言是一个民族文明的载体,失却语言的民族,也就失却了民族文明的根。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他的文本无疑为世界文化的大花园添了一朵异葩。”[1]
钱理群先生这一评价也给昭通作家很多启示,给许多使用方言写作的昭通作者一定的信心。在《神史》没有出版前,当孙世祥的两位兄弟为《神史》的出版到处奔走时,一些编辑和作家曾说:《神史》的语言不过关,《神史》文字上都不流利。客观上说《神史》的语言方式为《神史》的出版、阅读和传播带来了障碍。
孙世祥不是不能用普通话来写作。从孙世祥留下的没有方言夹杂的大量现代诗歌和古典诗词来看,孙世祥用普通话表达思想感情的能力也是十分突出的,通常的写作方法、修辞手段和文本结构方法等文学上技术性的东西,孙世祥也是熟练掌握的。口语和方言在《神史》中的运用,也不是孙世祥的写作话语策略,而是这些语言和表达习惯和孙世祥的生命感受有直接关系,这样的语言和他的灵魂表达紧密联系在一起。
孙世祥在《神史》中使用大量的方言土语,而且力图用得地道、自然,是他基于对自己的写作对象和写作内容特点的自觉,《神史》因为使用了方言,无论叙述还是对话,都非常有个性,书中的人物使用这一代代传承下来的语言来说家常、开玩笑、吹嘘、吵架,让人物也活灵活现,这鲜活的语言让每个人物都独一无二。《神史》中保留的原汁原味的民间语言,更能贴近小说中人物生存生活的现实状况,使得人物性格活灵活现。
孙世祥使用地方方言进行创作,还源于他对方言有了许多发现,体会到了这种方言的珍贵和在传承中华民族古老文化上的作用,这一点在《神史》中,他借人物对话可以看出来,在《神史》中,孙天主带地区文联一行人深入荞麦山采访,他和几位老师在谈笑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和猜想:“壬老师教汉语课,试问了一些话,均属北方方言区。而且包括天主在内的人说的方言,不川不滇,别具一格,壬老师惧然‘怕又是明南京方言,也未可知!这倒是个好题目,值得认真考证。’罗南老师就在南京读大学,说‘南京方言也不是这样。’天主说‘六百年了,天翻地覆、沧桑巨变。当时明朝的都城,尚且成为了签订《南京条约》,又成被残杀三十万众的地方。语言岂能没有什么变化?就像保留佛经的,不是印度,而是中国。保留唐朝遗风的,并非中华大地,而是日本列岛。保留古南京语言的,定非今之南京人,可能是滇北深山中的拖鸡人、法喇人。’大家皆然。”[2]
昭通籍国学大师姜亮夫先生早就发现了滇东北方言的多样性和意义,他特别写作了《昭通方言疏证》,为我们研究昭通方言做出了一个示范,可惜后来没有语言学者,尤其没有昭通本土语言学者继续来研究昭通丰富的方言,不知道孙世祥先生有没有研究过《昭通方言疏证》,将《神史》中使用的方言,和《昭通方言疏证》和南京方言相关书籍进行对照,将《神史》和使用了南京古方言的古典文学作品对照,印证了孙世祥的这一设想是正确的,但是,对照的结果,我们也可以看出《神史》中还有许多方言的写法是很不准确的,有的是用同音字代替的,有的则是错误的书写,一些方言音的纪录是大致的,许多语言符号是不准确的,有些语言音是那样读的,可是书写下来的字不是那个字,如果要全面的反映出这种方言的魔力,这些语言还需要更正,并加以考据后加注。
昭通方言的许多字词的写法,可以从古汉语、古典文学作品、四川方言、中原方言和其他相关传承语言中找到参考参照,可能孙世祥还要对照古南京方言进行研究过,再进行订正的,按照孙世祥对他使用的方言可能是南京古方言的推测,《神史》中一些副词虚词代词叹词的写法,也需要进一步确认,《神史》在使用方言上凸显了它的价值,但是因为《神史》中的许多方言写法的考证工作,孙世祥还没有完成,给这部书带来了巨大的遗憾,也给读者的阅读带来了难以弥补的阅读障碍。
昭通地方语言的魅力,在昭通作家中也早就被重视,写出了昭通第一部长篇小说后来又写出了多部长篇小说的老作家曾令云先生一直坚持使用昭通地方的方言进行小说创作,那怕这种语言影响了他的小说在主流文学刊物上的刊登,影响了小说在全国范围的阅读,用这种语言的进行创作给他的作品进一步传播推广带来许多麻烦,但是他也坚持到底,有许多地方语言的写法,曾令云先生要更为准确一些,因为曾令云先生为了一些地方话的写法说法和意义,不仅认真读过《昭通方言疏证》,而且曾经翻遍了《康熙词典》等等大词典,昭通地方方言中的有的字已经在我们现在通用的打字的字库里找不到了。
我们要感谢曾令云、孙世祥等昭通作家为我们保留了没有经过普通话的暴力清洗的昭通方言,这样的语言背后有着丰富的民族的文化的历史的内涵,同时也成为了昭通独特而深厚的文化底蕴的一个见证,同时,这种语言也是中华民族文化传承的多样性的一个支流。
如何继续展示昭通方言的语言魅力,需要语言学方面的专家介入对昭通方言的研究,为昭通作家的创作做一个方言的书写、解释方面的基础工作,同时,作家在用方言写作时,也要考虑到广泛的外地读者的阅读障碍,采用加注、解释、过滤等方法扫除阅读的障碍。方言写作对昭通文学来说是一场接力赛,这场接力赛,不是一个人的接力赛,可能是几代人的接力赛。在昭通文学创作中,这一场关于语言的接力赛还会继续下去。昭通籍作家中正在旺盛创作的中青年作家中黄代本、徐兴正、季风等人的小说语言也坚守了本土特色,他们使用着昭通的不同的小地方语言。
二、《神史》的“自叙传”特色,使《神史》有大心胸、大情怀、大视野和大理想的底色,给我们带来丰厚的精神启示。但小说对作者生活中的琐事记录和日记式记录未完成最终的“小说艺术化”,给作品带来了艺术上遗憾。
《神史》在写作内容上为我们指示了一座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文学写作富矿,那就是我们自身的生命就是我们的写作源泉。
作家的灵魂世界在作品中的地位非常重要,如果人人都能去记录发生在乡村的各种鸡毛蒜皮的事情的话,那么,用什么样的气势、什么样的精神基调去统领和组织这些事件人物,在许多作家那里就遇到了严重问题,他们容易停留在事物的表面,甚至写作会走向庸俗化。
在《神史》中,孙世祥本人非比寻常的精神气质、他的大悲悯为文本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是他切入事物心脏的洞见力为揭示人性的真实和灵魂的力量奠定了基础。
《神史》中弥漫的那种理想主义的情怀,主人公孙天俦怀抱着要用一己之力济世的大理想、大胸怀和大追求,孙天俦准备投身大时代准备建立大功名,在社会急剧转型和市场经济突变的今天,这种家国天下、建功立业的英雄主义理想主义情怀成了当今时代的稀世之宝。对于现代社会众多的丢失了理想的人来说,孙世祥在书中表达的那种追求真理、忧国忧民、勤奋精进、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刻反思的机会,催促人们重新肩挑起属于自己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神史》带有很强的自叙传性质,主人公孙天主(孙天俦、孙富贵)是以作者孙世祥为原型的。”[3]《神史》中如果没有了让人难以释怀的孙天俦的勇气、激情、孤傲、烦忧和执著,都带有孙世祥自己性格和经历的影子,甚至许多地方直接就是孙世祥自己的经历的记录,这部小说因为作者的这种人生体验灌注其中,增强了小说的感染力,没有了孙天俦雄浑理想和辉煌梦想的旋律在其中高扬,没有了孙天俦忧国忧民的情结,没有了孙天俦的悲天悯人,没有了孙天俦的灵魂的躁动和行为的特立独行,没有了孙天俦的超级浪漫和他的不合常规的生命突围,没有了孙天俦为了高远抱负而自我逼迫而拒绝享受人生,没有一种天地可鉴的正义感灌注其中,而仅仅只是乡村琐事和自己的经历的记录,那么,《神史》的价值将降低许多,《神史》会因为缺乏神气、精气和灵气而变得平常。
《神史》像一把锋利的刀一样,揭开了我们的伤疤,让我们不得不面对故土。
孙世祥把许多人已经忘怀了或者想要忘怀的记忆撕开了,孙世祥说了我们不敢说不愿说却长久地埋藏在心里的话,孙世祥直面现实地把亲身经历的事情和感受用小说的结构方式写了下来,让人的心找到了滴血的疼痛。《神史》能让读者心痛滴血,那是因为作者本人就曾经为这些体验滴过血。
《神史》为我们做了一个全新的其实也是本真的文学写作方向写作内容的引导,孙世祥先生生前从未在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他也没有研究文学刊物的爱好,他是顺应了自己心灵的呼唤来写《神史》的,也是按照自己心中的文学理想来写《神史》的,他没有给自己带上任何来自社会和外界的镣铐,这样的摆脱了社会各方面的压力和束缚来进行的最为真实的写作,终就显示了文学的正确方向和道路。
在《神史》中,孙世祥借助对学生作文的定位,说明了他对文学写作内容的定位。孙世祥从孙天俦写作文的经历中,道出了他对模式化命题作文的反感,当老师秦光朝见天俦擅改作文题目,不把天俦的作文当好作文时:“孙天俦愈觉无论人生还是作文,都要为所欲为,抒所欲抒,才叫人生,才是作文。后来,他当了教师后,又因为对学生作文的评判和有权势的高级教师杨知才发生了冲突,孙天俦一定要把学生写的:我的家乡在新加坡……。等等类似的作文判为低分,认为这些从来就没有到过新加坡的孩子这样写作文,首先是不诚实。”[4]看到这里,许多从事文学写作多年的人是不是应该为依然在写“我的家乡在新加坡”类似的虚假文字,而感到惭愧或者有所觉悟。
《神史》所写的东西曾经是许多从农村走出来的人期望早一点放弃的巨大的包袱,也是我们许多文学写作者放弃了的东西,但是,《神史》让人们重新认识到这个包袱的文学意义,也让阅读过作品的人共同来对这个包袱进行社会的历史的思考,一些因阅读了《神史》而进行了社会思考的人们,会重新肩负起社会责任,会重新确立自己的生命方向。
把类似《神史》的写作内容,作为一个包袱肩负起来的文学写作者,能从《神史》中挖掘到文学的黄金,我们能从《神史》中清晰地看到文学大家的大手笔方向,文学就是心灵史,文学就是社会史,文学就是时代画卷。文学不应该抛弃普通人经历的平凡事,我们祖先的历史,我们亲人的遭遇,我们心灵里的波浪,我们眼睛里的时代,我们经历的世事沧桑,就是文学的矿源,《神史》启发我们:文学写作的内容就是我们的心灵世界和我们生活的真实世界。
《神史》不完全是孙世祥先生的自传,作品中的孙天俦不是孙世祥本人,而是孙世祥先生的一个理想自我的镜像。孙世祥先生对这孙天俦这一主要角色的文学创造是基本完成了的,这一角色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麦田里的守望者》,《神史》中的孙天俦展示了作者孙世祥先生的心灵史,同时,作者也借助孙天俦的眼睛,用他的心灵作为底片,高灵敏度地为我们描绘下了法喇的社会风俗画卷,法喇的这幅风俗画卷的描绘在《神史》是非常成功的,同时,也是《神史》中最为精彩最有价值的部分。
三、《神史》的农村生活写得真实,留下了无数生动形象的圆形乡村人物形象,而城市生活的表现则十分失真,城里人的塑造面具化、平面化,留下了巨大的遗憾。
《神史》是有两条线索的,一条线索写法喇,一条线索写孙天俦自己的读书、教书、当记者、做北京的公务员,从法喇一步一步由乔麦地、米粮坝、乌蒙、昆明,最后走向京城的道路。
《神史》写法喇这一条线索引人入胜,人物塑造让人过目不忘。如陈福九去读书而最终放弃的一段,读了以后,让人心中久久不能平静,为陈福九想读书努力读书为了读书而做出了巨大努力而失败而心痛,也被陈福九这位美丽、聪明、勇敢的有见识的女性吸引,为她的悲剧命运而悲哀。《神史》中孙江成、孙平玉、孙江才、陈福英、陈福香、孙江华、魏太芬法喇众多的人物的语言心态行为命运震撼悲叹,这些人物凝聚了孙世祥的血水、泪水和汗水,许多人物在当代文学史上有着唯一性。
法喇的风俗画卷是一幅悲剧,虽然这一线索人物众多,人物间的关系复杂,但是人物的情态语言栩栩如生,细节丰富真实,结构宏大,铺陈上的前后照应,难得的是许多细节直入人心,讲述上细致如微,在日常琐事的叙述中展示人物的个别性,大量生活细节为我们还原出法喇生活的真实境况,使人感受到一种确信无疑的叙述力量。法喇人物细节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真实的体验有着巨大的人心穿透力,同时,也是和孙世祥有着相同生命背景的许多人对于一个时代的共同记忆。
《神史》写尽了法喇环境的艰难,物质上的贫困,人心的复杂丑陋,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人性的爱恨善恶交困矛盾,农村基层组织的涣散和权利暴力,人被异化的阴暗悲剧,这里的人们的心理、语言、行为、思想观念和道德标准矛盾冲突得非常厉害,家族的凝聚力一步步演变为窝里斗的内耗力量,书中为我们描述了家族内部各种各样无聊、无休止、无指望的莫名其妙争斗,用网状深邃、立体复杂、尖锐疼痛的矛盾事件,写出了一个贫困农村社会封闭的家族时代悲剧。
而《神史》中写孙天俦自我奋斗的一条线索,时空调动从容,从最边缘、最底层、最贫困的法喇村一层层写到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准备成为反映当今时代的巨幅画卷,构架也是大气磅礴的,但却留下了许多遗憾。总的来说,随着主人公奋斗的足迹,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和环境就越来越模糊,作品中写的荞麦地的人和事不如法喇,写的米粮坝的人和事不如荞麦地,写的乌蒙的人和事不如米粮坝,写的昆明的人和事不如乌蒙,而小说中写的北京就更为模糊了,地理场景和城市环境的描写都有许多问题。
以《神史》中重点写的孙天俦所在的中学和师专的老师们来看,人物众多,但是刻画得让读者糊里糊涂的,有些人物的语言和行为十分雷同,难以分清谁是谁,许多高校教师的生活方式、语言行为和心理状态写得和没有文化的人一模一样。小说中几位和孙天俦发生恋爱情节的女孩子,也写得有许多让人莫名其妙的地方,这些女孩子的性格模糊。造成这种遗憾,是孙世祥没有能走进老师们和这些女孩子们的内心,一些人物和人物的原型比较,甚至是有片面丑化的情况。这一部分有重要价值的是他对我国教育体制的批判,但是这一部分的人物刻画却远远不如法喇村的人物,因为他没有打开心灵去认识城市的现代社会世界。
“《神史》的沉重源于它的真实,真实是一种力量,这种力量像乌蒙山间的雾一样,弥漫在文本中,无处不在。面对乌蒙山区的贫困生活,作者孙世祥先生在创作《神史》时基本没有做艺术处理,而是将生活本身的模样搬进了小说文本。”[5]《神史》现在的许多文本内容是孙世祥为写一部小说的《神史》而收集的生活和民俗素材,他的许多带有材料痕迹的文字,还在等待他加工,一些人物还有矛盾的地方,如小说中孙天主的几位弟弟妹妹们的塑造也没有完成。
作为一部小说的文学作品,《神史》在孙世祥先生自己的眼里,是不成熟的不完美的甚至未成型的,《神史》没有在文学思考的熔炉中完成全部锻炼,没有能够完全升华为以虚构彰显大时代的小说。孙世祥的作品中真正已经完成了文学创造过程的是他的诗歌,同时,从他的现代诗歌和古诗词中也可以看出他是讲究修辞讲究写作技巧的。他是会语不惊人死不休地锤炼自己的作品的,他也是有能力对作品进行进一步的技艺上的锤炼的,从他的诗歌中可以看出在《神史》中他非凡的驾驭语言的能力远远没有发挥。用孙世祥自己的话来说,他还要用至少十年功夫来打磨、修改和补充完善《神史》。
一些评论者把《神史》说成是当代《红楼梦》。这种说法,孙世祥如在世,也不会同意。这种说法首先是降低了孙世祥本人的文学理想文学标准,孙世祥是在攀登文学理想的途中早逝的,如果他还在世,他还要继续攀登下去,而且攀登的路漫长而艰难。如果孙世祥能够完全把《神史》由风俗学、社会学的纪实上升到富有虚构之美的真正的小说,完成小说的前后勾连,人物完整塑造,结构上的整体建构,如老天假以孙世祥时日,《神史》非常可能成为《红楼梦》那样的文学经典,在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一定地位。但是这千古的遗憾终于是无人可以更改了。
[1] 苟元红,孙世祥获2006年度“当代汉语贡献奖” [N],昭通日报,2006年7月4日4版
[2] [4] 孙世祥,神史[M],昆明:云南美术出版社,2004:667-678.
[3] [5]李骞黄玲主编,文学昭通 [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4: 273-280.
(本文系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昭通文学的地域性”阶段性成果。编号2014Y503)
(作者系昭通学院副教授,硕士,主要从事文学、地方史研究)
责任编辑: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