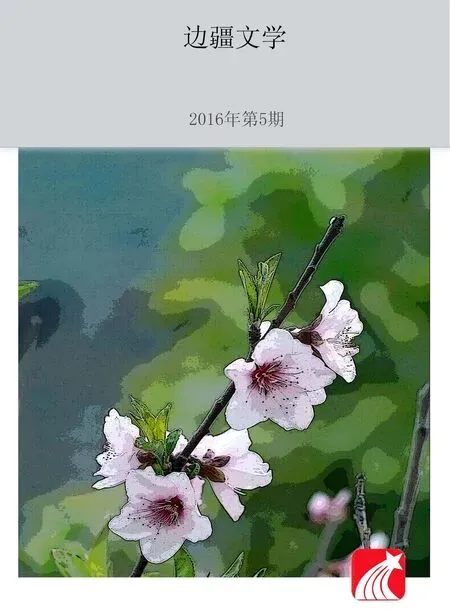诗歌是民族精神之“根”
——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诗歌综论
◎黄 玲
诗歌是民族精神之“根”
——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诗歌综论
◎黄玲
一、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诗歌现状
在这8个民族的文化传统中,诗歌都是表现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重要方式。在一个社会化转型的时代,民族诗歌承担着诸多重任。正如吉狄马加所言:“今天,全人类,包括我们每一个民族,都站在一个现代和传统、历史和未来的十字路口上。每一个民族要想获得自己的通行证,通过这个十字路口,毫无疑问,她的民族历史和文化就是最好的通行证。”[1]通过诗歌这些民族可以向时代发出声音,表达和证明自己的存在。
下面我将把《新时期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作品选集》各民族卷中收入的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诗人的作品进行简要的梳理总结,或许每个民族目前取得的诗歌成就并不相同,但是你可以看到他们都在努力寻找着目标和方向,用诗歌打造着本民族通向现代和未来的文化名片。
1、阿昌族诗歌
“阿昌族卷”共收入12位诗人的24首诗。其诗中最常表现的主题是民族历史文化和对故乡、田园的怀想。从他们的诗歌中,经常可以见到一些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和意象。比如一句“遮帕麻和遮米玛的子孙”就足以概括阿昌族诗歌的文化亮点,体现出一个民族文化上的共性和追求。应该说老一辈诗人在写作上有比较自觉的民族意识,其作品的民族特色也比较突出。因为他们对民族文化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和明确的艺术追求。
曹明强在接受采访时曾经对自己的写作特色有过总结:“我早期的诗着重写我的妈妈、我的大山、我的民族。我们这个民族人数很少,很多人因此心怀自卑,但我要去歌颂自己的民族,让他们对自己的民族产生认同感。这些年来,在政策的支持下,我们民族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提升,大家的民族自豪感被激发出来了。我想,我们的文学作品应该去表现、强化这种心理”。[2]他的诗《蹬起来,窝罗》,既是这种思考的具体实践,也可以视为阿昌族当代诗歌中的优秀之作。对弘扬阿昌族民族文化有很强的艺术感染。
赵家福也说:“阿昌族是一个很弱小的民族,她能够发展到今天,不知走过了多少坎坷路,不知道背负了多少包袱。当 我在作品中反映这些的时候,会有一些辛酸的历史和记忆,会有对整个民族发展的忧虑和期盼。作为这个民族的一分子,这些东西同样体现在我们身上,并通过文字 表现出来。”[3]他的组诗《太阳之恋》由《远古的梦》和《远古的爱》组成,从现代人的视角对天神遮帕玛造天、遮米麻造地,以及创造人类的传说进行了想象和重构,为读者“还原”出远古时期的民族生存景象。和民间诗歌比较,这组诗运用了现代思维和多重视角,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把诗人的自我融入民族历史。诗人回望民族历史的激情能给人一种震撼之感,他和天地对话,和祖先对话的视角已经超越单一的民族界限,上升到对大地上众多生命存在的关怀与追问:“我听见鸟鸣听见祖先说话的声音,远远地昭示源源生命永恒之谜”。诗人的目光所及的太阳,是世界万物的灵魂和源头。
另一位诗人孙家林也对民族历史文化表达过相同的意思:“我比较注重本民族的历史,因为你不懂自己民族的历史,就不会体会到自己民族的文化是深沉的。我自己的作品没有什么花哨,更讲究历史的厚重感。”[4]他的诗歌《我的筒裙花哟》视角很小,选择阿昌妇女身上的筒裙花作为切入点,却并不仅仅只是为了表现某种民族风情,而是有深深的忧思弥漫其中。曾经被视为民族骄傲和自豪感的事物,在诗人现代意识的观照下,有了新的认识和理解,所以他在诗的结尾中发出呼吁:“啊,亲爱的姐妹们,快把砍刀放下。快去接受知识甘露的滋润,来年织出更美丽的彩霞。”
具体到诗歌写作中,民族的历史文化应该由一些具体事物来体现。比如户撒刀既是生活用品,就是一种重要的文化象征,它与阿昌男人已经成为一对密不可分的存在。甚至在女性诗人的笔下,它们也是被歌颂和赞美的对象。朗妹喊的一首诗题目就叫《户撒刀与阿昌人》,她以充满激情的语言表达着对力量和勇气的赞美:“每一个打刀的男人都是乐师”,是赞美阿昌文化中的浪漫主义精神,突显了阿昌文化中的独特审美。“每一个打刀的男人都是一把刀”,则是赞美阿昌族民族精神中尚武和勇猛的历史传奇。这首诗取的是女人的视角,对男性的历史和精神进行了歌颂与升华。但是最后一句诗却把全诗绾收起来,把男人和女人的不可分离表现得非常生动:“阿昌的女人是刀鞘”。无论如何勇猛的男人,只有当他和女人共同创造,不可分离之时,世界才会更加完美和谐。
囊兆东、孙家奇、赵兴源的诗都在表达热爱故乡的主题,但风格上各有千秋。
曹先鹏的组诗《心灵之约》和李伟的组诗《习惯了》,都没有追求民族特色的表达,而是在两性之情的领域去书写主体心灵的思悟,强烈的情感能给读者以感染。文炯贝琶在组诗《月光》中吟唱故乡、亲情,也有军旅生活的投影,内容比较丰富。赵家健的《荷花》属于咏物抒情之作,体现了诗人对生活哲理的思考。其中还有已故诗人孙庭园的一组古诗词作品选,主要写故乡的山水风物,有传统文化的底蕴,虽然民族特色并不鲜明。
“阿昌族卷”中收入的诗歌不是阿昌族诗歌的全部作品,但是已经收入了重要的诗人和代表性作品,基本可以体现出阿昌族当代诗歌的水平和质量。无论诗的题材还是写作风格都比较多样化,民族特色并不是唯一的追求。生活在全新时代的民族诗人们,目光和视野已经变得开阔和多元。但是从总体上看,那些以民族历史文化为题材的诗歌,更有力度和厚重之感,更能体现一个民族的诗歌风格。
2、布朗族诗歌
“布朗族卷”收入5位作者的21首诗歌,从作者队伍上看有一定危机感。
布朗族是一个有着丰富民间文化的民族,生活中流传着很多和茶有关系的古歌和民间歌谣,体现着一个民族的古老历史。但是在现代诗歌的写作中,却面临一些问题和困境,应该引起关注。
“布朗族卷”中收入的21首诗歌,作为布朗族当代文学创史者的岩香南的作品有6首,但基本是民歌的风格。比如《话儿再甜也不能当糖吃》,《问你小妹何方人》,就是民歌体的叙事之作,最初就是收入《中国民间情歌》一书。其余两首《布朗山河换新颜》、《布朗山上如霞似锦》,采用的是新旧对比的视角,表现布朗族生活的巨大变化。另外两首《茶的欢歌》、《茶树之歌》,书写了茶和布朗族的古老历史和亲密关系,民歌风依然明显。
俸春华的《索玛乌》虽然标注为“布朗族史诗”,其实应该是取材于布朗族史诗,是对民族历史的书写和表现。诗的结构比较宏大,内容丰富多姿,但是基本没有脱出民间史诗的框架。他的另外两首诗《月亮·小鱼》和《小鸟》,更有现代诗的特色,主体性比较突出,借月亮和水中小鱼、森林中的小鸟,含蓄地表达了某种深层的复杂情感,能引人遐思。
鲍启铭的《教师勉语》,是对教师职业的歌颂和赞美。没有民族特色,但对教师的职业有生动形象的描绘和赞颂,情感真挚朴素。
陶玉明的诗收入两首,《澜沧江畔走来的精灵》应该是首组诗,其中分别书写了“黑精灵”、“蜂桶鼓”和“故园”,都是对布朗族民族文化的形象表达。诗的意象都和布朗族古老的事物相关,是对历史和传统的追思与怀想,通过它们在诗里营造了浓郁的民族文化氛围,体现了作者对民族的某种责任意识。《山谷中,那五星红旗飘扬的地方》,是对辛勤培育布朗孩子成长的教师的感激与赞颂。
值得一提的还有90后诗人郭应华的诗,他的加入为布朗族诗歌带来了新鲜的气息。他有向民族历史文化学习的自觉意识,在《布朗依依》的组诗里诗里他也和其他诗人一样,尽力捕捉和民族历史有关系的事物和意象,来抒发自己对民族文化的崇敬感。组诗分为三节,分别是“艾洛卜我”、“蜂桶鼓舞”、“恋恋竹筒茶”,每一种事物都是布朗族文化的写意。难得的是郭应华在诗歌艺术上的追求已经达到了某种高度,他的诗和老一辈诗人之间已经拉开很远的距离,可以和当代诗坛接轨和对话。这一点在他的另一组诗《自我抒情》中体现得更为充分。他的诗已经超越民歌体的时代,直接进入现代诗的诗境,体现了比较纯熟的诗艺。
比如来看看《烟波深处的玉蝴蝶》这首:
这个时候,你可能看着季节
也可能眺望远方归航的郎
阳光一束束拍打着
空气,池塘或者是一枚熟透的柿子
看得出隐隐约约的一抹红
此时,我正从柳后经过
一只玉蝴蝶?醉了一湖秋水
有人说时间总是一种巧合
我打扫干净这一石阶
等你上岸
诗中和布朗族的文化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却和人类复杂多变的感觉、心境有关系。玉蝴蝶的意象在诗中翩翩起舞,扇动着时间和思绪。这组诗让人看到了郭应华在诗歌上所达到的高度。作为一名布朗族青年诗人,他在诗歌中的追求同时也提高了布朗族当代诗歌的水平和境界。老一辈诗人们多年来的努力奋斗,为布朗族诗歌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现在已经到了新一代诗人大显身手的时候。
3、德昂族诗歌
“德昂族卷”中数量最多的文体是诗歌,一共收入12位作者的58首诗。这似乎也说明在德昂族当代文学中,成绩最大的文体是诗歌。
德昂族当代诗歌也经历着由民歌体到现代诗的转变过程。老一辈作者们从民间诗歌那里学习,开始写一些民歌体的诗,拉开德昂族书面文学的帷幕。那些今天看起来显得比较简单幼稚的作品,其实承担着为一个民族的书面文学奠基的重任,其意义不容小视。它们体现出的时代感和率真的情感表达,有一种朴素之美。
真正为德昂族诗歌争得荣耀,把德昂族诗歌带上一定高度的,是艾傈木诺和她的诗。她身上有好几个“第一”:第一个德昂族女诗人、第一个出版诗集的德昂族诗人、第一个以诗集获“骏马奖”的德昂族诗人。她的诗让德昂族诗歌真正实现了从民歌体向现代诗的转变过程。虽然身影单薄,后来者寥寥,但以艾傈木诺目前的创作实力来看,是可以为德昂族诗歌的发展起好引领作用的。
4、独龙族诗歌
“独龙族卷”收入的诗歌从数量上看并不少,一共是12位作者的31首诗。对一个人口不到一万的民族来说,已经是一个可喜的进步。
约翰的《独龙桥》是独龙族当代诗歌的奠基之作,以民歌体的形式传达出独龙族人对新生活的喜悦之感。这首诗和新学光的《杜鹃献给来自北京的使者》,是独龙族作者在20世纪80年代发表的仅有的两首作品。其意义自然非常独特。
进入新世纪之后,才有更多的独龙族作者加入到诗歌写作的队伍中来。比如李新明、马文德、巴伟东、李明元、新学先、杨向群、陈建华、陈雪芹、陈清华、曾学光,集合起一支十余人的写作队伍。这个民族的诗歌同样经历着由民歌体向现代诗的转变过程。一些诗人的出现 ,使这种转变成为可能。他们有着新的观念、新的艺术技巧,以及对待世界的不同的态度。他们的诗在民族特色上可能不如老一辈诗人那么突出,但是具有更为广阔的视野和高度。
一批70后诗人是独龙族诗歌的中坚力量。
巴伟东的《独龙招魂曲》,曾学光的《雄鹰之梦》,《独龙江》,陈清华的《苍狼》,陈建华的《独龙江》等作品集中代表了独龙族诗歌由传统诗向现代诗转变的成果,传达了一个民族渴望走向世界,与现代化生活接轨的向往与追求。就像陈建华在《穿越时空隧道》一诗中写的那样:
一条隧道/穿破高黎贡的肚腹/将两个世界连接了起来 /一边是“太古”之民/一边是“现代”文明……
90后诗人陈雪芹的诗体现了新一代独龙族诗人在诗歌艺术上的追求与提升。她的诗并不局限于民族特色的表现,而是以更广阔的目光和视野去探求历史缝隙中的秘密,在诗的观念和技巧上都有一种进步。比如在《仓颉》一诗中,她这样写:“多遥远多纠结多想念多无法描写/疼痛和疯癫你都看不见/想穿越想飞天想变成造字的仓颉/写出能让你快回来的诗篇……”这首诗意象和想象力都非常丰富,在个人情感和历史传说的纠缠中制造了新的审美效果。
从这些青年诗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独龙族诗歌的希望和理想。
5、基诺族诗歌
“基诺族卷”收入8位作者的28首诗歌。
和其他民族一样,基诺族很少有专门的诗歌作者,很多人在小说、诗歌、散文的文体中都有成果,三种文体兼而有之。所以基诺族的诗歌作者队伍年龄结构比较丰富多元,从50后到80后都有出现。
其中罗向明的诗《基诺山,我的故乡》,曾获第五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为基诺族文学带来了荣誉。这是一首抒情性很强的诗,抒发了作者对民族和故乡的一片深情,有浓烈的感染力:
“在那茂密的原始森林里/有一只美丽的翠鸟在飞翔/基诺山/你是我生长的地方/我爱你绿色的原野和美丽的山寨。”“在那茂密的原始森林里/有基诺族的村庄和竹楼/基诺山/你是我可爱的故乡/勤劳善良的基诺人民/正绘制美丽的图画/播种幸福和爱情。”
对基诺山风情和生活的书写,构成了当代基诺族诗歌的主要内容。诗人们开始写作时,那么迫切地急于表达出对民族和故乡的浓厚情感,抒发出对新生活的赞美与感悟。所以他们的诗歌在生活气息和民族风格方面有突出的表现。
比如张志华的诗《雨林中的基诺山》,《思念基诺山》,张云的诗《美在基诺山》,陶亚男的诗《故乡情怀》,书写的就是诗人对民族和故乡的热爱和赞美。比较集中出现的意象如茶园、竹楼、云海、太阳鼓……构成了基诺山的基本审美意象。诗人们在努力建构和创造着属于本民族的诗歌形象。
此外的一些诗跳出民族和地域性书写,在人类情感和心灵世界的丰富方面有所探索,拓展了基诺族诗歌的表现范畴。如陶润珍的短诗《小鸟飞走的时候》,只有8行,但对女性情感的描写却有其独到之处:
小鸟飞走的时候/江边的芦苇摇动着/你走过身边的时候/我的心颤抖着。
人不在林中的时候/知了鸣叫着/你不在眼前的时候/我轻轻呼唤着。
这首诗写得轻盈而空灵,传达了朦胧美好的少女情怀。
张志华的诗题材范围比较广泛,除了民族和故乡他还写军营、写人的情感的丰富性。《英烈之魂》就是对全国缉毒英雄的赞美。
基诺族诗歌已经有了很好的发展基础,但还期待着代表性诗人和作品的出现。培养年轻一代诗人,让他们尽快成长起来是当务之急。
6、景颇族诗歌
“景颇族卷”收入16位作者的56首诗,其作者和诗歌数量在8个民族中居于前列。其题材和表现形式都比较丰富,体现出比较成熟的诗歌风格。
书写故乡和民族,仍然是景颇族诗歌的主要特色。站在故乡的土地上开始写作,这是一种自然的选择。诗人和故乡永远是一种水乳交融的关系。而景颇山这个故乡同时也是民族生活的地方,是民族文化生长聚集的土地。所以,在诗人们的笔下和诗行中,景颇山、目瑙纵歌都是无法绕过去的存在,也是非常重要的文化意象。穆直·玛撒的《目瑙抒怀》《在等戛山》,木然·麻双的《目瑙曲》《宁贯瓦》,木然·诺相的《景颇人》,龙准·勒排早当的《瑞丽情怀》等诗中,民族历史和文化传统是诗歌表现的重要对象。诗人们通过书写,希望重新建构和夯实民族文化的根基。这是一种自觉的诗歌意识。
也有一些诗人绕开这些已经固化的内容,寻找着诗歌的突围方向。他们的诗歌体现出更加多样化的风格。比如岳丁的诗,就体现出强烈的现代性色彩,在人性的世界努力探索。他的诗写《人论》,写《冬妮娅,我想去筑路》,还写《星期六的思想》、《树上的鱼》:“树上的鱼翘着尾巴/身子忽闪忽闪/声音忽闪忽闪/目光忽闪忽闪/没有固定的眼睛/羞花闭月,躲躲闪闪/我迷恋这种气质。”这样的诗拓展了景颇族当代诗歌的领域,也提升了景颇族诗歌的品质。
景颇族女诗人群体的出现也值得提及。“景颇族卷”的诗歌部分收入了一批女诗人的作品,分别是勒普·创藏坤努、勒王·果鲜、恩昆·宽宝、恩昆·麻保、恩昆·玛芳、梅合东、梅何·木瑟等人。她们已经构成一个女性诗歌群体,这在景颇族诗歌史上是一件值得赞颂的事。在8个人口较少民族中也是唯一一个形成女性诗歌群体的民族。 她们的诗清新活泼,生动细腻,在情感表达上有自己的特色。而且性别意识在诗歌中也体现出觉醒的倾向。勒普·创藏坤努的一首诗就名为《我是女人》,对自己的性别身份并不避讳:“我是女人/一个很平凡的景颇女人/一个只有你爱着的淳朴的女人。”她的诗写自我,写母亲和奶奶,对女性的性别身份有明确的认知和理解。90后诗人勒王·果鲜的诗《突然在某一天遇到了你》在情感表达上轻盈而空灵。恩昆·宽宝的《思念》中的情感则是强烈而深沉的倾诉。梅何·木瑟的《一个你,一个我》,在爱情中寻找着哲理。这些女诗人的出现,在景颇族诗歌史上绝对是一个值得书写的事件。
7、普米族诗歌
“普米族卷”中收入15位作者的119首诗。其诗歌数量在8个民族中居于首位,体现了普米族在诗歌文体上的重要收获。其中已故诗人何顺明的《啊,泸沽湖》,获得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为当代普米族诗歌揭开了序幕。诗中抒发着对故乡、祖国的宏大情怀:
“啊,泸沽湖——生我养我的慈母
多像一颗晶莹的宝珠
闪亮在祖国的胸脯。”
近年来普米族已经成长起一支比较成熟的诗人队伍,在全国性报刊上发表了很多有影响的诗作,所以他们不仅在云南,甚至在全国诗坛都有一定影响力。这对一个只有三万多人口的民族来说,是一个文学奇迹。
其中殷海涛的诗对民族历史文化比较关注,他的叙事长诗《神奇的花鸟》就取材于民间题材,可以视为诗人对民族文化的学习和吸收。鲁若迪基、和建全、和文平、曹翔,这批60后诗人的诗成功实现了与现代诗的对接,他们的诗已经摆脱民歌体的影响,在思想性和艺术性上都有很大的提升。
鲁若迪基的诗歌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没有比泪水更干净的水》(后来成了他一部新诗集的名称)。它以深沉的情感表达和浓郁的诗意传达了诗人对故乡刻骨铭心的爱恋,读来令人感动。“人口较少民族”这个概念对鲁若迪基写作心理的影响是潜在而深远的,这在“人口较少民族”的诗人中是一个特例。他有诗人的敏感与自觉,也有哲人的缜密与多思。所以他的诗既关注世界上“大”的事物的壮丽与雄伟,更在意“小”的事物的丰富与生动。《小凉山很小》是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诗人在诗中探索着关于“大与小”的哲理表达。
和文平的诗对民族的历史文化有深入思考和表现,他在《白色的河流》、《送魂线》、《阿妈的头帕》《穿裙子的年龄》等作品中,对普米族文化有细致表现。其诗风深情、悠扬,为一个民族吟唱着最动情的歌谣。和建全在《祭祖节》中,渴望与祖先的心灵对话,其实是对民族精神的溯源,以诗歌寻找民族的灵魂。曹翔的诗在描写到故乡和民族的相关事物时,流淌出一种圣洁的忧伤感。类似于“闪着泪花的星星”这样的意象在他的诗里制造出一种浪漫的风格。他的诗写故乡和民族,但更注重主体心灵对历史的感受,现代精神和审美意识提升了他诗歌的品质。
70后的诗人以蔡金华为代表,他的诗中有一些关于人生和命运的思考,比如《南方本土》、《放飞十月》、《雏鸟》,借自然之物思考着世界的哲理。他的诗中还有亲情、民族和大地,展示着诗人和世界的亲密关系。
80后的诗人中戈戎比措的诗体现出很好的势头,他迄今已在《民族文学》等全国性报刊发表作品多首,他的出现喻示普米族诗歌后继有人。他的诗有着80后的特色,和民族、历史的关系不如60后、70后诗人那么紧密,其诗风体现出更开阔、高远的视野。他擅长用创造性想象对民族生活内容进行拓展,从更高的角度来抒发人和世界的关系。在《黄昏的随想》、《秋日随想》中透露了他的诗追求表达的是:“一切爱恋与歌唱/一切背叛与忠贞/一切火塘里涌动的悲悯。”他的诗里也出现高原、山野、神鹰等事物,但并不指向具体的民族,而是借诗歌创造出一个神性的世界。如他在《高原之神》中所宣称的:“而一路高歌的我/是大地的王者/是那片高原上神话和梦幻的孩子。”和戈戎比措的王者霸气相比,同为80后的曹媛的诗写得更舒缓明丽,有女性特色。她写故乡、亲情,情感表达如同小溪淙淙。
普米族当代诗歌的实力和后劲,正是通过这些诗人的努力得到体现。
8、怒族诗歌
“怒族卷”收入12位作者的34首诗。从整体上看,当代怒族诗歌还处于发展阶段,前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从整体基调上看,怒族诗歌是积极向上的,表达了一个民族的诗人对故乡、民族的深厚情感,以及对生活的理想和信念。已故作家罗世富的《怒江情》,施玉英的《怒苏情韵》,李金荣的《故乡感怀》、《石月亮》,李铁柱的《心灵歇息的地方》,陈军的《阿茸》,都是对怒江山水和怒族历史文化的追溯与赞颂,充满令人感动的情韵。地域和民族特色比较鲜明,让人感受到了一方山水养一方人的哲理。
还有一些青年作者在尝试着书写生活的思考与感悟,角度和题材比较广泛。比如刘文青的《青春短笛》,桑梅芳的《离别》,胡永春的《墙角的兰花》等等,他们书写的是生命深处柔软而宝贵的感受和体验,虽然没有突出的民族和地域特色,但同样是对人类精神之域的探索与表达。只是在诗的艺术性方面还需要努力。
以上对8个民族各卷中收入的诗歌作品进行研究的简要的梳理和归纳,因为历史和文化的原因,每个民族在诗歌上所取得的成就各不相同,但是都在努力学习和写作,争取在当代诗歌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诗人应该站在时代前沿,用自己的诗歌来表现生活,让人们通过诗歌看到一个民族的精神。从这个角度上看,他们的作品是成功的。他们的作品体现了民族文学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当然,如果要通向更高的高度,每个民族的诗人都还需要继续努力。
二、诗歌的焦虑与坚守
统观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诗人的创作,有的已经在民族文化传统的学习与继承方面作出了可喜的探索,写出了优秀的作品。有的还在传统的门前徘徊游走,寻找着入门之径。但随着写作的深入,他们总归会被民族文化的魅力所吸引,走上回归之路,为传承、坚守民族文化而努力。
所谓坚守,意味着对诗歌怀有不可催折的信念,以执着的精神为之努力。对一个民族来说,诗歌是精神的号角,是传承民族文化的重要途径。但是在一个经受着商品经济浪潮冲击的时代,诗歌也面临种种困境,需要诗人以坚韧的精神去守望自己的精神信念。
一些敏感的诗人的作品中已经体现出明显的文化焦虑感,所以他们的诗歌中有强烈的精神诉求感。独龙族诗人巴伟东的《独龙招魂曲》就是一例。他在诗的结尾吁叹着:“魂魄啊,魂魄,我的魂魄/归来……”他所呼唤的不仅仅是诗人个体的魂魄,更是民族文化的魂魄。普米族青年诗人戈戎比措也在诗中发出质疑:
“群山以怎样的方式伫立?
灵魂的方向
是否刻满荆棘?”
人口较少民族的诗人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都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意识,肩上承担着民族诗歌发展的重任。这种焦虑感体现在对一些承载着古老意蕴的事物上面,比如“我的猎枪已蒙上厚厚的尘土/搁置在寂寞和清冷中”(和建全《我的猎枪》)。进入城市的诗人,对故乡总会怀有一种失落和惆怅的心态:“而我/是故乡的一根草/在城市的霓虹灯下/无根无迹地飘着。”(勒普·创藏坤努(《梦里故乡》))。类似的情绪在一些诗人的作品中时隐时现,暴露了他们内心深处的焦虑与迷惘。诗歌是可以招魂的,既为诗人自己,也为民族文化的复苏。
责任感越强的诗人,文化焦虑感会越沉重。如果能在此基础上坚持思考与追问,必定会对他的诗歌写作形成一种动力,使诗的境界和内涵得到提升。如一位评论家所言:“在转型社会里,诗人就是在了解历史和现实的背景中,为社会的进步与成长,去探寻真相,让大众明晓自己的处境,以及对未来的憧憬,这或许才是有希望的写作。”[6]直面现实的写作对民族诗人来说,也是一种新的机遇和挑战。用诗歌的方式为自己民族的发展进步吹响号角,这是诗人不可推辞的责任和义务,也是诗人的光荣。
诗歌的坚守除了需要诗人有自觉的责任意识外,还需要诗人建立起自觉的“精品意识”,在诗歌的写作上多出力作。因为只有真正的艺术作品才能打动读者,把思想和艺术的美感传递给更多的人。
【注释】
[1][5] “诗,时代涌动的悠远回声——对话诗人吉狄马加”,2013年09月11日 人民日报。
[2][3][4] 保护阿昌族共同的精神家园——当代阿昌族作家访谈。来源:中国作家网2013年08月07日。
[6] 刘波.“直面现实、历史与传统的新格局”,2014中国诗论精选。
本文为2015年度中国作协少数民族作家重点扶持项目成果之一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云南民族大学教授)
责任编辑: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