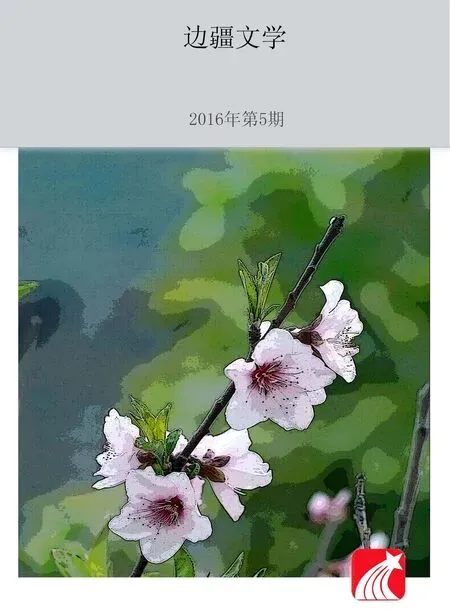苏雪林的文学批评思想
◎叶向东
学人观点
苏雪林的文学批评思想
◎叶向东
主持人语:苏雪林是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著名女作家,但同时亦是一个具有鲜明个性的批评家。叶向东教授的论文通过具体案例的分析,阐述了苏雪林对李金发、张资平、郁达夫文学创作的品鉴,从深刻性、尖锐性、情感性三个方面总结了苏雪林的批评个性和批评特点,为我们认识这个女作家提供了另一窗口。黄玲
教授的论文是对云南8个人口较少民族诗歌创作的概述。作者花了一定精力作资料收集和梳理,对这8个民族的诗歌创作现状有较具体的介绍,为我们了解这8个民族的创作提供了基本资料。(胡彦)
苏雪林不仅是现代著名的女作家,有散文集《绿天》、《青鸟集》、《屠龙集》、《蝉蜕集》、《归鸿集》、《天马集》、《欧游揽胜》、《闲话战争》、《秀峰夜话》,长篇小说《棘心》,传记文学《南明忠烈传》,戏剧《鸠那罗的眼睛》,诗集《灯前诗草》,译著《一朵小白花》、《梵赖雷童话集》等文学创作,而且她还是一位具有独特个性的文艺批评家,有《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蠹鱼生活》、《唐诗概论》、《辽金元文学》、《中国传统文化与天主古教》、《昆仑之谜》、《我论鲁迅》、《屈原与<九歌>》、《<天问>正简》、《楚辞新诂》、《试看<红楼梦>的真面目》、《文坛话旧》、《中国文学史》、《民国二三十年代作家》、《屈赋新探》等文艺理论著作。她的文学批评思想对中国现代文学和现代文学理论具有重要的影响。
一
对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创作的批评表现了苏雪林文学批评思想的深刻性。
苏雪林是较早评论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的文学批评家,并深刻阐述了李金发诗歌的特点及其在现代诗歌史上的意义。她在《论李金发的诗》一文指出:“在新诗人中李金发虽不算什么大家,但他作品产量最丰富而又最迅速,一九二零至一九二三年出《微雨》,一九二六年出《为幸福而歌》,一九二七年出《食客与凶年》,都是厚厚的集子。虽然翻开那些诗集只看见单调的字句,雷同的体裁,似乎产量虽多并没有什么稀罕,但近代中国象征派的诗至李氏而始有,在新诗界中不能说他没有相当的贡献。”[1]她对李金发及其象征主义诗歌的评价是非常客观和理性的,在研究文本的基础上对其特点给予了精细的分析。苏雪林认为李金发的诗歌的具有朦胧的特征。这也正是象征派诗歌的特色。李金发最钦佩的是法国诗人魏尔仑。魏尔仑认为,诗不过是音乐,须有优美的韵脚,但措辞不必过于明确。诗是诗人的感觉,爱憎,希望,绝望等奔放的表现。言语要打破古典的规则,只讲究诗歌内部的旋律之感,诗学的第一原则是音乐超于一切。李金发在《微雨》自序中写道:“中国自文学革新后,诗界成为无治状态,对于全诗的体裁或使多少人不满意,但这不要紧,苟能表现一切。”苏雪林认为:“李金发的诗没有一首可以完全教人了解。”[2]她并没有经过有意的选择,而是从《微雨》中随手翻出《生活》一首为例:
抱头爱去,她原是先代之女神,
残弃盲目?我们唯一之崇拜者,
锐敏之眼睛,环视一切,
沉寂,奔腾与荒榛之藏所。
君不见高邱之坟冢的安排?
有无数蝼蚁之宫室,
在你耳朵之左右,
沙石亦遂消磨了。
皮肤上老母所爱之油腻,
日落时秋虫之鸣声,
如摇篮里襁褓之母的安慰,
吁,这你仅能记忆之可爱。
我见惯了无牙之颚,无色之颧,
一切生命流里之威严,
有时为草虫掩蔽、捣碎,
终于眼球不能如意流转了。
在苏雪林看来,这首诗“分开来看句句可懂,合拢来看则有些莫名其妙。但它也不是一首毫无意义的作品,不过文字不照寻常习惯安排,所以变成这样形象罢了。又诗虽难解,而音调则甚和谐,有训练的耳朵可以觉出它的好处。”[3]这样,在中国新诗史上开始下起朦胧的“微雨”。苏雪林认为李金发的诗歌具有敏锐的艺术感觉。诗人、艺术家的感觉比一般人更加灵敏,音乐家的耳朵,能听到常人听不到的声音,画家的视觉,能看见常人看不见的色彩。李金发的诗具有视觉的敏感:“一个膀臂的困顿和无数色彩的毛发”,“以你锋利之爪牙溅绿色之血”,“绿血之王子,满腔悲哀之酸气”。还具有听觉的敏感:“黑夜与蚊虫连步徐来越此短墙之角,狂呼于我清白之耳后,如荒野狂风怒号,战栗了无数游牧”。李金发不仅感觉敏锐,幻觉也异常丰富。苏雪林指出:“《小乡村》想象其在原始时代时荒榛伏莽、巨兽纵横的光景,大加描写,历历有如亲睹,想也与幻觉作用有些连带关系。李氏有《诗人》一诗云:‘他的视觉常观察遍万物之喜怒,为自己之欢娱与失望之长叹。执其如椽之笔,写阴灵之小照和星斗之运行。’恐怕他正在拿感觉异常,幻想丰富自傲呢。”[4]苏雪林认为,李金发的象征主义诗歌充满了感伤与颓废的色彩。李金发的诗歌中“恸哭”、“悲哀”、“忧愁”、“恐怖”等词汇不可胜数。“我有一切的忧愁,无端的恐怖”,“无量数的伤感在空间摆动,终无休止也无开始之期”,“我仰头一望不能向青春诉我的悲哀”,“我仗着上帝之灵,人类之疲弱,遂恸哭了”,“耳后无数雷鸣,一颗心震得何其厉害,我寻到了时代死灰了,遂痛苦其坟墓之旁”,“流星在天心走过,反射我心头一切之幽怨”。观念联络的奇特是李金发诗歌艺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李金发的诗歌如“弃妇之隐忧堆积在动作”中的“堆积”,“衰老之裙裾发出哀吟”中的“衰老”,“脉管之跳动显出死之预言”中的“预言”,“一二阵不及数的游人统治在蔚蓝天下”中的“统治”,“隔树的同僚也一齐唱歌了”中的“同僚”。李金发把看似没有内在联系的观念连接在一起,具有令人惊奇的效果。苏雪林以李金发的诗歌《自题画像》为例,对李金发诗歌中的省略特征进行了批评。“这就是做象征派诗的秘密,我不妨在这里揭破它。原来象征派诗人所谓‘不固执文法的原则’、‘跳过句法’等等虽然高深奥妙,但煞风景地加以具体的解释不过应用省略法而已。旧式所谓起承转合虽不足为法,而每一首诗有一定的组织,则为不可移易之理。但象征文学的作品则完全不讲这些的,第一题目与诗不必有密切关系,即有关系也不必粘着做。行文时或于一章中省去数行,或于数行中省去数语,或于数语中省去数字,他们诗之暧昧难解,无非为此。”[5]
二
对张资平情爱小说创作的批评表现了苏雪林文学批评思想的尖锐性。
对张资平、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及其文学创作提出尖锐的批评,是苏雪林文学批评思想的一个突出特征。苏雪林认为,张资平小说是以为故事而写故事为目的的,所以其小说有教人不得不读完的魔力。文笔清新,结构虽然单调,但独具匠心。《木马》、《约伯之泪》、《不平衡的偶力》及《公债委员》等小说算得上是优秀作品。但在《多角恋爱小说家张资平》中对张资平的其他小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他的多角恋爱小说其实做得不好。第一,人物都像郁达夫式的表现,有病态的倾向,女主角尤甚。”[6]她认为张资平小说中的人物形象不仅是病态的,而且是模式化的。小说的主人公是女性,小说的故事情节是女性的恋爱生活,女性都是都市的少女,早熟、性感,欲望强烈,喜欢享乐的生活,喜欢壮美的男性,情感丰富,不受理智的控制,导致悲剧的结局。“总是女子性欲比男子强,性的饥渴比男子甚,她们向男子追逐,其热烈竟似一团野火,似乎太不自然,太不真实。以《最后的幸福》为例,即可看出他的缺点。这部书大体像模仿法国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女主角美瑛初以选择丈夫的条件太苛,遂致蹉跎青春,精神大受挫折,后与年已四旬、身体久被烟酒淘虚了的表兄士雄结婚,深感性的烦闷;与包法利夫人嫁了Charles Bovary后,感到平凡猥琐的人生打破了她早年在修道院里得来的美丽神秘的浪漫憧憬,因而郁郁不乐相似。美瑛后来与妹夫广勋,旧情人松卿,士雄前妻之子阿和,少时竹马伴侣阿根都发生恋爱关系,终被松卿所弃,且以传染梅毒死于医院;与包法利夫人恋爱的书记雷翁及地主坡郎齐借债挥霍,终以逼于债务服毒自杀相似。但福氏乃外科医生之子,禀有长于诊断和分析的医生的头脑,所以他的小说有生理学病理学上种种根据。他写包法利夫人‘性的忧郁’由无而有,由浅入深,有步骤,有层次,她最后自杀的悲剧则是‘必然的’的结果,一毫没有矫揉造作之处。张氏写美瑛‘性的忧郁’则错杂混乱,一开头便似疯狂,收局的悲剧又是‘勉强的’,他想学福氏,真是东施效颦愈增其丑了。”[7]张资平小说中的女性人物形象是模式化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女性对男性的追逐,三角四角恋爱的纠葛。《不平衡的偶力》中的女主角玉兰追逐均衡;《飞絮》中的女主角云姨追逐梅君;《公债委员》中的女主角玉莲追逐陈仲章。这种女性对男性的追逐,在其小说中具有普遍性和典型性。张资平小说中的男性人物形象则没有爱,只有性欲,并且残暴。“他的小说中男主角大都是一位家庭的暴君,就是当他在表白忏悔之时,我们也看不出这位作家的可爱处。这位男性过强具有残酷天性的人,无疑是作家自己的影子。”[8]《上帝的儿女们》中的余约瑟与《公债委员》中的陈仲章身世相似;《雪的除夕》与《小兄妹》结构雷同。苏雪林认为“张资平虽然自称为新文学作家,但他专以供给低级的趣味、色情或富于刺激性的题材,娱乐一般中等阶级因而名利双收为宗旨。”[9]苏雪林认为,作品的风格反映了作家的品格。“作者气量偏狭无容人之量,略受刺激必起反感,亦其品格欠涵养之一端。他自被人揭破了在家里‘秘密开小说商场’的黑幕之后,恼羞成怒,对于那些攻击他的人,动辄报以谩骂。外间谣传他作小说颇赚了些钱,置有洋房产业。他于是写了一部《明珠与黑炭》形容自己如何的潦倒穷困,直到了令人难以相信的程度。……这类于人无损于己反失尊严的牢骚,在《糜烂》、《天孙之女》、《脱了轨道的星球》中也发得不少。郭沫若和郁达夫也有此病。他们说话本粗鄙直率,毫无蕴藉之致,骂人时更如村妇骂街,令人胸中作三日恶。这几个创造社巨头似乎都带有岛国人的器小,凶横,犷野,蠢俗,自私,自大的气质,难道习俗果足以移人么?”[10]张资平在小说中丑化日本人,这种创作情绪蕴涵着阿Q式的精神胜利的成分。“譬如他憎恨日本人,对日本人没有一句好批评,作《天孙之女》乃尽量污辱。其人物名字也含狎侮之意:如女主角名‘花儿’又曰‘阿花’,其母与人私通偏名之曰‘节子’;其父名曰‘铃木牛太郎’,伯父则名‘猪太郎’。”[11]苏雪林认为,张资平的小说中过多运用了科学术语。在他的处女作同时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冲积期化石》中就运用了很多科学术语,让读者的阅读感受不太流畅。“这河的两岸也受了不知多少次的洪水浸洗变成一个很规则的河成段丘。”用了地质学的术语;“我像一块均质性的破碎石片无论你拿什么强度的十字聂氏柱来检查我,都不能叫我发生别种颜色。”用了心理学的术语;“申牧师此时气得几根鼠须倒竖起来,脸色像按着光色带的顺序,由红转黄,由黄转青。”用了物理学的术语;“她头上两条乳锁头筋只有一层苍白的薄皮包裹着。”用了生理学的术语;“是一种属柳叶菜科的植物,日本人称它做月见草。”用了植物学的术语;等等。“他在日本是研究日本地质学的,所以后来作品,别的科学名词虽略见减少,地质学名词则仍然是摇笔即来。这种‘掉书袋’的坏习惯殊不足取。”[12]苏雪林认为,张资平的小说具有浓厚的反基督教色彩。《冲积期化石》、《约伯之泪》、《公债委员》、《约檀河之水》等小说描写了教会的腐败和内幕。对教会的讽刺和打击在《上帝的儿女们》中表现得极为鲜明。小说中的男主角余约瑟穷苦出身,以善于逢迎美国传教士得到牧师地位。但他表面虽十分虔诚,暗中却与K夫人私通,并生一女儿。后来娶了已经怀孕的金恩。美籍主教爱恋中国女郎而致怀孕打胎。教友们偷偷摸摸抽大烟私贩烟土等等。“基督教徒固未必个个善良,而像这样丑态百出则亦未必。有人批评左拉作品为‘野兽的喜剧’,其实左拉小说人物尚有人性,如张氏之所作,则真是‘野兽的喜剧’了!”[13]
三
对郁达夫自叙传抒情小说创作的批评表现了苏雪林文学批评思想丰富的情感性。
苏雪林对创造社作家的不满非常明显:“在文艺标准尚未确定的时代,那些善于自吹自捧的,工于谩骂的,作品含有强烈刺激性的,质虽粗滥而量尚丰富的作家,每容易为读者所注意。所以过去十年中创造社成为新文艺运动主要潮流之一;夸大狂和领袖欲发达的郭沫若为一般知识浅薄的中学生所崇拜;善写多角恋爱的张资平为供奉电影明星玉照捧女校皇后的摩登青年所醉心;而赤裸裸描写色情与性的烦闷的郁达夫则为荒唐颓废的现代中国人所欢迎。”[14]郁达夫在1921年出版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沉沦》,引起了文艺界的猛烈批评,苏雪林就是对郁达夫的小说创作进行批评的代表。但当时著名的文艺批评家周作人却写文章为郁达夫的小说进行辩护,“虽然有猥亵的分子而并无不道德的性质”,是“一件艺术的作品”。[15]郭沫若认为:“他那大胆的自我暴露,对于深藏在千年万年的背甲里面的士大夫的虚伪,完全是一种暴风雨的闪击”,“这种露骨的率真,使他们感受着作假的困难。”[16]文艺界的争论,使郁达夫的名声大震。但苏雪林对郁达夫的小说创作提出了强烈的批评:“郁氏的作品,所表现的思想都是一贯的,那就是所谓的‘性欲’的问题。本来‘性’是人类一切情欲中最基本的一个,像弗洛伊德所说竟是情感的源泉,能力的府库,整个生活力的出发点,抓住这个来做谈话和写作的题材,决不怕听者读者不注意。何况中国民族本如周作人所说多少都患着一点‘山魈风’,最喜谈人闺阃和关于色情的事情,对于这些蒙着新文艺外衣的肉麻猥亵的小说……哪有不热烈欢迎之理?况且郁达夫的作品尽量地表现自身的丑恶,又给了颓废淫猥的中国人一个初次在镜子里窥见自己容颜的惊喜。”[17]苏雪林认为郁达夫小说中的性表现是病态的。郁达夫吸收了日本私小说的创作特点和现代主义小说的手法,偏重于暴露个人私生活中的灵魂与肉体的冲突和变态性心理,作为向旧道德旧礼教进行批判的艺术手段。《沉沦》中的自渎、窥欲,《秋柳》、《寒宵》中的嫖娼宿妓,《茫茫夜》、《她是一个弱女子》中的同性恋、畸形恋等缺少节制描写,可以看作郁达夫对社会和时代的一种畸形的反抗。郁达夫强调人的情欲在表达人的内在世界的重要性,从新的角度剖析人的生命和性格中与生俱来的情欲。他受到西方人道主义特别是卢梭的返归自然思想的影响,受到日本佐藤春夫、田山花袋、葛西善藏等作家的私小说颂欲思想的影响,主张人的一切合理欲求的自然发展,认为情欲作为人的自然天性应该在文学中得到审美观照和审美表现,他大胆地以自身为对象,在小说中通过性、性变态和同性恋叙事来阐释情爱生死的主题,对虚伪的传统道德观念进行批判。“不过郁氏虽爱谈性欲问题,而他所表现的性的苦闷,都带着强烈的病态,即所谓‘色情狂’的倾向者是,这是郁氏自己写照而不是一般人的相貌。像《沉沦》中的主人公一见女性呼吸就急促,面色就涨红,脸上筋肉就起痉挛,浑身就发颤,还有其他许多不堪言说的情形,这是一般青年所有的么?《夜茫茫》里的于质夫到小店女人处买针买帕回来自刺等等可笑的行为,又是普通男子感到性欲无可发泄时的情况么?这些地方若用自叙体的文字来写,我们无非说作者生理状态异乎常人而已,若用他叙体并声明这可为现代青年的典型那就大大地错了。小说贵能写出人类‘基本的情绪’和不变的‘人间性’,伟大作品中人物的性格虽历千百年尚可与读者心灵共鸣:郁氏作品中人物虽与读者同一时代,而已使读者大感隔膜,岂非他艺术上的大失败?”[18]苏雪林认为自我主义、感伤主义和颓废色彩是构成郁达夫小说的主要元素。郁达夫在小说中抒发主人公的苦闷情怀,紧紧抓住青年知识分子的生理的、心理的病态,描写由此产生的颓废言行和变态心理,指出青年病态的制造者是病态的社会,从中揭示出社会和时代的病态。“他的作品自《沉沦》到最近,莫不以‘我’为主体,即偶尔捏造几个假姓名,也毫不含糊的写他自己的经历。像《茫茫夜》里的于质夫,《烟影》里的文朴……谁说不是郁达夫的化身?郁氏曾说:我觉得‘文学作品都是作家的自叙传’是千真万真的。”[19]郁达夫的小说大多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事,以自我的个人经验和情感体验为线索,比如《茑萝行》、《青烟》、《春风沉醉的晚上》、《薄奠》、《过去》、《迷羊》等,写的就是叙述者自己的体验,具有郁达夫的精神气质,即使采用第三人称进行叙事,比如《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茫茫夜》、《采石矶》等,小说的主人公仍是作者自己的化身。“像郁达夫的自我表现,如其说他想踵美西洋,特意提倡这一派文学,勿宁说他艺术手腕过于拙劣,除了自己经历的事外便想象不出来罢了。他说没有这一宗经验的人决不能凭空捏造做关于这一宗事情的小说,所以没有杀人做贼经验的人不能描写杀人做贼。”[20]苏雪林认为,感伤主义是世纪病所给予现代文人的一种歇斯底里的病态。郁达夫以伤感的抒情为主线,注重抒发主人公郁郁寡欢、孤独凄清的情怀,坦诚率真地表现和宣泄人物感伤、悲观及颓废厌世的心境。其小说中的主人公大都是灰白色脸庞,高高的颧骨和深深下陷的眼窝,眼窝外必带一层黑圈,终日无缘无故自悲自叹,见了晓林薄雾,眼里会涌出两行清泪,对着平原秋色又会无端哭了起来,回答日本下女自己是支那人时,又感触至全身发抖而滚下眼泪。这种主观夸张的抒情,苏雪林却并不认可:“我们看起来那些事实不值得落泪发抖的,而作者却非如此写不可,那只好说作者自己神经有病了。不过自己神经有病,竟叫小说中人物也个个患着神经病,不知小说中‘个性’为何物。这样作家,居然在中国文坛获得十几年的盛名,批评家太不尽他的义务呢?还是读者太容易欺骗呢?”[21]郁达夫的民族自尊、性苦闷和沉沦的内心世界,在小说中化为激愤的控诉,大胆的暴露,无所顾忌的伤感,这种宣泄缺少理性的过滤,影响了小说的深刻性。苏雪林认为,小说人物的行动没有心理学上的根据,是郁达夫作品的突出缺点。
苏雪林的文学批评思想具有独特的历史价值,其突出的特点主要表现为微观的实用批评,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展开深入细腻的分析。她对李金发象征主义诗歌的客观理性批评所达到的深度和广度,后人的批评没有明显的超越。她对张资平的情爱小说和郁达夫的自叙传抒情小说的批评具有情绪化的特征,深刻性和片面性同时并存,表现了一个女性批评家天生的好恶和独特的气质。
【注释】
[1][2][3][4][5][6][7][8][9][10][11][12][13][14] [17][18][19][20][21]苏雪林:《苏雪林代表作》,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275页,第276页,第277页,第279页,第281页,第289页,第289页,第291页,第288页,第291页,第290页,第293页,第293页,第300页,第300页,第301页,第302页,第302页,第303页,第304页,第306页。
[15]周作人:《沉沦》,《晨报副刊》1922年3月26日。
[16]郭沫若:《沫若文集》第1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47页。
(作者系云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程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