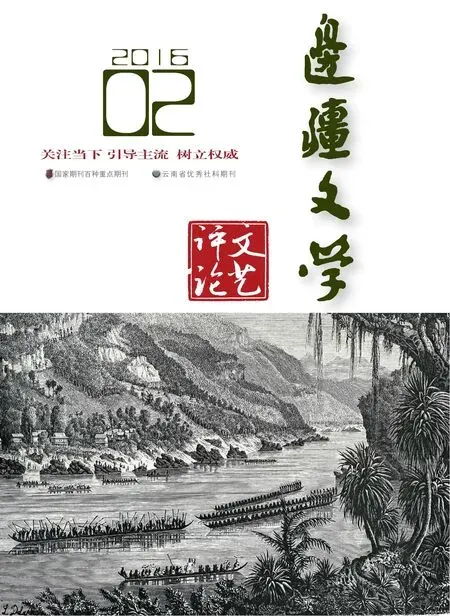舞剧《诺玛阿美》感受
——兼谈未来舞蹈艺术创作趋向
◎疆 嘎
舞剧《诺玛阿美》感受
——兼谈未来舞蹈艺术创作趋向
◎疆 嘎
再看红河州舞剧《诺玛阿美》,又有了新的感受,导演把序“南迁南迁”、第一幕“烽火狼烟”和第二幕“重建家园”进行了结构性调整,序和第一幕就把迁徙,战争和埋兵器等情节一气呵成的讲完,在第一幕父亲死去时送葬及第二幕重建家园里,新增加了打磨秋等哈尼族的传统民间文化样式,并把哈尼族传统民族民间舞蹈样式巧妙的镶嵌到剧目之中,我们感受到了棕扇舞的悲悯,图腾舞的狂野,木屐舞的俏丽,栽秧舞的欢快及摸奶舞的乐活,舞段把情绪渲染的严丝合缝竟毫无违和感,调整过后的叙述更加紧凑和凝练。
舞剧《诺玛阿美》源起于哈尼人的口述史诗,它通过贝玛的口述再现了哈尼人迁徙的艰辛历程,舞剧以哈尼部落的头人纳索一家率领着族人迁徙、生存、繁衍的这样一个故事为线索,以一种小中见大的叙述方式,讲述这个族群生存、发展和繁衍并与统治阶层抗争、妥协和再度抗争、迁徙的故事,哈尼人的族群历尽千辛万苦,以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最终抵达了自己的生存家园和心灵家园,也就是他们心中的诺玛阿美红河南岸。他们通过辛勤耕耘创造了千年农耕文明的辉煌成就——哈尼梯田。主人公纳索从一个鲁莽的青年,到一个迷茫的头领,再到一个顽强的百折不挠的斗士,这个转变的过程浓缩了一个族群的奋斗史,这个奋斗史的形成也离不开以戚姒为代表的一群坚韧不屈、耐力十足的哈尼族女性,她们的鼓励、期待、支持及族群的发展繁衍是纳索奋斗的原动力。他在莽撞中成熟、他在迷茫中成长,他在逆境中奋起,最终带领族群拼死抗争,以一种“我以我血荐轩辕”的精神完成了与统治阶级的抗争。纳索的扮演者刘迦的表演张力十足,有彪悍勇猛的愤怒,有失魂落魄的迷茫,也有情深谊长的爱恋,他塑造的纳索传神、刻骨、入画。舞剧传递着一种精神,这个精神是一个族群的精神,也是大山的精神、更是云南的精神。为了生存和繁衍,族人们不断的迁徙和抗争,迁徙是为了生存繁衍,抗争是为了更大的生存空间,也妥协,妥协是为了休生养息,舞剧故事性很强,叙述励志感动,戏剧冲突设置合理,环环相扣,缓缓推进,在以纳索为主要角色的舞剧里,导演通过女性也就是爱人戚姒的表达,把整个族群的坚韧和不屈的精神传递的淋漓尽致。戚姒时而是背起丈夫的恋人,温婉贤惠,坚韧不屈,因为戚姒坚信纳索会扛起族群的大旗;戚姒时而又是默默注视的母亲,暗暗鼓励,时时鞭策。母亲跪儿为苍生,感天动地,众人跪母为血性,可歌可泣。戚姒这个角色的戏剧性强,虽然剧目中已经有母亲自己的形象,但是导演却把母亲的情感功能放到了妻子戚姒这个角色的身上,它代表了那个时代的一种坚韧与不屈,他赞美了女性的隐忍和伟大。戚姒的表演者骆文博对角色把握精准,坚韧与温婉,不屈与刚烈,柔情和血性都拿捏的恰到好处,感觉多一分会肥,而少一分又嫌瘦。
舞台上写意的舞美深邃、贯穿,有苍凉和壮美感,舞美的典型元素是抓到一颗写意的神树,神树的形态随着场次的推进而不断变化,宽窄有序、高低起伏,但是神树的形态一直贯穿其中。神树代表了这个族群的信仰,神树是这个族群的心灵家园,舞台上呈现的道具中有几棵写意式的圆木,它时而象征心理枷锁,时而又是蜿蜒的路,时而又变成百转千回的梯田,时而是竖起的寨门,寨门是族人们用以安身立命的根本象征,寨门象征着生存家园,心灵家园关乎信仰,生存家园关乎繁衍,当神树被毁,寨门被砍,族人们奋起舍命相争,为的是生存家园和心灵家园也就是生存和繁衍。这些装置为舞台的表达提供了多种可能。服装设计以红土高原的褐色和暗红色为基本基调,它既有年代感又能够把红土地上的劳作感表达出来,服装既有民族性又具戏剧感,厚重、贯穿,有质感。灯光的设计很有想象,它随着剧情的推进,叙述感,故事性都缓缓推进,灯光清晰干净,准确灵透,作为剧目灵魂的音乐带入感很好,原性文化元素一直贯穿其中,智性手段层出不穷,哈尼族小王子李维真唱的主题歌很有味道,高亢的嗓音给歌曲架起了催泪的格调,几乎没有修饰和渲染的声音里既有叩问心弦的细腻,也有剑拔弩张的强悍,小王子李维真演绎了一种复杂却易于体会的忧愁,好听,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深刻和感动。
舞剧《诺玛阿美》故事好,叙述细腻,结构扎实,人物形象突出,典型事件,矛盾冲突设置的合理,更重要的是它为民族题材的舞蹈叙事提供了一个可供参考的样式,它解决了很多编导一直很困惑的情绪化舞蹈和叙述性舞蹈的不同表达方式。编导在解决战争场面的铺陈非常让人称道,战争之下人性和道德的价值选择,无关对错,有的只是对生存之道最基本的诉求。生存本能驱使下的抗争行径其实也是人类的进化史,抗争中对个体的关照、对家园的维护、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都是战争中人与人的救赎。 舞剧《诺玛阿美》编导认识清楚,洞察深刻,演员真诚给力,表演丰满,作品直指人心,这部戏既有导演编创的气度,也有演员情感的魅力。现场表演毫无刻意痕迹,鲜活如情形再现。舞剧《诺玛阿美》是一部值得一看再看的好戏。
随着舞剧《诺玛阿美》的完美谢幕,云南省第十三届新剧目展演也落下了帷幕,纵观此次新剧目展演歌舞类剧目的呈现,有很多的感受:现在的舞台艺术作品的出品,已经由过去单一国有专业艺术院团的主流、主旋律的鸿篇巨制过渡到现在多元体制下的不同院团所呈现的文化反思、身份自觉、文化反省状态,一些文化公司或机构已经拥有了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表达的艺术作品。云南就出现了诸如映象公司杨丽萍老师推出的剧目《十面埋伏》,大德正智文化传播公司推出的音乐剧《阿诗玛》等不同类别的艺术作品。
现阶段舞蹈作品的创作也有了很大的变化,由新中国成立之初学习、模仿苏联老大哥的创作方法也就是现实主义的风格至上,到风格突破后的元素解构,又到了编舞技法横扫舞台,再到近年来出现的艺术形象说话,呈现人物的风格苏醒,舞蹈作品的内核也从现实的生活空间到向叙事的逻辑空间转变,更有一些具有独立思考的编导正在逐步往心理空间进行拓展和延伸。事实上随着社会的逐步转型,文化的需求也由过去的功成做乐到现在的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表达。这种转变是出品形式的改变,也是创作思维的改变,专业院团和创作者要能够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做出与时俱进的转变,云南著名作曲家刘晓耕老师如是描述现阶段云南舞台艺术创作的多数状态:“浅表的民族风情,会掉进旅游歌舞的陷阱中。花花草草,刀耕火种不能承载一个民族的厚重和精神的诉求,“舞台腔”是硬伤,唯有创新才能摆脱旧的审美模式”。
未来舞台艺术的创作方向,将会更加重视塑造人物的艺术形象,作品的艺术风格,从以前的做什么、怎么做,到未来的说什么、如何说,作品会把思想内涵逐步延伸到观众的内心深处,作品会更有力量且意味深长。舞台呈现会逐步摒弃大歌舞时代的喧嚣和旅游晚会带来的流俗浮华,会真实的反映人性,舞蹈诗或舞剧,音乐剧等都是需要创新的艺术,若没有故事、情怀和价值观的支撑便不能称之高级,只能是流俗的文化垃圾或颂圣的精神鸦片。一部好的剧目应当具有扎实的结构,凝炼的叙述,动人的内核,丰富的细节,鲜活的人物和有视觉冲击力及令人赏心悦目的导演语言。要追求做到"视角独特,思想深刻,人物鲜活"。舞蹈诗、舞剧和音乐剧等艺术形式如果没有对人性、人道、人格的足够尊重;没有对公平、正义、善良的充分敬意;没有对艺术规律、审美品格的诚恳追求;没有对地域文化、地域民族风格的充分诠释,就不仅仅是文化艺术的自轻,更是对世道人心的亵渎。如果我们用这样的剧目去占领文化市场,无疑是饮鸩止渴,营造的就是浮世繁华。
(作者系一级编导、云南省舞蹈家协会常务理事)
责任编辑:胡耀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