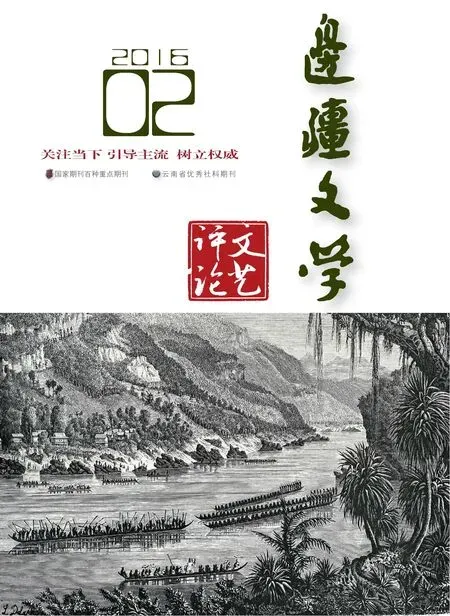轻灵的招魂
——读李夏长篇小说《大地子民》
◎雷杰龙
轻灵的招魂
——读李夏长篇小说《大地子民》
◎雷杰龙
大十六开,359个页码的李夏长篇小说《大地子民》摆在面前,掂一掂,堪称厚重的一本书。这样的厚重,对患了阅读餍足症的我,读它,料想又是一件头疼的事情。幸好,里面的文字并不厚重。不仅不重,而且很轻。那是带着飘逸灵动之气的轻,带着阳光雨露的轻,带着清风白云的轻,带着单纯、内敛、华美的人性气息的轻。就在这轻灵的文字中,跟着李夏走进了她笔下的世外桃源——彝族村庄罗玛沼,走进了那个村庄里的形形色色的人物,以及白云苍狗一般流淌过的一个世纪的时光。
轻灵的不仅是文字,还包括这部厚书的故事。故事是这样的:汉族茶师杨清远带着年幼的儿子世雄流落到罗玛沼,山穷水尽之时被罗玛沼土司苏吉老爷收留,替土司照管一片古茶园。巫医的女儿青珍爱上杨清远,和他结婚,生了罗玛沼最漂亮的姑娘拉措。土司的两个儿子,大夫人生的长子莫尼若少爷和三太太阿月秀生的小儿子阿鲁少爷都爱上了拉措。刘县长把罂粟花和枪支带进了罗玛沼,土司武装头领鹿丫试枪的时候不留神把杨清远打死了,但却没受到土司惩罚。三太太阿月秀为了让阿鲁少爷承袭土司职位,利用青珍的草药下毒谋害大少爷莫尼若,让莫尼若患了重病。大毕摩哈比为了拯救莫尼若念经作法,咒死了阿月秀,而自己也耗尽最后的元气,魂归摩玛山。莫尼若虽然洞悉隐情,但却不愿揭穿真相,和来到罗玛沼的美国姑娘珍妮赴美求医得愈,和珍妮结为夫妇。苏吉土司去世后,阿鲁少爷承袭土司职位,和拉措结合,在罗玛沼开始了系列革新举措。但此时,已是土司制度最后落幕的时刻,在战乱、革命的冲击下,土司制度和罗玛沼土崩瓦解,阿鲁少爷流落异国他乡,和拉措天各一方。
《大地子民》主要的故事就这些。当然,还有些“次要”的故事。比如世雄和布勒的故事,他们曾在罗玛沼受苦,后来走上了革命的道路,离开罗玛沼,又打回了罗玛沼(其中布勒和夜猫鬼的对话颇为精彩);新的毕摩沙额图的故事,大毕摩哈比死后,他来到罗玛沼,成了新的毕摩,在罗玛沼的土地上致力恢复那里曾经有过,但早已消逝的佛祖的教化;美国传教士安德神父的故事,在古老神灵居住的土地上,他孤绝地在人们心里精心种下上帝之爱的种子……这些故事串联在一起,虽然有些传奇的味道,但说不上有什么惊心动魄之处,当然也不能使这部小说显示出人们一般所称道的这类小说的一个重要特质——所谓厚重。
但这部小说依然出色!出色的理由不是厚重,而恰恰是与厚重相反的特质——轻!
是的,是轻。李夏以轻灵的方式,巧妙地编织了一个名叫“罗玛沼”的彝族部落桃花源,为早已消逝的云南哀牢山部落文明招魂。小说中,江南汉人杨清远茶师算不上贯穿整部小说的灵魂人物,但他的出现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味。在二十世纪初的丧乱年代,江南人杨清远为了谋生,沿着茶路流落到云南普洱,建立起自己的美满小家庭,但却又昙花一现般地迅速毁于丧乱,于山穷水尽时流亡到彝族部落罗玛沼。这个桃花源般的世界,不仅让他找到避乱的居所,还让他找到新的爱情,生命和精神都得以再次重生。和外面的丧乱世界相比,哀牢山深处的罗玛沼一切近乎完美,有如童话般神奇而祥和。童话般完美的罗玛沼四处洋溢着轻灵梦幻的色彩。这里的一切都是轻盈美丽的,有如杨清远迷恋的茶的淡雅和芳香。这里的自然山川奏鸣着淡雅的音符,仿佛受到神灵的护佑,极少一般彝区大山里的凌冽和苍凉。这里的风俗热烈而淳朴,散发着清冽而澄澈的光芒。而最关键的,是这里的人们内心简洁而轻盈,有一种罕见的优雅和美好。总之,李夏笔下的罗玛沼,属于部落时代的所有诗意和美好,似乎都被轻灵而巧妙地装进这只由语言编织的时光宝盒中来了。
当然,童话般的罗玛沼不可能没有冲突。倘若没有一点冲突,故事就不能存在,而罗玛沼也不能成立。小说中,罗玛沼不是存在于虚空中,而是存在于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丧乱时代中,因此,罗玛沼外面的许多事物无可避免地进入罗玛沼来了。这些进入罗玛沼的事物中有刘县长带来的汉人学校、罂粟花和枪支,有汉族商人周老板带来的银器,有李政委带来的红军和革命,也有美国传教士安德神父带来的上帝和新的毕摩沙额图带来的佛的教化。这些事物,必定会和罗玛沼的固有秩序和精神存在冲突。如何处理这种冲突?是用重的方式,也就是用社会历史方法论的工具进行辨析,仔细探寻这种冲突对罗玛沼激起的纠葛和嬗变,以及捕捉这种纠葛和嬗变所可能提供的历史经验和现实启示?还是用轻的方式,对这种冲突淡化处理,只是把它当作营造小说气氛,塑造人物的清淡布景?一般的家族史小说,地方传奇类小说里,小说家似乎都喜欢用第一种,也就是重的方式来处理。但李夏似乎没有犹豫,轻灵地选择了后者,也就是轻的处理方式。小说中,那些纷至沓来的外部事物虽然对罗玛沼产生了作用,但并没有什么化解不了的致命冲突,对人物的命运,尤其是人物的内心世界产生了那种所谓震撼性的影响。小说中,那些所谓时代带来的外部事物和罗玛沼的冲突并不是小说的主线,它们只是提供了一种人物活动的稀薄背景,为小说增添趣味而已。说得更准确一点,那些时代性的,外部的冲突并没有在小说人物的内心激起轰鸣。而在惯常的这类小说中,这种冲突是能激起轰鸣的。
李夏选择了轻的方式处理这种冲突,可能令一部分习惯重的处理方式的读者失望,但我却并不失望。因为那种重的处理太多了,甚至多到泛滥的地步。一般家族史,传奇史类型的长篇小说,作家似乎都对某一段社会历史片段津津乐道,喜爱进行各种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的辨析和探寻。这种处理方式不仅需要作者对时代和历史具有深刻的洞察和真知灼见,还需要作者对时代冲突中的人物具有非凡的性格审美塑造能力,倘若功力不到家,则容易陷入混乱、陈腐、无趣的叙述陷阱。而在我的阅读经验中,时代辨析肤浅、人物性格塑造虚弱,审美力量淡薄,陷入时代、历史、社会迷雾的叙述陷阱中的作品却并不鲜见。这类小说,作家为什么就不能另辟蹊径,绕过这种陈腐而无趣的陷阱呢?而李夏在这部长篇中,就聪明地绕过了这种陷阱,成功地开辟出自己的新空间。
在新的空间里,她关注和探寻的是另一种冲突——内心的冲突。
这种冲突来自内心热烈而微妙的感情。而这,也是这部小说的主线,真正成立,并且具有魅力的主线。在各种感情冲突中,又以少女拉措和莫尼若、阿鲁少爷的感情冲突为主线,串联起整部小说的故事情节。这个冲突简单说来就是莫尼若和阿鲁少爷都深爱拉措,而拉措也爱莫尼若和阿鲁少爷。这种冲突,本是这部小说最主要的冲突,是连接起整部小说的核心冲突,本该大书特书,但令人吃惊的是,李夏依然一意孤行地对此进行了轻灵的处理,以飘逸唯美的方式解决了这个冲突。小说中,莫尼若和阿鲁虽然都深爱拉措,两个人中只有一人能得到拉措,其中必有一人痛失所爱。这本是一大矛盾,但李夏处理的方式极其轻巧:莫尼若向拉措求爱,但拉措明白自己真正深爱的人是阿鲁之后就礼貌地拒绝了莫尼若。而莫尼若不仅深爱拉措,也深爱自己的弟弟阿鲁。不能得到拉措的爱,莫尼若虽然内心悲苦,但他却选择了隐忍,退避,完全沉浸到对部落和自己内心世界的精神探寻里。而在他得知阿鲁的母亲阿月秀为了让阿鲁承袭土司职位,利用拉措的母亲青珍的草药谋害自己,致使自己患病时,他内心的痛苦虽然更深,但却没激起他的仇恨心、报复心。为了不伤害阿鲁、拉措和任何一个人,他独自默默承受一切,打算在悲凉和忧伤中慢慢走向死亡。而在美国少女珍妮邀请他到美国治病之后,他几乎毫不犹豫地选择离开,主动让出承袭土司职位的机会,成全了弟弟阿鲁和拉措。面对这样的冲突,李夏就这样塑造了莫尼若这样一位神子一样的完美人物,让一切貌似激烈的冲突和矛盾无形中化为清逸乌有的云烟。
这样的处理方式是不是太轻了?是不是使人物内心冲突的烈度有所下降,感情的激荡幅度不够激越,灵魂挣扎的强度有所减弱?而最重要的,是不是使人物显得过于理想化,使人物性格的复杂性显得有些不够?是的,是这样的。这样的轻处理方式确实有造成上述弊病的嫌疑。不过,上述的弊病被这样处理方式带来的一个更大的方便冲淡了,以致显得不成其为弊病。
这个方便就是便于塑造小说中优雅的唯美人性。而李夏也最大限度地利用了这个方便,尽情描摹和肆意挥洒充分书写了这种唯美的人性。而这,便是这部小说最令人印象深刻,也最为成功之处!
在轻灵的书写中,小说中的拉措、莫尼若、阿鲁、杨清远、青珍等几个主要人物几乎无一例外地呈现出一种诗意的优雅和唯美。
看看李夏是怎么描写拉措这位罗玛沼的女神的。拉措的美好,让她成了罗玛沼莫尼若、阿鲁、布勒、周复生等男青年们的梦中情人。她的美,不仅是外貌、气质的美,更是内心清澈良善的美。她在深山中碰上布勒被毒蛇咬伤后,她不假思索施救,俯身吮吸布勒伤口里的毒血,丝毫没想到躺在地下的是一名卑贱的奴隶。她在罗玛沼每出现在一个地方,都带来一阵醉人心脾的美的清风。而对她最出彩的描写,出现在他被鹿丫追逐,独自逃到摩玛山之巅时。在山巅的那座废弃的庙宇前,李夏传神地写出了她人生最低潮的时刻的唯美的心性。“拉措叹了口气,抱着双肩,在寒凉的夜色中顺着那片光芒慢慢走出庙门。啊,她一出门,立刻就被眼前所看到的震撼了:那是一派仙境般的景色——月光劈开云层,白霜似的洒满群山,大山变成了万顷墨色波涛,起伏连绵,无边无际。湛蓝的夜空里,白云如羽如纱,轻飘曼舞,众星拱月,脱尘绝俗。四处弥漫着完全脱离了人间烟火的芳香,它们来自于泥土、雨露、森林、鲜花、山泉,还有那皎洁的月光。拉措呆呆地望着,慢慢走到了悬崖边上,看到乳白色的雾在她脚下的峡谷中流淌,汹涌奔腾,气象万千。她孤身一人站在万籁寂静的大山之中,站在这片明净皎洁的月光之下,没有了恐惧,没有了彷徨,没有了饥饿,没有了悲伤,她感到在这雄壮而绝美的山峦之中,人的生死是如此之轻,人的贪欲是如此之无聊,人的爱恨是如此之渺小。”[1]这段描写,是出色的景色描写,也是出色的心性描写,它以轻盈澄澈的笔调,写出了女主人公拉措的美,那是带着人性清澈之气的美,也是带着造物神性的美。
而对另一位男主人公莫尼若的书写也极为出色。在大毕摩哈比的眼里,身体已然中毒,面临着生命危险的莫尼若是这样的。“哈比望着他修长挺直的背影,自语说:他的脑袋里装着什么?一块冰,或者,是一把钥匙?想到钥匙哈比就想到光明,想到神灵。可接着他又想起莫尼若身上的毒,心里就像大海一样翻起波浪。早晨艳阳高照,晒化了田野水边的薄霜。莫尼若走到晨光之中,招来了无数惊羡的目光。太阳在他身后,正将他整个人儿地抱在明媚的金色中,所以看上去,他就是正从太阳里走来。他穿着黑色的,没有任何图绣的棉布衣裳,洁白的皮肤像羊脂一样闪耀着晶莹温润的光泽,双眼清澈堪比山泉。他那宽阔的裤腿下裸露着雪白的双足,脚步稳健淡定,轻盈如风,犹如一只云朵上惬意嬉戏的鹰。而这只鹰是如此悠然自得,如此年轻华丽,不带有任何猎手的杀机,他是一只温柔的、多情的、被太阳溺爱着的鹰。他的头发如他的衣服一样,漆黑地飘扬于晨风之中,闪烁着火焰般的光泽,有一群金黄色的蝴蝶正在他的头上盘旋翻飞。他的脸庞,怎样说才好呢?英俊,美丽,而他自己却浑然不觉。他眉梢带愁,双唇紧抿,浑然不觉地高贵优雅着。人们震惊地想,这分明就是从太阳里走出来的天神啊!可这是这个神子般完美的人,心里承受的苦和痛,又有几人知晓呢?”[2]这也是生命最低潮时期的莫尼若,知道自己被下毒后面临着生命危险时的莫尼若。这个时刻的莫尼若,正在承受着命运之重,可李夏却借大毕摩哈比的眼睛对他进行了如此轻灵,如此晶莹剔透,如此光彩照人的描写!而正是这样的描写,有力地塑造出莫尼若的人格的尊贵和骨子里美好的心性!而正是这样的尊贵和美好,支撑了他宁愿准备默默承受,默默牺牲也不愿挑破真相,伤害自己所爱之人的坚定决心。但他想不到的是,他的这种尊贵和美好却让大毕摩哈比下了一个决心:为了保护这个神子一般美好的人,他决定牺牲自己,拼尽暮年时分的所剩之力,作法攻击伤害莫尼若的始作俑者阿月秀,让莫尼若不再受到她的伤害。
不仅是对小说中的拉措、莫尼若少爷、阿鲁少爷、杨清远、青珍、布勒、周复生等几位人物进行了轻灵而唯美的书写,李夏还对苏吉土司、世雄、鹿丫、刘县长、大夫人、三夫人阿月秀、阿果小姐等有明显人性缺点的次要人物进行了轻灵的书写。在李夏笔下,这些人物有着这样那样的缺点,有的人物,比如鹿丫和刘县长,他们的缺点还很严重,有的时候甚至堪称小说里的“反角”。但李夏还是笔下留情,对他们进行了充分的理解,甚至还写出了他们性格里的可爱之处。总之,在李夏笔下,神灵之光笼罩的罗玛沼没有十恶不赦的真正恶人,他们的一点点恶,也在自己独自承受的命运里得到了清洗和救赎。
总之,李夏笔下的罗玛沼,一切事物、人物都是轻灵而诗意的,根本没有不可承受之重。她的笔下,甚至连罗玛沼最后灭亡的命运也是如此轻灵而诗意。对最后的罗玛沼,借用拉措之口,李夏写到:“这个冬季飞雪夏季飞花的美丽村庄消失于五十六年前雨季里的一场大雾。这场空前绝后的迷雾让罗玛沼陷入了混沌未开的状态,人们在家里点上灯也看不清门和窗的位置,没有人敢走出去。九天之后,待迷雾散开,人们发现自己身处不同的地方,周围都是陌生的人,陌生的村庄。他们想回去,但走了很多路,都找不到罗玛沼了。幸好,没听说有人伤亡,有些人家甚至连祖坟也在后来自己身处的陌生地方找到了。于是罗玛沼的人,就分别在各个不同的地方居住下来,把这个地方当作自己的故乡。人们说,罗玛沼变成了老虎,回归了森林。[3]罗玛沼的结局就是这样,结果就是:“人们慢慢地忘记了罗玛沼。”[4]
总之,在这部长达三十余万字的长篇里,李夏对小说里的一切元素的处理都是轻灵的。可这样的轻灵,是不是太轻了?轻得什么东西也捕捉不到,轻得让小说中出现的任何事物有如浮光掠影一般从语言编织的盒子中飞翔而去,归于虚空?
不是这样的。其实李夏已经成功捕捉到了一种东西。这种东西正是业已消逝在历史长河中的部落文明的灵魂。李夏正是以这种轻灵的方式,用小说语言的灵性,编织了这部小说,并在其中对部落文明进行了一次成功的招魂!
这个所招之魂同样轻灵,因为它是人类早期文明——部落文明——里的普遍的人性之美,魂灵之美。在《大地子民》里,这样的人性之美,魂灵之美,带着质朴、纯净、澄澈的品性,早已成功地附身于罗玛沼的一切事物、人物身上。这种人性之美,魂灵之美的极致,正如小说里的拉措、莫尼若、阿鲁等几位主要人物身上体现出来的那样,他们虽然没有受到多少现代文明的熏陶,但他们都无一例外地具有一种天然美好的心性,那是类似神子般纯净唯美的心性。如今,部落文明虽然业已远去,但这种神子般的心性却依然存留我们的记忆之中。虽然许多时候,这种心性饱受尘垢,深藏不露,但它却并未泯灭。它只是在沉睡,需要唤醒,需要招魂。而招魂的最古老的方式,便是语言,便是诗,便是小说,比如李夏《大地子民》这样的小说!
而李夏的招魂,是如此轻灵,比重还要有效的轻灵。
说到此处,忍不住想说点题外话,有关小说的轻和重。
长期以来,我们的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无比重视重。所谓分量重,厚重,几乎成了称道一部长篇小说的陈词滥调。
可是,我们却忽略了轻,严重忽略了轻。
殊不知,轻,却是现代小说的重要特质和方式之一。
说起来又是老生常谈。1985年,为了应邀到美国哈佛大学讲学,卡尔维诺撰写了文学讲义《美国讲稿》(又名《未来千年文学备忘录》),一共六讲,第一讲便是“轻逸”,谈论现代文学“轻”的课题。卡尔维诺一开篇就说:“第一讲我讲解轻与重的问题。我支持轻,并不是说我忽视重,而是说我认为轻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说明。我写了四十年小说,探索过各种道路,进行过各种实验,现在该对我的工作下个定义了。我建议这样来定义:我的工作常常是为了减轻分量,有时尽力减轻人物的分量,有时尽力减轻天体的分量(指卡尔维诺小说《宇宙奇趣录》,本文笔者注),有时尽力减轻城市的分量(指卡尔维诺小说《看不见的城市》,本文笔者注),首先是尽力减轻小说结构于语言的分量。在这一讲里,我将尽力向我自己并向你们说明,为什么我现在认为分量轻不仅不是缺陷反而是一种价值,指出过去的作品中哪些体现了我的理想——分量轻,表明现在我把分量轻摆在什么位置上,将来我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上。”[5]卡尔维诺对文学,尤其是小说和戏剧中轻的价值有深入而精确的论述,这里无需赘述。我只想强调他所极力强调的一点,那就是现代社会的事物越来越重,正如他所说的:“有时候我觉得世界正在变成石头,不同的地方,不同的人都缓慢地石头化,程度可能不同,但毫无例外地都在石头化,仿佛谁都无法躲开美杜莎那残酷的目光。”[6]在卡尔维诺看来,在日益石头化的世界里,轻的力量是无可或缺的,倘若没有轻的力量,世界就会失去平衡而完蛋。而文学,正是对抗世界石头化的一种至关重要的轻的力量。
可悲哀的是,有时,文学也正在石头化,比如一个鲜明的例子:在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领域里,那么多人对所谓重、厚重的崇拜简直到了病态的地步!
我不知道李夏是否读过卡尔维诺的《美国讲稿》,但我喜欢她的《大地子民》,因为它让我在我所喜欢的类似小说里,再一次看到了轻的力量,轻的美好!
【注释】
[1]李夏:《大地子民》,云南出版集团晨光出版社,2015年10月第一版,第262~263页。
[2] 同上,271页。
[3]同上,356~357页。
[4] 同上,357页。
[5] 【意大利】伊塔罗·卡尔维诺:《美国讲稿》,萧天佑译,凤凰出版集团译林出版社,2008年第一版,第2页。
[6]同上,第3页。
(作者系《边疆文学》杂志编辑)
责任编辑:杨 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