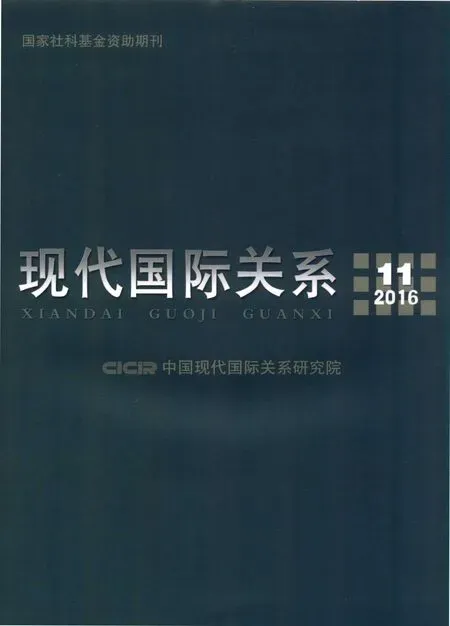全球能源治理变局:挑战与改革趋势*
马 妍
全球能源治理变局:挑战与改革趋势*
马 妍
全球能源问题的紧迫性凸显了国家间合作及能源治理的必要。随着国际能源格局与形势的变化,传统的安全风险正在降低,能源产业的投资安全和能源利用的环境安全问题正在成为全球能源治理面临的最紧迫的议题。在这一变局下,现存能源治理机制自身的缺陷日益显露,加之不同机制间互动不足,能源治理的成效差强人意。为了能够应对全球能源的新挑战,全球能源治理模式要从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向复杂的多层治理模式转变。在现有能源治理机制基础上,应尽可能吸纳新兴经济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参与,积极发挥金融工具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和加强法制建设,以实现更为公平、高效的国际能源治理秩序。
全球能源治理 能源安全 安全风险
[作者介绍] 马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主要研究全球能源治理、美国能源政策等。
在国际关系的发展中,能源已成为国家间争夺与竞争的焦点。但全球化的深入和科技的发展使能源问题不仅局限在国家层面,能源挑战的跨国性和跨议题性亟需国际关系各行为体间协调与合作,全球能源治理应运而生。特别是近年来,各主要能源消费国担忧能源供给安全,能源价格的波动严重影响了能源出口国的经济发展,非市场化因素依然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能源价格的不确定性,由传统能源消耗引发的环境负外部性正日益成为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上述能源议题的紧迫性受到了政策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进一步凸显了全球能源治理的必要性。
目前,全球能源治理的载体是一个多元、多层、分散的网络。*叶玉:“全球能源治理:结构、挑战及走向”,《国际石油经济》,2011年第8期,第45页。随着全球能源格局的发展变化,传统的能源风险正在降低,现存能源治理机制正面临严竣挑战。那当前全球能源治理的目标是什么?能源格局的发展变化对全球能源治理机制提出哪些挑战?未来改革方向又在哪里?本文将围绕以上这些问题展开研究。
一、全球能源治理的界定
在有关全球治理概念的种种界定中,以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最受注目。在该委员会1995 年发布的《天涯成比邻》的报告中明确指出“治理是指包括各种公共机构和个人在内的相关方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这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瑞典]英瓦尔·卡尔松、[圭]什里达特·兰法尔主编:《天涯成比邻———全球治理委员会报告》,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95 年,第2页。抽象来说,全球能源治理就是指国际关系行为体通过国际规则或制度解决全球性能源问题的过程,它涵盖了议程的设定与协商,规则的制定与执行,程序的实施与监督等环节。 能源治理作为全球治理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最复杂的问题领域之一。在传统国际关系与对外政策研究中,有关能源议题特别是能源安全的讨论带有浓厚的现实主义色彩。一方面,能源的稀缺性可能引发国家间竞争与对抗,历史上国家因争夺能源资源而引发的战争和冲突非常常见;另一方面,能源分布不均使得一些能源资源丰富的国家(如俄罗斯、欧佩克国家)将其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和国际谈判的筹码。*Jeff D. Colganal, “Oil and Revolutionary Governments: Fuel for International Conflict Article”,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No. 4, 2010, pp. 661-694.虽然有关能源地缘政治的分析比比皆是,但是全球化的发展使得以能源独立为目标的传统能源安全观念和保障体系变得越来越不合时宜。全球能源治理正是在这样一种背景下凸显了其必要性。
首先,能源议题的复杂性意味着其解决方案已超越了民族国家的范畴。当代能源议题所面临的挑战在全球层面相互交织,由能源生产和利用所带来的外部性不仅局限于某一区域和地区。可以说,能源领域面临的挑战具有系统性、全球性、紧迫性和大规模性等特点。从复杂系统理论来分析,由于没有所谓的世界政府和国际利维坦的存在,在全球化时代,关乎能源政策的协调与合作就是充满自愿与强制、劝导与胁迫的博弈。*Dult, A and Galaz, V, “Governance and Complexity: Emerging Issues for Governance Theory”, Governance-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Issue 3, 2008, pp. 311-335.虽然个别问题本身可能仅涉及部分国家或地区,但其影响范围及解决方案却是全球性的。*Aleh Cherp, Jessica Jewell and Andreas Goldthau, “Governing Global Energy: Systems, Transitions, Complexity”, Global Policy, Issue 1, January 2011, pp. 75-88.
其次,能源领域的市场失灵直接导致了全球能源治理的机制需求。*徐斌:“市场失灵、机制设计与全球能源治理”,《世界经济与政治》,2013年第11期,第80页。经典的公共政策模型主要关注四种市场失灵的原因:不完全竞争、外部性、信息不对称、公共物品属性。虽然能源产品具有竞争和排他性消费的特征,但是能源领域存在广泛的市场失灵,例如油价的剧烈波动、油气基础设施投资不足、垄断能源交易市场等,这些问题构成了当前全球能源安全的挑战。此外,能源消费产生的环境污染及气候变化问题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国家间若无相应的协调机制将极易产生搭便车的行为,从而使整个治理体系丧失效率,因此在全球层面的能源治理成为一种客观需要。
最后,各国在能源议题中的共同利益将助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建设。*Christopher J. Fettweis, “No Blood for Oil : Why Resource Wars are Obsolete”, Gal Luft and Anne Korin eds: Energy Security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A Reference Handbook, Praeger, 2009, p. 68.从新自由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在相互依赖的国际社会中,国家作为理性的行为体,能够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的驱动下,降低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等方面的考量,采取合作的姿态处理相关问题。更重要的是,各国家间在能源领域的摩擦可以依靠相应的国际制度安排来调解。*David G. Victor and Linda Yueh, “The New Energy Order: Managing Insecurit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No. 1, Jan/Feb, 2010, pp. 61-73.全球能源治理框架下的各项规范、条约和机制设计具有降低交易成本的功能,有利于加强各国在能源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减少各方在能源投资、贸易、运输等方面的冲突。各国已意识到为应对诸多共同风险与挑战,国际社会需要加强全球能源问题上的对话与合作。因而,各方通过理性选择,共同创立并努力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系的建设。
当前,全球能源治理的根本目标是通过国际社会的集体行动保证国际能源安全,防止与能源相关的问题扩散成国际性危机,并最终建立有序、合理的国际能源秩序。为了解决这些单一国家与市场无法自行解决的集体能源问题,包括国家政府、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社会团体、能源相关企业以及普通公民在内的各方广泛参与到全球能源治理的进程中。目前,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机构和规则主要分为以下几类:第一,政府间国际能源组织,包括国际能源署(IEA)、欧佩克(OPEC)、国际能源论坛(IEF)、天然气出口国论坛(GECF)、国际可再生能源署(IRENA)、国际原子能机构(IAEA)等。第二,国际能源规则,主要指具有严格法律意义和正式缔约方的国际《能源宪章条约(ECT)》。第三,国家间合作集团及首脑峰会,包括联合国、八国集团(G8)、二十国集团(G20)、金砖国家(BRICS)、亚太经合组织(APEC)等,这些组织有着宽泛的职能,能源问题仅是其关注的领域之一,但是在其运行中的首脑会晤却为解决紧急多边问题提供了一条更加灵活、高效的途径。第四,多边金融和贸易机构,主要包括世界贸易组织(WTO)规则、双边及多边投资条约和能够为各国政府提供资金技术援助及为能源项目提供贷款的开发银行。第五,国际非政府组织,主要指那些致力于减少或降低能源开发和利用过程中所带来的环境问题及生态问题的组织,如世界自然基金会、绿色和平组织等。这五种类型的治理者在规模和组织方式上各不相同,在设定议题领域里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全球能源治理主体的复杂集合。
二、全球能源治理的变局
近年来,国际能源形势的变化使得能源安全的内涵逐渐丰富,全球能源治理的目标也随之变得更加多元化。传统上,能源安全主要指的是供给安全、通道安全和价格安全,即能源进口国能够以合理的价格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海陆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畅通以及能源价格的平稳。从目前情况来看,这三种传统能源安全风险正在降低。
首先,从供给安全来看,北美“页岩气革命”的成功与美国“能源独立”的实现,预示着全球传统能源市场上多点供应、供大于求的局面正在形成。*范必、徐以升、张萌、李东超:《世界能源新格局——美国“能源独立”的冲击及中国应对》,中国经济出版社,2014年5月版,第103~111页。近年来,美洲、非洲和中亚地区的能源产量增加,欧佩克国家所占的石油产量逐年下滑,其作为石油出口国卡特尔的有效性不断下降。此外,为了能够应对能源供给的中断,各消费大国纷纷开始在国内推行能源多样化战略,国际能源署自成立之后也开始在成员国间推行石油紧急共享机制,要求成员国在遭遇石油供应量减少7%及以上的重大石油供应危机时交流石油数据信息,必要时动用储备、限制需求、转换燃料或增加国内生产。根据《国际能源计划协定》的要求,其各成员国(除石油净出口国外)均应具备90天以上石油净进口量的石油储备水平。*The Agreement on An International Energy Program, Article 3.1. http://www.iea.org/media/aboutus/history/IEP2014.pdf(上网时间:2016年6月20日)此外,从影响天然气的供应稳定因素来看,有学者研究表明,天然气供应国与消费国间的政治关系仅是影响天然气供应的因素之一,*Brenda Shaffer, “Natural gas supply stability and foreign policy”, Energy Policy, Volume 56, 2013, pp. 114-125.且近年来随着天然气在全球能源消费结构中所占的比例持续增加,国际能源署成员国在2009年的部长级理事会上,同意将联合起来对各国可能面临的天然气供应中断采取应急措施。*IEA: Energy Supply Security: The Emergency Response of IEA Countries—2014 Edition, p. 41.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ENERGYSUPPLYSECURITY2014.pdf(上网时间:2016年7月25日)可以说,虽然能源出口国使用能源武器向消费国进行政治施压的可能性仍然存在,但想靠中断油气供应威胁一国或整个世界的可行性几乎不存在,上世纪发生的二次石油供给危机不再可能重演。
其次,从通道安全来看,国际能源贸易主要涉及海路与陆路两种运输模式,其中陆路运输又以管道运输为主,铁路运输为辅。虽然管道运输初始投资成本较高,建设周期长,运输量不及海运,但其安全性最高。具体到三大传统能源而言,国际煤炭贸易量占消费总量的比例不大,绝大多数通过海上运输完成交易,极少数通过铁路方式进行边境贸易。*刘敬青、李宏:“世界煤炭贸易及我国煤炭进口的新趋势”,《运输市场》,2013年第1期,第53页。由于其主要发生在邻近的国家之间,因此运输安全风险很低。相比之下,石油和天然气产地与消费地区之间却往往远隔重洋,约有70%左右的油气跨国贸易通过海路运输。目前主要的海上石油运输通道包括霍尔木兹海峡、苏伊士运河、马六甲海峡、直布罗陀海峡、曼德海峡、巴拿马运河等。*张湘兰、张芷凡:“现状与展望:全球治理维度下的海上能源通道安全合作机制”,《江西社会科学》,2011年第9期,第5~9页。虽然这些重要能源运输通道的安全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地缘政治和海盗等因素的影响,但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已明确规定了能源通道的法律地位,为维护国际航道安全提供了法律基础。*参见《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19 条, 第38 条, 第87 条,http://www.un.org/chinese/law/sea/(上网时间:2016年8月3日)在这一问题上,国家主权原则与国际合作原则相互协调,各相关国家政府也积极参与到维护海上能源通道安全的队伍中,加强海岸巡逻,联手海上反恐,着力打击海盗。
最后,从价格安全来看,由于能源产品的特殊属性,其价格不是像在自由竞争市场中一样完全由生产、运输成本及供需关系决定。传统能源价格受到国家政策与博弈、美元汇率、金融市场投机、地缘政治等非市场化因素的影响较大。比如第一次石油危机中,欧佩克国家为了打击以色列及支持它的西欧国家,宣布石油禁运,暂停出口,造成油价上涨并引发了经济衰退。然而,随着各国能源储备增加和消费类型多元化,任何国家或企业都无法单独操控国际能源价格。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油气市场产能过剩,加之国际避险投资会随着美国经济的持续复苏流向美元市场。因此,国际原油市场价格可能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保持低位,当然,也不是说能源价格越低越好,从经济学原理上来看,在经济上升期能源价格的大幅上涨会推升通胀,从而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同样能源价格急剧下跌若发生在经济下行期也会加深经济衰退程度。特别是对那些在财政上依赖能源出口收入的国家而言,能源价格走低会增加其国内经济的脆弱性。目前,俄罗斯、阿塞拜疆、委内瑞拉和尼日利亚等国因油气价格下降受到很大冲击,甚至可能引发国内政治方面的危机。不过,整体而言,传统能源价格安全问题不再突出,对全球经济不会带来震荡性影响。
随着国际能源格局与形势的变化,上述三个传统安全风险虽然仍将长期存在,但引发全球性能源危机或经济危机的可能性基本上可以排除,全球能源治理面临的最紧迫议题还是来自新的能源安全风险的挑战。
首先是能源产业的投资安全。时至今日,全球仍有约14亿人无法使用现代能源,能源贫困(energy poverty)问题亟待解决。*World Energy Outlook 2010, IEA: Energy Poverty, How to Make Modern Energy Access Universal? pp. 8-15.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weo2010_poverty.pdf(上网时间:2016年8月5日)然而,能源投资项目需要面对的风险却越来越多,投资稳定性不足严重影响到了投资者信心。能源投资项目多以合作开发的模式展开,所需资金量大、项目周期长,在具体执行过程中正面临一系列的政治、法律和金融方面的风险。首先,全球最为动荡的中东地区每年接受的能源外国直接投资比较集中,但地区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外部势力干预等多重因素错综复杂,直接影响了企业能源投资收益的稳定性。比如中东多国的政治转型危机、“伊斯兰国”在中东地区的肆虐、沙特政局的脆弱性、什叶派与逊尼派阵营的纷争。上述地区政治的不稳定因素都极大削弱了投资者的信心。其次,投资对象国的腐败问题也是影响能源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比如尼日利亚等国腐败问题比较严重,外国投资公司为了获得明确的政策信息可能会参与到各个利益输送环节,但这无疑增加了投资的法律风险,使得这些跨国企业面临腐败指控。再次,一些发达国家因国内政治需要也会责令政府相关机构有选择性地对某个项目投资进行限制,比如美国外商投资委员会会对涉及国家安全的各项外国投资进行审查,其中能源直接投资与并购占了不小比例。此外,国会作为立法机构也会参与到相关投资项目的审批过程中去,诸如加拿大管道公司的“拱心石XL”项目等最终遭到了国会的投票否决。上述这些因素都会对能源投资的安全带来极大的负面影响。
其次是能源利用的环境安全。近年来,由能源消耗而引发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等议题凸显,如何控制能源利用所带来的环境问题成为了各方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特别是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福岛核电站事攻、北极冰川的加速融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等因素使得国际社会越来越关注能源开发和利用安全。*David G. Victor and Linda Yueh, “The New Energy Order: Managing Insecuritie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Foreign Affairs, No. 1, Jan/Feb, 2010, pp. 61-73.国际能源署最新发布的《全球能源展望2016》中明确了能源生产和利用是迄今最大的人为空气污染源。*IEA: World Energy Outlook 2016, p. 2. http://www.iea.org/publications/freepublications/publication/WorldEnergyOutlookSpecialReport2016EnergyandAirPollution.pdf(上网时间:2015年8月15日)因而,当前的能源消费结构正在朝着低碳化的方向转型,各方开始致力于推动能源效率的提高、能源产业的升级和能源消费结构的调整。节能技术、减排技术等开始在科技创新中占据重要一席,清洁能源备受瞩目。虽然从目前情况来看,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在全球能源生产和消费中所占的比重依然不高,但其作为影响未来能源发展的重要因素,作用仍不可忽视。新近签署的《巴黎气候协定》就是在各国自愿的基础上,确立了全球减排温室气体的长期目标。这一系列变化使得全球能源治理正在面临着一些新的课题。
三、全球能源治理的机制困境
全球能源治理面临着复杂的制度困境:一方面,为了减少能源领域的信息不对称、不透明问题,避免危害能源安全的金融投机,需要建立一整套规则来降低交易成本,并调试市场失灵引发的各种社会问题。另一方面,能源本身作为重要的战略资源关乎国家主权与安全,其有限性与排他性通常被地缘政治论者赋予“零和博弈”的战略考量。因而,对于全球能源治理而言,更加迫切地需要一套科学合理的制度设计。当前,全球范围内的能源治理机制仍是分散而又复杂的,虽然联合国于2004年建立了综合性的能源协调机制(UN-Energy),*United Nations, http://www.un-energy.org/what-is-un-energy.(上网时间:2015年8月2日)旨在推动建立一个可持续发展的能源系统,但该机制并非全球治理意义上富有影响力的实体。现有的能源治理机制主要包括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国家间合作,但在新的能源形势下,各种机制自身的缺陷日益显露,加之不同机制间互动不足,能源治理的成效差强人意。*Navroz K. Dubash, “Mapping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Global Policy, Volume 2. Special Issue, September 2011, pp. 6-18.
首先,国际能源组织成员分散,机构存在功能缺陷,不能有效应对全球性能源风险与挑战。当前,以国际能源署、欧佩克、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国际原子能机构等为代表的能源组织均致力于稳定国际能源市场,保障能源安全,但各个组织的成立背景不同,关注重点各异,且正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内部压力。比如国际能源署的定位是能源消费国集团,虽然经过40年来的实践发展,国际能源署已在应急反应机制、能源储备建设、信息系统共享和能源技术研发等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是其代表性不断受到挑战。按照《国际能源计划协定》的要求,其成员国必须首先满足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国家的身份,然而当前能源消费增量主要由非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新兴经济体拉动,根据《2016BP能源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新兴经济体占到全球能源消费增量的97%,*BP: Statistical Review of World Energy 2016, p. 2. http://www.bp.com/content/dam/bp/pdf/energy-economics/statistical-review-2016/bp-statistical-review-of-world-energy-2016-full-report.pdf(上网时间:2016年8月15日)虽然IEA秘书处于2012年提出了“协作国(Association)”倡议,*该倡议涉及的7个国家包括巴西、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俄罗斯和南非。目前,除墨西哥外,其他六国均与IEA签订了联合声明。不断强调将加强与重要协作国的关系,*IEA Energy: IEA Turns 40, Issue 7, p. 3. http://www.iea.org/media/ieajournal/Issue7_WEB.pdf(上网时间:2016年6月20日)但是若其不能在成员国身份的界定问题上取得突破,将很难在未来全球能源治理进程中挑起大梁。
欧佩克的定位是石油输出国集团,但因受到内部利益分歧和外部竞争压力影响,在全球能源治理中逐渐被边缘化。天然气出口国论坛2008年才转变为正式的国际组织,羽翼尚不丰满。能源输出国集团面临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第一,外部竞争的压力使其作为能源输出卡特尔的有效性不断下降。由于近年来美国、巴西及中亚一些国家的能源投资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传统能源的供给不再集中于欧佩克和天然气出口国论坛成员国。随着其占全球能源供应和贸易的份额逐年下滑,这些国家集团对于能源定价机制和贸易流向的控制程度也相应下降了。第二,内部的利益分歧使得能源出口国集团采取集体行动的有效性受到挑战。比如欧佩克各成员国基本上都是严重依赖原油出口的发展中国家,虽然在维护世界石油需求稳定并保持合理价格等问题上存在广泛的共同利益,但各成员国在具体国情上差别很大,其石油生产政策和油价政策也有不小差异。由于没有明确而严格的惩罚机制,各国采取一致行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刘冬:“欧佩克石油政策的演变及其对国际油价的影响”,《西亚非洲》,2012年第6期,第53~59页。如2016年以来,沙特为保持自身市场份额、打压伊朗石油出口,坚持“不限产”政策,导致欧佩克多次有意达成的“冻产”协议无果而终。第三,气候变化议题使得全球经济朝着低碳化的方向发展,各主要消费体都致力于减少碳排放量。一方面使得未来各国对于石油资源的需求充满变数,另一方面也使得欧佩克集团在全球气候问题的谈判中处于比较被动的地位。*Andreas Goldthau and Jan Martin Witt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The New Rules of the Gam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2010, pp. 3-11.
此外,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作用则更为单一,仅关注全球能源治理中的一个方面。国际可再生能源署主要致力于推动全球可再生能源发展,为成员国提供可再生能源政策咨询,并加强对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利用可再生能源的支持力度。虽然近年来为了应对气候变化,国际可再生能源署在能源治理中的作用日益凸显,*Thijs Van de Graaf, “Fragmentation in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Explaining the Creation of IRENA”,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No. 3, August 2013, pp. 14-33.但是可再生能源占全球能源消费的比例仍然不足3%,所以该组织应对传统能源风险上仍然很乏力。与之相类似,国际原子能机构则是对核能开发利用进行强制检查监督的国际机制,被视为最有约束力的核能安全国际规范,在防止核扩散和强化核能使用的主体责任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是目前该组织尚缺少应对能源危机的经验案例。
其次,能源治理机制中涉及的国际条约仅有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机制措施不足。《能源宪章条约》作为能源治理领域中唯一的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多边条约,以争端解决机制为核心,按相关条款解决国家间在投资方式、贸易规则、运输保护、环境保护等方面的争端。特别是在能源投资方面,该条约致力于为从事国际能源投资活动的投资者提供保护其权益的法律依据。*白中红:“《能源宪章条约》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外交评论》,2011年第3期,第88~99页。然而,到目前为止,相比双边投资保护协定和其他能源治理机制而言,该条约争端解决机制的利用率并不高。虽然《能源宪章条约》的成员国类型广泛,既吸纳了能源生产国,也包括了消费国与运输国,但到目前为止累计只有61个国际仲裁案以该条约为主要依据,致使其在国际投资仲裁中的知名度不高。*查道炯:“中国要不要加入《国际能源宪章条约》?”,http://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98825(上网时间:2016年8月5日)
最后,一些地区国家协调机制也将能源治理议题列入日程,但涉猎议题非常分散,难以形成领导全球能源治理的合力。比如,八国集团也曾试图建立新的国际能源合作机制,促进能源生产国和消费国开展对话,并且愿意在“能源-气候”相关联的问题领域承担全球治理责任。虽然少数大国的协调在操作层面上更加灵活,但其缺少具体的规则体系,也不具备敦促成员国遵守承诺的监督机制,在领导全球能源治理进程中显得颇为乏力。特别是俄罗斯与其他七个国家的关系忽冷忽热,使得整个八国集团的凝聚力下降,且近年来新兴经济体的能源大国地位显著提升,缺少这些重要的非成员国参与,其具体的政策建议和影响力受到了很大限制。*李昕:“G7/G8 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功能演变和制度缺陷”,《国际展望》,2011年第1期,第47~60页。然而,代表新兴经济体力量的金砖国家,虽然在能源贸易、投资和消费领域所占的比例逐年提高,国际社会关于其参与全球能源治理的呼声也日渐加大,但是各新兴经济体因国情、社情不同,在具体的能源议题存在较大利益分歧,难以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成为推动全球能源治理体制改革的有效力量。*赵庆寺:“金砖国家与全球能源治理:角色、责任与路径”,《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14年第1期,第145~150页。Christian Downie,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do the BRICS have the energyto drive reform?,International Affairs, Issue 4, 2015, pp. 799-812.
相比之下,在成员规模上,二十国集团覆盖了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且近年来,其关注解决的全球性问题更加多元化,不仅仅局限在刺激经济复苏和制定全球金融规则领域,能源议题也成为二十国集团领导人讨论的重要方面。作为凝聚了全球能源领域核心国家参与的政策平台,二十国集团被视为未来最有影响力和最具前途的全球能源治理领导机制。目前其面临的主要挑战是,由于在制度设计层面的约束力不强,各方在讨论中达成的原则性共识难以有效贯彻落实。*Kirsten Westphal, “The G8 and G20 as Global Steering Committees for Energy: Opportunities and Constraints”, Global Policy, Special Issue, September 2011, pp. 19-31.同时,二十国集团各平台会议在整体经济、金融等方面已面临沉重压力,无暇就能源议题进行更深度讨论,能源治理问题整体上在二十国集团中仍处于相对边缘地位。
从上述分析中不难发现,当前全球能源治理的主要机制仍是分散的,各相关国际组织和国家间协调机制在参与治理过程中都面临一定的功能缺陷,且各方之间缺少协作,使得整体治理体系没有连贯性。目前尚没有一个主体有能力将这些资源整合,共同形成一套权威的、具有约束力的治理机制。*Ann Florini, Benjamin K.Sovacool, “Who Governs Energy? The Challenges Facing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Energy Policy, Volume 37, 2009, pp. 5239-5248.虽然不能简单通过列举当前能源治理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对能源治理制度的有效性进行评判,但是当前能源贫困问题、投资安全稳定性问题和能源利用与气候变化议题的久议不决至少说明了当前的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取得的实质性进展不足。*Benjamin K. Sovacool and Ann Florini, “Examining the Complications of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Journal of Energy & Natural Resources Law, No. 3, 2012, pp. 235-263.当前对于这些机制的讨论是以国家为中心的,关注的是国家进行合作的行为、动机、条件和结果,但全球能源治理涉及的是一个多主体、多层次的复合结构框架,仅从以国家间合作为核心的国际制度层面探讨全球能源治理的有效性是不够的。我们既不能理想化地指望它能够彻底解决所有能源问题,也不能悲观地认定现有能源治理体制一无是处,而是应结合当前能源形势的特点为现有机制改革提出思路。
四、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的改革趋势
全球能源形势的变化使得能源治理机制改革成为大势所趋。当前全球能源治理的目标不应局限在应对传统能源安全所面临的风险上,能源的投资安全及使用安全也应列入能源治理的范畴中来,各方应提高对低碳发展和消除能源贫困紧迫性的认识,并采取相应的支持方案。在这一过程中既有能源供应、经济效率与环境保护多重价值目标的竞争,又有国家、部门与私人机构等多种利益的博弈,因而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的改革短期内可能很难在各种力量之间的妥协与平衡中取得一致意见,这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除了各方的利益博弈之外,能源议题领域本身的多样性也使得治理的目标变得多元化,很难通过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全面的治理机制或机构来实现这些目标。基于上述两个原因,未来全球能源治理机制很有可能会以机制复合体(Regime Complex)的形式存在,即多层次的治理模式,多元化的治理主体和多渠道的参与方式。为此,全球能源治理模式要从传统的以国家为中心的治理结构向复杂的多层治理模式转变。
首先,全球能源治理既需要传统能源大国的协调,也需要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当前的全球能源消费格局呈现出北美、欧洲和亚太地区三足鼎立的局面,但能源治理的体系却尚未体现出能源贸易重心已向亚太转移的趋势。全球能源治理的改革应为新兴经济体提供更广阔的平台,进一步密切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合作。一方面,二十国集团应进一步提高其在能源治理领域的领导作用,可定期组织召开能源部长级会议,为应对全球能源问题提供机制性的平台。另一方面,国际能源署应加快自身改革,拓展现有的“协议国”形式,进一步加强与发展中能源消费大国的合作,进而发展成全球性能源机构。其中,中国、印度的深度参与至关重要。
其次,全球能源治理应进一步发挥金融性国际机制的作用,弥补传统能源治理机制的功能性缺失。以国际机制和国家间合作为代表的传统治理模式,难以适应国际能源形势的发展变化,且对日益凸显的新安全风险重视不够、作用有限。*Neil Hirst, The Reform of Global Energy Governance, December 2012, p. 2. http://www.imperial.ac.uk/media/imperial-college/granthan-institute/public/publications/discussion-papers/The-Reform-of-Global-Energy-Governance---Granthan-DP3.pdf(上网时间:2016年6月25日)特别是在应对能源贫困和推动新技术研发方面,全球能源的治理迫切需要一些金融性机制,这些机制包括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多边发展银行、信贷机构以及一些双边或区域的贸易、投资协定等。它们可以通过控制能源投资和贸易的方向带动能源技术的创新和能源结构的调整。若这些金融工具能够与能源政策之间实现良好的互动,那么其对未来能源规则的制定和能源治理的影响将不可或缺。*Morgan Bazilian, SmitaNakhooda, Thijs Van de Graaf, “Energy Governance and Poverty”, Energy Research & Social Science, March 2014, pp. 217-225.
再次,全球能源治理应发挥非国家行为体的作用,自下而上地推动能源政策制定。由于能源资源的排他性和环境问题的公共物品属性,两种因素交织使得主权国家在应对全球性能源问题时会发生集体行为的困境,加之受到国内政治因素和地缘政治博弈的影响,各国的中央政府层面在推动全球能源治理进程中也面临着重重阻力。因而,为了有效应对全球能源风险,包括非政府组织、学术科研机构、跨国企业、跨国城市网络和私人关系等在内的各种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性均应被调动起来。特别是在节能减排和减少能源利用的环境污染等问题上,非国家行为体有着独特的优势,一些非政府组织可以直接以观察员的身份参加国际能源会议,或通过信息宣传、政治游说、监督实施等方式间接参与或影响政策决策过程。
最后,全球能源治理应加强相关法律建设。当前,除《国际能源宪章》和世界贸易组织的一些相关条款之外,没有其他专门针对国家间能源投资与贸易的国际法律规定。随着能源市场全球化趋势越来越明显,这些国际法方面的空白亟待弥补。全球能源治理必须由利益攸关方承担的法律义务所主导,由确保机制实施的相应的法律规则和规范所主导。*[美]迈克·穆尔著,巫尤译:《没有壁垒的世界——自由、发展、自由贸易和全球治理》,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142页。这不仅仅是保证国家间投资与贸易公平进行的有效手段,更是以“法律”代替“大国”作用,用“法律”规范“政府”行为的最佳机制。
总之,全球能源形势正在朝着多点供应、供大于求的方向发展。供给方的多元化加上需求方向亚太地区和新兴经济体转移,使得传统的能源安全风险正在下降。但与此相伴随的是,能源贫困问题亟待解决,促进未来能源增长的投资缺口较大,能源利用所带来的气候变化和环境污染也日益凸显。在这种形势下,如何有效降低能源投资的风险,保证国家间能源贸易有序进行,促进新技术的研发节能减排就成为了全球能源治理需要解决的新课题。面对着新的能源风险,现有全球能源治理机制作用有限,加之以政府间国际组织和国家间合作的传统能源治理机制本身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功能缺陷,使得能源治理的有效性面临挑战。为此,全球能源治理机制的改革势在必行。为了能够应对全球能源的新挑战,现有能源治理机制应尽可能吸纳新兴经济体和非国家行为体广泛参与,积极发挥金融工具的作用,进一步健全和加强法制建设,以实现更为公平、高效的国际能源治理秩序。○
(责任编辑:张一萌)
* 本文受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支持,项目编号:3162015ZYKD07。
————不可再生能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