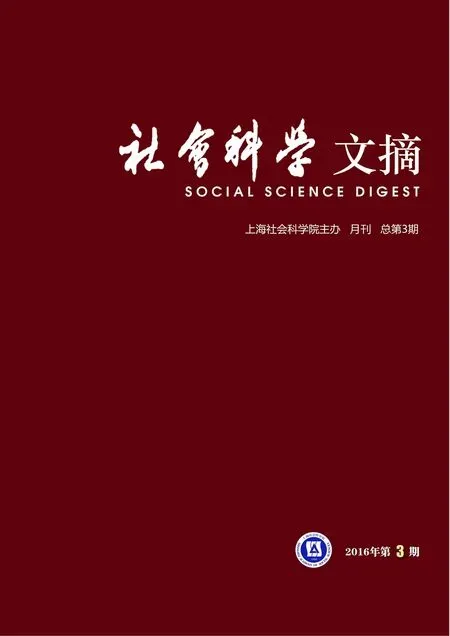论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的方式
文/谢晖
论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的方式
文/谢晖
近代以来,随着主权国家观念的发展,国家立法被普遍认为是正当秩序形成的“合法渠道”,而其它秩序形成规则似乎是秩序形成的旁门左道。我国学者,特别是深受法律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法律本质观影响的学者,更是把被国家立法认可作为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的唯一前途,舍此,民间法便不存在自主的作用。对此,尽管我不敢苟同,但基于民间法与国家法互动关系的学术考量,探讨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的方式,仍不乏意义。本文认为,它主要有如下五种进路:
主体自治、权利表达(运用)和权利推定的结构进路
1.主体意思自治的自治权利选择与民间法被代入正式秩序
权利是自由的外在形式或规范表达,是自治主体选择性地从事某种思想、行为和事情的资格。只要一个国家强调人们自由、自主,便必须“认真对待权利”。“认真对待权利”不仅是每个自治主体个人的事,更是政府的事。
那么,政府认真对待权利的基础是什么?一言以蔽之,就是依法赋予、充分尊重并且保障社会主体的自治。所谓社会主体,这里既包括作为公民个人的私人主体,也包括作为法人和非法人团体的其他社会组织,还包括地方(区域)自治组织等。对于法律明令的权利而言,法律的一切权利空间,最后都必须具体落实到自治主体上,否则,权利便徒有其名,无以落实为人们交往中的秩序。这对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具有关键的意义。它意味着在法定的权利范围内,社会主体对民间法的运用,就是把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的具体行动,是把法定的权利行动化、活动化的具体展示。
2.主体的权利推定与民间法被代入正式秩序
当事人这种对权利的自主性,不仅体现在作为主体意志的自主性上,而且也体现在规范选择的自主性上。因为选择不同的纠纷解决主体,就意味着同时选择不同的纠纷解决规范。换言之,这里不仅意味着主体自治,而且意味着主体的规范选择自治。我在此强调在纠纷处理中自治主体的规范选择自治,或者规范选择权利,实质上是要表达民间法可能通过主体自治和主体的权利表达而被结构进正式秩序的过程。因为在权利的空间里,主体究竟选择何种规范,不但是主体自治的,而且是法定权利理应涵摄的——只要法律没有命令禁止主体所选择的民间法,那么,其理所当然地应属于、或者推定属于权利的范畴。既然属于法律权利的范畴,顺理成章的是,它也照样属于由官方法所决定或控制的正式秩序的范畴。
只要自治主体能够在权利范围内选择民间法作为交往行为或个人行为的规范,就必然意味着自治主体把该民间法的选择推定为其权利,进而也表明因为自治主体的规范(民间法)选择,业已把民间法代入到正式秩序中去了。这正是即使在现代国家中,自发秩序仍然不可避免的原因。不但如此,而且在一个大型社会,这种融于正式秩序中的自发秩序更具有优越性。
国家立法认可或授权的结构进路
1.西方民治国家立法中对民间法的认可或授权
即使在号称民治的近、现代西方国家,国家对社会的影响、个体和社会对国家的依赖,也是有增无减,所谓市民社会和政治国家两分所带来的社会对国家权力的制约格局,并未影响国家对社会之全方位的支配关系。
尽管这种情形的形成,是国家力量对社会的僭越,但也同时表明是国家及其权力因为人民参与这一因素而神圣化之必然。无论人们如何对待这一现象,但这一现象的客观存在已然是一种不争的事实。这就是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有赖于国家法认可或授权的原因。
2.我国立法中对民间法的认可或授权
我国法学界在给法律下定义时,通常把制定(创制)和认可作为立法的最基本的方式。“法,又称法律(就广义而言)。国家按照统治阶级的利益和意志制定或认可、并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其实施的行为规范的总和。包括宪法、法律(就狭义而言)、法令、行政法规、条例、规章、判例、习惯法等各种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显见,在这一有关法律的定义中,一方面,认可作为国家法律产生的基本方式,得到了学理的肯定;另一方面,习惯法也被纳入法律这一概念的外延中。
无论在当代西方,还是中国,尽管在理念上和立法上对于民间法、特别是习惯法进入正式秩序,并不持特别友好的态度,但中西立法的实践并没有摒弃立法中的认可这一形式,相反,无论是议会的制定法,还是法院的判例法,都通过认可这种方式或者法律授权的方式,对民间法予以必要的认可或授权,从而使民间法能够被结构在国家正式秩序体系中。其中法律中的授权和本文将要探讨的下一问题具有紧密关联。
地方立法或者变通的结构进路
一般说来,国家并非铁板一块的一个整体,而是有诸多不同地方、不同部分组成的一个整体。这种情形,即使对那些小国也适用,更遑论那些疆域广大的国家。但是,前述所谓国家层面的立法,无论在何种国家,都是针对全国而言的。在此情形下,倘若国家立法的结果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效力和实效,那当然没什么问题;但倘若国家立法一旦落实到各个地方后,和地方实情相比,或者南辕北辙,或者捉襟见肘,那么,在国家宪法或法律中赋予地方立法权并通过地方立法中的变通措施,把通行于地方的民间法结构到地方正式秩序中,就既是地方贯彻落实国家法律的必要举措,也是地方把通行的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的必要方式。
1.联邦制国家的地方立法之于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
在联邦制国家,在全国统一的宪法(政治契约)安排下,至少存在一级不受中央直接管辖的独立的立法机构,以及与之相应的行政机构和司法机构。这样,立法权以及行政权、司法权,不是由中央相关机构所独享,而且地方立法机构在宪法安排下,拥有各自独立的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种由地方所享有的独立自治的立法机构,对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而言,提供了明显的灵活性和方便性。
既然联邦制的实质是为了建构或者整合民族主义,使一个国家在统一前提下呈现出民族的、文化的、生活方式的以及规范的多样性,也就必然意味着在立法中需要充分展示这种多样性。然而,这种多样性不能在中央立法中直接展示,而是在宪法所预设和规范的框架下,由地方自治地去完成地方的、民族的、多元的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的问题。
地方自治立法的好处,在于一方面,在保护对象上,它能够把区域的地方习惯、民族习惯以及地方社团规范纳入地方法律体系中;另一方面,在功能上,拥有这些民间法的地方社团习惯,虽然不能在全国法律中被结构于正式秩序,但在地方居民的交往行为中,通过地方立法方式被结构于正式秩序。各个地方对其民间法纳入正式秩序的事实,必然意味着一个国家的正式秩序在整体上对待民间法的基本态度;再一方面,在效力上,不同地方的民间法被纳入正式秩序的范围虽然有限,但各个地方的民间法被纳入正式秩序体系中的整合效应事实上必然会整体性地提升民间法在正式秩序体系中的作用和效力。
2.单一制国家的地方立法与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
单一制国家的特质,使得自来具有地方性、民族性、多元性和团体性的民间法处于明显不利的地位。因为一国要通过宪法的权威,强制性地使地方听命于中央,就不可能事无巨细地照顾地方利益,周备无遗地把民间法纳入国家正式秩序体系中。如果是那样,反倒只能使地方当局坐大,宪法所既定的秩序格局必然因此受到影响、甚至挑战。所以,在国家立法中,除了在全国通行有效的那些民间法可以直接纳入国家法,并被直接地结构于国家正式秩序中外,至于仅仅在地方、特别是民族自治地区、特别行政区有效的民间法(习惯),全国统一的法律(如“民族区域自治法”“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等)只是表明对其予以保护的态度,但具体如何保护,则由这些法律授权地方通过其立法予以具体保护。于是,在全国法律中,这些地方习惯或民间法,只是间接地被结构于正式秩序,而不是直接被结构于正式秩序。其根据在于国家不能直接将某一地方习惯(民间法)结构于统一的正式秩序,因为这些地方习惯在实质上只具有属地效力,即只对在该地方从事活动的行为产生效力。全国法律的授权,其实意味着地方获得了通过立法把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的权力,并因此而获得了地方在一定程度上的自治。行文至此,不得不论及的是:尽管单一制国家结构具有主权悉由中央统一代理、国家统一担当的宪法基础,但这并不意味着除了主权之外的其它权力,地方一概不能享有,从而并不意味着地方只是中央的派出机构。这表明,地方尽管不享有主权自治,但享有一定的“事权自治”。这种“事权自治”就是在全国性宪法和法律授权范围内的事项,中央非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
法律渊源与法律执行(适用)的结构进路
1.法律渊源中的习惯或习惯法
几乎在中西方所有的法律渊源理论中,习惯或习惯法都被学者们或者法官们赋予了法律渊源的地位。在中西方的学理上和实践中,都把习惯和习惯法作为法律渊源看待,这已经预示着包括习惯和习惯法在内的民间法,通过法律渊源的定位,被纳入或可能被纳入正式秩序体系中。被纳入,是指法律直接认可某一具体习惯为法律时;可能被纳入,则是指法律授权某一类习惯可以被保护或可以获得法律效力时。
需指出的是,所谓习惯等民间法作为法律渊源,事实上不仅具有形式渊源的意涵,也具有社会渊源的意涵。如果把后一意涵也考虑进去,则更能说明民间法的法源地位与其被结构于正式秩序中的内在逻辑关联。它表明,一般说来,作为非正式制度的民间法往往是作为正式制度的官方法(国家法)的根据,是国家法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
2.执法与司法中民间法被纳入正式秩序
在现代法治政治中,行政是公权体系中贯彻国家法律的主导力量。既然行政被赋予了执行国家意志,即执行国家法律的机能,并且在现代民治体制下,“行政体制不承认或几乎不承认官员之间有任何隶属关系,只强调每个官员对拥有表达国家意志权力的机关所制订的法律的效忠”,则必然意味着法律渊源对于行政的一般作用,意味着法律渊源绝不仅是增益于司法,由司法机关独享的概念,同时也是可增益于行政执法的概念。
无疑,法律渊源对司法的意义尤为重要。这种重要性既取决于司法的特征,也取决于司法在一个法治国家所拥有的独特地位——司法优位。就司法特征而言,司法享有社会主体在日常生活中最棘手问题的最终裁处权,因此,其公正与否,关注度格外高;就司法地位而言,司法以和平的、合法的方式处理日常生活中的具体冲突,所以,它是法治国家缓释社会矛盾的最基本的机制。这既取决于司法自身的地位和职能的尊荣,当然也需要法律的保障。更兼之法官在司法中只能唯法是尚,故在此意义上讲,法律渊源的确立,无论是直接渊源,还是间接渊源,对司法来说尤为重要。尤其当法律直接渊源供给不足时,包括民间法在内的法律间接渊源对司法而言就是解决无米之炊的应急方案。显然,当法官运用法律的间接渊源,尤其是运用习惯和习惯法来裁决案件时,就意味着法律渊源理论和实践支持了司法把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的条件和可能。
公共交往与契约合作的结构进路
1.古代社会的契约合作与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
诚然,人类历史从古至今的历时性递进在近代发生了质的转型,因此,以此为界把人类文化两切为古代和近现代、等级和平权、身份和契约并无不可。但在我看来,契约本身有典型契约和非典型契约之分。典型契约即近代社会契约的观念普及和公民社会建立以来,主体交往中以平等资格和平权身份所展开的契约合作。非典型契约则指社会契约观念尚未普及、公民社会尚未建立之背景下,人们借助契约而合作。
按照这一理念,身份制在社会理念以及立法上,固然是应受鞭挞的,但当人们普遍地接受了这一理念及其立法,本身就意味着达成了某种约或契约。在这个视角上,身份制本身就是一种约的结果。是人们按照上帝所安排的身份,而各安其分、各得其所,履行义务,享有权利的一种秩序状态。当然,在这种秩序状态下,人们赖以组织秩序的规范,既可以是被神圣化了的教法,也可以是经由神圣而转化为世俗的习惯法(中世纪后期纷乱的西欧各国,所奉行的就是如此)。所以,这种看似和现代平权契约很有距离的“契约合作”,仍然具有把民间法纳入正式秩序的功能。
2.近、现代社会的契约合作与民间法结构于正式秩序
正如梅因的著名论断那样,从古代社会到近、现代社会的发展,乃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进化过程。在近现代社会,无论社会契约的产生,还是在个体主体性基础上人们凭藉其内在要求而展开的契约型合作,都蕴含着把民间法更好地纳入正式秩序体系的必要和可能。
就社会契约而言,既然一个国家的统治目的是根据法律为众人谋福利,且一旦不能给众人带来福利的国家和统治当局,本身失去了统治合法性,而毋宁被称之为暴君,那么,就必然意味着立法也罢、行政也罢,司法也罢,必须以能否满足和实现公民的利益和要求为职责。而公民和其他社会主体的要求,每每并不取决于法律,反倒经常取决于习惯、风俗、人情以及自治团体的内部规则。自然,统治者乐于保护这些内容,就意味着其能悉依法律,实现保障公民权利、维护社会秩序的契约承诺,否则,法律作为契约文本,就只能是一份具文。即便统治者面对宪法宣誓也罢,或者面对神祗(上帝、真主或佛陀)宣誓也罢,只要当局不能根据法律满足自治主体的要求,社会契约就未产生实效,是否依法统治就值得怀疑。
就社会主体之间的契约合作而言,一方面,主体自治(无论是公民、法人还是非法人团体)本身表明:每个自治主体的交往行为和契约合作是因其意思自治、行为自主,且在合作中能实现偏好保留、需求互补而展开的。另一方面,根据双方或多方所认可、且不违法律精神的习惯、风俗、道德、信仰体系以及社团规则等民间法进行交往,既是其行使权利(往往是推定权利)的具体表现,也是其通过契约合作把民间法代入正式秩序体系中的基本方式。
综上所述,契约合作在近、现代民治国家中,具有把民间法代入正式秩序的更为方便的条件和更加有效的实现手段。那就是人的自治、自主和自由所带来的全新的权利观念,以及为了实现这些权利观念而在契约性合作中对民间法的自主运用、权利推定和规范吸纳。
(作者系中南大学特聘教授;摘自《政法论坛》2016年第1期)
——马鞍山市博物馆馆藏契约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