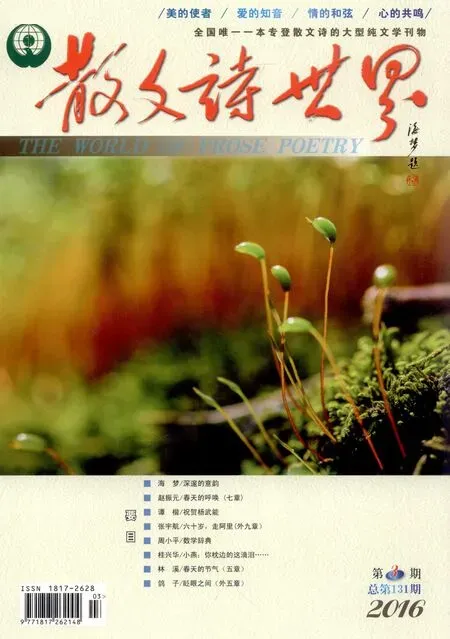稻 田(十章)
上海 任俊国
稻 田(十章)
上海 任俊国
于父亲开田时,大地开春
起浪了。
稻田里起了一层薄薄的水纹,像父亲皱巴巴的手抚过有些皱巴巴的衣襟,抚过那年那月有些皱巴巴的生活。
在刚刚过去的冬天,稻田除了结冰,其他日子仅作为一面镜子,让天空对照着梳理几朵乱云或发一点小脾气。
往日的翠鸟也不知飞哪里去了。
田埂上的铁线草却长得比冬天还长。那个清晨,父亲踩过铁线草上的白头霜去挑水。岁月在他铁线草一样的头发上布满的白头霜,显得那么浅、那么淡了。
井水清亮。太阳如一尾鲜活的鱼,在父亲的水桶里晃荡。
这些,只是父亲站在田埂上的一丝儿回想,有如此时稻田里的一线细浪。然后,他毫不犹豫挽起裤腿,下田。
于父亲开田时,大地开春了。
那时,父亲是我心中的太阳。当尝试着跟父亲下田时,我才知道父亲远比太阳勇敢,远比太阳温暖。早春的阳光浅尝辄止,根本没有深入稻田深处,那里藏着一个冬天的阴谋,整个稻田的寒冷瞬间笼罩住我的全身。当本能把我抽回到田埂上时,我看见父亲连眉头都没有动一下。
在父亲面前,倒春寒也没敢停留太久。
经过父亲鼓励的稻田,成为育秧的温床。
此后,我趴在田埂上,仔细看过稻种长出雪白的根须,长出春天的乳牙。
稻田从不培养好高骛远
从稻田里一天一天长起出还有蛙鸣。
突然,水草动了一下,又动了一下。看仔细些,是几粒黑豆在动。再看仔细些,黑豆是拖着长长尾巴的小蝌蚪。这些小逗点,在给水波断句。
一条阳光的线牵着小蝌蚪游出来。小时候,我以为蝌蚪是吃阳光长大的。
天空生动起来,下一场淅沥的春雨。稻田也跟着生动起来。
涨水了,蝌蚪的快乐比水涨得还快。
一支绿色的歌被一场雨淋燃,又被一场月光擦亮。
青蛙隐于稻田,以45度的最佳视角,巡视略高于稻秧的高度。这就够了,稻田从不培养好高骛远。
青蛙之于稻蛾,等同灯火之于飞蛾。青蛙以自己的舌头为炮,打击来犯之敌。随便,击破关于井底的流言和关于胡夸的蜚语。
在生命灿烂之前
育秧时,父亲把谷种均匀地撒在平整的田泥上。白天铺一层纸薄的水,好让阳光晒透。夜黑前又向秧田加水,防止受冻。
父亲弯腰从水塘里向秧田灌水。一木瓢一木瓢的水铺开来,再铺开了。尽管浅浪如线,但秧田里每增加一瓢水,温暖就增加一瓢。水塘里每减少一瓢水,黄昏也减少一瓢。
当夜色的姿势和父亲一样低时,田角上亮起的那杆烟比天边的寒星还亮。
父亲离开时,一定是每一粒谷种都安静地睡着之后。父亲回来时,一定是每一粒谷种都醒来之前,牵引第一缕阳光照进它们的梦境。
终于,谷种长出谷须,用雪的白深入泥的黑,编译生命的密码。
终于,浅黄的谷芽针一样锥出水面,穿上阳光的线,牵引无限春风。
生命灿烂时,父亲站得很远,隐在杏花深处。
一盆三月的快乐
盆地,丘陵,天气暖得早些。
桃李盛开。我们在花团锦簇的地方住惯了,没人记得燕子归来的日子。听见燕子啁啾,我们抬头看天,看天空的翅。看二月的风筝歇在三月的树枝上,看三月的云和它又细又密的根须,淋湿故乡。
秧苗长起来,抽高了春露。
鱼腥草使劲钻出田埂,长出耳朵,听春声和浪的细语。
三月的太阳是一尾产卵的红鲤,它的鳞片落满了稻田。油菜花开过了头,过早地浸润着我们住的那个不大不小的村庄。太阳只是一个比喻。而此时,稻田里所有的风生水起,都是鱼们在追求爱情。
水黾在水波上里练习凌波微步。小爬虫们从田泥里爬出来,加入破坏稻秧或保护稻秧的队伍。
有星月出来的夜,黄鳝也跟着出来,带着小黄鳝看外面的世界,听三两声稚嫩的蛙鸣。
稻田养稻,也养鱼虾和蛙声。养肥我清水般的童年。
整个三月,稻田都端着一盆快乐。
繁星一样的蛙空有流星划过
田野的露珠与天上的星星一样多,蛙鸣也与天上的星星一样多。
秧鸡在稻田里对歌,如流星划过蛙空。
布谷鸟在山巅播种,很少来到田间。秧鸡高蹈于稻秧之间,筑巢于稻秧之巅,用鸣叫悠扬夏夜。与此情此景无关的露水,兴奋得簌簌而上。
秧鸡于五月恋上稻田,于六月怀春,七月产卵,八月雏飞,然后隠于九月和山的背影中。
秋收过后,稻田低调而清闲,一遍遍默记即将远走他乡的燕子和云影。几穗遗落的稻谷,以发芽的方式,提示遗忘和辜负时光都是一宗罪。
好在黄昏过后,还有蛙鸣起于夜凉,还有月亮越过山冈。
彼时,比天空更加恬静的是稻田。
一尾秋鱼浮出水面。
时间是最后的裁判
稻田危机四伏。
穿着稻子外衣的稗子,如一匹披着羊皮的狼潜入羊群。
抽穗之前,稗子一直是婢子的态度。突然,稗子站高身子,争夺养分和阳光,抽出长长的穗,不想再跟稻子做姐妹,抢占风头,要做王妃。
此时,饱满的稻子却谦卑地弯下腰去,向大地鞠躬。
几只麻雀飞进稻田,搜食虫子,也偷食稻谷。这让稗子得意,也让稗子失意。有时,不被环境臧否褒贬,内心难免会生出惊慌。
镰刀把稻子和稗子割倒在同一水平面上。然后,稻子会变成大米或种子,稗子一直还是稗子。
时间是最后的裁判。
一条鱼游过波澜不惊的四季
三月,孵化。
在稻田的产床上,小鲫鱼开始睁眼看世界的第一课,便是蹬开水波的襁褓、蹬开天光云影。生命最初的一丝丝儿陌生,慌乱了水花。
田埂的菜花纷纷而落,落下纷纷的安抚。
小鲫鱼已经平静,以吐泡泡的方式说话,说无尽的美好,春雨也来,开小朵小朵的水花。天地虽远,世界虽大,只要回到春天,就有流动的情感。
一条小鲫鱼游过犁耙的铁刃,游过黑鱼的尖齿,游过翠鸟的利目,看一声声蛙鸣从水底跃上岸去,看吃鱼虎爬上稻秧,蜕变成夏日黄昏的翅。然后,鲫鱼长大了。
稻田的呼吸越来越大,牵扯着鲫鱼的心思。于倾盆的雷雨中,只要有一线流水,鲫鱼就会溯游到上一层梯田,抓住每一次时间打开的缺口,刷新生命的高度。
稻秧越来越密,但有足够的缝隙漏风、漏雨、漏阳光和星光。
漏过稻子的扬花。在秋天的门前,于鲫鱼而言,这是它的生命里应有的一场雪。
在金黄的秋天,鲫鱼学会了稻子和乡人的谦卑,收集割稻人脚窝里的温暖和阳光,并在最深的脚窝里,迎接生命中最寒冷的一天。
春天孕育在鲫鱼低沉的呼吸里。
秋收,一件很简单的事
鹰,拔高晴天,扯出空间来盛放秋收。
这么盛大的场面,由一把小小的镰刀开启。一切那么郑重其事,又那么若无其事。
镰刀的牙,刚刚经过碳火淬炼和铁锤的考验,青黑着,一不小心划破了夜的脸。
血色,洇染天边的鱼肚白。
稻叶上的秋露,在寂静中亮起来,又寂灭于暗下去的蛙声中。
天边的半块月亮正在消隐……
正午时分,看见父亲仰头喝水,太阳也有些口渴。
母亲背着一篓稻子和一篓夕阳回家,蛙声跟在她脚印后重新长起来。
燕尾收拢夜色。它们一家老小,在去南方之前,一次又一次讨论母亲的咳嗽声、父亲的关节炎。
一天的劳累坐下来。父亲用一盏老酒,喝浅了夜深。
一缕淡淡的愁绪完全淡了
稻田恢复平静。
一再被我忽略的稻草人还站在田埂上,晒着十月的阳光。看着儿女们长大,又看着儿女们离开,对稻草人来说,心情的起伏只不过增减几根稻草而已。
还是简单的好,手中那把破扇的摇动频率,风说了算。它只用肤色表达季节变换、时光流逝。
雀鸟离它很远。蟋蟀离它很近,它的流浪的歌声让远来的暗霜停住了脚步。
面对已经和正要经历的风花雪月,夜和稻草人都失眠了。
终于,捆扎稻草人的稻草绳和时间都松懈了。稻草于风之喙,回归稻田,回归泥土。
该放下和放弃的都放开了,于天寒地冻时,稻田无波。
一尾过冬的鱼跳动着整个稻田的脉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