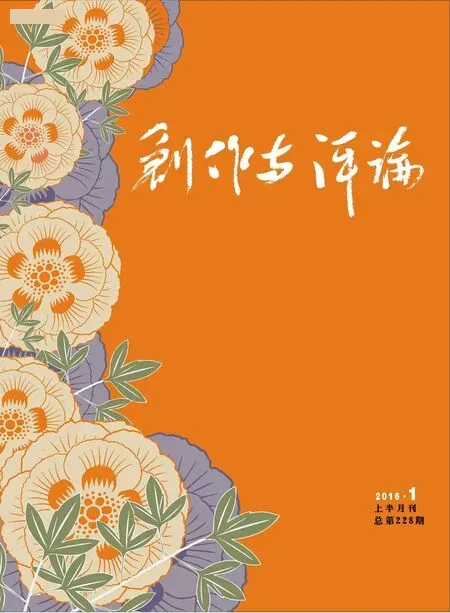白纸坊情事
○潘恭
白纸坊情事
○潘恭
1
按现在街道办事处管辖范围,白纸坊地区往东扩大许多。老北京人认为的白纸坊,是指枣林前街以南,右安门内以西,直到西南两面城墙。这一大片地面。现在说就是以右安门内大街和枣林前街为界,到西南二环路。这一片里还有些小地名,提到时,要加白纸坊。标明方位:外城西南角。比如陈家胡同、安家庄等。要先说白纸坊。
枣林前街南边是枣林后街。后街往南,靠东是陈家胡同和崇效寺。靠西是安家庄。
1955年冬天,安家庄(现在菜园东里)2号,开纸房的张金山,和他雇的抄纸工刘昶和,打起架来。刘昶和鼻子破了,眼角青了。跑到牛街麻刀胡同宣武区人民法院,把掌柜的告了。掌柜的打工人,剥削阶级打领导阶级。反了你了?!法院把他押起来。过了两三天说“过堂”,法院门前的黑板上也公布了。
张金山的父亲张六爷到枣林街找马四爷,还找了街坊武谦。托他们“过堂”时去旁听,希望能帮助说句话。至少证明张金山是傻子(智障),也许减轻点罪名。马四爷,七十多了,回民。一米八以上的大高个儿,长方脸,浓眉毛、高鼻梁,挺长的花白胡子。腰板儿不塌,挺着胸脯走道,精神头儿足。站桩走拳、摔跤扔掷子,年轻时常练。底子好。他秉性直。爱管事,也善了事。曾经替人打官司,赢了。成了这一带的土“律师”。遇上事,就找马四爷。街坊四邻宾服他。武谦是个辍学在家的学生,算“有学问”的。说话能有板眼。和马四爷不认识,没说过话。去法院各说各的,认识不认识没关系。麻刀胡同在现在牛街邮局南侧,东西走向,连着牛街和教子胡同。从牛街进去,走不远,往南是寿刘胡同,寿刘胡同东侧是一片坟地。解放后迁坟占地。一东一西,坐南朝北,盖了两座青砖楼,楼前有院子,院墙不高,也是青砖。东院大,楼外靠东边有个礼堂,楼里是区委区政府办公。西院是区人民法院。那天马四爷八点以前就到了。穿棉袍,黑缎子面皮坎肩。在法院对面北墙根,揣着手眯着眼,冲刚出来的太阳站着。等法院开门。太阳地儿有五六个人,蹲着、站着、来回转悠着,谁跟谁也不搭话,默默的等法院上班。武谦个头儿不高,又是个孩子,更没人搭理。八点法院大门开了。俩警察站门口,告状的进去。旁听的说没安排,进不去。武谦没经过事儿,跟在马四爷后头。看马四爷被拦住,没往前凑就向后转了。马四爷一肚子气,直接奔了张家。堵着门叉着腰,骂开了:“拿我老头子耍着玩儿!说去人也没去,寒碜我!这是人办的事儿吗?!”他认为在法院门前没人和他打招呼,受到冷落丢面子。张家人没敢露面,别人连哄带劝把老头子搀走了。武谦挨埋怨“你跟老头子点点头、说句话,就惹不出这事儿了。”
张金山认可打了人,被判二年。送东北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劳改。还好,按期释放,回了北京白纸坊,成了造纸生产合作社社员。
出事那年张金山三十岁出头,三个孩子,两儿一女。女孩最大,五岁。儿子三岁多,小儿子还不会走。纸房的活儿一家子忙,人手不够,也只雇抄纸工。晒纸,是内掌柜操持家务之外,带手儿干。杂活,掌柜的全包。抄纸工大多来自山东,带家眷的少。抄纸的,时间灵活,按数计工。晚饭前后抄够数,不误下道工序,就行。刘昶和,山东人。一个人在京打工。
张金山斜视,两个黑眼珠挤在一块儿,都只露半个。小时候得病吃药过量,伤了脑子。耳朵聋,跟他老得喊。他是半语子,嘴里有热茄子。吐不清字。生人甭提。熟人也得带手势比划着才懂。个子不高,壮实,有力气。纸房的杂活,要三两个人搭帮干。在井台上洗纸浆,至少仨人。一人搅辘轳打水,俩人淘洗。行话“淘麻”。大木桶二三百斤抬来抬去。他外号叫傻子,都愿意跟他一块干活。没心眼,实在,不惜力,不耍滑。他媳妇比她小两岁,除了肤色黑些,鼻眼周正,没有缺陷。能说会道,有心计。跟公婆、邻居,关系都好。嫁给傻子,别人背地里为她抱屈。但她跟傻子一心一意的过日子。很有“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嫁给扁担抱着走”的精神。人毕竟是复杂的,心里头有什麽,别人怎知道。不过傻子不懂也不会心疼媳妇,是明摆着的。
刘昶和在北京,媳妇在老家。过年回去住上个把月,俩人牛郎织女的姻缘。抄纸的活累,可时间灵活。没有家眷的单身汉,寂寞难耐。就跑下处,或找相好的。刘昶和难免寂寞时,傻子媳妇也有不足处。虽然不是“以美玉配明珠,适获其偶”,可毕竟“移干柴近烈火,无怪其燃”。一天晚饭后,傻子去别家纸房搭帮干活。忘了拿烟袋,中途跑回家,屋门反锁了。敲了几下,媳妇开了门。刘昶和在屋里站着,见他进来,就往外走。傻子挡住门不叫出去,右手把着门框拦着,左手拽过媳妇,顺手伸进裤裆。抽出手来,给刘昶和一大耳瓜子。俩人揪拔起来。傻子生真气,下手狠。刘昶和心虚,招架躲闪。媳妇到门外喊人劝架,说“不知道为什么打起来了”。来了两三个人,把他俩拉开。傻子始终没吭声,去接着干活。刘昶和被人送回住处。也说“不知为什么”傻子动手打人。穿着衣服躺了一夜。第二天没洗脸,带着伤痕血迹,跑到牛街麻刀胡同宣武区人民法院,告了张金山。法院派人跟刘昶和一同到安家庄,找劝架的,了解情况。果然是刘昶和挨了打,吃了亏。又把傻子找来,问为什么打人。傻子见了穿官衣儿的有点含糊,只咬着舌头说“打哦、打哦……”法院人说:你跟我们回去说清楚。把傻子带回了法院,没再回来。
傻子劳改了家也没了。媳妇带着最小的孩子回了娘家,和傻子办了离婚手续。再没回过安家庄。俩大点儿的孩子是爷爷奶奶带大的,一直一起生活。妈妈走不走,孩子并不在意。当初她嫁给傻子,一半是冲着他的家庭。一半是旧观念:听信媒妁之言,服从父母之命。北京的底层文盲多,妇女识字的更少。开化慢,闹市街头情侣们勾肩搭背耳鬓厮磨,这一带还男女授受不亲呢。传统习惯顽固的做着挣扎。
张金山的父亲也开纸坊,在安家庄11号。有四只“陷”(四个抄纸的水池子),是纸房大户(小业主就一个池子)。那会儿,吃喝不愁就是好人家,嫁人当然嫁给好人家!张金山媳妇相中张家了。男人有欠缺,家里没挑剔。婚姻也不能十全十美!
张老爷子,人称张六爷。不识字,好喝酒。练拳脚,会摔跤。在纸房行业有一定声望。合作化(1956年)以前,是造纸业同业公会副主任:成立造纸合作社他也是副主任。热心公益,公众的事,跑在前头。捎带行善,舍药,找上门来,免费赠送,白给!只两种:秘方配制跌打丸和专治臁疮腿的膏药。另外是义务给受惊吓的小孩“收魂儿”,随时随地“施治”。爱管事,一人难趁百人意,有感谢的也有不满的,背后叫他“瞎张六”(一只眼斜视)。
他文化大革命时故去。孙女孙子那时已经上中学了,张金山没有再婚。他媳妇也没再露面。刘昶和把媳妇接到北京,单位给了房,日子舒心。而今是退休工人。还住在白纸坊。常去路边小花园,遛早儿,下棋,侃大山。
2
1957年,白纸坊造纸社成立的第三个年头(1955年冬天开始有了合作社名称,是筹备阶段。实际运作一年多),这一年不顺当,春节后开工第三天,2月8日(农历正月初九)办公室南院,原料仓库着大火。损失惨重。仓库是晒纸墙道改的露天大院子。放买回来的废纸、废麻绳。废纸废麻绳都是打成包的,一包一米多长,七八十公分高,五六十公分厚(纸料行经营这些,收购的废品分类打包,卖给造纸厂家),地上垫枕木,上面一包包码齐,摞成大小高矮都有四五米的原料垛。有十几个垛。仓库北墙居中留出入口。墙外两旁是坐南朝北的简易厂房。靠东是成品库,靠西是烘干室(屋里砌火墙)。仓库南面是菜地。2月7号晚上刮起西北风,越刮越猛。风大天冷,值夜班的四个人,院里转转,就回屋暖和暖和。12点多,发现西北角的纸垛冒烟。四个人顾不上冷,抄起水桶、铁锹,奔了纸垛。水离着远,在火墙屋里。铁锹先到,拍打,溅火星,风一吹,腾地起了火苗!纸包是草绳捆的,还有飞在绳子外头的纸片,都见火就着。有风,火借风势,风助火威。纸垛窜着火苗子,水桶泼水,压不住火势。很快,纸垛都着起火苗,仓库大院一片火海!带班的跑去打电话。派人去喊领导,还敲起办公室前枣树上挂着的一截钢轨(平时上下班敲几下)。人们被急促的声响惊醒,从炕上爬起来,蹬上棉裤,裹着棉袄,往社里跑。火势太猛,人无法接近。社领导正束手无策。消防队及时赶到。四辆汽车,消防员下来熟练地拉开水龙带,接上水源。北面的简易厂房,房顶不能上人。只能从出入的豁口,用水枪喷射。有的纸垛够不上。南墙不高,但北风吹得火苗从墙头往外扑,人上不去。水柱喷射的地方没了火苗,一挪地方,火苗子又从里头喷出来。直到五点多钟,火才扑灭。仓库院里积了没膝的水。消防员浑身湿透,在寒风中冻结成冰,胳膊腿都不能回弯儿。把他们让进屋里,化化冰,稍微暖和一下,不然都上不去汽车。这场大火损失近八千元,占合作社家业的五分之一。对社员,在心气儿上是个打击。女社员有的瘫坐在地上,双手拍着大腿嚎哭:“血汗哪!我的家业呀!白搭啦!”入社时社员家的驴、碾子、原料、成品都作价入股,社里的损失就是自家股本亏蚀。看了心疼。不幸中的万幸是没有人员伤亡。京城报纸报道了这场火灾。作为地区大事还载入了《白纸坊街道志》。
四月初,出了一件人命关天的大事。报纸没登,《街道志》也没提。当时可轰动了白纸坊。现在地名崇效胡同,是白纸坊造纸作坊南北两片的分界线。北边枣林前街,十几户纸房,大户是王家。往南安家庄十多户,大户张家、侯家、刘家。南到白纸坊西街,从路北蔡伦庙往北,大户宗家、苑家、杨家、沈家、丁家。原先白纸坊胡同迤西,有和它平行的两条路(现在还剩一条叫白纸坊北里。靠东的盖楼堵死)。都叫白纸坊街(崇效胡同也叫白纸坊街。崇效寺庙东叫陈家胡同)。靠东这条街路西第一个院是丁家纸房。丁家大闺女,小名大菊子。她学的抄纸。女的抄纸工极少,全社八十八位抄纸师傅,只有两位女性。抄纸,就是用竹帘把水里的纸浆捞成纸,劳动强度大:定额一天七百张。双手举着抄纸帘子,垂直插进混有纸浆水里,端平晃动,看纸浆铺匀,端出水面。再重复一次,才成一张纸。转身,把带湿纸的帘子,轻缓的放平在木板上,纸粘留在板上。揭起帘子再插到水里抄纸。七百张就是同一动作重复一千四百次(一般都超额五十张)。技术要求高:质量好坏、利润高低,都由抄纸决定。薄厚不一,不好卖。抄厚纸,费原料,赔钱。造纸行业,抄纸是关键环节。抄纸劳动条件差:整天不见阳光,在低矮潮湿的屋子里闷着。放纸浆的水池,是一米深的坑。人站到另一小坑里,双手无论冬夏泡在臭水里。手洗得再干净,也有味儿。冬天,冰一样的水,抄两张纸,手就木了。身旁生小炉子,坐铁锅烧热水,手伸进去,缓缓劲。双手交替着冷热。抄纸工的手泡得煞白,冬天红肿皴裂。女孩子难承受这累、这苦。
学了这手艺。入社以后还抄纸。她人高马大,粗线条。男女老少,跟谁都自来熟,都敢开玩笑。像愣小子。一条又粗又黑的大辫子,甩吧着,才觉着是丫头。老在屋里干活,晒不着。也没捂白,红红的脸蛋,浅眉毛,单眼皮。小眼睛老像是笑着眯上眼,炯炯有神。透着喜兴。1956年夏天,造纸社的产品积压,卖不出去。增加跑外的业务员,出去推销。大菊子被调到供销股,每天骑着她爸的28男车,联系业务,跑四九城。在外头跑,就认识外头人。谈业务,就得套近乎,拉关系。一回生两回熟,大菊子认识了不少人。一个河北的小伙子,在北京当采购。从大菊子手里买过几回纸,是她老客户。跟老客户,生意场的应酬话用不着了。联系不能断,题外的话就多了。聊得投机对路,自然引为知己。
以前,单干的时候,大菊子在家里抄纸。纸房抄纸的拿头份工钱。自己家不挣工钱,说话占地方。父母让她三分,说一不二。她有两个妹妹,一个弟弟。都还小,吃闲饭。当然服从大姐。她跟河北小伙儿接触一段,挺投缘。就让到家里来了。他北京没家,熟了以后,公休日就到丁家来。他大叔大婶叫的很亲切,弟弟妹妹哥哥哥哥的,喊的也热闹。像一家子人了。
旧历年,小伙子回老家了。返回北京,造纸社刚着过大火。社员普遍情绪不好,都高兴不起来。小伙子带了不少农产品,丁家人虽然连声道谢,可没有心情招待他。小伙子很懂事,说不少宽慰的话。有上级领导,他们不会不管。别太为这事着急。借口单位有事,就告辞走了。大菊子还跑外,增加了采购原料的任务。保持着和老客户的关系。河北小伙子到白纸坊串门的次数少了。
甭管人间出什么事,“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冬天过去,春天准到。那时候北京外城(二环以内,地铁1号线以南),没有特意修的街头花园、绿地。可是杂树多,野草地多。春天也“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柳绿花红一片。跑外的人,心在业务上。顾不上看。杨树“虫子”柳树毛儿,地下撒天上飞。一刮黄风,细沙迷眼,粗沙打脸。这些跑外的觉得出来。
春夏之交,不冷不热的时候。大菊子病了,一脸倦容。又黄又瘦,小辫儿发锈。有时衣扣不系,两手俛着怀。鞋不提好,趿拉着。到办公室转转。别人开玩笑:“菊子,多会儿结婚?”她苦笑着:“我还结婚呐。都快‘接三’了。看我这脸色儿,盖上张纸,哭得过儿了”。别人笑着,劝慰:“你瞧你,大今儿个的,不许说丧气话!”她常和人说笑,没人当回事。
四月上旬,早晨上班(那时是八点上班),造纸社办公室人还没到齐,电话响了(全社只一部)。一接,听的人呆了。楞说不出话来。放下电话才缓过劲儿来:“真想不到出这事,大菊子跑南西门外头卧轨了!叫咱们去人。”跑到主任办公室找头儿汇报。主任立刻派俩人去右安门。这个消息很快传开。右安门铁道离白纸坊不远,自动前去的也有。
从右安门回来的人说,死了两个人。不是卧轨,俩人牵着手跑向开过来的火车,撞上去弹回来,摔死的。道边上有他俩坐着的报纸,还有吃剩的橘子什麽的。流血不多。大菊子家里没去人,她妈听说后,昏过去了。脸白的像纸。两三分钟才缓过来,双手拍打胸口,大声哭喊:“我造的孽呀!报应啊!”不停地骂“不要脸的东西!坑死你爹妈呀!”围着的人劝着,安慰着。她爸低头不语,默默流泪。跟社主任说,(后事)社里看着办吧。我心里乱成一团儿了,一点主意都没有了。什么也顾不上啊。
社里派人、出钱,买棺材,到派出所开死亡证明。拉到久敬庄南郊公墓埋葬。小伙子的后事,他所在单位办的。也埋到南郊公墓了。
这件事,一段时间里是白纸坊人谈论的话题。“真想不到这孩子性子这么烈。”“养这么大,爹妈容易么?你不是要爹妈的命吗?”“干嘛非跟那小子?鬼迷心窍!”
对二人寻死的原因,有种种猜测。多年之后,听说是小伙子过年回老家,父母给他订了亲,大队书记的女儿。退亲,得罪人。会招来是非。同村乡亲,爱恨情仇,辈辈相传,事比天大。和菊子分手?无情郎、负心汉,一辈子心上压石头。倘若菊子三长两短……菊子铁了心,嫁定了他。于是牵着手一生相爱。
爱情,没有专属。市井街巷,碌碌小民,或更单纯,更强烈。
潘恭,男,1937年生于北京,老北京人。幼时读私塾,在学校只三年。喜看书涂抹。多年不得写。年过花甲,拾起旧时爱好。有作品刊见于《北京晚报》《北京纪事》《中国名城》《湘声报》《粤海风》等报刊。
责任编辑张韵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