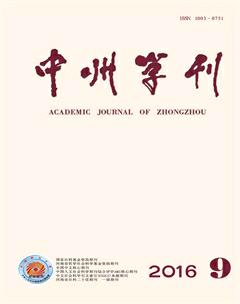中国先锋派话剧对莎士比亚经典的传承
孙艳娜
摘 要:在跨文化交流中,莎士比亚经典经常被借用,更是成为中国先锋派话剧的宝贵资源。受后现代手法影响,以林兆华为代表的中国先锋派导演在莎剧编演上多有强制阐释的不良倾向,存在着“轻文本”“重形式”“主题先行”等不足之处。先锋戏剧人在借用莎剧时,需加强经典传承的责任感,而不是过分追求个性化、新奇化,在对经典怀有敬畏之心的前提之下,遵循“期待视野”规律,以服务剧场和观众为核心,对原著作“有限的否定”,找到原著精神与现实生活的契合点,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再塑经典,使其历久弥新。
关键词:莎士比亚;先锋派话剧;林兆华;经典传承
中图分类号:J802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16)09-0154-06
2016年是世界文学巨匠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全球各地陆续举办以“纪念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为主题的研讨会、展览、莎氏经典朗诵和戏剧节等活动,以此来缅怀莎翁为世界文化做出的巨大贡献。2016年2月18日至21日,来自莎士比亚故乡斯特拉特福特的皇家莎士比亚剧团(the Royal Shakespeare Theatre)在中国国家大剧院的首站演出拉开了莎氏“王与国”三部曲——《亨利四世》(上、下)和《亨利五世》——世界巡演的序幕。中国国家话剧院也在北京举行系列纪念活动,上海戏剧学院亦于9月份拉开“国际莎士比亚戏剧节”的帷幕。值此之际,探讨中国先锋话剧舞台上莎氏经典编演及其传承更具特别意义。
一、话剧舞台上莎士比亚经典传承的方式
在莎士比亚经典传承中,一直存在着重现经典和重构经典两种方式。重现经典强调原著精神,坚持以原汁原味的方式把莎剧精神传承下去,以英国皇家莎士比亚剧团为代表。该剧团一直秉承莎士比亚戏剧当年演出时的原样,对莎氏文本从不做任何改动。重构经典有两种表现:一是从表演形式上对经典加以创新,二是借用经典,让经典为我所用。在中国先锋话剧舞台上,借用莎士比亚经典成为主流形式。借他山之石来攻己之玉,是跨文化戏剧改编中最常见的手法,其核心是“我者”。先锋派导演“改编外国戏剧往往不是为了再现外国的生活场景,传达原剧作者的意图,而是为了向本土的观众讲述一个与他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的故事”①,体现的是洋为中用的观点和外为我用的主张。导演吕效平说:“我认为莎士比亚对我来说就是极其伟大的思想和灵感的资源,我并不介意莎士比亚的舞台是什么样的,我只想表达我自己。”②著名话剧导演林兆华更是直率地表示:“对戏剧,我没有责任感,我就是喜欢,我觉得好玩。我也从来没有将西方古典剧目介绍给国人的想法。”③
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曾指出,导演对剧目的诠释是“与本真性的遭遇”,“把艺术作品解释成人自己对世界的定向和人自身理解的整体”。④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莎剧舞台上出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多元化阐释局面也是情有可原的。但随着后现代、后后现代主义的盛行,中国先锋话剧舞台以彰显个性为主的多元化编演,极易导致朱寿桐教授所说的“执意误读”:“接受者或评论者明明知道这是一种对作品的曲解,但仍然执意而为,导致另一种他所期望的阅读和批评的效果。”⑤经典存在的价值在于其精神内涵的世代相传,这种“执意误读”会给莎氏经典带来一定的误读和曲解,因而引发业内人士的担忧:“曾经极度抛洒快意的莎翁戏剧,让人看得疲倦不已;不知从何时起,莎士比亚变成了一个变异的源泉,许多以他展开的当代诠释经典的解构、重组之作,却难唤起我们的共鸣。”⑥“对于中国观众来说,莎士比亚其实并没有那么熟悉,过多解读也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大家会以为,莎士比亚就是这样的。”⑦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以林兆华为代表的中国先锋话剧人对莎氏经典颠覆性的舞台阐释手法进行深刻反思。
二、林兆华莎剧编演的舞台手法
林兆华是中国当代先锋派话剧的领潮人,也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探索戏剧和小剧场的开拓者之一。他与著名剧作家高行健联手打造了《绝对信号》《车站》《野人》等具有西方象征、荒诞戏剧风格的探索戏剧,打破了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第四堵墙”的现实主义传统模式独霸舞台的局面,再次开启中国现代主义戏剧大门。林兆华共有70多部舞台作品,其中对莎士比亚经典戏剧的改编有3部,即《哈姆雷特》(1990年)、《理查三世》(2001年)和以《科利奥兰纳斯》为蓝本的《大将军寇流兰》(2007年)。林兆华的每部莎剧对于中国戏剧几乎都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虽然林兆华公开声称自己既无风格,亦不属于任何流派或主义,但在现实舞台之上,他却执着地探寻每出戏的风格,并以个性化和主观化的舞台手法赢得业内人士的青睐,素有“一戏一格”之赞誉。对于在中国话剧舞台上活跃一个多世纪的莎剧经典,林兆华亦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即从经典中寻求突破口,以阐释个人内心世界为宗旨,以自我主观艺术顿悟为核心,对莎士比亚戏剧进行二度创作,通过新的舞台表现手法,展现现代人的精神风貌及其思考与关注的问题。
1.捕捉现实契合点,挖掘舞台“第二主题”
林兆华对莎剧主题的改编尤显个性。他一直坚持:“人物的个性是次要的,体现我导演的思想是主要的”⑧,并把主要精力放在搭建现实关注与剧本定向感悟的平台上,深挖“第二主题”,努力寻找剧本之外的自我感觉。因为在他看来,“第一主题是文学的”,“但我强烈地把我自己的一些东西,把我独立的一些思索、独立的状态,放在这个戏当中。这是导演的“第二主题”。每排一个戏,我都这样,我追求这个”。⑨
莎氏《哈姆雷特》讲述的是丹麦王子为父复仇的故事,演出多重在人物性格的刻画。林兆华则一反传统,从社会学及哲学层面对《哈》剧进行挖掘。他认为,哈姆雷特痛苦的根源在于其是个有思想的人,而活着的有思想的人都有可能面临哈姆雷特式的抉择,这样就将宫廷王子置换为大街上你我中间的一员。在林兆华改编《哈姆莱特》的1990年,改革开放的大潮使国人面临去与留、资与社的抉择与思考,剧中丹麦王子生存还是毁灭的疑问正是人们心中的块垒。林兆华借助“角色转换”,让扮演国王克劳狄斯的倪大红、重臣波洛涅斯的梁冠华分别在适当时候与哈姆雷特的饰演者濮存昕进行角色换位,以此强调人的处境永远处于变化之中,今天的王子明天可能就是国王或小丑,今天的国王明天也有可能就是王子或小丑,以此彰显导演的“第二主题”——人人都是哈姆雷特,人人都可能面临着这一同样的无解的难题,从而在原著与观众之间搭建了一个关联的通道,一部性格悲剧也由此转变成一出社会哲理剧,引发现场观众的共鸣。
2001年,在编演《理查三世》时,林兆华更是宣称:“我不替莎士比亚说话,我替我林兆华说话。我是当代的人,我身处在当代的生活环境当中,我遇到的是当代的事,我看到的也是当代的现象。”⑩与原作不同,他选取的立足点是:我们生活当中就常有亲人、朋友、同事在算计你,你还把他当作至交,正是这种对阴谋的麻痹感助长了阴谋的扩张。他认为:“麻痹的人群好像和谋杀者是敌对的,但在麻痹的状态下,在谋杀中他们成了谋杀的帮凶。”B11在林兆华的舞台上,《理查三世》这部宫廷争斗剧出现了“第二主题”:阴谋就在身边,但人人对阴谋视而不见,这种麻痹感助长了谋杀的成功。对人性的思考与探究成了永恒的主题。
2.打破幻觉舞台限制,力求叙述艺术出新
20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现代话剧一直把斯坦尼拉夫斯基以“体验”“营造幻觉”为主体的写实主义理论奉为圭臬,舞台上进行的一系列演出都要给台下观众以正在发生的真实幻觉,从而在观众与演员之间竖起一道无形的“第四堵墙”,形成叙述者的现场缺失。这种千篇一律、单调乏味的导演式样令人腻烦,舞台艺术形式创新势在必行。作为中国小剧场创始人之一的林兆华对舞台表现手法进行了大胆尝试,自由的叙述方式是其舞台艺术的一大亮点。
在林版《理查三世》的舞台上,理查身兼两职,一是作为故事的主要人物,按照莎氏原著中的情节实施着篡权夺位的阴谋;二是作为叙述人,时不时从戏中跳出来,以一个旁观者的口吻把理查的谋杀行径讲给观众听。诚如林兆华所言:“我没有把他当做一个人物去演,而是想要建立理查的叙述这样一条线……也就是说他一边实施着这些阴谋,一边叙述着理查的故事,我想建立这样一种东西:他既是叙述人,又是故事里边的人,还是事件的导演,这个阴谋是他策划的。”B12
在反映古罗马故事的《大将军寇流兰》中,林兆华借用重金属摇滚乐队制造的叙述效果更加明显。演出一开始,马勒《千人交响曲》飘荡全场,旋律刚一结束,三个长发飘飘手抱电吉他的摇滚歌手就冲上舞台,在强烈粗犷的音乐中,由群众演员扮演的公民手持棍棒成批地涌到台前,“讲述着”他们对主人公马修斯的强烈不满。马修斯率领罗马军队攻打伏尔斯人寇流兰城之时,两支摇滚乐队在舞台现场即兴发挥,以重金属摇滚的力度演绎着两军之间血与火的拼杀。在中场休息时,乐手与歌手现场献技,好似一场摇滚演唱会,诉说着马修斯被放逐的悲伤情绪。中场休息一结束,两位刚刚还在“斗乐”的乐手转身成为两国的间谍,互相交换情报,由此嫁接起大将军寇流兰/马修斯被放逐出罗马的故事。
林兆华导演让演员在剧中角色与真实身份、舞台与现实之间自由切换的做法完全不同于传统写实话剧舞台的叙事模式,他故意放大舞台演出本身的假定性,彻底推倒了“第四堵墙”,打破了观众真实生活的幻觉感,使其充分意识到此时此刻他们正在剧场观看演出,舞台上表演的也只是虚拟故事,仅仅是一场演出而已,从而在观众与演员之间制造一种间离效果,强调剧目阐释的哲理,引发观众强烈共鸣与批评意识,进而作出理性的裁断。
3.挖掘演员表演潜质,拓展自由发挥空间
“表演艺术是一个动态的审美意象的创造过程。体现着艺术创造主体对审美对象的直觉和形象的把握,并予以审美完形,最终完成审美符号的系统创造。”B13舞台艺术形象的创造依赖于演员的领悟、想象及其表演动作与造型。林兆华对独霸中国话剧舞台的写实模式持否定态度,认为戏剧舞台上不能只是纯体验,也要发展创造收放自如的表演手法,让演员自己去感觉戏的节奏与风格。
受“戏曲空舞台却蕴含无限表演空间”美学原则的影响,林兆华坚持话剧演员的表演也要进入一个自由王国的境地。他常对演员讲提线木偶:“演员的表演状态既是木偶,又是提线者,而体验艺术只演那个木偶。演员与角色时而交替、时而并存、时而自己都讲不清此时此刻我到底是角色还是我自己;经常还时不时地同观众一起审视、欣赏、评价、调节、控制自己的表演,这种中性的状态能使演员获得心理的、形体的、声音的解放。拉开这个距离他能感觉得到自己是如何扮演角色的,自自由由地与观众交流,时而进、时而出,叙述的、人物的、审视的、体验的无所不能。这才是表演的自由王国,是表演艺术成熟的标志。”B14他非常重视挖掘演员的表演激情与潜力,几乎很少和演员说戏,甚至不告诉他们要达到何种状态,只是让他们做减法,去掉理论、经验和套路,在一种似与不似之间找寻自然的“自我”状态。事实上,对于这种表演状态,他自己心中也只有模糊的方向,知道自己不要什么,但具体想要什么自己倒也不见得清楚,在演员不断的形体表演尝试之中,思路逐渐明晰,最后确定下来。
林兆华对《理查三世》的编演最为典型。在排练该剧时,莎士比亚的经典台词是给定的,演员自己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状态去表演,“导演是说通过做游戏来体现一种状态,人物与人物心灵的交流的那种状态”B15。排戏天天处于一种放松的游戏状态,演员没有了“我就是”典型环境下刻画典型人物的传统话剧表演规律的束缚,取而代之的是找寻一种心态,一种不借助台词、人物性格与人物关系,却能表现内外不一致“我来演”的感觉:“演员形体上做的事和他说的话表面是不搭杠的,形象也不搭,衣服、头饰都不搭,就通过声音传达人物内心的东西。”B16当理查向安夫人求婚时,他口中称赞着安夫人的美貌,却与另一个女演员随意地做着或亲热或疏离的动作。这种形体动作与台词内容的相悖或矛盾意在突出人们对阴谋的麻痹感。为实现这种即兴式的、随心所欲的演出目标,演员根据个人对剧目的理解,创造一些“老鹰捉小鸡”“排排队开火车”等儿童游戏动作,一帮成人在轻松明快的孩提游戏中实施着残酷的杀害与被杀。林兆华说:“戏剧舞台本来就是演员的,不是导演的。梅兰芳演《宇宙锋》,你看的是梅老板还是导演?艺术创造不是说完全一个导演就能够弄出来的,真的不是。我对表演的要求和追求,是濮存昕给我实现的,他成就了我的戏。因为戏剧主要是表演,我们忽略了表演,而且现在缺的就是好的演员,好的创作者。”B17为此,他给演员很大的创作空间,鼓励演员“兴之所至”的即兴表演。以演员当众扮演为中心的表演,是对舞台戏剧性特质的回归。
三、林兆华莎剧编演中存在的问题
在林氏舞台上,叙事方式与即兴表演都是为具有当下性的“第二主题”服务的,通过演员在舞台上的“演”与“评”充分发挥中国传统曲艺的艺术手法,打破幻觉剧场带来的真实感,消除横亘在演员与观众之间的“第四堵墙”,给观众以思考、反省空间。林兆华不愿重复历史、重复别人,着力打造经典的“第二主题”,形成自己的标签,这是一种求新的表现。但“主题先行”的做法有时会导致对舞台形式和表演手法的过分追求,其对莎剧颠覆式的解构在给观众带来全新感受的同时,也容易误导大家对莎氏剧目的理解。
林兆华的莎剧演出,遭受非议最多的是对文本案头分析重视不足,“轻文本”是他的硬伤。高行健在肯定林兆华艺术革新性时曾指出:“我们之间的讨论,绝少思辩。我们也几乎从不讨论一部剧作的主题、情节、矛盾冲突诸如此类的问题,可以说把这种令人头疼的文学分析都从我们的讨论中排斥出去了。”B18“重舞台轻文本的戏剧理念也使得他们大多忽视铺排情节与塑造人物,人物往往成为剧作家传达思想理念的工具与符号。”B19对此,蔺海波批评说:“林兆华的戏剧创作在对原著的理解方面存在着绝对化的倾向,原著丰富的思想内涵往往没有得到完美的展现……由于其在思想的深度与感受的深度上尚不够深厚,其明确的追求目标与在实践中实现的程度存在着一定的差异。”B20林兆华的戏剧属于实验性戏剧,其对原著的阐释超越观众的认知水平是情有可原的,观众有时也需要导演的引导和提升。但由于缺少文本案头分析的基础工作,他的“第二主题”或偏离原作主题太远,或缺乏从原文本生发至“第二主题”的顺畅通道,有时显得非常突兀,背离了观众的“期待视界”,因而无法获取观众对戏剧欣赏的认同,演出效果也大打折扣。正如张江教授所言:“如果预设立场,并将立场强加于文本,衍生出文本本来没有的内容,理论将失去自身的科学性和正当性……如果我们预设了立场,并站在这个立场上重新认识甚至改写历史,那么历史事实的真实性和历史文本的真实性又在哪里?”B21
在林版《理查三世》舞台上,主观预设缺陷特别明显。该剧的主题从揭露理查的残暴变为批评公民的麻木,靶标发生了改变,演出的重心及舞台手法也随之变化,但台词却不变,表现出一种明显的不协调性。这本是导演的故意而为,意在通过语言与行动的悖论凸显麻痹感。然而,许多观众反映无法跟上舞台的节奏,总在揣摩导演的寓意,难以融入其中而身心俱疲。林氏的改编“是否过重于、甚至有点主观上故意抽离出原剧那些灰暗、极不明显的地方,然后把它过分夸大,夸大到或许就有歪曲。抽离得太厉害,就偏离得太远,远到几乎可以摆脱原剧本”,“对于这样一部戏来说,发现的价值过于片面,只做这样的发现是否有点遗憾”?B22
过分强调“一戏一格”形式出新的艺术追求导致的结果是:实验永远在路上。在改变不好习惯的同时,成功的经验也往往易被丢弃,致使舞台表演元素不能达到最优质的稳定组合,演出效果波动很大。“在这样一种艺术追求的驱使下,有的表现形式运用得成功到位,有的表现形式则非常晦涩难懂,不尽人意。”B23比如在《查理三世》演出中,导演把升降机拉上了舞台,理查手拿扩音喇叭站在升降机上喊叫,让人觉得滑稽可笑。整场演出形式花哨,录像上的台词几乎听不清,剧情不连贯,其另类的诠释手法使得并不熟知莎氏经典作品的中国观众愈发感觉陌生而难懂。“过于追求出新的结果,是遗漏了原作中本应着力表现的何以出新的基础,使得舞台呈示时常缺乏必要的铺垫,观众往往莫名其妙。”B24
戏剧的生命力在于不断的创新之中,只有破而后立,方能发展戏剧,但不能一味“为新而新”。求新求奇在成就先锋话剧的同时也成为其短板,对此我们应加以重视。林兆华在接受张弛采访时说:“如果我的戏剧能够被所有大众接受,我就没有做戏的价值。如果我的戏有一点能给人一点新的思索,我这个戏就有价值。”B25张弛对此提出质疑:“我理解你的这个基点就是说艺术家要非常顽强地去表达他认为好的东西。但这样解释太笼统,否则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弄到钱排一部戏,然后对大家说你们爱怎么评价就怎么评价。”B26
艺术创新确实需要提倡与支持,但同时也需要有所节制,不能盲从个人偏执,只为个人艺术追求,而不在乎别人的理解、观众的反应。由于林兆华对新奇形式的过分追求,观众跟不上其舞台调度的节奏,不能真正参与到演出之中,这样也就违背了观演规律。同为先锋导演的孟京辉有着如此感悟:“我感觉我需要一种更多人的交流,但是在和更多人进行交流的时候,不可能完全像以前那样很任意、很任性。你必须将很任性的东西, 在美学上让更多的人接受。更多的人其实是支持你的人,没有这些人你就无的放矢了。”B27所以,对导演及舞台演出而言,观众很重要,让观众看懂你的戏更重要。
四、对经典传承的反思
“林兆华是位擅长思考、尤其是非常痴迷于社会学层面上的思考的导演,这正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崛起的一代先锋艺术家的共性。然而,坦率地说,由于这一代艺术家很少是真正伟大的思想家,在知识资源储备方面的先天不足,使这些思考在多数场合不仅不能提升艺术作品的价值,反而成为障碍。”B28林兆华改编的3部莎剧映射出了国内先锋话剧导演对待莎士比亚等经典作品的态度与思考,其成败得失可以为国人如何改编传承经典提供有益的借鉴。
林兆华曾说,演戏如放焰火,放完就没了。昙花一现的艺术无法持久恒远,全新的舞台样式也许会激起观众一时的好奇与热情,但等烟火落地之后一切都归于无,经典便难以长久保留。固然,先锋话剧的实质在于探索与实验,探索新的舞台表现手法,经典传承并非其责任与义务。但既然借助了经典,就必须对经典传承做出贡献,先锋戏剧人需要加强对经典传承的责任感,调整经典传承的策略。
单一传统的表演模式不能满足多种需求,所以经典的创新改编势在必行,但忠实原著与创新经典也不是完全对立的。对于经典,我们首先要怀有敬畏之心,没有这个态度就无法与圣贤对话,无法读懂经典深厚的精神内涵。对于改编的标准与尺度,虽不能用数字来量化,但也是有规律可循的,经典改编不能全凭导演个人的主观感受。戏剧是现场表演的艺术,受众是普通观众,评判戏剧优劣的决定性因素是剧场和观众。诚如著名戏剧家曹禺在给林兆华和高行健的复信中所言:“我赞同你们提出的‘充分承认舞台的假定性,又令人信服地展示不同的时间、空间和人物的心境的创作方法、演出方法。其中,‘令人信服四字很重要,不要弄到‘我明白了,大家当然应该明白的地步。”B29
习近平同志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提出:“把人民作为文艺表现的主体,把人民作为文艺审美的鉴赏家和评判者,把为人民服务作为文艺工作者的天职。”B30在对经典进行改编时,先锋戏剧人更应该考虑观众的审美情趣及需求关注,即尧斯提倡的“期待视界”。“期待视界”是观众走进剧场前对剧本的前理解,就经典而言,观众一般都会对剧情有一个基本的定式思维,所以对导演、改编者而言,在消费经典的知名度的同时,也要受观众“期待视界”的约束。
对经典改编而言,如果一成不变,容易造成审美疲劳;如果改变太多,则容易丢失原作的精神。所以,改编经典时一定要对原著进行“有限的否定”,即找到原著精神与现实关注的契合点,在大同中求小异,在主旨下寻外延。“就是实验戏剧,其目的在于破除已有的艺术成规,探索戏剧的空白领域,谋求全新的表现方式,传达逆时代的观念,也不可能超越‘有限的否定性界限。”B31任何一场炫手法而缺思想的演出都不会成功,在脱离经典原著太远的前提下,仅有导演个人的思想深度而忽视观众审美情趣的演出也赢取不了观众的喝彩。正如习近平同志所言:“艺术可以放飞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脚踩坚实的大地。”B32
莎氏经典在中国先锋话剧舞台上的传承是一个永远在路上的难题。如何把握好忠实于原作与创新发展的分寸,将在宏观上决定改编作品的取向与质量。故步自封不可取,但盲目求新亦不可取,需要在尊重原作思想的前提下实现导演艺术的再造与创新。也就是说,要本着“有限的否定”导演原则,以服务于剧场和观众为核心,以倡导正能量的作品为追求,赋予经典以新时代的艺术生命。唯其如此,我们方可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再塑经典,使经典历久弥新。注释
①②何成洲:《全球化与跨文化戏剧》,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22、25页。
③⑦潘妤:《一千个导演有一千个莎士比亚》,《东方早报》2014年4月23日。
④[德]伽达默尔:《伽达默尔集》,邓安庆译,上海远东出版社,2003年,第479页。
⑤朱寿桐:《文学误读的执意、曲意与恶意》,《文艺争鸣》2015年第4期。
⑥颜榴:《守望与省思——外国戏剧在中国30年》,《戏剧文学》2013年第10期。
⑧B22B25B26张弛:《林兆华访谈录》,《戏剧文学》2003年第8期。
⑨⑩B11B14林兆华:《戏剧的生命力》,《文艺研究》2001年第3期。
B12B15B16张誉介:《〈理查三世〉采访笔录》,《戏剧》2003年第2期。
B13B31戴平主编:《戏剧美学教程》,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56、155页。
B17《走近“大导”林兆华谈风格:当代or传统》,新浪娱乐,http://ent.sina.com.cn/j/2010-12-27/18193189926_3.shtml,2010年12月27日。
B18林克欢编:《林兆华导演艺术》,北方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2页。
B19陈文勇:《1990年代中国话剧的反思与批判》,《戏剧艺术》2015年第1期。
B20B23B24蔺海波:《90年代中国戏剧研究》,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第263—264、263、264页。
B21张江:《强制阐释论》,《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
B27孟京辉:《先锋戏剧档案》,作家出版社,2000年,第347页。
B28傅瑾:《〈大将军〉和“人艺”的林兆华时代》,《读书》2008年第4期。
B29引自曹禺在《绝对信号》演出之后给林兆华和高行健的复信。
B30B32习近平:《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5年10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