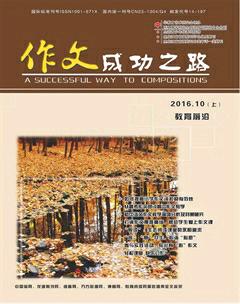切忌盲目崇拜作者
郭刚
中学语文教学有个很俗的现象:某作家的作品进入教材,进而进入课堂,该作品及作者就被推上了神坛,师生千方百计地要去阐说作品的每一处是如何的精妙,作家行文中的每一个小动作是如何的必须和唯一,老师就引导着学生开始了造神运动。这是普通语文老师的课堂教学中大量存现的事实,即使这部作品不是同类作品中最好的,即使这部作品不是该作家作品中最好作品,即使作品中的观点、构思、某处表达不是最好的处理状态,都无碍这种以崇拜为基础的验证性解构——反正教师又的是权威。这有点像官场崇拜,上级的任何表现哪怕是不雅行径也都是风度,上级的任何话哪怕是套话废话都是重要指示。更像是歌星崇拜,哪怕是台风不好,哪怕是歌唱的走调,也都不影响在人们心中的地位。语文教学中的作品、作家崇拜正反映了社会习惯心理和文化恶习。于是探讨这个问题,就不仅仅是为语文教学着想,还有攸关教育的功能:情感、态度、价值观,是个“育什么的问题”。
在作者的崇拜中,最突出的表现是存在的即是优秀的,于是文章的导读(教学)就成了解证其优秀的过程。笔者曾经同一天连听两节优秀公开课,执教者都是当地选拔出来的优秀教师,却依然没有跳出作者崇拜的套子。
一节课是《我很重要》,毕淑敏的作品。我们的老师一开始就说“毕淑敏的散文在散文界有盛名,被选入多种教材。我们要注意咀嚼揣摩她的语言强大张力和优美文辞”,于是整个课堂就为此作注作解证。然而,事实上,毕淑敏此文却是有问题的,她通篇在说“我很重要”,而最终表达的结果却是“我对于父母、对于朋友、对于自然、对于事业的重要”,实际上游离了自己的主题,恰恰是表达自己对于自己来说不重要。这个问题的造成与毕淑敏写作此文的背景——中国社会还刚刚开始关注自我意识的觉醒——有关系,也就是说作家自己还没有真正地弄明白“我为什么很重要”。课上到后半部,老师设计了一个拓展延伸,请谈谈你熟知的一位古代人物,结合他们的言行说说他们是怎样认识自我的,并进一步阐发“重要”的内涵。(教师举例)李白、杜甫、屈原、司马迁……或对以下几人说几句话:三毛、海子、张国荣、富士康跳楼职工。这个设计的意图本身是无可非议的,通过学生举出更多的人,以考察或加深学生的理解。但从课堂上看,学生举出的例子和老师所举的李、杜、屈、司马雷同,问题就出现了。表明在老师和学生的头脑里,把这几个人的坚持目标、执着追求、成就功业与“主体觉醒”和“个人权利意识”混为一谈。从中可以看出教师自己并引导着学生对“我很重要”所作的理解彻底跑偏。而这个跑偏明显是收到毕淑敏原来文字的影响,又一次证明了,《我很重要》是一篇有问题的不适合给学生读的文章。然而,我们的老师从没想到这一点,努力地,不遗余力地,引着学生去赞美毕淑敏的文字——为了表达对作者的崇拜,不惜误读误解。
另一课是《可以预约的雪》,林清玄的作品。一个惯性思维是,“原来的题目——可以预约的雪——是个不可替代的好题目”。观察过的多个课例中,教师都引导学生去分析本文的题目精彩在何处,然后列出其他几个题目——当然是故意的弄出的面目可憎的或直白或僵死的题目——“不可预约的人生”、“常与变”等等,与之相较,达到排除其他的目的。这种设计,如果是为了在题目的比较重进一步理解主旨和作者语言艺术,当然是很好的,但如果只是为了证明这个题目有多好,显得做作,我想林清玄自己都不一定同意。意之所到,兴之所来,定个题目,是作家常有的事。就此文来说,我觉得“菅芒花又开了”或“菅芒花还会开”就是很好的可以与原题媲美的题目。与原题相比,两者都只是少了个比喻,而那个“雪”与“菅芒花”之间的比喻其实对于全文的主旨表达和“增美”来说并无用处。具体来看,“菅芒花又开了”明示花开和季节变换,“又”字则饱含人事变化的感慨和伤感,以此作为文章起笔的由头,一点都不算浅陋,而肯定的语气则又提示了作者的主旨。如果考虑到作者的文字止于“尚未看到菅芒花的此时”,也可以把这个题目微调成“菅芒花又开了吗?”估计也不差,既然如此,我们的老师为何一定要引导学生去证明原题是最好的呢?这是一种典型的一言堂。
崇拜作品和作者反映出两个问题:
一是对文本的解读不能有自己的独立思考,往往是浅读,或者是随着教参一类的东西附和着读,甚至是误读而不自知。老师在不深入地读文体的情况下又如何设计出真正有效的精彩的教学呢?
二是对学生来说,长期的唯作者是尊,满足于解证作品之“优”,从不怀疑,不会辨析,学生学语文除了获得一些“告诉”的内容之外,独立、主动、质疑的精神都将无从谈起。就那个《可以预约的雪》的“题目问题”来说,即使我们不能肯定自己所拟的题目比林清玄好,但起码可以鼓励学生去创造自己的“优”,这才是教学的本质。
所以我们应该鼓励不唯作者是尊,不天生的惯性的去崇拜作者,敢于去发现作者之“失”,并提出自己的“更优”,这样的教学对学生来说,才是真正的培养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