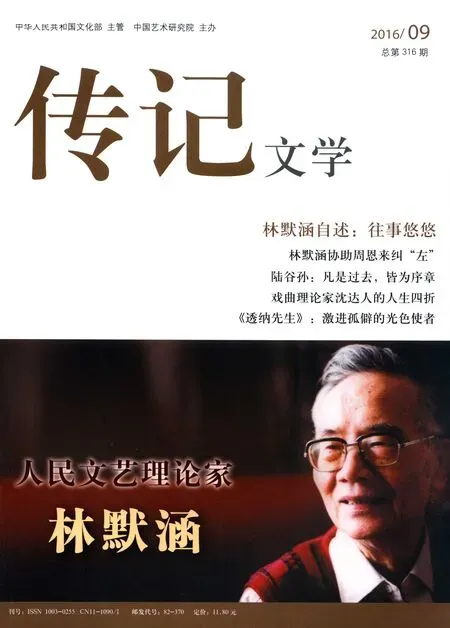陆谷孙: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文|林金壹
陆谷孙:凡是过去,皆为序章
文|林金壹

“我是我父亲的儿子”
陆谷孙先生一生扮演过各种角色:翻译家、名师、委员……世人一提起先生,第一反应多是“译界泰斗”“复旦教授”,但陆谷孙自己引以为豪的却是“父亲的儿子”这一再普通不过的身份。
1940年,陆谷孙出生于当时还处日寇铁蹄下的上海,后因日伪扫荡,全家匆匆搬离,迁入建国路合群坊。陆谷孙的童年记忆由此始,也是在这里,父亲陆达成开始了对他的文学启蒙。据陆谷孙回忆,父亲用其读书时获得的奖品《拉封丹寓言》作为教材教他看图识字,后来逐渐扩展至《三字经》《百家姓》等中国古代文学典籍,还讲《最后一课》等爱国故事给他听,给幼小的陆谷孙带来强烈的心灵震撼。1945年,抗战胜利在望,美军B-29袭击日本占领上海,便有谣传称上海将沦为焦土,陆家全家协商后,由陆达成携妻老和子女返回余姚老家生活。即使时事纷乱,社会动荡,陆达成依旧不忘对子女施以文学教育,除了要求孩子们背诵晦涩的古文如《二十四孝》《增广昔时贤文》《曾文正公家书》等,还每晚开设法国文学讲堂,给孩子们动情地讲述书中故事情节,选用的书籍多是文学巨匠的作品,如大仲马的《侠隐记》《基督山恩仇记》和雨果的《银烛台》等。几个孩子听完故事觉得不过瘾,还要到院子里表演,起初大家纷纷争抢主角,到后来都自觉没趣就“罢演”了,唯有陆谷孙兴致不减,一人分饰多角,“抡起根门闩,独自在那儿手舞足蹈,口中念念有词”。父亲对法国文学的热爱让幼小的陆谷孙沉醉其中,使得陆谷孙自小就结下了与语言文字的不解情缘,也为后来父子合译法国作家都德的短篇小说集《星期一的故事》埋下伏笔。
陆谷孙虽出自书香门第,但并非名门望族,父亲陆达成五六岁时因家境困窘仍只能在家识方块字而无法上学,待从县立高小毕业意欲出外升学时,又因家中债台高筑而被迫进了钱庄当小文书,直到15岁时到上海投考中法学堂才得以重返校园。也许是因为儿时学业被无奈中断的遗憾,父亲陆达成对儿女的学业要求十分严苛,强调凡事“以学为先”。陆谷孙回忆,一生没有受过父亲的表扬,除了某年读小学时因考试成绩优秀,父亲专程到书店买来一册商务版的《辞源》,在首页用工整的毛笔小楷写下:“为谷儿……本学期考试成绩优良特购赠此书”等鼓励的字样。母亲早亡,父亲又因工作缘故常年在外,陆谷孙便交由祖母抚养。即便如此,父亲仍坚持通过书信至少每周一次对陆谷孙的学业进行远程“遥控”监督,孩子们写的文章,陆达成必定每篇审阅并用红墨水进行修改。
陆达成虽多年从商,但骨子里仍是个文人,自有一副文人的风骨和性情。陆谷孙幼时习字,父亲陆达成秉持“胸中不正,则眸眊;眸眊,则手抖笔颤”的书法理论,认为字若歪斜,必定是心有邪念。除去临帖,陆达成有时兴之所至也会写下“世之方物”“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等字句要儿子模仿,实是在其练书法的同时灌输刚直豁达的人生态度,希冀儿女们不仅要练字,更要修炼心性。陆达成一生爱穿唐装,心中的那股中国士大夫的正气也坚定不移。陆谷孙后来在文章《我的父亲陆达成》中回忆,父亲曾如何正色训斥当年国民党浙江省省主席黄绍竑的女婿,当面称他是“猥琐小人”。面对强权,陆达成丝毫不畏;面对弱势人群,他则始终热情以援。不论是被国民党囚禁的表叔裘柱常,还是遭鲁迅先生批判过的徐懋庸,或只是在港工作期间的一位“小同事”,父亲陆达成都不吝援手。这种不阿权贵、帮助弱小的秉性深深地埋进陆谷孙的血液中,伴其终生。1981年,陆谷孙邀请父亲旧友董浩云先生进餐,董问是否需要带上几件物品回国,被婉言谢绝,陆谷孙只要求一张父亲在董手下工作时留存的字迹的复印稿,因此被赞为“达成先生家风不灭”。除却为人处事的言传身教,父亲在生活上的作风也深刻地影响着陆谷孙。陆谷孙念中学时,想要一台60元的唱机,父亲觉得太过奢侈,且不利学习,就不批准;当陆谷孙已在上海念高中时,父亲仍严令禁止他穿皮鞋,戴手表。某次为了满足虚荣心,陆谷孙擅自戴着父亲的手表去上学,父亲发现后,派陆谷孙表哥来学校没收,还要求他回家写检讨书。直到研究生时代,陆谷孙在日记里提到男女同学的暧昧关系,被父亲察觉后仍遭到严厉批评。陆达成还很注重地板清洁,陆谷孙攻读研究生时,父亲退休回沪,父子同室,陆达成每天必早起从底楼扫到三楼,这个习惯也同样延续到儿子身上。而且,陆谷孙始终谨记父亲“小富可,大富不敢”的教诲,一生清贫,不慕虚名,自得其乐地过着知识分子的“草根生活”。

1962年,陆谷孙与父亲在杭州西湖留影
可以说,陆达成集家师、严父和益友于一体,以自身的思想行为为准则,给陆谷孙树立了人生楷模。陆谷孙曾说,现世给了他不少虚荣,但他并不看重这些,唯一想做的就是“父亲的好儿子,以长驻记忆的父亲的修身言行,当作绳墨,努力‘克隆’出一个无愧于他的儿子来”。
“无偿写作,虽成无荣”
父亲陆达成带领幼小的陆谷孙迈进了法国文学的殿堂,一心想成为“父亲的好儿子”的陆谷孙本打算继承家学从事法国语言方面的研究,却不料命运弄人,最终被复旦大学的英语系录取。于是,1957年,17岁的陆谷孙进入复旦从零基础开始学习英语,当时年少的陆谷孙绝不会想到,正是英语成就了他一生最负盛名的功绩。
1965年,陆谷孙从外文系硕士毕业并留校,在紧接着的“文革”浪潮中,他被打成“逍遥派”,生性乐观的陆谷孙后来回忆说,自己不会闹革命,被划到该派别后就是看书,看完书就给小朋友们讲故事。“托‘四人帮’的福”,陆谷孙在写作组担任编译期间,读了不少的外文书籍和文章,政治任务反而成为陆谷孙学习外文的绝佳机会。在1970年的“一揪三反”中,陆谷孙又被认为是“裴多菲俱乐部”成员而遭隔离。所幸陆谷孙出身清白,没有任何参加过“反动”组织的“前科”,也没有海外关系,一个月后就被释放。同年,他被分配进入由工宣队领导的《新英汉词典》编写组,从此开始了他的漫漫编纂长征路。在那个革命风暴席卷全国的红色年代,编写词典也必须“上纲上线”,纳入既定的“革命”流程:首先,以大批判开路。编写组需要从过往的词典中揪出政治毒素,把从牛津、韦氏,到以《英华大词典》为首的国人所编写的词典作为反面教材狠狠批判一番;其次,要秉持“以我为主”的原则,即以词典为载体对外积极宣传新中国的文明成果,例如毛泽东语录、样板戏、五七干校等。这样的硬性要求使得陆谷孙内心挣扎,一直从事英语研究的他深知词典是学习语言的工具,而非政治宣传的手段,照这样的规定编纂出来的词典已失去其原有的实用价值。为了保留心中的学术底线,陆谷孙最终决定和他的一群英语票友共同“曲线救书”,就这样,编写《新英汉词典》就变成了编写组和工宣队的暗中博弈。陆谷孙借着自己的编译工作之便,和编写组其他人员私底下交流英文书刊,变戏法似的把实用生动的英文条目塞入“红色语录”的庞大队伍中。后来由于陆谷孙等“救书”心切,拼命地往“政治军队”中添加“新兵”,以致工宣队看到红、黑、蓝各色标记混杂的校样时斥责说:“你们打翻了墨水瓶吗?”《新英汉词典》总共编写了五年时间,自1975年第1版问世后,累计共售出1000万册以上,堪称中国辞书史上的销售奇迹。现居香港的翻译家黄灿然至今记忆犹新,当初他去《大公报》编辑部考国际新闻翻译能“一考而过”,多亏了出自陆先生之手的这件宝物。尽管词典多以政治内容为主,但不少外国人士仍从中看出了新中国的变化,陆谷孙和那几位学术前辈功不可没。
《新英汉词典》的任务顺利完成,陆谷孙得以重返讲台,可上天似乎不愿这位能人只做一名教师,一项重大任务又指派下来:1976年,周恩来总理亲自决定要筹划《英汉大词典》的编纂,陆谷孙于是再次被调派进入新的编写小组。词典草创时还处“文革”末期,与现在观念不同,那时的教员可都垂涎这只“喷香的鸭子”,因为它相当于国家赐予的一块“免劳金牌”——可以取代“五七干校”的体力劳动,所以一时间编写组“门庭若市”,成员多达108人。而到了改革开放,很多人选择了出国深造,或是奔向了条件更为优越的工作岗位,编写组不断萎缩,最少时只剩下17人。加之资金匮乏,编写词典的工作越来越难以为继。就在许多领导都已不把它当回事的情况下,陆谷孙依旧憋着一口气,在跑道中尽心尽力地跑着,和时间展开了拉锯战:别人上完课就回家休息,他上完课就得去编词典。为了保证词典排印的质量和进度,陆谷孙不得不打电话一再拜托印刷厂,恳求他们帮帮忙。没有经费,连专门印制的卡片都买不起的编写组只好另辟蹊径,将印刷厂印封面多余的纸裁剪成四方形状,然后在背后的空白面记录词语和例句。在编写组几已走向穷途末路之际,陆谷孙却主动揽下了主编的活儿,并立下铿锵誓言:词典编完之前不出国、不写书、不兼课。随后,为争取国家经费,陆谷孙拿着自己苦心经营十几年的“论文草稿”,斗志昂扬地去北京“答辩”,成功说服了在场的几位大师级前辈,使《英汉大词典》光荣跻身“七五”规划重点项目的行列。直至1991年,长途跋涉了15年的《英汉大词典》终于出版,两卷词典收录词条达20万,囊括历史神话、宗教流派、文化风俗、中医药学及各种自然社科的专名术语,包罗万象,俨然一部英汉百科全书,学术性和实用性并举,坐稳了中国辞书界的“大佬”位置。后来此书成为联合国的必用工具书之一,享誉国内外。

陆谷孙主编《英汉大词典》第2版
在语言学方面颇有造诣的学者陈原先生曾不解地问陆谷孙:“陆谷孙,你晓得欧洲要惩罚一个人用什么办法,就是把他发配去编词典,你怎么会编得这么来劲?”的确,借用当下流行语,编纂词典就是个“磨人的老妖精”,正如陆谷孙亲口所言“编词典就像做厨子,受不了做饭做菜的热气,就不要轻易进词典编纂的厨房”,可陆谷孙却是在日复一日的热气蒸腾中挖掘出了“当厨子”的乐趣,就“在于遨游英语语词的海洋”,而编词典的报偿,则在于“翱翔英语文化的天地”。陆谷孙一生痴迷莎士比亚,常喜欢引用他的一句名言:What’s past is prologue(凡是过去,皆为序章),一切都还是开始,他还在前行。“找乐子”的心态伴随他度过编写两本大词典的几十个春秋,直至其已过花甲之年,仍让他不愿停歇。2001年,本该颐养天年的陆谷孙再一次决定出面主持《英汉大词典》的修订工作,拾起老行当又兢兢业业地工作了6年,2007年,《英汉大词典》的第二版面世。而早在20世纪90年代,陆谷孙因受友人启发,便萌生想编汉英词典的想法,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于是每天面对密密麻麻的中英文资料,不断地整理和删改。外人看来着实太过辛苦,他却似乎乐在其中,还不时为发现中英互译中的绝妙表达而开怀大笑。直至2015年8月,这本耗去陆谷孙15年光阴和心力的《中华汉英大词典》终于出版,陆谷孙也完成了他人生中的最后一项事业,算是对他的“role model”梁实秋及林语堂两位大师的深切致敬。
陆谷孙在词典编纂的路上一走就是30多年,两本词典几近倾注了他所有的青春年华,但他从未后悔,从未抱怨。很多人都看到了陆谷孙在词典大功告成后的荣耀,可却忽略了支撑他一路走下来的并不是聚光灯下的闪亮光环,而是作为一名文化人,自觉背负中英文化沟通使命的责任感和对这个苦难祖国深沉的爱。这样的“无偿写作”给陆谷孙带去的或只是虚名,但对于千万曾为其殚精竭虑的学者,对于从中受益的读者,对于整个社会,却是一个大写的“恒”,一颗饱含真情的心以及包裹在这心里的“诚”,无一不让人为之肃然起敬。
“我的天职就是教师”
陆谷孙曾戏称自己从《新英汉词典》到《英汉大词典》,欲罢不能,“成了一个专门编词典的匠人”,然而除了编纂词典外,陆谷孙还是另一领域的匠人:教书。“我喜欢教书,我喜欢和学生们在一起”,每每被采访陆谷孙总是如是对记者说。从“文革”前作为研究生代师授课算起,陆谷孙已经从教半个多世纪,除却革命年代因种种缘故被迫离校的时间,陆谷孙可说是一生都离不开讲台。在研究生时期,即使是代课,陆谷孙也一丝不苟,必定“精细地备课”:把课堂上要说的每一句话都写下来,背出来,然后对着镜子反复练习。等真正成为一名教师,陆谷孙对待上课的认真和严谨只有增无减。除了因身体原因而无法上课,陆谷孙从不愿欠学生一堂课,严寒酷暑,始终如一。在上课这件事上,陆谷孙一直对自己严苛。当他升格为外文院院长后,对于因出访开会而缺课的老师,他总会询问今年的缺课次数和补课情况,如果得到的回答是“让博士生去上的”,陆谷孙就打心底里不认同,因为他觉得这是作为一个老师最基本的要求和底线,必须对学生负责。如果说教室是他的“战场”,那讲台就是他的“阵地”,而一旦站上讲台,他就定要全力以赴。陆谷孙坦言,自己上课是有表现欲的,并且认为没有表现欲的老师上课会非常无聊,因此,即便满头花白,陆谷孙依旧能以一腔激动的“老血”在这个三尺“阵地”里挥洒汗水——他逐字逐句地为学生分析莎士比亚的剧作,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受点莎翁的熏陶;慷慨激昂地讲解英美散文,深度解剖英语的魅力所在。他讲课幽默风趣,常使学生捧腹大笑;又不失睿智大气,总让听者心悦诚服。不仅复旦学子爱听陆谷孙的课,连许多工作在外,与其素未谋面的人士也都慕名前来,因为陆谷孙的课往往人满为患,来者宁愿站着也要“听君一席言”。陆谷孙的敬业也赢得了学生们的爱戴,在一年评选“十大最受欢迎的教授”的活动中,陆谷孙位居榜首,他高兴地说:“我一生中得过不少奖,但这次活动完全是‘民办’的,是给我喜悦最多、让我最感动的一次。”一位老师能得到学生发自内心的认可,对陆谷孙来说,足矣。
陆谷孙尽管热衷于在自己的“阵地”上高谈阔论,却并不拘泥于高台之上,而是时常走进学生中间,做一位和学生“零距离”的良师益友。在校园里,他喜欢和学生在课堂上辩论,互相交流看法;课后他爱和学生一起在校园中散步,探讨一些学术问题;学生交上来的作业,他都一字一句地看过,逐一指出错误,有时还加上一大堆的批注。离开了校园,陆谷孙自家的饭桌也是学生常爱光顾之地,师生自由地切磋和谈论,洋溢着愉快的气氛。陆谷孙在学术上的高度负责让其下门生钦佩不已,而让所有接触过陆谷孙的学生们对其敬重有加的是他强大的人格魅力。编词典是个苦活儿,陆谷孙却以此为乐,他像个稚童探索新世界一样在浩瀚的英语海洋中自在徜徉,最喜欢“琢磨一些词语,发现它们既能在汉英里用,又能在英汉里用”,这样“以苦为乐”的豁达也给学生们树立了榜样:永远要带着好奇的眼光去看待世界。作为老师,他从不摆架子,课上有一个单词念错了重音被学生课后纠正,他下堂课第一件事就先声明,自己念错了哪个字,是某某纠正的。陆谷孙生活简朴,从不追求名牌,吃穿用也向来崇尚简单,但对于学生,他却是无条件地慷慨。一次,有个学生生病住院,他二话不说就拿出1000元送到系里,一再叮嘱“一定要交给他”。此外,陆谷孙多年坚持捐款到系里,惠及多位学生。他一直教导学生做人要真,要透明,并总是以身作则。系里有老师生病住院,陆谷孙即使不方便亲自过去,每次也都会嘱托学生带信封去探望;学生参加歌会,他跑去帮忙加油打气;有人生活遇到困难,他就耐心地开导安慰;教工宿舍摆书摊的小摊主和陆谷孙相熟,有事儿就招呼陆谷孙帮忙看会儿摊,他就认认真真地帮别人“吆喝”,书卖得挺不错;逢年过节,陆谷孙就像位大家长一样给学生们发红包……这种对人以诚相待、热心关怀的性格让陆谷孙不像传说中的名师一样高高在上,而是像位和蔼可亲的长辈,打动了无数师生。受陆谷孙影响,其门下的学生们特别友爱,一直都以师哥师姐相称,就像一个温暖的大家庭。

陆谷孙在课堂上
“留住我们的精神线索”
陆谷孙一辈子潜心研究英美语言及文化,但内心深处仍保留着一份对母语的真切热爱。这一方面和父亲陆达成对他的古典文化教育是分不开的。前文已提及,陆谷孙从小就被父亲要求背诵古诗典籍,即使当时不明其意,等逐渐识字后,便“有一种‘重新发现’的乐趣”,对汉语的精妙体悟也就更深一层。另一方面,陆谷孙虽多次倡导学生读莎士比亚,从中汲取英语文化养料,但同时,他要求学生要“热爱母语,敬畏母语”,除却父亲的文化播种外,更深层的是他作为一名中国知识分子,始终怀有的对于中华文化的热忱。他认为,语言具有一种超时空的力量,是贯穿古今文化的精神线索,而母语,则是一个民族的精神纽带,“是继承和发展有形和无形传统最有力的工具”。陆谷孙是一名英语大师,有人曾问他能否用英语思维,陆谷孙自己也不甚明了,但他清楚,自己的第一反应仍是母语,比如在飞机上无意碰触到他人,冒出口的第一句话便是“对不起”。这是所有生长在中国的华人都应有的文化自觉,正如对古诗有所了解的国人一旦看到古诗词或者听到古文吟诵,会不自觉生发出归属感和认同感一样。
作为语言研究学者,陆谷孙对语言向来秉持严谨和尊重的态度,对其敬畏的母语更是如此,但如今随着新生事物的不断涌入,追求个性的年轻人以使用网络新词、外来词为时尚,一些公众人物为迎合市场也大量使用不规范语言,无疑对汉语造成巨大冲击。陆谷孙曾在一次演讲中客观地分析这种现象的来由,一是历史上五四运动的“全盘西化”和“文革”期间对汉语的糟蹋,二是新兴科技如电脑、手机的普及使得语言趋向碎片化和口语化。当然,陆谷孙并不是要抵制外来文化的进入,更不是反全球化进程而行之,相反地,陆谷孙其实是个很时髦的“小老头儿”,在编纂和修订词典时总是注意引入新词,并且把敏感的“新词意识”视作词典编纂者必须练就的功夫之一。只是让陆谷孙深为痛心的是当下的一些人以语言错误为新潮,以玩弄字词为骄傲,抱着事不关己的态度滥用词汇,轻视甚至侮辱汉语,那些充斥在广告里,流行音乐、影视剧乃至书本中的文字污染令陆谷孙对现代人,尤其是年轻人的汉语修养忧心忡忡。为此,他恳切地提出了三点建议:一、自觉抵制流行文化中践踏汉语的文字,并尝试读一些直排本,识些繁体字,不论是对于两岸三地的文化交流还是对书法艺术的领悟都极有好处;二、做一个“杂食动物”,广泛涉猎各类书籍,从书中找到自己;三、中英互补。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在中国已成席卷之势,但切不可荒废母语,中英互补对于汉语的发展也大有裨益。陆谷孙到晚年仍有感于儿时背诵的对联“晚照对晴空,飞鸟对鸣虫”所呈现的整体美,他殷切地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端正对汉语的态度,把敬畏母语当作一种文化责任,切实地提高汉语修养,“留住我们的精神线索”。
此前英语退出高考统考的信息传出,陆谷孙难掩失望之情:“现在整个社会的观感不对,语言和国家完全是两回事情……这是整个教育文化程度的问题,我再三强调英语和中文不是零和游戏。”在全民“英语热”的背景下,汉语被英语强势挤压,陷入“冷宫”的窘境,对英语的声讨之势也愈演愈烈。和一些惯于将英语和国家实力挂钩的人士不同,陆谷孙始终冷静沉着,对于当前英语在中国“横行霸道”的现象,他有着自己的看法:英语是表音文字,在互联网时代,它的转码接轨相较汉语这种表意文字要容易些,因此具备成为国际通用语的优势,而不单纯依靠政治和经济力量。但这并不意味着要摒弃汉语而全面吸收英语,而是要持有兼容并蓄的心态,学习借鉴英语词汇的丰富性和表意上的清晰,中英对照,共同促进。陆谷孙一针见血地指出,国民对英语的热捧和对汉语的冷落,根本上反映出民族自信和自尊的缺失。要想重振汉语,首先应该做到热爱母语,保护母语。陆谷孙曾说,翻译令他想起“抵达”,从一种文字出发,去“抵达”另一种文字的彼岸。他钻研英语,是想从另一种文化抵达中华文化,在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上,为中华文明拂去尘埃,重焕光彩。
倔强的“老神仙”
在编词典上,陆谷孙注意引入新词;在社会时事的关注上,陆谷孙也同样紧跟潮流,曾和年轻人一样在微博上“闯荡”过一段时间。在那一年里,陆谷孙义务帮网民解答各种有关翻译和英语的问题,还针对一些热门事件作出犀利的点评。主旋律大片《建国大业》上映时曾受到广泛关注,一时间票房急剧上涨,但陆谷孙认为,高票房的背后实是“明星效应”的支撑,至于内容,则是默认为观众都已知晓,就无须费力交代;并且,片中的新内容部分有违史实,是“过度‘高于生活’的杜撰”。陆谷孙本是为图新鲜而开微博,却不料网络世界里鱼龙混杂,过了一段时间陆谷孙就发现不对劲:一些网民完全把陆谷孙当作翻译机器,连一些在词典里一翻就能查到的词也拿来问;还有人因与陆谷孙意见不合就谩骂、指责陆谷孙,甚至有人故意找茬。陆谷孙最终由忍无可忍到失望透顶,决定退出微博。
也许是在网络上感到了世态的冷漠,除了上课,陆谷孙几乎不愿走出自己的“洞穴”——这是他对自己简陋而陈旧的住所的戏称——只想安静地待在家里做学问。等到卸去复旦外文学院首任院长的职务后,陆谷孙更是深居简出,每当学生朱绩崧拿着一些学术机构的邀请函,去他“洞府”领“法旨”时,陆谷孙总是让他以“探亲”的理由推掉。因为常常闭门不出,也多次拒绝记者的上门采访,上海译文出版社的某位编辑就给陆谷孙取了一个“老神仙”的外号,暗指他“不食人间烟火”。的确,以陆谷孙的声望,过名利双收的日子并非难事,而他却甘愿蜷在自己的老窝里,过最为简单的生活。平日里,他就孤身一人在家看书,写文章或改稿,家务由保姆打理,每天的花销经陆谷孙要求须限制在10元以内。逢年过节,保姆回家了,陆谷孙就泡个方便面充饥。其实,陆谷孙大可办张“绿卡”和妻女一起定居美国,安享晚年,但老人就是如此倔强,宁愿每年去美国探亲也不肯住在国外。有人对此颇为不解,陆谷孙只说:“我在中国更有用。”在一次采访中陆谷孙坦言,美国的空气和咖啡香的确对自己有诱惑力,但他总觉得在美国女儿家像是客人,听到秋虫的鸣叫声都会马上想起在余姚的童年生活,因而在那边待不长久。可能有人把这看作一种高尚的节操,但陆谷孙却觉得这与政治无关,而是“故园情结”在他心上扎下的根,正如捷克作家克里玛所言:“我不能离开布拉格鹅卵石的街道,和走过这条街道所有苦难的灵魂。”同样地,陆谷孙也无法割舍自己深深眷恋的故土,以及在这篇故土上生活着的人们。
走完几十年编纂长征路的陆谷孙原可以抱着两本大词典,享受世人加于其身的无尽荣耀,但他不愿,并对《英汉大词典》的频频获奖感到惭愧:“凭一本书到处揽奖,只能说明学术浅薄。”有的刊物想让他做个挂名编委,但汇款单一寄到学校就被他退了回去,原因很简单,无功不受禄。世人给陆谷孙送去鲜花和掌声,但他不需要,只想和宁静为伴,希望大家能“leave him alone”。陆谷孙感叹现在的人都太浮躁,年轻人不爱读莎士比亚,一部分固然是因为读不懂,但更重要的是,没有一份能静下来阅读莎翁的心。缺少这份宁静,想要走进古典文化的殿堂就十分困难。一个人的时候多了,伴随安静而来的便是孤独。很多人耐不住寂寞,但陆谷孙相反,他觉得孤独是灵感的催化剂。当无人可谈心时,他就向内回到自己的精神王国,审视自我,越发体悟每个人不过是宇宙间的一个微小粒子,诞生或逝去都不会对整个宇宙长河产生多大影响,最终不过是复归尘土罢了。对这一点悟得彻底,所以他活得率性,活得真诚,经得起风雨,也守得住底线,不为名利所累,不为俗世所牵。“偏向疏篱断处尽,亭亭常抱岁寒心。消磨绚烂归平淡,独步秋风无古今。”陆谷孙的这首诗是他一生心境的真实写照:过最纯粹和质朴的生活,做一个精神上的“贵族”,活出生命的本色。
陆谷孙生前最喜欢在课堂上背诵杨绛在《我们仨》中写的一段话——“我们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如今,这位倔强的“老神仙”溘然长逝,但他已成为所有敬爱他的人心中永恒的存在。陆谷孙先生,请一路走好。
责任编辑/胡仰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