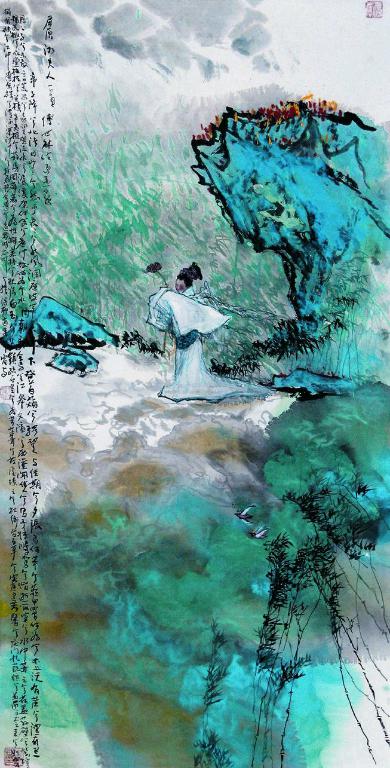诗可以怨【一】
钱钟书
尼采曾把母鸡下蛋的啼叫和诗人的歌唱相提并论,说都是“痛苦使然”。这个家常而生动的比拟也恰恰符合中国文艺传统里一个流行的意见:苦痛比快乐更能产生诗歌,好诗主要是不愉快、苦恼或“穷愁”的表现和发泄。这个意见在中国古代不但是诗文理论里的常谈,而且成为写作实践里的套板。因此,我们惯见熟闻,习而相忘,没有把它当作中国文评里的一个重要概念而提示出来。我下面也只举一些最平常的例来说明。
《论语·季氏》讲:“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怨”只是四个作用里的一个,而且是末了一个。《诗·大序》并举“治世之音安以乐”“乱世之音怨以怒”“亡国之音哀以思”,没有侧重或倾向那一种“音”。《汉书·艺文志》申说 “诗言志”,也不偏不倚:“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司马迁也许是最早不两面兼顾的人。《报任少卿书》和《史记·自序》历数古来的大著作,指出有的是坐了牢写的,有的是贬了官写的,有的是落了难写的,有的是身体残废后写的;一句话,都是遭贫困、疾病、甚至刑罚磨折的倒霉人的产物。他把《周易》打头,《诗三百篇》收梢,总结说:“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还补充一句:“此人皆意有所郁结。”那就是撇开了“乐”,只强调《诗》的“怨”或“哀”了;作《诗》者都是“有所郁结”的伤心不得志之士,诗歌也“大抵”是“发愤”的悲鸣或怒喊了。中国成语里似乎反映了这个情况。乐府古辞《悲歌行》:“悲歌可以当泣,远望可以当归。”从此“长歌当哭”是常用的词句。但是相应的“长歌当笑”那类说法却不经见,尽管有人冒李白的大牌子,作了《笑歌行》。“笑吟吟”的 “吟”字并不等同于“新诗改罢自长吟”的“吟”字。
司马迁的意见,刘勰曾顺便提一下,还用了一个巧妙的譬喻。《文心雕龙·才略》讲到冯衍:“敬通雅好辞说,而坎壈盛世;《显志》《自序》亦蚌病成珠矣。”就是说他那两篇文章是“郁结”“发愤”的结果。刘勰淡淡带过,语气不像司马迁那样强烈,而且专说一个人,并未扩大化。“病”的苦痛或烦恼的泛指,不限于司马迁所说“左邱失明”那种肉体上的害病,也兼及“坎廪”之类精神上的受罪,《楚辞 ·九辩》所说:“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北朝有个姓刘的人也认为困苦能够激发才华,一口气用了四个比喻,其中一个恰好和南朝这个姓刘人所用的相同。刘昼《刘子·激通》:“梗柟郁蹙以成缛锦之瘤,蚌蛤结疴而衔明月之珠,鸟激则能翔青云之际,矢惊则能逾白雪之岭,斯皆仍瘁以成明文之珍,因激以致高远之势。”后世像苏轼《答李端叔书》:“木有瘿,石有晕,犀有通,以取妍于人,皆物之病。”无非讲“仍瘁以成明文”,虽不把“蚌蛤衔珠”来比,而“木有瘿”正是“梗柟成瘤”。西洋人谈起文学创作,取譬巧合得很。格里巴尔泽(Franz Grillparzer)说诗好比害病不作声的贝壳动物所产生的珠子;福楼拜以为珠子是牡蛎生病所结成,作者的文笔却是更深沉的痛苦的流露。海涅发问:诗之于人,是否像珠子之于可怜的牡蛎,是使它苦痛的病料。豪斯门(A.E.Housman)说诗是一种分泌,不管是自然的分泌,像松杉的树脂,还是病态的(morbid)分泌,像牡蛎的珠子。看来这个比喻很通行。大家不约而同地采用它,正因为它非常贴切“诗可以怨”“发愤所为作”。可是,《文心雕龙》里那句话似乎历来没有博得应得的欣赏。
司马迁举了一系列“发愤”的著作,有的说理,有的记事,最后把《诗三百篇》笼统都归于“怨”,作为其中一个例子。钟嵘单就诗歌而论,对这个意思加以具体发挥。《诗品·序》里有一节话,我们一向没有好好留心。“嘉会寄诗以亲,离群托诗以怨,至于楚臣去境,汉妾辞宫;或骨横朔野,魂逐飞蓬;或负戈外戍,杀气雄边,塞客衣单,孀闺泪尽;或士有解佩出朝,一去忘反,女有扬蛾入宠,再盼倾国。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日:‘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说也奇怪,这一节差不多是钟嵘同时人江淹那两篇名文——《别赋》和《恨赋》——的提纲。钟嵘不讲“兴”和“观”,虽讲起“群”,而所举压倒多数的事例是“怨”,只有“嘉会”和“入宠”两者无可争辩地属于愉快或欢乐的范围。也许“无可争辩”四个字用得过分了。“扬蛾入宠”很可能有苦恼或“怨”的一面,譬如《全晋文》卷一三九左九嫔《离思赋》就怨恨自己“入紫庐”以后,“骨肉至亲,永长辞兮”,因而“欷欺涕流”;《红楼梦》第十八回里的贾妃不也感叹“今虽富贵,骨肉分离,终无意趣”么?同时,按照当代名剧《王昭君》的主题思想,“汉妾辞宫”绝不是“怨”,少说也算得是“群”,简直就是良缘“嘉会”,欢欢喜喜到胡人那里去“扬蛾入宠”了。但是,看《诗品》里这几句平常话时,似乎用不着那样深刻的眼光,正像在日常社交生活里,看人看物都无须荧光检查式的透视。《序》结尾又举了一连串的范作,除掉失传的篇章和泛指的题材,过半数都可以说是“怨”诗。至于《上品》里对李陵的评语:“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更明白指出了后来所谓“诗必穷而后工”。还有一点不容忽略。同一件东西,司马迁当作死人的防腐溶液,钟嵘却认为是活人的止痛药和安神剂。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只说“舒愤”而著书作诗,目的是避免“姓名磨灭”“文彩不表于后世”,着眼于作品在作者身后起的功用,能使他死而不朽。钟嵘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强调了作品在作者生时起的功用,能使他和艰辛孤寂的生涯妥协相安,换句话说,一个人失意不遇,全靠“诗可以怨”,获得了排遣、慰藉或补偿。大家都熟知弗洛伊德的有名理论:在实际生活里不能满足欲望的人,死了心作退一步想,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替代品的功用,借幻想来过瘾。假如说,弗洛伊德这个理论早在钟嵘的三句话里稍露端倪,那也许不是牵强拉拢,而只是请大家注意他们似曾相识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