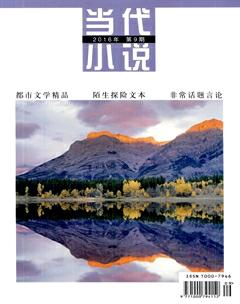人生是一本读不完的书
张丽
狄更斯在《双城记》开篇中写道:那是最美好的时代,那是最糟糕的时代。那时与现在非常相像,随着社会文明的不断发展,我们生活在一个最现代而又最蛮荒的世界。人生就像是一本读不完的书,我们含着泪,一读再读。这个时代充满了疼痛,而文学的存在就是为了揭穿这种伤痛,引起疗救的注意。那些关于时代的、人性的、宿命的东西总能触动心中最柔软的那根弦,且让我们到文学里窥探浮世人生。
曹军庆的《煤球往事》收录于《滇池》2016年第6期,这是一篇极具先锋色彩的短篇小说,文中充满了隐喻和叙事圈套。正如莫迪亚诺《暗夜街》中的主人公一般,作为一个失忆者,“我”的过去一片朦胧。周围的一切对“我”而言都是陌生的,“我”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亦不知晓当初是如何来到此地,更无法确认自己的身份。“我”的记忆就像穿过渔网、筛子、蜂窝等一切带有漏洞的东西,一些被漏掉,另一些被留下。“我”似乎是一个离家出走、失踪、被警方确认已经“死亡”的人,但后来又“活”过来重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并拥有两个名字。“我”究竟是刘一福,还是刘立希?在现代社会飞速发展的重压下,“谁他妈的不想一走了之呢”,现实的焦虑与抑郁使人想要逃离,火车南站以及铁路等意象象征着诗意的远方。惶惑不安的凡人无法找到栖居之地,身份的游离与不确定性尽显世界的荒诞。作者用娴熟的技法描摹普通人变形的日常,触摸人的存在状态与生命体验,在虚无中寻找可能。
2016年第6期《上海文学》刊载了残雪的《与人为邻》,这篇小说延续了作者一贯的先锋姿态,以一只中年雌喜鹊的视角,观察周围各色人等。“人的心思是猜不透的”,作为喜鹊的“我”永远不懂人们心中在想什么,即使安家于高大的杨树上,“我”也是终日忐忑不安,担心遭受人的射击或巢被捣毁。学校的小花园是我们觅食的场所,50余岁的女校工和善的外表下潜藏着阴谋,因为这名校工,“我”的同胞开始离奇失踪。父亲、母亲、“我”的邻居和孩子们先后不见,最后只剩“我”和妻子胆战心惊地过活。而住在学校附近瓦屋中的人更是奇怪,他们在家里争吵打闹,一出门却又变得极其安静、沉默、犹豫,半夜发生火灾时甚至无一人逃离住所。望着那些冲天的鬼火,“我”居然想流泪。大火熄灭后,校工再次出现,在洞里栽种白骨,故事至此戛然而止,留给读者想象的空间。残雪的思维跳跃性极强,小说呈现出碎片化、断裂化倾向,布满阴森、诡异、恐惧的气氛。
陈希我的《摇篮与坟头》发表于《福建文学》2016年第6期,作者一如既往地采用一种极端化的叙述方式,描述诸神退隐后的社会与人生。“我”是万千精子中最强壮的一个,在爸爸的一次情感发泄中来到妈妈体内,成为孕育在子宫内的新生命。尽管国家已经全面放开二胎,但随着养育子女所需费用的日益增高以及生存环境的日益恶化,已有一个骄纵刁蛮女儿的爸爸妈妈丝毫不顾及“我”的感受,千方百计地阻止“我”来到这个世界。然而,在外公、外婆和奶奶的劝阻等诸多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我”终于平安地呱呱坠地,在母胎中被迫看到世间丑陋的“我”并未像其他婴孩般大哭大闹,只有种“摇篮”即“坟头”的冰冷触感……当代人终日生活于垃圾场中,他们的灵性也被垃圾所污染,常假借“善”的名义去做一些卑劣的勾当,比如扼杀无辜的生命。生命,是关系到民族与人类存亡的大事,它隐藏着“造化永恒的秘密”,陈希我以“生还是不生”为线索,将人物内心的情感世界展现得淋漓尽致。
李浩的《会飞的父亲》刊载于《广西文学》2016年第6期,这是他以此为题创作的第三篇小说。“我”的父亲是一位善于奔跑、跳跃的体育老师,却因一次本可以躲避开来的车祸再无站起来的机会,只能在轮椅上度过余生。父亲是一个骄傲的人,他无法接受这样惨痛的事实,出于羞愧、耻辱、自尊等一系列复杂心理,像一座孤岛般将自己囚禁在卧室发呆,不愿与人打交道。在除夕这一天,父亲终于打开那座无形的栅栏,从卧室到客厅观看他最爱的体育频道节目。当父亲看到滑翔的节目时,他忘记了胃痛、绝望与不安,与飞翔者融为一体。他想飞跃这庸俗的日常,从日常中出走是他心中积蓄已久的渴望,就算不能实现,能有那种姿态也是好的。李浩拥有高度的叙事自觉,在他的笔下,故事总是呈现出无数种可能,诉说无可名状的孤独与生命的奥秘。
2016年第3期《大家》收录了李昕的《废墟》,废墟之下,安有完卵?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是一位摄影师,她总是一个人在夜间的马路上游荡,拍摄夜空下的灯与尘。她的世界除了自己再无别人,父母离开人世后,她依旧住在残存父母气息的旧房子中,只有在这里,她才能感受到安全与温暖。与她的住宅相平行的也是一栋旧房,它是阻断世间一切恶意的栅栏,承载着所有美好的记忆。“世界简直就像一个强拆队,不断地在拆毁着她所珍爱的每一样东西。”她把房子作为掩护自己不被世界一览无遗的幕布,当旧宅被拆成一座废墟时,她内心的最后一道防线也随之崩溃,无奈之下选择在一片火光中结束一切。作为80后作家,李昕的小说带有一种青春文学的孤独与感伤、痛苦与绝望,但又不仅仅拘泥于这些情感。小说中的废墟隐喻着死亡,结尾时的大火代表懦弱的主人公对某种强大力量的渴望,其自我毁灭是对世界的无言反抗。
《海燕》2016年第6期刊载了寒郁的《缤纷》,讲述两个孤独灵魂于异乡漂泊、不知归处的故事。在时代的挤压下,西北汉子郑凡失去了手中最珍重的“底牌”——陪伴他三年的女友,而后在广场偶遇文化公司美编丛美云,并展开一段新的爱欲纠葛。郑凡起初只是为了与丛美云发生关系才追求她,得到她的身体后又想索取对方的心。丛美云也不过是俗世芸芸众生中的一员,她想留在大城市,即使付出与猥琐“别墅男”结合的代价也在所不惜。当丛美云与“别墅男”闹掰后,旋即找到郑凡并与他在一起。可是,这两颗看似找到依靠的心灵却依旧不安,郑凡还保存着前女友的戒指,他想把戒指戴在美云手上,又担心“套不住”;美云手机里存着“别墅男”愿意重修旧好以及朋友帮忙联系新工作的短信,尽管她不知何去何从,但一定不会因郑凡而停留。他们都是生活于大时代的小人物,残忍的世相让爱这个字眼变得太过沉重,生存的碾压使人不堪重负,作者浓墨重彩地呈现出无处不在的孤独、寂寞与虚无,引发读者的深思。
尤凤伟的小说《选举日》发表于《中国作家》2016年第6期,这是一个关于发生在社区选举日艰难维权的故事。一次突发性肠炎后,老钟在社区公园附近的药店买了应急药,服用数片后没有丝毫起色,反而愈加严重。经老伴儿提醒后方知买了假药,病好之后义愤填膺地到药店找“四眼娘儿们”算账,但药店老板不仅不承认错误反而态度恶劣,诘问老钟没发票还维什么权。当老钟的牌友也来支援老钟,向店主讨要说法时,她竟然向警局熟人报警谎称有人寻衅闹事,一行人被带往派出所问话。僵局的打破来自于居委会梁主任的一通电话,在社区换届选举之日,她若想连任必须获取老钟等人的支持,警局这才将人放走。尤凤伟在小说中针砭时弊,平实的语言下暗含着对社会的嘲讽,日常生活中总是有那么多荒谬又让人无力的事情。作者针对当下造假卖假、警察的不作为以及选举中贿赂选民等情况作文,极富思想深度与现实穿透力。
2016年第6期《湖南文学》收录了少鸿的《最后的交谊舞》,这是一篇很有吸引力的小说,故事开头就写道“江英杰被人打脸了”,进而不断地诱惑读者阅读下去。江英杰在梦巴黎舞厅偶遇冒小雨,被她那曼妙的舞姿所吸引,他最大的愿望就是能与她共舞一曲,享受一次高超舞艺的美妙。在与她接触的过程中,作者又开辟出另一条线索:冒小雨的父亲是一位会计,他是第一个将交谊舞带入莲城的人,因为跳交际舞在文革中受到批判;之后又在严打中被诬陷强奸某个女子,不堪其辱的冒会计只能选择自杀。在江英杰的努力下,他终于得到了与冒小雨跳舞的机会,中场休息时却因为提到冒会计不欢而散,而她欠下的半场舞则成为一个永远无法实现的诺言——冒小雨在一场医疗事故中殒命。交谊舞其实代表着一种不愿服老的心态,一种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而冒会计和女儿却先后因交谊舞失去生命,使小说充满了荒诞色彩与讽刺意味。
《中国铁路文艺》2016年第6期发表了原昌的短篇小说《想不明白的案情》,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些事情是善良的人想不到的。周振飞是皮鞋厂的一名工人,他善良、心软、乐于助人,总是在人最困难的时候伸出援手,他的妻子边素云正是因为相中了这个人才嫁给他。可是好人也会走霉运,当下夜班后的周振飞将向他求助的年轻女子送回家时,却被那位女子及其丈夫联手勒索。无奈之下的周氏夫妇将计就计,把钱送给他们后,边素云同他们一起上车,谎称自己的钱丢了,公车司机遂将车开往附近派出所。恶人虽被绳之以法,但故事却让我们有些哭笑不得,即使最后剧情出现反转,却依旧让人怅然若失。原昌的文笔似乎总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吸引读者不断读下去,他们在阅读中思考,体悟百味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