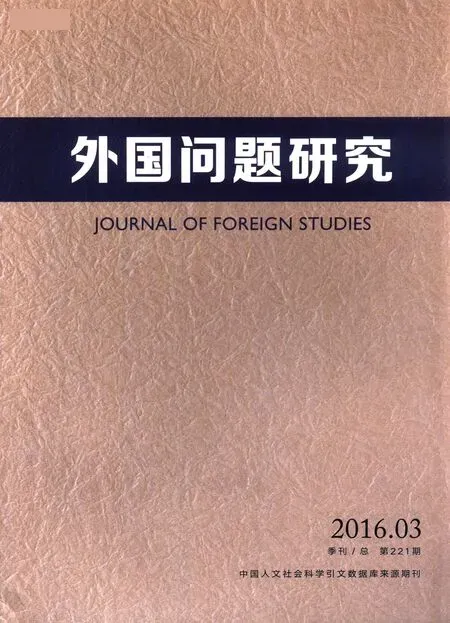沙特的瓦哈比主义:温和抑或极端?
——基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历史解读
马 洁 光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沙特的瓦哈比主义:温和抑或极端?
——基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历史解读
马 洁 光
(南开大学 历史学院,天津 300350)
瓦哈比主义作为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官方意识形态,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宗教理论和政治理论。从伊本·瓦哈卜创立瓦哈比派至今,宗教理论的兼容性、政治理论的去极端化,教俗合一宗教政治体制的完善,构成了沙特官方瓦哈比主义的基本特征。结合官方瓦哈比主义在沙特国家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可见官方瓦哈比主义适应于沙特的现代化道路,是温和的、进步的宗教政治意识形态。
“一带一路”;沙特阿拉伯;瓦哈比主义;伊本·瓦哈卜
沙特阿拉伯王国作为中东大国,是我国“一带一路”战略中不可忽视的一环。习主席访问沙特期间,双方签署了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双方强调坚决反对威胁世界和平稳定的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愿在该领域加强安全合作,反对将恐怖主义与任何宗教或教派挂钩。*详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沙特阿拉伯王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http://www.fmprc.gov.cn/web/zyxw/t1333110.shtml.自“9·11”事件之后,瓦哈比主义成为了国际学术界研究的热点问题,对于瓦哈比主义的特点,学者们众说纷纭。*关于瓦哈比主义的重要著作包括:大卫· 康明斯的《瓦哈比主义的使命和沙特阿拉伯》、曼苏尔·贾希姆·沙米希的《沙特阿拉伯的伊斯兰教和政治改革:政治变动和改革的探索》等,瓦哈比主义与沙特国家体制之间的关系是研究的重点。对于瓦哈比主义的特征及其发展趋势的评价,国际学界由于研究角度和评价标准不同,形成了截然相反了两种看法。一种观点基于对瓦哈比主义在王国的建立过程以及稳定国家局势方面的作用给予了肯定的评价,穆罕默德·安尤布和哈桑·柯西巴拉坂编著的《沙特阿拉伯的宗教和政治—瓦哈比主义和国家》、艾曼·雅辛的《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宗教和国家》是这类观点的主要代表。一些学者对沙特现代化进程中的瓦哈比因素持否定态度,他们认为瓦哈比主义与现代化并不相容。马克· A. 考迪尔的《王国的暮年:对沙特的理解》、约翰· R· 布兰德利的《揭露沙特阿拉伯:王国内部的危机》、内夫扎特·苏库克的《原教旨主义下的全球主义和伊斯兰主义》是这类观点的主要代表。国内对瓦哈比主义研究的相关文章有:张志华的《瓦哈比派运动的始末及其影响》、李振中的《瓦哈卜一神教派运动—阿拉伯伊斯兰近代哲学思想》、希文的《“回归传统”的瓦哈比主义》和吴彦的《沙特阿拉伯宗教政治初探》。值得注意的是,学界对于瓦哈比主义理论奠基者伊本·瓦哈卜的思想研究方面尚显薄弱。*关于伊本·瓦哈卜思想的主要著作有:扎马鲁丁·穆泽尔波兹的《穆罕默德·伊本·瓦哈卜的生平、教导和影响》,该书引用了大量可靠的阿语史料,对伊本·瓦哈卜进行了细致的研究。阿卜杜勒·萨利赫·奥赛敏的《穆罕默德·伊本·瓦哈卜其人和他的作品》,该书从伊本·瓦哈卜的宗教思想中寻找有关政治方面的论述,并且从政治学的角度给予解释。艾布·艾米纳·比俩里·菲利普斯的《伊斯兰教唯一神轮的基础》从宗教学角度阐释了伊本·瓦哈卜的陶希德思想,详细的论证了伊本·瓦哈卜陶希德思想的宗教合法性,是瓦哈比派内部对伊本·瓦哈卜思想的一种解释。中国学者仅有马福德《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先驱——瓦哈卜及其思想研究》一书,对伊本·瓦哈卜思想生平及思想进行了专门阐释。此外,郭兰茜和王戎的《瓦哈卜思想的产生与影响》、李维建的《思想的继承与创新—瓦哈比派和赛莱菲耶派的早期理论家》对伊本·瓦哈卜的思想持肯定的态度。许多学者对早期瓦哈比主义的认识不清,对瓦哈比主义有一定的误解。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之下,基于对沙特的社会环境和政治生态认识的需要,亟待对沙特的瓦哈比主义进行时代解读。本文拟以瓦哈比主义形成的伊本·瓦哈卜时代作为研究起点,梳理瓦哈比主义宗教理论和政治理论形成及演变的过程,进而探讨沙特阿拉伯官方瓦哈比主义的特征及发展趋势,并对瓦哈比主义认识的一些误解进行澄清。
一、苏非派和教法学派:瓦哈比主义宗教理论的兼容性
一直以来,瓦哈比主义被冠以严厉批判苏非主义的名声,瓦哈比派与苏非派貌似水火不容、势不两立。有学者提出:“在瓦哈比派看来,苏非主义是敌对思想,因为瓦哈比派对于任何形式崇拜先知的行为都是最为谨慎的,他们只从字面意思去理解问题。”*John R. Bradley, Saudi Arabia Exposed Inside a Kingdom in Crisi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5, p.8.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伊本·瓦哈卜从来没有公开的攻击过苏非主义,其子甚至声称伊本·瓦哈卜并不反对苏非主义。*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p.79.

伊本·瓦哈卜深谙传统苏非主义的诸多理论和实践,在不反对苏非主义合理性的基础之上,伊本·瓦哈卜对苏非主义诸多理论进行了再解读。首先,伊本·瓦哈卜反对圣墓崇拜的思想,很大程度上是受其导师穆罕默德·哈雅·信德的影响。在伊本·瓦哈卜时代,人们将先知穆罕默德以及圣门弟子,还有著名的苏非大师的坟墓统称为圣墓。有相当数量的半岛穆斯林将圣墓崇拜视为宗教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伊本·瓦哈卜在纳季德就目睹过人们对一些圣墓的崇拜行为。据说伊本·瓦哈卜在麦地那学习期间,他在先知穆罕默德的墓前看到一伙人在寻求圣人的庇佑和帮助,恰好穆罕默德·哈雅·信德经过,他问穆罕默德·哈雅·信德这些人的行为会产生怎么样的作用。信德的回答是:“他们的行为应该被禁止,这样做对他们没有丝毫好处。”*Abd Allah Salih Al-Uthaymin, Muhammad Ibn Abdul-Wahhaab: The Man and his Works, London: I.B. Tauris& Co. Ltd., 2009, p.34.这引起了伊本·瓦哈卜对于圣墓崇拜行为的再思考。
其次,从“安拉的卧里”到“撒旦的卧里”,是瓦哈比主义对苏非主义“卧里”概念的再认识。“卧里”,原意为“任命”、“委任”,引申意为“被任命的人”。在苏非主义的语境里,特指那些苏非教团的创始者和修为较高的苏非大师。苏非教团的首领对于普通成员拥有绝对的权威,教团的创始人则往往被后来者视作圣贤并加以尊崇。*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02页。由于苏非主义在奥斯曼苏丹的支持下日渐兴盛,一系列针对“卧里”的崇拜行为逐渐盛行。人们给“卧里”修造奢华的陵墓,并且虔诚的在“圣墓”周围举行纪念活动,甚至有个别的教团常以朝拜圣墓取代朝觐克尔白。*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第302页。伊本·瓦哈卜对卧里崇拜带来的宗教生活中的迷信深恶痛绝。但是伊本·瓦哈卜并没有攻击任何苏非派的卧里,而是对“卧里”的理解与众不同。在瓦哈比主义者看来,一个真正的卧里并不是以飘逸的长袍、宽大的袖筒和念珠为标志,而是在于他心中的虔诚。一个真正的卧里是严格履行宗教义务并且真心实意的遵循《古兰经》和圣训教导的人。*Abd Allah Salih Al-Uthaymin, Muhammad Ibn Abdul-Wahhaab: The Man and his Works, p.125.
最后,伊本·瓦哈卜在对卧里概念创新阐释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构了传统苏非主义说情权思想的历史内涵。伊本·瓦哈卜秉持“回归经训”的态度,在说情权问题的理解上可谓有理有据。如其所言:“如果一个人问道,你会拒绝承认安拉的使者有说情权并与之撇清关系吗?告诉他,我不拒绝更不会与之决裂。事实上,他(安拉的使者)是说情者,他的说情是被安拉接受的。我希望得到他的说情。”*Jamaal Al-Din M. Zarabozo, The Life, Teachings and Influence of Muhammad ibn Abdul-Wahhaab, Riyadh:The Ministry of Islamic Affairs, Endowments, Dawah and Guidance of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2010, p.257.他进一步指出:“对于一个穆斯林来说最大的权力也不能高于穆圣。一个人对信仰的誓词证明他承认了穆罕默德是安拉封印的使者,你该知道如果将任何一位圣贤与圣人的地位相提并论,那么你就会成为一名不信道者。”*Jamaal Al-Din M. Zarabozo, The Life, Teachings and Influence of Muhammad ibn Abdul-Wahhaab, p.226.值得注意的是,伊本·瓦哈卜强调先知穆罕默德不能因为自己的喜好而引导那些不被安拉所喜悦的人,也不能给多神教徒求情。*Ayman Al-Yassini, Religion and State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Boulder:Westview Press, Inc., 1985, p.27.瓦哈比主义兼容了苏非改良主义的诸多理论,撼动了传统苏非派对苏非主义的一般阐释。
在教法学的理解方面,传统的教法学派反对伊智提哈德原则。*伊智提哈德,阿拉伯语原意为“努力”,引申为“创制”。特指依据《古兰经》、圣训的总精神,运用理智,通过推理、比较、判断等方法,对新的历史条件下出现的新情况、新事物以及特殊情况等,推演出与整个教法宗旨并行不悖的法律结论与条规的整个思维过程。包括对《古兰经》、圣训选择、释义、应用,直至形成新的判例。引自: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编委会:《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第114页。逊尼派伊斯兰世界在公元10世纪左右已经形成了哈乃斐派、沙斐仪派、马立克派和罕百里派这四大教法学派,教法体系已经日趋完善。在1258年,巴格达陷落伊斯兰世界陷入了动荡不安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教法学家认为继续进行教法演绎容易被异教徒利用,故而他们一致同意放弃教法演绎*Bruce Masters, The Arabs of the Ottoman Empire, 1516—1918, p.124.教法学家们由此提出了一个教法学原则——泰格利德(taqlid),*泰格利德,阿拉伯语音译,意为“仿效”、“音讯”。作为一种教法学概念,它认为创制教法学的阶段已经结束,后世教法学家的任务仅仅是因袭和遵循前人的法律学说和法学理论,不得“标新立异”,创制新的教法律例。由此产生了所谓“创制之门关闭”说。引自:《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第548页。凡遵奉此学说的法学家皆称为“穆盖利德”(即遵循者)。伊本·瓦哈卜时代,纳季德宗教学者恪守罕百里派教法学传统,能够阅读并且理解罕百里教法学派著作的人,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被冠以谢赫或者阿林(学者)的称号,并且有机会成为卡迪。*Abd Allah Salih Al-Uthaymin, Muhammad Ibn Abdul-Wahhaab: The Man and his Works, p.22.可以说,阿拉伯半岛的教法学家对于教法的理解是僵硬保守的,所谓的教法学知识无非是背记前人的说法,在教条主义风气的影响下他们极少思考教法判决的原则。正如伊本·瓦哈卜忧虑的那样,逊尼派教法学的发展使很多人盲目跟从各个教法学派的不同判断和推理,这就导致了穆斯林社会的分裂。他最为鲜明的立场是对教法学派教法判断的质疑,其中包括对当时罕百里教法学派的质疑。对于伊本·瓦哈卜来说,他更担忧教法学与《古兰经》和圣训之间的冲突,以及伊智提哈德和泰格利德之间的矛盾。*Madawi al-Rasheed and Robert Vitalis, Counter-Narratives: History, Contemporary Society and Politics in Saudi Arabia and Yemen, London: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90.
瓦哈比派在教法学理解方面具有明显兼容各教法学派理论的倾向。第一,瓦哈比主义在教法学方面坚持“回归经训”的基本原则。处于对各自教法学派理论的恪守,所谓的穆盖利德并不赞同教法学方面的“回归经训”的主张。正如伊本·瓦哈卜所描述的:“那些反对我的教法学家令人惊奇的是——当我向他们阐明《古兰经》和经注学家的解释时,他们回复我说:‘像我和你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按照《古兰经》和圣训或者早期学者的要求行事的。我们不能违背古典时代那些伟大教法学家的理论。’”*Jamaal Al-Din M. Zarabozo, The Life, Teachings and Influence of Muhammad ibn Abdul-Wahhaab, p.119.对于这种看法,伊本·瓦哈卜引用圣训给予了有力的回击:(1)据阿布·德拉达传述,我们在和圣人同行时,他仰望着天空然后说起了一件事:“那将是一个知识泯灭的时代。”宰德·伊本·拉比德·安萨尔问道:“如果我们背诵《古兰经》并且将它传授给我们的孩子,然后他们将它再传授给他们的孩子直到末日审判之时,那么知识怎么会泯灭呢?”圣人回答说:“宰德啊,你让我感到很惊讶,我认为你是麦地那最有学识的人。那些犹太人和基督徒不按照《讨拉特》和《引支勒》的教诲去做难道是因为他们看不懂那些经文的内容吗?”(2)阿卜杜勒·伊本·欧麦尔说道:当犹太人开始心存期待时,他们的心开始生锈。他们自己编造了自以为合适的经典。真理在他们中间因为各自的私欲变成了争论的焦点。最终他们忽略了安拉的启示。*Muhammed Bin Abdul Wahhab, The Excellent Qualities of the Holy Quran, Trans.by Muhammed Iqbal Siddique, Riyadh:The Ministry of I Slamic Affairs, Endowments, Dawah and Guidance of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 2010, pp.5-7.
第二,瓦哈比主义坚持教法学判断上的伊智提哈德,秉持跨教派原则的瓦哈比派学者认为《古兰经》和圣训是穆斯林判断合法与非法的准绳,如果四大教法学派的法学判决背离了《古兰经》和圣训,那么必须拒绝它们的判断。*Ayman. Al-Yassini, Religion and State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p.29.18世纪纳季德的教法学家不重视教法学原理的研究和思考,伊本·瓦哈卜则博采众长反驳墨守成规的教法学家。正如他所说:“我和哈乃斐派的人辩论时会引用哈乃斐派学者的观点,和马利克、沙菲仪和罕百里派的学者都是如此。我和他们辩论时都会引用他们学派中著名学者的著作来作为依据。”*Michael Cook, “On the Origins of Wahhābism,”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 Ireland , vol. 2, 1992, p.199.可见,瓦哈比运动绝非罕百里派的内部改良运动。瓦哈比派的教法学主张兼容并蓄提倡打破教派壁垒。伊本·瓦哈卜虽以伊本·罕百里的追随者自居,但是其子阿卜杜勒宣称:“我们并不提倡完全的伊智提哈德,通常情况下我们是跟随罕百里教法学派的。但是如果关于某个教法问题的判定上,其他教法学派遵循了《古兰经》或圣训的明文规定,那么我们就会放弃之前罕百里教法学派关于这一教法问题的观点,转而遵循其他教法学派的判断。”*Jamaal Al-Din M. Zarabozo, The Life, Teachings and Influence of Muhammad ibn Abdul-Wahhaab, p.106.
二、从暴力到非暴力:瓦哈比主义政治理论的去极端化
吉哈德思想是伊斯兰教传统的政治主张,“吉哈德”,阿拉伯语,原意为“奋斗”、“努力”,引申意为圣战。在伊斯兰教的信仰体系中,吉哈德思想包含广义的“为主道奋斗”和狭义的“圣战”两个层次。先知穆罕默德时代的圣战思想有特定的历史内涵:其一,传统社会的血族仇杀往往表现为世俗的暴力行为,而穆斯林的战争却被伊斯兰教赋予神圣的色彩;其二,穆斯林的圣战源于信仰的差异和宗教的对抗,体现文明与野蛮的尖锐矛盾;其三,穆斯林的圣战并非个人的随意行为,而是温麦的国家行为。*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2010年,第88页。在古典伊斯兰时代,圣战的对象被明确规定为对异教徒的征伐。
早期的瓦哈比派对吉哈德的理解经历了从温和的“为主道奋斗”到武力圣战的过程。伊本·瓦哈卜在胡赖米拉、阿伊纳生活期间都是以著书立说、演讲辩论的温和方式进行传教。甚至在德拉伊耶传教的初期都没有把吉哈德和圣战相提并论。正如瓦哈比派历史学家伊本·安纳尔记载的那样:伊本·瓦哈卜坚持用明确的证据和优雅的方式传播安拉的中正之道。他没有首先判定任何人是不信道者,他也没有迫害任何人。相反他生怕自己的行为不够虔诚,希望安拉指引那些反对者走出迷误。然而那些反对者以怨报德。他们宣称伊本·瓦哈卜和他的追随者是叛教者,甚至杀死瓦哈比主义者。这些反对者坚决不以《古兰经》和圣训作为依据,他们声称自己的行为是为了反抗伊本·瓦哈卜,故而他们认为迫害瓦哈比主义者是合法的。他们大肆惩罚和流放治下的瓦哈比主义者。在这些敌人杀戮瓦哈比派信徒之前,伊本·瓦哈卜并不允许他的追随者杀戮或者武力抵抗那些迷误的人。直到1746年,利雅得的埃米尔攻击了德拉伊耶的盟邦穆富哈,在这种情况下,伊本·瓦哈卜首次将吉哈德和圣战相提并论。伊本·瓦哈卜令其追随者在沙特家族的带领下发动反击。*Jamaal Al-Din M. Zarabozo,The Life, Teachings and Influence of Muhammad ibn Abdul-Wahhaab, p.41.
有学者批评道:“他(伊本·瓦哈卜)利用武力手段背叛了他斥责为叛教者的穆斯林群体,这就等于违背了伊本·泰米叶的教导。与其说他是伊本·泰米叶的追随者,不如说他的行为更多的体现了贝都因人好战的传统。”*Fazlur Rahman, Revival and Reform in Islam—A Study of Islamic Fundamentalism, London:Oneworld Publications,1999, pp.160-161.自伊本·瓦哈卜和伊本·沙特结盟之后,德拉伊耶的埃米尔从瓦哈比主义中找到了使自己取得优势的思想武器。伊本·沙特从一个劫掠邻居的首领一跃成为了为“纯洁信仰”奋斗的战士。而他的敌人则成为了“魔鬼的奴隶”、“偶像崇拜者”和“多神崇拜者”。用圣战反对“多神教徒”成为了最重要的责任。瓦哈比主义成为了军事征伐和突袭劫掠的意识形态。*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New York: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 p.78.伊本·瓦哈卜对圣战的理解极具政治意义和现实意义,借助宗教的神圣外衣,瓦哈比派在纳季德的征服可谓师出有名。伊本·瓦哈卜时代对吉哈德思想的解读与国家秩序的建立之间存在逻辑联系,内忧外患的政治生态决定了瓦哈比派对吉哈德思想理解的暴力性和极端性。
在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建立过程中,吉哈德思想的极端性和暴力性被推向了另一个高潮。20世纪初,沙特家族与瓦哈卜家族再次联手,在半岛提出了复兴瓦哈比主义的又一场宗教政治运动——伊赫瓦尼运动。吉哈德思想给伊赫瓦尼运动提供了理论和合法性依据,同时瓦哈比派乌莱玛将伊赫瓦尼运动的薪火传播到了贝都因人部落中。伊赫瓦尼运动通过游牧部落的定居与圣战相结合,形成一种强大的宗教政治力量。瓦哈比派伊斯兰教和伊赫瓦尼运动对顺从安拉和伊玛目以及严格恪守宗教功修的强调,成为阿卜杜勒·阿齐兹驾驭贝都因部落和控制民众进而强化国家权力的重要工具。阿卜杜勒·阿齐兹和欧莱玛希望利用瓦哈比派伊斯兰教恪守宗教戒律的特点,来约束贝都因人的自由散漫和叛服无常。*吴彦:《沙特阿拉伯政治现代化进程研究》,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0页。伊赫瓦尼战士崇尚圣战,追随伊本·沙特,自1918年起成为沙特家族对外征服的核心军事力量。瓦哈比派宗教思想的传播无疑导致狂热的宗教情感和激进的宗教实践,战利品则是伊赫瓦尼获取财富的主要途径。伊赫瓦尼运动的兴起,改变了纳季德与拉希德人以及希贾兹之间军事力量的对比。沙特家族、瓦哈比派与伊赫瓦尼的三位一体,构成伊本·沙特角逐权力和拓展疆域的有力工具。*哈全安:《中东史:610—2000》,第762页。
在完成了对阿拉伯半岛的征服之后,伊赫瓦尼运动终被沙特家族打压,吉哈德思想的极端性和暴力性原则亦不再合时宜。近几十年来,沙特王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以便将重新定义的瓦哈比主义树立为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并使之成为沙特国家认同的一个重要属性。所谓的重新定义则是指把吉哈德思想中过于激进的军事属性做出相应的调整。*Joseph Nevo, “Relig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Saudi Arabia,” Middle Eastern Studies, vol. 34:3 (Jul. 1998), p.41.沙特官方在重释吉哈德思想时着重强调广义的“为主道奋斗”,即宣教和工作被视为吉哈德。比如,沙特的宗教学者在评价谢赫·伊本·巴兹时说道:“伊本·巴兹并没有虚度他九十年的光阴,他将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了吉哈德——传播伊斯兰教,他耐心的倾听人们的诉求,对别人的麻烦和困扰感同身受。”*Mansoor Jassem Alshamsi, Islam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Saudi Arabia: The Quest for Political Change and Reform, London: Routledge, 2010, p.57.沙特政府投入大量的资金进行伊斯兰教的宣教工作,并且在宗教教育和舆论宣传方面宣扬宽容。瓦哈比主义对吉哈德思想的认知经历了从宣扬圣战到提倡宣教的变化,符合沙特国家形成过程中各阶段的实际需要,也是瓦哈比主义对吉哈德思想的时代解读。
三、从教俗合作到教俗合一:瓦哈比主义宗教政治体制的演进
教俗合作权力观的形成,表现为对瓦哈比派宗教学者的尊崇和教权的膨胀。伊本·瓦哈卜时代的权力观包含服从宗教学者和服从世俗统治者的双重倾向。1758年,伊本·瓦哈卜的追随者在朱拜拉打败了哈立德部落及其盟军的进攻,这场战役极大地鼓舞了瓦哈比战士的士气。很多部落因此向德拉伊耶求和称臣,德拉伊耶成为了一个新的政治中心,控制了汗尔吉、泽尔米达、乌沙吉尔、苏代尔和其他一些贝都因部落。*Jamaal Al-Din M. Zarabozo, The Life, Teachings and Influence of Muhammad ibn Abdul-Wahhaab ,p.46.在这种情况下,伊本·瓦哈卜提倡宗教学者应该积极的参与到政治生活中去,他援引伊本·泰米叶的思想提出一种特殊的手段以限制世俗统治者——权力的共享与合作,即紧密宗教学者和世俗统治者之间的合作关系。在解释《古兰经》关于服从安拉、先知和埃米尔的原则时,伊本·瓦哈卜宣称这里提到的埃米尔指两种:宗教学者和世俗统治者。如果他们能听民言,人们就服从他们。如果他们是腐败的,民众就应推翻他们。*Frank E. Voge,Islamic Law And Legal System: Studies of Saudi Arabia,p.203.教俗合作的权力观,在德拉伊耶埃米尔国家建立之后逐渐形成。伊本·瓦哈卜强调:“为了国家的统一和团结,就必须服从有能力的领袖。”*Mohammed Ayoob Hasan Kosebalaban,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Saudi Arabia——Wahhabism and the State, p.28.他认为服从领袖是一种义务,即使世俗统治者是一个残暴者。在宗教学者的帮助和监督之下,只要世俗统治者的命令不违背信仰原则,就必须服从世俗统治者的命令。伊本·瓦哈卜要求信众对残暴的世俗统治者要忍耐,谴责用武力手段进行反叛。他也警告统治者要公正,尽管大部分世俗统治者难以做到公正严明。伊本·瓦哈卜认为维持统治必须要依据沙利亚,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世俗统治者则必须和宗教学者合作。*Ayman Al-Yassini, Religion and State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1985, p.30.与伊本·沙特合作时期,瓦哈比主义者对教俗两界领袖的服从可谓并驾齐驱。甚至有迹象表明瓦哈比主义者虽服从伊本·沙特的命令,但伊本·瓦哈卜得到了瓦哈比派信徒更多的尊崇。
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历史的早期,教权的膨胀一度达到了顶峰。在瓦哈卜家族的领袖——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阿卜杜·拉提夫的提议之下,1903年在利雅得建立了沙特历史上第一个劝善戒恶公会。该公会被赋予权力可以逮捕、审判和监禁那些违背瓦哈比派信条的有罪之人。*Ayman Al-Yassini,Religion and State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p.68.在20世纪20年代,阿卜杜勒·阿齐兹借助劝善戒恶公会的力量从伊赫瓦尼手中夺得了维持地区稳定的治安权力和宗教裁判权。此时的劝善戒恶公会是一个半司法性的机构,由瓦哈卜家族成员管理。全国各地大小分会有2000多个。分会的人数5至30人不等,其中有政府官员、宗教学者、知名人士和虔诚的教徒。它既可以命令地方警察,也可以在地方警察的协助下,强制公众遵守伊斯兰教各项要求,服从瓦哈比派的训诫,如通知和监督居民按时祈祷、守斋,取缔宗教活动中的异端表现,禁止饮酒、跳舞、祛除“有罪的偏见”和异端信仰,以及对犯戒者做出处理等。他们的权力范围极大,男人留长发者要被他们剪短,女子穿短裙者要被他们抽打腿部。*北京大学亚非研究所西亚研究室编著:《石油王国沙特阿拉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144页。
教界权力的膨胀日益危及沙特家族的政治影响力,沙特家族的执政合法性一度受到挑战。一直以来,沙特王室认为其家族权力来源于1744年伊本·瓦哈卜与伊本·沙特的联盟。瓦哈比主义不仅是沙特王室权力合法性的主要依据,也是凝聚部落力量的原因。国王不仅是半岛的世俗统治者,而且是瓦哈比派的伊玛目和部落联盟的最高领袖。*Joseph Nevo,“Relig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Saudi Arabia,” pp.34-53.但是,有激进的瓦哈比主义者认为:“所谓伊本·瓦哈卜与伊本·沙特之间的结盟之说并不准确。伊本·瓦哈卜只不过得到了一个无关紧要人物的效忠,而他是阿拉伯半岛中部一个默默无闻的小镇——德拉伊耶的首领(伊本·沙特)。”*Roel M, Global Salafism:Islam’s New Religious Movement,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09, p.309.这种说法从宗教角度否定了沙特家族权力的合法性来源,引起了沙特家族的警觉。宗教学者支持下的穆陶威以瓦哈比主义的维护者自居,认为其教权是世俗统治者都不能侵犯的,逐渐的穆陶威开始骄横跋扈甚至公然反对阿卜杜勒·阿齐兹的一些政策。*Ayman Al-Yassini,Religion and State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p.69.
面对如此处境,沙特家族采取一系列措施成功赢得了舆论的支持并及时削弱了教界的权力。沙特家族宣称以伊本·瓦哈卜的思想为宗教生活的指导,并且以伊斯兰教中的正统派的捍卫者自居。沙特国王既是国家的最高世俗统治者又是瓦哈比派的伊玛目。在沙特的官方学者的解释和宣传之下,这样一个理论被民众所接受:伊本·瓦哈卜的宗教政治思想是支持君主专制的,而且君主专制得到了《古兰经》和圣训的支持。*Mansoor Jassem Alshamsi, Islam and Political Reform in Saudi Arabia: The Quest for Political Change and Reform, p.220.阿卜杜勒·阿齐兹在1930年签署了一个王室法令,将劝善戒恶公会并入警察总指挥部的管辖之下。他剥夺了穆陶威一直以来享有的逮捕权,并且限制了他们的权力范围。为了防止公会的领导和警察的领导发生争论,该法令中规定国王是双方的仲裁人。*Ayman Al-Yassini,Religion and State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p.70.20世纪30年代,阿卜杜勒·阿齐兹下令,任命15位乌莱玛领袖成立一个宗教研究理事会。然而15位理事中只有一位来自瓦哈卜家族,这也可以看作是沙特家族不允许任何团体拥有比王室家族更广泛权力的政策体现。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瓦哈卜家族在宗教机构中的代表人数和影响力都在下降。*Ayman Al-Yassini,Religion and State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p.71.
司法权力由一元到多元,体现了教俗权力斗争中力量的此消彼长。现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形成过程中,教界曾长期掌握了王国的司法权力。在建国之初,沙特家族主张在希贾兹地区继续执行奥斯曼法,然而他的这种政策受到了激进的伊赫瓦尼战士的强烈反对,在他们看来奥斯曼法与沙利亚是对立的。为此阿卜杜勒·阿齐兹征求瓦哈比派宗教学者的意见,希望从乌莱玛那里得到支持。1927年2月11日,瓦哈比派乌莱玛发布了一个法特瓦支持伊赫瓦尼的观点。乌莱玛们一致认为如果在希贾兹还有任何奥斯曼法的残留则应该被立刻废除,纯正的沙利亚应该被遵循。*Ayman Al-Yassini,Religion and State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p.74.此后,教界曾长期独霸司法权力。随着沙特阿拉伯王国现代化进程的发展,尤其是沙特石油时代的到来,使得王国的经济社会发生了巨大变动。司法机构面临更多对外经贸方面的法律纷争,许多案例的判决已经超出了宗教法官的能力。在这种情况下,申诉委员会于1955年由沙特王室下令成立,沙特国王拥有申诉委员会的最高决策权。*Ayman Al-Yassini,Religion and State in the Kingdom of Saudi Arabia, p.77.申诉委员会分割了沙利亚法庭的部分权力,该委员会有权裁决刑事纠纷和商业纠纷,并且是唯一有权利审判涉外案件和执行仲裁的机构。*Ayoub M. Al-Jarbou,Judicial Independence, “Case Study of Saudi Arabia, Arab Law Quarterly,” vol. 19:1/4 (2004), pp.26-27.
此后,在王室的授意下行政委员会也应运而生。行政委员会是由沙特政府中各个要害部门的部长下令组建,这些委员会由政府的各个部门直接管辖,行政委员会主要负责沙利亚法庭和申诉委员会没有按照政府的要求办理的重大案件。这些案件经常让宗教法官难以抉择,比如对于银行股份、保险合同等金融方面的案件。申诉委员会和行政委员会的建立引起了沙利亚法庭的不满,许多理应由沙利亚法庭审理的案件却被王室下令由行政委员会判决。*Ayoub M. Al-Jarbou,Judicial Independence,“Case Study of Saudi Arabia, Arab Law Quarterly,” p.41.行政委员会和申诉委员会的相继出现极大地削弱了沙利亚法庭的权威。这两个执法机构皆属于沙特王室命令组建,成员都是其他部门的公务人员,直接对沙特王室负责。*Ayoub M. Al-Jarbou,Judicial Independence,“Case Study of Saudi Arabia, Arab Law Quarterly,” pp.41-42.1970年大穆夫提去世,沙特王室没有组织选举新的大穆夫提,而是签署王室法令建立了司法部。*Alexei Vassiliev, The History of Saudi Arabia, p.125.这标志着司法领域多元化结构的确立。沙特的宗教学者逐渐成为了依附于沙特家族的公务人员,宗教机构成为了国家官僚机构的一部分。*Joseph Nevo, “Religion and National Identity in Saudi Arabia,” p.42.瓦哈比派学者对宗教政治体制的演变由抵制逐渐走向了认可乃至宣扬。
结论
从伊本·瓦哈卜时代到当今的沙特阿拉伯王国,阿拉伯半岛经历了从部族向国家的社会转型。瓦哈比主义的宗教政治内涵也经历了形成和演变的过程。瓦哈比主义宗教理论的兼容性和政治理论的去极端化,决定了沙特官方瓦哈比主义作为王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温和性。教俗合一宗教政治体制的演进,一方面保证了在沙特国家社会力量的集中,推动了王国现代化的进程;另一方面体现了沙特官方瓦哈比主义的进步性和对现代化的适应性。总之,瓦哈比主义既非浑然一体,亦非一成不变。作为沙特官方意识形态的瓦哈比主义经历了现代化的洗礼,亦逐渐形成了较为成熟的现代宗教政治意识形态。作为逊尼派伊斯兰教的重要一支,沙特官方的瓦哈比派并非极端派别。进一步来说,瓦哈比主义与恐怖主义之间并无直接联系。
实际上,沙特阿拉伯也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极端的圣战分子和恐怖组织曾多次对沙特国家发起过恐怖袭击,其中1979年11月20日发生的麦加禁寺袭击案影响尤为恶劣。在朱海曼·本·穆罕默德·本·萨伊夫·欧泰比的带领下,400余名武装分子占领麦加的禁寺长达两周。在国王哈立德的要求之下,瓦哈比派官方宗教学者颁布法特瓦支持沙特家族。1979年11月24日,官方宗教权威颁布了法特瓦要求叛军投降和放下武器,并且批准沙特政府使用武力镇压叛军。*Joseph Kechichian, “The Role of the Ulama in the Politics of an Islamic State:The Case of Saudi Arabi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vol.18,1998, p.67.在此次事件中,官方宗教学者首开先例允许政府在禁寺使用武力。体现了当代沙特官方瓦哈比派在面对危及国家安全问题时的积极作用和正确认识。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之下,对沙特的瓦哈比主义的客观认识,有利于深化中沙两国的政治互信,也为两国在安全领域的合作提供了理论基础。
(责任编辑:郭丹彤)
2016-08-21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沙特阿拉伯伊斯兰主义运动研究”(编号:15CSS009)。
马洁光(1989-),男,青海西宁人,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
A
1674-6201(2016)03-0076-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