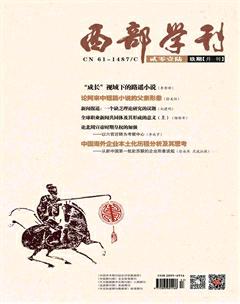“成长”视域下的路遥小说
摘要:路遥是当代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家,他的小说表现出年轻知识分子的成长历程。成长就是在城乡之间,选择主体寻找自己的身份认同,个人时间与历史时间相融合的过程;成长表现出人物的内心世界由矛盾、焦虑到自信成熟的过程;成长也表现为,溢出路遥创作的文本,在文学史范围之内,主题前后承续发展的过程。
关键词:路遥小说;成长;城乡二元对立;身份认同
中图分类号:I207.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成长对于个体来说是个永恒不变的主题。在古代封闭农业文明社会里,把人生分成几个重要的阶段,在每个阶段都有一种通过仪式,在时间的凝定与突显中,成长是个体获得集体认可的权利和自己应当承担的义务的过程。而成长真正赋予现代含义,是源于“进化论”思想,历史成为有逻辑的时间发展。真正对小说中的成长作为一个主题,并进行全面深入研究的是巴赫金。巴赫金在论述欧洲“教育小说”时意识到这种小说主题的重要。他阐释了成长小说的根本特征:这一类小说在时间中塑造的是成长中的人物形象。这里主人公的形象,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统一体。主人公本身,他的性格,在这一小说公式中成了变数......时间进入了人的内部,进入了人物形象本身。成长就是动态的变化,只不过人物的成长与历史的变化之间,发生了一种紧密的互为阐释的关系,也就是说历史的“进步”,促使人物的性格发生变化和成长,人物的成长和变化,也是历史进步的产物。当然,这种个人和历史的相互“成长”也不是自然和谐的,有时充满着矛盾冲突。“他与世界一同成长,他自身反映着世界本身的历史成长。他已不在一个时代的内部,而处在两个时代的交叉处,处在一个时代向另一个时代的转折点上。这一转折是寓于他身上,通过他完成的。他不得不成为前所未有的新型的人......成长中的人的形象,开始克服自身的私人性质,并进入了另外一种十分广阔的历史存在领域”。[1]230
当个人的成长和历史的进步互为影响和互为“镜像”关系时,成长也变成了觉醒后的必然选择。在路遥小说中的成长中的选择问题,是我们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正如路遥所说:“当历史要求我们拔腿走向新生活的彼岸时,我们对生活过的老土地是珍惜的告别,还是无情的斩断?”路遥认为,这是俄罗斯作家拉斯普京的命题,其实,他的全部小说,也许都可以包含在这一主题之中。陈泽顺重读路遥时也认为,新旧转变过程中的矛盾书写是路遥小说的总主题。[2]555路遥在《人生》的首页上,引用了柳青的言论鲜明地表达出他的思考。柳青的这句话,告诫年轻人,在人生的奋斗历程中,紧要之处的岔道,将会面临艰难的选择,而选择的有效处理,对整个人生意义非凡。这个言论,不仅奠定了《人生》的基调,而且成为他创作小说的总纲。
在中国新旧交替的特定时期,抛出这样的问题,就具有了一定现实意义。首先是城乡之间的选择问题。来自农村的知识分子受现代思想文化的熏陶,渴望逃离农村奔向城市,过一种没有肉体苦难和精神屈辱的现代生活。其次,成长也是一种重新的身份认同的过程,就是不断叩问我是谁,以及为什么我不能过自己想要的生活的过程。认同主体处于丧失归属感的内部分裂状处,充满了过去和未来的时间冲突中绵延的焦虑。为了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困境,成长就必须选择奋斗,选择跨越城乡界限,找寻自我的理想身份。在悖论式的抗争中,会遇到很多体制和文化方面的牵绊,带来了内心世界的挣扎与困惑,在困惑、选择、挣扎中人物得到了成长。从普遍意义上说,解除这些困惑或许是人类面对的永恒话题,是没有终极答案的。而路遥在不断地强调选择在成长过程的重要性,实际上,路遥是在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指导下,对特定的历史阶段人物的成长做出了选择和判断。本文主要选取了路遥的三个代表性作品——《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与《平凡的世界》来论述。如果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路遥的成长主题的创作有其重要的历史贡献,既体现出对革命现实主义小说中这一主题的继承,也反映出这一主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发展。随着新世纪的到来,路遥笔下的农村知识分子形象,又面临新的困境和新的挑战。
一、想成为他者
鲍曼认为,“足以让他前进的东西是他所看到的东西的厌恶和反感……,是厌恶而非诱惑才是历史前进的根本动力。因为人类对他们在自己的状况中所发现的令人痛苦和不快的东西感到羞愧和烦恼,因为他们不希望这种状况继续下去,还因为他们寻找一条减轻或补偿他们所受痛苦的道路,历史变革才发生。”[3]18鲍曼看到了“厌”一方面,其实,厌恶是因为有了诱惑的存在,差异效果下才会产生的一种情感,厌恶的极处,就有追求诱惑摆脱厌恶的豪壮之情。路遥小说中主要人物,展开的厌恶和诱惑的互动,就是在城乡二元对立的背景下展开的。城乡二元对立是社会存在的普遍现象。乡村作为农耕文明的代表,总是与封建、落后和贫困相联系,而城市则是现代文明的代表,常常与进步、发达、富有等相联系。乡村和城市彼此对立,前者的是乃后者的非,反之亦然。乡村和城市存在某种对称,但是历史发展选择了城市,正如斯宾格勒所说的,城市的心灵采用了一种新语言,他极快的便与文化本身的语言等同起来。当城市成为主导叙事时,乡村也被重新建构了,它们之间形成的对立是伸展与畏缩、进取与固守、主导与被主导、作用与反作用的对立。当差异的存在使得农村内部同质已经过剩时,就催生了对匮乏的异质的追求。路遥的小说中主要人物的成长,就是要进入以城市为代表的历史时间,打破这种城乡形成的默契的对立,在跨界中,努力变成一个城市的“他者”。
在路遥小说中,来自农村的知识分子厌恶贫穷、苦难,于是,他们热切向往一种异质的城市文化,并把这作为自己前进的动力。成长过程就是奋斗的过程,奋斗主要表现为对知识的渴求。马建强家贫无法继续完成学业,他没有仿效周围休学的学生,也不听父亲让回家务农的劝告,在淳朴的乡亲们的慷慨救助下,进入高中。求学道路的延伸,在他心里是充满了魅惑的神圣,弥散出虔诚的庄严。在城市的学习过程中,他对知识充满无限的渴望,因为他认为只有热爱知识,他才不会和自己的理想渐行渐远,只有求知他才能享受到城市的现代文明,这样个人才能与历史一起成长。因此,才会有期中考试时,他从第二名变成倒数第二时,内心感到很大的痛苦;当城里的同学向他请教问题时,他才获得了久违的自信与尊严;也不难理解,他宁愿忍受着肚子的饥饿,但还光顾书店,因为知识带给他的是成长过程中自信与希望。高加林,也是在中学被启蒙的对象。高中毕业后返回农村,还保持着城市人的习性,爱讲卫生,穿着也留着城市人的痕迹。他确实没有做好成为一个农民的准备,他坚信他的未来在城里,为了实现成为“他者”的目标,他认为最重要的是要具有城里人的文化,城里人的现代视野。高加林初中就养成了每天看报的习惯,他在努力争取这些,即使到了县城去卖馍,还是抽空去阅览室看报,而且首先看的是《人民日报》国际版,他关注国际问题,努力要超越乡村的局限。孙少平也是经常阅读《参考消息》,因为这张报纸,在特定的时代有其符号意义。陈丹青有过这样的表述,“70年代,神州大地亿万尧舜就凭那几页纸‘参考世界上一星半点的消息”。[4]210陈丹青有点对那个时代的调侃,但至少表明《参考消息》在当时的影响。路遥小说中一再出现这个意象,表现出被启蒙的年轻知识分子,追求开放的思想和现代的思维,他们已不是黄土高原上封闭保守的陕北农民。他们对生活的要求,已非本能需要,而是更高的精神追求。他们阅读具有人文色彩的西方名著,对人生的理解已上升到一个境界,他们的精神世界在小说中得到了进一步的延伸。即使在矿井下,孙少平也利用休息时间,不仅自己研读《红与黑》,而且,还给工友讲述书中的要义。路遥在谈到经典著作时说,不仅仅是治狂妄病,更主要的是它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营养。年轻的知识分子对知识的渴求,就是要在不断的成长过程中,实现自己成为“他者”的梦想。
路遥小说中知识分子的成长,和作者自己的生活经历是分不开的。路遥,出身寒微,身世不幸;生活于封闭的陕北农村,常常忍受着生活的困苦,过往的这些记忆留给他心灵中深深的痛。他变得敏感、自卑甚至有些神经质,有时又走向极端,变得更加自负。他想赢得更多的尊严和价值,于是,他在选择,他在挣扎,这个过程,就是他认识世界自我成长的过程。最后,知青的到来才是他真正觉醒的开始。1970年左右,成千上万的北京知青来到了贫瘠闭塞的陕北,他们带来了外面强劲的现代文化,这种文化对古老土地上形成的传统文化和革命话语,形成了强大的冲击。路遥在与知青的交流学习过程中,激荡的内心开始发生了转变,他尝试用一种全新的理念来思考农村的社会和现实,也开始沉思自己的前途和人生的价值。他曾对人说,我心里有种预感,我未来的女朋友就在他们中间,可见路遥对北京知青的倾心不仅仅在于外在的形象,更多是对他们的学识和视野的钦慕。
现实的苦难催生了对城市的向往。农村年轻的知识分子就是想摆脱农村,过一种代表现代文明的城市生活。他们想成为“他者”的过程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但这过程是艰辛的,而且充满悖论的。马建强在学校里经常过着饥饿难耐的生活,而他的同学则没有这种对肉体的担忧。当马建强在马路上饿着肚子,透过窗户望见同学们的吃相时,心中的不悦难以言说。出身的差异让他产生愤恨之情。他认为,原因在于他来自农村,父母是地地道道的农民;而别人则生活在城里,父母是衣食无忧的干部。在城乡对立形成的“互文”空间中,马建强发现了自我与“他者”的差距,开始思考什么意义上能够说我适合城市的这个位置呢?他已经不是一个单面人了,城市已在他心中划下了印痕。高加林的成长,就是要变成一个城里人,过自己认为有价值的现代生活。高加林想用自己的奋斗去创建一个“他者”给与的有条件的身份。当个人想成为“他者”的理想受到制约时,反抗制约因素也是不可避免的。当以城里人自居的王克南母亲对他挖苦和嘲讽时,他的自卑瞬间化作了决心和反抗,“我非要到这里来不可!我有文化,有知识,我比这里生活的年轻人那一点差?我为什么要受这样的屈辱呢?。”[5]45高加林强调了知识和文化在个人发展中的重要性,也暴露他追求的“他者”的理想和现实的冲突 。
年轻的知识分子在越界想成为“他者”的过程是充满矛盾的,他们要与以无意识方式存在的城乡差异相抗衡。黄亚萍得知高加林失去工作变成农民的现实处境时,找到父亲谈及此事,她多么想找到安慰,事实却超乎她的想象。原来父亲不仅知道高加林的处分结果,而且他还是这个事件的参与者。当她抱怨现实的残酷时,父亲说:“不要抱怨生活!生活永远是公正的!你应该怨你自己,”“咱们马上要到南京了,那个小伙子是农民,我们怎么能把他带去呢?”[5]126农民的身份是注定的背后,其实是社会共谋的结果。而高加林成长过程中的抗争,就有了一种悲剧意味,不断的奋争过程中,直面了人生最坏方面,让人们瞥见了城乡之间的距离,以及对农村青年成长过程的伤害。成长过程中面临的体制问题被凸显出来。这种制度以暴力的方式对这些农村的青年形成了戕害,人物的成长表现出对现实矛盾的激烈反抗。到《平凡的世界》主人公孙少平,这种冲突已经转变了方向,矛盾被淡化处理了。从省里到地方的干部,变成了现代化的领头人,他们掌握并执行改革政策,不断创造着经济“业绩”。孙少平也被安排了一个巧合的户口,某种程度上解决了法律上的身份问题,人物在城乡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很大的缓解;人物的自我世界与现实达成了妥协,通过劳动获得了尊严,让自己融入历史的大潮中,成为人民中的一员。“真正的勇士向来默默无闻,喧哗无止的永远是自视清高的”。 [6]138“人的痛苦只能在生活中和劳动中慢慢消磨掉。劳动,在这样的时候不仅仅是生活的要求,而且是生活的需要”。[6]149
城市已经成为他的镜像,农村是他的原罪。他们由农村带来的饥饿和屈辱,希望通过城市来拯救。主人公成长过程,就是在努力想变成“他者”的充满悖论和不可能实现的奋斗过程。
二、我是谁
马建强、高加林、孙少平的奋斗虽然充满艰辛和冲突,但他们还是在不断地追求自我超越自我。他们对爱情的追寻就是这样一个不断的寻找自我的过程。他们心中的美好爱情,不是一种身体强烈吸引的激情型,也不是攀附权富的实用型,而是一种具有“进化爱情”特点的友谊型。在这种状态下,爱情强调更多是安静和友爱,突出了女性帮助下男性的成长。他们内在的性格,由敏感、自卑逐渐变得成熟自信,这个成长过程就是寻找自己的过程。
马建强(《在困难日子里》这篇小说的主人公)就是由于天使形象的吴亚玲的引导,才从敏感而自卑变得自信而自强。马建强由于生活困顿,甚至被一些同学嘲讽讥笑,他的局外人身份使他失去了个人的尊严。马建强眼中的完美的城市姑娘吴亚玲,变成了他的知音,她不仅给他物质上的满足,而且也知晓他精神上的需要。最后,带动大家来关心他解救他,使他摆脱了人生的困境。马建强对吴亚玲暗恋式的爱情最后在友谊万岁中结束,这样的处理多少显得有些浪漫的幻想。《人生》中的高加林在刘巧珍和高亚萍之间的周旋,就显得更接近现实了。高加林对爱情的选择,是以处于无意识状态的“成长”作为标准来选择的。高加林与她俩之间缺乏真正激情的爱,他对爱情的选择虽然有一点虚幻性,但更多是充满目的性。他选择刘巧珍是被迫的,虽然这个美丽的农村姑娘心地善良,对爱有牺牲奉献精神,但高加林还是最后放弃了她。因为高加林已经是一个被启蒙了的知识分子,知识更丰富,视野开阔了。他已经厌倦了农村的生活,认为选择了农村就是选择了艰辛。他没有做好当农民的准备,内心世界也不想做农民,他知道他成长的方向在城市,虽然现在自己的肉身处在农村。这也就不难理解他听到了巧珍的真情表白后的矛盾:“爱情?来得太突然?他连一点精神准备也没有,他还没谈过恋爱,更没有想到过要爱巧珍”。 [5]222高加林后悔了,感觉和一个没文化的农村姑娘发生恋爱,简直是一种堕落和消沉的表现,等于承认自己一辈子当农民了。他的选择不是出于发自心底深沉的爱,而是为满足落魄孤寂时情感的需要。他对巧珍的爱与悔常常相伴相随;他不好好珍惜巧珍对他全心全意的爱,而是理智而又自私地担心外人知道他们的恋爱关系;他不是爱现在的巧珍,而是想把她改造成自己理想中的对象(比如让巧珍刷牙讲卫生的问题)。他对巧珍的爱就如同对农村的感情,他向往的是存在别处但现在匮乏的“她者”,追求的是与农村相对的现代城市生活。与王亚萍的邂逅满足了他内心的感觉,他认为亚萍就是他理想中的爱人。因为她有文化、聪敏、家庭条件好,身上又有神秘的魅力,而巧珍则是一眼看到底,单纯的、单调的。他感觉他与亚萍的爱情是充满浪漫的现代的。高加林对爱情选择,看重钟爱的对象所处的位置,以及是否有利于自我的成长。
爱情对成长的巨大推动力,在《平凡的世界》中表现得尤为深刻。孙少平在大亚湾煤矿和田晓霞的对话透视出孙少平的成长历程。(田晓霞)她拿出小圆镜照了照说:
“我和你在一块,才感到自己更像个女人。”(孙少平)“你本来就是个女人嘛!”“可和我一块的男人都说我不像个女人。我知道这是因为我的性格。可是,他们并不知道,当他们自己像个女人的时候,我只能把自己当做他们大哥”[6]84
田晓霞自认为在孙少平跟前更像个女人,正是表现出他的成熟,性格上克服了城市带给他的压抑,而这背后暗含着他们俩的过去,田晓霞声称在面对女人般的男人时,自己只能像大哥,这个大哥形象其实就是少年的田晓霞在少年孙少平眼中的形象。田晓霞见证了孙少平的成长:在历史的潮流中,从一个敏感自卑的男孩变成了自信自强的男人。田晓霞是孙少平成长的助推器,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友谊大于激情。另一个情节是他们在热恋过程中,孙少平总感觉他们的爱情,存在职业巨大差距背后潜藏的裂缝,冷静思考后常常认为这种爱情就是一种梦幻。孙少平对爱情的态度是自我怀疑到自由否定。这种态度可以用斯滕伯格曾提出了“爱情三角形”理论来解释,他认为亲密、激情、承诺三个因素的组合对应着各种类型的爱情。从这个理论来看,孙少平和田晓霞的爱情,缺少激情缺少对未来的承诺,有的更多是恋爱的通信,和富有罗曼蒂克的话语,这只是一种喜欢,他也时常理性思考着他们的未来,经常是一种哀叹:“唉,归根到底,他和晓霞最终的关系也许要用悲剧的形式结束。这悲剧性的结论实际上一直深埋在他心灵深处”。[6]77孙少平对田晓霞的追求,最后以田晓霞的死而结束,这是个隐喻,意味着引导着他让他走向成熟的梦想破灭。归根结底,路遥小说中主要描述的爱情,男女之间是缺少真正的情感联系的纽带,女主人公是作为男主人公投射的目标出现,内心世界充满低落情绪的主人公,追求理想的过程就是追求内心世界自我完满过程,也许目标最后渐行渐远,但目标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追求过程中奋斗精神背后体现出的人物的心路历程。通过爱情,他们找到了在城市中矛盾和迷失的自我,寻找到了自我存在的尊严和价值。
如果说他不断的追求知识,以获取在城市的合法身份是一种表面的追求,也是现代文化的发展与他自我的发展的一种融合的过程。那么他内心世界的微妙变化也是经历过这样的成长过程的。这个过程其实是一种对城市向往的欲望投射的过程,也是自我欲望得到满足的过程。正如勒内·吉拉尔认为这实际上是一种欲望的模仿。这种模仿其中一种是内模仿,主体追求欲望客体,通过模仿他们之间的介体达到对客体追求的欲望的满足。这种对欲望介体的模仿与超越,也是自己丧失的内在敏感与自尊的找寻过程。而路遥一直在宣称自己的写法中运用了对比的手法。这种对比,本质上就是主体对作为介体的“他者”的欲望的模仿。《人生》中高加林进城卖馍,遇到了张克南和黄亚萍。他自卑的加重来自于张克南。本来是一句同学之间真诚的话语,但高加林自我敏感把这解读成是炫耀优越感,他内心显示出的是自卑后的自傲。张克南就是高加林对欲望客体黄亚萍的介体,高加林把张克南当做自己模仿的对象,战胜他才有一种成就感,才能克服内心的自卑。最后,黄亚萍选择了他而抛弃了张克南时,他内心的自由才彻底释放出来,但张克南这个介体阻挠高加林的美梦,当高加林被开除返乡时,实际上把这个矛头指向了束缚限制的体制,把这个矛盾泛化了。高加林通过模仿、超越介体,追求欲望客体,就是追求自我的发展,克服内心世界的自卑的过程。如果说《人生》中主体和介体矛盾冲突明显,那么在《在困难的日子里》的马建强则是以超越介体郑大卫,赢得吴亚玲而结束。马建强喜欢吴亚玲,但是由于自卑,不敢表达自己的感受,当他成绩超越郑大卫时,他才感觉到有了自尊;吴亚玲了解他内心感受,给他赠送书籍达到内心的真正沟通之时,他的自信才真正恢复起来,自信的回复是超越介体所感受到的。《平凡世界》中的孙少平性格,在成为煤矿工人后,性格基本趋于了成熟,他和介体之间没有真正的接触,体现出的主体内心已经回归到确定的自我。马建强、高加林、孙少平追求爱情过程中都设置了介体,而且介体都是城市人,有优越的外表和良好的家庭环境,主人公把模仿超越介体作为自己的目标。整体来看,这三个人物有走向成熟的递进过程。马建强把超越介体理想化,最后出现了三个人成为朋友的和谐处理;高加林则是完全取代介体又被介体打翻在地,和介体的矛盾冲突最大;孙少平则在成为矿工之后,自己的内心世界变得越来越强大,介体和他之间几乎没有什么更大的冲突。这三个人物都在模仿超越介体,达到无限靠近客体。他们从焦灼的渴望走向了内心的平静,自我也从自卑走向了自信,从自己的单枪独马的个人主义走向了在集体中充分发挥自我力量的劳动者。
路遥小说就是一个找寻自我的过程。通过爱情中的欲望客体和介体,把迷失的自我从现实中解救出来,让城乡二元对立映照的内在矛盾达到了统一,虽然这种自我的找寻不是西方形而上自我意义的追寻,而是个人在紧贴历史话语背景下,在集体中找到了自我,在现实中寻找到价值。
三、“我从哪里来”“我将成为谁”
成长过程也牵扯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从哪里来”,“我将成为谁”。如果把这一主题溢出路遥的小说世界,放到文学史的大背景下来审视,就能发现成长主题的延续和发展,就会发现路遥小说中的这一主题和十七年文学关系紧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讲话会以后,革命文学的成长主题具有了一种规范性,因为这类主题既可以体现“历史的进步”,也可以强调“党的作用”。柳青、赵树理就是接受了这一传统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观和文学创作观,他们认为历史就是新旧事物的斗争史,也是新事物战胜旧事物的发展史。他们坚守这种二元对立的观念,来创作现实主义题材的革命文学。张清华认为革命文学是一种“类成长小说”,体现出类型成长主题,这类主题是以革命为诉求的的成长小说,人物成长常常体现的是被动,和故意被拔高的特性。虽然革命现实主义的成长小说有类型化模式化倾向,但他们坚持个人和历史时间融合的思维方式是不变的。赵树理的小说中有很多以“成长”为主题创作的小说。例如《三里湾》这一部小说,塑造的玉生和小俊这对年轻夫妻由结合到分离。背后的原因,在于小俊自私自利整天闹分家,好吃懒做缺乏劳动热情。他们离婚之后,初中毕业生的灵芝选择了玉生,她看中的是玉生聪明能干、勤劳善良,紧跟党的路线政策。玉生俨然就是一个农村里的“能人”,他身上体现的是具有先进特点的历史革命话语。改革开放初期,这种革命话语发生了很大变化。对经济的现代化追求上升为一种历史的话语,而农村走的是一条农业现代化的道路。路遥小说中的孙少安,就是延续以前的历史主题创作出来的。孙少安选择乡村不是由于能力不够,他曾以出色的成绩考上了城镇中学,而是现实生存状况毁灭了他的进入城市发展的机会,被迫回乡成为乡村的“能人”式的年轻农民,他吃苦耐劳有奉献精神,聪明有领导能力。他选择的道路也符合历史进步的要求。他是要进行农村经济现代化建设,带领广大民众走上致富道路。这与同时期的很多作品有遥相呼应之势。如陈忠实发表于八十年代初期的著名中篇小说《初夏》。这部小说也在思考城市化过程中的知识分子的选择问题。退伍军人冯马驹和民办教师薛淑贤婚约可谓一波三折,冯马驹由于失去了变成城市人的机会,最后遭到了薛淑贤毁约退婚。冯马驹选择农村姑娘彩彩,则是他们有共同的理想,愿意执守于乡村,建设自己的家园。爱情的选择体现出对农村现代化的认可。孙少安成为乡村的能人,复兴自己的家业,赢得广大乡邻的尊重靠的是发展砖窑,而马驹发展乡村经济也主要靠砖窑,甚至把烧砖这个产业放到很高的地位。小说开篇就描绘了一番砖窑厂兴旺的景象,充分表现出作者对乡村经济的发展是由衷的赞美和内心充满希望的。梁鸿创作的《中国在梁庄》在新世纪引起了巨大反响,她对这个农村的现代性做了自己表述和思考。她说,走进北方的农村,会发现许多废弃的砖窑,这些深深浅浅的大坑,是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重新复苏的重要标志之一。她的这种反思不无批判意味,但说明了了那个时代个人是如何践行着历史化的发展,以及个人是如何在历史中成长的。成长主题在路遥小说确实体现出一种延续和发展。
路遥的小说对以前的文学思想有一定的继承,但由于自身的局限,路遥小说中成长主题还是受到了制约。中国改革开放向前发展,市场经济引发的弊端也暴露出来了。我们一直在思考,路遥笔下的孙少平和孙少安将向何处发展?同样是陕西的作家贾平凹,写于八十年代末期的小说《浮躁》对这个问题有了自己的深入思考。小说中主要人物金狗,一直希望冲出乡村走向城市。面对城市的诱惑,特别是异己力量对他“招安”,金狗何去何从选择是那样直击人心。他不愿同流合污,甘愿被放逐,回到乡村做起了自己的商业梦。结局看起来是两全其美的选择,既没有离乡背井与乡土文明割裂,同时也有现代文明昭示的“发展”,仿佛金狗变成了又一个孙少安,但这些都是作者塑造一种理想的投射。九十年代初期,贾平凹直言不讳的给出了金狗的结局,他就是那个彻底堕落的文人庄之蝶。金狗没落的归宿证明了农村现代化神话的荒谬。农村在城市化的建构中苦难越发沉重,乡村被城市占有,被城市俘虏,成为城市的牺牲品,农村彻底沦陷了,呈现虚空化和荒漠化。“在中国当代发展的情景下,农村成为他们想要挣脱和逃离的生死场,而不是希望的田野,希望的空间做人的空间是城市。”[7]随着农村的陷落,背后承载的优秀传统文化也逐渐的消亡,导致了现代文化对德性的戕害也越发深重。中国乡村向何处去?这个没有答案、没有终结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
有的评论家说,路遥小说回避了洪水猛兽的城市文明而以一种谅解的态度来看待这些问题。 他笔下人物的成长,还未对现代性产生焦虑,对城市的“恶”做出自己的反思,也没有表现出城市人的荒芜与孤独。正如斯宾格勒说,城市不仅意味着才智,并且意味着金钱。路遥小说中主人公看重的是一种才智,一种现代社会带来的自由进步的东西,他没有更多关注金钱带来的巨大作用。他的小说确实缺少了“反进步论”的审美维度,缺少了对生命和成长的更为整体和真实的关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后,城乡之间对立冲突更加明显,人们更多是对城市抱有否定性的批判态度。贾平凹的小说《高兴》中对刘高兴的塑造,已经同孙少平有了天壤之别。刘高兴还是向往城市希望扎根于城市,他为了迎合城市修改姓名,渴望得到城市对自己的身份认同。当他背着五富的尸体试图利用火车运回老家时,他的农民身份也暴露无遗。可他们回不去了,乡村已经把他们抛弃,城市也厌弃这些被看作“垃圾”的底层人物。他们比起孙少平,城乡矛盾在他们身上体现得更明显,孙少平还能找到自我的尊严,刘高兴则是完全的自我分裂;孙少平在劳动中找到价值,刘高兴则是体现出现实生活的荒诞。新一代“农民工”的出路在哪里?未来又在那里?
路遥小说中的成长主要写的是进城的知识分子,凸显了文化身份带给他们的极大差异。成长意味着追寻历史时间,由农村到城市的空间变化,知识分子由内心自卑到自信的成熟变化的心路历程。成长也意味着路遥创作既传承了启蒙和革命现实主义的传统,也连接着后来农村人进城的继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苏)巴赫金.小说理论[M].白春仁,晓河译.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陈泽顺.重读路遥·代后记[M].华夏出版社,1995.
[3](英)齐格蒙特·鲍曼.共同体[M].欧阳景根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
[4]陈丹青.多余的素材[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路遥.人生[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
[6]路遥.路遥全集(卷三)[M].陕西人民出版,1992.
[7]严海蓉.虚空的农村和空虚的主体[J].读书,2005(7).
[8]赵树理.赵树理文集(第二卷)[M].工人出版社,1980.
[9]张清华.狂欢与悲戚[M].新星出版社,2014.
[10]白兰达·卡诺纳.僭越的感觉 欲望之书[M].袁莜一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5.
[11]王西平等著.路遥评传[M].太白文艺出版社,1997.
[12]石天强.断裂地带的精神流亡[M].北京大学出版,2009.
[13](美)罗伯特·J·斯特博格等著.爱情心理学[M].中国出版集,2010.
[14](德)斯宾格勒.西方的没落[M].北方联合出版集团,2015.
[15](法)勒内·吉拉尔.浪漫的谎言与小说的真实[M].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
作者简介:李青峰,男,西北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杨立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