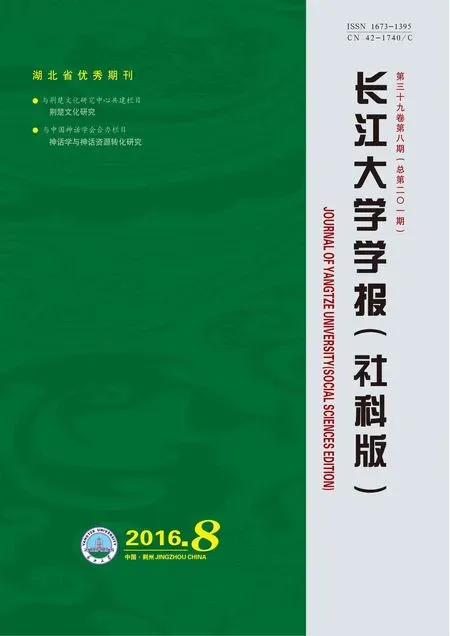山与物:《山海经·五臧山经》“物”记述
高莉芬 谢秀卉
(政治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 台北 11605)
山与物:《山海经·五臧山经》“物”记述
高莉芬谢秀卉
(政治大学 中国文学系,台湾 台北 11605)
《山海经·五臧山经》(以下简称《五臧山经》)分为《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由五方之山所藏之金、石、草、木、禽、兽、虫、鳞等“物”记述构成其主要内容。《五臧山经》中“明标山川道里方位”与“述明物之位置、种类、质量、功能”、“总校群山祠礼”等三种程式化的记述方式,使其文本形式自成体系,呈现独特的规律性。五方之山,山各有“臧”,“臧”有其“用”。“臧”有“常”、“异”之分,“用”有“善”、“恶”之别,而“记物”之博与“辨物”之异的思维就鲜明地体现在《五臧山经》的“物”记述中。《五臧山经》就在“以山聚类”、“常异分述”、“善恶有别”的记述原则中形成一个平常自然与怪奇谲丽兼而有之的“记物”与“辨物”体系。
山海经;五臧山经;博物;辨物;神灵物类
一、前言:奇书与奇物
在浩繁的古代典籍文献中,《山海经》无疑是一本特殊的书,由于书中内容述及“山川道里”,《山海经》在历来图书分类中多被视为地理书,如《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崇文总目》、《中兴馆阁书目》、《郡斋读书志》、《遂初堂书目》、《直斋书录解题》、《文献通考·经籍考》等,皆将本书归为地理类图书。自汉以来,学者对于《山海经》一书的性质多有探讨,汉代学者刘歆、王充以《山海经》为大禹、伯益治九州山川地理之书*刘歆《上〈山海经〉表》言:“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里仁书局1995年版,第477页。王充《论衡·别通》亦言:“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参见黄晖:《论衡校释》,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597页。,晋代郭璞同意刘歆之说,以此书为博物之作[1](P478~480),明代胡应麟则以之为“古今语怪之祖”[2](P314),《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视其为“小说之最古者”[3](P755)。近现代学者更对《山海经》投以多元丰富的论述,如鲁迅以之为古之“巫书”[4](P15),郑德坤以为是“记载中国神话最重要的一部书”[5],袁珂视之为“神话之渊府”,李丰楙名之为“神话的故乡”*袁珂称《山海经》“匪特史地之权舆,乃亦神话之渊府”。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里仁书局1995年版,序页第1页。李丰楙则言:“神话为每一民族的梦,山海经为神话的故乡,反映了中国人古老的梦境。”参见李丰楙:《山海经:神话的故乡》,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序言页第21页。,凡此则强调《山海经》保存了远古的神话材料。可见,因《山海经》具有地理博物与巫术神话之内容的殊异性,历来学者多会关注其奇书、异书、语怪之特质。
而《山海经》除了文字记载外,又有《山海经图》之作,明代胡应麟即以《山海经》部分乃为述图文字*如胡应麟说:“《经》载叔均方耕,讙兜方捕鱼,长臂人两手各操一鱼,竖亥右手把算,羿执弓矢,凿齿执盾,此类皆与纪事之词大异。近世坊间戏取《山海经》怪物为图,意古先有斯图,撰者因而纪之,故其文义应尔。”参见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四部正讹下》,上海书局出版社2009年版,第314页。,清代毕沅[6](P3176)与郝懿行[7](P603)亦多所论述,今人马昌仪更有《古本山海经图说》之作[8]。在这些论述中,不论视《山海经》为地理志、方物志、民族志、民俗志、博物志乃至于巫书,论者皆会注意到《山海经》所显现的繁富瑰奇、千奇百怪的“物”记述。早在汉代,司马迁即说:“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9](P44~46)王充也说:“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10](P597)二者皆论及书中对怪物与异物的记载。汉代刘歆《上〈山海经〉表》云:
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臣秀领校、秘书言校、秘书太常属臣望所校《山海经》凡三十二篇,今定为一十八篇,已定。《山海经》者,出于唐虞之际。昔洪水洋溢,漫衍中国,民人失据,崎岖于丘陵,巢于树木。鲧既无功,而帝尧使禹继之。禹乘四载,随山刊木,定高山大川。益与伯翳主驱禽兽,命山川,类草木,别水土。四岳佐之,以周四方,逮人迹之所希至,及舟舆之所罕到。内别五方之山,外分八方之海,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及四海之外,绝域之国,殊类之人。禹别九州,任土作贡;而益等类物善恶,著《山海经》。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孝武皇帝时尝有献异鸟者,食之百物,所不肯食。东方朔见之,言其鸟名,又言其所当食,如朔言。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孝宣帝时,击磻石于上郡,陷得石室,其中有反缚盗械人,时臣秀父向为谏议大夫,言此贰负之臣也。诏问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其文曰:“贰负杀窫窳,帝乃梏之疏属之山,桎其右足,反缚两手。”上大惊。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故《易》曰:“言天下之至赜而不可乱也。”博物之君子,其可不惑焉。臣秀昧死谨上。[1](P477~478)
刘歆指出《山海经》所记之物:“纪其珍宝奇物,异方之所生,水土草木禽兽昆虫麟凤之所止,祯祥之所隐。”所载之地理空间从“五方之山”以迄“八方之海”、“绝域之国”,所记之族类为“殊类之人”,录及异方、异物、异人、异闻,俨然是一个异于此界的他者世界。故刘歆论此书的功能为“考祯祥变怪之物”与“见远国异人之谣俗”:“朝士由是多奇《山海经》者,文学大儒皆读学,以为奇可以考祯祥变怪之物,见远国异人之谣俗。”[1](P478)
在刘歆与汉儒的眼中,《山海经》成为一本具备博物知识及实用性的奇书。但考今日所传之《山海经》内容,书中并非仅记珍宝奇物、“祯祥变怪之物”等奇物,生活世界中常见的草木、禽兽、昆虫亦在记述之列。从记物的角度而言,《山海经》乃是一本兼记常物与异物之书。今所传世《山海经》版本,可明确分为《山经》与《海经》两大部分。二者文本叙述方式有异,体例不同。今考《山海经》一书,《五臧山经》除了记载山川方位、地理数据外,记群山之物无疑为其主要内容。《五臧山经》分为《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由五方之山所藏之金、石、草、木、禽、兽、虫、鳞等“物”记述构成其主要内容,那些为人所注意的怪物与异物就与常物交错出现于各山经的记述之中。《五臧山经》的“物”记述具有相当的规律性与一致性,有大量程式化语法与修辞,本文旨在分析《五臧山经》中“物”记述的特点并探究其后所蕴涵的思维方式。
二、志山:以山聚类的记述规律
《五臧山经》依南、西、北、东、中五个方位依序叙述群山,每一方位群山下再以“之首”、“次二”、“次三”等,依次条列式记述,每一山系中依序记其方位、道里、名称、物产乃至祭祀,颇具规律性与一致性,每一经末又有总结:
右南经之山志,大小凡四十山,万六千三百八十里。[1](P19)
右西经之山志,凡七十七山,一万七千五百一十七里。[1](P66)
右北经之山志,凡八十七山,二万三千二百三十里。[1](P99)
右东经之山志,凡四十六山,万八千八百六十里。[1](P116)
右中经之山志,大凡百九十七山,二万一千三百七十一里。[1](P179)
“山志”即“志山”,“志”者,“记也,知也”[11](P24b)。就文本内容而论,《五臧山经》即是以志山为主,所志者乃天下名山,言其“五臧”,而“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1](P179)。志山、记山,应是《五臧山经》成书的重要宗旨之一。志无疑是《五臧山经》重要的表述方式,值得深究,可分析如下。
(一)程式化的记述方式
《五臧山经》志山的方式,除了明标山之方位、名称外,尤重对山中所生聚之物的记载,它们具有明显的规律性与一致性。这种程式化记述约可分为明标山川道里方位,述明物之位置、种类、质量、功能,总校群山祠礼等三种类型。
1.明标山川道里方位
第一类为明标山川道里方位的记述类型,南山、西山、北山、东山、中山各经皆有之,方位、道里、山名是记述的重点,常见的有如下记述形式:
又东三百里,曰堂庭之山……[1](P2)
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1](P47)
又北二百里,曰少咸之山……[1](P76)
又南三百里,曰泰山……[1](P104)
又东南一百三十里,曰龟山……[1](P175)
此类记述略有变化之例为插入“水行”、“山行”等字,或改“曰”为“至于”等例,如:
又南水行五百里,曰诸钩之山……[1](P111)
又北水行五百里,至于鴈门之山……[1](P98)
又北山行五百里,水行五百里,至于饶山。[1](P96)
其中,“(又)方位……里,曰……(某山)”是反复出现于各条记述的文字。
2.述明物之位置、种类、质量、功能
第二类是述明物之位置、种类、质量、功能的记述类型,可分为以下四型:
第一型是指示位置的记述:“其阴……”、“其阳……”、“其上……”、“其下……”、“其中……”,如:
又东三百里,曰基山,其阳多玉,其阴多怪木。[1](P5)
又西三百五十里,曰天帝之山,上多椶枏,下多菅蕙。[1](P29)
又北三百二十里,曰灌题之山,其上多樗柘,其下多流沙。[1](P74)
又东三十五里,曰葱聋之山,其中多大谷,是多白垩,黑、青、黄垩。[1](P119)
又东三十里,曰雅山。澧水出焉,东流注于视水,其中多大鱼。[1](170)
第二型是标明物种类别的记述:“其草……”、“其木……”、“其鸟……”、“其兽……”,如:
又北二百二十里,曰盂山,……其兽多白狼、白虎,其鸟多白雉、白翟。[1](P60)
又南水行七百里,曰孟子之山,其木多梓、桐,多桃、李,其草多菌蒲,其兽多麋鹿。[1](P111)
又东南一百二十里,曰洞庭之山,……其木多柤、棃橘、櫾,其草多葌、蘪芜、芍药、芎藭。[1](P176)
第三型则是标明物种数量的记述:“多……”与“无……”,如:
又东三百里,曰堂庭之山,多棪木,多白猿,多水玉,多黄金。[1](P2)
又东三百五十里,曰羽山,……无草木,多蝮虫。[1](P11)
又东五百里,曰仆勾之山,……无鸟兽,无水。[1](P13)
又东五百里,曰灌湘之山,……多怪鸟,无兽。[1](P17)
第四型则是指示性质、功能的记述,以“有某焉”的记述形式出现。这类记述是用于记录具有罕见、奇异、变怪的形貌与功能的生命体,可以是草、木、鸟、兽、蛇、鱼,后续则或接以“其状……”、“其鸣……”、“其味……”、“其名(曰)……”等性状、名称的描述,末尾则是物之功能的说明。说明功能,有些是能预示吉凶征兆,而以“见则”如何云云呈现。其例如下:
有兽焉,其状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狸力,见则其县多土功。[1](P8)
有蛇焉,名曰肥虹遗,六足四翼,见则天下大旱。[1](P22)
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彩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1](P35)
有兽焉,其状如菟而鸟喙,鸱目蛇尾,见人则眠,名曰犰狳,其鸣自訆,见则螽蝗为败。[1](P107)
有些则说明人类因取用而产生的影响,如浴之如何,食之如何,服之如何,佩之如何,养之如何,或可以如何,如:
有草焉,其名曰黄雚,其状如樗,其叶如麻,白华而赤实,其状如赭。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1](P25)
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谷,佩之不迷。[1](P1)
有鸟焉,其状如乌,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奇鸟 余鸟 ,服之使人不厌,又可以御凶。[1](P57)
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养之可以已忧。[1](P120)
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鯥,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1](P4)
有草焉,名曰莽草,可以毒鱼。[1](P164)
有白石焉,其名曰礜,可以毒鼠。[1](P30)
有桂竹,甚毒,伤人必死。[1](P175)
这类与物之位置、种类、数量、性质、功能相关的记述是《五臧山经》用以记物的程式化记述。
3.总校群山祠礼
《五臧山经》各经在每一山群末尾,又有属于总校群山及其祠礼的记述,以《南山经》为例:
凡鹊山之首,自招摇之山,以至箕尾之山,凡十山,二千九百五十里。其神状皆鸟身而龙首,其祠之礼:毛用一璋玉瘗,糈用稌米,一璧,稻米、白菅为席。[1](P8)
凡《南次二经》之首,自柜山至于漆吴之山,凡十七山,七千二百里。其神状皆龙身而鸟首,其祠:毛用一璧瘗,糈用稌。[1](P15)
凡《南次三经》之首,自天虞之山以至南禺之山,凡一十四山,六千五百三十里。其神皆龙身而人面。其祠皆一白狗祈,糈用稌。[1](P19)
其中,“凡……之首,自……山至(于)……山,凡……山,……里,其神状……,其祠……”是重复出现的文字,见于各经山群记述末尾。
上述明标山川道里方位,述明物之位置、种类、质量、功能,总校群山祠礼等三种记述,使《五臧山经》呈现出规律性与一致性的形式特色,它们是与山之所臧相关的记述类型,而正是由于“言其五臧”[1](P179),因而有《五臧山经》之称。*郝懿行云:“藏,古字作臧,才浪切;《汉书》云,山海天地之臧,故此经称五臧。”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里仁书局1995年版,第180页。
(二)以山为中心的体系化记述
在《五臧山经》中,每一座山构成一条记述,《五臧山经》主要是由采取条列式记述之山所组成。每一条记述即是由明标山川道里方位,述明物之位置、种类、质量、功能的记述类型搭配组合而构成其内容。
每一座山以明标山川道里方位的记述起始,这种程式化记述与《五臧山经》依五方之山分篇相关。《五臧山经》依南山、西山、北山、东山、中山分立,其中的南山、西山、北山、东山、中山皆非实指某一座山之专名,而是总称分别坐落于南边、西边、北边、东边、中央等方位上的无数大小山脉。南山、西山、北山、东山、中山之称名就有将处于南、西、北、东、中各方的山脉化约为五方之山之用意。因此,每一座被记述的山,皆在此五方之山的空间范围中,每一座山都有它在整体五方之山的地理空间中的相对位置。“(又)方位……里,曰……(某山)”的反复使用,就把每一座山所属的方位、山与山之间的道里距离、山的名称明确标示出来,它正是《五臧山经》用以指示某山在整体五方之山所据有之空间坐标的程式化记述。
接续于明标山川道里方位的记述之后,则是述明物之位置、种类、质量、功能的记述,以记各山所生与所藏。因之,可以是指示位置的其阴、其阳、其上、其下、其中,或指示种类的其草、其木、其鸟、其兽,或指示数量的“多……”与“无……”,乃至指示性质、功能的“有某焉”记述。其例如下:
又北四百里,曰尔是之山,无草木,无水。[1](P81)
又北三百五十里,曰白沙山,广员三百里,尽沙也,无草木鸟兽。[1](P81)
又南三百里,曰藟山,其上有玉,其下有金。湖水出焉,东流注于食水,其中多活师。[1](P101)
又西二百里,曰鹿台之山,其上多白玉,其下多银,其兽多牲乍牛、羬羊、白豪。有鸟焉,其状如雄鸡而人面,名曰凫傒,其鸣自叫也,见则有兵。[1](P35)
东五百里,曰祷过之山,其上多金、玉,其下多犀、兕,多象。有鸟焉,其状如鵁,而白首、三足、人面,其名曰瞿如,其鸣自号也。泿水出焉,而南流注于海,其中有虎蛟,其状鱼身而蛇尾,其音如鸳鸯,食者不肿,可以已痔。[1](P15)
由这几则例子视之,它们在记述类型的搭配组合上繁简不同。愈是蕴藏富饶之山,出现的程式化记述类型愈多。如上引例的“鹿台之山”,即有指示物之位置、数量的“其上多白玉,其下多银”,指示种类的“其兽多牲乍牛、羬羊、白豪”,以及指示性质、功能的“有鸟焉,其状如雄鸡而人面,名曰凫傒,其鸣自叫也,见则有兵”。再如“祷过之山”,亦有指示位置、质量、功能的程式化记述,这些皆属物产丰厚之山。相对于此,亦有物产贫乏之地,如“尔是之山”只述明“无草木,无水”,“白沙山”更是“无草木鸟兽”之地域,两者皆为仅运用了指示数量的记述类型。各山虽有富厚薄稀之别,然大抵而言,皆是围绕一座山而记物,述明某山所生藏之金、石、草、木、虫、鱼、鸟、兽乃至罕见或变怪之物,凡此皆显现出以山聚类的记述规律,是以山为中心而形成的体系化记述。
三、生藏之山:常物与异物
山,在古人的认知传述中,乃具有生育万物之能力,《释名》曰:“山,产也,言产生万物。”[12](P14)它能容受各种生命游走其间,“草木生焉,万物植焉,飞鸟集焉,走兽休焉”[13](P129),由是而“宝藏兴焉”(《礼记·中庸》),而“四方益取与焉”[13](P129)。《五臧山经》即是记述各山所蕴含宝藏的一本书。“五臧”之“臧”,同“藏”,作“储藏”义解[14](P3642),“五臧”即五山所以蕴藏,五山之宝藏。*如李丰楙解释“五臧”云:“所谓‘五藏’,就是山海天地之藏——山海的富藏,天地的宝藏。”参见李丰楙:《山海经:神话的故乡》,时报文化出版事业公司1982年版,第21页。在《五臧山经》中,各山普遍有其所生所藏,然而,丰沃贫瘠不同,因之,既有“万物无不有焉”的积石之山,亦有“尽沙也,无草木鸟兽”的白沙山,而大部分被记述之山就是处于这两种极端之间的地域。即使是那些被记述为无草、无木、无鸟、无兽的地区,仍然可见记述者由“有”、“无”来思考山所生藏。在《五臧山经》每一条以山聚类的记述中,又有常见之物、罕见之物乃至变怪之物,它们是分布在常、异两端之间的纷繁物类,其记述又显出常异分述的特点。《五臧山经》在记常物与异物时,又各有其记述的程式。
(一)“其……”:记常物的程式化记述
在《五臧山经》中,记常物主要采用指示位置、种类、数量的程式化记述,并以记物之种类、名称为主。其例如下:












这类只出现物类名称者,应为记述者乃至同时期人所熟悉,或是日常生活经验乃至理性认识所及,因此,并未就其性状、功能加以补述。某些类别下所罗列之物类非仅一项,而是数项归为一类,研究者即指出其中已有依照相似性而归属为同一类的现象。*如丁永辉研究《山海经》之植物分类,即指其划分植物之类型是依据其形态、气态、习性、功用方面的相似性而分。详见丁永辉:《〈山海经〉与古代植物分类》,载《自然科学史研究》1993年第3期。在上举例子中可见,记常物之记述组合,可以是记山之上下的“其上”、“其下”,或是主要记水域之中的“其中”,亦可以是记山之方位的“其阴”、“其阳”,乃至记类别的“其草”、“其木”、“其鸟”、“其兽”,以及记数量的“多……”、“无……”,凡此属于“其……”的记述类型会集中成群记述,是以山为中心坐标,而见其上下四方空间所生藏之物类。这类“其……”的记述类型是《五臧山经》用以记常物而使用的程式化记述。
(二)“有某焉”:记异物的程式化记述
相对于记常物只记物类名称,采用“其……”的记述类型,又有详记物类之性状、名称、功能的“有某焉”,所记以罕见之物、变怪之物为主,是与常物相对的异物。《五臧山经》中,这类“有某焉”的记述如下:属于植物类的“有草焉”24条,“有木焉”19条;动物类的“有鸟焉”46条,“有兽焉”84条,“有蛇焉”3条,“有鱼焉”3条;矿物类的“有石焉”2条。就种类之整体而言,动物类最多,植物类次之,矿物类最少。动物类以“有兽焉”之记述数量最多,植物类则以“有草焉”之记述数量最多。各山经出现“有某焉”的记述,则以《中山经》所记数量最多,共计55条。相关数量统计见表1:
表1《五臧山经》中各山经“有某焉”的记述

类别山经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东山经中山经合计植物动物矿物有草焉16001724有木焉24121019有鸟焉616133846有兽焉111722151984有蛇焉012003有鱼焉101103有石焉010012合计2145392155
“有某焉”的记述,后续接以“其状……”、“其鸣……”、“其味……”、“其名(曰)……”等关于物类之性状、名称的说明,最末则是物类之功能的说明。其例如下:

又西七十里,曰羭次之山,漆水出焉,北流注于渭。其上多棫、橿,其下多竹、箭,其阴多赤铜,其阳多婴垣之玉。有兽焉,其状如禺而长臂,善投,其名曰。有鸟焉,其状如枭,人面而一足,曰橐,冬见夏蛰,服之不畏雷。[1](P26)
又北二百里,曰潘侯之山,其上多松、柏,其下多榛、楛,其阳多玉,其阴多铁。有兽焉,其状如牛,而四节生毛,名曰旄牛。[1](P75)
又东五十二里,曰放皋之山。明水出焉,南流注于伊水,其中多苍玉。有木焉,其叶如槐,黄华而不实,其名曰蒙木,服之不惑。有兽焉,其状如蜂,枝尾而反舌,善呼,其名曰文文。[1](P144)

又南三百里,曰景山,……其上多草、藷藇,其草多秦椒,其阴多赭,其阳多玉。有鸟焉,其状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名曰酸与,其鸣自詨,见则其邑有恐。[1](P89)

若所记罕见之物或变怪之物数量非一,就不完全采用“有某焉”的记述,而是运用记常物使用的指示位置、种类、数量的记述文字,再加上“有某焉”记述的性状、名称与功能,其例如下:
其中多玄龟,其状如龟而鸟首虺尾,其名曰旋龟,其音如判木,佩之不聋,可以为底。[1](P3)

其鸟多寓,状如鼠而鸟翼,其音如羊,可以御兵。[1](P70)
其中多珠蟞鱼,其状如肺而有目,六足有珠,其味酸甘,食之无疠。[1](P106)
由此可见,《五臧山经》对于记异物有其一定的叙述规律。
(三)常异分述
常物与异物皆为山之所臧,既有一般常见的金、石、草、木、鸟、兽、虫、鳞,亦有居于常与异之间的珍稀罕见之物,如今仍可见乎青藏高原的牦牛,或是太湖中富产之“鮆鱼”*据郭璞注:“鮆鱼狭薄而长头,大者尺余,太湖中今饶之,一名刀鱼。”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里仁书局1995年版,第12页。,当然也有更偏向“异”一端的变怪之物,如结合多种物类者,如“其状马身而鸟翼,人面蛇尾”的“孰湖”,或是器官数量异于常者,如“其状如鸡而赤毛,三尾、六足、四首,其音如鹊”的“鯈鱼”。在此由常到异的两端之间,就排列分布着常、异比例浓淡不一的各种生命存在。在以山聚类的记述中,当兼有常物与异物时,其记述就显现出常异分述的特点。亦即,在以山为中心所构成的体系化记述中,较具普遍性而为人熟悉之物类,主要使用指示位置、种类、数量的“其……”之记述形成一记述集群,是依物所在之山、位置、种类、数量等原则而记述。“其……”之“其”,指的即是所记述之某山,因之,重点在山有何臧,以历述山所蕴藏为若干云云为主;而属于异物一端的罕见之物与变怪之物,则采用“有某焉”的记述而自成一记述集群,明显以物为其记述主题,物类本身之性状、名称与功能成为记述重点。
四、博物之山:辨物与用物
《五臧山经》所载丰赡富丽的“物”记述,在汉世已为人所知,更被视为能使人“见物博”[10](P598)之书。在这之中,又以“有某焉”一类记述所记之罕见之物、变怪之物最引人注目,此亦为《山海经》一书备受负评的主要原因。如司马迁即对此书所载怪物采取“弗敢言之”的态度,班固亦直接以“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放哉”[15](P2705)评之,王充更以太史公“弗敢言之”乃“谓之虚也”[10](P476)。这些对《山海经》“虚妄之言”的批评,皆是针对书中所记之异物与怪物而发。而《五臧山经》中对怪物与异物的记载不同于记常物的“多……”与“无……”或是“其……”的方式,而大多是采用“有某焉”的叙述方式,特别标出山中的异物。若抛开儒家“不语怪力乱神”的理性思维,《五臧山经》中“有某焉”的记载,其背后乃是古人面对未知宇宙的一种观物、辨物乃至于知物的系统思维,而这种思维方式即鲜明地表现在古代博物君子的辨物活动中。
《五臧山经》中“有某焉”的记述重点在于标明罕见之物、变怪之物的性状、名称与功能,而这又与古代博物君子的辨物活动有若干相符之处。《五臧山经》中“有某焉”的记述是关乎辨物与用物的文字记述。以下即对此进一步分析阐释之。
(一)辨物:性状、名称、功能
《五臧山经》中对于罕见之物、变怪之物,多以“有某焉”的方式记述,以物类为其主体,记其性状、名称、功能。其例可见表2:
表2《五臧山经》中以“有某焉”方式记述之物类性状、名称、功能

分类种属性状名称功能地点出处植物有草焉其状如韭而青华其名曰祝余食之不饥招摇之山南山经有草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名曰薰草佩之可以已疠浮山西山经有草焉其叶如葵而赤茎,其秀如禾名曰鬼草服之不忧牛首之山中山经有木焉其状如谷,而黑理,其华四照其名曰迷谷佩之不迷招摇之山南山经有木焉其状如棠,而员叶赤实,实大如木瓜名曰櫰木食之多力中曲之山西山经有木焉其叶如柳而赤理湖灌之山北山经有木焉其状如杨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实其名曰芑可以服马东始之山东山经有木焉叶状如樗而赤实名曰亢木食之不蛊浮戏之山中山经动物有鸟焉其状如鸠,其音若呵名曰灌灌佩之不惑青丘之山南山经有鸟焉其状如翟而赤……是食鱼,其音如录名曰胜遇见则其国大水玉山西山经有鸟焉其状如蛇,而四翼、六目、三足…其鸣自詨名曰酸与见则其邑有恐景山北山经有鸟焉其状如凫而鼠尾,善登木其名曰絜钩见则其国多疫山东山经有鸟焉其状如鹊,青身白喙,白目白尾……其鸣自叫名曰青耕可以御疫堇理之山中山经有兽焉其状如马而白首,其文如虎而赤尾,其音如谣其名曰鹿蜀佩之宜子孙杻阳之山南山经有兽焉其状如猿,而白首赤足名曰朱厌见则大兵小次山西山经有兽焉其状如貆而赤豪,其音如榴榴名曰孟槐可以御凶谯明之山北山经有兽焉其状如牛而虎文,其音如钦……其鸣自叫其名曰軨軨见则天下大水空桑之山东山经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首虎爪名曰梁渠见则其国有大兵历石之山中山经有蛇焉六足四翼名曰肥虹遗见则天下大旱太华之山西山经有蛇一首两身名曰肥遗见则其国大旱浑夕之山北山经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其音如留牛……冬死而夏生其名曰鯥食之无肿疾柢山南山经有父之鱼其状如鲋鱼,鱼首而彘身食之已呕留水北山经有鱼焉其状如鲤,而六足鸟尾……其名自叫名曰鮯鮯之鱼跂踵山东山经矿物有白石焉其名曰礜可以毒鼠皐涂之山西山经有石焉五色而文,其状如鹑卵,帝台之石,所以祷百神者也名曰帝台之棋服之不蛊苦山中山经
由表2所举各山经所载“有某焉”记述可见,从植物、动物到矿物的“物”记述,几乎不离性状、名称、功能此三大要素,语序排列先述性状,次标名称,再言其功能。《五臧山经》对于异物、怪物的认识,不离开对其性状、名称与功能之掌握。此种叙述形成《五臧山经》关于异物、怪物知识的系统性说明与载录。此种对异物、怪物知识的载录、说明,其背后正隐含着一套时人面对纷陈多样的自然宇宙的对应方式与态度解释。
面对令人感到疑惑、惊惶的神、人、物等未知物,除了消极的畏惧、避逃外,另一种积极的态度,则是寻求解答,掌握其形貌状态,进而能为我所用,而提供此一生冷知识的即是古代的博识者。刘向《说苑·辨物》载有以下两则叙事:
楚昭王渡江,有物大如斗,直触王舟,止于舟中。昭王大怪之,使聘问孔子。孔子曰:“此名萍实,令剖而食之。惟霸者能获之,此吉祥也。”其后齐有飞鸟,一足,来下,止于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又使聘问孔子。孔子曰:“此名商羊,急告民,趣治沟渠,天将大雨。”于是如之,天果大雨,诸国皆水,齐独以安。[16](P465)
虢公梦在庙,有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立在西阿。公惧而走,神曰:“无走!帝今日使晋袭于尔门。”公拜顿首。觉,召史嚚占之。嚚曰:“如君之言,则蓐收也,天之罚神也。天事官成。”[16](P466)
第一则述楚昭王渡江遇异物,齐侯遇异鸟;第二则述虢公梦神。面对这种无所知悉的现象,在未知其所从来,未知其名称,乃至未知其善恶的情况下,人会感到疑惑、奇怪,如上引例中楚昭王与齐侯皆“大怪之”,或有强烈防卫心理,遂因恐惧而生避逃,如虢公于梦中见“人面白毛虎爪,执钺”之神,遂“惧而走”。再如《墨子·明鬼下》载:“昔者郑穆公,当昼日中处乎庙,有神入门而左,鸟身,素服三绝,面状正方。郑穆公见之,乃恐惧,奔。”[17](P332)除此疑惑畏避之心理与行为外,另外即是透过耳目直接观听所遇对象可见之声貌,人会根据已有知识而对来至眼前的陌生、怪异的现象进行观察与描述。在上引的文献数据中,用以描述萍实的“有物大如斗”以及描述蓐收神“人面白毛虎爪,执钺”等例,其中,如斗、白毛、虎爪,所执为何云云,即是根据人已有的知识而对观察对象显现于外的形貌状态进行辨认,在无法对观察对象进行整体掌握的情况下,至少运用已有知识把握观察对象可辨识的部分特征。
楚昭王使聘问孔子,虢公请史嚚占,作为解答者,他们显然比一般人握有更多属于正常、理性的认识范围之外的知识。如孔子辨大如斗之物为萍实,并指:“惟霸者能获之,此吉祥也”,辨一足之飞鸟为商羊,并以此为“天将大雨”之兆;史嚚辨“人面白毛虎爪,执钺”之神为蓐收,并指为“天之罚神”。他们不仅能知其性状,还能进一步知其名称、功能。这类因博览、博物而能为众解惑者,虽然有假托人物以立说的色彩,然而,他们却代表着古代文化知识体系中存在的博览之人与博物君子。面对这类超乎平常的现象,他们以指迷破盲的角色出现于这些场合中,而他们对疑惑众人之观察对象的性状、名称与功能加以辨识与区分的行为,即是古代文化语境中的辨物活动。
刘歆《上〈山海经〉表》将《山海经》定位为一部可以提供辨物、知物知识的论著。其中载有东方朔辨异鸟和刘向辨异人的叙事,见前文。
东汉王充《论衡·别通》亦载有董仲舒、刘子政能知晓异物之事:
董仲舒睹重常之鸟,刘子政晓贰负之尸,皆见《山海经》,故能立二事之说。[10](P598)
根据刘歆《上〈山海经〉表》所述,东方朔识异鸟,一则“言其鸟名”,二则“言其所当食”。刘子政辨异人,亦是就“反缚盗械”此外显之状,而与经文载贰负“桎其右足,反缚两手”相符,而指此异人为贰负之臣。在东方朔与刘向辨异人、异物的活动中,一则辨异物或异人之习性、外形,一则指出异物或异人之名称,由此而解开群众之疑惑,两人所为即是同于前述博物君子的辨物活动。这些记载显示出《山海经》能使人“见物博”之特点,汉人亦是以此实用角度而将《山海经》视为博物书籍而读学,期望从中获得辨识与区分那些令人陌生与怪异现象的能力与知识。
东方朔辨异鸟之名与所当食,刘子政晓贰负之尸即是类似于孔子、史嚚等人的辨物活动。这类辨物活动的观察与辨识要点即在观察对象之性状、名称与功能。这几项要点并不是在每一辨物活动中皆具足,有时只涉及辨识观察对象之性状与名称,并未言及功能如何,如东方朔辨异鸟、刘向辨异人之例即是如此。面对众人“何以知之”的询问,东方朔言“即《山海经》所出也”,刘向“亦以《山海经》对”,而这又透露出《山海经》可提供二人辨异人与异物所需的知识。在《山海经》中,与此异物认知活动最密切者,即是《五臧山经》的“有某焉”记述,它们与古代辨物活动之间有着相似性,两者皆以物类之性状、名称与功能为观察重点。辨物是针对对象物的辨识与确认,辨明其性状、名称与功能,只是在今日《五臧山经》的文本中,“有某焉”记述则已失去了辨物活动所存在的整体场景与言说语境,而简化成一条条文字记述被保存下来。《五臧山经》的“有某焉”记述,就是一种辨物记述,它以观察对象之性状、名称与功能为记述重点,就是一种在书面上进行的辨物活动。
(二)用物:善与恶
在本文所分的三种记述类型中,还有一类总校群山祠礼的记述,是关于祭山祠礼的相关说明,它多以“凡……之首,自……山至(于)……山,凡……山,……里,其神状……,其祠……”呈现。其例如下:
凡《西次三经》之首,崇吾之山至于翼望之山,凡二十三山,六千七百四十四里。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其祠之礼,用一吉玉瘗,糈用稷米。[1](P58)
凡萯山之首,自敖岸之山至于和山,凡五山,四百四十里。其祠:泰逢、熏池、武罗皆一牡羊副,婴用吉玉。其二神用一雄鸡瘗之,糈用稌。[1](P128~129)
此类总校群山祠礼的记述所划定的山群与道里范围乃适用于同一祠礼祭法,除了《东次三经》末尾可能因文有脱阙而未有神状及祠物的记载外*《东次四经》末尾则少此神状及祠物的记录,袁珂疑文有脱阙,参见袁珂:《山海经校注》,里仁书局1995年版,第116页。,其余属同山群之末尾皆有之。《礼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民所取财用也。”
由是,山林、川谷、丘陵亦在祀典之列。总校群山祠礼的记述,附于各山群记述完毕之末尾,即是对能够供人取用的有臧之山的祭祀与礼敬。《五臧山经》的明标山川道里方位与述明物之位置、种类、质量、功能,及总校群山祠礼等三种记述类型,恰好呼应了古人对山林、川谷、丘陵所怀有的见其所臧、知其所用,从而祀之的认识角度。
取用,即是从所取之对象如何与人类世界发生关联着眼,对人有利益者为善,对人有损伤者为恶,刘歆在《上〈山海经〉表》中即拈出“类物善恶”为《山海经》之作书目的,而在《山海经》全书中,与物之善、恶相关记述,又主要出现在《五臧山经》中“有某焉”记述末尾关于物类功能之说明。关于物类之用,有征兆性功能、医疗性功能、巫术性功能及日常性功能四类。带有征兆性功能者,往往是物类出现于人间,就有预示人间吉凶之征兆。其例如下:
有兽焉,其状如豚,有距,其音如狗吠,其名曰狸力,见则其县多土功。[1](P8)
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采文,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1](P35)
是有大蛇,赤首白身,其音如牛,见则其邑大旱。[1](P98)
有兽焉,其状如夸父而彘毛,其音如呼,见则天下大水。[1](P103)
有兽焉,其状如蝯,赤目、赤喙、黄身,名曰雍和,见则国有大恐。[1](P165)
又有医疗性功能者,需藉由食用、服佩而预防或治疗身体疾病。其例如下:
有鱼焉,其状如牛,陵居,蛇尾有翼,其羽在魼下,其音如留牛,其名曰鯥,冬死而夏生,食之无肿疾。[1](P4)
有草焉,其名曰黄雚,其状如樗,其叶如麻,白华而赤实,其状如赭,浴之已疥,又可以已胕。[1](P25)
有草焉,名曰薰草,麻叶而方茎,赤华而黑实,臭如蘼芜,佩之可以已疠。[1](P26)

有木焉,其状如杨,赤华,其实如枣而无核,其味酸甘,食之不疟。[1](P113)
又有巫术性功能者,经由食用或服佩、豢养而达到超自然的神秘功效。其例如下:
有草焉,其叶如蕙,其本如桔梗,黑华而不实,名曰蓇蓉,食之使人无子。[1](P28)
有鸟焉,其状如枭而白首,其名曰黄鸟,其鸣自詨,食之不妒。[1](P91)
有兽焉,其状如狸,而白尾有鬣,名曰朏朏,养之可以已忧。[1](P120)
有木焉,叶状如樗而赤实,名曰亢木,食之不蛊。[1](P148)
又有日常性功能者,其例如下:
有白石焉,其名曰礜,可以毒鼠。[1](P30)
有草焉,其状如槀茇,其叶如葵而赤背,名曰无条,可以毒鼠。[1](P30)
有木焉,其状如杨而赤理,其汁如血,不实,其名曰芑,可以服马。[1](P114)
有木焉,其状如棠而赤叶,名曰芒草,可以毒鱼。[1](P123)
这类征兆性功能、医疗性功能、巫术性功能及日常性功能等说明,是关于用物的记述。无论是罕见之物或变怪之物,关于用物的记述正说明,物类之所以为人所认识,除了性状、名称外,最重要的是它如何与人类世界发生关系,而这种关系的建立与认识角度是从对人有利与有害着眼,从而由此分出善物与恶物。用物既是对物类功能之描述,同时,也是一种从人类与物类相互间的利害关系所建立的物的认识观。《五臧山经》终篇以“禹曰”总结:
天下名山,经五千三百七十山,六万四千五十六里,居地也。言其五臧,盖其余小山甚众,不足记云。天地之东西二万八千里,南北二万六千里,出水之山者八千里,受水者八千里,出铜之山四百六十七,出铁之山三千六百九十。此天地之所分壤树谷也,戈矛之所发也,刀铩之所起也,能者有余,拙者不足。封于太山,禅于梁父,七十二家,得失之数,皆在此内,是谓国用。[1](P179~180)
此段文字亦见于《管子·地数》。清代郝懿行指出:“今案自禹曰以下,盖皆周人相传旧语。”但不论此段叙述为周人相传旧语,抑或是《五臧山经》记述者本来所述,综观《五臧山经》之记述,仍可见山之所臧乃有其用,是相沿已久的物的认识观,对于物之功能的记述即可见《五臧山经》之记述者对此用物观的承续与重视。
五方之山,每山各有其臧与用,臧有常、异之分,用有善、恶之别,见其所臧,辨其性状、名称、功能,而后能用之,从而祠礼之。常/异乃就物之性状区分,善/恶乃就物之功能区分,彼此又可配搭组成四种对物的认识观:有益于人的常物、有益于人的异物、有害于人的常物、有害于人的异物。《五臧山经》就在以山聚类、常异分述、善恶有别的记述原则中,形成一个平常自然与怪奇谲丽兼而有之的记物与辨物体系。以山聚类与常异分述的记述特点,使《五臧山经》显出其记物之博,而辨物与用物又显现出它识物之博。五方之山,既是万物生藏之山,供人取用之山,同时也是多识金、石、草、木、鸟、兽、虫、鳞的博物之山。
五、结语:“虚妄之言”与博物知识
在《山海经》一书中,《五臧山经》以丰赡富丽的“物”记述构成其主要内容,这使它一方面被誉为“见物博”之书,另一方面,亦因其中的“祯祥变怪之物”而招来“虚妄之言”的批评,这两种意见在《山海经》的流播史上经常是并行存在的。王充即同时持有这两种看法,他对太史公“至《禹本纪》、《山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一段论评继续加以引申,以司马迁“弗敢言之”乃“谓之虚也”,并云:“案太史公之言,《山经》、《禹纪》,虚妄之言。”[10](P476)这种评价虽踵步司马迁,但却可发现,他所说的“虚妄”乃是相对于“真实”之评,亦即,以《山经》为“虚妄之言”,乃是在太史公“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的传统史学思考脉络与张骞“使大夏,穷河源”的地理征实经验上,质疑《山经》、《禹纪》关于昆仑山上有醴泉、瑶池的叙述所建立起的批评。然而,若就《五臧山经》所记载的物的知识体系而视之,它也是古人所面对的众多知识类型之一,这是王充一方面以之为“虚妄之言”,一方面又肯定“董、刘不读《山海经》,不能定二疑”[10](P598)的原因。因为,在博览的知识视域中,“虚妄之言”可以是另一种类型的知识。博览可以启明,烛照人类因未知所生的智识闇盲。王充即说:“人不博览者,不闻古今,不见事类,不知然否,犹目盲、耳聋、鼻癕者也。”[10](P591)并以日光为喻而说明知识启蒙人智之作用:
日光不能照幽,凿窗启牖,以助户明也。夫一经之说,犹日明也;助以传书,犹窗牖也。百家之言,令人晓明,非徒窗牖之开,日光之照也。是故日光照室内,道术明胸中。[10](P593)
人对经典或书籍的阅读接触,就似把日光引入屋室内部的经验,书籍所蕴含的智慧就似日光,一经之传,就像是开窗牖而引入屋内的亮光,而博览百家之说则是日处室中,光照四隅,正所谓“日光照室内,道术明胸中”。从王充之言可知,博览就像是一把汇聚百家之说而燃烧的火炬,可为人类智识幽闇处带进炽然照耀的光明,而《山海经》也是在这种思想脉络中被王充所识见。他说:“《山海》之造,见物博也”,并说:“使禹、益行地不远,不能作《山海经》;董、刘不读《山海经》,不能定二疑”。《山海经》即是东方朔、刘向、董仲舒等博物君子所以通明博见、所以定疑的知识来源之一,而《五臧山经》就是这种博物知识本身。
《五臧山经》所载物的知识,特别是怪物与异物的部分,在理性、征实的眼光看来,自然有其闳诞迂阔之处,但有趣的是,一旦人们在平常、理性的世界中因遭逢异鸟、异人而感到迷惑不解时,藉以寻求解答的知识来源却是如《山海经》一类的书籍。我们对于出现于古代文献数据中的辨物记载,自然不能未经思辨地就把它当作曾经真实发生过的历史,也就是说,对于它是否真为历史事实可以存疑。然而,从传世文献所记看来,至少从先秦两汉以来,如史嚚、东方朔、刘向的博物君子代有其人,记载于史料文献中的辨物活动可能并非史实,而有假托人物以立说的色彩,但在辨物活动中,面对无法以理性认识之怪物、异物,根据已有的知识以辨其性状、名称、功能,却是自然的行为反应。史实容或有疑,但此类行为确有存在于古代文化语境的可能性,它们也许就代表着古代一部分人心目中的“真事实”或实际的生活经验。*顾颉刚认为,《山经》所载怪物、神祇,当然为理性所不信,但这批被视为怪诞之说,却也可能代表着“作者心目中之真事实”。参见顾颉刚:《〈五臧山经〉试探》,载北京大学潜社编印:《史学论丛》(第一册),国立北京大学潜社1934年版,第4页。而蒲慕州研究春秋战国时代之民间信仰亦指出,使用史料文献要注意有时其中所载的人物对话很可能是作者的编造,亦即,是作者根据一些事后的记载或是他对当时情况的了解和想象而重建的结果,然而,另一方面,宗教经验和鬼神信仰,虽则今人视为无稽,但对古人而言,却是实际的生活经验,而它们也是一种历史事实。参见蒲慕州:《追寻一己之福:中国古代的信仰世界》,麦田出版社2004年版,第66~67页。
面对未知,人会冀望寻求解答或至少弄清楚自己所面对、遭遇的事物究竟为何,在这种由未知迈向已知的过程中,被视为“虚妄之言”的《山海经》又以它蕴含着与正常、真实、理性相对,而属于非常、虚构、非理性的博物知识而提供了解释权。在“问朔何以知之,即《山海经》所出也”、“诏问(向)何以知之,亦以《山海经》对”,就说明在此实用功能取向下的《山海经》,甚至上升为“皆圣贤之遗事,古文之著明者也。其事质明有信”[1](P477)的知识高度,其中就透露出《山海经》如何被汉人接受与定位的信息。
原先为人所“弗敢言之”的边缘异端,就在人们对眼前的异事、异物因长时期的“不语”、“弗敢言之”而导致的失语境况中成为经典。对于《山海经》的“经”,郝懿行笺疏云:“经,言禹所经过也。”[7](P282)袁珂认为:“乃‘经历’之‘经’,意谓山海之所经,初非有‘经典’之义。”[1](P181)叶舒宪则认为:“地理之书,多以经名。”[18](P120)今日重读《山海经》,我们也即是在“经典”与“经历”的两种视域交汇中接触这本古今第一奇书,透过眼目以“经”山川道里,而在这种“目经”的阅读行旅中,在一条接连一条“物”记述的书面翻阅中,一点一点地感知它跨越千载的经典价值,又仿佛在这种“目经”中,再经一番启识照明,而让光亮透进既有认知视域的暗蔽边荒。郭璞在《注〈山海经〉叙》中曾说:
夫以宇宙之寥廓,羣生之纷纭,阴阳之煦蒸,万殊之区分,精气浑淆,自相濆薄,游魂灵怪,触象而构,流形于山川,丽状于木石者,恶可胜言乎?[1](P478)
在这段说明中,我们不难见出郭璞对《山海经》载述物类之纷繁所怀有的惊艳赞叹之情。由今以视古,郭璞注《山海经》那如许时光终究是远了,然而,今时此刻,捧读神游其间,人之所知,莫知其所不知之感,却也有几分仍然近于郭璞当时所言。
[1]袁珂.山海经校注[M].台北:里仁书局,1995.
[2]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三十二)[M].上海:上海书局出版社,2009.
[3]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第142卷)[M].台北:汉京文化事业公司,1981.
[4]鲁迅.鲁迅小说史论文集——中国小说史略及其他[M].台北:里仁书局,2006.
[5]郑德坤.《山海经》及其神话[J].史学年报,1932(4).
[6]文清阁.历代山海经文献集成(第7卷)[M].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6.
[7]郝懿行.山海经笺疏[M].台北:艺文印书馆,2009.
[8]马昌仪.古本山海经图说[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9](日)泷川龟太郎.史记会注考证[M].台北:洪氏出版社,1981.
[10]黄晖.论衡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
[11]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93.
[12]尔雅(卷7)[M].台北:艺文印书馆,1981.
[13]赖炎元.韩诗外传今注今译(卷3)[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
[14]台湾中华书局《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中册)[Z].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80.
[15]班固.汉书[M].台北:鼎文书局,1986.
[16]向宗鲁.说苑校证[M].北京:中华书局,1987.
[17]吴毓江.墨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8]叶舒宪,等.山海经的文化寻踪:“想象地理学”与东西文化碰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
特约编辑 孙正国
责任编辑 强琛E-mail:qiangchen42@163.comMountains and Objects:Describing “Objects” ofTheClassicofMountainsandSeas·FiveZangShanjing
Gao LifenXie Xiuhui
(DepartmentofChineseLiterature,NationalChengchiUniversity,Taibei11605)
TheClassicofMountainsandSeas·FiveZangShanjing(hereinafter referred to asFiveZangShanjing) divided into Nanshan Jing,Xishan Jing,Beishan Jing,Dongshan Jing,and Zhongshan Jing,the main contents of describing objects are composed of the gold,stone,grass,wood,bird,beast,worm,and loong. InFiveZangShanjingthere are three stylized narrative methods,such as “marking the direction of the mountains and rivers”,“describing the location,type,quality,function of the objects”,and “proofreading the total mountains temple ceremony”,the formation of its text into a system showing a unique regularity. Mountains of the five party have their own “Zang”,then “Zang” has its “Yong”. “Zang” divided into “general” and “difference”,“Yong” divided into “good” and “evil”,the differences between “describing profoundly objects” and “identifying objects” reflected in the describing “objects” ofFiveZangShanjing. Describing principles conclude “mountain clustering”,“distinguishing general and difference” and “differences between good and evil”,which form a natural and strange beautiful system of “describing objects” and “identifying objects ”.
The Classic of Mountains and Seas;Five Zang Shanjing;describing profoundly objects;identifying objects;gods
2016-07-10
台湾“科技部”补助专题研究计划(MOST 103-2410-H-004-139-MY2)
高莉芬,女,教授,主要从事神话学与文学人类学研究。
B932
A
1673-1395 (2016)08-0001-12
编者按:
中国神话学的百年学术史,从多个视角切入,可以发现丰富多样的方法论模型与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想。进入21世纪,神话学研究的多样性与转型特征十分显著。基于此,本刊与中国神话学会商议,自2015年1月起,计划用两年的时间,较为系统、深入地考察当代中国神话学的20位代表学者,每期刊发两篇论文:一篇是代表学者的最新研究成果,一篇是对代表学者神话学研究的综述与批评。期望以代表学者的学术思想来构拟中国神话学的当代形态,思考中国神话学的当代问题与未来走向,建立起古典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本土文化逻辑,进而为中国文化转型的良性发展,贡献中国神话学的理论与智慧。本期特推出高莉芬教授和谢秀卉博士《山与物:〈山海经·五臧山经〉“物”记述》及鹿忆鹿教授《原型的探求:高莉芬的神话研究述评》,敬请学界关注并惠赐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