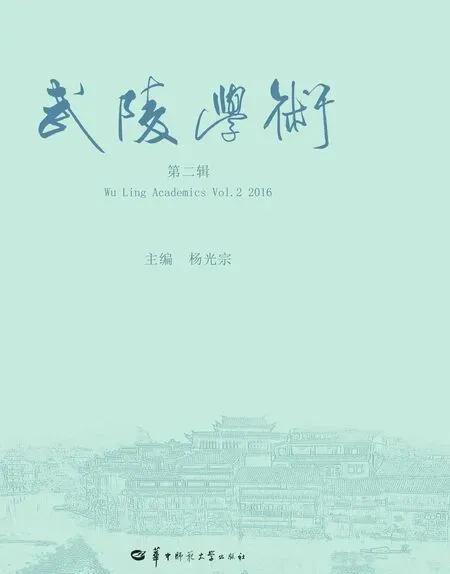《礼记子本疏义》残卷校读札记
陈云豪
(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 湖北恩施 445000)
《礼记子本疏义》残卷校读札记
陈云豪
(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湖北恩施445000)
日本早稻田大学所藏《礼记子本疏义》残卷,为唐初或唐以前的古抄本,至晚在8世纪已传日本并为日本皇家所收藏。虽然只残存455行,但文献价值极高。文章先就该写本的命名进行了疏理,次就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经籍志》中的校改问题略作商议,再就此书在史志目录中著录出现的歧异现象进行了考证,最后选取本写卷部分内容进行了校读。
《礼记子本疏义》目录学校勘
《礼记子本疏义》残卷,仅存卷第五十九,现藏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尾题“丧服小记子本疏义第五十九”,并有“内家私印”朱印一方斜盖于“丧服小记”四字之上。“此乃八世纪光明皇后所用之印,则此本传入日本,时代极为古远。明治时代归田中光显伯爵收藏。后由田中氏惠赠早稻田大学”*严绍璗:《日本藏汉籍国宝钩沉(二)》,《中国典籍与文化》,1994第1期,第116—120页。。全卷455行,首行残缺数字。据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著录,全卷长642.5厘米,宽28.5厘米。
一、 命名的探讨
关于此卷何以称为“子本疏义”,前人多有讨论。首先,“疏义”大体同于“义疏”,如严绍璗先生云:“九世纪藤原佐世于《本朝见在书目录》中,著录《礼记子本义疏》百卷,署‘梁国子祭酒皇侃撰’。此处题‘义疏’与此本尾题‘疏义’,意义大约相同。”而岛田翰认为“疏义”比“义疏”更好,其文云:“《隋、唐志》之作‘义疏’、‘讲疏’,当依此本订其误矣。而《隋志》少一卷,是不加算目录也。但灼师皇侃作《论语疏》,亦名‘义疏’,盖依佛书名也。然当是作子本已与常名异,恐以‘疏义’为正。”*岛田翰:《汉籍善本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2年,第77页。关于为何称“子本”,主要有四种看法,或云“别本”,或云“经注”,或云“示谦”,而桥本秀美则认为是一种注疏体式。这四种观点,又可以大体分为两类。一类主区别说,如孙诒让云,“‘子本’之名,他书未见,疑即灼所题,以别于皇疏原本者。‘子本’犹‘别本’云尔”。 胡玉缙的看法和罗振玉相近,认为“‘子本’二字,殆即灼以之为区别以示谦”。一类主注疏说,如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古文旧书考》即《汉籍善本考》。云“而其题曰‘子本’犹曰‘经注’也”。桥本秀美在其博士学位论文《南北朝至初唐义疏学研究》中认为:
至“子本”之名,盖据此书钞写体例而言。义疏之为书,本皆单行,不具经注。……即赵宋刻本犹为单行,所谓单疏是也。然今此卷经注具备,不可不谓此书特例。书写体式,每录经注一小段,下空一格直接写其疏;其无疏,则竟录经注。如此则疏文紧从在所释经注之下,犹子之从母也。……此书名“子本”,岂非谓以经注为本,疏义为子,分章断句,事类相从之意?今既破胡说,且为推测如此,然固无确证,亦不敢定论也。
综观以上诸家之说,本文以为桥本秀美所说“其名为《子本疏义》,盖因其合写经注之故,非为内容有异于皇侃原书也”,堪为定论。
二、 对点校本《隋志》的订正
今中华书局点校本《隋书·经籍志》有“《礼记讲疏》九十九卷,皇侃撰。《礼记义疏》四十八卷,皇侃撰”。《隋志》校勘记称据《两唐志》、《梁书·武帝本纪》、《经典释文叙录》改。而百衲本景元大德刻本作“《礼记义疏》九十九卷,皇侃撰。《礼记讲疏》四十八卷,皇侃撰”。据此卷,则疑当以百衲本作“《礼记义疏》九十九卷”为是。
孙诒让、胡玉缙、罗振玉和岛田翰几乎一致认为此残卷为梁陈时期的郑灼钞录其师皇侃之《礼记》疏,而增益己说而成*吴承仕《经典释文叙录疏证》亦持此说,其文曰:“今日本藏旧写《丧服小记》残卷中有‘灼案’之文,陈有郑灼,皇氏之徒,此之写本盖郑氏敷衍师说以为讲疏者也。”。如罗振玉《六朝写本礼记子本疏义残卷跋》曰:“则此卷者,郑灼所钞之义疏,而‘灼案’诸条则灼钞时所增益也。传言灼钞义疏不言钞何人所作,今验此卷参以历代史志所记,确知所钞为皇侃义疏。”
今天著录此卷时或题郑灼撰,或题皇侃撰。岛田翰即主张应该题郑灼之名,并认为《隋志》所载“《礼记义疏》九十九卷”当题灼名,而误题侃名。如其题跋云:“《礼记子本疏义》,陈郑灼所撰。”又在补记中称“惟卷中有‘灼案’、‘灼谓’、‘灼又疑’等之语,而灼之案语悉为释义断案,尝疑本书非皇侃所撰,必为名灼者所制。止据《丧服小记》,即居《戴记》之半,而本书卷尾之题第五十九,与隋唐诸志皇侃《礼义疏》一百卷者相符,姑从俗称以为皇氏之撰”。根据《陈书·儒林传》及《隋志》“《礼记义疏》九十九卷,《礼记讲疏》四十八卷”,岛田翰进一步推论,“侃之《礼疏》实为重录。意者《讲疏》即侃之作,《义疏》即当是郑灼撰之误矣”。并认为,《隋志》误将郑灼《礼记义疏》九十九卷题皇侃之名,从而导致了积误相承。“盖隋唐之际,流俗认灼书误题侃名,而长孙无忌则未及推论之也。《唐志》、《见在书目》之误,则《隋志》实作之俑也。”胡玉缙认为“是书塙为灼撰,今仍阙其姓名,以示慎焉”。本文认为,此卷题侃名,灼名皆可,如前文所述,此写卷为灼增益其师之作而成。但其所增益的究竟是“《礼记义疏》”,还是“《礼记讲疏》”,则仍需讨论。
皇侃关于《礼记》方面的著作至少有两种,一名讲疏,一名义疏,或约百卷*本文百卷与九十九卷不加区别,五十卷与四十八卷亦不加区别。罗振玉云:“隋志别出九十九卷(自注:九十九卷殆即百卷,古人箸书例有序篇在卷末,九十九卷者,除序篇言之耳)。”,或约五十卷。而郑灼“以日继夜”所抄之《义疏》,根据前文所引岛田翰之推论,显然应该是百卷本的《礼记义疏》。百卷本除《隋志》外,计有《日本国见在书目录》(作“礼记子本义疏百卷。梁国子助教皇侃撰”)、《旧唐书·经籍志》(作“《礼记讲疏》一百卷”)、《新唐书·艺文志》(作“皇侃《礼记讲疏》一百卷”)和《通志·艺文略》(作“《礼记讲疏》*据中华书局点校本《通志·二十略》,此本据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将“讲疏”、“义疏”互换,和中华书局本《隋志》著录相同。而四库本、浙江书局本皆作“《礼记义疏》九十九卷,皇侃;《礼记讲疏》四十八卷,皇侃”。 (见(宋)郑樵撰,王树民点校:《通志二十略》,中华书局,2009年。)九十九卷”)等文献著录。而五十卷本,除《隋志》外,则有《经典释文叙录》、《梁书·武帝本纪》(并作“《礼记义疏》五十卷”)、《梁书·皇侃传》(作“《礼记讲疏》五十卷”)、《旧唐书·经籍志》(作“《礼记义疏》五十卷”)、《新唐书·艺文志》(作“《义疏》五十卷”)和《通志·艺文略》(作“《礼记义疏》四十八卷”)等文献著录。结合以上文献分析,似乎百卷本为《讲疏》,五十卷本为《义疏》。但此卷尾题“丧服小记子本疏义第五十九”则证明郑灼所钞正是皇侃《礼记义疏》或《礼记疏义》,而不是《讲疏》。孙诒让也认为“《隋志》所载之皇氏《礼记义疏》有二部,其九十九卷者,即此本。藤原氏《日本国见在书目》著录,称《礼记子本义疏》百卷,为并目录数之。其考证颇详塙”。由此,《隋志》所载皇侃《礼记》疏仍当作“《礼记义疏》九十九卷,《礼记讲疏》四十八卷”。至于皇侃《礼记》疏,后世何以会出现“讲疏”与“义疏”,“百卷”与“五十卷”,互相抵牾的情况,则下文再试作分析。
三、 钞写时代与卷数的分析
关于《礼记子本疏义》的成书时代,没有什么疑问,只要考察皇侃(488—545年)、郑灼(513—581年)二人的生平就可以知道。《梁书·武帝本纪》载,大同四年(538年)“冬十二月丁亥,兼国子助教皇侃表上所撰《礼记义疏》五十卷”。 罗振玉云:“卷中不避陈、隋、唐诸帝讳,灼卒于陈而在梁已官西省。其家贫,写书殆当梁世。”则郑灼撰《礼记子本疏义》大约在皇侃献书之后,入陈以前,也就是成书时代约在538年至558年之间。但对于此写卷是六朝写卷,还是唐写卷则有不同看法。罗振玉认为“必不在宦成之后,则此卷者或即灼所手书耶”?罗振玉甚至在1916年11月16日给王国维的信中说“《礼记子本疏义》弟考为郑灼手抄本,似甚确,不知先生以为何如”*虞坤林编:《王国维在一九一六》,山西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182页。。而岛田翰则认为钞写者为8世纪的日本学者,其文曰:“笔者其在于天平宝字(元年为757年)、神护景云(767—770年)之间乎?……是书今虽不知出于谁手,笔力沉着,字体谨严,波撇之末,咸有法度。妙妙不可思义,非学唐人者,决不能。”桥本秀美则进一步细考讳字,发现此卷不仅以“长”代“衍”,避梁武帝讳,且以“前”代“先”,避陈武帝讳,认为“此卷钞写当在陈以后,或谓唐初钞本,未必为误”。
前文所引《梁书·武帝本纪》“《礼记义疏》五十卷”,《梁书·皇侃传》则作“礼记讲疏五十卷”,两处皆记“书成献上”的史实,则当指同一书而言。而《梁书》不载皇侃有百卷之《礼记》疏。而史志目录中,称为《礼记讲疏》者仅有一种,即皇侃所撰之书。而名为《礼记义疏》者仅《隋志》就有四种,其一为刘宋雷肃之撰,至《隋志》以前已亡。其二为皇侃的老师贺玚所作《礼记新义疏》。其三为皇侃所作,其四为梁武帝撰。疑《梁书》所载两书实为一书,“讲疏”,“义疏”同义,仅在《隋志》中经子两部皆有讲疏和义疏。盖皇侃所作仅有《礼记义疏》五十卷。而此《礼记义疏》仅有皇氏义疏,不含《礼记》白文与郑玄注文,故仅有五十卷。经文、注文与义疏之关系,如同今日教师所用教本与讲义。诚如桥本秀美所言“义疏之为书,本皆单行,不具经注。是以徐遵明‘每临讲座,必持经执疏,然后敷陈’,即赵宋刻本犹为单行,所谓单疏是也。然今此卷经注具备,不可不谓此书特例”*桥本秀美:《南北朝至初唐义疏学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96页。。又,《梁书·皇侃传》载皇侃献《礼记讲疏》后不久就“召入寿光殿,讲《礼记义》,高祖善之”。离其去世有六七年时间,皇侃自己或许有所增益。皇侃去世后,其弟子郑灼再将经注与义疏合钞,篇幅必然增多,或即增为百卷亦未可知。而《皇侃传》称“《礼记讲疏》五十卷,书成,奏上,诏付秘阁”,可知皇侃于大同四年所献之书,一直藏于秘阁,不再变化。而皇侃手中的《礼记讲疏》五十卷,则由皇侃传于郑灼,在民间流传,变成了百卷本。至修《隋志》时,长孙无忌等人既能见到秘阁保存之《礼记讲疏》五十卷,又能见到民间一直流传的《礼记义疏》一百卷,不计卷末序篇则为九十九卷,故《隋志》兼录两书。而“义疏”与“讲疏”于义本无区别,故《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皆著录两书,而卷数相反。实则一为单疏本,五十卷,一为注疏合钞本,一百卷。
四、 校读记
以下据早稻田大学图书馆公开之《礼记子本疏义》照片,节录开头部分,试为分段标点,以作分析。取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礼记正义》为参校本,文中简称《正义》。阮元《校勘记》简称《校勘记》。录文以[ ]示补文,以( )表删字。

“堂下之位时则异矣”,《正义》作“至拜宾竟后,子往即堂下之位时则异矣”。“□□发至成服”《正义》作“而成服”。“”,《正义》作“免”。《释文》:“免,音汶,篇内同。” 本卷下文《皇侃》:“名为,免者,也。”又《仪礼·士丧礼》“众主人免于房”*“众主人免于房”,《原本玉篇残卷》“”字条引此作“众主人于房”。。《郑注》:“今文‘免’皆作‘’。”下同,不复出校。
母服轻,至免可以布代麻也。为母,哭而免。
此为郑玄注,《正义》与此卷同。
又哭即是小敛拜宾竟后,即堂下位哭踊时也。或问曰:“为父括发至成服,其中二敛之祭应有冠弁,而括发除而犹括发乎?”崔云:“为父括发一作以至成服,若应冠弁临祭,则于括发上着之也。括发本为丧变,非代冠者故也。”崔又云:“大夫以上尸袭后,而孝子素弁,素弁乃素冠,以其绖日。故《檀弓》‘叔孙武叔,小敛出户,投冠’是也。若士丧日浅小敛前不冠也。”
此一段《正义》仅取“又哭即是小敛拜宾竟后,即堂下位哭踊时也”一句。
灼案,前儒悉云“冠弁临祭”故其然矣。崔言袭后而冠弁复与小记异,何者?案礼无冠弁临祭者也。《杂记》云:“小敛环绖公士大夫一也。”《丧大记》云:“君将大敛,子弁绖则不云临祭”,又云“将敛则非始死,袭后而冠弁矣。《檀弓》已释然,括上有冠此,则随人通耳”。
以上为郑灼按语。《正义》不取。
齐衰,恶笄,以终丧。
《校勘记》:“闽、监、毛本同,石经同,岳本同,嘉靖本同,卫氏《集说》同。《考文》引古本,足利本‘齐衰’下有‘带’字。按注云‘笄所以卷发,带所以持身’,先释‘笄’后释‘带’,是脱‘带’字,不当在‘恶笄’之上。《正义》亦云:‘此一经明齐衰,妇人笄带终丧无变之制。’亦先‘笄’,后言‘带’,是皆‘恶笄’下有‘带’字确证,段玉裁是也。《正义》出经文,此句二见,并脱‘带’字,亦当补。按段玉裁又云:《仪礼·丧服》‘布总箭笄’疏引《丧服小记》云‘妇人带恶笄以终丧’,有‘带’字,而在‘恶笄’之上,是各本不同也。”桥本秀美云:“此卷经文正无‘带’字,皇侃特释经无‘带’字而注连言带之义,可知段、王二家俱失。”*桥本秀美:《南北朝至初唐义疏学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97页。
前明男子为父,此明女子为母也。为父故据男为说,说其初丧之礼。为母故以女为论,论其成服之法也。此服乃多,今主谓女子在室为母也。恶笄者,榛木为笄也。妇人质,笄以卷发,带以持身,于其自卷持者,有除无变,故腰绖及笄不绖受易,至服竟一除,故云要笄终丧也。
“前明”至“为母也”,《正义》无。“恶笄”至“不绖受易”,《正义》作“‘恶笄’者,榛木为笄也。妇人质,笄以卷发,带以持身,于其自卷持者,有除无变,故要绖及笄,不须更易”。钞本“不绖受易”当为“不须更易”形近之讹。
笄所以卷发,带所以持身也。妇人质,于丧所以自卷持者,有除无变。
艳言带耳
按,上一行郑玄注,《正义》同。“艳言带耳”四字,《正义》无,虽无“灼案”二字,当为郑灼所加,其义不可解。
男子冠而妇人笄
因妇人有终丧之笄,故此以下明男女冠笄恒相对也。吉时男子有冠,则女子吉笄也。若亲始死,男去冠,女去笄,若成服为父,男则六升布为冠,女则箭筱为笄。若为母,男则七升布为冠,女则榛木为笄。故云男冠妇笄也。
按,经文“男子冠而妇人笄”之下为皇侃疏,与《正义》大体相同。《正义》作:“此明男子、妇人冠笄,髽免相对之节。但吉时男子首有吉冠,则女首有吉笄,是明男女首饰之异,故云‘男子冠而妇人笄’也。若亲始死,男去冠,女则去笄。若成服,为父,男则六升布为冠,女则箭筱为笄。为母,男则七升布为冠,女则榛木为笄。故云‘男子冠而妇人笄’也。”
男子免而妇人髽
此一段皇侃疏文,不见于《正义》。
此段皇侃疏文见于《正义》。“乃异”《正义》作“有异”。“而同”《正义》无“而”字。“所以谓髽者,妇人着之则髽,髽可憎因为名耳”一句不见于《正义》。“男子之俛”《正义》作“男子之免”,据前文《皇疏》:“若男去冠而,则妇人去笄而髽,故云男俛妇髽也”,当以“免()”为是,且“男俛妇髽”亦当作“男妇髽”。写卷之“俛”当为“”之形讹。“以对男括发时”据《正义》当作“以对男子括发时”。“《丧服》云”《正义》无“云”字。
此段见于《正义》。“郑云”《正义》作“郑玄云”。“括发用麻”《正义》作“括发以麻”,写卷下文用“以麻者”,则“以”字近是。“故言”《正义》作“故云”。“不辩括发形殊”《正义》作“不辨括发形异”。“以对男括[发]”据《正义》补“发”字。


此段见于《正义》。“对[冠]”、“[有]着笄者”两处“冠”、“有”二字皆据《正义》补。

庾云:“丧服往往寄异以明义,或疑免、髽亦有其旨,故解之以其义。止于男子则免,妇人则免,妇人则髽,独以别男女而已,非别有义也。贺玚云:“男去冠,犹妇人去笄,义尽于此,无复别义,故云其义也。”
此段皇疏见于《正义》。“庾云”《正义》作“庾蔚云”。“止”《正义》作“以上”。《校勘记》:“闽、监、毛本同。卢文弨校云‘以上’‘以’字疑衍,‘上’当作‘止’。按卫氏《集说》‘以上’作‘言’。”今写卷正作“止”,可证卢校甚确。
此为郑灼案语,不为《正义》所取。
通过以上比刊,则《正义》对《皇疏》的去取之迹,可得一斑。大体十取八九,或原文照录,或省并文句,或改换说法,或删其冗句。
五、 写卷价值之评价
关于此写卷的价值,前人题跋之中已多有论述。如岛田翰以其“六朝名人诸说,仅藉此以存”称其为“旷代之奇”。孙诒让认为“其所援引马融、王肃、刘智、蔡谟、庾蔚之、贺玚、崔灵恩佚说甚多,尤足宝贵”。胡玉缙通过持此卷与经典比勘,认定此卷“可称一字千金矣”。此类“各本皆误,独赖此卷足以订正”(胡玉缙语)的情况,只要细加比刊,还能发现许多。如桥本秀美发现“齐衰恶笄以终丧”本无“带”字,见前文校读记。又云“礼,不王不禘”注:“禘,谓祭天。”当作“禘谓郊天”,今此卷正作“郊天”*桥本秀美:《南北朝至初唐义疏学研究》,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1999年,第97页。。如《礼记正义》云“以上于男子则免”阮元引卢文弨校语谓“以上”当作“上”,今此卷正作“止”,详见前文校读记部分。以上为辑佚与校勘价值。在目录学方面,如前文所述,此卷也可以证明《隋志》“《礼记义疏》九十九卷”之说无误,亦可对《两唐志》皇侃《礼记疏》著录相互矛盾的情况提供分析的角度。总之,此残卷虽仅存450余行,仅一万多字,但在校勘、辑佚乃至目录、版本学的价值是极高的。
陈云豪(1983—),男,湖北鹤峰人,土家族,北京大学文学博士,湖北民族学院文学与传媒学院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