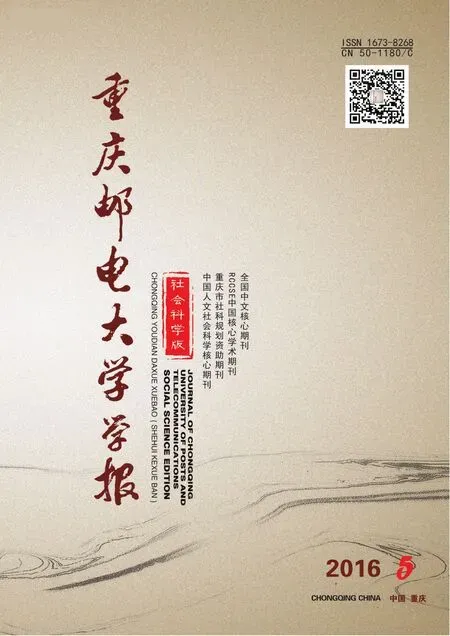网络诽谤行为的法律问题研究
袁辉霞

网络诽谤行为的法律问题研究
袁辉霞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 401120)
诽谤与网络的结合使得网络诽谤行为具有不同于传统诽谤行为的特征。应根据网络诽谤的基本特征,厘清网络诽谤治理需处理的三个基本问题:网络诽谤之公诉与自诉的平衡问题,网络诽谤之言论自由与网络诽谤的平衡问题,网络诽谤之责任追究问题。追究网络诽谤行为的法律责任应对针对普通公民的诽谤和针对公权力主体的诽谤两种情况进行区分。公民的名誉权受法律保护,是言论自由的不可逾越的红线。无论行为人是故意还是过失,均应承担法律责任。针对公权力主体的网络诽谤行为,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应避免报复性惩处现象。网络诽谤信息的发布者、网络诽谤信息的传播者、网络平台管理者是直接责任主体。在责任追究过程中,应合理区分三个直接责任主体的社会危害程度。
网络诽谤;言论自由;法律责任
一、问题的提出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空间和网络社会逐步形成,呈现出“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并存的“双层社会结构”。网络社会独立于现实社会,但其结果又反馈于现实社会。毋庸置疑,网络社会给人们带来了巨大便利,人们可足不出户通过网络尽可实现购物、娱乐等要求,但其同时也带来了一些危险,这些危险滋生于网络空间之中,网络空间为其提供了孕育的温床,而离开了网络,这些危险将不复存在。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在网络上随意捏造事实、恶意损害他人名誉的网络诽谤行为。根据我国《刑法》第246条,传统诽谤罪是指捏造事实诽谤他人,情节严重的方才构成诽谤罪,除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外,属于告诉才处理的犯罪。而网络诽谤固然有传统诽谤罪的基本特征如捏造事实、散布消息等,但由于与网络平台的结合,因而有其独特性,具体表现如下:(1)低门槛性。行为人只要会上网皆可通过网络发布诽谤信息,成本较低;(2)传播速度快。目前人们可通过各种网络平台如微博、微信、QQ空间等,在极短的时间内可使数以万计的人们知晓,例如2013年的王菲、李亚鹏离婚事件;(3)网络诽谤中被告的隐匿性。在网络平台中,大部分都是以匿名方式发布信息,即使行为人就在被害人身旁,也难以发现行为人的身份,在网络诽谤中,传统诽谤罪要求的被害人自诉几乎不可能;(4)网络诽谤中出现组织化、集团化倾向。在现实中出现一些网络公关公司,也就是通常人们所说的网络水军,其打着网络公关的名号,实质上却是接受雇主委托,捏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他人名誉。例如,“中国代骂旗舰网”曾在网上大肆招揽代骂生意“并称可以提供职业骂手,通过各种手段用下流语言对他人进行诽谤和攻击”[1];(5)损失的不可弥补性。网络传播具有无限复制性和延展性,被害人几乎没有解释的机会或者解释毫无意义,被害人的损失根本得不到弥补。例如农夫山泉砒霜门事件、网络公关损害伊利商誉事件等,虽后来受害人对以上事件进行澄清,但给消费者所带来的心里阴影已无法消除,公司名誉也难以回复如初。鉴于网络诽谤的这些独特特征,将现实社会中诽谤罪概念引入网络社会,是无法实现维护网络秩序、达到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民目的的。
随着网络社会的逐步兴起,其被赋予了更多的民主属性。针对网络言论而言,网络言论正是宪法视域下言论自由的延伸和拓展,是民众表达意愿的重要途径。一方面,通过网络,人民的民意可不加删减直接通往执政者,避免了民意在过去逐级上报中所出现的层层过滤现象;另一方面,网络也是公民行使批评建议权、监督权的重要平台,在反腐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近年来发生的“房叔”“表叔”“房婶”事件。但在现实中表现的却是公权力机关滥用权力以网络诽谤行为打击过激言论的监督者,例如2012年陈平福发贴被捕案、2013年张家川微博少年因言获罪案。而当一些不法行为人利用网络诽谤他人,侵害普通公民名誉时却得不到救济。根据有关学者的调查显示,在2003年至2012年普通网络诽谤案件样本中,在网络诽谤行为人法律责任承担方式中,未承担法律责任的案件数最多,民事责任次之,刑事责任则较少[2]。因此,可以说同样的网络诽谤案件,仅因为针对对象的不同,导致案件结果迥异。如何使“诽谤”不至于沦为公权力机关打击公民舆论监督权的工具,以及有效平衡言论自由与网络诽谤之间的关系,将成为治理网络诽谤的关键问题。
在法律责任的承担上,毋庸置疑,网络诽谤信息的发布者应该承担责任,但是跟帖者以及网络管理者的责任应如何界定呢?网民往往具有较高的跟帖意向,例如新闻《美越联合声明谈及南海问题:外交解决纠纷》全文仅170字,共获得了380 985次点击,4 220条跟帖,即90.28次点击便产生一条跟帖评论[3],如此高的跟帖比例应如何界定跟帖者的责任呢?针对网络管理者而言,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负责网络的基础设施服务,保障网络的正常运行,但他们也是网络诽谤传播状况的最佳知情者,当网络诽谤事件已经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时,其是否有责任暂时封闭该信息的传播或者当被害人要求停止传播时,是否有停止的义务呢?另外,应注意一种特殊情形,若网络诽谤是基于受害人炒作目的并由受害人授权下实施的,此时应如何追究网络诽谤制造者、传播者以及网络管理者的责任呢?
综上,笔者认为在分析网络诽谤案件时必须解决以下三个问题:一是如何根据网络诽谤的特点,实现公诉与自诉的平衡问题;二是网络言论自由与网络诽谤之间的平衡问题;三是网络诽谤的责任追究问题。
二、网络诽谤之公诉与自诉的平衡
根据《刑法》246条之规定,普通诽谤罪原则上是自诉的,只有在“但书”(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况下方可公诉。但网络诽谤在何种情形下属于网络诽谤中的“但书”呢?2013年9月,最高检和最高法共同发布了《关于办理利用信息网络实施诽谤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该《解释》第3条从行为的影响、后果和危险程度三方面对网络诽谤行为的入罪标准作了细化和限定,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了网络诽谤行为入罪的三种具体标准: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 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造成被害人或者其近亲属精神失常、自残、自杀等严重后果的;二年内曾因诽谤受过行政处罚,又诽谤他人的[4]。
但笔者认为,此种标准设置是不合理的,其忽视了网络诽谤最基本的特征——诽谤发布者的隐匿性以及网络诽谤损失的不可弥补性。如果网络诽谤没有达到上述标准,被害人在不明确侵害人的前提下,根本没有自诉机会。因为在现实中,一方面,大部分被害人没有充足的资源和能力调查侵害人;另一方面,鉴于网络传播速度极快,在介入公诉之前,被害人的损失已经不可弥补,即使后来达到公诉标准,受害人也无法得到合理救济。所以在某种程度上可认为,此规定是对标准以下网络诽谤行为的放任。
刑罚的目的在于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行政处罚的目的在于维护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保护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刑法具有作为保障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偏重于制裁,行政法则具有过程性控制的作用,偏重于预防损失。“刑事不法行为在质上显然具有较深度的伦理内容与社会伦理的非难性,而且在量上具有较高度的损害性与社会危险性;相对地,行政不法行为在质上具有较低的伦理可责性,或者不具有社会伦理的非难内容,而且它在量上并不具有重大的损害性与社会危险性”[5]。反映到网络诽谤上,应既要重视刑法的最后威慑作用,又要注重行政对于损失的预防性控制。而要对网络诽谤行为实施行政控制,必须要证成的是公诉以前网络诽谤行为的行政不法性。基于我国相关法律规定,行政处罚所针对的行为一般是违反公共场所秩序的行为。而公共场所是公众工作、学习、经济、文化、社交、娱乐、体育、参观、医疗、卫生、休息、旅游和满足部分生活需求所使用的一切公用场所及其设施的总称。在当前“双层社会”背景下,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人们的“第二空间”,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人们通过网络可以满足现实生活中的一切需要[6]。因此,网络秩序属于公共秩序的组成部分。当然,并非所有网络空间都属于公共场所,正如现实社会中也并非所有空间都属于公共场所一样。例如“微信”,其只是朋友之间的信息传递工具,具有一定的封闭性,不属于网络公共场所。而微博则属于开放性空间,任何人皆可发贴、评论,则可认定为网络公共场所。综上,笔者认为网络社会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和拓展,两者密不可分,应立足于现实中的社会运行规则,并根据网络社会自身特点对规则予以补充和发展以适应网络发展的需要。
具体到网络诽谤,笔者认为,首先,行政机关可主动介入到公诉标准以下的网络诽谤行为。我国可仿效英国,行政机关可发布禁止令。在出现比较恶劣的网络诽谤行为时,发布禁止令责令网络管理者停止在该平台上传播该信息,以避免损失的进一步扩大。其次,2000年发布的《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明确规定,对扰乱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谣言,电子公告服务提供者有权立即删除,并保存有关记录,向国家有关机关报告。此规定对于防止网络诽谤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其属于部门规章,法律位阶较低,而“删除”意味着对公民言论自由的剥夺。根据我国《立法法》第8条规定,对于公民政治权利的剥夺应由法律规定,言论自由属于公民基本政治权利的组成部分。所以,对“删除”的规定应上升到法律层面。但笔者认为“删除”并非是对谣言处理的最佳选择。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而言,其针对“谣言”的价值判断并不客观、准确,往往带有浓厚的主观倾向,并不是最佳判断者。最佳的选择是当网络服务提供者发现带有危害社会秩序、破坏社会稳定的谣言时,应暂停该信息的传播并做好信息记录,及时通报给行政机关,由行政机关作出判断。最后,为保障被害人的诉权,应立足于网络诽谤行为人不可知性的基本特征,行政机关在得到有关被害人的网络诽谤信息后,进行处罚之前,应及时将该信息通报给被害人,由被害人决定是否提起自诉,当被害人决定不提起自诉时,方可进行行政处罚。
三、网络诽谤与言论自由的平衡
言论自由属于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一个国家的言论开放程度是衡量该国民主程度的重要标准。正如有学者所说,“民主的社会是一个讲话的社会”[7],“在一个社会中把言论自由限制到什么程度,也就在同样程度上限制了民主”[8]。而网络言论呢?笔者认为,网络言论自由是言论自由的组成部分,正如上文所说,网络言论是宪法视域下言论自由的延伸和拓展。因此在针对网络诽谤的治理中,面临着公民个人名誉权的保护与言论自由的平衡问题。但从目前针对大部分网络诽谤案件的处理情况来看,大部分公民对公权力机关强行介入持批评态度,这也使得公权力机关在处理网络舆论案件时遭受越来越多的压力。主要原因在于公权力机关为保障其权威滥用权力,诽谤罪沦为公权力主体打击对其异议的普通公民的工具,保护个人名誉权成为公权力主体打击公民言论自由的“幌子”。例如河南“王帅案”、内蒙古“吴保全案”等,都是当举报政府的违法行为失实时,判定行为人犯诽谤罪。那么应如何实现两者之间的平衡呢?
笔者认为,言论自由与名誉权都是公民权利的重要组成部分,两者并不存在矛盾和冲突,更不能对其中任何一方有所舍弃。对言论自由而言,其并非是毫无边际的自由,任何自由都应有所限制。密尔曾将言论自由的条件限制为“不要超出公平讨论的界限”,既一个人的言论不得对其他处于平等地位的主体权利有所侵犯。但若是处于不平等地位的两个主体之间,为保障两者之间的平衡,处于弱势主体的言论自由会有所放大,其可能针对强势主体提出一些正当或者不正当的言论,公权力主体则有责任虚心听取乃至接纳网民正当或者不正当的言论。并且公权力主体未必有不可挽回之损失,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首先,即使政府机构受到错误指责,一般不会给它履行法定职能带来严重的影响,也不会造成经济损失,不存在什么精神损失;其次,公权力主体有能力有条件回击不实的言论,有机会通过行动澄清人们的认识[9]。当然,公权力主体的名誉权与言论自由都是公共利益的要求,针对公权力主体的言论也并非是毫无限制的,应保持在合理的限度以内。综上,本文认为有必要对网络诽谤对象做如下区分:对普通公民的诽谤;对公权力主体的诽谤。
首先,针对普通公民的网络诽谤而言,言论自由与公民个人名誉权是均衡的。公民言论自由不得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这是言论自由的权利界限。如果超越了该界限,导致受害人社会评价降低,行为人就应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受害人可主动提起民事侵权诉讼,若损害后果比较严重,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可主动介入,制止该行为并对其进行处罚。
其次,针对公权力主体的网络诽谤,行政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应避免过多干涉。对于公民所散发的批评性言论不能盲目地定性为网络诽谤。当然,若诽谤行为给作为行政主体的当事人带来损害,导致其社会评价严重降低,则可按照网络诽谤中针对普通公民的诽谤行为处理。对公权力主体避免过多干涉并非是不干涉,对该行为认定为诽谤罪必须有严格的限制。笔者认为应主要包含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1)行为人主观上具有恶意,必须证实行为人在发布诽谤消息时具有丑化政府形象,扰乱公共秩序的故意。正如美国著名大法官奥利弗·霍姆斯所说:“对言论自由最严格的保护,也不可能保护在剧院里谎呼失火而引起恐慌的人。哪怕仅仅说一些可能导致暴力结果的话也不能得到保护。”[10](2)行为人所实施的客观行为造成了危害结果。其可参照《解释》第3条认定危害结果的标准:引发群体性事件的;引发公共秩序混乱的;引发民族、宗教冲突的;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的;造成恶劣国际影响的。第3条中的兜底性条款“其他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国家利益的情形”则主要是指损害地方政府形象,影响地方招商引资等情形。只有主客观相互一致,才可对针对公权力机关的网络诽谤行为认定为诽谤罪。
在此,还需对另一问题作出说明:公民的名誉权是否可以放弃?在现实中,不乏存在一些人为炒作自己,允许他人诽谤,进而提高其知名度的情况。对于此种行为应如何界定呢?根据我国《宪法》第38条之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对公民进行侮辱、诽谤和诬告陷害。”《民法通则》第101条规定:“公民、法人享有名誉权,公民的人格尊严受法律保护,禁止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公民、法人的名誉。”由此可知,名誉权属于公民的法定权利,具有强烈的人身属性,是不可放弃的。当行为人故意在网上散发诽谤自身的言论时,若造成严重的社会影响(可参照《解释》规定),公权力主体应主动介入,发出禁止令并可对其实施行政处罚。若造成网络秩序严重混乱的,可按寻衅滋事罪处理[11]。若是行为人委托网络公关公司对自己实施诽谤行为时,网络公关公司得到了行为人的授权,且对象是行为人自身,主观恶性相对较低,不宜对其实施刑罚,但行政机关应按照社会危害程度对其实施行政处罚。
四、网络诽谤之责任追究
针对网络诽谤行为的责任追究有两种模式:以德、韩为代表的严厉刑罚防控模式和以英美为代表的整体趋轻的刑法防控模式[12]。前者注重网络诽谤的专门立法,以刑罚为主要惩治手段,后者则给予言论自由较高的保障,在美国还确立了诽谤的“实际恶意原则”,总体上对网络诽谤行为采取“除罪化”的态度。笔者认为,以上两种责任追究模式都构筑于各国国情基础之上,在该国具有积极作用。例如美国历来都比较注重言论自由。我国针对网络诽谤的责任追究机制同样需筑基于我国的国情之上,既不能畸重也不能畸轻,而应适合我国的网络发展。从我国网络诽谤行为的形成发展上看,主要涉及三方行为主体:网络诽谤信息的发布者、网络诽谤信息的传播者和网络平台管理者,有必要区分三种行为主体的社会危害程度来追究责任。
(一)网络诽谤信息发布者
网络诽谤信息的发布者是违法犯罪性行为的根源,一般情况下,其应当对自身的行为承担责任。网络诽谤信息的发布行为是指行为人捏造信息并通过自媒体的方式进行发布和传播。当然,信息制造者和信息发布者可能出现分离的状况,但是诽谤是一种严格责任,并不区分故意和过失,只要发布错误就已经形成,就应追究发布者的责任,只是责任追究程度的不同。对主观上“过失”的发布者而言,可能由受害人追究民事赔偿责任或者行政责任,对主观上“故意”的发布者,则可追究其刑事责任。
针对网络诽谤信息的发布者,还可做进一步分类:作为普通公民的网络诽谤信息的发布者和作为网络公关公司的网络诽谤信息的发布者。对前者,按照损失程度的不同可追究其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根据针对对象的不同可按诽谤罪、损害商业信誉罪处理。对后者,由于网络公关公司(俗称“网络水军”)发展的异化,其实施的诽谤行为有较强的隐秘性、组织性和社会危害性,可称其为“职业加害人”。笔者认为,网络公关公司已构成《刑法》第26条规定的犯罪集团。理由如下:一般网络公关公司人数达到三人以上;其犯罪公司组织比较固定,具有明显的首要分子并在其领导下形成统一的组织形式和纪律;其实施的行为一般都是有组织有预谋的实施犯罪行为。另外,该行为还形成了刑法中罪名之间的竞合,网络公关公司实施一般的诽谤行为可构成一般的诽谤罪或者损害商业信誉罪,但是其非法经营互联网业务,已构成《刑法》第225条的非法经营罪。综上,对“网络水军”可按非法经营罪,并对其按总则中的犯罪集团追究,对首要分子从重处罚。
(二)网络诽谤信息传播者
网络诽谤信息的传播者虽然并非诽谤信息的直接制造者,但其每一次转发都相当于信息的再次发布,并且基于人理性的有限性,大部分人会对社会上一些敏感信息加以分享。调查统计表明,近70%的被调查者凭借自己的经验与感觉判断网络内容的真实性,而62.5%的人则会把网络上新奇或有趣的内容进行转发与他人分享[13]。作为一般人而言,人们普遍对诽谤信息的认识程度不够,主观恶性不足。所以,笔者认为不应对网络诽谤信息的传播者实施处罚。当然,若传播者恶意转发甚至在进一步夸大的基础上进行转发,则需追究责任。
(三)网络平台管理者
网络平台管理者一般是网络诽谤信息的最知情者,根据2000年发布的《互联网电子公告服务管理规定》,其有权对破坏社会稳定的信息进行删除,并保存相关记录,向行政机关报告。所以,当发现网络诽谤信息时,网络平台管理者有权力也有义务及时封锁该信息,若网络平台管理者对已造成恶劣社会影响的信息不及时封闭或者放任信该息的传播时,行政机关可对其实施行政处罚,情节严重的可追究刑事责任。当然,鉴于网络管理者认识的有限性,立法者可设置网络管理者封锁信息的标准,其可参照《解释》第2条第1款的规定,即:同一诽谤信息实际被点击、浏览次数达到5 000次以上,或者被转发次数达到500次以上的,网络管理者就有权封锁该消息、禁止该消息的传播。另外,若受害人在网上发现有关诽谤自己的网络信息时,有权通知网络平台管理者,要求在其平台上停止该消息的传播,若网络平台管理者不及时处理,受害人可要求网络平台管理者对其承担民事连带责任。
[1]徐盛楠.专业代码公司在各地现身[N].南方周末,2015- 09- 08(10).
[2]于冲.网络诽谤行为的实证分析与刑法应对——以10年来100个网络诽谤案例为样本[J].法学,2013(7):149.
[3]唐红,王怀春.网络新闻跟帖评论的特点及功能[EB/OL].(2012- 02-14)[2015- 07-13].http://media.people.com.cn/GB/192301/192359/192362/17111115.html.[4]赵秉志,袁彬.网络诽谤入罪标准的细化科学合理[N].检察日报,2013- 09-18(3).
[5]陈兴良.论行政处罚与刑罚处罚的关系[J].中国法学,1992(4):26.
[6]于志刚.“双层社会”中传统刑法的适用空间——以“两高”《网络诽谤解释》的发布为背景[J].法学,2013(10):106.
[7]约翰·弥尔顿.论出版自由[M].吴之椿,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45.
[8]科恩.论民主[M].聂崇信,朱秀贤,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170-171.
[9]侯建.舆论监督与政府机构的“名誉权”[J].法律科学,2001(6):53-55.
[10] 哈罗德·伯曼.美国法律讲话[M].陈若桓,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120.
[11] 骆琼.网络诽谤、寻衅滋事司法解释之评析[J].重庆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43-49.
[12] 于冲.网络诽谤刑法处置模式的体系化思考——以网络水军为切入点[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2(3):47- 48.
[13] 赵远.网络诽谤的刑事责任问题研究[J].中国刑事法杂志,2010(8):68.
(编辑:刘仲秋)
Study on Legal Liability of Internet Defamation
YUAN Huixia
(SouthwestUniversityofPoliticalScience&Law,Chongqing401120,China)
The combination of libel and Internet makes the network libel different from the traditional libel behavior. At present, it is necessary to clarify three basic issues of the need to deal with the treatment of network defamation based on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twork defamation. The first problem is the balance of network defamations of the public and private prosecutions. The second is the balance of free speech and Internet defamation. The third problem is the responsibility of network defamation investigation. Network defamation against ordinary citizens or public power body should be different to legal liability. Citizen’s reputation is protected by law. Freedom of expression can't infringe upon citizen’s reputation. Whether intentional or negligent, the infringer shall bear legal responsibility. Administrative or judicial organs should avoid from vindictive punishment when the network defamation object is the public power body. Network defamation information publishers, defamatory information platform for the disseminator, and the network manager are all directly responsible. It is necessary to differentiate the social harm of three direct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process of responsibility.
network defamation; freedom of speech; legal liability
10.3969/j.issn.1673- 8268.2016.05.009
2015-10-27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我国信息网络安全现状及其治理法治化研究(2015YBFX099);重庆市教育委员会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大数据时代的个人信息安全与法律应对(14SKF04)
袁辉霞(1981-),男,四川阆中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行政法、信息规制研究。
D924.3;D915.1
A
1673- 8268(2016)05- 0050-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