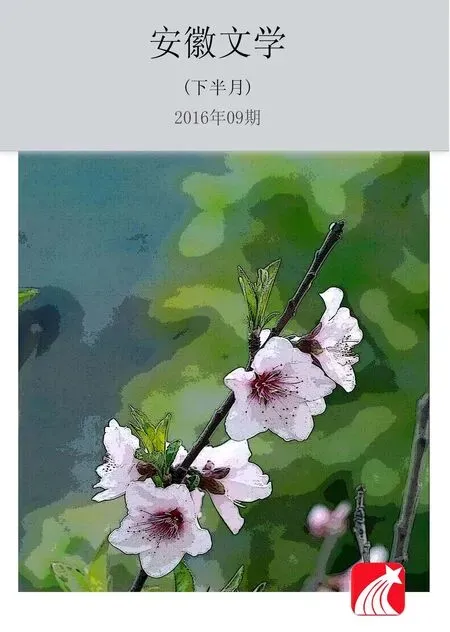论《暗店街》中“追寻”的寓意
朱林染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论《暗店街》中“追寻”的寓意
朱林染
河南大学附属中学
《暗店街》以主人公的“追寻”为线索,将过去、现在和将来连为一体。无论是过去的逃离、现在的寻访,还是将来的漂泊,“我”都处于“无根”的困境,这既是个体面临的生存状态,也是二战时期法国的状态,更是人类永恒的体验。
《暗店街》追寻 无根
《暗店街》是帕特里克·莫迪亚诺的长篇小说,讲述了患有遗忘症的私家侦探助理“我”试图找回真实身份的故事,它以“追寻”为线索,既捕捉到了二战法国被占领期间普通人的命运,又“唤醒了对最不可捉摸的人类命运的记忆”①过去、现在和将来,“我”一直在“追寻”。现在的“追寻”基于自我身份的迷失;十年前的“追寻”是为“逃离”德占的法国;最后没有结局,“我”还在“追寻”。整个小说像一座迷宫,任何一个信息都将“我”引向新的未知。“我”是谁,“我”从哪里来?一切都在变动不安中。
一、追寻:“总有一天你将寻回你的过去”
十年前当“我”突然患了遗忘症,于特给了“我”一个身份“居依·罗朗”。其实,遗忘过去的不只是“我”,还有于特和战时受了心灵创伤的无数人。于特本是网球运动员,英俊、一头金发的波罗里海男爵康斯坦丁·冯·于特,现在成了筋疲力尽的退休私人侦探C·M·于特。于特鼓励“我”同时觉得“我”是徒劳:“我一直相信总有一天你将寻回你的过去。……我在考虑是否真值得这样做。”②这种无根状态,莫迪亚诺也有深刻体会:“我对自己的‘根’十分珍视,这只为我所有。”③遗忘症暗示了身份的遗失,米兰·昆德拉曾说,“忘”是“自我丧失似的死亡。但是这个自我是什么呢?它是我们所记得的一切的总和。因此,我们对死亡感到恐怖的不是丧失未来,而是丧失过去。遗忘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死亡形式。”④为寻回被遗忘的身份,“我”开始了追寻。
“我”走访过许多地点,却从一个未知到另一个未知:阿纳托尔-德拉弗日街的酒吧、阿夫雷市的餐馆、克洛德·洛兰街俄罗斯东正教教堂、希尔顿饭店……;“我”结识了各种人:俄国流亡者、酒吧老板、饭店钢琴演奏师、美食专栏编辑、城堡花匠……;随着脚步行进,“我”的身份也在不断变化:让·厄尔特回忆说,“我”是夜总会“夜游神中间的一个”(第10页);在斯蒂奥帕给“我”看的旧照片上,“我”是俄国侨民乔吉亚泽及其孙女身边的年轻男子;据瓦尔多·布兰特叙述,“我”是明星约翰·基尔伯特的心腹弗雷迪;当“我”到弗雷迪的家乡,花匠鲍勃却告诉我,“我”不是弗雷迪而是弗雷迪的朋友、南美某国驻巴黎公使馆的佩德罗;当“我”按照鲍勃给的电话号码找到房东海伦·皮尔格拉姆,她却认为“我”是德妮丝的男友麦克埃沃伊;根据德妮丝的出生原件证明书,“我”又是希腊人吉米·彼得罗·斯特恩……“我是谁”成了永远的疑问。追寻过程中,“我”曾借助各种资料,它们环环相扣,指引“我”一次次开始新的追寻,例如社交人名录和电话号码簿,表面上它们是重启追寻的桥梁,深层上“是逝去世界的唯一见证”(第1页)。小说还将书信、明信片、文件、照片、护照等作为追寻的线索和重要的历史印记,如于特多次从尼斯寄来的明信片和德妮丝逃离法国前写给海伦的信。
过去身份的缺失导致了“我”现时的彷徨,彷徨又促使“我”追寻过去,然而追寻未果。“我”的身份是流动的、不断被建构的。
二、逃离:“流亡,一个悲惨的题目”
如果说失忆是现时的“我”追寻过往的起因,那么十年前的逃离则开启了漫长的漂泊。“我”和朋友们因为流亡、家族迁移等原因来到法国,但并未拥有真正的法国身份,索纳希泽、斯蒂奥帕、佩德罗、盖·奥尔洛夫等都是流亡者。我们是“无根之人”:“我”和德妮丝选择逃离;盖·奥尔洛夫先是和瓦尔多·布伦特结婚以逃避美国政府驱逐,后又和吕西亚诺结婚是为“取得法国国籍”(第42页),最后自杀才结束痛苦;还有无数流亡者将苦难深藏心底,当“我”告诉斯蒂奥帕“我写一本关于流亡的书”时,他凄凉地说:“流亡,一个悲惨的题目……可是你怎么会叫我斯蒂奥帕的”“叫我斯蒂奥帕的人大多已故世了,剩下的恐怕也屈指可数了。”(第24页)
“我”的失忆源于二战时期经受的折磨,莫迪亚诺曾说:“我总是觉得自己是污浊时代的产物,是战争的产物。人们总是在谈论‘占领时期’,可是对我而言,却并非是无缘无故的。”⑤对处境极度焦虑又无力的情绪在小说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暗店街》一开始就说:“我什么也不是。”(第1页)十年间“我”被不安全感和恐惧感追逐,“我相信我的焦虑感和当年是一模一样。”(第120页)“每次我走上米拉波街便感到害怕,怕被人注意,怕被抓住,怕有人要我出示证件。”(第124页)无根性结尾时仍在持续,“追寻”或许永无意义。
逃离其实也是追寻,是自我意义无法实现后的消极性选择。一群没有法国身份的人处在社会和政治的边缘。“我”可能是俄国流亡者——像斯蒂奥帕和装满盒子的旧照片上的那群人;也可能是德占时期的犹太人——“从小,他就从父辈的故事中了解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排犹主义给犹太人带来的苦难,犹太人那种艰难的处境、永远偿不清债务似的命运,给了他极深的印象。”③也可能是任何一个现代人——莫迪亚诺曾说:“我所表现的却是今天世界的一个极度扩大化了的形象。”③
三、无根性:“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海滩人”
《暗店街》中的无根性既是“我”的私生活状态,也是政治上的德占法国的状态,更是整个人类存在本身。
在政治的意义上,恐惧是很多人经历了纳粹迫害后的本能反应,“在这种感觉中,有两种紧张的担忧清晰可辨:一是警觉,一是焦虑。”⑥例如“我”找到瓦尔多·布伦特时,“他刚才走得那么快,或许是因为他以为有人盯梢,抑或为了甩掉我。”(第39页)又如让-米歇尔·芒苏尔从咖啡馆走回家时,“他加快步伐,不时朝左边人行道上海蓝色的酒吧间偷偷看上一眼……正当我们穿过日耳曼-皮隆街的时候,我见他惊恐万分地朝这条房屋低矮阴暗、坡度较陡、一直通向林荫大道的窄街望了一眼。”(第103-104页)这种无根性也指向纳粹占领时期的法国,如同米兰·昆德拉所说:“遗忘同样也是政治的重大问题。当一个大国想要剥夺一个小国的民族意识时,它采用的方式就是‘有步骤的遗忘’。”④在存在的意义上,无根性也指向人类,就像于特所称的“海滩人”:“于特一再说,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海滩人,我引述他的原话:‘沙子只把我们的脚印保留几秒钟。’”(第50页)
四、结语
《暗店街》的远景是二战,却没有描绘被占领的场景以及战争的场面,而是通过“我”的遗忘和追寻间接反映了战争的伤害。战争使世界笼罩在黑暗之中,“我们”逃离的不仅仅是巴黎,还有伤害和恐惧。但逃离是失败的,“我”因此丧失了记忆和身份。个体身份的丧失又揭示了人的存在本质的虚无,“其实,我或许根本不是这位佩德罗·麦克埃沃伊,我什么也不是。”(第92页)寻访没有答案,但这是对“我是谁”的永恒思考。不过,莫迪亚诺也鼓励我们面向现在,像索纳希泽所说的“必须在现时生活”(第14页)。
注释
①诺奖授奖词.
②帕特里克·莫迪亚诺.暗店街[M].王文融,译.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5:4.以下引用该作品均出自此版本,不再一一标注,只在引文后标出页码.
③小禾.“神秘的年轻人”——法国当代作家莫迪亚诺[J].读书,1986(2).
④李凤亮,李艳.对话的灵光——米兰·昆德拉研究资料辑要[M].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8:525.
⑤(法)洛朗斯·利邦,辑录.莫迪亚诺访谈录[J].李照女,译.当代外国文学,2004(4).
⑥(美)段义孚.无边的恐惧[M].徐文宁,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3.
朱林染(1999-),女,河南大学附属中学临风文学社社长,校刊《花屿》主编,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