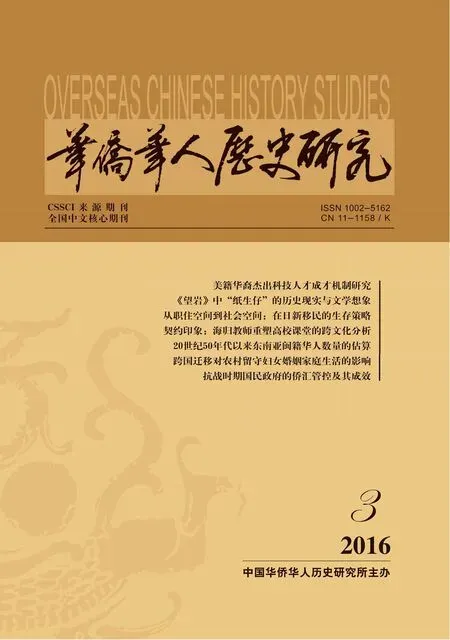从“职住空间”到“社会空间”*
——在日中国新移民的生存适应策略探讨
张慧婧(天津理工大学 法政学院,天津300384)
新移民研究
从“职住空间”到“社会空间”*
——在日中国新移民的生存适应策略探讨
张慧婧
(天津理工大学 法政学院,天津300384)
日本;新移民;移民社区;职住空间;社会空间;社团网络;社会资本
论文基于笔者对新移民组织和文化祝祭活动的资料收集与实地调研,运用社会学相关理论,以“社会空间”的形成作为切入点,探讨了在日中国新移民的生存适应策略。认为中国新移民通过“节点”的纽带作用积累“社会资本”,进而构建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在动态变化的社会空间,中国新移民可以利用各种平台,运用各类社会资源,在与他者的相互关系和互动中求得共生。网络式移民社区空间的构建,更符合中国新移民高流动性、高层次性、高创造性的特点和当今时代特征。它的存在不仅使在日中国人在远离故乡的生活世界里找到族群公共圈,产生连带感和归属感,而且避免了与日本社会的正面冲突,有利于新移民在与当地民众和平共处的前提下推进族群活动的日益丰富和活跃。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向日本的国际移民数量较少。由于受到日本政府对劳动型移民的入境限制,①从1899年颁布敕令352号直至现在,对不具备特定专业、职业技能的简单劳动力入境的严格限制是日本入国管理法规的基本方针。加上当时日本社会对在日中国人并不宽容,在日老移民大多是自主创业的商业型移民。1980年以后,中国政府为探寻改革开放新时期的现代化建设道路,将大批派遣留学生出国学习先进科技和文化提上日程;[1]同一时期,日本政府也为加速国际化进程提出招收10万留学生计划;[2]由此,中国出现了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人员结构都史无前例的留日热潮(参照图1、表1)。1990年,日本修订出入国管理法,明确了“人文知识·国际业务”②“人文知识·国际业务”是指和日本公私机关基于合同开展具有法律学、经济学、社会学及其他的人文科学方面知识的业务,或者从事具有基于外国文化为基础的具有思考和感受性的业务活动。如翻译、语言学校的语言教师、市场、商品开发、广告、宣传、海外交易业务、服饰或者室内装饰设计等。引自国际劳动法务事务所网站:http://krh-office.com/cn/visa/humanities.html。、“日本人配偶者”等在留资格,不仅促使中国人移居日本的数量迅猛上升,也致使留学不归的人数逐年增加。[3]这些滞留日本未归的留学生,正是新华侨的构成主体和最基本来源。[4]廖赤阳指出,留学生以及毕业后在日本就业或创业的这一群体,对以后的日本华侨社会具有决定性影响。[5]邵春芬的研究证实了以“原留学生”为主的在日中国人的新华侨化现象,论述了原留学生在日本社会上升性社会移动过程中对日本华侨社会与中日交流的深远影响及扮演的重要社会角色。[6]因此,讨论在日中国人社会的现状、中日关系等问题,尤其要重视对赴日中国人中具有高学历、高技术、高人脉之特征的知识型新移民群体的持续关注和研究。近些年,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学科视角进行了探讨,既有纵观日本华侨社会变迁历程的,[7]也有综观记录从留学生到新华侨的成长轨迹的,[8]还有选取某个时间段对新来中国人移居过程进行分析的。[9]特别是伴随新移民队伍日益壮大的趋势,一些学者开始着力于新移民社会组织与网络、新移民社区等方面的研究。[10]但总体来看,国内外学术界专门针对日本中国新移民的研究成果尚少,有待进一步开拓。
2006年后,日本总务省大力推进地方政府构筑地域社会“多元文化共生”,这为中国新移民带来彰显族群特色和自身优势的发展新机遇,新移民势力迅速崛起。2007年,在日中国人成为日本最大的外国人族群。然而,由于日本不属于传统移民国家,单一文化主义和排外心理由来已久,日本民众对于多元文化共生的认知度依然薄弱。尽管受过高等教育、拥有专业技术的新移民的出现使当地人对中国人有了更加良性的看法,但从“东京中华街”构想夭折的实例不难看出,新移民并未得到当地社会的真正接纳。[11]在当前中日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在夹缝中生存”的新移民如何不被主流社会同化或边缘化而最终实现“文化整合”①文化整合是指文化适应中的非主流文化族群既重视保持个体的传统文化,也注重与其他群体进行日常交往。,仍是他们面临的巨大压力。新移民不断尝试新的可能性,特别是以商业精英、知识精英为主力的年轻中产阶层,力求“在夹缝中架桥”,为重振中日民间交往发挥作用。

图1 在日中国人的人口数量变化(单位:人)
那么,新移民采取了哪些不同于老移民的生存适应策略,由点到面、由弱到强、稳中有为地立足于日本社会,并站在全球大背景中重塑中国移民国际形象的呢?本文将基于社会学视角,从“节点”与“社会资本”相互作用的方法论入手进行解析。首先,揭示在人口流动性大、居住分散化的全球化潮流下,日本中国移民社区空间形态从飞地式“职住空间”到网络式“社会空间”的变迁及其特点;其次,分别以新移民组织和文化祝祭为材料,阐述新移民如何利用中国对外开放新格局和自身独有的优势,实现节点创造与社会资本积累,并在跨国社会空间中创造理想的生存方式,从而更好地应对中日关系新常态下的机遇与挑战。

表1 在日中国人的中长期居住者人员构成 单位:人
二、日本中国移民社区空间形态的变迁:从飞地式“职住空间”到网络式“社会空间”
山下指出,民族飞地(ethnic town)具有以下三个特征:一是族群同胞的聚居地(特定的地理区域内人们的集合),二是族群商业中心(可以自给自足的内部经济关系网),三是有继承并维系着传统生活方式的族群设施(社团组织、学校、宗教设施等)。[12]这三方面体现了少数族群在主流社会的生存适应策略。拥有150余年历史的横滨中华街,正是老一代移民在日本社会对华歧视、住宅限制、职业限制等外因和老移民的防御与斗争、抱团互助、传统保持等内因的共同作用下,[13]聚居于日本政府规定的外国人居留地一角,而逐渐形成的集住宅、商业、教育于一体的封闭式生活社区。正如首个提出社区概念的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描述的“礼俗社会”的特征,19世纪末期,生活在中华街的中国移民几乎过着“亲密无间的、与世隔绝的、排外的共同生活”[14]。尤其是第一代老移民人力资本低下(语言不通、专业技能不高)、没有社会关系(远离亲朋、邻里等社会支持)、缺乏人身安全感(没有政府庇护)、缺乏精神归属(远离民族文化),被主流社会边缘化的中华街正是其赖以生存的聚居地和避风港。可以说,横滨中华街等飞地式“职住空间”(job-housing space)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代表了以贸易商和从事“三把刀”等传统服务业的手艺人为主的中国移民特有的生活方式与人际交往模式,它的形成是老移民历经几代人与当地社会磨合的历史产物。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第一代老移民及其子孙大多扎根日本,由于受到主流社会的重重限制和多种因素的影响而被同化,他们在与当地市民互动的漫长过程中形成某种“复杂的认同感”[15]。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人口的跨境迁移日趋频繁,移居到日本的中国新移民以散居为主,他们在社会阶层及其生活环境等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变化。[16]新移民人力资本整体相对较高,交通、通讯工具的发达促使地域内及跨地域、跨国界的社会关系网络更容易建立,中国国际地位提高、驻日使领馆设立以及侨务法规和方针政策的不断完善使人身安全得到保障,新移民的文化创造活力和跨文化意识等不断增强。第一代新移民基于新理念,试图与主流社会在多元文化共生中寻求平衡,重视保持“自我认同”,力求实现融入而不被同化的文化整合策略。如陈天玺、陈于华等论述了新移民的成长与日本构筑多元文化共生社会的关系,[17]大量中国新移民为了追求人生价值的最大升华,顺应中日关系新常态,在各领域不断开创新的可能,重塑在日中国人与日本社会的相处新模式。
中国新移民彰显异质性(分为技术型、资本型、劳务型)特征,生活方式与行为手段也呈现出多样化和个性化趋势。他们从事的职业不再局限于传统服务业,也在向气功针灸、按摩、休闲娱乐等现代服务业,特别是旅行、教育培训、传媒、文化、咨询、IT等知识型服务业大幅扩展。因此,在中华街限定的地域空间内高度集中居住且活动内容仅限于传统框架的飞地式生存策略,难以满足新华侨的生存发展需求,取而代之的是营造以节点(node)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的相互作用为基础的关系网络模式的“社会空间”(social space)。
根据帕特南(Putnam)的定义,“社会资本是个体之间的联系,即社会网络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互惠和信赖的价值规范”[18]。社会资本包括强关系网络的“结合型社会资本(bonding social capital)”和弱关系网络的“桥接型社会资本(bridging social capital)”。社会资本并非个人拥有的财产,而是通过纽带才能接触到的社会资源,为目的性行为所使用。换言之,也就是说特定目的的行为者通过搭建沟通桥梁并加以维系,建立社会资本。[19]而“节点”正是使行为者之间相互连接的、复杂人际关系网络的中心。[20]节点作为媒介,是社会资本形成的纽带;社会资本存量的不断提升,又进一步促进新的节点平台构建;节点和社会资本相互作用过程中积蓄的社会资源,是社区筑造的基础和源泉,也是社区顺利运营的润滑剂。[21]“社会空间”是实际生活中不同的个人和群体的多层关系和行为所形成的场域。[22]与职住空间不同的是,社会空间在各种各样的关系场域中动态变化着;而在脱域化的社会空间里,集团成员的生存战略、行为规范、人际圈及意识构造等要素,也在被不停地再生产和体系化。[23]当前,在日本中长期居住生活的中国新移民,正在通过节点创建(新移民组织、文化祝祭等)和社会资本积累,摸索着构建以网络式“社会空间”为特征的现代都市型新移民社区。可以说,这既符合他们散居型、流动性、开放性、更强适应性和多元意识的特点,也能满足其多样化和个性化的生活需求。
本文拟站在节点和社会资本相互作用理论之新视角,基于笔者对新移民组织和文化祝祭活动的资料收集与实地调研,以“社会空间”的形成作为切入点,探讨在日中国新移民的生存适应策略。
三、基于社团组织创立与多层关系网络的移民社会空间建构
全球化背景下,血缘和地缘不再是中国新移民构建社区的必要因素,族群成员之间的相互交流和共通目标存在下产生的社会感情(族群意识、责任意识、依附意识)起着更为关键性的作用。近些年日本新移民的组织化倾向明显,逐渐形成社会网络。[24]新华侨组织由学缘、业缘、志缘、地缘、趣缘等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发展而结成,涉及的领域不断扩大,数量也持续增加。这些民间组织和社会团体作为节点,将族群成员连接在一起,共享特定的公共圈,促使他们在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实践活动中不断扩展人际关系网络,积累社会资本。本文主要围绕以服务在日数量庞大的华商群体、留学生群体、中国人草根阶层为主体的新移民社团组织进行讨论。
(一)业缘关系——以华商为服务主体的“日本中华总商会”
华商是日本华侨社会构建的中坚力量。基于职业、行业、事业等“业缘”关系而形成的以华商为主体的商业组织“日本中华总商会”(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in Japan)成立于1999年9月,目前拥有企业会员近300家,其中230余家是以华侨经营者为主体的正会员,另吸纳70家与中国经济关系密切的日本企业和跨国公司作为赞助会员。总商会成立的时代契机有两方面:一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赴日留学的很多人走上创业之路,成了新华侨中的企业家;二是中日之间的经济差距缩小并出现逆转,中日之间的市场与经济联系日益紧密,为在日华商提供了良好的发展机遇。[25]在会员企业的持续支持下,日本中华总商会坚守“日本、中华、总商会”的三层定位,不断走向成熟而发展壮大,为华商、中资及日本企业之间多种形式的交流与合作,发挥着日益重要的节点作用。
第一,面向日本,提高族群凝聚力,增强扎根之力。商会举办了多种形式的活动,一是研讨会。定期邀请中日专家进行专题讲座,组织开展集中研讨,观点博弈有利于增强会员间更高层次的交流互鉴,帮助华侨企业家在日本社会拓展事业发展空间,提升企业的实力和影响力,为会员事业发展铺路搭台。二是亲睦会。为了增加会员相互交流的机会,每三个月召开一次中小型例会兼晚餐会,增进了会员之间的深度融合;此外,只要经会员介绍,社会各界人士都可参加,这也为会员拓宽新的人际圈牵线搭桥。三是文体会。每年元旦与春节之间定期举办迎春会;每年举办一次CCCJ杯高尔夫友谊赛和中日友好高尔夫大会;每两年举办一次华商杯高尔夫大会等等。以“趣缘”为纽带的休闲娱乐活动作为开放性平台,不仅拉近了会员之间的情感,增进了友谊,也为中日两国民间交往创造良好氛围,同时扩大了总商会的影响力。四是编辑发行会刊:每月汇编一次CCCJ NEWS电子会刊,面向全体会员发送。策划发行纸质会刊《交游》,发布商会活动信息和内外交流动态等丰富的内容,以会刊为载体,通过多元化信息服务平台,增强会员对族群的认同感和归属感。综上,会员以研讨会、亲睦会、文体会、会刊等作为媒介,在互动过程中实现人际网络由弱关系向强关系的转化,积蓄社会资源,形成社会资本,增强了网络型新移民社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
第二,面向中国,与祖国保持密切联结。一是总商会长期活跃在中日经贸合作的前线,组织华商代表团走访中国各地进行考察和交流,充分发挥了“侨”的独特优势和海外关系的软实力,每年组团访华,成为中日友好的高层次中介桥梁;在基于跨国界“业缘”交往过程中相互联结,形成跨地域的社会关系网络,积累了桥接型社会资本。不仅探索出自身发展的国际化路径,而且为促进祖国经济建设和中日两国互利双赢等发挥了积极作用。二是连续多年组织华侨会员的子女参加由国务院侨办组织的“寻根之旅”夏令营,推动青少年对中国历史与传统文化的认知和热爱,帮助日本新华侨的第二代、第三代在寻根之旅中建立志同道合的青少年朋友圈,形成以社会关系网络为基础的公共空间。
第三,面向世界华商圈,借助华商强大的人脉网,成为日本与各国华商团体进行交流沟通、友好合作的重要窗口,助推旅日华商在区域化和全球化潮流下实现跨国发展。总商会作为节点,促使旅日华商间、中日两国间、世界各国华商间形成发达的跨国商业网络和相互依赖、相互作用的社会资本,从而进一步构成“跨国社会空间”,成为影响多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量。
日本中华总商会在日本华侨社会是非常有影响力的组织,逐步发展成为日本规模最大的华商平台和互通纽带。一方面,总商会为会员提供开发结合型社会资本和桥接型社会资本的平台,助力他们在以多层面、多方位的社会关系网络为支撑的广阔“社会空间”里实现跨越性发展;另一方面,搭建了中国、日本乃至世界华商圈民间友好交流的便捷桥梁,为所在国和祖籍国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二)学缘关系——以留学生为服务主体的“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
王辉耀认为,中国在推进“一带一路”战略、进一步扩大开放等方面,留学人员是非常重要的特需资源。[26]中国人留学日本的跨国移动,不仅构成了联系中日两国民间交流、人际关系网络与文化知识传播、观念转变的重要纽带,而且成为推动今后中日关系发展不可或缺的宝贵资源。[27]近年来,基于“学缘”因素的日本留学人员社团组织活跃度不断提高,值得关注。“全日本中国留学人员友好联谊会”(Association of Chinese Students and Scholars in Japan,简称“学友会”)成立于1992年4月,分会设置在东京、名古屋、大阪、京都、福冈、北海道等留学生比较集中的地区,包括二级地区分会和三级大学分会200余所,汇集了在读留学生、访问学者及毕业后在日就职的原留学生等,总人数超过5万人,是日本最大的非营利性中国人组织。学友会以“爱国、团结、友好、服务、奋进、奉献”为宗旨,多年来各分会探索着各种有益身心的联谊模式。如通过每年召开新生欢迎会、举办面向留学生的体育比赛、传统佳节联欢会、学术座谈会、春游秋游等集体户外远足以及邀请当地政府部门和企业开展中日友好交流活动、学习会等,积极团结和联络广大新老留学人员,丰富大家在日本的生活。同时,提供升学、打工、就职(当地日企、华人企业及国内高校招聘信息)、房源及物品赠送、转让等其他各类生活方面的信息,帮助解决留学生活中的实际困难。
根据笔者的调查,各地区学友会有着相似的运行模式,实施手段具有可行性和创新性。
首先,重视线上线下结合。学友会创建了专用邮箱和实名制QQ群(包括姓名、所属学院)。QQ群是中国留学生最早广泛使用的一种方便快捷的信息共享方式,群主或群活跃分子多为现任或前任的学友会干部,通过促进新老生之间的相互结识,以老扶新,帮助新生走出留学新环境带来的生活和学习上的困境。作为桥梁纽带,学友会本着互助互信的原则,尤其重视线上和线下资源的充分结合,通过策划和组织上述各类联谊活动,促使网络平台的线上社交关系在线下得以巩固。学友会正是以资源共享的方式增强成员的组织归属感,在相互感染、相互激发、相互支持的互动下形成情感共鸣,促使组织内部社会关系网络逐步构建。有组织性的线下联谊活动,不仅营造了真实的集体归属感,而且促使人际关系网络得到进一步扩展,为留学期间乃至以后的就业与人生发展积累社会资本。
其次,利用微信和朋友圈等新潮社交平台,实现新突破。随着信息产业的发展与移动网络的普及,微信公众平台和朋友圈在日本华人圈迅速兴起,虽然相对晚于国内,但已经成为被广泛认可的新联结纽带。近两年,日本各地学友会开始相继利用微信公众账号创建网络社群,如仙台地区学友会、静冈地区学友会、熊本地区学友会、横滨地区学友会、德岛留学生学友会、阪大学友会、京大学友会、神户学友会、北海道学友会、岩手县学友会等。相比QQ群的内部信息交流平台,微信公众平台发布的图文消息对外公开、内容丰富、形式多样,不仅在第一时间将学友会的活动信息推送给本地域的族群同胞,而且增加了不同地域各分会之间相互了解、借鉴、合作的可能,同时也打开了国内对留日人员日常生活、学习、工作等各方面密切关注和深入了解的窗口,成为嫁接祖国与海外同胞的新渠道。而微信朋友圈发布的即时滚动信息更是打破了地域、身份地位、阶层、领域行业等界限,促使人际交往的视野和范围在频繁的信息互通中由“内圈”(地域内紧密关系的小群体)向“外圈”(跨地域松散关系的大群体)扩展。
学友会是在日中国人的重要组织之一。它有效结合了公共邮箱、QQ群、微信群等网络平台的线上实时互动和以学友会为组织者的线下深层交流活动,发挥着“联情、联利、联志、联心”的节点纽带功能,促使结合型社会资本和桥接型社会资本逐步积累。纵横交错的亲密型强关系社会网络和松散型弱关系社会网络相互协调,构成族群“社会空间”,支撑着新来中国人在当地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密切了与祖国的联系,为今后要回国工作、服务祖国的留学人员积攒了一定的社会资源。
(三)志缘关系——以新移民草根阶层为服务主体的“中日志愿者协会”
2006年2月“中日志愿者协会”是由留学生出身的新移民发起成立,这是以有着共同价值观的在日中国人志愿者为中心,同时吸纳日本民间友好人士加入的草根非营利组织。总部设在东京,关西和中部地区设立了支部。目前500余名志愿者(包括研究人员、公司职员、学生、家庭妇女等)和12名日本律师因“志缘”相互联结,共同致力于长期免费帮助陷入困境的在日中国人维护合法权益,减少其与日本社会的误解和摩擦,促使与日本社会的融合与共生。[28]志愿者协会的工作得到了中国驻日大使馆和日本政府的认可,受到日本律师援助团、各地劳工组织、中日友好协会等社会各界协助,也获得中新网、新华网等国内权威媒体,《每日新闻》等日本媒体,《中文导报》等日本华文媒体的关注,吸引越来越多志愿者加入。
笔者认为,该协会的显著特点有二:第一,致力于服务弱势群体。该协会不同于以知识精英、商业精英为主的强势阶层组织,而是站在草根阶层的立场上,更多服务于有语言障碍、维权意识和知识不足、对日本社会缺乏了解、饱受日本社会歧视的相对弱势的在日中国人群体。通过提供法律等方面的服务,帮助他们解决劳工问题、研修生问题、国际婚姻问题、遗孤问题、签证问题、交通事故、家庭矛盾、人身伤害、健康医疗、诈骗、与日本雇主之间的纠纷以及生活中出现的各种心理烦恼。随着求助者越来越多(从青年到老年都有,女性占6成),涉及面也越来越广。
第二,采用“互联网+精准帮扶困难同胞”的服务模式。协会每周在《中文导报》刊登免费助人专栏,开通24小时中文热线电话接受咨询和援助请求,与需要帮扶的同胞建立联系。更值得一提的是,协会公共网站、论坛的开通,专用邮箱、微信群和“中日志愿者电子杂志月刊”等的设立,筑构了庞大的虚拟社区空间,克服了时空距离,架起了“连心桥”,扩展了以往仅通过电话和面对面传播的沟通方式。由于志愿者协会的服务内容具有突发性、时限性或潜在性、持续性等特点,“互联网+精准帮扶困难同胞”的模式适合于繁杂琐粹的日常运营管理,互联网为同胞之间构筑相互支撑、相互依存的强连接(小圈子)和弱连接(大圈子)提供了便利的平台。强关系网络与弱关系网络共同组成纵横交错的社会资本,极大地丰富了信息来源、提高了信息传播速度,推动志愿者协会发挥更大作用。可以肯定地说,志愿者协会作为节点纽带,为减少新移民与日本社会的误解和摩擦,尤其是为帮助新来中国人的弱势阶层与日本市民和谐相处,打造互相信任、理解和包容的共生关系,做出不菲贡献。
以上笔者列举了日常活动覆盖面较广的在日中国人组织,由于篇幅所限,无法对其他更多的组织一一详述。例如区域性新华侨华人代表性团体——西日本新华侨华人联合会、中部日本新华侨华人会、北海道华侨华人联合会等,地缘团体——中国各省市同乡会、日本江苏发展促进会、日本黑龙江经济文化促进协会、日本福建经济文化促进会等,专业团体—在日中国科学技术者联盟、在日中国律师联合会、日本华人管理科学学会、日本华侨华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全日本华人书法家协会等,以及华侨创办的中日文化交流中心等。这些组织的创立者多数属于文化程度较高、经济相对富裕、精力充沛、有强烈族群意识的新移民精英,他们是在日中国人社会的引领者、建设者、促进者。新移民组织的活跃助推了在日中国人社会的迅速发展,进而以侨为桥,推进中日友好。
总之,以网络式“社会空间”为特征的脱域化移民社区模式,符合新移民的生存适应需求。而讨论现代都市型移民社区空间建构,不容忽视“节点”和“社会资本”的相互作用。作为节点的新移民组织,不仅拓宽了新移民的日常生活圈、专业学术圈、跨地域商业圈等多层面人际关系网络,而且有利于新移民确立自身在当地的社会经济地位、提升族群整体形象。可以说,新移民组织呈现多样化、当地化、国际化等显著特征,重视各领域各阶层同胞之间的结合型社会资本积累、重视与主流社会的桥接型社会资本积累、重视跨文化交往模式下的跨地域社会资本积累。
四、基于祝祭创造与文化认同的移民社会空间建构
杉浦认为,某个少数族群面对着被当地同化的压力,为区别于主流社会及其他族群,他们会尽可能地维护本族群的空间领域与文化认同。[29]王维通过对日本三大中华街华侨社会空间与祝祭文化的研究,揭示了日本华侨以再造文化符号来建构和维系族群性的特点。[30]极具民族特色的“祝祭”(culture festival)作为族群活动的重要节点,实现了族群文化的可视化表达。在日本,除了早已闻名海内外的传统华埠街区的“横滨—神户—长崎流”春节庆祝活动之外,由中国新移民在大都市中心繁华街开创的“名古屋流”文化祝祭更是独具新意,渐成中日两国媒体的关注热点。[31]作为在日中国人社会的新时尚,一年一度的中国春节祭、中秋明月祭等,以越来越盛大的规模和气势在日本各地相继展开,不仅有利于展示在日中国人的新风采、树立新形象,增强族群的社会存在感和影响力,而且成为植根于当地民间的可持续性的中国文化品牌。
笔者基于多年来在日本的实地调研,将文化祝祭的节点作用归纳为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推进地域内各阶层同胞间的强弱关系产生与社会资本积累。山本认为,“民族祝祭”使移民集团的文化和价值体系得以体现;即便有些祝祭活动以经济目的或政治目的为主,但移民自身若没有对族群原初的留恋,就难以动员他们参与其中。[32]感情是相互行为的基础,集团成员间的感情共鸣程度越强烈,集体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33]笔者通过深度访谈了解到,散居状态的新移民以发起祝祭活动为契机,在日常的频繁接触中建立了信赖感、加深了依附感、形成了归属感;在每年祝祭活动的筹备工作例会及各阶段准备过程中,各界精英阶层组织之间不断增进互通往来与合作,以祝祭为纽带的共同目标促使侨领们交往、交流、交融,产生对族群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最终形成华侨精英阶层的强关系社会网络。不仅如此,祝祭活动专门场地的设置为在日中国人大众阶层提供了相互结识的“公共空间”,广场内布置的各类衣食住行用等服务推广展台琳琅满目,使他们在娱乐和休闲中互通信息、共享资源,挖掘了族群内部潜在的弱关系社会网络。总之,通过节庆平台形成的强关系和弱关系社会网络,在族群同胞“社会空间”构建中优势互补、共同发挥作用,既满足了各阶层在日中国人某种程度的社会需求,为他们立足日本社会带来实际利益,也维系了该地域华侨社会的稳定。
第二,提供了跨地域侨界间交往与社会资本积累的可能性。2007年,名古屋侨界开创了由新移民主导的、在传统华埠以外的非聚居区域举办春节祭的先例。祝祭作为文化象征符号,在中日媒体的宣传中唤起各地域、各阶层在日中国人对民族的情感共鸣。此后,各地侨界互相呼应,纷纷借鉴名古屋春节祭祝模式或赴名古屋考察取经,在推介中国“软文化”上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如福冈春节祭(首届2009年)、大阪中秋明月祭(首届2009年)、大分春节祭(首届2014年)、新泻春节祭(首届2015年)、东京中国节(首届2016年)等等。以举办祝祭活动为契机,每年不同地域的侨领都少不了相互之间的走访、见学,除了共享祝祭成功经验之外,还会围绕新移民社区建设的先进有效模式等话题进行交流探讨。随着生活在不同地域的华侨之间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交往范围越来越大,他们在互鉴互勉中形成彼此信任和优势互补的社会关系网络,增强了今后在经济等各领域强强联合的可能性。同时,跨地域侨界间的凝聚共识,推进了日本新华侨社会的秩序逐渐形成,提升了日本华侨社会整体发展的动力。
第三,以祝祭为节点,搭建改善中日两国国民感情的渠道;以跨文化传播为特点,促进中日两国及两国城市间的友好往来。春节祭、中秋明月祭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日本民俗“祭”(节日庆祝)的创意式结合,不仅成为广大侨胞的感情依托,也成为日本市民体验异国文化的特色窗口。在筹备和举办祝祭活动的过程中,日本地方政府的支持、日本大型企业的资金赞助、日方各界友好人士和团体的后援、日本各大知名新闻媒体的报道等,更加激发了日本民众想了解和感受中国文化的意愿。在祝祭公共空间里,中国式牌坊、中国地方特色美食、土特产和调味品、传统手工艺品、书法艺术、按摩技艺、汉语学习和旅游信息服务以及独具民族风情的文艺表演项目的可视化表达,使日本游客充分体味到中国文化的魅力;同时,也吸引日本市民与在日中国人近距离接触、面对面交流,增进相互了解与融合。祝祭让文化交流缔结友谊纽带,安全有序、欢乐和谐的节庆平台促使两国民众之间相互信任和相互尊敬的感情慢慢扎根于心,进而形成良好的跨文化社会关系网络,建立桥接型社会资本。
正如安田所述,“桥接型社会资本可以使不同立场的人们达成共识,是打破僵局状态的万能药”。[34]一方面,日本主流社会对中国新移民的态度逐现理性化,接纳程度有了一定提高;另一方面,在日中国人更好地融入当地社会,才能更大程度发挥自身优势,为促进中国文化走进日本搭建友谊之桥。例如,国务院侨办主办的“文化中国·四海同春”活动自2010年2月起在日本各地成功举办,这离不开日本地方政府和当地市民的理解和支持,而侨胞正是实现日本社会与中国对话和沟通的重要纽带。再比如,中国各地的民间文艺团体为祝祭助力助兴,赴日本主要城市演出逐年增多,这也全靠日本侨界的牵线搭桥。2015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中日友好交流大会上强调,“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中日关系前途掌握在两国人民手里”。[35]新移民以祝祭为节点,积极与当地社会建立桥接型社会资本,维持共生关系。这不仅符合日本社会的多元文化发展需求,促进地方繁荣,而且加快了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与传播的国际化步伐;同时,通过加强中日民间交流,缓解了中日紧张关系,构筑了互利双赢的模式。
综上三点,独具中国特色的祝祭已成为新移民着力打造的民族文化品牌,它的确立与维系象征着族群的新生力量。祝祭不仅作为文化象征符号,使族群成员确立身份认同,实现精神联结,而且每年固定的活动场地作为可视化的特有公共空间,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同胞乃至日本民众汇聚一堂,在互动交流中建立关系场域,最终形成以网络式“社会空间”为特征的社区空间。祝祭活动的成功举办,有利于增强族群社会存在感,重塑在日中国人的形象,并广泛团结留学生、新移民、老移民及“后”移民(新华侨子女一代)归属族群社区。这一新成就、新气象,既表明了新移民一代的成长与崛起,也证实了文化祝祭的创造是新移民基于世界潮流变化、立足日本社会的生存适应策略。
五、结语
近些年,长期生活居住在日本各地的中国新移民纷纷提出了兴建中华街的构想(如东京中华街、名古屋中华街、札幌中华街等),但都未能付诸实践。无论是因环境卫生问题遭到当地居民反对,还是右翼组织散布“中华街威胁论”等,都说明像传统中华街那样固定在某个地理区域内的飞地式“职住空间”构筑,在今天往往受到各种现实因素的制约而难以实现。本文的分析可见,中国新移民通过“节点”的纽带作用积累“社会资本”,进而构建以人际关系网络为基础的“社会空间”。在动态变化的关系场域里(社会空间),中国新移民可以利用各种平台(节点),运用各类社会资源(社会资本),在与他者(包括本族同胞和当地民众)的相互关系和互动中求得共生。网络式移民社区空间的构建,更符合中国新移民高流动性、高层次性、高创造性的特点和当今时代特征,它的存在不仅使在日中国人在远离故乡的生活世界里找到族群公共圈,产生连带感和归属感,而且避免了与日本社会的正面冲突,有利于新移民在与当地市民和平共处的前提下推进族群活动的日益丰富和活跃。
今天,横滨、神户、长崎日本三大中华街作为华侨社区的功能早已弱化。随着中国的发展壮大以及海外中国移民的整体层次和生存能力的提升,日本华侨社会呈现出显著的新特征、新趋势。以新移民组织和文化祝祭为“节点”编织和巩固的多元化、多层次社会关系网络,成为族群社会“社会资本”的重要载体;同时,具备动态性、开放性、多元性和发展性的“社会空间”的建构,成为中国新移民在日本社会生存与发展的重要适应策略。
[注释]
[1]梁志明:《当代留学大潮与中外文化交流》,《公共外交季刊》2012年第10期。
[2]马岩、肖甦:《日本留学生扩招政策与高等教育国际化进程》,《比较教育研究》2012年第12期。
[3]鞠玉华:《日本华侨华人子女文化传承与文化认同研究》,暨南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1~52页。
[4]段跃中:《日本における新華僑華人社会の現在》,《教育学研究》2011,78(1)。
[5]廖赤阳:《跨越疆界:留学生与新华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第2页。
[6]邵春芬:《从留学生到新海外华侨华人:日本的事例》,刘泽彭主编:《互动与创新:多维视野下的华侨华人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86~408页。
[7]朱慧玲:《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的日本华侨华人社会的变迁》,厦门大学出版社,2003年。
[8]鞠玉华:《日本華僑華人社会の変容—留学生から新華僑華人へ》,《岡山大学大学院文化科学研究科紀要》2005,20。参见注5第377页。
[9]梁其姿、张存武编:《第四届世界海外华人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Ⅲ》,台湾“中央研究院”出版社,2001年,第221~229页。
[10]邵春芬:《日本における中国人コミュニティ》,《日中社会学研究》2002,10;江卫、山下清海:《公共住宅団地における華人ニューカマーズの集住化—埼玉県川口芝園団地の事例》,《人文地理学研究》2005,29;山下清海:《池袋チャイナタウン—都内最大の新華僑街の実像に迫る》,洋泉社,2010年;张慧婧:《浅析日本网络型华侨社区的兴起——以名古屋地区为例》,《八桂侨刊》2011年第4期。
[11][25][27]同注5,第170、223~224、4页。
[12][13]山下清海:《エスニック·ワールド》,明石書店,2008年,第31~32、30页。
[14]夏建中:《城市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77页。
[15]S.カースルズ·M.J.ミラー著,関根政美·関根薫訳:《国際移民の時代[第4版]》,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11年。
[16]张慧婧:《日本中国新移民人口迁移的特征分析》,《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4年第4期。
[17]驹井洋:《多文化社会への道》,明石書店,2003年,第231~260页;陈于华:《新来中国人のコミュニティの成長と日本社会への関わり》,《アジア遊学》2007,104。
[18]ロバート·D·パットナム著,柴内康文訳:《孤独なボウリング:米国コミュニティの崩壊と再生》,柏書房,2006年,第14页。
[19]ナン·リン著,筒井淳也等訳:《ソーシャル·キャピタル:社会構造の行為の理論》,ミネルヴァ書房,2001年。
[20][33]バリー·ウェルマン著,野沢慎司·立山徳子訳:《コミュニティ問題:イースト·ヨーク住民の親密なネットワーク》;野沢慎司編《リーディングスネットワーク論:家族·コミュニティ·社会関係資本》,勁草書房,2006年,第161页。
[21]猪俣圭介:《コミュニティ概念の再検討:『地域』を軸にした教育の実証的研究へ向けて》,《大阪大学教育学年報》2011,6;前林清和:《Win-Winの社会をめざして:社会貢献の多面的考察》,晃洋書房,2009年,第79页。
[22][30]王维:《华侨的社会空间与文化符号:日本中华街研究》,中山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0~11页。
[23]项飚:《传统与新社会空间的生成:一个中国流动人口聚居区的历史》,《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6期。
[24]游仲勋先生古稀纪念论文集编辑委员会:《日本における華僑華人研究》,風響社,2003年,第281页。
[26]参见“中国强化欧美同学会建设,打造留学人员之家”,http://www.coea.org.cn/472/2016/0808/4938.html。
[28]张剑波:《よりよい共生のために―在日中国人ボランティアの挑戦》,日本侨报社,2015年。
[29]杉浦直:《文化·社会空間の生成·変容とシンボル化過程》,《地理学評論》1998,71(12)。
[31]张慧婧:《日本名古屋华侨社区的演变与重建》,《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1年第4期。
[32]山本明代:《アメリカ合衆国におけるハンガリー系エスニック集団の形成とコシュート像建設運動》,《スラブ研究》1998,45。
[34]安田雪:《パーソナルネットワーク:人のつながりがもらたすもの》,新曜社,2011年。
[35]参见《“中日友好的根基在民间”——专家解读习近平出席中日友好交流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http:// japan.xinhuanet.com/2015-05/25/c_134266409.htm。
[责任编辑:乔印伟]
From “Job-housing Space”to “Social Space”:The Adaptation Strategies of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Japan
ZHANG Hui-jing
(School of Law and Politics, Tianj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Tianjin 300384,China)
Japan;new Chinese immigrants;immigrant communities;association networks;jobhousing space;social space;social capital
This paper is based on sources from print materials and field research and follows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It uncovers how new Chinese immigrants in Japan create the bonds and accumulate social capital (networks). It indicates that new Chinese immigrants have built network-style“social spaces”for ethnic communities to replace the enclave-style“job-housing space”of the early Chinese immigrants. This paper also examines how new Chinese immigrants adjust themselves to the new environment to meet their needs even if when Sino-Japanese relations become unstable.
D523.8;D634.331.3
A
1002-5162(2016)03-0017-10
2016-04-15;
2016-08-02
张慧婧(1984—),女,日本名古屋大学社会学博士,天津理工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城市社会学、人口迁移与跨文化交流、海外华侨华人问题研究等。
*本文为2015年度天津市“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程资助项目和2015—2017年度中国侨联课题(项目编号:15BZQK205)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