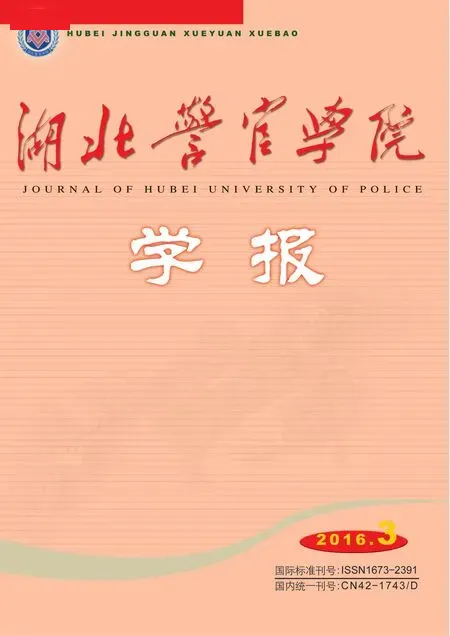军事司法的国际趋势
Arne·Willy·Dahl(著),夏 勇(译)
(1.挪威武装部队、军事法与战争法国际协会,挪威 奥斯陆;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430073)
军事司法的国际趋势
Arne·Willy·Dahl(1著),夏勇(2译)
(1.挪威武装部队、军事法与战争法国际协会,挪威 奥斯陆;2.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湖北 武汉430073)
国际社会近年对军事刑事司法问题表现出浓厚兴趣,各国军事司法制度在和平时期的发展趋势是从完全的军事法院向民间体制转换——减少军事法院的管辖、取消军事法院或者取消军事起诉。这在欧美和非洲诸国的军事司法改革中得到了明确体现。
军事司法;趋势;军事法院;民间法院
各位朋友,各位同仁:
军事司法得到了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密切关注。
2001年,我所在的军事法与战争法国际协会作了相关的比较研究,并于同年在希腊罗德岛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提交了研究报告。这项研究是协会在1979年安卡拉大会类似成果基础上的延续,而在今年9月下旬将要举行的大会——罗德岛第二次会议上还要进一步发展。
同时,匈牙利分会组织的一年两次的学术会议,围绕军事司法和犯罪学的几个方面,积极地推进这项研究。今年9月上旬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会议将聚焦军事司法领域的某些人权问题。
2007年9月,社会防卫国际协会在西班牙托莱多市组织了一次会议,论题是国际军事干预中的刑事司法与合作。11月,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事处会同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和巴西政府举行了有关人权和军事法院司法管理的专家会议。
2009年6月,设于日内瓦的“武装力量民主控制中心”举办了专题研讨会,主要讨论了一些阿拉伯国家进行军事司法改革的可能性。
还有一些其他的相关会议和倡议,其中之一是我未出席的2010年在韩国召开的一次会议。总之,这些活动显示出世界范围内对军事司法的浓厚兴趣。
为了评估军事司法的国际趋势,我从2011年开始研究。当时,受访者在回答其他问题时也回答了以下问题:
请指出是否存与人权有关的对贵国军事法律制度的讨论、评估或改革,诸如《欧洲人权公约》或者其他适用于贵国的类似文本所规定的内容。
自2011年以来,我通过个人接触、访问以及匈牙利组织的一年两次的会议上提交的发言收集到了更多的资料。然而,直到2011年9月罗德岛第二次会议,这些资料才得到系统更新。
本文对军事司法国际趋势的评述将集中于两个因素:(1)人权对法院公正、被告人权利等的影响;(2)民间社会总体上日渐增多的怀疑倾向可能导致改革的要求,以防止任何放纵罪犯的可能性或者由多少是自给自足的军事司法体制造成的错案。
近年来,很多国家的军事司法制度发生了巨大变化。要把握趋势,就必须简明扼要,而不能纠缠于细节。
我首先做的简化工作,是把军事司法制度分成两种类型。军事法与战争法国际协会2001年的调查显示,35个受访国家的军事司法制度可以分成基于个案召集军事法庭的英美体制和基于常设法院的欧陆体制。
英美体制首先见于英国及其前殖民地,而某些实行欧陆体制的国家可能在遥远的过去也曾有过类似于英美的体制。应当注意的是,有几个国家完全取消了军事法院,将军事刑事案件交由民间法院审理。在一些国家,这可能是带有特殊性或者军事元素的民间法院;而在另一些国家,则可能是没有任何特殊性的完全的民间法院。军事司法体制还有平时与战时之分。
这促使我按照一条中轴线来分布各种军事司法制度——一端是完全的军事法院体制,另一端是完全的“民间体制”。

个案召集的军事法庭常设军事法院特别的民间法院和平时期普通的民间法院平时与战时的普通民间法院
我所知道的军事司法制度的所有变化,都是按照上表中从左到右的方向发生的。
澳大利亚的军事司法制度自2006年以来,在国会中遭到强烈的批评。针对军事司法的独立性,公众对军事司法体制有效性的质疑和其他有关事项提出了许多建议。其中一项是要引进常设军事法院,以替代个案召集的军事法庭。澳大利亚于2007年通过了这项提议,但2009年澳大利亚高等法院宣布其违宪。
比利时2004年废除了军事法院在和平时期的存在。1899年的旧法被认为与《欧洲人权公约》不相适应。因而新法规定,在和平时期,比利时军人即使在比利时境外犯罪,也由比利时普通法院审判。在战时,则有新创立的军事法院和诉讼程序。
在加拿大,作为宪法的主要部分之一的《加拿大权利和自由宪章》明显促进了军事司法制度的变化。宪章精神导致军事和民间司法制度的迅速收缩。然而,加拿大最高法院于1992年重新确认了与众不同的独立军事司法制度的必要性和军事法院的合宪性。
1999年9月,加拿大进行了军事司法制度的重大改革,以适应现代化需要,并确保能够反映加拿大的社会准则和价值。这包括取消虽然自1945年以来就再未适用但仍然作为军事司法制度中的刑罚而保留的死刑。
在捷克,军事法院于1993年被废除。这是国家政治和经济社会变迁的结果之一。军事法院的任务由民间司法组织承担。
在丹麦,2005年的改革区分了刑事审判案件和即决处罚案件。丹麦军事诉讼由国防部长领导,但独立于军事指挥和行政管理系统。改革后,军事诉讼没有即决处罚的权限。
芬兰2001年进行了军事诉讼制度的改革。为了避免军事当局对法院审理程序产生影响而招致批评,军事起诉人不再由军事法律顾问担任,而改由公诉人担任。根据2009年6月的一份报告,进一步的改革正在进行之中。最令人感兴趣的建议可能是对简易处罚的上诉权利。
爱尔兰为了使《欧洲人权公约》融入国内法和欧洲人权法院的相关裁决,正在对其军事法律制度进行全面审查。军事案件由常设法院的终身法官审理。
几个世纪以来,荷兰武装力量自行决定军人是否必须被起诉任何涉嫌的罪名。针对军事的法律制度完全由军事司法掌控。一旦决定起诉,军人必须在军事法庭受审。这就意味着指控、判决、处罚、执行全由军队负责而没有民间社会的参与。
1990年,几部新的法典通过立法审查后出台,实现了军事刑法和军事纪律法体系的现代化。对军人的司法管辖交给了民间法院,并集中于阿纳姆地区法院和阿纳姆上诉法院。单独的军事审判庭保证了法院必要的军事元素。目前,公诉人——文职人员而非军官决定是否对军人起诉。
突尼斯于2000年6月13日修订了《军事司法法典》。在一方当事人不是军人的情况下,除了个别的例外,军事特别法庭不再享有对触犯普通刑法典的犯罪行为的管辖权。作为最近政体变化的结果,更多的现行立法要被重新审议。这可能也会影响军事司法制度。
英国军队的军事纪律制度自1996年以来发生了广泛的变化,以确保其更加贴切地反映《欧洲人权公约》。伴随欧洲人权法院对芬德利诉英国案判决的出台,1996年《英国武装部队法》修改了程序,主要是使军事法庭的召集人、法庭成员以及公诉人脱离通常的军事指挥系统,以保证军事法庭的客观性和公正性。
接下来的情况很清楚,英国的军事简易处理程序也面临《欧洲人权公约》第6条的挑战。因此,2000年的《武装部队纪律法》对程序进行了修改,前所未有地允许军人可在所有的即决案件中随其所愿地选择由军事法庭审判;而且,即使不做这种选择,现在也有权向即决案件上诉法院上诉。这种制度也获得了法理上的支持。
对英国制度有实质影响的最近一项国内立法是2006年的《武装力量法》。该法于2006年底得到了英王的御准,并于2009年生效。该法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三军建立统一的军事纪律制度。
《军事法与战争法评论》2006年第3—4卷中的一篇文章介绍了新西兰军事司法制度的最新变化。就该文而言,最重要的因素似乎是新的军事法院结构,以固定的军事法院取代临时法庭,并增加了被告人选择由军事法庭审判以取代受到简易审理的权利,这也是获得法定代理的权利。
在南非,1957年有关军事司法的法律被1999年军事纪律补充法》所取代。如果被告人选择简易处理并且服罪,则可以按照简易程序处理。上尉及以上级别的军官不能以简易程序处理,而必须被起诉到军事法庭。这种限制也许会被终止。
西班牙的上诉程序复杂,被批评与《欧洲人权公约》第7议定书(未被批准)和1966年《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4条第5项不一致。看来,上诉救济管道将不得不被改革,包括对军事法院判决的上诉。
在美国,自2001年5月以来,改革的建议在“考克斯报告”中得到推进。建议之一是增加军事法官的独立性、实用性和责任性。
根据该报告,军事法官长期以来既缺乏充分的独立,也没有被赋予足够的权力而在审判中担任有效、公正的裁决者,从而引起人们对军事司法制度的质疑。有建议创立由职业法官组成的常设巡回法庭,并授权其在一定地域范围运作军事法庭;也有建议对担任军事法官的军官设立固定期限,全面增进军事法官的独立性。增进司法独立被认为是关键所在。它能使正当程序的标准得到坚守,公众对军事法庭公正性的信心得到维持,美国军事司法也可以更加接近世界上其他军事刑事司法制度的标准。
然而,2001年9月11日的悲剧事件和随之而来的反恐战争已将注意力引向其他事务,诸如由军事组织审判恐怖嫌犯,以至于上述问题没有提上这次会议的日程。
人权的影响
人权的影响明显在那些《欧洲人权公约》缔约国和这些国家的附属国尤为强烈,如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欧洲人权公约》产生特别强烈影响的原因似乎是感到冤屈的个人在获得欧洲人权法院有束缚力的裁决通道。在这样的裁决中,公约不仅被适用,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被理解为不断发展的标准。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第5条第1段第1项的规定:
每个人都有个人自由和安全的权利。除非在下列情况下并符合法定的程序,任何人的自由都不能被剥夺……
同样说明问题的是第6条第1段的规定:
在决定一个人的民事权利和义务或者决定针对一个人的任何犯罪指控时,每个人都有权获得由依法设立的独立而中立的组织进行公平公正的审理。
这些条款限制了那些未经正当程序的简易程序就能作出处罚的范围。它们也要求军事法院必须是独立的,即不能由与审理结果有利益关系的指挥官召集军官组成。尽管法庭也许在事实上能做到充分的公正,但司法不能只是做了什么,还必须是看起来做了什么。
普遍怀疑
大众传播媒体和政治家所代表的普通民众不时爆发对军事法院的普遍怀疑。批评往往由不幸事件引发,却并不一定理所当然。
例如,在英国驻伊拉克部队于2003年和之后牵涉的一些丑闻事件中:
——假如军队或宪兵或政府作出的决定是不起诉,就会被指责为掩盖政治动机。
——假如起诉被告人中的一些人而不是全部,同样地,各方都会面临这样的断言,如“要承担责任的是士兵,为什么要试图毁掉那些功勋卓著的军官们的戎马生涯呢”,又如“要承担责任的是获得高薪的军官,为什么要指控贫穷的士兵呢”,再如“军人只是试图做那些从一开始就绝不应当着手进行的困难且危险的工作而已,为什么要起诉他们中的任何人呢”。同样的批评也发生在其他国家,并不时导致把军事司法任务向民间组织转移的不可逆转的改革。
为何当今会出现这样的发展,而过去,如半个世纪之前则没有?一种可能的理由是,正在经历“民间化”的各国对于可能危及自身生存的战争威胁视而不见,因而未把军事效能的考虑放在首位。另一种可能的理由或者起作用的因素是征兵制的取消,久而久之导致公众与军事疏远。
我们还可以从武装力量对民间政治体制的从属性中寻求解释。作为一个宪法问题,它被西方式民主视为理所当然,但事实上并不尽然。在宪法之外,这也是一个观念问题:政治家应该插手军事事务吗?社会是多样的。在一些国家,民间社会和军事大致是两个平行的系统。这类国家中,军事司法制度的“民间化”在最近的将来难以期待。
结论
可见,国际背景中的军事司法发展的明确趋势与涉及人权标准的被告人权利有关。其要旨为:
——法官更加独立;
——常设法院;
——增加选择审判方式代替即决程序的权利;
——增加法定代理人的权利。
进而,尤其在和平时期,存在从军事司法转向民间管辖的趋势,表现在:
——减少军事法院的管辖;
——取消军事法院;
——取消军事起诉。
在那些受《欧洲人权公约》影响的国家,这些趋向特别明显。
反响
对于那些从事并相信军事司法制度的人来说,成为怀疑的对象和失去自己的任务是痛苦的。
然而,反响不应当是针对人权保护的争论。依我所见,值得关切的问题是军事案件的处理需要优先性和专业性。军队是为数不多的社会分系统之一,允许使用致命的暴力,并且它也是要求其成员为了完成任务要承担额外的甚至放弃自己生命的危险的唯一分系统。
军事案件应当由熟悉士兵和军官生活的人来起诉、辩护和裁判。问题的关键是由同僚裁判。
在伊拉克的射杀案件中,阿纳姆法院上诉庭引起了公诉人办公室的不满。前者明显缺乏对军队活动的了解,而后者抓住此案不放。①公诉人是平民(即非军人身份——译者)。因此,建议公诉人办公室和国防部建立对话和资料分享机制,以避免同样情况的再次发生②摘自《荷兰军法评论》2005年6月刊,第213-224页。(该案详见2006年在斯海弗宁恩召开的军事法与战争法国际协会第17届大会公报)。
在本案中,法院胜任其职,而检察官明显不称职。民间化的步子似乎太大了。
谢谢在座的各位。
【责任编校:王 欢】
International trends in Military Justice
Aine·Willy·Dahl
(Norwegian Armed Forces,Oslo,Norway)
There are trends with regard to shifting from military to civilian jurisdiction, particularly in peacetime, by:1)Reducing the competence of military courts;2)Abolishing military courts;3)Abolishing military prosecution. These trends are particularly visible in countries that are under influence of the European Convention on Human Rights. There are clear trends in the development of military justice to be seen on the international scene with regard to the rights of the accused with reference to human rights standards.
Military Justice; Trends; Military Courts; Civilian Courts
E126
A
1673―2391(2016)03―0102―04
2016-06-12
Arne·Willy·Dahl(阿恩·威利·达尔)将军,挪威武装部队军法署长,时任军事法与战争法国际协会主席;夏勇(1956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军事法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刑法和军事法。本文是作者在耶鲁大学法学院军事上诉国际研讨会”(2011年4月1日至2日)上的演讲,原文见http://www.law.yale.edu/news/gmas_readings.htm。本文的翻译发表得到了作者本人的授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