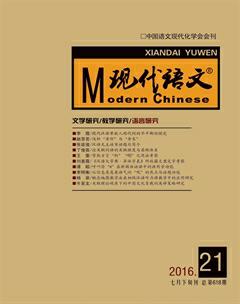解读《斯通与骑士伙伴》的后殖民互文性
○李筱洁
解读《斯通与骑士伙伴》的后殖民互文性
○李筱洁
摘 要:《斯通与骑士伙伴》是奈保尔唯一一部与第三世界毫无关联的小说。这部小说与英美经典文本存在着明显的互文性关系。这种互文性同时具备了“模仿”与“改写”的双重含义,模仿是对语言与文体的延续,改写则成为颠覆英美文学传统的有效手段。奈保尔“戏仿者”的后殖民文化身份在小说的互文性中得到确定。
关键词:《斯通与骑士伙伴》 后殖民 互文性 模仿 改写
一直以来,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V.S.奈保尔都被文学研究者们视为后殖民主义代表作家,他的作品多以亚、非、南美等地社会生活为题材,以“边缘人”的视角冷静的记述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与欧美中心世界的碰撞与交融,如小说类作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抵达之谜》《模仿者》等,又如非小说类作品《幽暗国度》《印度:受伤的文明》《印度:百万叛变的今天》等。在奈保尔众多充满异域特色的作品中,1963年出版的小说《斯通与骑士伙伴》显得非常特别。在它之前和之后的小说中,奈保尔的主人公们都身处英国以外的第三世界或者来自第三世界,研究者都能在他们身上找到奈保尔本人的影子,而这部小说却是唯一一部完全以英国为背景的作品,其中的所有人物亦均是英国白人,他们的身份和经历与奈保尔本人更是相去甚远,研究者们似乎很难给这部小说贴上后殖民的标签。
据笔者了解,目前国外发表的《斯通与骑士伙伴》的相关研究文章并不多,最早可追溯至Walter Allen于1964年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又见伦敦》。Anthony Boxill的《<斯通与骑士伙伴>中的春天概念》一文探讨了小说中反复出现的春天意象和主人公心理变化的关联。Gillian Dooley发表的论文《奈保尔“失实的”伦敦小说:<斯通与骑士伙伴>》通过横向与纵向的文本分析对该小说的“失实性”做出了论证。在我国,与它之前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1961)和之后的《模仿者》(1967)相比,《斯通和骑士伙伴》显然没有引起太多研究者的注意,通过笔者在中国知网上所做的相关搜索可窥一斑:在摘要检索中搜索奈保尔上述三部作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和《模仿者》分别显示48条结果和43条结果,而《斯通与骑士伙伴》则没有任何搜索结果。我国研究者仅在介绍奈保尔写作生涯时对该小说有所提及,且都是一带而过式的,甚至在研究奈保尔的专著中出现了对该小说的错误描述。[10]多年来,国内外研究者不遗余力地反复解读奈保尔那些有关第三世界作品的政治性、历史性以及后殖民文化属性,强调特殊身世与经历赋予他的独特书写视角,分析其小说中众多人物所具有的文化无根性,却忽视了这本“小书”所暴露出的奈保尔本人的后殖民文化身份。
《斯通与骑士伙伴》讲述了斯通先生暮年的一段人生经历。小说初始时,六十二岁的斯通先生还是个孤独的单身汉,住在伦敦南部的一幢宅子里,由一名同样上了年纪、邋里邋遢的女管家照顾他的生活起居。斯通先生是一名普通的图书管理员,供职于一家名叫伊斯卡尔的公司,退休指日可待。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斯通先生结识了小他十来岁的寡妇斯普林格太太,两人很快相爱结婚,但婚姻生活并没有消除斯通先生的孤独感,反而使他感到距离亲人更远了。退休意味着衰老甚至死亡,这让斯通先生惶恐不已,在此压力下他设计了一个拜访退休员工的计划,这个被称作“骑士伙伴”的计划被公司采纳并付诸行动,斯通先生藉此登上了人生的巅峰,但事实上真正从计划中获益的是他的年轻搭档,而斯通先生在短暂的荣耀后依然要面对即将到来的退休生活。小说篇幅尽管不长,却涉及了衰老、死亡、人性、婚姻、家庭关系、工作、友谊等诸多主题,叙事充满奈保尔惯有的不动声色和辛辣讽刺的风格。而与其他作品不同的是,奈保尔这部“白人”小说中多次出现了文本互文现象,互文性成为这本小说的一大特征。
“互文性”概念最先由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提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本文都是其它本文的吸收和转化。”[1]互文性理论具有极强的包容性与概括性,许多结构主义理论家认为,从广义来讲,互文性在文学作品中无处不在,不论作家有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一个文本有很多方法来提及另一个文本,例如戏仿、拼贴、呼应、典故、直接引用以及平行结构。保罗·瑟洛克斯在其第一部研究奈保尔的专著中盛赞他“也许是现在唯一一位未受他人影响的作家”。[2]但这一褒奖放在任何作家身上都显得过于武断,包括奈保尔。曾在牛津大学攻读英语语言文学的奈保尔,研读英美经典文学作品是他的必修课,在创作初期写作题材和写作风格都还处于摸索阶段时,这些来自西方的经典必定成为作家参考模仿的对象,这就解释了为何奈保尔会在早期创作出《斯通与骑士伙伴》这样一部完全由英国白人构成的小说。在一次访谈中奈保尔曾直言自己在创作《斯通与骑士伙伴》期间尚处于“非常摇摆不定”[3]的阶段,在作家本人的漂泊经历不能为他提供充足的参考素材时,向英美宗主国的文学传统提取灵感并模仿其中经典形象与桥段是作家的必然选择,因此文学作品间的互文性成为解读该书一个重要通道,而奈保尔的后殖民文化身份又使得这种互文性具备了“改写”的第二重涵义。
一、模仿——语言文体的互文
奈保尔的小说语言一贯以冷峻、直接著称,其中不乏幽默的反讽,读者经常能够从他的小说中读到可与王尔德媲美的机智诙谐,在这本《斯通与骑士伙伴》中,奈保尔更是以各种方式多次向王尔德致敬,实现与西方经典文本的互文。其中最明显的当属斯通先生的侄女格温曾在一次家庭聚会上表演了王尔德的《不可儿戏》:
在全神贯注的状态下,她表演了剧中的一段,其间还一人分饰数个角色,用头部的忽然晃动来表示角色的转换。她没有一处忘词,也没在表演中失去镇静。在压低了嗓子说“在手提包里”这句台词时,因为把声音压得太低,以至于“手”这个词听起来像是喉咙间发出的干吼。[4](P50)
除了这样直接的借用,书中一些幽默辛辣的人物刻画也可以被看做是对王尔德式悖论(paradox)的互文与效仿。在描述公司老板哈里时,奈保尔是这样写的:“老哈里——不熟悉他的人是这么称呼他的,而那些能和他说得上话,并以此为荣的人则称他为哈里爵士——是个让人敬畏的人物。”[4](P77)众所周知,通常人们会用较为亲昵的叫法(“老哈里”)来称呼自己熟悉的人,而用带有头衔的叫法(“哈里爵士”)来尊称不熟悉的人,奈保尔的这段描写显然与常识相悖,但是这种似是而非的描述却恰好反映出老哈里爱慕虚荣的个性,这样的行文风格不能不让人想起王尔德对萧伯纳的讥讽式评价:“他在世上绝无敌人,也绝无朋友喜欢他。”[5]同样,奈保尔笔下的寡妇格蕾丝与《不可儿戏》中那位丧夫之后“足足年轻了二十岁”“头发因为悲伤而变成了金色”[6]的哈伯里太太有异曲同工之处:
这个憔悴的妇人,在冬天的凄风苦雨中,却一周比一周神气起来。悲伤渐行渐远,直到有一天突然踪迹皆无。……那张全是皱纹、憔悴的脸庞逐渐饱满起来;松弛的脖颈似乎也挺拔了些;眼睛变得明亮;一贯低沉的声音,变得更加低沉,语调则越来越振奋。她的行为举止中,多了一种自由感,好像是从某种枷锁中挣脱了出来。[4](P134-135)
如果说奈保尔对王尔德的模仿还只是停留在语言文字的层面上,那么他对另一位作家的模仿则深入到了文体风格的层次。《斯通与骑士伙伴》的一个关键主题是衰亡,这不得不让人想到创作主题常常与衰亡相关的伊夫林•沃。事实上,沃对奈保尔的影响是有据可循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奈保尔开始了他的创作生涯,当时伊夫林•沃在英美文坛中正备受瞩目,这位杰出的讽刺小说家给初出茅庐的奈保尔带来不少启发。在接受诺贝尔奖获奖访谈时奈保尔坦言:“我从十七岁时开始写作,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伊夫林•沃的影响,那时我写的是以特立尼达为背景的闹剧。”[7](1:46-2:00)对研究者而言,审视对比两个作家的创作时,文体风格的相似性显然不如语言文字的相似性那样易于识别。文字是可看到的存在,而风格则是潜于文字之下、体会得到却看不到的东西。在描写人物如何面对衰老/死亡上,奈保尔和沃采取了风格相似的手法。沃在《亲者》中如此描述女主人公生命中的最后经历:
从她的套房到“丛林低语”短短的行程中,她没有遇见任何人。……她的心中摆脱了焦虑。……艾梅迅速沿着石子路走到殡葬场大门。在接待室里,值夜职员正在喝咖啡。当她默默穿过他们时,他们漫不经心地瞥了她一眼,因为时时刻刻都有紧急工作在做。她乘电梯来到顶楼,那里除了覆盖着的死人外,一片静寂,空落落的。……她没有写告别信或道歉信。她已经远离社会习俗和人的义务。[8]
奈保尔在最后一章这样描述斯通先生:
他迈开步子,很高兴发生了这样的意外,希望这样一直走下去,把自己累倒,这样内心的痛苦就不能再折磨他了。他对周围的人没有什么知觉,对他而言,他们长得一样,穿得也一样。……对人来说,这些身外之物都不重要,而重要的身躯却脆弱不堪,终有一天会腐朽。……走回家的那段路上,他迈着大大的、艰难的步子,感觉自己变得高大起来。他觉得自己像一个摧毁者,带着毁灭地球的使命。[4](P163-164)
尽管奈保尔的遣词造句与沃不尽相同,但行文的紧凑和冷峻却与沃如出一辙,此外,斯通先生与艾梅一样都是通过一场置身世外的行走完成了对衰亡的领悟。
谈到文本的互文性时,罗兰•巴尔特将文本比为织物,笔者认为,模仿是第一层次的互文,是庞大的文本织物中最清晰的脉络。奈保尔通过模仿英美作家的语言文字以及文体风格充实了自己的创作,延续了语言与文体的生命活力。不过,这部小说的互文性并不仅仅停留在对英美经典作家的模仿上。
二、改写——文化符号的互文
《斯通与骑士伙伴》中出现了两只黑猫,与美国小说怪才爱伦•坡的《黑猫》——同样是出现了两只黑猫的著名恐怖小说——有着明显的互文。西方民间传说中,黑猫被视作不祥之物,它的出现常常意味着厄运与悲剧的到来。坡的小说就借用了黑猫的这一符号意义,将其成功地塑造为经典的恐怖形象。《斯通与骑士伙伴》则以斯通先生与黑猫的不期而遇开始,又以他与黑猫的后代——另一只黑猫的相遇收尾,从最初对黑猫的痛恨到遗忘再到最终的惺惺相惜,斯通先生与两代黑猫的关系经历了一系列变化。两部小说对黑猫的描写存在许多相似之处:黑猫都是突然出现在主人公眼前,从而激怒他采取一定手段(暴力或者引诱)意图伤害黑猫;第二只黑猫都延续并加强了第一只黑猫的特征以及与主人公的关系。而两部小说的黑猫形象所营造的氛围和代表的含义却不尽相同:爱伦•坡笔下的两只黑猫象征着绝望与罪恶,揭示了现代人精神的异化与分裂。而奈保尔笔下的两只黑猫则毫无恐怖意象可言,虽然第一只黑猫曾令斯通先生愤恨不已,以至要索其性命,但愚蠢可笑的诱杀未遂暗示着全书忧伤而不乏幽默的基调,小说后半部中,当斯通先生被抛弃于骑士计划之外后,他看黑猫时不再是憎恨,而变为惺惺相惜。第二只黑猫的出现更凸显了作家对衰老与生命更迭的领悟,读者在它身上读出了谅解与希望。最后一次看到黑猫,斯通先生感到“惶恐里掺杂着内疚,内疚里掺杂着爱怜。”[4](P164)黑猫这一意象的设置显现了作者对西方文学乃至西方文化传统符号的颠覆,他的创作更新了“黑猫”这一经典意象的内涵,赋予其更具生命力的意义。
圆桌骑士的故事是任何一名西方文学研习者必读的文本,亚瑟王和他的骑士们的传说不断被历代作家重写、改编和沿用,其文化影响之深远,足以与《圣经》媲美。亚瑟王与圆桌骑士的故事是凯尔特神话中的著名传说之一,亚瑟通过拔出石中王者之剑而赢回王位,他与圆桌骑士一起击退了央格鲁-撒克逊人的入侵,亚瑟王由此成为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君主之一。亚瑟王的骑士们品德高尚,骁勇善战,在捍卫国家和寻找圣杯的征程中英名永存。在无数英美文学艺术作品中,亚瑟王和圆桌骑士已成为正义与美德的化身,而他们商讨国事时使用的圆桌更被赋予特殊的含义。据传亚瑟王与骑士们举行会议时,不分上下主次围桌而坐,避免了因座位等级的差异而引起的纠纷,于是圆桌成为人文意识中平等思想的集中体现,是西方引以为荣的民主精神的雏形。而在《斯通与骑士伙伴》中,奈保尔则借用这一古老而又意义重大的神话,对亚瑟王、骑士和圆桌会议这三个意象进行了重构。书中具有亚瑟王特征的人物是公司老板哈里爵士,与他的爵士头衔不符的是,老哈里本质是个平庸自私、装腔作势的人。他写给《泰晤士报》的信全部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话题,而这些信却使他成为公司上下敬仰的人,“每一封信的发表都让他显得更加难以接近。”[4](P79)公司的表彰年会上,仿照圆桌会议,温珀设计了一次圆桌晚宴,但席间气氛却与圆桌精神相去甚远,首先是座位的设置,很显然哈里爵士占据了最重要的位置,其次是宴会发言,并不是每个人都有畅所欲言的机会,整个宴会的高潮是哈里爵士的致辞,这再次显示了他独一无二的重要地位。而老哈里的虚伪在他讲话的最后部分显露无疑。
“好了,最后——啊哈!”哈里爵士猛地抬起头,视线从打印稿件上离开,“你们肯定觉得我会说‘最后但并不代表最不重要的’!而我要说,最后,也是最不重要的,就是那个让你们重新回到工作中,成为今晚真正的明星的人。”……他在大家疯狂而热烈的掌声中和“好哈里,老哈里!”的呼喊声中坐下。[4](P124)
欲擒故纵的话语中暗示了他自己才是最重要的人物。老哈里这一角色完全颠覆了传说中正直的亚瑟王形象,而奈保尔颠覆的还不止这个,除此之外,圆桌骑士也成了他揶揄的对象。书中的“骑士”实际上是一群已经从公司退休的老人,因为斯通先生提出的“骑士伙伴”计划而被召集起来,委以拜访其他退休员工的任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老“骑士”们既没有凯尔特骑士的强健体魄,他们为之奔波的事业也远非寻找圣杯那样神圣重要,他们甚至缺乏代表正义诚实的骑士精神。有人假借拜访之名,对被访者宣传宗教教义,更有人虚报费用,中饱私囊。备受西方推崇的骑士精神在这部小说中被完全改写,西方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在奈保尔这个“外人”看来是不可靠的。
当然,西方文化将黑猫妖魔化,其根源来自于人类对自然力量的不解和敬畏,将亚瑟王和圆桌骑士英雄化,其本质是对正义、民主和平等的颂扬,这些都是被普世认可并接受的常识,因此不能简单的说西方文化是虚伪丑恶的,造成奈保尔以如此视角来改写西方文化符号的真正原因在于文化差异,更在于强势文化与弱势文化之间的不平等。差异引发歧义,互文与模仿不再是一维的重复,而变成了带有延异性的挪用。不平等的文化对话背景下,互文与模仿必然成为带有反讽意味的戏仿,是“从殖民想象的高级理想向其低级模拟效果的喜剧性转向。”[9](P85)
值得注意的是,模仿是一个文本对另一个文本浅层的吸收,而改写则是深层的颠覆。存在于这部小说中的互文现象,作者的主要目的并不是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致敬,甚至也不是再现文本之间的共性,事实上,奈保尔的互文模仿展现了文本间以及文化间的差异,英美文学经典的强势地位在这部小说中不再牢不可破。正如霍米巴巴所说,“模拟是殖民权力与知识的最无从捉摸、最有效的策略之一。”[9](P85)文本的互文其实就是主体间的对话,也就是主体背后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在当下文化殖民霸权已经全面取代地域殖民霸权的时代背景下,强势文化影响并改变着弱势文化,这种文化上的渗透乃至入侵往往难以阻挡,那么弱势文化该如何在这种影响和改变下葆有自我独立性,这就成为后殖民视域下文学作品互文性所要关注的关键问题。可以说后殖民文学作品的互文与戏仿挑战了宗主国殖民话语的整体性与权威性,为弱势文化的自立和发展另辟蹊径。奈保尔回顾创作生涯的早期阶段时曾说自己那时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要发掘我是个什么样的人”[7](1:24-1:36),当然,对于那时的奈保尔来说,这个问题可能的确令他困惑,但在当下奈保尔的研究者眼中,《斯通与骑士伙伴》——这部与第三世界毫无关联的小说——则最好的印证了奈保尔“戏仿者”的后殖民文化身份。
注释:
[1][法]朱丽娅•克里斯蒂娃:《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引自朱立元:《现代西方美学史》,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3年版,第947页。
[3][美]Bharati Mukherjee and Robert Boyers:,Feroza Jussawalla ed:,Jackson:University Press of Mississippi,1997,p78.
[4]吴正译,[英] V.S.奈保尔:《斯通与骑士伙伴》,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13年版。
[5]余光中译,[英]王尔德:《不可儿戏》,台北:九歌出版社,2013年版,第23页。
[7][瑞典]Horace Engdahl:Interview with V.S.Naipaul,http://www.nobelprize.org/mediaplayer/index.php?id=1022:2001.
[8]胡南平译,[英]伊夫林•沃:《亲者》,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327-328页。
[10]杨中举先生所著《奈保尔:跨界生存与多重叙事》一书在以时间为顺序综述奈保尔作品时将《斯通先生与骑士伙伴》归为描写加勒比海地区的作品一类(见杨中举:《奈保尔:跨界生存与多重叙事》,东方出版中心,2009年1月版,第17页),但如本文之前所述,该小说的背景与人物均在英国,所以杨先生的归类显然是不准确的。
(李筱洁 河南郑州 河南农业大学外国语学院450046)
——评《后殖民女性主义视阈中的马琳·诺比斯·菲利普诗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