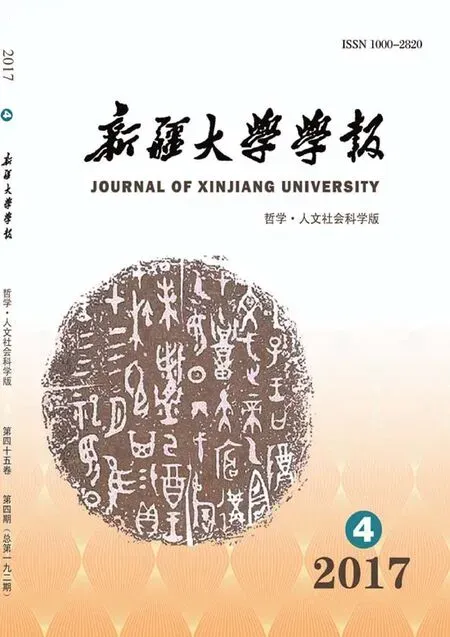“都”“并”“全”的历时演进及相互影响*
曹利华
(1.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四川成都610064;2.攀枝花学院人文学院,四川攀枝花617000)
汉语史上曾表总括、语气,现代汉语仍常用的单音节副词,主要有“都”“并”“全”。它们在汉语史上比较活跃也引起了学界广泛关注,总体看历时研究不多,并且一般只研究单个副词的语法化,语法化动因探讨上也只关注考察对象本身。
关于“都”的语法化路径,代表性观点主要有:张谊生:动词>范围副词>语气副词[1]56-62;杨荣祥:动词>语气副词>范围副词[2]100-103;谷峰利用佛经对勘论证东汉时期“都”根本没有语气副词用例,否定“都”由动词虚化为语气副词的观点;葛佳才认为“都”由动词到范围副词的虚化以方式副词为过渡[3]。关于“并”的语法化过程,胡勇认为:动词>方式副词>范围副词>语气副词,总括对象的消失是“并”演化为语气副词的关键[4];邱峰则认为“并”用作范围副词和语气副词,不存在谁先谁后谁衍生谁的问题,都是在本意的基础上自然衍生的[5]。“全”的语法化研究很少,武振玉描述了历史上“全”用作总括副词、语气副词的总体情况,对语法化未作探讨[6]。
显然,各家对“都”“并”“全”的历时演进和语法化历程尚有分歧,但不难看出:他们一致认为在中古近代汉语时期三者都经历了从动词到副词的虚化,都曾表示总括,都曾在否定句中加强否定语气。
既然在相同的历史时期三者的语法化历程和语法功能有诸多相同,那么基于语言平衡性的考虑,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关系也应当纳入我们的研究范围,作对比研究,统筹考量。正如王云路先生所言:“不但要探讨单个词语的语源和变化……还要发现词与词之间的联系,词族与词族之间的联系,发现某类词语构成和演变的规律。在词义研究的模式上,不能只对词语作单个的、零散的分析,要对一组词、一类词或相似类型的词语作整体考察,要有俯瞰全局的本领,善于概括出同类词语的本质特色……总之,我们应当从史的角度考察词义的发展演变,从整体上系统探讨词汇构成、变化的规律和内部机制,使语汇研究更加科学化、系统化。”[7]
这里我们不揣浅陋,选取中古、近代汉语15种代表性口语文献,穷尽考察“都、并、全”三者在平行历史时段各自的语法功能、语义变化及相互补充、相互制约的关系,以及共存竞争过程中服务语言发展需要而作出的让步和主要功能选择,并从这一角度对它们的语法化路径做出补充解释。
一、“都”“并”“全”的历时演进及功能分化
“都”,本为名词,“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说文·邑部),“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后引申为国都、大都,如“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左传·隐公元年),“是月,六鹢退飞过宋都”(公羊传·僖公十六年)。再进一步引申为动词“聚集”,如:“淮海维扬州,彭蠡既都,阳鸟所居”(史记·夏本纪),“卑也者,道之室,王者之器也,而水以为都居”(管子·水地)。当动词“都”经常性地处于状语位置,就虚化为方式副词和总括副词,如:“而桑弘羊为治栗都尉……置平准于京师,都受天下委输”(史记·平淮书),“莫知其所施为也,而积年之疾一朝都除”(列子·周穆王),“心凝神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列子·黄帝),“儒不能都晓古今,欲各别说其经,经事义类,乃以不知为贵也”(论衡·谢短篇)。一般认为“‘都’的语法化进程早在先秦就已经开始了”[1]56-62。
“并”,源于历史上的“并、倂、竝、並”。《说文》“竝,倂也”[8]216,《广韵·迥韵》:“並同竝”[9],王力《同源字典》认为四字同源[10]。一般讲“合一为并,对峙为倂”,“副词常写作並”[11]。不过,这四字在汉语史上或分或合,没有一定的规律[12],如,秦汉时“并”“並”可通用;《金瓶梅》(1—10回)用作副词21例均作“並”,连词18例均作“并”;而《西游记》副词、连词共现123例,一律作“並”。故我们在讨论其发展和语义分化时,不再辨析,一律作“并”。
“全”,《说文》:“纯玉曰全”[8]109,如“天子用全”(周礼·考工记·玉人)。引申为纯粹,进而为形容词和动词。形容词意为“完备、完全、整个”等,如“天下之非誉,无益损焉,是谓全德之人哉”(庄子·天地),“其为舟车也,全固轻利”(墨子·辞过),“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庄子·养生主)。动词意为“使完整、使保全、保全”等,作谓语,如:“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孙子·谋攻)。先秦时期,“全”只有以上三种实词用法。
“都”“并”“全”三者含义相关,但语义重心不同:“都”的核心义素为[+聚集],指多个单一个体的聚集;“全”的核心义素为[+完好],突出事物的整体性;“并”的核心义素为[+相同、同时],强调两个事物的相关性。可见,三者的语义核心各有侧重,不过随着语言的发展、语义的泛化,三者的语义、用法又有交融现象。三者在平行历史层面上的相似经历和各具特色的演变轨迹,见表1。
据表 1 可知,使用频率方面,“都”“并”“全”三者差别明显,中古汉语时期使用比率为4.4∶4.7∶1,近代汉语时期为6.8∶1.8∶1,整个汉语史上使用比率为6∶2.9∶1,“全”的使用频次明显较少。
从主导语法功能看,“都”“并”“全”三者也各有侧重:整个汉语史上,“全”主要用作动词、形容词;“都”主要用作总括副词。而“并”则比较复杂,动词、情状副词、连词用法贯穿始终;尽管中古时期总括副词用法在其诸种用法中略显优势,但中古汉语时期“并”共现570次,其中用作总括副词119次,仅占总使用量的20.9%,也不占绝对主导地位。这对“都”“并”“全”总括副词、语气副词用法的竞争、演变有直接影响,后文将详述。
从语法功能的分化演进看,“都”在中古时期已很少单独用作名词、动词,一般作为实语素用于地名、职官等词语中,如中都、都尉等。值得强调的是,尽管“都”与其它总括副词的竞争中,直到元代才成为使用频率最高的总括副词[2]316,但是自南北朝以后,“都”的总括副词用法在其诸种用法中便一直占主导地位,这种状况并未因“都”其它用法(主要指语气副词用法)的发展而被动摇,通过表1可见一斑。
“全”汉代开始主要用作动词和形容词,且在整个汉语史上从未间断,直到现代汉语。就我们的统计看,整个中古汉语时期“全”的动词、形容词用法与副词用法的比例为204∶4,占绝对优势;近代汉语时期,“全”的动词用法明显减少,形容词比例增加,副词用法渐强,后两者旗鼓相当,副词略胜。
“并”在汉语史上一直比较活跃,通过其在各历史时期的用法统计可知,“并”用作动词、连词和情状副词贯穿中古、近代汉语时期;用作总括副词和语气副词,则分别出现于中古汉语和近代汉语阶段,时间上呈互补分布,唐五代时期《敦煌变文》 《祖堂集》中两种用法兼具,可视为过渡阶段。

表1 中古、近代汉语时期“都、并、全”的义项分化及使用频次统计①表中“吐鲁番”指唐长孺先生主编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
“并”较“都”“全”又发展出连词的独特用法,且无论从使用频率还是使用时间长短都是其重要的语法功能。例如:
(1)王长史宿构精理,并撰其才藻,往与支语,不大当对。(世说新语·文学第四)
(2)王见女身端政殊特,欢喜踊跃,不能自胜,即敕严驾,王及夫人女并女夫,共至佛所。(贤愚经·波斯匿王女金刚品)
以上两例中的“并”分别连接谓词性、名词性成分。郭齐先生认为“并”连接谓词性成分的用法先出现(公元1世纪),由“并”的副词用法虚化而来;连接名词性成分的用法后出现(公元3世纪),由“并”的介词用法虚化而来。虚化路径分别是“动词(相合)—副词(一并)—连词”和“动词(合并)—介词(连带)—连词”[12]。我们的统计数据与此相符,略作补充:《史记》“并”作连词9例、《论衡》18例、《世说新语》5例,均连接谓词性成分;《百喻经》“并”用作连词5例,连接名词4例,其中3例与“及”同义连用;《贤愚经》“并”用作连词37例,13例连接名词性成分且独立运用,连词用法趋于成熟。至《西游记》《金瓶梅》“并”连接名词性成分的用法已占绝对优势,就前20回的统计数字看,各达79%和92%,至现代汉语此功能基本由“和”担任。“并”较“都”“全”发展出连词的独特用法,主要由三者的核心义素不同所致,如前所述“并”的核心义素为[+相同、同时],强调两个事物的相关性,具有虚化为连词的语义基础。
二、“都”“并”“全”总括副词用法对比分析
“都”“并”“全”三者在历史上都可用作总括副词,我们以详尽数据动态呈现三者在各历史时段代表性口语文献中总括副词的分布及使用情况,并分析各自特点及相互影响(见表2)。
总体看,“都”的总括副词用法贯穿中古近代汉语时期直到现代汉语;而“全”的总括副词用法集中在近代汉语时期,“并”的总括副词用法集中在中古汉语时期,二者在历史时段上基本呈互补分布。

表2 中古、近代汉语时期“都、并、全”总括副词用法统计①表中“吐鲁番”指唐长孺先生主编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
“都”用作总括副词,中古汉语时期初步发展,功能还不完善。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所在句子的谓语多为单音节光杆动词;二是“都”用作总括副词经常和“一切”“皆”“咸”等其它副词连用,共同总括其前的复数性成分;三是受“都”核心义素的影响,整个中古汉语时期“都”的总括对象一般限于多数。举例如下,阐释从略:
(3)始发讲,坐裁半,僧弥便云:“都已晓”。(世说新语·文学第四)
(4)后十日,此家死亡都尽。(搜神记·卷十七)
(5)便作念言:“我已破一戒,既不具足,何用持为?”一切都破,无一在者。(百喻经·杀群牛喻)
(6)王及夫人群臣彩女,闻是语已不能自宁,咸悉都集。(贤愚经·梵天请法六事品)
(7)一切人民男女大小,睹斯瑞应,欢喜踊跃,来诣佛所,十八亿人,都悉集聚。(贤愚经·须达起精舍品)
(8)三十六物一时都捉,不生惭愧,至死不舍。(百喻经·为王负机喻)
近代汉语时期“都”的总括副词用法异军突起,用法灵活多样,对新语言现象的适应性也极强,取得了绝对优势地位,并且完成了对“并”的替代。对此,杨荣祥先生《近代汉语副词研究》[2]315-327论述甚详,此不赘述。
“全”用作总括副词和“都”差别明显,一是使用频次上远少于“都”,整个中古时期只有2例,近代汉语时期也只是零星使用,中古近代汉语时期两者的使用比率为1 322∶60,“都”是“全”的22倍。二是几乎整个中古近代汉语时期(除禅宗文献《祖堂集》、清末文献《红楼梦》),“全”并未用作典型的总括副词,不像“都”“并”等在肯定句中总括其前的复数性成分,而是用在“靠、凭、杖、赖”等凭依类动词前对未完全呈现的话题主语予以总括,如:
(9)刘洪道:“学生到此,全赖诸公大力匡持”。(西游记·第九回)
(10)嫂嫂是个精细的人,不必要武松多说,我的哥哥为人质朴,全靠嫂嫂做主。(金瓶梅·第二回)
(11)若老爷们再要改时,全仗大爷谏阻,万不可另寻地方。(红楼梦·第六回)
(12)晁大舍道:全仗赖用心调理,自有重谢。(醒世姻缘·第十八回)
以上诸例中的“全”,没有明确的总括对象,在一定程度上蕴含了一种语气,表示对所凭之事在整个事件中作用价值的肯定,但是更侧重总括。我们把这一类的“全”看做总括副词,它既可总括相关各事件,如例(9)—(10),又可总括一件事的全部经过,如例(11)—(12)。例(9)可以理解为“学生到此”前前后后所有事情和经过都依赖“诸公大力匡持”。例(10)应该理解为武大郎家里的全部事情,尤其是遵守妇道等事,都由嫂嫂做主。例(11)的“全”总括“阻止老爷再改”一事的全部,例(12)总括“病情好转”一事的全部经过,“全、赖”连用。这种功能是“都”不具备的,这一点相对“都”的总括副词用法具有互补性和不可替代性,所以在使用频率上遥遥领先的“都”并未完成对“全”的替代,而是并行用作总括副词。
“并”和“都”的总括副词用法,在中古时期也有一定的互补性。由于受核心义素的影响,“并”可以总括两个事物,进而范围扩大至多个事物;而“都”的核心意义为“聚集”,具有[+多个]的区别特征,所以整个中古时期“都”的总括对象仅限于多数。近代汉语时期,“并”用作总括副词,总括其前的两个或多个对象,多见于肯定句,偶见疑问句,极少用于否定句,统计范围内仅发现6例,这与肯定句中的比例为6∶197,仅占到全部总括副词用法的0.03%,可见,在总括副词用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方面“并”不如“都”。
“都”发展成为最常用的总括副词,“并”作为总括副词退出历史舞台,原因应该从“都”“并”两方面来分析。从“都”的角度看,一方面,其总括副词用法灵活多样,适应性强,兼有其它总括副词的各种用法;另一方面,其语法功能单一,基本只有总括、语气两种用法,且总括副词用法在数量上占绝对优势,这为“都”发展成为最主要的总括副词,作了充分准备。从“并”的角度看,其总括副词用法不具竞争优势,一方面,总括副词用法的多样性和灵活性方面逊色于“都”;另一方面则兼职过多,动词、连词、情状副词、总括副词等诸种用法并行使用,影响了“并”作为总括副词的竞争力,最终让位于“都”。正如汪维辉先生所言:语言的演变具有自我更新调节机制,通过词义的分担来不断寻得系统内新的平衡,一个词词义负担过重,“就会把某些义项卸给其它词。”[13]
可见,一个词的语法化过程不仅仅和自身的句法位置、语义基础、使用频率等因素有关,还和相关词语的语法功能及使用频率密切相关,这是我们进行对比研究的重要原因,也应该是语法化研究不容忽视的问题。
三、“都”“并”“全”语气副词用法对比分析
“都”“并”“全”三个总括副词都发展出了语气副词用法,它们在汉语史上的使用情况及此消彼长的关系,详见中古、近代汉语时期“都、并、全”语气副词用法统计表3。

表3 中古、近代汉语时期“都、并、全”语气副词用法统计①表中“吐鲁番”指唐长孺先生主编图录本《吐鲁番出土文书》。
通过表3可知,中古汉语时期,“都”一枝独秀,既可用在肯定句中加强肯定语气,意为“完全、确实”,又可用在否定句中加强否定。近代汉语时期,“都”的这种功能由“并”“全”接替,自己又另辟蹊径,在“连+NP+都+VP”中强调其前的“极端事物或现象”,用以加强主观性语气或情感。而“并”“全”的功能也不完全相同,“并”到近代汉语后期发展出“否定预设”的功能。
“都”的语气副词用法经历了两个阶段(参看表3)。第一个阶段为中古汉语时期,主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都”用在否定句中加强否定语气,意为“完全、根本、一点儿也不”等。这种否定句有两种格式,具体为:“都+否定副词(不、未)+VP”和“都+无+NP(VP)”,句子主语一般是VP或“无”的施事,否定副词主要是用于单纯否定的“不”和已然否定的“未”两个单音节词;“无”是本身带有否定意味的动词,故其后可兼接名词性或谓词性成分。去掉“都”句子仍通顺,只是语气减弱。例如:
(13)陶公疾笃,都无献替之言,朝士以为恨。(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14)自然兴慈,等视众生,如父如母,如兄如弟,爱润之心,都无增减。(贤愚经·降六师品第十四)
(15)主人喜,自尔后有役召事,往造定国。定国大惊曰:“都未尝面命,何由便尔?(搜神记·卷十七)
(16)如彼伐树,复欲还活,都不可得。(百喻经·斫树取果喻)
(17)孙曰:“此子神情都不关山水,而能作文。”(世说新语·赏誉第八)
例(13)—(14)“都无”后分别跟名词性、谓词性成分,例(15)是“都+未+VP”,例(16)—(17)为“都+不+VP”,具体又有所不同:例(16)是“都”典型的语气副词用法,句义为“砍伐之树,重新复活,根本不可能”,例(17)中的“都”可看做总括副词与语气副词的中间状态,似乎“都”可两解,既可总括其前的“神”、“情”,也可加强“不关山水”的否定语气。结合上下文和社会背景,后者准确,实际含义为“此君根本不会欣赏山水,怎能作文?”
“都”的这种用法在《世说新语》中异军突起,盛行于整个南北朝时期。在《世说新语》中的“都”共现38例,用于加强否定30例,所占比率达到80%,“都”加强否定的用法占主导地位的状况,《世说新语》以外未发现其它文献。《搜神记》仅2例和总括副词用法旗鼓相当,占总使用量的33%,《百喻经》11例,勉强可与总括副词抗衡,两者比例为11∶17,《贤愚经》明显衰落,与总括副词的使用比率为3∶23,占到总使用量的11%,《太平广记》中,加强否定的副词“都”106例①这里直接使用张谊生先生《副词“都”的语法化与主观化——兼论“都”的表达功能和内部分类》中的统计数字,见《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1期第58页。,但是太平广记500卷,“都”共现1 114次,“都”加强否定的用法仅占9.5%,优势并不明显。之后这种用法比较少见,金元以后,基本消亡。
另外,“都”作为语气副词,也可用在肯定句中,加强肯定语气,义同“完全”,强调程度的百分之百。例如:
(18)王右军年减十岁时,大将军甚爱之,恒置帐中眠。大将军尝先出,右军犹未起。须臾钱凤入,屏人论事,都忘右军在帐中,便言逆节之谋。(世说新语·言语第二)
(19)昔有一人,事须火用,及以冷水,即便宿火,以澡灌盛水置于火上,后欲取火而火都灭,欲取冷水而水复热,火及冷水二事俱失。(百喻经·水火喻)
例(18)大将军与钱凤密谋造反,“屏人论事”,完全忘记了王右军还在帐中,便直言“逆节之谋”。这里“都”主要强调语气,同时也含有程度百分之百的意思,又有程度副词的意味。这里的“都”不能理解为总括副词,因为“都”语义指向“忘”,而只有大将军一人知王右军仍在帐中,只有大将军一人“忘”,这里“都”强调大将军“忘”的程度,而非总括大将军一人。例(19)据文意,此人准备用火发现火完全灭了,准备用冷水,水却是热的。这里“都”强调“火”熄灭的彻底和已然性,而非总括所有的“火”。在其它文献中很少发现“都”的这种用法。
第二个阶段为近代汉语中后期,“都”与“连”呼应,组成“(连)NP都不VP”格式,强调极端的事物或现象,以加强主观性语气或情感。例如:
(20)只怕大虫不死,向身上又打了十数下,那大虫气都没了。(金瓶梅·第一回)
(21)我倒也连这伙人都怕来不成,若说骑马,只怕连你们都还骑不过哩!(醒世姻缘·第一回)
“全”用作程度副词和语气副词,中古汉语已经出现,普遍应用则在近代。在肯定句中强调程度的百分之百;在否定句中用于“全+不+VP”和“全+无+NP(VP)”格式,加强对否定的强调。“全”的这种用法基本上同“都”,此不赘述。例如:
(22)扶到床上,昏沉了半晌,肚胀也全消了。(醒世姻缘·第十八回)
(23)一味瞒天大谎,全无半点儿真实。(金瓶梅·第七回)
(24)谁知晁大舍道这班人肩膀不齐了,虽然也还勉强接待,相见时大模大样,冷冷落落,全不是向日接洽的模样。(醒世姻缘·第一回)
“并”的语气副词用法与“都”“全”不同,它只用于否定句中加强否定语气,且语气较“都”“全”稍弱。另外,“并”又发展出了“否定预设”的功能。“否定预设”即“强调事实或看法不是所认为的或可能会推想的那样”[14],一般认为这是现代汉语中“并”的用法,其实近代汉语后期已有用例。例如:
(25)妇人又道:“莫不别处有婶婶,可请来厮会也。”武松道:“武二并不曾婚娶”。(金瓶梅·第二回)
(26)张生并不曾人家做女婿,都是郑恒谎,等他两个对证。(西厢记·第五本·第四折)
(27)火烧到别家,随又折回,并不曾延烧别处。(醒世姻缘·第四回)
(28)老夫人治家严肃,内外并无一个男子出入。(西厢记·第一本·第二折)
例(25)对句话中“妇人”的预设是“武松已婚娶”,武松指出实情并非如此,用“并”强调。例(26)红娘对“张生做人家女婿”的看法做出否定,用“并”强调。这两例均强调事实或看法不是所认为的那样。
而后两例的“并”强调事实或看法不是对方所推想的那样,即说话者本人主观意念上认为对方可能有某种推测或设想,并对这种推想予以否定。例(27)中说话人认为对方可能会有这样的推想:“火会烧到别家”,例(28)中说话人认为听话者会有这样的推想:“老夫人家是大户人家,家里肯定会有男子出入”,说话人直接对这种可能的推想予以否定,“并”的这种独特用法和其本义有根本性的关联。“并”的核心义素为[+相同、同时],强调两个事物的相关性,总是寻求二元关系,而“任何一个否定句都预先假设了一个相应的肯定句,即其先设”①这里的“先设”包含于“预设”。胡勇《语气词“并”的语法化》对“先设”“预设”做了区分,认为“肯定句和否定句都有预设,但只有否定句先设相应的肯定命题,肯定句则不先设相应的否定命题”。见吴福祥、崔希亮主编《语法化与语法研究(四)》,商务印书馆,2009年第96-115页)。,这样“并”便同时关联了否定句本身及其“先设”(相应的肯定句),既表对否定的强调又表对“先设”的否定。随着意义扩散和功能转移,否定先设的功能便得到凸显,发展成了“并”的特殊用法。
“都”“全”可以用在肯定句中,表示程度的百分之百,加强肯定语气,而“并”无此用法,这也与它们的核心义素有密切关联。“都”的范围是“可计量的全体”,“全”突出事物的完整性,它们本身就有程度高的蕴含,如“全强”各方面都强,“全盛”各方面都繁盛,自然就引申出“极其”等程度副词用法,而“并”重在两个事物的相关性,不易表示数量大、程度高,故未能衍生此用法。
“都、并、全”均可用在否定句中加强否定语气,这一功能是从总括副词用法演变而来的。当总括副词出现在否定句中,总括对象省略或蕴含时,便失去了其发挥作用的典型环境,只能进一步虚化转指语气;从语言主观化的角度看,否定句更易表现人的主观情感;对全部的否定,则情感更强,尤其省略总括对象时,总括副词便转化为语气副词了。
四、小 结
通过以上对“都”“并”“全”在平行历史时段各自的语法功能、语义演进及相互补充制约关系的考察,我们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语法系统具有自我调节机制,不断通过系统内各成员语法功能的分配调整来寻求新的平衡,反映到各成员就表现为服务语言发展需要而做出的让步和功能选择。“都、并、全”三者在各平行历史时段的发展演进能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总括副词用法方面,中古汉语时期三者并用,随着“都”总括用法的发展及对新的语言现象的适应而取得主导地位,“并”总括副词用法骤减并很快消失,而“全”具有“都”不可替代的用法故得以保全与“都”并行发展。作为加强否定的语气副词,中古汉语时期“都”占绝对主导地位,近代汉语时期其地位被“全”“并”取代,而二者又各有侧重,“全”只表纯粹否定,“并”却衍生出“否定预设”功能;“都”又另辟蹊径,在“连+NP+都+VP”中强调其前的“极端事物或现象”,用以加强主观性语气或情感。可见,一个词的语法化过程不仅仅和自身的句法位置、语义基础、使用频率等因素有关,还和相关词语的语法功能及使用频率密切相关,这应该是语法化研究不容忽视的问题。
第二,一个词的语义演进和语法化路径,总是与其本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如“都”在整个中古时期只能总括多数,“并”只能用于否定句,也只有“并”衍生出“否定预设”的功能等等都与其本义有密切关联。如正如杨荣祥先生所言“一个由实词虚化来的副词,无论其词汇意义多么‘虚’,总能找到它与其所来自的实词在意义上的联系”[2]192。
总之,既要坚持语法化的单向性规律,又要注意相关词语功能和使用频次的影响,一个词的历史演进过程会影响到相关词语的演进轨迹和速度。语法化不只是单个词的单向性发展,而是相关系统的平衡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