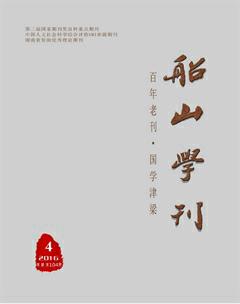道德哲学:《中庸》思想的核心维度
任仕阳+杨明
摘 要:
道德哲学是《中庸》思想的核心维度。我们认为,《中庸》的道德哲学大体可归为三个部分:道德本体论、道德修养论、道德境界论。道德本体论阐释了形上依据与本体源泉,道德修养论讲明了主体功夫与道德锤炼,道德境界论诠解了价值追寻与理想目标,三论虽各有偏重,但密切联系,浑然一体。在其道德哲学建构过程中,承继性、人文性、超越性、系统性等四大理论特质也凸显与明晰起来。
关键词:《中庸》;道德本体论;道德修养论;道德境界论
与《论语》主要强调人伦日用和《大学》特别注重为学次第等不同,《中庸》将儒家基本思想高度思辨化、抽象化、哲学化,建构了一套完整的道德哲学体系。正如钱穆先生所言,《中庸》“陈义甚远,天人性命之渊微,非初学所能骤解也”①。总体看来,《中庸》通过道德本体论、道德修养论与道德境界论的阐发与诠解,具有承继性、人文性、超越性、系统性的道德哲学体系得以建构起来。这一道德哲学的建构奠定了后世儒家道德哲学体系的基本规模、核心范畴与主要理念,在儒家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其体系完备,且影响深远。
一、 道德本体论
在中国哲学语境下探讨本体论问题,在某些人看来似乎有“以西释中”或“以中附西”之嫌,但是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本体论非西方哲学之孤家发明与学术专利,中国哲学有一套不同于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具有中华文化特色的本体论思想。在西方哲学中,其本体论基于主客二分之思维模式试图寻找现象世界背后的终极实体,力求探寻某一具有超越性与不变性的实在。与此不同,中国哲学所言之本体是一道德本体,这一本体具有全整性、真实性、动态性、生生性,其呈现与确证有赖于主体的生命体验与内在体悟,相较西方哲学之本体可谓大异其趣、殊途殊归。考之中国儒学史,这一道德本体实则为“仁”,可名之为“仁体”。我们认为,此一“仁体”在《中庸》中的显现是以“一分为三”的形式来展开的,即“人伦本体”“价值本体”与“超越本体”,“分而为三”又“合而为一”,统摄于“仁体”,构成《中庸》道德哲学架构的本体论基础。
其一,从现实路径来说,表现为人伦本体。所谓“人伦本体”是指道德本体落实于现实生活,不离日常生活,强调人伦日用,突出生活性、实践性,主要从现实路径角度言说。《中庸》作为儒家道德哲学建构的理论范型,毫无疑问是充分体现形上致思的,但《中庸》注重本体与生活、实践、人伦的统一性亦显而易见。“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道不可须臾相离,是说主体对道体的把握,不可与道相离却,因为道本来就是关于日用事物的当然之理,在一定程度上表达了道寓于生活之中的理念。“子曰:‘道不远人,人之为道而远人,不可以为道。”这里,《中庸》引孔子之言明确表明了道之人文性与在世性,道如果远离于人,则不成其为“道”;人若修道,却好高骛远、远离于人,则无法把握“道”。《中庸》强调生活性、实践性,突出体现为“造端乎夫妇”的人伦性。“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现代新儒家方东美先生曾就中国哲学建构的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作过阐述,方氏认为:“在中国,要成立任何哲学思想体系,总要把形而上、形而下贯穿起来,衔接起来,将超越形上学再点化为内在形上学。儒家中人不管道德成就多高,还必须‘践形,把价值理想在现实世界、现实人生中完全实现。”②我们认为这一论述是符合中国哲学思维方式与理论特征的,在中国哲学中,尤其是就儒学而言,形上性与形下性始终相互贯通,而不是与此相反。“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易传·系辞》),“道器统一”是中国哲学的重要特质。当然,这里提“人伦本体”不是要将道德本体完全下落至世俗生活而罔顾终极关怀,此处仅就某一向度而言,这是要特别说明的。
其二,从终极价值来说,表现为价值本体。所谓“价值本体”是指道德本体作为价值源泉,强调价值本源,突出生生性、创造性,主要从终极价值角度言说。《中庸》开篇即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里的“之谓”为“就是”之意,与“谓之”为“叫作”之意不同,戴震认为“古之言辞,‘之谓‘谓之有异”,“之谓”是“以上所称解下”,而“谓之”是“以下所称之名辨上之实”。(《孟子字义疏证》)天、命、性、道、教之顺承,体现了天道、性道与人道的有机统一,体现了本体论、人性论与社会论的有机统一,此处之本体论实则为一种价值本体论。人之性来自于天,此天不是自然之天、物质之天,而是价值之天,是人性善的价值源泉。从《中庸》的文本结构来看,全书存在着明显的断层,第一章(按朱熹所作分章)、第二十章后半部分至第三十三章可归为一部分,第二章至第二十章前部分可归为另一部分,从“哀公问政”章后半部至第三十三章与前一部分突出“中庸”有所不同,“诚”在后一部分成为核心范畴,而“诚”从本体论角度来说,就是一种价值本体,可名之曰“诚体”。“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诚”关乎物之终与始,若“不诚”则无物。显然,这里并不是讲“诚”为物质世界创生之本原,而是突出“诚”作为一种目的性原则的生生创化之源,“至诚”便能成己成物,便能参赞化育。因此,《中庸》说:“唯天下至诚,为能经纶天下之大经,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只有达至“至诚”才能经纶天下、挺立大本、参赞化育。“天地之道,可一言而尽也。其为物不二,则其生物不测。”此处所谓“一言”即是“诚”,“诚”能生生,则生物不测。诚如牟宗三先生所言,儒学“直接由我们的道德意识呈露那内在的道德实体。这是四无依傍而直接觌体挺立的,不是来回旋转,驰骋妙谈,以求解脱或灭度的。在这样面对所呈露的实体而挺立自己中,这所呈露的实体直接是道德的,同时亦即是形上学的。因此,此实体所贯彻的万事万物(行为物与存在物)都直接能保住其道德价值的意义。”③endprint
其三,从形上意蕴来说,表现为超越本体。所谓“超越本体”是指道德本体的形上意义,强调内在超越,突出无限性、内在性,主要从形上意蕴角度言说。道德本体的无限性与超越性在常人看来似乎是一种隔膜性,难以把握、无法体悟,《中庸》引孔子之言曰:“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孔子认为,中庸之道为极致之德,百姓少有能体验、运用者,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孔子并非想要表达中庸之道至高玄远、无法企及,这里更多地是想要从侧面突出中庸之道的无限性与超越性。“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祸福将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诚如神。”如果认为《中庸》此处具有渲染某种神秘主义的倾向,实际上是对其超越性之误解。“现实地说,人是有限的;理想地说,人可是无限的。其现实地为有限者,是因为他有感性;其理想地可谓无限者,是因为他能超越乎其感性而不为其感性所囿。他超越乎其感性而不为其感性所囿,他即呈现一无限心。因此,他即以此无限心为体。他之可为无限,是因为他以无限心为体。他若能充分朗现此无限心,他即是一无限的存在。他之为无限是即于有限而为无限的,即是说,他不必毁弃感性而始可为无限。”④通过对超越性的道德本体的把握和体验,呈现道德本心,人可以实现有限性与无限性之统一。与西方哲学追求外在超越不同,中国哲学强调即内在即超越,内在而超越,超越而内在。儒家道德哲学提倡在个体道德生活中追寻终极实在,内在无限心之呈现也即道德本体之把握,每一个体均有此内在潜力,在天人合一思维方式观照下,即内在即超越体现了儒家传统的独特的道德哲学理念。
二、 道德修养论
“即本体即功夫”是中国哲学独特的致思模式。“功夫不离本体,本体原无内外。只为后来做功夫的分了内外,失其本体了。如今正要讲明功夫不要有内外,乃是本体功夫。”(《传习录》)在王阳明看来,本体与功夫是“不一不异”的关系,功夫离本体则无以立,本体离功夫则无法显。尽管宋明儒将其发展至理论最高峰,但这并不是宋明儒(尤其是明儒)的独创。我们认为,《中庸》文本中已内蕴这一致思模式,本体的确证有待功夫的锤炼,功夫的极致赖于本体的呈现,因此在揭示《中庸》的道德本体论思想后,我们将对其道德修养论(功夫论)作一诠释。总体而言,《中庸》阐发了“戒慎恐惧,自反慎独”、“随时执中,和而不流”与“诚明相通,性修不二”的道德修养论思想。
第一,戒慎恐惧,慎独自反。在儒家看来,道德修养的提升要通过向内探求或向内翻转的途径来实现。《中庸》在儒家经典中较早地提出了“慎独”概念,曰:“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惧乎其所不闻。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慎,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心部》云:“慎,谨也。”即为谨慎之意。《礼记·礼器》亦云:“德产之致也精微,观天下之物无可以称其德者,如此则得不以少为贵乎?是故君子慎其独也。”慎,亦有内心珍重之意。《庄子·在宥》:“慎女内,闭女外,多知为败。”此“慎”字在廖名春先生看来应训“珍重”,“慎女内”即“珍重你的内在精神”⑤。独,《广雅·释诂》:“特,独也。”即以特为独。《易·大过》:“君子独立不惧。”《吕氏春秋·制乐》:“圣人所独见,众人焉知其极。”独即道德主体内心之独一且诚。在郭店楚墓竹简《五行》篇中,其对“慎独之功”甚为强调,于第16简、第17—18 简中两次提及,并引《诗经·曹风·鸤鸠》《诗经·邶风·燕燕》加以阐述,可参释。回到《中庸》文本,我们可以看到《中庸》极为强调主体在“隐”“微”处的“视听言动”,因为在此种独处境地下最能透见个人的内在修为,能否在“未动之时”“将萌之时”保持与养护“天命之性”都取决于此。职是之故,“戒慎恐惧”成为“慎独”的内在之意。此外,与“慎独”相联系,《中庸》提出了“自反”的修养方法。《中庸》引孔子之言曰:“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皓,反求诸其身。”在孔子看来,射箭与君子有一定相似性,如果射箭未能射中靶心,那么我们要返回自身寻找原因而不是怨天尤人。这就是后来孟子所说的“反求诸己”,《孟子·公孙丑上》曰:“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者。反求诸己而已矣。”《中庸》提出“戒慎恐惧,慎独自反”,最能考究儒者内在的功夫修为,即要求在独处时仍能做到切己省察、遵道而行、抱礼循义,体现了其具有儒家特色的修养方法,对后世亦影响深远,兹不赘述。
第二,随时执中,和而不流。“中和”之“中”不仅具有静态的、名词性的意义,也具有动态的、动词性的内涵,我们可以从道德本体论角度来理解,亦可从功夫论、方法论角度来理解。⑥《中庸》云:“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中庸》在提出“君子小人之辨”的同时,也倡导了“时中”原则,即“随时执中”之意。所谓时中就是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根据不同条件、时间、地点做出与之相适的调整和应对,而非固执其一、死守原则。“时中”注重“中”这一大本大源,同时亦强调“时”这一灵活原则。在中国哲学史的发展演变历程中,“经”与“权”的讨论从未间断,即所谓“经权之辨”,其中“经”和“权”的统一与“时中”的内涵具有一定程度之相似性、关联性。“执一无权”既不符合“时中”原则,也不合于儒家之基本精神。例如,关于嫂溺水是否应该伸之以援手的问题,在儒家看来就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问题,儒家注重生命的养护与安顿,强调生生之德,在“生生”这一根本原则下,“男女授受不亲”此一下位原则应当让位,施以援手乃“时中”之体现。值得注意的是,“时中”并非毫无原则地简单折中,亦非和稀泥式的“乡愿”作派。职是之故,《中庸》又提出了“和而不流”的主张,“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儒家历来反对“和而流”的“乡愿”之徒,孔子说:“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朱熹《论语集注》注为:“盖其同流合污以媚于世,故在乡人之中,独以愿称。夫子以其似德非德,而反乱乎德,故以为德之贼而深恶之。”儒家式的道德修养并不是“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孟子·尽心下》),而是要真正做到“随时执中,和而不流”。endprint
第三,诚明相通,性修不二。“自诚明”与“自明诚”是两种不同的道德修养路径,前者为“性”,后者为“教”,但此两者并非孤立隔膜,而是彼此相通,我们称之为“诚明相通,性修不二”。《中庸》云:“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诚则明矣,明则诚矣。”所谓“自诚明”指的是圣人之功夫,即“生而知之”之类,儒家视域中的圣人无需刻意的、特别的功夫便能达至“至诚”,这就叫做真真实实、自自然然,自然而中道,“诚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从容中道圣人也。”所谓“自明诚”指的是普通人之修养功夫,即“学而知之”“困而知之”之类,必须通过自身的不断努力和内在修养,择善固执,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不过这要付出更多的汗水和精力,“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如此也能实现“至诚”,“果能此道矣,虽愚必明,虽柔必强”。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自诚明”与“自明诚”实际上体现了“天—人”和“人—天”两种传统和谱系,所以《中庸》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孟子·离娄上》也讲:“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前已论及,在《中庸》中,“自诚明”与“自明诚”之分即为“性”与“教”之分,正如《中庸》开篇所云:“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圣人能保持与养护天命之性而不失,事事循理而行,处处皆合于义,因此可率性而为。与圣人不同,普通人无法做到如圣人般“从容中道”,后天受到染污,天命之性有所毁伤,此种情形下之率性而为是不可取的,这就需要不断地“修道”,教化之功日益凸显而本心愈加澄明,复见天命之性,也就“自明诚”而“至诚”。此外,我们应该重视《中庸》所主张的“致曲之功”,即“其次致曲,曲则能诚”,此为相对于圣人尽全体之性而言的另外一种功夫,属于自明而诚。朱熹《中庸章句》认为“其次则必有其善端发见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极。”所谓“曲”就是“善端之偏”,“致曲”是要将“善端之偏”推至极致,这种端绪由此便可扩充,所以“致曲”功夫亦可视为“积善”,“积善”而“至诚”。
三、 道德境界论
如上所述,《中庸》的道德修养论讲究“戒慎恐惧,自反慎独”“随时执中,和而不流”与“诚明相通,性修不二”,那么这样的功夫论究竟欲达至何种道德境界?综观《中庸》文本,我们认为可从三个方面来理解。其一,追求“中和”,即“大中至正,圆融和合”;其二,落实“生生”,即“成己成物,参赞化育”;其三,成就“人格”,即“砥砺君子,成贤作圣”。兹将分而述之。
其一,大中至正,圆融和合。“中庸”具有本体论、方法论意义,同时亦是儒家所追寻的道德境界,集中体现为“致中和”理想。《中庸》云:“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在宋儒看来,所谓“中”就是无过无不及、不偏不倚,寂然不动,为天下之大本;所谓“和”就是感而遂通,为天下之达道。朱熹将“中”“和”与“性”“情”相联系、对举,作出了其基于理学家立场的阐释,主张“心统性情”,他认为“情之未发者性也,是乃所谓中;性之已发者情也,其皆中节则所谓和也,天下之达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朱子全书·道统一》)张载首提“大中至正”,云:“大中至正之极,文必能致其用,约必能感而通。”(《张子正蒙·卷四·中正篇》)王阳明的入室弟子徐爱在描述其师的“圣人气象”时说:“不知先生居夷三载,处困养静,精一之功,固已超入圣域,粹然大中至正之归矣。”(《传习录》)崇尚“中正”是中华文化之一大特色,也深刻沁入中国人之民族气质。我们也可以从《易经》卦象爻位来理解“大中至正”。在六十四卦中,每一卦的第二爻与第五爻是内外卦的中位,初、二、三爻分别对应四、五、上爻,如果相对的两爻为一阴一阳,则为“正应”,若均为阳或均为阴,则是“敌应”。如果占蓍所得之爻既“中”且“正”,则多吉,例如:比卦第二爻为阴爻、第五爻为阳爻,处中位且正应,同时阳处阳位、阴处阴位,六二的爻辞是“比之自内,贞吉”,九五的爻辞是“显比;王用三驱,失前禽。邑人不诫,吉。”故而占得六二爻与九五爻的结果都为吉。“圆融和合”体现的是《中庸》对“和”的境界追求,包括人己和、人人和、天地和、天地合等,兹不展开。历代儒家圣贤著书立说、入仕为官,无非想要实现由“内圣”而“外王”的终极理想,在我们看来,此终极理想在一定程度上可用“致中和”来概括,“人类与天地万物皆能各得其所而互相协调和谐、相济相成而生生无已,这乃是儒家的‘致中和所宜达成的最高境界,也是人类大同社会的最高理想境界。”⑦
其二,成己成物,参赞化育。我们认为,儒学从其价值理念与内在诉求来说,可以称之为“生生之学”,强调合内外之道而生生不已。《易传·系辞》云:“生生之谓易。”“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所秉持之至上德性就是生养万物,男女、夫妇、父子、君臣等皆由天地生养、护育。与西方哲学之自然主义纯粹强调自然属性不同,中国哲学视域下之自然具有价值意义与道德内涵,正如唐君毅先生所言:“西方以往自然主义之短正在于其自然, 可不言其价值与德行。故表现西方文化之向上精神之哲学思想,必反对自然主义。中国人之以自然有德性、有价值,其根据则在中国人之道德精神之不私其仁与其德,故能客观化其仁德于宇宙间。”⑧就《中庸》来看,其具有极强的生生哲学内涵,与《易传》生生主张相呼应,《中庸》之生生哲学可以概括为“成己成物,参赞化育”,这也是其追求的道德境界之一。“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达至“至诚”则能透见天命之性,又“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若能透见自身禀赋之天命之性则能透见他人之性,进而可尽物性,便可辅助天地之养护、培育。如此,则能与天地并列为三,这便是“参赞化育”之生生境界。此外,《中庸》还提出了“成己成物”主张。“诚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故时措之宜也。”儒学也是“为己之学”,强调“尽己”,《中庸》称之为“成己”。但同时儒家讲究内外相合,己立立人、己达达人,当然也包括万物在内,《中庸》称之为“成物”。既仁且智、推己度物,即是“成己成物”。endprint
其三,砥砺君子,成贤作圣。任何一种类型的文化都有对理想人格之追寻,中华文化亦是如此。在多元融合的中华文化中,佛教的理想人格是“佛陀”,道家的理想人格是“真人”,儒家的理想人格则为“圣人”。儒家之“圣人”向来是儒者孜孜不倦所追求的完善人格,是儒家理想人格的最高层次。不过,理想人格在儒家思想中有层次之差别,《论语·述而》云:“圣人,吾不得而见之矣;得见君子,斯可矣。”相较于“圣人”的尽善尽美,“君子”则显得切实可达。就《中庸》而言,其主张君子要“素位安命”“自迩自卑”“知人知天”。“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素富贵行乎富贵,素贫贱行乎贫贱,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难行乎患难。君子无入而不自得焉。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于人则无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侥幸。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诸正皓,反求诸身。”君子要素位而行,各安其命,正己修身,贵在自得,与小人之行险侥幸不同,真正的君子是居易俟命。“君子之道,譬如行远,必自迩;譬如登高,必自卑。《诗》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乐且耽。宜尔室家,宜尔妻孥。”君子之道,如同远行,定从近处出发;就像攀登高山,定从低处开始。这启示我们,欲成君子,自家庭始,自小事始,自细节始,不可好高骛远。“质诸鬼神而无疑,知天也;百世以俟圣人而不惑,知人也。”这是说君子要“知人知天”,所谓“知人”就是要明了“人道”,所谓“知天”就是要通达“天道”,因此君子也是贯通天人的。君子作为切实可达的理想人格范型,将其推至极致,就是儒家追求的最高人格境界——圣人。《中庸》在其后半部分,着重描述了“圣人气象”。在《中庸》看来,圣人具有如下五种品质:聪明睿知,宽裕温柔,发强刚毅,齐庄中正,文理密察。实际上这五种品质就是圣、仁、义、礼、智五种德性,也即是荀子批评思孟学派“僻违而无类,幽隐而无说,闭约而无解”之“五行”学说(《荀子·非十二子》),可考之于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本《五行》与荆门郭店楚墓简本《五行》。此外,《中庸》还以孔子为例,阐述了圣人之气象,“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辟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为大也。”孔子通达上下(天人),如同天地般持载覆帱,有如四季之运行、日月之光辉,能够参赞化育、生生不已,至达圆融和合。总而言之,《中庸》在塑造理想人格方面提出了两大类型,可概括为“砥砺君子,成贤作圣。”
四、 《中庸》道德哲学建构的四大理论特质
以上我们对《中庸》道德哲学建构的三大有机组成部分进行了梳理与分析,道德本体论阐释了形上依据与本体源泉,道德修养论讲明了主体功夫与道德锤炼,道德境界论诠解了价值追寻与理想目标,三论虽各有偏重,但密切联系,成浑然一体。可见,道德哲学是《中庸》思想之核心维度。此外,任何一种哲学思想的生发或理论体系的建构必是各种理论与现实因素交融和合的产物,从中亦可窥见其理论特质,《中庸》道德哲学的建构亦不例外。在对《中庸》道德哲学建构的认识、理解和评价过程中,我们发现其至少具有以下四大理论特质,即承继性、人文性、超越性、系统性。
首先,承继性:道德哲学建构的历史相续。所谓“承继性”指的是《中庸》道德哲学建构有其清晰的思想源流与坚实的理论基础,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亦非肆意妄想、凭空创造,是在有所承继后的发展与创新,充分体现了其道德哲学建构的历史相续。一般认为,《中庸》的核心概念是“中庸”和“诚”,并非直接将“仁”视作核心范畴,但不论是“中庸”还是“诚”皆指向“仁”,实则是“仁”的展开与分疏。因此,在我们看来,《中庸》最主要的理念是“仁”的思想,坚持了儒家的基本立场。《国语·周语下》云:“仁,文之爱也”“爱人能仁”。《左传·成公九年》云:“不背本,仁也”,《左传·哀公七年》云:“子服景伯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大所以保小,仁也。”这些都是《中庸》道德哲学建构的有益滋养。众所周知,孔子儒学之核心范畴是“仁”,我们认为此“仁”兼具本体论、修养论与境界论意涵。孔子儒学为儒学初创期之理论,尚未有意识地建构道德本体论,但是已有“仁本体”之发显,《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显然,孔子在这里指点了本体之仁,不过并未深入而已。考之《论语》,其探讨“仁”主要是从修养论与境界论来言说的。“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论语·学而》)“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仁在其中矣。”(《论语·子张》)等等,这些对于《中庸》道德修养论与道德境界论的构建产生了巨大影响,兹不赘述。任何一种哲学思想的提出或理论体系的建构都其来有自,有其理论源流,《中庸》道德哲学建构是历史相续的,具有明显的承继性。
其次,人文性:道德哲学建构的现实关怀。所谓“人文性”指的是《中庸》道德哲学建构具有强烈的人文取向与深沉的本真情怀,并非空中楼阁、高悬庙堂,亦非纯粹思辨、远离生活,是将人的因素置于诸方面的融摄与调和,充分体现了其道德哲学建构的现实关怀。儒家向来注重人文关怀,徐复观先生说:“此种人文主义(儒家人文主义),外可以突破社会阶级的限制,内可以突破个人生理的制约,为人类自己开辟出无限的生机、无限的境界,这是孔子在文化上继承周公之后而超过周公制礼作乐的最伟大勋业。”⑨我们认为,儒学的基本属性就是人文性。从儒学诞生时起,人始终是其关注之核心。无论是“天人统”还是“人天统”,从未离却人这一道德主体,天、命、性、道、教皆依人而言说。《中庸》承继孔子儒学之人文精神,并将这种人文情怀落实为现实的政治关怀,提出“三达德”“五达道”与“治国九经”。所谓“三达德”即智、仁、勇三种德性,所谓“五达道”即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五种人伦关系,此“三达德”与“五达道”是相互贯通的,《中庸》云:“天下之达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想要实现“五达道”,处理好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间的关系,达到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夫妇和睦、兄友弟恭、朋友有信,必须具有智、仁、勇“三达德”。此外,为了实现政治清明、社会安定、百姓乐业,《中庸》提出了九条具体的治国方略,即“治国九经”:修身、尊贤、亲亲、敬大臣、体群臣、子庶民、来百工、柔远人、怀诸侯。实际上,这是孔子“为政以德”治国思想的承继与展开,也与《大学》修齐治平的推演路径相契合。可见,《中庸》道德哲学建构的重要理论特质之一就是人文性,强调生生,重视生活,具有强烈的人文取向与现实关怀。endprint
复次,超越性:道德哲学建构的形上追寻。所谓“超越性”指的是《中庸》道德哲学建构具有内在的超越属性,在现实观照的基础上注重对意义世界与可能世界的探求,充分体现了其道德哲学建构的形上追寻。这一理论特征在我们看来是不言自明的,《中庸》作为儒家道德哲学建构的理论范型,将儒家基本思想高度抽象化、思辨化、哲学化,形成道德本体论、道德修养论、道德境界论三大理论构架,毫无疑问是极具超越性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一论断不仅是《中庸》的思想主旨,亦可视为儒学的理论纲维。儒家的基本价值诉求与核心理念,皆可以从此三句中透见明了。天人一体,天人不二,是《中庸》一切主张的预设前提,在此思维模式下,天、命、性、道、教是顺承而贯通的,天道、性道与人道贯通而无隔膜。这种超越性不同于西方哲学之外在超越,而是即内在即超越,内在而超越,超越而内在。这种超越性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宗教性,杜维明先生认为:“儒家思想作为哲学人类学的一种形式,充满了深刻的伦理宗教的意蕴。它对人的宗教性的唤起和它对人的理性的表达一样充分。”⑩在他看来,这种宗教性的“终极关怀”体现在《中庸》所强调的“自我转换”理念中。确实如此,《中庸》承继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倡导道德主体的功夫修养与境界提升,实现理想人格的全面塑造。《中庸》云:“诚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诚者物之终始,不诚无物。是故君子诚之为贵。诚者非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内外之道也。”注重主体的内在修为与德性内充,这种“自我转换”既要实现“成己”,也要实现“成人”、“成物”,这样才能复归天命之性,彰显性之大德。“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诚者”即“自诚明”,“诚之者”即“自明诚”,此两种不同的道德修养路径,最终都指向“自我转换”。职是之故,我们认为《中庸》的道德哲学建构具有超越性。
最后,系统性:道德哲学建构的整体塑造。所谓“系统性”指的是《中庸》道德哲学建构具有全面的理论关涉,一方面融道德本体论、道德修养论与道德境界论为一炉,另一方面系统协调天、地、人三大领域,充分体现了其道德哲学建构的整体塑造。道德本体论阐释了形上依据与本体源泉,道德修养论讲明了主体功夫与道德锤炼,道德境界论诠解了价值追寻与理想目标,三论虽各有偏重,但密切联系,成浑然一体。系统性又突出体现为影响性,这一道德哲学的建构奠定了后世儒家道德哲学体系的基本规模、核心范畴与主要理念,在儒家伦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体系完备,影响深远。例如:宋明儒建立的理本体、心本体等本体论理论形态均受《中庸》的深刻影响;有明一代,刘宗周提出了通过“慎独”来“格君心之非”,他说:“此慎独之说,而陛下已一日而尧舜矣……故曰慎独可以行王道,愿陛下深信于斯而笃行之。”(《刘子全书》)刘氏笃信“慎独”之说,希冀通过此一途径“格君心之非”,从而使得君主成为尧舜式的圣王,“慎独”之修养功夫在蕺山一系得到扩充与发展。“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唯天下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系统协调天、地、人三大领域,天、命、性、道、教相顺承而贯通,个体通过尽性自修而参赞化育,乃可与天地并列为三。质言之,系统性是《中庸》道德哲学建构的重要理论特质之一。
【 注 释 】
①钱穆:《四书释义》,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第241页。
②方东美:《原始儒家道家哲学》,黎民文化事业公司1987年版,第16页。
③④牟宗三:《现象与物自身》,学生书局1990年版,第435—436、450—451页。
⑤廖名春:《“慎”字本义及其文献释读》,《出土文献与君子慎独—慎独问题讨论集》,漓江出版社2012年版,第79页。
⑥杨明:《儒家“中和”理念及其现代价值》,《道德与文明》2010年第2期。
⑦徐儒宗:《儒家中和思想的现实意义》,《儒学的当代使命——纪念孔子诞辰256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第三册),九州出版社2010年版,第411页。
⑧唐君毅:《中国文化之精神价值》,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79页。
⑨徐复观:《学术与政治之间》,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35页。
⑩杜维明:《论儒学的宗教性——对〈中庸〉的现代诠释》(英文版第二版前言),段德智译,林同奇校,武汉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页。endprin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