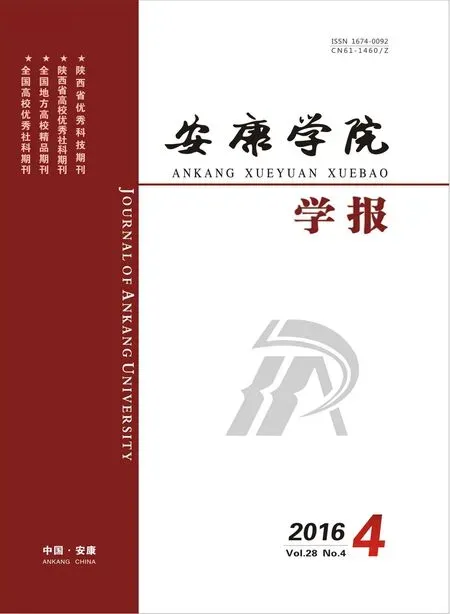电影《郎在对门唱山歌》
———基于社会权力话语秩序下的悲情故事
李小雨
(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 临汾 041000)
电影《郎在对门唱山歌》
———基于社会权力话语秩序下的悲情故事
李小雨
(山西师范大学 戏剧与影视学院,山西临汾 041000)
章明导演的电影《郎在对门唱山歌》是根据陕西籍作家李春平的同名中篇小说改编的,借助于紫阳县当地富有质感的空间背景和独有魅力的紫阳民歌,电影呈现了一个浪漫与残酷并存的爱情故事。然而在显性的故事文本下,却隐藏着导演对于基层权力秩序的描写。正是在隐性权力的干预下,无望的县城青年们走向了压抑和失语的结局。
《郎在对门唱山歌》;基层社会;权力;章明;李春平
郎在对门唱山歌,
姐在房中织绫罗。
那个短命死的、挨刀死的、发瘟死的,
唱的那个歌来哎,好哇!
唱的奴家,脚耙手软,手软脚耙,丢不得云板,丢不得梭耶,绫罗不织听山歌。
本文开头这首山歌是流传在陕西紫阳县一首传统民歌,被陕西籍作家李春平用在描写家乡紫阳的一部同名中篇小说《郎在对门唱山歌》[1]31中,而章明导演的命题电影《郎在对门唱山歌》更是对于同名民歌和同名小说的完美结合。山歌中“那个短命死的、挨刀死的、发瘟死的”三句歌词“看似恶毒,实则是男女青年打情骂俏之语,是爱,又是假意的恨。”更是电影中主人公刘小漾和冯冈爱情的催化剂,刘小漾第一次遇见冯冈,再到两个人的恋情升温以及最后的点题呼应,它都在恰当时刻出现。两个青年因为山歌而结缘,从而展开了一段艰难的爱情历险。具有反讽意味的是,在遭到冯冈爱情背叛之后,这三句歌词作为对冯冈的“怨恨”也一点不为过,同样的歌词在爱情甜蜜和失望两种情况下却解读出两种截然相反的意味。主人公刘小漾遭遇了两个男人,不管她爱与不爱,她的生命都留下了刻骨铭心的记忆和伤害。
电影于2011年公映,却讲述到了2014年的故事,用导演章明的话来说“是他对未来的想象”。原著小说是李春平为家乡紫阳县量身打造的一部小说,紫阳元素无处不在,“它写了我的故乡紫阳,我的精神母体。这些小说使故乡的影像在文本中得以确立,文本与现实故乡之间形成了一种超越时空的对话关系。”[2]当笔者重新回顾李春平在2015年出版的小说集《郎在对门唱山歌》,顿时觉得此时再来回顾电影是一个最好时机。此时我们不必像导演章明那样用一个虚焦的镜头来展现对未来时空的想象,恰恰相反,我们需要的是回顾,以此来验证章明在2011年时对未来的预测是否正确。
一、电影表现与小说的异同
电影开头有一段字幕“根据李春平同名短篇小说改编”,小说自然便作为解读电影的一个重要文本。笔者比较了发表在《小说月报》(中篇小说)上和2015年出版的同名小说集两个文本,故事线索和人物基本上没有大的变动。后出版的小说集更像是吸收了电影剧本上的一些台词并且增添了细节上的描写,是基于电影基础之上的一个修订版本,因此笔者依照发表在2007年第一期的《小说月报》(中篇小说)上的同名小说《郎在对门唱山歌》作为参考文本来分析。由于电影和小说两种艺术载体的不同,很显然电影在人物身份设定、人物性格和情节故事上对原著进行了修改。小说中男女主人公分别叫做冯刚和小样,电影中则叫做冯冈和小漾,这点改动对故事没有太大的影响。
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对于小漾父亲刘在水的身份设定做了巨大的修改。小说中刘在水仅仅是一个县工商局管市场的小股长,直到影片最后才升为工商局副局长,而电影中一出场则是公安局的副局长。电影删除了男二号张学锋妈妈作为小漾钢琴教师的角色,并且将其在市里当秘书的爸爸直接改为县长,随后更是升任为书记。两个家长一出场便是门当户对的权力地位,用剧中张县长的话来讲:县长学体育的儿子刚好配上局长学艺术的闺女。同时父亲刘在水为了自己的政治前途,在县长的“点拨”下暗示女儿积极和县长儿子张学锋来往。基层官场的权力角逐是影片一个无处不在的影子,刘在水可以违规在江边盖海景房、刘在水能够给女儿安排教书的工作、张学锋更可以给小漾安排坐办公室当公务员,聊聊几笔勾勒出县城真实的生层状态,只不过因为剧中女主小漾的严词拒绝而显得不明显。
剧中厨子李春贵在开头的家宴上有过惊鸿一瞥,随后在张学锋醉倒在街上再次出现,并且对前来寻人的刘在水说了一句“平时难得见你们这些当官的”,看似一句简单的牢骚,实则正是官员和群众疏于联系的真实写照。醉倒在地的张学锋嘟囔了一句醉话“紫阳处处是我家”,令人不免过多解读。身为县长之子的张学锋在剧中是一个不依赖父亲权力而显得正面的上进少年,不能忽视的是他却拥有着普通青年难以匹配的政治资本。这种对于基层社会现实的勾勒,显示出李春平对于生活的细致观察和感悟。“当代作家要有当代意识,你可以从各种不同的文学流派中去吸取营养,但你的目光一定要关注当下生活。如果一个作家面对热火朝天的时代浪潮毫无感觉,他写出的作品可能就是远离大众的,技巧再高也只是形式上的东西。”[3]在这里我不能回避李春平作为一个官场小说作家的角度,作为一个拥有多年基层机关生活经验的作家,李春平对于基层权力的观察和反思也增加了文本的丰富性。导演章明也是追求介入现实的创作,“电影还是要介入社会。要介入这个社会有一些前提,不管是在方式上、内容上、形态上都能够介入这个社会。”[4]287对于社会生态的真实记录和权力的反思这在导演和原作者身上得到了呼应。
不得不说电影在音乐植入方面做得非常成功。电影首先改掉了冯冈北大历史系高材生的身份设定,而作为中国音乐学院高材生的冯冈自然便成为了小漾的家庭音乐教师。把小漾和冯冈在紫阳的教师工作改为在县剧团工作,这样也大大提高了紫阳民歌出现的几率。紫阳民歌《郎在对门唱山歌》在小说中仅仅出现了一次,是在小样十八岁生日那天,冯刚和张学锋一对情敌第一次公开面对时小样所唱。然而在电影中这首山歌却出现四次,贯穿在冯冈和小漾的爱情之路上。第一次是心动,因为见到了“好帅”的冯冈指挥了好听的山歌演出,小漾对这个男人产生了好奇;第二次是定情,冯冈作为家庭教师教授小漾音乐,小漾一边学唱这首山歌,一边用含情脉脉的眼神望着冯冈,此时的小漾已经完全倾心于冯冈;第三次是分歧,二人貌合神离的去乡村采风,一个民间歌手唱了一遍原汁原味的《郎在对门唱山歌》,可是此时的冯冈却在小漾强烈的爱情攻势下有了逃避的姿态;第四次是因为心碎,遭到冯冈爱情的背叛,小漾全身被掏空一般,此时电影开头小漾初见冯冈时的音乐再次响应,呼应开头,却有了不一样的心境。可以说同名歌曲贯穿了男女主人公的爱情之路,在相遇相恋和分歧分别中分别参与了叙事。电影中通过冯冈教授小漾音乐、县剧团排练民歌和乡村采风等多种形式,分别把不同种类的紫阳民歌一一展现,既增添了电影的艺术魅力,又满足了观众对于紫阳民歌的向往和喜爱。在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上本片更是荣获了最佳电影音乐奖,则是对于电影音乐最好的肯定。
电影对于冯冈这个人物做了最大程度的修改,删除了其性格上主动性成分,塑造了一个清高而又沉默寡言的小镇艺术青年形象。在中国传统文学中,此类家贫而又上进的书生最易得到富家小姐的青睐,但也是最容易背叛爱情的陈世美。不同于电影中冯冈只知道被动接受小漾的爱情,在李春平笔下,冯刚面对爱情是主动而又大胆的。冯刚可以蓄意“监视”小样的行踪,以便增加和她相处的机会,更是用“那个可爱的人”来挑逗小样。在小样脚肿后,冯刚借为小样疗伤的机会亲吻了小样的脚,这一极具诱惑性的动作细致的刻画了冯刚在爱情面前的主动攻击性。小样在西安上大学的四年时间,冯刚几乎每周花费四个小时车程来看望她,既使贫穷也要在城郊租一间民房作为二人爱情的暖巢。相反在电影中冯冈完全是作为一个被动的角色来描写的,在这场爱情较量中,小漾是主动出击的一方,作为学生可以买水果和鱼来看望冯冈;毕业后违背了父亲让她做公务员的愿望,一心去县剧团发扬紫阳民歌,更拒绝了高富帅张学锋的苦苦追求,死心塌地的跟随冯冈。剧中小漾有一句台词:“女孩是这样的,如果她愿意,她就能掏心给你。如果她不愿意,她就能掏你的心。”[1]47将一个女孩泼辣、敢作敢为的性格刻画的淋漓尽致。然而因为冯冈的不主动、自卑所带来的逃避行为,当小漾四年大学毕业后舍弃一切跟随他时,他却逃避了爱情。如果说采集民歌是为将来自此走出去做准备,那么接着一场出轨的戏码彻底将二人最后一点联系扯得干干净净。
二、基层形象建构:纯粹爱情之不可能
以往的评论者也都注意到了电影有着泾渭分明的两段故事:以小漾上大学为界,前者是清新甜美的初恋故事,后者则是充满着残酷现实的爱情背叛。在电影开头,电视机里出现了2009年国庆阅兵的画面,小漾大学四年结束应是在2014年,诡谲的地方在于电影上映却是在2011年。出现在剧本中的年份提醒却没有在电影中出现,许多观众甚至忽略了这一隔断性的叙事,四年时间在电影中以一个虚焦的镜头一闪而过。
在电影前半部分,为了女儿能够艺考考上一所好的大学,父亲刘在水为小漾请了家庭音乐教师冯冈。学音乐出身的冯冈自身带着一种艺术的气息,因其家庭原因带有一丝忧郁的神情,而这也恰巧俘虏了青春少女小漾的芳心。以音乐为媒介,自此拉开二人爱情历程。后半部分由于小漾大学毕业返回故乡工作,电影褪去了理想主义的色彩,开始关注现实的生活状态。小漾违反父命,一心追随所爱执意在剧团工作,父亲则对她发出:“真正的人间生活,就是世俗的生活……因为只有世俗的东西,才是真正能够让人成熟的东西。所以,凡是成熟的人都是懂得世俗的人……”[1]44后半部分以张学锋买走了小漾的钢琴开始,张学锋重新走进小漾视野,最终也与小漾发生了一段纠缠不清的悲情故事。电影以音乐为载体,钢琴作为主要的贯穿道具将女儿小漾、父亲刘在水、冯冈和张学锋四个人串联起来。钢琴既是刘小漾和冯冈爱情信物,又象征着一种理想、爱情或者人生。当钢琴被张学锋搬走,那也像是理想的动摇,它发生了位置上的移动,而且是在不知情的状况下。
电影中父亲刘在水是作为权力的象征存在的。小漾和冯冈结缘,是因为父亲为她做主请了家庭教师;小漾和张学锋酒后发生关系,也是因为父亲执意让小漾护送醉酒的张学锋回家才造成的。在小漾爱情开始和破碎无处不在受到父亲的干涉,这种以亲情面貌出现的权力控制也是导演章明刻意想要去探讨的。对于父亲的压制,小漾一直是积极反抗的。当父亲通过监视器干涉女儿恋爱时,小漾执意让父亲认错并写下保证书;毕业之后也拒绝了父亲的工作安排,而是追随所爱去了剧团。在这对父女斗争中包含了两种性格状态之间的复杂组合关系,小漾一直是处于躁动状态,父亲则是非躁动状态。按照格雷马斯的符号学矩阵的四要素模式,则应该加入平静和非平静两个要素。这样就有了冯冈代表的平静,张学锋代表的非平静,从而我们可以根据躁动、非躁动、平静和非平静之间四种性格组成的符号矩阵。

以小漾的爱情之路和对于父亲的反抗两条线索,电影能够组成六种人物关系及其演进过程:
1.躁动对非躁动。刘小漾可以说是整部戏的灵魂人物,许多事因她而起,许多人因她而联系在一起。小漾和父亲最大的冲突一个是工作一个是爱情,虽然父亲百般的阻挠和压制,但是都以小漾的反抗而失败。但最终单纯的小漾却遭到了爱情的重创,此时她或许才明白父亲当初说“我说这些你现在还不懂,以后会慢慢理解”的论断[1]44。作为父亲,刘在水不仅仅是作为女儿对立面出现,更是女儿落魄之后的最终港湾。潜意识里父亲有对女儿的保护、嫉妒和占有,同时基于现实的妥协和摆布。
2.躁动对平静。在爱情这场游戏中,小漾一直处于主动进攻的状态,冯冈是被动接受的。这样的爱情怎么可能持续呢?小漾爱情的幻觉与残酷现实的迎头相撞,冯冈最后的背叛是注定的结局。
3.躁动对非平静。相反的是张学锋对于小漾一直处于进攻的态势。作为一个官二代没有用行政的权力去追求自己的爱情,甚至不惜去剧团“拉大幕”只为了和小漾多多接触。小漾最终对理想的爱情失望,在现实生活中最好的选择就是选择一个爱自己的人,况且这个男人还是通俗意义上的高富帅,张学锋就是她最佳的选择。
4.非躁动对非平静。父亲和张学锋两人是相互欣赏的,在价值观选择上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张学锋走的是上层路线,拿下了未来岳父,也就成功了一半。父亲得益于张学锋父亲县长/书记的背景,自己的政治前途也是有保障的,更重要的是这个未来女婿还是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如此也就无形中消弭了自己用女儿换取政治前途带来的罪恶感。
5.非平静对平静。这是一对割裂的关系,两个情敌之间在全剧中竟然没有一场正面冲突。矛盾的缺失,是冯冈面对情敌选择漠视态度,他从心底没有全心全意维护自己的爱情。
6.非躁动对平静。不同于张学锋和小漾父亲的亲密关系,冯冈和小漾父亲只有在教授小漾音乐时有过一段交集,随后当小漾回乡工作时二人正式谈起了恋爱,冯冈竟然和未来的岳父没有半点接触。
由此观之,冯冈对于女友小漾、情敌张学锋和小漾父亲采取的是一致的被动、消极态度,自始至终处于一个平静乃至于冷漠的心理状态,既不主动又不负责。最终在爱情遇到阻碍时,也没有一个端正的态度去道歉和认真的说明,而是选择了悄然离去。冯冈用南下寻找父亲置换了去北京追寻梦想,似乎在回避小漾指责他想在家乡搜集一些民歌素材,好去北京继续自己的音乐梦想。同时在冯冈写给小漾的邮件中写到“我相信,你会有成功的那一天,那是你的理想,实际上,那也是我的理想。只是现在,我只能把这个理想也寄托在你的身上……代问张学峰好,无论如何,你是他的理想。”这里面有两层含义,其一回避了小漾去剧团发扬紫阳民歌是因为冯冈也在剧团的事实,其二则是有将小漾托付给张学锋的意味。小漾自始至终属于自己,只是冯冈面对爱情时的不主动不勇敢不负责任,才导致爱情的天平失衡,最终落得一个惨淡的下场。小漾困于这三个男人之间,处于反抗、进攻和被进攻三种状态,没有一场是胜利的。在一个清高而又多才的情人的抛弃下,只能又选择那个物质的、多金的但是一心一意爱自己的人,也就是应验了父亲关于成熟和世俗的断言,最终以回归到父亲规划的爱情和职业之路上为结局。
三、浪漫幻影下的现实主义艺术主张
毫无疑问,再也没有比“郎在对门唱山歌”更诗意的片名了。郎住河对岸的桥头,与女主角隔江相望,一座桥连接了二人的爱情,一条江又无情的分割了理想和现实。如同剧中两人的爱情故事一样,看似触手可及,却又咫尺天涯。同样电影故事是富有浪漫主义色彩的,既有家庭音乐教师和女学生的伦理之恋又有底层穷小子和富家女的阶层之恋。前半段纯真美好的少女初恋成功的将观众引入一个浪漫主义的情调中,然而剧情却在电影后半段跌入了现实主义的冰冷深渊。这条贯穿紫阳县城的汉江也是别有深意的,因为“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所以才会“汉有游女,不可求思。”[5]这首出自于《诗经·周南》篇的诗歌的发生地恰巧也就是陕南安康地区,只不过千年前的男女是因为汉江之广而不可相恋,今日之男女却是因为物质上的巨大悬殊而不得不分开。如同电影中连接了老城和新城重复出现的那条桥,不单单是男女主人公地理空间的链接,更是两个人精神世界的分割线。这座大桥即是工业化的象征,男女不会因为交通不便而不能见面,可是却弥补不了二人巨大的心里落差。同样“县城又作为一座桥梁,连接起了采集山歌的山村和更高文化象征的大城市。山歌的命运不知所踪,但在最远处,它是古老的歌谣,表达出原生态的情意,不加掩饰。大城市是结尾冯冈的去处,他终于要换另一种生活,不在刘小漾的预料。”[6]
电影用诗意的镜头将紫阳老县城、街道、大桥、古城门和汉江水一一记录,同时将紫阳民歌挖掘出来成功推广到了国际舞台上,可以说是圆满完成了当地政府“文化搭台,经济唱戏”的初衷。在电影的叙事割裂之下,则充溢着导演章明自己的艺术主张。紫阳县城作为本片外景地承担着重要的叙事功能,而章明对于县城也是情有独钟,“县城质感的地理空间与人、事之间的密不可分,他强调自己的电影中的空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故事的发生必须在某种特定的空间中展开。”而“中国的县城是城市的未完成形态,它的内里蕴含着更多遭受转型冲击的纠结。”[7]也正是如此,县城青年在面对巨大的社会重挫时遭受到的精神上出现挫败、失语的状态。县城中的人们“最能代表中国老百姓的生活状态的人,他们希望什么?在寻找什么?他们想干什么?想象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要关注这一点,就是关注中国未来。中国就是由这样一批人构成的。这样的关注就是对中国整个命运的关注,这种关注的意义应该说是深远的。”[4]288
在章明的成名作《巫山云雨》中桌子是一个重要的意象,电影中的人物经常性的或坐或趴在桌子上无所事事,冷漠而空洞的脸庞尽是迷茫的表情。回到电影《郎在对门唱山歌》,第一场便是刘在水借着中秋家宴宴请县长、书记、剧团演员和小漾同学们的宴会,一张桌围坐了一圈人,这便构成了一个简单的人际关系圈。就这一张简单的饭桌,就把一个基层的关系圈给涵盖完了,借助于这个意象章明把住了时代的脉搏。这种讲述三角恋爱的电影极易陷入一般言情剧“撒狗血”的情境中,然而导演选择了在真实环境中拍摄,赋予剧中主人公社会性身份,同时也是对于基层社会现实的一种记录。紫阳地方元素的不断出现强调了故事的真实性,电影中被影像具体化的紫阳正是广大中国的一个普通样本,“从各个角度来讲有代表性的普通人正是生活在城市与农村之间的地方,这个地方就是小城镇。”[8]无处不在的基层权力关系网网住了每一个人,县城青年男女的现实牵绊也就有了可信度。
作为返乡大学生的冯冈本身并没有发扬紫阳民歌那般崇高的使命,作为中国音乐学院的高材生不应该在基层埋没了自己,他是为了照顾瘫痪的母亲才不得不返回故乡。可以说背负着“沉重的翅膀”,既使满腹才华也挣脱不掉现实的阻力。作为专业军人的张学锋很明显是县城青年一辈的中坚力量,自身带有强烈的建设家乡的愿望,更不用说自身还拥有着强大的社会资源。张县长也坦言自己的儿子学习不好,能够借助于体育生的身份考入市里面的安康学院可能就是最好的出路了,可是张学锋却选择当兵这条路,然后再转业回到地方,如此走了一条完整的人生之路。“好电影的里面是虚构的,外表是真实的。电影也一样,很多东西可以去掉,保留一些自然(真实)的东西,处在自然与不自然(真实与不真实)之间,就是这个道理。”[9]刘在水则希望女儿做个老师,这样就可以长久的留在父母身边了。电影的故事是虚构的,可是里面父母的期望却也正是现实生活中的父母们所苦苦期盼的,这种2014年父辈们作出的选择,也正是当今父辈们求之不得的职业选择。在今天700多万大学毕业生就业艰难的时刻,做老师只是小漾保底的选择,只要她愿意,县城里的公务员立即就可以上任。基层青年走出乡村无外乎也就两条路,可是读书归来却无法再回故乡安家,当兵归来却无法转业到地方,这也正是基层青年自我升阶的天花板。在电影爱情的外核下,却有着基层权力的不断角逐。
四、结语
而今我们再回顾这部所谓对于“未来的想象”的电影,电影中未来的2014年在今天看来成为了过去式,然而现实生活中的人和事不见得比导演期望的过得好。原著小说更文艺,“人性和人命的矛盾层面上解读着人生的无奈和悲凉,这种悲哀成为众所感知而挥之不去的愁绪,融在小说的底蕴,生出永不绝断的忧伤。”[10]电影通过对于原著故事情节的压缩和人物性格、身份的改写,借助于一个爱情的外衣,成功的将紫阳民歌、紫阳县城推广到世界舞台上,这不单单是发生在紫阳县城的爱情悲剧,更是中国千万个县城中可能存在的爱情故事。“异化处理的故事格局、灵肉交织的人物关系、蒸腾雾气的水乡小镇。这一切都好似理想主义的臆造空间,而导演却选用写实主义的拍摄手法将其杂糅在一起,反而使得这部电影独具一种诗性气质。”[11]在这场以民歌和凄美爱情故事为卖点的电影中我们不能忽视权力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1]李春平.郎在对门唱山歌[J].小说月报(中篇小说),2007(1).
[2]李春平.郎在对门唱山歌[M].吉林: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5:3.
[3]李向红,杨小玲.闯荡与回归中的文学华章——著名作家李春平访谈录[N].陕西日报,2007-01-14(3).
[4]程青松,徐伟.此情可待——章明访谈录[J].北京电影学院学报,1996(1).
[5]余冠英.诗经选[M].北京:中华书局,2012:11.
[6]木卫二.《郎在对门唱山歌》:带我去月球[N].第一财经日报,2011-06-24(7).
[7]李蕾.章明“巫山三部曲”的县城影像和精神空间[J].电影新作,2015(4):101-103.
[8]章明.致友人的一封信[J].当代电影,1996(4):54-56.
[9]张果,章明.找到一种电影方法——导演章明访谈[J].南京艺术学院学报(音乐及表演版),2002(2):53-55.
[10]侯红艳.是画,是诗,亦是歌——从宗白华的意境创构理论解读《郎在对门唱山歌》[J].安康学院学报,2014 (3):11-12.
[11]丁钟.和理想说再见——电影《郎在对门唱山歌》的艺术风格[J].西部广播电视,2014(15):105-106.
【责任编校龙霞】

J905
A
1674-0092(2016)04-0008-05
10.16858/j.issn.1674-0092.2016.04.002
2016-05-13
李小雨,男,河南邓州人,山西师范大学戏剧与影视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影视批评和影视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