捍卫生命尊严,发展我国和缓医疗事业
——访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任直教授
文图/《中国医药导报》记者 刘志学 孙君伟
捍卫生命尊严,发展我国和缓医疗事业
——访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王任直教授
文图/《中国医药导报》记者 刘志学 孙君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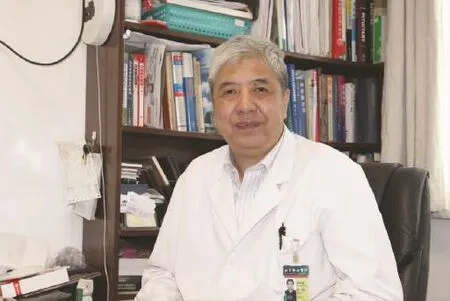
王任直教授近照
阳光从窗外投射进来,照在背光而坐的王任直教授满头银发的发梢上,跳跃出一丛丛炫目的光芒。在万木争荣的春天里,他平静舒缓的话语,一直在“和缓医疗”、“临终关怀”、“生命尊严”等庄重而又严肃的话题间切换。
2016年4月6日,这位神经外科的顶级专家,向本刊记者剖析了一上午我国和缓医疗事业的现状和发展问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王任直教授时而发出的一声声叹息,体现着一位医学大家对于生命的敬畏和体恤……
80%的抢救性支出有没有意义
采访一开始,王任直教授首先提到了中央电视台曾经播出的一期节目,那是关于当今社会医疗支出的一项调查。该调查的一个数据显示:中国人一生中在健康方面的投入,有60%至80%的医疗支出都花费在临去世前一个月的抢救性治疗上。“也就是说,中国的整体医疗的投入,80%都是用在了最后的抢救上。”王任直教授质疑道,“那这80%的抢救性支出到底有没有意义?”
为了解答这个问题,王任直教授以自己的亲人举例说:“我父亲已经去世了,我的岳父也去世了。我是学医的,在他们生命的最后关头,我一直守在旁边。在当时,那些姑息性的气管切开、上呼吸机、心脏复苏按摩等抢救措施,都被我们拒绝了……这种拒绝不是说我不爱我的父亲和岳父、不想挽留他们的生命,更不是因为家庭经济条件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觉得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只能增加患者的痛苦,只能增加亲人的痛苦。没有任何意义的临终抢救没有必要去维持——这是我从一个医生和一个患者家属的角度作出的决定……有时候我也在想,如果我自己将来到了这个时候,会怎么办?我们都是唯物主义者,如果临床诊断已经明确所患的病已经是治不了的病了,我也一定会采用和缓治疗的方法——只要让我在最后不感到痛苦就行了……”
王任直教授接着说:“事实上,这个话题在我们医生圈子里也经常讨论。有一句老话叫‘好死不如赖活着',我觉得这种观念对于危重病患者而言,是不科学的。比如说癌症晚期,明知道生命已经无法延续了,仍然要强制性地通过化疗、放疗去‘赖活着',那就会让患者活得没有尊严。所以从尊重生命尊严的角度来看,和缓医疗是符合人道主义的。从尊重科学的角度来讲,如果一名绝症患者真的没有什么办法延续生命了,那就只能让他活得有尊严一些,让他在离世前痛苦少一些——通过和缓医疗手段,就能达到这些目的——这是最佳的选择……”
和缓医疗的核心内涵在于重视患者的尊严
在接下来的采访中,王任直教授系统地阐述了他对和缓医疗的认识。
他首先介绍说,和缓医疗也称为舒缓医疗或姑息医疗,是指通过控制疼痛、缓解躯体上的不适症状和提供心理、社会和心灵上的支持,为无治愈希望的末期患者提供积极、人性化的服务,为患者和家属赢得尽可能好的生活质量,让患者人生的最后一段旅程舒适、平静、有尊严和少痛苦。
王任直教授进一步解释说,和缓医疗肯定了生命的重要性,认同和接纳死亡,既不刻意缩短生命,也不有意延长生命;重视临终患者最后的自主选择权,致力于提升患者的生活质量,从而使其获得较好的心理慰藉。其核心内涵在于重视患者的尊严,力图通过有效的手段为患者减轻痛苦、满足患者延年益寿的需求。当代和缓医疗的思想核心,不仅符合我国的社会伦理,也是基于唯物主义领域的生死观而作的概括。
他进一步介绍说,这门学科发轫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英国的西塞里·桑德斯博士提出了现代和缓医疗这一概念,经过半个世纪的发展,在西方国家已渐趋成熟。就我国而言,和缓医疗的理念在很早之前就出现了。我国传统的佛、道
以及儒家文化,都可以找到与和缓医疗相对应的思想文化源头。现代和缓医疗在我国的发展最早是从20世纪80年代引进国外和缓医疗理论文献开始的,发展到现在,我国境内的和缓医疗服务机构已突破200家,这个行业的从业者接近5万人;而且和缓医疗在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也得到了很好的发展。这对于很多临终患者而言,都是极大的安慰。
在采访中王任直教授还表示:“随着社会经济水平以及医疗技术的发展,和缓医疗已经成为社会文明的核心构成元素之一。尽管我国和缓医疗事业有了长足的发展,但在实践环节,仍暴露出了一系列的问题和缺陷。”
他认为,当前我国和缓医疗事业的发展面临五大困境。“首先是经典医学倡导的人道主义理论对人们的影响。”王任直教授说,传统的医学理念认为,医疗的意义就在于救死扶伤,每一位医护人员都需要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去减轻患者的痛苦,最大可能地给予他们生的希望,放弃治疗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同时,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孝道文化对于和缓医疗发展的制约也不容小觑。”王任直教授着重分析说,在我国传统的孝道文化里,“孝”是人们最高层级的行为规范;传统思想更为看重养老送终的思想,也十分重视患者生存的长久性。但在实际医疗领域,患者本人的意愿并没得到有效的满足,临终患者往往需要承受很大的痛苦,传统理念带给患者的只是煎熬,这也严重阻碍了我国和缓医疗的进步。
王任直教授继续阐述说:“第三,当前我们国家也缺乏对和缓医疗知识的普及与人才培训;第四是国家缺少相关政策的支持和资助。我国当今和缓医疗事业的发展还十分有限,和西方国家相比,缺乏产业化规模,而且波及面也较为狭隘,开设的项目也十分有限。最后一个问题是医护人员对家属关怀的缺失。在当前的医疗实践中,医护人员往往只注重患者疾病本身,对其心理和精神的需求缺乏全面性认识。临终患者的家属会在其医治期间付出巨大的心思和精力,精神上遭受着各种刺激,这也使得患者自身的心理负担十分沉重,往往得不到相应的心理疏导,得不到同情、理解和帮助,认为和缓医疗服务与一般的医学服务没有多大差别,这在很大程度上也限制了和缓医疗事业的发展……”
突破困境,发展我国和缓医疗事业
王任直教授认为,和缓医疗目前已经成为普遍的社会需求。因为随着人们生活质量的提高,大家更看重生活的幸福指数;而且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显著,一些癌症的发病率也不断攀升,社会领域对和缓医疗的需求也逐渐增加。和缓医疗的理念必将越来越被更多的人接受、采纳和应用。这是和缓医疗事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国外多项研究表明,和缓医疗不仅可提高晚期癌症患者的生存质量、减少临终治疗措施、延长生存期,使患者享受生命所赋予的幸福与乐趣,还能避免有限医疗资源的浪费,大幅度压缩医疗服务成本。
鉴于以上认识,王任直教授对我国和缓医疗事业的发展提出了如下建议:首先,和缓医疗要得到制度化发展。“因为就其性质而言,和缓医疗应该表现为一种医学模式,而且需要不断加以推广,提升这种体制的覆盖面。政府应制定出一整套完整的规章制度,通过全方位的服务保证该制度的享受者受益,同时从现实的财力出发,将提供的服务仅限于经济条件允许的范围内,从而为和缓医疗的发展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其次要实施多样化、多学科综合管理。政府部门要重视医疗卫生领域的发展,加大扶持力度,通过健全的体制来推动社会医疗卫生水平的发展。例如,可以强化一些临终关怀医院的建设,在综合医院或专科医院中开设和缓医疗病区,在社区卫生机构中开设和缓医疗病房、居家临终关怀服务等,以适应临终患者的需求。此外,在心理和精神层面,临终患者也需要得到慰藉;在实际医疗领域,要为这一类群体配备专门的医师及心理治疗师、康复师、社会工作者等,还要针对这一群体开展一些特色活动,使其感受到自己人生最后阶段的意义,从而促进我国和缓医疗向着规模化、系统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
“最重要的是和缓医疗要得到专业化发展。”王任直教授强调,“我们要把和缓医疗当作全新的学科来对待。一些医科院校应开设一些相关的专业课程,为我国和缓医疗事业的发展提供更多的专业性人才。医疗服务机构或科研机构应设立和缓医疗专业,加强对和缓医疗专业人员的培训,强化与和缓医疗相关的理论研究,不断开拓全新的医学模式,深入开展人文主义关怀在医学领域的运用,不断强化医疗卫生领域的评价体制建设,从而为我国和缓医疗事业的发展提供有利条件。同时,发展和缓医疗事业,还需要人们在观念上进行一场革命。要改变大众对死亡的传统观念,即濒死患者、家属及医生都要坚持唯物主义,清醒地认识到一些病症医治的无效性,在临终患者的最后阶段,致力于为其提供高质量的生活。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体现出人文主义关怀和人道主义精神,才能促进人类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以“四全服务”呵护生命尊严
在采访中,王任直教授还着重谈到了临床工作者如何参与和开展和缓医疗工作问题。他首先说:
“毛主席有一句话说得很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惩前毖后'是另外一层意思了,但‘治病救人'这四个字归纳得很好。现在很多医生都是‘治病'的,不是‘救人'的。举个例子说,过去评判一个肿瘤外科大夫是好是坏,两张片子就决定了:一张片子是治疗前的、带着肿瘤的;另一张片子是治疗后的,肿瘤没有了。不管是谁看见这两张片子都会说,你这个外科大夫是好大夫,因为肿瘤没有了。但是作出这种表面判断时,大家很少去想,肿瘤患者在这个大夫的治疗过程中,综合获益是什么?如果你把肿瘤切掉了,血管出血了,损伤到神经了,结果患者瘫痪在床、走不了路了,甚至成了植物人,那你光是‘治病'了,能叫‘救人'吗?所以我很赞赏把‘治病救人'结合起来去论述。”
王任直教授继续阐述说:“一个患者经过医生的治疗,得到什么综合性的益处,这一点很重要。不是说你把患者的肿瘤治没了,你就是好大夫;而是患者通过医生的治疗,有哪些综合性的收益,这才能真正体现我们经常所说的‘以病人为中心'的理念,而不是‘以医生为中心'。在临床上,‘以医生为中心'就是治病。不管是什么病,都不惜一切代价去治,家属也要求不惜一切代价去治。实际上病人的很多想法是随着医生的想法去转变的,医生在这里边是起主导作用的;但我认为在整个治疗过程中,医生其实只是是一个观察者,是个外人,只有患者自己才是一个承担者。所以医生治病就要把疾病和患者的整体情况联系在一起去综合考虑。既然患者是疾病的承担者,那么所有的主导权,包括治疗方案,病人都应该参与到里边来。这并不是说一切治疗措施都要由病人去决定,他们毕竟不是学医的,但医生一定要尊重患者的意见。这从另一个角度来说,也是在帮助医生思考很多问题。医学的发展,也是按照这路去走的……”
王任直教授认为:“不管是作为正常人还是作为患者,快乐、幸福和尊严是三个基本的人格需求。这是人只要活着都要追求的,一辈子都要追求的。那么一个人一旦患了绝症,到了生命末期,是不是这种生命的尊严就得无条件服从于治疗呢?认识这个问题,大概有两点需要分析。第一是医生。医生首先要尊重科学,科学地认识疾病,科学地认识自己的能力和专业。第二,如果患者确实已经到了危重期了,尤其是神经外科的重症患者,最重要的就是‘我到底怎么去治疗这个患者'的问题了。积极的治疗理念不仅仅是药物治疗、手术治疗,还要把和患者之间的沟通、心理疏导,如何能让患者在最后的时光活得更有尊严、更幸福等问题,看作是和手术治疗、药物治疗同等重要的问题,甚至有的时候还会重于药物治疗或者手术治疗的。作为一名医生,还要向患者、患者家属宣传普及这种知识。宣传的声音多了,和缓医疗的理念能被社会认可了,大家也就慢慢接受了……”
采访到最后,王任直教授归结说:“现在面对人口老龄化进程的不断加剧以及癌症患者、心脑血管病等慢性疾病数量持续上升,和缓医疗的重要性进一步凸显,这也应该成为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把握的重要方向。所以,不管从哪个角度说,作为一名临床工作者,都必须重视以临终关怀为主要内容的和缓医疗事业的发展,真正以人为本,以患者为中心,为患者提供‘全人、全队、全家、全程'的‘四全服务'措施,最终造福广大患者,确保社会健康有序的发展……”
专家简介
王任直,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北京协和医院神经外科主任。系中华医学会会员、中国神经外科学会青年委员、中国微循环学会理事、世界神经外科学会会员、日本神经外科学会荣誉会员、中央保健局专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委、教育部出国留学人员科研基金评审委员、中国医学科学院伦理委员会委员。从事神经外科工作30余年,尤其擅长垂体腺瘤、颅咽管瘤、颅底肿瘤、脑干肿瘤、脑血管病、脊髓髓内肿瘤等疾病的治疗。在垂体性疾病、颅咽管瘤及脑血管病等基础及临床研究方面都有独到之处。参与并且承担过多项国家“八·五”“九·五”“十·五”攻关课题及北京协和医院重大课题,作为课题组成员参加的科研项目曾获原卫生部及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科技部及北京市医疗成果三等奖。在基础研究方面,作为课题负责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卫生部科研基金课题、国家863课题、国家教委博士点基金课题多项。在脑血管病研究方面,尤其是缺血性脑血管病研究方面有很多创新之处,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自创了可在动物活体直视情况下观察脑血栓形成的动物模型;在动物活体直视情况下观察脑血栓形成前后脑局部微循环和病理学变化;在动物活体直视情况下观察溶栓药物溶栓过程,了解最佳溶栓时机、最佳以及判断溶栓药物疗效。近年致力于应用先进的基因转入技术和神经干细胞移植的方法治疗缺血性脑血管病,取得了很大进展,其研究成果曾经获得第一届“世界脑卒中大会青年研究者奖”,第一届亚洲微循环大会“优秀论文奖”。发表医学论文100余篇,参与编写医学论著6部;现为中华医学杂志等多家学术期刊编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