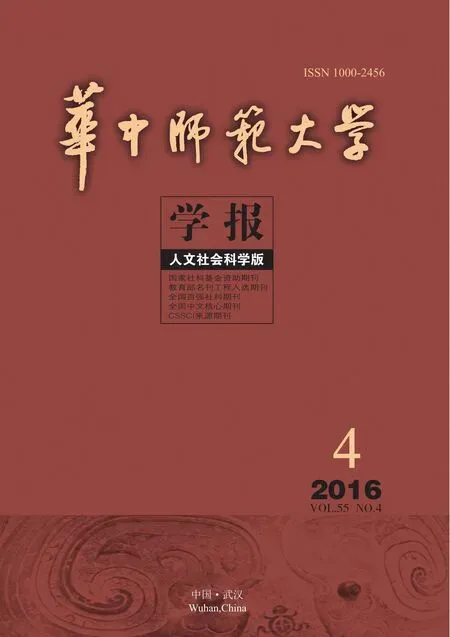儒学研究的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
何晓明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儒学研究的时间维度与空间维度
何晓明
(湖北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62)
儒学的时间维度研究,是一把尺子,一根线,讲究的是“联结”功夫;而空间维度研究,是一把刀,需要的是“切割”手段。无论联结或切割,其实都是一种学术建构。研究者境界的高下、襟怀的宽窄、识见的深浅,往往通过这种建构体现出来。儒家基本的文化态度、文化观念、文化品格是“和而不同”。儒学的时间维度的研究,重在说明“和”,而空间维度的研究,重在说明“不同”。这“不同”,应是特定自然环境、物质生活、文化遗存与学人“心力之为”的有机结合,而非儒者个人或派别简单的自然地理意义上的方位归属。儒学的空间维度研究,必须同时参照时间维度的因素;另一方面,儒学的时间维度研究,也必须同时考虑空间维度的因素。从学界的既往成绩看,相较于时间维度,儒学的空间维度研究,尤须小心谨慎,以避免主观化、简单化、模式化的弊病。
儒学; 时间维度; 空间维度; “和而不同”
一
儒学是中国文化史、思想史、学术史上巨大的时空存在。两千多年来的儒学研究,也总是在时间与空间两大维度间展开。
儒学的时间维度研究,是一把尺子,一根线,讲究的是“联结”功夫;而空间维度研究,是一把刀,更需要“切割”手段。无论联结或切割,其实都是一种学术建构。研究者境界的高下、襟怀的宽窄、识见的深浅,往往通过这种建构体现出来。
时间维度的学术建构,最常见的是儒学发展源流问题方面形形色色的分期说。在总体、宏观层面,牟宗三、杜维明等现代新儒家提出“儒学三期”说:“从先秦源流到儒学成为中国思想的主流之一,这是第一期;儒学在宋代复兴以后逐渐成为东亚文明的体现,这是第二期,这一期一直延续到19世纪末叶;所谓第三期,就是从甲午战争、五四运动以后”①。李泽厚颇不以为然,认为其说存在以心性—道德理论来概括儒学、抹杀荀学及汉代儒学、理论晦涩、脱离大众社会等“六大问题”,因而针锋相对提出“儒学四期说”:“孔、孟、荀为第一期,汉儒为第二期,宋明理学为第三期,现在或未来如要发展,则应为虽继承前三期、却又颇有不同特色的第四期”②。杜维明显然注意到了李泽厚的批评,不无情绪化地反驳道:“回顾儒家思想的发展,你分十期都可以”③。在断代学术层面,王国维有“我朝三百年间,学术三变”说:“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④。钱穆大致赞成王说,但稍作修正,在《清儒学案》序里提出“清代理学四阶段”说:“一曰晚明诸遗老,其次曰顺康雍,又其次曰乾嘉,又其次曰道咸同光”。修正的理由是:“不治晚明诸遗老之书,将无以知宋明理学之归趋。观水而未观其澜,终将无以尽水势之变也。”⑤显而易见,这些分期的歧异,反映了学人把握儒学精髓的不同学术理念、评判基准,而绝非时段划分方面简单的标新立异。
时间维度的尺子,上有刻度。我们运用时,有时关注大的跨度,如“道统问题”。儒家的道统建构,由古人和今人共同完成。孟子、韩愈、程朱以及现代新儒家诸公,都有贡献,非以百年、千年计的长时段不足以说明问题。长时段的意义,如布罗代尔所论:“更有用的概念是结构的概念。这一概念对处理有关长时段历史观念的问题非常之重要。对社会的研究者而言,结构意味着组织、一致性、社会实在与社会团体之间一套非常稳定的关系。对于像我们这样的历史学家而言,它在一方面当然意味着一系列的部分的集成、一个框架,同时它又标志着某些在长时间内一直存在的和只是缓慢地衰亡着的特定实在。”⑥这方面的一个很有代表性的说法是学界对儒学阶段性划分的如下归纳:先秦子学(其时儒学为诸子学之一),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援佛入儒之学,宋明理学,清代朴学,晚清经世实学。在这一时间维度儒学研究的常见格局中,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的时间跨度以百年计,晚清经世实学的时间跨度以十年计。有的时候,我们又特别关注小的时间跨度,如康、梁以今文经学为指导以推行维新变法时,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其惊心动魄的情节演进,则是以小时计,甚至以分秒计。时间跨度的长短,本身并不决定价值、意义的大小。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曾说:“只有那些用尺子和每次的‘报纸趣闻’来衡量世界历史的德国小市民才能想象:在这种伟大的发展中,二十年比一天长,虽然以后可能又会有一天等于二十年的时期。”⑦列宁则在引述这段话后强调道:“观察运动时又不仅要着眼于过去,而且要着眼于将来,并且不是按照只看到缓慢变化的‘进化论者’的庸俗见解进行观察,而是要辨证地进行观察。”⑧
空间维度的学术建构,最常见的是地域性学派的划分,其格局亦有广狭之别。最大端者,有所谓东西南北之分。梁启超曾论道:“孔墨之在北,老庄之在南,商韩之在西,管邹之在东,或重实行,或毗理想,或主峻刻,或崇虚无,其现象与地理一一相应”。到汉代,北方独盛儒学,南方犹喜道家,“《春秋繁露》及其余经说,北学之代表也;《淮南子》及其余词赋,南学之代表也。”⑨南北朝时代政治分裂,更助长了南北学风的分道异途。正如《隋书·儒林传序》所称:“大抵南人得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刘师培曾以长江为分界,论南北学派及学风之差异。“要而论之,南方学派析为三:炫博骋词者为一派,摭拾校勘者为一派,昌微言大义者为一派。北方学派析为二:辨物正名者为一派,格物穷理者为一派。虽学术交通,北学或由北而输南,南学亦由南而输北,然学派起源,夫固彰彰可证者也。”⑩

二


徽学乃徽州之学。1121年(宋宣和三年),朝廷改歙州而置徽州,辖境为今安徽歙县、休宁、祁门、绩溪、黟县及江西婺源。之后,元朝升徽州为路,明朝改为府。中华民国建立后,1912年废徽州建置。此地人文荟萃,历史名人有朱熹,戴震,詹天佑,黄宾虹,胡适,陶行知,以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提到的唯一的中国人王茂荫等。
徽州既有“东南邹鲁”的美誉,又是闻名天下的商贾之乡。在相当的意义上讲,徽学是儒商之学,又是商儒之学。

三
说到空间维度,从历史上看,儒家之学有没有地区性、地域化的问题?回答是肯定的,同时又是有变化的。





两宋时期,儒学进入兴盛繁荣的新阶段。其明显标志是不同学派的纷起林立,相互辩难。




其实,认真思考,这些判断都是有疑问、待商榷的。论者以“地方的儒学学派”与王安石“临川学”(又称“荆公新学”)的冲突来论证地名学派“与官方对称的民间性和与中央对称的地方性”,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但是起码难以作为全称判断而成立。其一,历史上像王安石这样做了宰相、在皇帝的支持下厉行改革,只是个别案例,不足以概括思想史、文化史、学术史论辩的普遍政治背景。更关键的是,众所周知,当年反对王安石最力的是司马光。我们能说王安石的“临川学”就代表官方、中央,司马光的“涑水学”就代表民间、地方吗?以地名命名学派,许多时候并非为了与“官方”划清界限,而是为了凸显此派与彼派在学问、学理方面的分歧。王安石与司马光的分歧,是政治理念、学术路数的分歧,这里的此派、彼派,无论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都与“官方”没有冲突,且均代表着“官方”的利益和立场。至于中国儒学史上存在的更多大大小小以地名命名的学派,无论是北宋的濂、洛、关、闽之学,南宋的永嘉学派,还是清代的桐城派,其学问宗旨、价值诉求、学理重心,都很难与是否对立于官方、独立于中央扯上关系,也不好统统解释为文化中心与非文化中心的不同。
四



另一方面,儒学的时间维度研究,必须同时考虑空间维度的因素。

五
从学界的既往成绩看,相较于时间维度,儒学的空间维度研究,尤须小心谨慎,以避免主观化、简单化、模式化弊病。



论及儒学的空间维度研究尤须谨慎,大师早有警惕。梁启超的名文《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开篇即声明:“本篇以行政区域分节,理论上本极不适当,贪便而已。抑舍此而别求一科学的区分法,亦非易易也。”因此,他只能采取“案而不断”的态度,“胪列事实略为比次而已”。梁启超特别提示从空间维度应该注意研究的诸多问题,例如:
何故一代学术几为江、浙、皖三省所独占?
何故考证学盛于江南,理学盛于河北?
何故山西介在直隶、陕西之间,当彼两省学风极盛时,此乃无可纪述?
何故湖北为交通最便之区,而学者无闻?

何故文化愈盛之省份,其分化愈复杂——如江南之与江北,皖南之与皖北,浙东之与浙西,学风划然不同?
何故同一省中文朴截然殊致——如江苏之徐、海一带,安徽之淮、泗一带,可述者远逊他郡?
何故…………?
何故…………?

注释
①杜维明:《杜维明文集》第二卷,武汉:武汉出版社,2002年,第603页。
②李泽厚:《己卯五说》,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9年,第13页。
③杜维明:《世界汉学》创刊号,北京,1998年,第20页。
④王国维:《观堂集林·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720页。
⑤钱穆:《清儒学案》序,原载《四川省立图书馆图书集刊》第3期,1942年11月。
⑥何兆武主编:《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808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四卷,第348页。
⑧列宁:《列宁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二卷,第602页。
⑨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84页。
⑩刘师培:《南北学派不同论》,汪学群编:《清代学问的门径》,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305页。

























责任编辑梅莉
On Time Dimension and Space Dimension of the Research of Confucianism
He Xiaoming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bei University, Wuhan 430062)
The study of Confucianism from time dimension is like a ruler or a line, which pays great attention to “connection”,while the study from space dimension is like a knife, which emphasizes on the function of “cutting”. However, whether connection or cutting, it is actually a kind of academic construction, reflecting a researcher’s attainments, visions and insights. “Harmony in diversity” is the basic cultural attitude, conception and character of Confucianism. The study of Confucianism from time dimension focuses on “harmony”, while the study from space dimension focuses on “diversity”. When it comes to “diversity”, it means the organic combination of specific natural environment, material life, and cultural relics with mental and physical efforts of the scholars, rather than simply geographical belonging of some individual Confucian or schools. As a consequence, the study from space dimension should refer to the factors of the time dimension as well as the study from time dimension should do. According to the previous achievements in academia, the study of Confucianism from space dimension, compared with that from time dimension, should be more careful to avoid subjectivization, simplification and modeling.
Confucianism; time dimension; space dimension; harmony in diversity
2016-0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