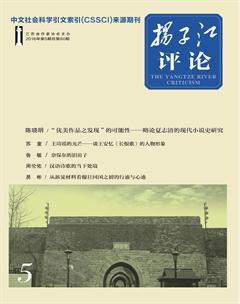奈保尔的旧房子
鲁敏
大师们在青年时代,如同美人初长,气韵丰沛、动作认真,对自己的影响力,尚无乔张做致的顾盼感。相对于声名响亮的印度三部曲、《河湾》、《抵达之谜》,我更偏爱奈保尔的早期作品《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此书出版于1961年,十年后,他获得布克奖,四十年后,获得诺奖。
同属早期的《米格尔大街》已被太多的蜜汁与撒花淹没,这里且不费口舌。相较而言,更早一些的长篇处女作《灵异推拿师》少人赞赏。写作此书时,奈保尔刚从牛津大学毕业三年,连续应征26份工作皆遭拒,寄居在伦敦某个穷亲戚的地下室里:这听上去是有点辛苦的吧。但此书行文宽裕,节奏极为自信,戏谑化的田野生存哲学,弄拙成巧的灵异事件,有如多幕轻型喜剧,滚滚烟尘中自有一股生猛。稍许有点轻飘,年轻人特有的,值得原谅甚至值点羡慕的轻飘。他到底才25岁呀,指缝里处处透出熠熠光华。并且,从这部处女作开始,奈保尔即大致划定了他的自留地:殖民文化与原住民、印度移民与新世界。以致最后获得诺奖时,人们很直接地,像给水果贴上标签:移民写作。我估摸着他老人家并不喜欢。
但地缘交错的写作背景,确乎总有异样之处,他们在作家身上铸成一种动荡而开阔、混浊河水般的基因——
老牌的如亨利·詹姆斯,长年客居欧洲,去世前一年索性加入英籍,他一辈子所写的,都是老欧罗巴与年轻美国人之间的诸种瓜葛,并纠缠成独特的心理小说,当然,他本人似乎也深陷某种跨域心理的泥淖,终生对女性都带有叶公好龙式的畏惧。再如纳博科夫,其繁复的气韵、纯正的邪念与哀伤的幽默感,俄式、法式还是美式?实已辨不出真正的产地。或许每居一处,便会像刷油画一样,使得他更加得层叠缤纷。近年大热的石黑一雄,日式的慎终追远,格调清冷又现代派,与拉什迪、奈保尔被并称为“英国移民作家三杰”(还是像水果论堆儿。他们三个,实在太、太不一样!)。再比如诺奖得主赫塔·米勒、前几年大红的《恶童日记》三部曲、畅销到近乎俗气的《追风筝的人》等,他们的“锁扣”也都在于种族等级、殖民压迫、战乱、流亡等。尤其是《恶童日记》,其独特处还在于其文辞中特有的童稚笨拙之魅,这等神奇从何而来?出生于匈牙利的雅歌塔承认,她用非母语写作时,语言上尚无力达到文学性与复杂化。更年轻一代里,孟加拉裔的裘帕·拉希莉(代表作《疾病解说者》 《不适之地》)在美国当代文坛颇受注目,写作主题仍然是对移民身份的抗争与重建……
太多了,像一张偏执者的购物单,能拉出很长的一串来。拉什迪本人对此也说过,“我们是一种不完全的存在,我们就是偏见本身。”是啊,殖民文化、革命迫害、种族式迁徙等,多么当下、多么全球、多么政治正确!读者、评论界、媒体、影视、翻译,都会扑上去的。
讲远了,回到奈保尔的房子。相对于处女作《灵异推拿师》的飘动感,《毕司沃斯先生的房子》则绝对“压得住秤”了。
这是一个男人与房子的故事。幼时的毕司沃斯因父亲突然亡故,家中房屋被出售,他从此开始在不同亲戚家辗转寄居。成年后入赘到女方大家庭,众多的长辈,女人们、孩子们、家具与饭食、进项与用度,使他日夜愤怒、疲惫不堪。他雄心勃勃试图另立门户、自己造屋,却处处上当乃至最终被人纵火。经过一次精神崩溃后的离家出走,他似乎走出了阴沉的运气,奇迹般地谋得一份差事,并终于替晚年的自己买得一幢房子,算是拥了头顶上的一小片屋顶。事情就此完了吗?奈保尔可绝不会饶过主人公的。他分派给毕司沃斯先生的,是一幢破绽百出、能把人折磨至死的旧房子。新一轮的、更为深重的噩梦就此拉开伴有刺耳噪音的序幕……
索引派认为此书是以奈保尔父亲为原型。因小说的主人公也是特立尼达的印度移民,也做过小报记者,也动笔写点东西,也有一个瞧不起这个家庭的儿子——简直与奈保尔父亲形成镜像对位。父子关系,确实对奈保尔影响深远。从《奈保尔家书》里起码就可以瞧出这种带点励志与重托式的“家传之风”。奈保尔成名后,位置上升很高,越来越傲慢,并开始俯看山河,出过一本随笔集《作家看人》,以英式幽默刻薄掐捏若干名人与同行,比如甘地、福楼拜,包括他青年时代仰慕不已、对他亦有提携之恩的作家鲍威尔。其中,他也给父亲以相当的篇幅,定性后者为加勒比海地区一个不被世人所认知的失意作家,言辞间投射出复杂的孤岛式亲情与接力跑者的体恤。
这些也都是题外话了。人物原型、灵感出处、写作动机、作家心理活动等等,从单纯阅读角度而言,可算作身外之物,或也不必纳入“阅读契约”的范围,又瞎又聋一无所知的阅读是最客观、最鲜美的。回到书本身。前后数数,我读过三遍。这对我而言,算是比较高的记录。倒也不是因为多么的出色,是一流的杰作。这些形容词,都是太大的帽子,不适合轻易戴到哪本小说头上。一再重返现场的原因很简单,只是对它的一种惦记,对初读时那种心境的回顾之想。
引人重读的小说,与其是否华美、是否智性,并不构成正比例相关,关键在于性格魅力,像结交一个富有个性的人。《船讯》 (安妮·普鲁)是笨拙的天真汉,《拉格泰姆时代》 (多克特罗)乃十足浪荡子,《五号屠场》 (冯内古特)是旖旎的神经质,《我们的小镇》 (桑顿·怀尔德)是垂眉菩萨,《谁带回了杜伦迪娜》 (卡达莱)则是人间灵媒。它们都以其独特的调性而令我常年系怀。这大概也正是理想小说的独有境界。
奈保尔的这幢破房子,所吸引到我的,又是什么呢?率直地说,是一种满目疮痍、处处遭殃的倒霉蛋气息。我的口味向来不大上台面,对卑贱的、困厄、辛酸的东西总有天然的亲近感。毕司沃斯先生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如此,每一粒细胞、每一个毛孔都散发出无可弥合的悲剧与失败感,他那么努力、谨慎、动用心机,却处处跌跤、满嘴泥巴。就算偶尔看上去小有胜算,读者也会毫无同情心地等待着:看着吧,这里准有个绊子,他下一步就要四仰八叉了。奈保尔以一种特别的耐心,像连环套一样地反复勾勒,残忍地一刀又一刀,把毕司沃斯先生割得遍体是伤,却又滴血不出。起码他脸上都好好的,他总还是带着尴尬、轻蔑甚至有几分飘逸的笑,即便要骂人,也只会借着刷牙的时机,满嘴的漱口水,没有人能听得清。
中外小说里,有各样的畸零者、不识时务者、被损害与被污辱者,有时能看出来作家是爱这个人的,是怜惜和维护的。奈保尔却未必,或者说,他的态度,是严厉的,不赞同的,毫无原宥,这是男人对男人的,是移民者对移民者的,是替代式的儿子审看替代式的父亲的——这种审看,淋漓纷披,毕司沃斯先生身上一直没有暴露出的伤口、一直没有流出的败血,可能一点不少的,反转到奈保尔身上。我觉得,他写作此书,伴随着泣血无情的疼痛,近乎与他的整个青年时代,进行义无反顾的道别。这道别的力量,连绵不绝,反复地击打读者,反复践踏自己,反复质问人间。
还不止于此。
与这样一个几乎不愿与他目光对视的落拓男人相比,整部小说的环境,或所谓的“典型环境”,更是不堪到令人愤怒。奈保尔看起来既醉心于此,亦擅长于此。他用一种病态的、沉湎式、自虐式的精细笔调,去描写毕先生各个阶段所置身的周边境况。
出产欠丰的土地。烂泥道路。房屋上威胁性的裂痕。他亲手豢养的家畜与软弱不忠的狗。儿子的订制校服,价格昂贵,又被弄坏。妻子至为重视但总是空空如也一无所有的装饰柜。对付慢性病的各种药片,无效的。不断捣乱的下等雇工……虱子般的琐碎,一波波涌上来,充溢着每一个白天夜晚,形成粘乎乎的、尘灰满面的生之压迫。
能看出来的,这是奈保尔着意为之。他写得夸张,写得畅意。他或也清楚地知道,这会形成独特的质地,自会吸引到白白胖胖的优裕阶层,闲置的脂肪里挤压出苦涩但愉悦的文学汁水。推而广之地说,这也是移民小说中常用的一个技术性标配:衰败的底层情调。
低层与情调似乎不宜搭配。但从早已中产化了的审美来看,确乎又是一种蔚然成风的情调。与此类似的,还有绝症情调、失败者情调、自杀情调、背世者情调、亚文化情调等等我不知该如何命名和归类的趋向。臂如我们总会看到,一到时间点,过节般的,人们就会抡圆了膀子拼命纪念梵高、卡夫卡、三岛由纪夫、茨维塔耶娃、海子、萧红、顾城、王小波……艺术家本身是孤美的,所遭逢的境遇是合乎时代情理、近乎必然的,但被后世者以一唱三叹、小合唱、大合唱的方式来反复传诵、抚摩把玩,便会面目全异了。实在都是误会。
似乎又跑远了,还是回到那幢旧房子。六十年代的特立尼达是否真像奈保尔笔下那样的破破烂烂、污水横流,人们跌跌冲冲地从一个陷阱跳往另一个陷阱,这说不好,但对一个寄人篱下、财富拥有量极低的异乡人来说,必须如此。移民的诸种诉求中,生存压迫是最初级的,但恰恰也是最根本的,任何一个水滴大小的纠葛都可以折射和放大出巨象般的异化感。何况奈保尔自有匠心所在。这本书的核心,并非气息沉沦的毕司沃斯先生,亦非这一无是处、等而下之的环境。奈保尔的焦点确乎只有一个:房子。
像钩住一条羸弱的不断挣扎的鱼,奈保尔花费580页,从毕司沃斯先生的出生一直追踪到他的死亡,漫长时光,千绕万转,絮絮叨叨,水尽石烂,反复着力的,即是这一个点。奶嘴似的,魔咒似的,安眠药似的,被人用枪逼指着似的:他想要一处自己的房子。
书中有一段。有一天,毕司沃斯先生终于得到一块无人肯要的坡地(此处根本不宜造屋),他兴头头地去找一个木匠,后者手艺极差、要价很高,但善于扼住要害。他在纸上画两个端正的正方形:“你想要两间卧室。”毕先生点头补充:“还要一间客厅。”木匠于是又添上一个正方形。“还要一条走廊。”于是又画半个正方形。木匠主动接下去描绘:“走廊和前卧室之间,一扇木头门。”“客厅门是彩色窗格玻璃。”“走廊上你想要漂亮的围栏。窗户漆成白色。带台阶的花园。坡地上得有柱子和凉亭。”是的,是的。完全正确。听起来不错。毕先生一直在点头。他们在谈这笔交易的过程中,不断被各种家畜叫声和老婆骂声打断。但毕先生镇定得如临大事,他反过来安慰满怀憧憬(主要是憧憬工钱)的木匠:“罗马非一日造成。我们一步步来。”……自然,这只是毕先生多次上当、然后落得众人嘲笑中的一个小环节。但我相信,就在木匠画在纸上的那几个正方形里,他获得了高潮般的短暂幸福,并且凭此来抵御他亦早有预感的长期的不举之败。
我痛恨又欣赏毕先生这愚蒙的固执,这固执,正是奈保尔本人的固执,他深谙这固执里的寓言意味。屋檐之下,栖身之所,破败欲坠的房子,移民者的房子,老鼠一样在其间繁衍生息。这房子就像一个小小的墙上黑点,死命地深挖进去,变成巨大的黑洞,隐喻到全球语境中迁徙挪移的族群与他们所苦苦寻求的空间。无根的,无维系的,辛苦建构又不断崩塌。
不知奈保尔本人最终是否满意这份隐喻的完成程度,毕竟明显到几乎成为明喻。有时候,小说中的投射与象征,也是个古怪东西,倘若过了头,或干脆以此作为全部生发点,就有些像是装了太多重物的马匹,就别再指望它能够奔跑出优美自若的姿态了。它做的每一个动作与走向,都带着预设的目的性和力学上的撕扯。它用极高超的人工,一层层地铺设叙事逻辑,每一个拐角,每一道风景中的树木与灌木,都有所暗示、有所服务,直到达到约定的终点——作家有力地搁下笔,投来迷雾中的深邃一瞥:我这故事,讲完了,你,“真的”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比如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 《双生》。比如被奉为至典的《城堡》。包括我一直很喜欢的三岛由纪夫,他在《假面自白》中对“死亡、性、血”的反复寓指,像是缀挂了太多蕾丝边,大大伤害了小说的匀称感。再比如二十世纪以来最为人们称道的政治寓言小说《1984》,它的价值,窃以为从来就不是文本意义上的,尽管它独创了许多专有名词与术语并沿用至今。讲这些话可能要挨骂,连我自己也要加入这个骂。毕竟,谁又甘心仅仅是讲一个“睡前故事”呢,就连说书人都要时不时猛拍响木,指点一番世道人心。“言外之意”是作家永远的祸心所在,他固然是要讲一个故事哄你睡觉,可他必定会苦心孤诣、同时矢口否认地在故事里包裹点沉甸甸的玩意儿,他希望能向你当晚的睡梦伸去章鱼般的触角,甚至希望在你次日睁眼醒来时,视线里仍然盘踞着那摇晃着的阴影。
是啊,不止是次日,这些年来,这位素未谋面、却形容俱全的毕司沃斯先生一直都在我前面不远处,挺讨厌地踽踽独行。我真说不清,我到底是在乎他,痛惜他,还是烦他,想甩脱他。
可能是因为我总会看到房子。人们所栖身的各种房子。窄巷里,窗口投射出黄白色光线。面目酷似的公寓笼子,相同的位置,安置着相同的马桶与床铺。春天去往郊区,那里有暗红色外墙、优裕之感的别墅。火车铁道边,闪过粗鄙但也算实用的工房。我一点没打算抒情,也反感我一向警惕的寓指,但的确,我会挺不痛快地想到半个世纪以前,特立尼达地区的毕司沃斯先生的旧房子。随之,一股凉丝丝的满足感,氧气一样,补充至机械跳动的心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