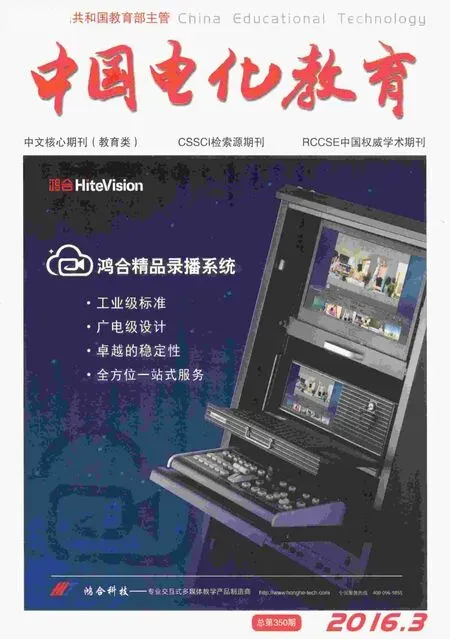利用技术变革教与学
——访哈佛大学教育技术专家克里斯·德迪教授
杨现民,潘青青,李冀红,李 馨,赵云建
(1.江苏师范大学 教育研究院,江苏 徐州 221116;2.中央电化教育馆 中国电化教育杂志社,北京 100031)
利用技术变革教与学
——访哈佛大学教育技术专家克里斯·德迪教授
杨现民1,潘青青1,李冀红1,李 馨2,赵云建2
(1.江苏师范大学 教育研究院,江苏 徐州 221116;2.中央电化教育馆 中国电化教育杂志社,北京 100031)

编者按:克里斯·德迪(Christopher Dede)现为哈佛大学教育学院(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教授,是美国国家教育技术专家组成员,曾作为召集人之一参与制定2010年美国《国家教育技术计划》。德迪教授长期从事技术变革教育方面的研究与实践工作,其研究方向包括新兴学习技术、教育技术政策分析与评估、教育创新、多用户虚拟环境、在线教师专业发展等。此外,他还是国际移动学习领域的先行者和领军人物之一,提出了被广泛采用的教育创新扩展框架。德迪教授主持包括EcoXPT、EcoMOBILE等在内的多个国家科学基金项目,研究成果在世界一流顶尖刊物《科学》上发表。
在访谈中,围绕“技术变革教与学”这一话题,德迪教授与我们分享了他对技术变革教育的内涵、技术与教学集成、新千禧年学习风格、未来学习特征、多用户虚拟环境研究、教育创新的扩展性、数字化教学平台等问题的理解。他指出,我们应该主动采用“社会技术法(Sociotechnical Approach)”去认识和发挥技术在变革教育中的作用;根据技术变革教学与学习环境的不同程度,可以将技术集成分为初级集成、中级集成和高级集成三个层次;技术支持的下一代学习具有三个明显特征:沉浸性、泛在性和个性化;多用户虚拟环境在重塑人类学习上具有无限潜能,可以从多维视角、情境学习和迁移三个方面提升教育效果;教育研究要提前从深度、可持续性、传播、转换和进化五个维度,设计考虑教育创新的扩展性问题。最后,德迪教授比较了数字化教学平台与学习管理系统的区别,并对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提出了一些建议。
技术变革教育;新千禧年学习风格;多用户虚拟环境;数字化教学平台;教育创新扩展
访谈者:德迪教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此次采访。我们了解到,您是美国《国家教育技术计划》(以下简称“NETP2010”)的主要参与者,全程参与了该计划的制定。该计划的核心理念和目标是利用技术“变革”美国教育。为什么要变革当前教育?您是如何理解 “变革”的?
克里斯·德迪: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世界和社会都已经彻底地改变了。高中毕业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比例在下降,而不是在上升,尤其是在科学和工程方面。由于我们目前的教育系统既不能吸引学生,也不能帮助他们成功,美国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人才。美国教育面临的首要挑战是如何变革学生的学习过程,包括校内学习和校外学习,以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和参与,获得21世纪需要的知识和技能。当前教育必须调整课程设置和学习方式,并和社会经济发展紧密结合起来,才能成功应对挑战,适应全新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技术在教育变革进程中发挥着“杠杆”作用,通过与教育方方面面的融合可以“撬动”整个教育系统。
我们需要重新设计全球教育体系,其目标不是让传统的教育模式变得多么高效,而是要让学生为21世纪做好准备。没错,NETP2010的目标就是要适当地使用技术变革美国教育。这里的“变革”意味着整个教育结构的改变,而不是对教育系统某个方面的进化式的“小修小补”。当前,我们完全有能力利用新兴信息技术创造一个面向21世纪全新的教育系统。然而,在技术变革教育的过程中,应极力避免 “技术中心法(Technocentric Approach)”(将新技术看成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主动采用“社会技术法(Socio-technical Approach)”(将技术产品的使用看成是社会、组织、人与工具互动的结果)。教育变革不应该是独立的改革,而是整个社会变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访谈者:大数据、云计算、增强现实等各种新技术,已经出现并开始服务于教育。我们应该如何定位信息技术的价值及其在教育中的变革力量?
克里斯·德迪:技术的价值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把平常事做得更好(Do Conventional Things Better)和做更好的事情(Do Better Things)。尽管把平常事做得更好也有价值,比如效率更高、效果更好,我认为技术对教学更深层次的价值在于重新思考学校教育,为学生提供更多个性化的学习机会,让师生都能更好地利用21世纪的学习资源。做更好的事情包括培养学生在全球化的、以知识为基础、以创新为核心的社会文明中更好应对机遇和挑战的敏感性和快速反应能力。
为了更清晰地描述技术变革教学与学习环境的不同程度,我将技术在教学中的集成应用分为三个等级:
等级一:初级集成。该级集成是技术在教学中最常见的切入点。教师在大型的讲授型课堂中使用技术主要用来提高学生的兴趣或动机,也可用于课堂管理,或者让原本不参与课堂的学生参与进来。这时的技术主要承担“演示”角色,用于辅助教师更好地讲解、辅助学生更好地理解教学内容。技术的功能并未完全与教学过程整合,技术的优势潜能也未充分体现。举个例子,21世纪早期英国投入巨资在中学推广交互式电子白板。一项针对白板技术对教学影响的研究发现,大量的教师使用了电子白板的类似投影仪和幻灯片的演示功能,却很少有老师利用白板的便捷交互功能去增强课堂的有效交互。
等级二:中级集成。该级集成是指每个学生都要有自己的设备,或者有足够的技术设备支持同伴之间以及小组之间共用。此外,学校应当合理配置网络,保证网络畅通,允许学生访问一切经过适当筛选的网络资源。在此级别上,教师可以在自己的教室使用计算设备,而不需要将学生带到管理繁琐、使用不便的网络机房;可以利用技术对不同水平的学习者实施差异化教学;可以利用形成性评价数据对学生实施个性化教学;各种协作工具和技术开始成为最有效、最受关注的教学集成技术。
该级别技术集成的一个例子是基于计算机的教学环境,该环境使用人工智能技术跟踪和监控学生学习过程,以可视化方式为教师提供全面展示学生学业进展的“仪表盘”,帮助教师监督和改进教学。另一个例子是应用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以及其他个人计算设备创设的课堂学习环境,该环境中每个学习者都可以使用自己的计算设备完成个人或小组项目作业。
等级三:高级集成。该级集成强调技术在教学中应用的广泛性。就像NETP2010中写到的那样,技术的应用超越了学校和课堂范围,走向对宽生学习(Life-wide Learning)的支持。在此级别上,教师能够熟练地利用技术精心安排校内和校外学习活动,为学生创造个性化的学习条件,而这在当前的教育教学实践中还不太常见。技术支持下的协作学习法在该技术集成级别上是最有效的,学生的学习参与情况以及学校中所获技能在生活中的迁移应用也是最佳的。
目前,达到高级技术集成上的教学案例还很少。但是,随着网络技术越来越普及以及学校逐渐适应快速变化的世界,将出现更多体现该层级技术应用集成的教学案例。阿伦·柯林斯和同伴在其2009年出版的著作Rethinking Education in the Age of Technology中写到一系列正在浮现的教育场景,从在线教育到兴趣驱动的创客空间以及在线多人游戏,学习者可以在更复杂的教育场景中通过自由聚集和自组织的方式开展灵活学习。2013年由Ito等人发布的一份关联学习(Connected Learning)研究报告中描绘了拥抱上述新场景的学校教育,便可以纳入高级技术集成这一类别中。
需要说明的是,在这个技术集成框架中,技术集成等级的确定不仅要看教室中安装了哪些技术装备,还要看这些技术是否可用以及如何使用,而这便与教师以及课程材料设计者所秉持的学习理论和理念有关。总的来说,较之技术功能本身,教学法和教学情境是影响技术在教学中应用的更重要的因素。
访谈者:快速发展的信息技术正在重塑学生的学习风格。21世纪的教育应该建立在学生新的学习风格基础之上。我们发现,您曾提出一个“新千禧年学习风格”(Neomillennial Learning Styles, NLS)的概念。您可否对NLS做些解释?
克里斯·德迪:当然可以!目前,已有很多学者探讨了媒体比如互联网对学生学习风格的影响。例如,互联网具有开放共享的本质特征,有利于用户比较多源信息、发现个体认识的不全面性以及集体认识的不一致性。因此,基于网络的学习是建立在探寻、筛选和合成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从书本、电视和某个教授的演讲中获取单一的经过验证的知识。
同样,数字媒体技术支持多任务处理,也可能对学生的学习风格带来影响。现在许多青少年在做家庭作业的同时,还会快速浏览课本、听音乐、收发邮件、使用搜索引擎,或者通过即时聊天工具与同学交流。这种多任务处理是否会导致学生形成一种获取信息或者整合形成复杂观点时的浅层次的、易分心的学习风格,取决于这种学习策略是如何使用的。毫无疑问,在处理某些并行任务时,这种策略会导致认知负荷加重,处理效果变差。
这种基于互联网的学习风格,最初认为是“千禧年”学生(1982年之后出生)所独有的。然而,随着各种工具和媒体在日常生活中的普及应用,这种风格在越来越多年龄段的人们身上开始出现。此外,随着计算机和通信技术的不断发展,“新千禧年”学习风格正在兴起。这种新学习风格是基于媒体使用生成的,比如即时通讯软件、多用户虚拟环境和手机。新千禧年学习风格的主要表现如下:
(1)熟练应用多种媒体技术,重视每种技术在交流、活动、体验、表达等方面的价值发挥。以前的“千禧年”学习风格,往往是选择一种最适合自己的单一媒体工具。因此,“新千禧年”学习风格超越了“千禧年”学习风格。
(2)学习是基于集体的探寻、筛选和整合信息和经验,而非独自从最好的某个单一渠道中定位、获取和吸收信息。这也超越了“千禧年”学习风格,“新千禧年”学习风格更喜欢从多样化的、隐性的、情境化的实践经验中学习,而非从单一的、分散的、显性的信息源中学习,同时认为知识既分布式存在于社区和环境中,也存在于个体的头脑中。
(3)喜欢基于真实体验和模拟体验的主动学习。该种学习方式提供了经常反思的机会,也在学习沉浸性、去中心化等方面超越了“千禧年”学习风格。
(4)喜欢用非线性的、关联网页表征的方式表达想法,而非线性的故事。比如,编写一个模拟程序或一组网页表达自己的理解而不是撰写一篇论文。与“千禧年”学习风格不同,“新千禧年”学习风格偏爱富关联的、富情境化的模拟表征体验,而非高度层次化、分支化的多媒体表征。
(5)协同设计满足个人需求和偏好的独具个性的学习经验,而非像“千禧年”学习风格那样从一系列预先定制好的服务范围内进行选择。“新千禧年”学习风格强调人人参与下的协同创造,在参与中学习,各种社交化媒体、工具和平台的出现为此提供了支持。
访谈者:技术为我们重塑学习提供了可能性。您认为技术支持下的未来学习会是什么样子?
克里斯·德迪:我认为,技术支持下的下一代学习具有三个明显特征:沉浸性、泛在性和个性化。
第一是沉浸性。当前的大多数学习由于缺少足够的沉浸感,因此难以导致深度学习的发生。应用虚拟现实技术打造多感官参与的沉浸式学习环境,是未来学习的重要发展趋势。研究发现,虚拟现实技术可以极大地提升学生学习过程中的沉浸感,保持更长时间的专注投入状态,沉浸其中,乐在其中。
第二是泛在性。以无线可穿戴设备、移动终端为代表的普适计算技术的发展,为无处不在学习的发生创造了条件。我们正在步入一个泛在学习的时代。学习者可以在任何地方、任何时刻获取所需的任何信息;即时感知周边环境和服务,发现相关的信息,自动过滤掉无关的信息;通过多种工具便捷地开展互动交流,结识更多潜在的学习伙伴。未来,你所携带的任何智能终端都将成为你的“数字第六感”。
第三是个性化。我认为技术变革教育的一项重要使命便是实现真正的个性化学习。没有技术的支持,个性化学习难以实现规模化,必将在推广上面临巨大困难。随着大数据技术的出现,尤其是教育数据挖掘与学习分析技术的发展,未来的学习将真正实现“个性化”。无论是在校内还是校外,每位学习者都能获得最适合自己的个性化的学习路径、学习计划、学习内容以及学习方法。当然,这种个性化学习的实现需要大量学习者学习数据的支持,同时也依赖于在线学习平台的智能化水平。
访谈者:技术的发展可谓日新月异,每次新技术的出现都是对教育变革的一次助力。您认为未来哪些技术最有可能成为变革教育的核心力量?
克里斯·德迪:这是个很有趣但又很难回答的问题。技术对于教育变革的价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其价值的发挥更多取决于使用技术的人。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普适计算等都有可能成为变革教育的核心力量。但是,未来不管技术如何发展,教育的改变终将由需求驱动而非技术驱动。
我不是预言家,也不喜欢靠直觉评说未来。我的研究团队多年来一直从事多用户虚拟环境(Multiuser Virtual Environments,MUVEs)研究,根据我们的研究经验和发现,MUVEs在重塑人类学习上具有无限潜能。学习者通过“化身”与其他学习者以及虚拟代理进行交互,逼真的情境设置和活动设计,再加上游戏机制的引入,MUVEs能够大大提升学习体验,增强学习的沉浸感,使学习者实现高度参与下的主动学习。随着增强现实、物联网、普适计算等技术的发展,MUVEs中的场景将越来越逼真,运行更加顺畅,参与时间、地点和设备将逐步泛在化,交互将更多元化、便捷化,诊断评价服务越来越智能化。
当前,MUVEs在教育中的应用仍处于起步和发展期,对教育的变革作用还未凸显,仍有很多实际问题值得研究。但是,我相信未来的学习必然走向虚实融合,多用户参与下的虚拟学习有可能从现在的“辅助”角色走向“主导者”,成为终身学习的一种主要形式。大家如果对MUVEs研究刚兴趣,可以阅读我2009年在《科学》上发表的文章Immersive Interfaces for Engagement and Learning。
访谈者:您提到您的团队一直从事多用户虚拟环境方面的研究,可否简要介绍下您主持的研究项目?
克里斯·德迪:在国家科学基金的资助下,我们团队开发了一系列旨在提升中学生科学探究能力以及21世纪技能的交互式计算机仿真软件,比如说River City(http://muve.gse.harvard.edu/rivercityproject/)。River City虽然看起来像一款电子游戏,但符合国家科学教育标准、国家教育技术标准以及21世纪技能培养要求。River City是基于国家内容标准以及生物学、生态学、传染病学和科学探究评估需求所设计的一门技术支持的中学科学课程。该课程采用角色扮演的方式,学生作为River City的访问者穿越到19世纪,用他们的21世纪技能去解决当时的问题。
River City是一个被健康问题困扰着的小镇,它的设计完全基于真实的历史、社会和地理环境。在游戏中学生通过与研究小组进行合作,探索小镇居民生病的原因。他们使用技术追踪可能导致居民生病的原因,以此形成假设,然后设计对照试验验证假设,最后根据收集的数据撰写建议书。在2007年和2008年两年内,北美有近100位教师和5000名学生使用了River City。美国有12个州(亚利桑那州、佛罗里达州、乔治亚州、伊利诺斯州、印第安纳州、马塞诸塞州、密歇根州、新泽西州、纽约州、被卡罗莱纳州、德克萨斯州和威斯康星州)的教师成功地应用了River City。
EcoMUVE(http://ecolearn.gse.harvard.edu/ecoMUVE/overview.php)是由美国教育部教育科学研究院资助,哈佛教育研究院针对中学生所开发的一门采用虚拟环境教授生态系统和因果模式知识的探究式课程。EcoMUVE项目的目标是通过设计基于多用户虚拟环境的探究式课程,促进学生对生态系统和因果模式的深层理解。EcoMUVE采用3D技术搭建,通过计算机再现真实的生态系统,提供类似电子游戏的画面感及趣味体验。学生可以利用计算机进入到虚拟环境中,采用小组协作的方式探索和收集相关信息。沉浸式的交互界面可以让学生在探索和解决现实环境中问题的过程中学习科学知识。EcoMUVE课程包含两个模块,分别是池塘(Pond)和森林(Forest),每个模块持续两周时间。
EcoMOBILE(http://ecolearn.gse.harvard.edu/ecoMOBILE/overview.php)是EcoMUVE课程的最新扩展。在EcoMUVE 中学生探索的是虚拟的池塘生态系统,但是在EcoMOBILE中学生有机会在真实的池塘环境中开展探究学习。通过使用两种移动技术——移动宽带终端和环境探测器,学生可以获得更为真实的学习体验。EcoMOBILE项目正在探索如何通过有效集成沉浸式虚拟环境和包含真实的生态环境,使生态系统教学变得更加有效和迷人。
访谈者:多用户虚拟环境的基本特征是沉浸。根据您长时间对多用户虚拟环境的研究,它对教育和学习的主要影响是什么?
克里斯·德迪:多用户虚拟环境的沉浸性至少可以从三个方面提高教育效果,分别是多维视角、情境学习和迁移。
改变视角或者改变参照标准是理解复杂环境的一种有效方式。沉浸式学习环境提供了以自我为参照(Egocentric Frame of Reference)和以环境为参照(Exocentric Frame of Reference)之间进行转换的机会。以环境为参照得到的是从外在的角度看对象、空间和现象的观点;以自我为参照得到的是从内在角度看对象、空间、现象的观点。自我视角的主要优点是通过具体的、有形的学习提高参与者的行动动机和沉浸感,而环境视角则可以使学习者跳出情景,得到更加抽象和象征性的见解(从整体出发而不是局部)。
沉浸式界面通过模拟真实的问题解决社区,可以实现高质量的情境学习。在该模拟社区中,学生可以与不同技能水平的虚拟实体,包括参与者与计算机代理,进行交互。我们团队开展了一些游戏方面的研究,比如利用虚拟仿真游戏培养年轻人高水平探究能力。研究发现,沉浸感能够提升学生的学习参与度和成就。River City项目的研究也表明,与传统教学以及具有类似学习体验的游戏相比,沉浸式的模拟环境能够使更多的学生获得实质性的科学知识和科学探索技能。其他研究项目(如Quest Atlantis、Whyville等)同样发现,沉浸式虚拟环境能够提高学习者的参与度和学习效果。如果能够懂得如何更好地使用这种沉浸式的模拟体验来设计我们的教学,沉浸式媒体将极有可能激发更多学习者的智慧和参与度。
基于沉浸式界面的情境学习如此重要,某种程度上是因为涉及到“迁移”这一关键问题。已有研究区分出两种测量迁移的方式:隔离式问题解决(Sequestered Problem Solving)和为未来学习做准备(Preparations For Future Learning)。隔离式问题解决往往专注于知识的直接应用,并没有考虑学生应用知识时所处的真实环境与资源。标准化测试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首先演示如何解决标准化的问题,然后测试学生解决相似问题的能力。而这只涉及到“近迁移”,即把在某种情况下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类似的表面上又有所不同的情境中。如果将为未来学习做好准备的成功学习作为评价目的,研究者则需要通过评价学生的拓展性表现来测量迁移。学生在一个丰富的环境中学会如何学习,然后在真实世界的情境中解决相关真实问题。这种迁移属于“远迁移”,而现如今对于讲授式教学的主要批评便是其产生的“远迁移”太少。即使学生在教育环境中得到了练习,也不能将他们学到的知识应用到真实世界的相似情境中。沉浸式界面对于情境学习的另一个潜在优势是,它能模拟真实世界的问题和情境。这就意味着,学习者只需通过虚拟环境获得“近迁移”,就能快速达成为未来学习做好准备的“远迁移”目标。
访谈者:据我们所知,目前美国、中国香港等地已有许多学校在使用您上面提到的EcoMUVE等虚拟环境来支持生态系统的教学以及教师的专业发展。教育研究常见的难题之一便是“小范围的创新研究成果如何持续扩展、推广应用”。请问您是如何扩大研究成果的影响力,推动其在实践领域不断推广应用的?
克里斯·德迪:由于教育情境的复杂性,一体通用的教育创新是行不通的。某个有限条件约束下提出的创新教学模式,当进一步扩大教学实验范围时,其结果往往是不理想的。研究已经表明,与其他社会领域不同,小范围验证过的教学项目如果想成功推广到更大范围、更多样化的教育情境,是非常困难的。一般来说,创新越复杂,适用的情境越宽泛,尝试在原有实验情境和其他情境间实现成功“跨越”的新的实践越有可能失败。教育研究如果不提前设计考虑扩展性问题,那么将会继续浪费大量的资源进行教育干预,尽管这些干预在其他地方可能是有效的。
基于前期研究,我们提出了一个用于指导可扩展性教育创新设计的框架。该框架旨在提升一项教育创新在更广泛的教育情境下的适用性,这里我们称其为“稳健设计”(Robust Design)。
教育创新的扩展包括五个相互关联的维度:深度、可持续性、传播、转换和进化。“深度”是指一项教育创新导致的某些方面的重要变化,包括课堂实践、教师观念、社会交互规范、课程教学原则等。“可持续性”是指这种深度变化可以维持的时长。“传播”是指这种创新成果可以向更多的学校和课堂扩散应用。“转换”是指学区、学校和教师从实践者变为教育创新的“主人”,主动对创新成果进行改造,以不断深化、保持和扩散创新的影响。“进化”是指教育创新的采纳者们对创新进行的合理改造,开始影响到创新的最初设计者,使他们重新思考这项创新。如此一来,在教育创新的设计者和实践者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实践共同体,可以促使教育创新不断进化发展。
上述创新维度不是一个线性的阶段过程,而是描述了教育创新扩展涉及到的几方面重要问题,以帮助教育创新设计者实现创新成果的持续扩展。这些问题(或者说过程)以异常复杂的方式相互关联。举个例子,“可持续性”通过“传播”不断增强,而“转换”又加速了“进化”。根据这个框架,我们成功推广了一些MUVEs项目,比如River City和EcoMUVE。有关该框架的更多详细内容,大家可以阅读我们在《科学教育与技术》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可测量性设计:River City课程的案例研究》。
总的来说,将一项技术创新应用到教育中需要进行足够灵活的设计,以便该技术可以在不同的教育情境中使用。同时,该设计也应该足够“稳健”,以保证其可以在缺少条件的情况下仍然可以取得成效。这就需要研发各种教育创新的变体,类似为不适合植物生长的地区设计杂交植物一样。设计一项具有可持续性和扩展性的教育创新,是一个不断迭代循环的过程。同时,需要教师与创新者一样参与到教育创新的评价和设计中。
访谈者:对教育技术研究者而言,为了增强研究工作的可扩展性,我们应该怎样开展技术支持下的教学研究?
克里斯·德迪:教育技术研究者经常探讨一些“使用某种技术教授某个主题要比其他方法更有效”的比较性问题。这些研究的结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是不确定的且总是视情况而定。一个更富有成效的做法是探究什么样的技术应用能够产生我们想要的理想的教与学,而不是继续探讨现存技术及其支持下的比较性教学实践问题。基于设计的研究(Design-based Research, DBR)代表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它建立在这样的思想之上,即教学干预与优化的创设是设计整个学习环境,其中技术以及其他物化的资源仅仅是其中的一个部件。我们认为,基于设计的研究方法为开发宝贵的有效教学干预,提供了最有希望的路径。
DBR的提出者艾伦柯林斯指出,为了促进教育的持续改善,我们需要把教育当做类似工程学的设计科学对待,把教师当做研究的伙伴和共同主持人,让教师参与创新迭代,灵活地修改我们的想法,检验理论指导下的最有希望的想法,比较多种创新方案,进行创新效果的评估,理解和验证由创新导致的观察结果。不是去问某项技术或者干预是否比其他方案更有效,DBR更加关注教与学的情境,问的是“整个系统功能如何更好发挥以支持学习?”。
DBR的最新发展是基于设计的实施研究(Design-Based Implementation Research, DBIR)。DBR的一个缺陷是它常常聚焦在单个课堂或小组层面,而不是学校系统层面。小规模的DBR通常难以产出超越研究和开发环境的、具有良好可扩展性和可持续性的研究成果。为了解决该问题,毗努伊勒、菲什曼和同事于2011年开始倡导一种最开始就将可扩展性和可持续性作为关键问题的DBR方法。DBIR集成了学习科学领域的迭代、以学习为中心的工作思想,关注组织的变革以及实施条件的有效性。我认为DBR和DBIR的结合是开发稳健型技术干预,促使教与学走向中级或高级技术教学集成的关键,同时也是实现教与学组织方式变革的关键。
访谈者:您在2012年与约翰·理查德合著过一本书Digital Teaching Platforms。这里的DTP具体是指什么?DTP和LMS相比较有何不同?
克里斯·德迪:数字化教学平台是一类新型教育产品,为现在的技术密集型教室提供了主要的教学环境。与之前的综合课程和评估产品不同,DTP专门为教师主导的课堂教学而设计,是课程内容传递的主要载体。为了全面支持教师的教学,DTP提供了一系列集成化的工具,包括课程设计工具、课堂管理工具、学生评估工具等。T2K(The Time To Know)是首个商业化的大规模运行的DTP案例。T2K用交互型数字课程作为课堂交互媒介,完全代替了传统的纸质教科书。同时,它还提供了便捷的工具可以轻松管理课堂,支持教师顺畅地开展个体教学和小组教学,实现学习活动的个性化定制。
DTP支持一对一教室环境下的教与学。在该环境中,每个学生拥有一台笔记本电脑,或者类似的其他计算设备,可以通过无线连接到互联网。教师也配备一套具有联网功能的计算机可以连接到交互式白板或者投影机。在教师的指导下,借助联网的计算设备,师生之间以及生生之间的交互得到了增强。DTP以学习活动序列的方式递送课程内容,每个序列可以由小工具、多媒体演示、练习、游戏等组成。课前,教师利用教学设计支持工具进行备课;课中,教师使用多媒体讲解知识,使用小工具探索数学概念和布置课堂练习;课后,教师可以检查每个学生的学业进步、课堂表现趋势,同时为下次课做好教学计划。
和DTP相比,学习管理系统专门为课下学习而设计,并且不需要教师的额外管理。因此,LMS的理想使用环境是网络机房或者校外环境。LMS很少在课堂上使用,其应用的目的包括满足特殊学生补习的需要,为补修课程考试做准备,或者是为了高效使用网络机房。LMS还常常用于企业的培训项目或者社会机构组织的非学历教育项目。总之,二者的应用场景和目的是不同的。LMS主要用于课外教与学,而DTP重在支持课堂教学。
访谈者:中国正在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已经颁布了《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2011-2020年)》等规划文件,目前正在征求教育信息化“十三五”发展规划方面的意见。您是教育技术发展规划方面的国际知名专家,可否为中国教育信息化发展提供一些建议?
克里斯·德迪:我去年到上海参加过一次国际会议,了解到中国政府正在大力推进“技术变革教育”的发展战略,而这和美国NETP2010目标是一致的。中国发达地区的信息化水平很高,学校的软硬件配置都很不错,说明中国已经具备了技术变革教育的基础条件。我也了解到,中国有很多教育技术领域的研究者正在从事技术支持创新教学、移动与泛在学习、混合式学习、智能教育、大数据教育创新应用等方面的前沿研究。中国也有很多地区、很多学校在开展翻转课堂的教学实验,且发展规模越来越大,高校的MOOC发展也很迅速。因此,我感觉到中国的技术变革教育之路越来越清晰,前景很好。说到政策建议,根据我个人的研究与规划方面的经验,未来中国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力推动技术变革教育。
第一,积极制定专门政策保证技术变革教育的顺利实施。任何国家教育改革的成功都和科学的政策分不开。教育改革的最大阻力往往不是来自技术、师资和资金,而是来自民众对教育改革的态度和认识。中国应通过多种媒体渠道对广大社会公众宣传技术变革教育的重要性,通过政策的制定和宣传,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技术变革教育观,同时支持国家政策的推行。此外,政策制定方面还应发挥大数据的作用。中国区域经济和教育发展都不均衡,因此政策的制定应避免一刀切,而应基于多方数据,因地制宜。
第二,让企业参与进来。与学校相比,企业更善于创新。他们在技术、运营、管理等多方拥有巨大的优势,可以成为技术推动教育变革的主要力量。我了解到,中国已经在探索教育信息化过程中如何引入市场机制,引导更多企业参与到教育变革中来。这种做法很好,美国也在这么做。下一步,中国需要制定更加明确的市场规范,让更多有担当的企业在技术变革教育的历史进程中发挥更大价值。
第三,让技术做更好的事情。前面已经谈到过,技术变革教育不仅仅是使用技术改善当前的教与学,而是对整个教育系统的重构。技术应当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除了把常规的教学事情做好,更要做一些以前无法完成的事情(Do Better Things)。比如,创客技术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将学生的分数提高几分,而在于培养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动手能力;大数据能够将个性化教学实现“规模化”,而没有技术的支持“个性化”与“规模化”是难以兼容的。
第四,加强研究成果的转化和推广。我与中国的教育技术研究者进行过多次交流,有一点需要注意,研究成果如何在实践中扩展应用,前面我也谈到过教育创新的扩展性问题。我想,中国研究者在开展研究设计时应当将扩展性纳入考虑范围。因为只有这样,产出的研究成果才更有可能在后期推广中取得成功。此外,研究方法上建议采用DBR。根据我们团队的研究经验,这种方法更适合教育技术研究。
Editorial Commentary: Christopher Dede is a professor in learning technologies at the graduate school of education of Harvard University. He is also a member of 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expert committee, who participated in writing the national educational technology plan of year 2010.His research spans emerging technologies for learning, infusing technology into largescale educational improvement initiatives, developing policies that support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ing leadership in educational innovation. He is currently conducting funded studies to develop and assess learning environments based on virtual worlds, augmented realities, transformed social interaction, and online teacher professional development. Dede is a leader in mobile learning initiatives and has developed a widely used framework for scaling up educational innovations. He is the PI of several projects sponsored by the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such as EcoXPT and EcoMOBILE. One of his papers has been published on the world rank-top journal of Science.
In this interview, Dede talked about his understandings of several key topics, including the connation of educational transformation using technology, the technology integration in teaching, neomillennial learning styles, future learning, multi-users virtual environment, the scalability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and digital teaching platform. He indicated that: (1) we should take a sociotechnical approach to analyze and use technology in transforming education; (2) there are three levels of technology infrastructure/integration that help to describe the extent to which technologies are used to transform teaching and learning environments; (3)the next-generation learning shaped by technologies have three obvious characteristics: immersive and richly contextualized, ubiquitous,and personalized; (4) MUVEs can enhance education in at least three ways: by enabling multiple perspectives, situated learning, and transfer; (5)researchers should design the innovation considering from five inter-related dimensions: depth, sustainability, spread,shift, and evolution. Finally, Dede compare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digital teaching platform and the learning management system, and propose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onization in China.
Utilizing Technology to Transform Teaching and Learning—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Christopher Dede at Harvard University
Yang Xianmin1, Pan Qingqing1, Li Jihong1, Li Xin2, Zhao Yunjian2
(1.Institute of Education, Jiangsu Normal University, Xuzhou Jiangsu 221116; 2.Chinese Educational Technology,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31)
Technology Transforming Education; Neomillennial Learning Styles; Multi-user Virtural Environments; Digital Teaching Platforms; Scalability of Educational Innovation
G434
:A
1006—9860(2016)03—0001—07
杨现民: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泛在学习、知识进化、智慧教育、技术增强学习(yangxianmin888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