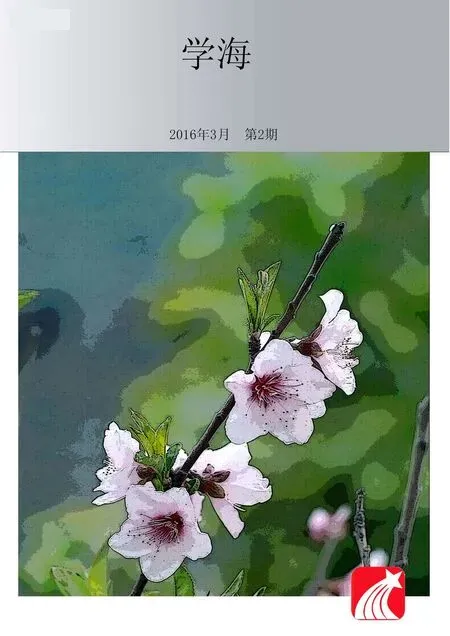伦理道德的中国精神哲学范式与中国话语*1
樊 浩
伦理道德的中国精神哲学范式与中国话语*1
樊浩
内容提要中国精神哲学传统一以贯之演绎的是伦理与道德“相濡以沫”的文化正剧,而拒绝向“相忘江湖”的道德自由方向发展。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哲学形态的“中国范式”就是孔子的“克己复礼为仁”。如果进行话语转换,与黑格尔“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西方范式”相比,“礼——克己——仁”的“中国范式”最重要的“中国风情”便是“克己”。“中国范式”在现代以文化坚守与问题共识两种方式呈现,一方面表现为对伦理型文化的坚守,以及“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的转型轨迹,另一方面是在关于分配不公和官员腐败两大问题诊断的高度共识中所表现的伦理忧患意识。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话语,就是“伦——理——道——德——得”的精神哲学过程和精神哲学体系。
伦理道德精神哲学形态中国范式中国话语
中国文明史和精神史以历史叙事的方式演绎了由伦理与道德构成的人的精神世界发展的一般规律,并且从文明的开端就戏剧般地显示其作为伦理型文化的特殊走向。孔子与老子、《论语》与《道德经》的同时诞生,似乎隐谕伦理与道德之间不可分离的文明关系,关于这种关系,《大宗师》中庄子以寓言体裁发出了“相濡以沫”还是“相忘江湖”的哲学追问,似乎展示了一种历史必然性。有趣而令人深思的是,日后几千年的精神史,伦理与道德并没有沿着庄子式的智慧指引走上以道德自由为追求的“相忘江湖”,始终是不离不弃、同甘共苦的是伦理性的“相濡以沫”。这是伦理型文化的宿命,也是伦理型文化的悲怆情愫,中国精神史,演绎的就是伦理与道德“相濡以沫”的文化正剧。于是,在体现伦理道德发展的一般精神哲学规律的同时,中国伦理道德建构了特殊的精神哲学形态,显现出精神世界的特殊风情,即“中国风情”。
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范式”
伦理道德发展的中国精神哲学形态具有几个特别要素。其一,对于伦理与道德“相濡以沫”的坚守,和对于“相忘江湖”的拒绝;其二,老子哲学智慧与孔子伦理情怀的合璧,老子以“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的哲学智慧道破精神世界的秘密,完成对精神世界的批判,孔子以“仁”的道德创造及其向“礼”的伦理的辩证复归,进行精神世界的重建;其三,伦理道德精神哲学形态的经典表述或中国表达,就是孔子“克己复礼为仁”的精神哲学范式。①
“克己复礼为仁”作为标示伦理与道德关系的中国精神哲学范式,具有三个基本的结构元素:“礼”的伦理实体;“仁”的道德主体;由“克己”而达到的“礼”与“仁”、伦理与道德之间的和解,或由此建构的精神世界的同一性。如果对这一历史命题进行哲学分析,“礼”不能一般地诠释为周礼,而是血缘、伦理、政治三位一体的伦理实体,或家国一体的伦理实体;“仁”也不只是一种德,在《论语》以及日后的中国道德哲学发展中,“仁”既是一种德,又是一切德,是全德之名;这一命题中最重要的内涵是以“仁”的道德诠释“礼”的伦理,认为“仁”的道德是为实现“礼”的伦理,而实现的路径则是通过“克己”的自我超越。在这个精神哲学命题中,“克己”之“己”是个别性之“己”,“克己”的要义是扬弃和超越自己的个别性或个体,达到普遍性,即孟子所说的“养其大者为大人”。由是,“礼”是实体,“己”是个体,“仁”是主体,“克己复礼为仁”指证的便是一个“实体——个体——主体”辩证运动的精神哲学形态,或“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辩证发展的精神世界,而作为其中介的“克己”则极富表达力地呈现伦理世界向道德世界的辩证转换。由此可以表明,人类的精神世界,人类文明的大智慧,在哲学的层面相通,难以沟通和理解的只是话语形态,如果进行话语形态的哲学转换,就可以发现人类文明的精髓。
“克己复礼为仁”的精神哲学范式有两大“中国风情”。(1)“礼”的伦理风情。与黑格尔范式相通,它强调伦理与道德,准确地说,“礼”的伦理与“仁”的道德的一体,但与之不同或更为突显的是,它以“礼”释“仁”,以“礼”为“仁”的价值目标,在“礼”—“仁”合一,伦理与道德一体中,伦理处于具有某种终极价值的优先的地位。虽然黑格尔强调“实体即主体”,“德是一种伦理上的造诣”,但“克己复礼为仁”的中国话语对伦理的优先地位显然更加突显,因为它不仅是对人的精神发展的诠释,而且是对“礼”的伦理与“仁”的道德在价值体系中不同地位的诠释。(2)“克己”的风情。在“克己复礼为仁”所创造的“礼——克己——仁”的精神哲学范式中,“克己”是体现中国哲学智慧、中国文化创造和中国精神境界的关键性话语,藉此这一命题比黑格尔范式更合理。因为,“克己”已经不是一般性地指证和承认个体,而且包含着教化世界中个体的自我超越及其向道德主体提升的精神的自我否定性。正因为如此,它成为中国伦理道德对人类文明的特殊贡献,也是人类精神世界的独特风情。
无论“克己复礼为仁”还是中国精神哲学传统,如果试图与世界文明对话,如果要对它进行充分的倾听和理解,如果要使其具有某种哲学的普遍性,就必须澄明和揭示它在“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或“实体——个体——主体”的辩证运动中对那些具有普遍意义的精神哲学问题的中国话语、中国解决和中国智慧。这些基本问题是:伦理世界中家庭与国家的关系;教化世界中公与私的关系;道德世界中理与欲的关系;最后三大世界辩证发展中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关系。
黑格尔伦理世界中的基本元素与基本矛盾是家庭与民族两种精神形态的关系。黑格尔认为,伦理世界的语言是规律,两大元素分别代表两大规律,即神的规律与人的规律,它们具有两种性质,即黑夜的规律与白日的规律。当两大规律处于自在状态即没有通过人的行动向现实转化时,它们保持“安静的平衡”,创造伦理世界的“无限与美好”。然而,行动打破了这种“安静的平衡”,因为在行动中“家庭成员”与“民族公民”两种自我意识相互撕扯——或者从“家庭成员”出发,或者从“民族公民”出发,二者只能居其一,最后导致伦理世界的精神分裂。于是便造成这种状况,“只有不行动才无过失”,“伦理行动本身就是具有罪行的环节”。②在中国传统哲学尤其是儒家传统中,两大元素的话语形态是所谓家与国,或家庭与国家,与之相对应的伦理规律即所谓“天伦”与“人伦”。它们与黑格尔话语的区别在于:家庭与民族的话语,是基于西方“民族国家”的传统,而在中国,无论国家还是民族的概念,都是包含多民族或多种族的综合性话语。在中国传统中,家庭与国家两大元素之间同样存在某种紧张,所谓“忠孝不能两全”,但家国一体的“国家”结构,注定了它们之间只是“乐观的紧张”,因而行动不仅不构成罪过的环节,而且是达到家与国伦理和解的过程。如何对待家庭这个人类最重要也是延绵力最强的原始遗产,不仅决定伦理的文化气质,甚至在相当程度上也决定人类的命运。诚然,正如黑格尔所说,在人的精神发展中,一个人如果只属于家庭而不属于民族,那他只是一个“非现实的阴影”。但是,如果没有家庭,一个人也可能只是一个“非现实的幽灵”。黑格尔精神哲学消解两大伦理规律紧张的出路,是将人从“家庭成员”与“民族公民”同时还原为个人,于是进入以抽象个人为世界主宰的“法权状态”,即单子化的原子世界。中国传统消解二者紧张的路径是以家庭为本位,通过“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伦理,和“移孝作忠”的道德,达到二者之间的和解,最后“天下如一家,中国如一人”,从而缔造出与西方迥然不同的“教化世界”。
黑格尔教化世界的基本问题是个体与实体的矛盾。在教化世界中,一方面人成为“抽象的个人”,另一方面人的本质依然是实体性。人的个别性与普遍性的统一在对象化的财富与国家权力中达到,但只能抽象地达到,在教化世界中精神的最终命运是分裂为“顽固的单点性与冷酷的普遍性”。在中国精神哲学话语中,个体与实体的关系被现实化为公私关系。中国哲学认为,义利关系是精神世界的基本问题,“天下之事,惟义利而已。”③但义利只是一种形上话语,所以在日后的历史发展尤其到宋明理学中义利关系被具体化为公私关系,“义与利,只是一个公与私也。”④“凡一事便有两端,是底即天理之公,非底即人欲之私”。⑤“己者,人欲之私也;礼者,天理之公也。一人之中,二者不可两立”。⑥以义利为精神世界的基本问题的形上表达,以公私表述教化世界中个体与实体关系,是典型的中国话语,也是典型的伦理型文化的话语,与实体——个体——主体的话语系统相比,义利—公私的话语气质,是将哲学话语转换为伦理话语,赋予其善恶判断的价值属性。
黑格尔道德世界的核心是所谓“道德世界观”。道德世界观作为人的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以自我意识中出现道德与自然的对峙与对立为前提,但其真谛却是在道德与自然的对峙中对道德的坚守和对自然的扬弃,因而“道德世界观”的本质是“道德主宰下的世界观”,因其是对自然的扬弃和超越,成为“对其自身具有确定性的精神”。不过,道德世界观的精髓是建构道德与自然之间、义务与现实之间的“被设定的和谐”。这种预定的和谐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道德与客观自然即现实世界的和谐;二是道德与主观自然即感性欲望之间的和谐,两大和谐的终极目标,是“使道德规律成为自然规律”。在中国精神哲学中,道德与自然的和谐被宋明理学用一个命题表达:“存天理,灭人欲”。理欲关系即道德与自然关系的中国话语,理欲观即宋明理学的道德世界观。它一方面突显天理与人欲的对立与紧张,“天理人欲,不容并列。”⑦另一方面强调二者之间的和谐:“有个天理,便有个人欲,盖缘这个天理,须有个安顿处,才安顿得不好,便有个人欲出来。”⑧但紧张是二者的本质,“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⑨于是,“存天理,灭人欲”便成为道德主体,也成为道德世界建立的标志。
以“克己复礼为仁”为范式的中国精神哲学的特殊风情,不仅在于关于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基本问题及其话语系统,更在于三个世界关系。如前所述,最能代表关于三个世界关系理念的话语就是所谓“克己”。在“克己复礼为仁”的精神哲学范式中,“克己”是在义与利、公与私、理与欲的对立中通过个体性的扬弃,通过对伦理实体的认同与回归,达到主体性的道德建构。克己者胜己也。“克己”在日常话语中被表述为“修养”。在中国精神哲学中,“修养”是包含关于人的精神的“修”与“养”的肯定与否定两种结构的哲学话语。“修”什么?“修”一己之“身”;“养”什么?“养”作为人的实体之“性”,所谓“修身养性”。“身”是个别的“单一物”,是“私”,是自然,因而存在某种紧张;“性”是普遍物,人人具有,因而只需要“养”或“存养”。“修养”的对象分别对应着性(心)与身、公与私、理与欲,最后对应着义与利。显然,这是一种“求诸己”的精神哲学范式。正因为如此,中国伦理道德,中国精神哲学的基本问题,并不是个体与整体,或公与私的关系问题,而是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的关系问题。个体与整体或公与私的关系,可能是任何伦理道德和精神哲学的基本问题,因为精神的本质就是个体的“单一物”与实体的“普遍物”的统一,伦理道德所创造的精神哲学的根本任务,是如何将个体从个别性存在提升为普遍性存在,因而善是其绝对价值。诸精神哲学形态的区别在于,个体的善与社会的善到底谁处于更优先的地位?实现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统一的价值逻辑是什么?以伦理优先为取向和气质特征的中国精神哲学的价值逻辑是:“人人可以为尧舜”,一旦人人都为尧舜,社会也就圣化即至善了。这是典型的德性主义伦理精神的体系。这种德性伦理精神的哲学智慧是基于“人人可以为尧舜”的性善信念,一方面将道德的主动权交给个体,另一方面也将道德的责任全部交给了个体。与之相对应,从苏格拉底开启的西方精神哲学传统的主流是正义论的伦理精神,它以社会正义或社会至善为个体至善的前提,苏格拉底对德性及其教育的诠释就是,做具有良好法律城邦的公民。这一命题遭遇的文明难题是:如果城邦没有良好的法律,是否做它的公民?如何做一个好公民?需要辩证的是,正义与德性一样,本质上是一种信念和理念,完成了,就终结了;因为没有完成,没有实现,所以成为追求的理想状态。个体至善与社会至善关系的合理性在于二者之间的辩证互动,不同精神哲学的别样风情,在于到底以何为基点或原点?以个体至善为着力点的中国精神哲学从未放弃社会批判即对社会至善的诉求,孔孟周游列国以诸侯为游说对象甚至被讥讽“好为帝王师”,其实质就是通过对统治者的道德劝导和伦理批评而追求社会至善。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哲学具有相通的文明本质,区别在于不同的文化气质。
“中国范式”的现代呈现

反“三纲”与反“五常”、伦理批判与道德批判在近现代转型中有何不同意义?中国为何是“伦理型文化”而非“道德型文化”?决不能将这些被广泛接受的命题只当作一种话语方式,其中隐含着对中国传统精神哲学形态的重要的认知与判断。自五四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至今已有一个世纪,几番激烈的冲击,“孔家店”之所以“打”而不“倒”,其内坚韧的依然提伦理,其最根本的原因是,孔孟儒家学说,不仅建立在家国一体、由家及国的社会结构基础上,而且就是这种“国家”文明的理论,体现了“国家”文明的伦理真理及其精神哲学诉求。20世纪狂风暴雨般接连发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革命,虽然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的伦理关系,但是“国家”文明的本质没变。在相当程度上,计划经济体制使“国家”文明更为完善,因为它在“家”与“国”之间找到并建构起一种体制过渡与精神中介,这就是所谓“单位”。“单位制”的最大魅力,在于它不仅在经济和政治上成为“家”与“国”之间的链接,而且在文化上和精神上兼具“家”与“国”的双重意义。计划经济下的“单位”,既有“国”的政治与经济功能,又是个体走上社会之后的“第二家庭”;既是政治与经济的实体,更是直接的伦理实体,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人的精神的第二家园。
问题在于,经过最近三十多年市场经济的激荡,中国的伦理道德,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到底呈现为何种精神哲学形态?这一问题的另一表达方式是: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到底以何种方式呈现?显然,当今中国并没有形成关于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自觉理论,乃至这一问题的提出还刚刚开始,在相当程度上,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是以“问题式”,即伦理道德的现实发展所遭遇的现实问题的方式呈现。因此,必须也只能从现实的伦理关系和道德生活中对伦理道德的中国精神哲学形态进行实证分析。

可以支持这一判断的还有另一组数据,即伦理道德转型中“新五伦”与“新五常”的变化曲线。在传统社会,“五伦”与“五常”分别被当作伦理与道德的范型。三次调查,“最重要的伦理关系”中居前三位的毫无例外都是家庭血缘关系,并且排序完全相同,即父母子女,夫妻,兄弟姐妹;排列第五位的都是朋友关系,唯一变化是第四位,或者是同事同学关系,或者是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然而,“最重要的德性”的新五常的排序是:爱,诚信,责任,正义,宽容。两组数据可以得出的结论是:与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的传统“五伦”相比,“新五伦”只有君臣一伦发生变化,表明在现代转型中伦理上的变化率是20%;与之相对照,与仁义礼智信的传统“五常”相比,“新五伦”中只有爱与诚信两大德目与之接近,其余三德都是“新道德”,表明道德上的变化率是60%。20%VS60%,伦理与道德的现代发展呈现“伦理上守望传统,道德上走向现代”的“同行异情”的转型轨迹。有待追问的是,经过一个多世纪的激荡,为何伦理上的变化率只有20%?中国社会为何表现出如此坚定而坚韧的伦理守望?“同行”与“异情”分别传递了何种民族精神信息?一个多世纪激荡中20%的伦理变化率只能说明,伦理在对中国民族、中国社会、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具有更为根本的地位,是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精神发展中的多中之一,变中之不变,是中国文化和中国民族精神的内核所在。结合以上关于处理人际冲突中两个最重要的选项,伦理与道德的“同行”表明,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依然是伦理与道德一体;而伦理与道德的“异情”则表明,在“同行”中伦理具有比道德更为优先的地位。
“问题轨迹”从否证的维度以更强烈的方式佐证当今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全国性调查提供了另外两个重要信息。(1)当今中国社会最令人担忧的问题是什么?三次调查,不仅选择相同,而且排序完全一致:两极分化;腐败不能根治。(2)“你对什么人在伦理道德上最不满意?”三次调查的共同选择是:政府官员,演艺娱乐圈,商人和企业家;“你对什么人在伦理道德上最满意?”三次调查的共同结果是:农民,工人,教师。以上两大信息,表面上指向经济与政治,然而问题的因果链及其实质都在伦理。在精神哲学意义上,分配不公与官员腐败的根本问题是“伦理存在”,具体地说,这两大问题最终解构和颠覆的都是社会的伦理存在。在人的精神发展中,伦理有多种存在形态:在伦理世界是家庭与民族;在教化世界或世俗世界是财富与国家权力;在道德世界中是良心与善。三种存在形态中,世俗社会中的财富与国家权力是马克思所说的最具决定意义的客观基础。财富与国家权力在经济、政治和伦理三大领域中的关系在于:只有当财富具有普遍性,国家权力具有公共性时,它们才“有精神”,才成为伦理性存在,一旦丧失普遍性与公共性,便在经济和政治领域丧失伦理合法性。分配不公与官员腐败的根本原因,是财富与国家权力的伦理性解构,作为最严重的社会后果,是由财富与权力的伦理合法性解构而导致的社会的伦理存在的颠覆,原因和结果,在终极性上都指向伦理。政府官员、演艺娱乐圈、商人和企业家三大精英群体,农民、工人、教师三大草根群体,分别成为伦理道德上最不被满意和最被满意的群体所透露的严峻信号,是当今中国社会正从经济上的两极分化走向伦理上的两极分化,潜在甚至已经开始生成两大“精神集团”。之所以说是“精神集团”,是因为它们并不是或者还不是两种经济的和政治的集团,而是由伦理态度、道德评价在精神世界中所形成的两大集团或两大阵营。“集团”的意味是,主体并只是“某一个”的群体,而是“某一类”即分别在政治、文化、经济上处于优势地位的“精英群体”,与三大领域中相对处于弱势地位的“草根群体”在精神世界的对峙。重要的是,不能简单地将它们看作是由不同经济地位和经济利益而形成的两大精神集团,与以上两大社会问题相同的是,它们无论在原因还是结果方面都指向伦理,不仅两大精神集团因伦理态度与道德评价而生成,而且最严重的是,它们可能表现为精神世界中的两种截然对峙的伦理认同。当然,因为这些数据来自全国,代表全社会而不某一群体的伦理态度和道德评价,其中包括精英群体自身的选择,因而它在本质上并不只是两大精神集团的对峙,而且传递另外一些更为严峻也更为令人担忧的信号:一方面,整个社会可能已经出现伦理上的精神分裂,另一方面,生活世界中的政治、经济、文化地位与精神世界中的伦理地位之间已经出现倒置,即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强势地位的群体,在伦理上处于弱势地位;而在政治、经济、文化上处于弱势地位的群体,在伦理上造于强势地位。这种状况很容易让人们想起孔子“礼失而求诸野”,和毛泽东“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的告诫,因而无论如何必须引起全社会的警醒,也必须向全社会发出预警。诚然,它们只是一种主观的评价,然而,评价表明态度,态度影响行为,更重要的是,评价和态度都根源于社会现实,具体地说源于由分配不公与官员腐败两大问题所导致的伦理存在被解构至少遭遇威胁和危机的现实。同时,“问题轨迹”的两组信息必须审慎辨析的是:它们根本上是伦理问题,而不是熟知中所说的道德问题。人们总是对当今中国社会的道德状况忧心忡忡,感叹“道德滑坡”,总是呼吁加强“道德建设”,试图通过一场道德拯救走出目前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危机。然而两组数据传递的深层信息是:当今中国社会最深刻、最严峻的问题,不是道德问题,而是伦理问题,至少首先是伦理问题。
综上,转型轨迹与问题轨迹从正反两方面呈现或折射当今中国社会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其中,转型轨迹呈现精神气质和精神体质,问题轨迹体现精神素质。人际关系的调节方式方面80%左右对伦理手段的首选,“新五伦”之于传统五伦80%的相通,两个80%以数据的精确性表明当今中国人精神世界的伦理气质与伦理素质;同时,伦理与道德在行为选择与变化轨迹方面的巨大反差,同样也以数据的客观性表明伦理之于道德的绝对优先地位。问题轨迹中的“两大问题”与“两大精神集团”之间潜在深刻的因果关联,其精神哲学要义是道德生活与伦理关系在精神世界中的因果链,因它无论分配不公还是官员腐败,都始于道德而见于伦理,即道德问题积累和积聚为严峻的伦理后果。在相当程度上可以说,因为两大问题,所以生成两大精神集团;因为道德问题,所以形成严重的伦理危机。显然,分配不公与官员腐败的问题可能在任何文明中都存在,但一方面可能问题的严重程度不同,另一方面两大问题形成如此强烈和如此严峻的伦理后果,却可能是中国社会的特有现象,它从反面诠释了中国现代社会的伦理型文化的素质特征。转型轨迹和问题轨迹以现实而强烈的方式申言:当今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依然是或必须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的形态。
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话语”
综上,无论传统范式还是现代呈现,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都是伦理道德一体、伦理优先。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的“中国话语”是什么?
行文至此,两个问题具有前提意义:其一,对伦理道德来说,精神哲学是否必要,如何必要?换言之,伦理道德与精神哲学到底何种关系?其二,“精神哲学形态”能否“中国”,如何“中国”?
迄今为止,中国并没有黑格尔意义上那种自觉的精神哲学理论和体系,但是,并不能由此断言中国没有精神哲学,更不能断言精神哲学没有民族形态。精神哲学是人的精神发展史和民族精神发展史的理论体系,在黑格尔那里,“精神”相对于“自然”,“精神哲学”与“自然哲学”相对应,它们是两种最大的哲学类型。这里所讨论是狭义的即精神走出个体进入社会而作为“社会意识”的那种精神哲学。在这个意义上,精神哲学的基本问题,是伦理与道德的关系问题,因为伦理道德是实现个体与自己的公共本质的精神统一的意识形态,伦理道德与精神哲学是一种相互诠释的关系,精神哲学是关于伦理道德关系的理论与体系,其文化传统与实践智慧,就是精神哲学形态。中国文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必定有精神哲学传统,只是在形上层面没有形成西方式的体系化的精神哲学理论,事实上,西方精神哲学也只是在黑格尔体系中才达到理论和体系的自觉。时至今日,精神哲学无论对中国还是西方都是一个陌生的话题,在西方,可能因为它的形上取向和体系诉求,更可能因为它似乎是黑格尔的专利,常常被认为是具有“终结”性质的多此一举;在中国,它可能直接就是一个曲高和寡的“异乡客”。然而,对精神哲学的拒绝和冷落,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在这个碎片化的时代人们的思维和研究还没有达到相当的广度与深度,以至缺乏这样的抱负和能力,对人类精神发展和精神史进行总体性鸟瞰和检阅。可以断言的是,如果没有精神哲学,不仅关于伦理与道德关系的争讼永远不可能终结,而且人的精神和精神世界永远只是美丽的现代性碎片。
精神哲学形态及其话语体系如何“中国”,能否“中国”?两种努力显然是重要的。一是体验和反思,借助黑格尔精神哲学理论,参照性地把握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传统;二是建构,由于中国没有自觉的精神哲学理论和体系,关于中国精神哲学的传统及其现代发展的把握都是一种历史建构。历史建构的真义是什么?是用新的理念和框架对传统进行理解和呈现。于是,建构既是尊重,又是创造,是孔子所说的“温故而知新”。关于伦理道德的中国精神哲学形态的把握,一方面要尊重那些经过千百年文明传承锤炼的概念话语,另一方面要对这些概念话语在精神哲学意义上进行新的组织与诠释。五千年伦理型文化一脉相承的发展,已经凝结为一些对民族精神极具表达力的话语,在这方面,也许最重要的不是标新立异,根据西方舶来品衍生一些激发人们好奇心而缺乏现实内容更缺乏生命力的概念,而是通过充分倾听和理解那些作为民族传统精华的标志性话语,把握伦理道德的中国精神哲学形态。因此,关于中国话语的把握,既是对学术品质的考验,也是对学术功力的考验。胡适先生说过,新思潮本质上是一种新态度。关于中国话语的寻找,体现对中国传统,对中国文明,对创造中国传统和中国文明的先人的一种文化态度,由于它以所谓“现代话语”或“世界话语”为参照,因而也体现对世界的文化态度。对文化传统的尊重本质上是一种自尊,这种自尊将形成一种文化心态上的自信,而无论自尊还是自信,都来源于学术自觉。一个缺乏自尊的民族很难赢得世界的尊重,就像缺乏自尊的个人很难赢得他人的尊重一样。不过,对传统的倾听和理解,需要深厚的文化功力,因为它是一种穿越时空的自我理解和历史理解,其中渗透了诸多情绪和情结。精神哲学的中国形态与中国话语的理解,本质上是对精神世界的自我理解,是精神上的理论自觉,它与保守无关,却预示和标志一种精神归宿和文化认同。
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的中国话语是什么?很简单,答案已经存在于问题之中,就是“伦理道德”。在中国,伦理与道德具有与英文中“ethics”和“moral”十分不同的文化意蕴。在古希腊,它们分别对应于社会的风俗习惯和个人的品质气质,然而在中国,“伦理”与“道德”两个概念的话语重心从诞生始便在于“伦”与“道”。“伦理”是“伦”之“理”,“道德”是“道”之“德”(“得”)。黑格尔将精神的客观形态表述为“伦理世界——教化世界——道德世界”的话语体系,在中国,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话语就是“伦——理——道——德——得”的体系。这个体系包括微观层面的三大关系——伦与理的关系,理与道的关系,道与德的关系;宏观层面的三大关系——伦与道的关系,伦与德的关系,德与得的关系;最后,是伦理与道德的关系。



由此可以发现,“伦——理——道——德——得”,既是中国精神哲学的话语,也是中国精神哲学的体系。其中,“伦”是根源性和家园性的话语,由“伦”向“理”、“道”、“德”、“得”转化的过程,相当程度上是人的精神从实体的家园中诞生并向生活世界转化的过程。“伦”是实体,“德”是主体,“理”与“道”是精神,“伦——理——道——德”构成人的精神世界的体系,这个精神世界是“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体系,是“伦理道德”与“精神哲学”、精神世界同一的体系,充分体现了伦理型文化的气质和智慧。而“德者得也”的逻辑,使伦理道德的精神世界成为与生活世界辩证互动的开放性结构。“伦——理——道——德——得”的精神哲学的话语与体系,与黑格尔精神哲学体系有诸多相通之处,更有许多异样风情。在这个体系中,“德”是“伦”的实现,是“伦”的造诣,正如黑格尔说,“德在本性上是一种伦理的造诣”,在中国精神哲学中,“德”就是一种“伦”的造诣,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过程,就是实体性的“伦”转化为主体性的“德”的过程。但是,第一,这个体系和话语系统更为简洁和清晰地呈现伦理道德如何在精神世界中一体,伦理到底如何比道德具有优先的地位的问题;第二,在伦理世界和道德世界之间,没有黑格尔教化世界中的那种紧张,而只是通过“理”与“道”的中介由实体向主体的转化,是一种伦理型文化的“乐观的紧张”;第三,最大的特点,是在“伦——理——道——德”的精神世界建构和完成之后,与生活世界互动,精神世界的价值建构处于比生活世界更为优先的地位,精神世界对生活世界指引的诉求更为清晰。第四,“德者得也”的“德得相通”使精神世界和生活世界在辩证互动中走向善恶因果律的超越,这种超越因其终极性而具有某种宗教气质,进而现实化为一种文化信念,从而与西方精神哲学形态相通;同时又是一种现实的超越,因为它可以将从文化信念和价值追求转化为对社会的现实批判,因而使伦理道德,使人的精神世界既成为内在超越的力量,又成为社会改造的力量。这是伦理型文化的大智慧,也是一道伦理型文化的绚丽风情。
①注:关于“克己复礼为仁”的精神哲学形态,参见樊浩“孔子伦理道德思想的精神哲学诠释”,《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7期。
②黑格尔:《精神现象学》,贺麟、王玖兴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4页。
③二程:《遗书》卷十一
④二程:《遗书》卷十七。
⑤⑨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三。
⑥⑧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
⑦朱熹:《孟子集注·万章句上》
⑩戴震:《与某书》







〔责任编辑:吴明〕
樊和平,笔名樊浩,东南大学教授,江苏省社会科学院副院长,东南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主任,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中国伦理学会副会长,fhhp59@163.com。南京,210096
*本文系江苏省“2011”工程“公民道德与社会风尚协同创新中心”和高校重点研究基地“道德哲学与中国道德发展研究所”承担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招标项目“现代伦理学诸理论形态研究”(项目号:10&ZD072)、重点项目“伦理道德的精神哲学形态”(项目号:10AZX004)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