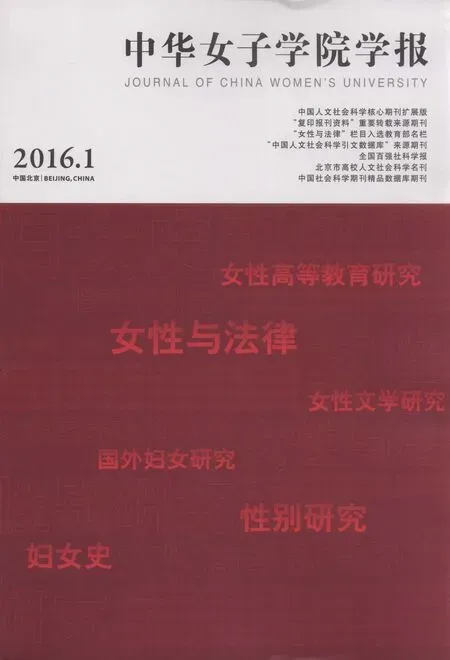儿童忽视的保护原则与机制探究
李军
儿童忽视的保护原则与机制探究
李军
儿童忽视是对儿童的伤害。保护儿童避免受到忽视的举措需要遵循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和必要时剥夺不合格监护人的监护资格的原则。儿童忽视保护机制涉及刑法、未成年人法庭、强制报告和保护服务四大内容。现阶段,在我国构建儿童忽视保护机制应着力完善儿童忽视保护制度的政策法律,强化儿童忽视强制报告和咨询决策制度,加强公众有关儿童忽视的专题教育和获得社会支持。
儿童忽视;保护原则;保护机制
近些年,许多儿童伤亡事件,都指向一个社会现实问题——儿童忽视。本文基于儿童保护的立场,将重点探讨针对儿童忽视的保护原则,并对构建儿童忽视保护机制提出政策性建议,以唤醒社会对儿童忽视问题的关注,进一步推动我国儿童保护工作的开展。
一、儿童忽视的界定
儿童忽视与儿童遭受的情感冷漠、身体虐待和性侵犯通称为儿童伤害(Child Maltreatment)。世界卫生组织(WHO)1977年就认为:儿童虐待与忽视是一个社会现象和公共卫生问题,存在于所有社会的所有时段中。[1]
儿童忽视虽自古就有,但直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被侵害、被忽视以及受虐待的儿童问题才开始引起一些欧洲国家、社会组织的关注,并逐步从儿童权益保护和社会政策制定层面来积极干预儿童忽视问题。
如何界定儿童忽视,西方学者做了大量探索性研究。舒马赫和海曼认为,儿童忽视是一种虐待,是指家长或照顾者未能提供与孩童年龄相适的所必须和必要的护理,包括住房、食品、服装、教育、监督、医疗保健以及体力、智力和情感能力发展所需要的其他基本需求。[2]戈登指出,儿童忽视是监护人等因忽视而未履行对儿童需求的满足,从而危及或损害了儿童的健康发展。[1]世界卫生组织将儿童忽视定义为:在孩子发展的阶段,由于照顾者的不作为或注意力不集中,对儿童的健康、智力、精神、道德和社会发展造成损害。[3]
近些年,我国儿童忽视问题的发生愈发频繁,已引起各级政府、社会机构和学者的高度重视。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潘建平等认为儿童忽视指长时间且严重地有意忽略了儿童的基本需要(如足够的衣食住行、教育及医疗照顾等),危及或损害了儿童的健康发展;或在本应避免的状况下使儿童面对巨大的威胁(包括缺乏照料而忍受的饥寒、强迫儿童从事与其年龄、身体状况不相符的工作等)。[4]李媛等认为,儿童忽视包括两个要件:一是监护人具备为儿童的身心健康、营养、安全庇护和教育等方面提供照料的能力;二是监护人事实上长期对儿童放任不管以及怠慢,不满足儿童的基本需求,对儿童的健康和安全漠不关心,对衣食住行及卫生不予照顾等。[5]
在西方学者看来,忽视最初被概念化为由于家长的疏漏导致孩子缺乏足够的照顾。隐含的前提是父母或照顾人没有伤害孩子的故意;而中国的学者一般认为,儿童忽视不排除监护人、照顾人的有意为之(如潘建平等人的定义)。
实际上,儿童忽视是监护者不履行某些职责的状态,可在孩子的个人形象和行为中观察到。[6]78不论中外学者对儿童忽视定义如何,儿童忽视至少具有两个要素:(1)任何一个被父母、监护人或照顾人遗弃的孩子;(2)由于父母、监护人或照顾人的过错或习惯而造成孩子缺乏适当的照顾。
我国儿童忽视研究起步较晚,目前还没有儿童忽视状况的国家统计数据。潘建平等人开展的有关研究数据显示:我国城市3—6岁儿童总忽视率为28%,男、女儿童忽视率分别为32.6%和23.7%,单亲家庭中的儿童受忽视率高达42.9%,“三代同堂”家庭中儿童忽视率最低,为25.5%;与安全、医疗方面相比较,儿童在身心情感方面受到的忽视较多。[7]
一项对陕西省的调查显示,被调查儿童的总忽视率为32.5%,总忽视度为42.5。[8]另一组资料显示:6—8岁年龄段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忽视率分别为 48.5%和 37.5%,忽视度分别为(47.64+9.44)和(45.34+8.53),(P值均 <0.01),9—11岁年龄段留守儿童和非留守儿童忽视率分别为49.7%和37.4%,忽视度分别为(46.61+10.58)和(43.59+10.15)(P值均<0.01)。[9]
在我国,传统的照护伦理容易导致儿童忽视。照护伦理强调监护者对被照护者无私的、非对称对等的情感付出。[10]59但我国传统文化以成人为本位的儿童照护、教育的观念侵蚀着家长对待儿童的方式,儿童更容易受到轻视、忽视乃至蔑视。父母长辈往往以工作忙、事业压力大为借口,没时间和精力打理儿童的需要,即使教育儿童也常常是棍棒式教育。
此外,家庭保护功能的弱化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儿童忽视问题。人口控制政策一定程度上造成现代家庭规模小型化,许多传统家庭所承担的功能正在消退消失。不可否认的一个社会现实是,儿童与家庭面临的压力和风险陡增:当家庭因为离婚、经济不济、意外等事件发生时,家庭甚至会解体,即使是亲生父母,也会对自己的子女造成伤害,中国农村大量的留守儿童就是现实的写照。[11]
儿童忽视可对儿童的生命发育与安全、行为与情感认知、教育和社会化产生短期或长期的严重损害。“尤其是发生在生命早期的忽视对儿童以后的发育具有更为严重的危害,它可导致从儿童到成人发育过程中不良的社会或情感反应,造成体格与心理、行为的失常或变态。”[12]
二、儿童忽视保护的主要原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第一章第五条规定了未成年人保护工作的原则:(1)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严;(2)适应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的规律和特点;(3)教育与保护相结合。这些原则对儿童忽视保护有指导作用。但是儿童忽视问题涉及儿童的安全、身心情感健康、父母(照顾者)的权益和责任等领域,有其特殊性,还应该遵循下列主要原则。
(一)最佳利益原则——孩子的最佳利益和福利
任何影响儿童的行为,都必须以儿童的最佳利益为首要考虑因素。最佳利益原则体现在《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第3条,即“关于儿童的一切行动,不论是由公私社会福利机构、法院、行政当局或立法机构执行,均应以儿童的最大利益为一种首要考虑”。[13]最佳利益原则涉及的不同方面,如国家、社会、家庭、父母、儿童等都有明确的界定。因此,儿童公约就成为防范儿童虐待和忽视必不可少的国际准则。[14]
最佳利益原则效力囊括与儿童有关的一切事务,把解决儿童有关问题提升到利益保护的更高层次,本质上更能体现儿童主体的权利理念。在处理儿童忽视问题时,需要考虑怎样做才能最大限度地满足这些儿童的最佳利益的需要。最佳利益原则的实施,对于父母和儿童权利的实现具有双重性:它既是在厘清儿童的权利,也是在分配父母的权利。因此,父母和儿童的利益应该是相辅相成的。儿童最佳利益的实现有赖于作为监护人的父母的亲权的行使和相应义务的履行;父母以往对子女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履行,自然也会作为衡量子女“最佳利益”的参照;在斟酌最佳利益标准时,不能不考虑父母权利的现实。[15]
(二)对不称职的父母可以选择托管或剥夺监护权原则
尽管最佳利益原则常常涉及这样的推定:父母行使监护权可实现孩子的最佳利益。但当父母过去的行为一直不令人满意时,需要考虑这些行为是否会在未来重复发生。不道德、虐待、遗弃和忽视等是判断父母是否称职的常见理由。[16]
在各类有关儿童忽视的定义中,一个显而易见的共同点是这些定义都隐含着这样一个原则:如果父母没有给儿童提供最低限度的保护和照顾的话,那么国家则有理由介入或干涉。[17]选择托管或剥夺监护权原则,其理论依据是“父母权责失灵”和“国家亲权”。
父母权责失灵是指父母或监护人因主观或客观原因不能承担照料、保护儿童的职责,而导致儿童处于被危害的边缘。
国家亲权是指国家作为公权力主体方对儿童的法定监护人(如父母)的自然亲权进行干预,在自然亲权不能履行担责时承担儿童监护人之职。[18]随着儿童权利主体的社会认可,国家亲权在保障儿童最佳利益方面逐渐弥补和填充父母责任,介入家庭以保护受害儿童的权利。[18]现今国家亲权成为许多儿童权益保护法规的基础,涉及虐待和疏忽、家庭寄养、收养、医疗决策、抚养、保护性立法和青少年犯罪等。[19]
国家亲权是国家干预主义的一种体现。生养、庇护和教导儿童长期以来被视为家庭内的私事,且这种自由历来受到法律的保护。父母权责一旦失灵,家庭就变成压迫与控制儿童的中心,而非保护与养育家庭成员的避风港。当发生父母权责失灵时,国家应该介入并阻止滥用,以保护个体家庭成员的权利。[20]
国家亲权干预的观点是基于这样一种理念:虽然家庭本应是温暖、友爱、安全、相互扶持的,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家庭都如此。不幸的家庭往往不再是儿童的避风港,而是“一个充满压迫、原始意愿和权威、暴力和野蛮的中心”。[21]基于此,国家亲权替代父母亲权对儿童进行保护与照顾是适当的。[22]
需要强调的是,儿童忽视的政策法规并不是拆散家庭,而是修复不满意的家庭环境,让孩子尽可能与父母生活在一起。国家亲权的行使是扮演合作性亲权的角色。合作性的国家亲权比父母照顾儿童的责任更广泛,它涵盖了不同服务,是一种集体责任的体现,旨在维护和促进受照护儿童的生活机会。国家亲权旨在家庭和国家之间建立一种平衡,即需要对儿童保护和对家庭进行支持。国家亲权的行使仅仅靠公权力的介入难以有效保障儿童权利,因此应该强调社会中其他主体的参与和责任承担。社会责任不仅强调非营利组织、社区乃至个人对父母亲权的监督和救济,还强调通过社会各个部门的共同参与,为儿童的生存和发展共同营造一个有利的环境。[22]
三、儿童忽视的保护机制
在西方,一些国家提供了通过健全的福利制度和行之有效的司法体系来保护儿童权益的范例,国家公权通过干预家庭来保护儿童的利益,剥夺不履行责任父母的监护权,甚至将儿童带离原生家庭,逐渐承担起保护儿童的主要责任。[23]183-184
鲍尔森将有关儿童忽视保护的机制分为四大类:刑法、未成年人法庭、虐待儿童报告法律和通过立法建立的“保护服务”等。[24]这四方面在保护体系中各司其职(见图1)。其中刑法主要是允许可以起诉那些伤害孩子或对孩子造成伤害的父母或照顾者;未成年人法庭制定的条例,允许此类法院对“被忽视”的儿童进行保护或监督;一般国家和地方的司法机构都给予少年法庭紧急司法管辖权,将孩子从危险的家庭暂时解救出来;儿童忽视报告制度的建立,则主要是鼓励或授权公民对实际的或可疑的虐待或忽视儿童行为进行报告,此外,还需要国家、社区、社会组织等对儿童忽视的家庭提供支持。鲍尔森儿童忽视保护机制提供了分析我国现有的儿童忽视保护措施的基本框架。

图1 鲍尔森儿童忽视保护机制架构
《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国家机关、武装力量、政党、社会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城乡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未成年人的监护人和其他成年公民共同承担保护儿童的责任。这种共同责任在现实中的困境是很难在我国找到一个组织和机构来明确履行儿童保护之职。
我国目前尚缺乏专门的防治儿童虐待和忽视的法律,也没有明确的对儿童忽视的法律界定,针对儿童忽视的法律保护工作亟待加强。即便是儿童忽视的危害需要司法定铎,也往往只能参照散见于各类单独法律、法令中的条文。如宪法中有关禁止虐待老人、妇女儿童的纲领性规定;刑法中有关“虐待罪”的规定等。《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虽然明确规定了保护未成年人的包括生存、发展、受教育等权利,禁止虐待未成年人等内容,但现实中缺乏一套可落实的司法程序,因此这些法律对儿童虐待和忽视行为的惩戒性不足。
在儿童忽视保护政策方面,国务院于2011年7月30日颁布的《中国儿童发展纲要 (2011—2020)》突出了儿童优先原则与儿童最佳利益原则并重,强调为防范和遏制家庭虐待忽视和暴力等事件的发生,需要着力为儿童提供良好的家庭环境,建立预防“强制报告”和“紧急救助和治疗辅导”等处置儿童受侵害问题的工作机制等。[25]
关于儿童忽视报告制度主要体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相关条文中,该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有权对侵犯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予以劝阻、制止或者向有关部门提出检举或者控告。对发现儿童被虐待和忽视的组织和个人而言,该法只是授权而非强制他们向有关部门报告,也就是说组织和个人有权报告而非必须报告,而且报告形式、渠道无明确规定。在现实中人们往往不知如何和向谁报告儿童忽视问题。
尽管国家亲权(国家监护权)在西方国家已被广为接受和运用,但我国目前还没有相关的政策和法律明确规定国家亲权的行使和效力。国家亲权对受虐和忽视儿童如何提供临时保护和长久安置缺乏法律、政策支持。
另外,我国专业做儿童忽视保护项目的公益机构寥寥无几,社会支持力量薄弱。这样的公益项目的执行需要大量的志愿者参与,及时的心理辅导和慰藉介入,广泛的社会资源和临时收养救济的机构,还需要政府相关职能部门、社会各界的协助,应对这样复杂的局面,众多公益机构则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
四、构建儿童忽视保护机制的建议
保护儿童基本权利,使其免受虐待和忽视,不仅是监护人、家庭的责任,而且是国家和全社会的义务。
(一)完善我国儿童虐待和忽视保护制度的政策法律
要解决儿童问题,不能止步于关注和满足儿童的生物性个体成长发展需求,如住处、食物、医疗和教育等,更重要的是提高和优化儿童所处的社会环境。[26]1对于儿童保护而言,与其过多强调儿童具有权利的重要性,还不如强调和落实父母、监护人乃至全社会应该如何承担对儿童的义务。[27]在现代社会,如果儿童保护不能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法律、政策等落实为一种制度安排,那么任何对儿童保护的谈论都只能是停留在道德或应然层面上的权利诉求。国家应通过制定政策约束监护人、家庭行为,督促其承担保护、照料儿童的法律责任。
在我国现阶段,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为蓝本,建立完备、具体、可实施、可操作的法律体系是儿童忽视保护制度有效运行的保障。针对当前儿童忽视事件频发的现实,应当抓住时机,统一认识,着力将散布于各个独立法律中有关儿童虐待、忽视的条文予以整合,实现对儿童忽视保护的系统、全面的国家顶层设计。明确国家、地方各级政府、社会(社区)、学校、家庭、父母(监护人)等对于儿童忽视问题防范的责任;热情鼓励和积极引入社会力量和慈善组织,建立类似于儿童福利院的具有一定养护功能的防治儿童忽视机构,并在工作中注重社会各部门、各机构、各组织间的合作。同时在法律和政策层面明确儿童忽视的定义、种类、儿童权利保护原则、对儿童忽视风险家庭、监护人行为的早期发现机制等重要议题;明确针对儿童忽视的强制报告制度,处理流程,司法介入、紧急庇护和临时安置程序,撤销监护人资格和国家亲权的适用,国家监护与最终安置等。[28]
(二)强化儿童忽视强制报告和咨询决策制度
国家、政府可以通过民政、妇联和司法等公权机构对儿童忽视问题进行干预和介入,将传统上在家庭范围内解决儿童忽视问题纳入国家意志的调处范围中,国家、社会、学校、父母(监护人)等共同负有对儿童权益保护的职责,应协同共治儿童的各种问题。[11]
在国家层面明确统一的儿童权益保护机构,由其专职负责处理儿童虐待和忽视问题。任何组织和个人(如邻居、老师、社区工作者、警察等)一旦发现儿童有被忽视的危害,必须即行报告(强制报告制度)。为了鼓励组织和个人行使对儿童忽视问题的报告职责,需要制定和完善各项配套措施以保障报告人的权益,如允许匿名报告,对报告人的身份严格保密;对于善意误报者,应豁免其相应的法律责任。[29]
儿童权益保护机构应制定一套具体而详尽的标准来决定是否对儿童忽视报告进行调查。这些方案应明确这些疑似“儿童忽视”报告是否符合国家法定定义。要考虑的因素包括:(1)儿童的年龄;(2)监护者的身份和与孩子的关系;(3)疑似存在的符合国家法定的儿童忽视和虐待的事件或情况;(4)存在明显的伤害或损害孩子的风险。[30]
在接受儿童忽视报告后,儿童权益保护机构需要制定具体的准则,决定什么样的干预是必要的,以及是否提起强制干预。在判定儿童忽视的危险程度和确定性证据上,下列因素至关重要:(1)父母或监护者的行为和不作为;(2)父母或照顾者的行为对孩子的影响以及涉嫌虐待的严重程度;(3)孩子的年龄;(4)涉嫌忽视的频率;(5)报告者的可信性;(6)证据的类型和数量;(7)涉嫌忽视的人与孩子的关系;(8)父母或监护者保护孩子的意愿;(9)父母或监护者保护孩子的能力。
儿童权益保护机构需要经过多学科的咨询来做出决定。咨询可以非正式地完成或通过更为正式的机制——由不同领域专家组成的“多学科小组”来进行。经过专家和多方评议后,使儿童权益保护机构的决策变得更具针对性、更具有成效。
(三)加强对公众有关儿童忽视的专题教育
我国社会公众和学者对儿童忽视问题的关注时间并不长。对于公众和社会如何负责任地在预防和制止儿童忽视中发挥应有作用方面的宣传还是一片空白。我国公众和家长一般还缺乏对于父母权责的理解和认识,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父母,如何履行父母亲权,如何避免对儿童的忽视问题等等,都是公众需要补修的知识。提高公众对儿童忽视的认识和意识,需要对公众进行儿童忽视问题的普及教育。
对公众实施儿童忽视专题教育,教育材料和方案应包括以下内容:(1)明确忽视儿童的法律定义;(2)给出所报告儿童忽视情况(包括具体的例子)一般性描述;(3)说明报告会发生什么事情。[31]对公众教育的小册子和其他材料,包括公共服务通告,对什么该报告、什么不该报告应该给出具体信息。此外,公众儿童忽视教育还应让公众了解可用于防范和解决儿童虐待或忽视问题的社区支持资源。
(四)加强对儿童忽视问题处置的社会支持
防范和处置儿童忽视问题需要社会各界支持体系的综合干预。首先,儿童权益保护专业人员应与儿童虐待、忽视家庭的成员及其朋友、邻居、工作同伴进行直接的接触,获取真实全面的信息,提供恰当的有针对性的指导和训练,化解冲突,促进交流。其次,儿童权益保护专业人员对儿童忽视问题调查后,可以为儿童忽视家庭、父母(监护人)和儿童提供服务,包括法律咨询、家庭服务和支持以及被忽视儿童的寄养服务等。再次,培训志愿者,内容包括如何识别和帮助被虐待、忽视的儿童,如何教给孩子们自我保护的方法以及给父母、监护人以指导,使志愿者成为联络忽视家庭和干预组织的中间环节等。效仿美国等西方国家,在幼儿园和中小学阶段就教给儿童识别属于虐待和忽视的种种行为,教育孩子面对虐待和忽视的行为如何求助于社区和社会机构来保护自己等等。这些教育能增强儿童面对危害的自我保护意识,从而有效降低儿童虐待和忽视对儿童的伤害。[30]第四,将社区服务作为国家和社会干预手段的一部分,把家庭的具体需要(如食物、住房、医疗服务、教育和法律帮助等)与社区服务相结合;也可以让邻居、社区成员参与到给忽视家庭提供家庭管理指导、抚育孩子的知识和技能、儿童照管的工作中来。第五,动员全社会力量参与到儿童忽视保护的工作中来,创造一个有利于干预性计划交流和实施的环境。[29]
[1]潘建平.儿童忽视的分类和表现以及预防工作进展[J].中国全科医学,2007,(3).
[2]Schumacher,J,Slep,A.M.&Heyman,Richard.Risk Factors for Child Neglect[J].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2001,(6).
[3]Asya Al-Lamky.Modernization and Child Neglect in Oman:Trends and Implications[J].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World Peace,2004,(21).
[4]潘建平.不能忽视对儿童的忽视[J].中国全科医学,2007,(10).
[5]李媛.儿童虐待防治体系的比较研究[D].首都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3.
[6]Lela B.Costin.Child Welfare:Politics and Practices[M].New York:McGraw-Hill,1972.
[7]潘建平,杨子尼,任旭红,等.中国部分城市3—6岁儿童忽视状况及影响因素分析[J].中华流行病学杂志,2005,(4).
[8]潘建平,李玉凤,马西,韩春玲,等.陕西省3—6岁城区儿童忽视状况的调查分析[J].中国全科医学,2005,(5).
[9]杨文娟,潘建平,杨武悦,王维清,马乐.中国农村留守与非留守儿童忽视现状分析[J].中国学校卫生,2014,(2).
[10]甘绍光.人权伦理学[M].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
[11]孙艳艳.儿童与权利:理论建构与反思[D].山东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
[12]覃明.儿童忽视问题的教育人类学分析[J].教育导刊,2010,(9).
[13]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EB/OL].http://jtjy.china.com.cn/2008-12/23/content_2644648.htm.
[14]王雪梅.儿童权利保护的“最大利益原则”研究(下)[J].环球法律评论,2003,(春季号).
[15]雷文玫.以“子女最佳利益”之名:离婚后父母对未成年子女权利义务行使与负担之研究[A].台大法学论丛[C].台北:台湾大学出版社,2014.
[16]Simpson.Judicial Considerations in Child Care Cases[M].NY:WAYNEL,1965.
[17]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The Custody Question and Child Neglect Rehearings[J].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1968,(35).
[18]郑净方.国家亲权的理论基础及立法体现[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4,(3).
[19]Ramsey,Sarah H.&Abrams,Douglas E..Children and the Law:In a NutshellM].St.Paul,Minnesota:Thomson/West,2008.
[20]Olsen,Frances E.The Myth of State Intervention in the Family[J].Journal of Law Reform,1985,(1).
[21]马忆南.父母与未成年子女的法律关系——从父母权利本位到子女权利本位[J].民商法杂志,2009,(25).
[22]Judith Masson.The State as Parent:The Reluctant Parent?The Problems of Parents of Last Resort[J].Journal of Law and Society,2008,(35).
[23]范斌.福利社会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
[24]Monrad G.Paulsen.Legal Protections Against Child Abuse[J].Children,1966,(13).
[25]黄晓燕,徐韬,刘文利,潘建平,等.中国儿童虐待防治法律法规与政策规定现状分析[J].中国妇幼卫生杂志,2015,(6).
[26][美]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M].吴燕莛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27]Onora O’Neill.Children’s Rights and Children’s Lives[J].Ethics,1998,(98).
[28]钱晓峰.儿童虐待国家干预机制的构建[J].预防青少年犯罪研究,2014,(6).
[29]李环.建立儿童虐待的预防和干预机制[J].青年研究,2007,(4).
[30]Douglas J.Besharov.Child Abuse and Neglect Reporting and Investigation:Policy Guidelines for Decision Making[J].Family Law Quarterly,1988,(22).
[31]Gaudin JM,Wodarski JS,Arkinson MK.Remedying Child Neglect:Effectiveness of Social Network Interventions[J].The Journal of Applied Social Sciences,1991,(15).
责任编辑:秦 飞
Exploration on Protective Principles and Strategy for Child Neglect
LI Jun
“Child neglect”is a kind of injure to children.Measures protecting children from neglect must followthe best interests of the child and occasionally may require children to be taken away from improper guardians.The protection of children’s right against neglect should be enforced through the four avenues of criminal justice,juvenile courts,mandatory reporting,and protective services.In the first phase of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is strategy,the country will make efforts to strengthen policy of law concerning child neglect by increasing reports through policies requiringmandatoryreportingand surveillance,and increasing public awareness through education campaigns to gain recognition and support fromgreater society.
child neglect;protective principle;protective mechanism
10.13277/j.cnki.jcwu.2016.01.015
2015-12-30
C913.5
A
1007-3698(2016)01-0107-06
李军,男,民政部社工研究中心副教授,香港城市大学公共及社会行政学系哲学博士,中国政治研究学会(美国)会员,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政策、社会福利、民政政策等。100010
——从虐童事例切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