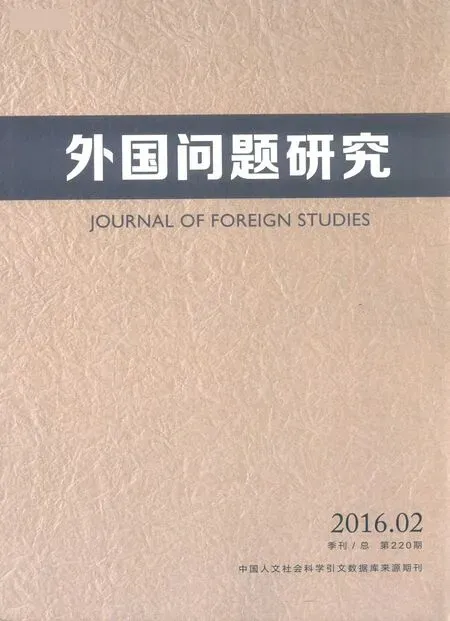论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
郭 丹 彤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论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
郭 丹 彤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吉林 长春 130024)
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是目前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从现有的埃及文献以及出土于迦南和埃及两地的考古资料看,尽管奈苏蒙图石碑、索白克胡石碑和孟菲斯铭文记录了埃及在迦南的军事行动,但是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仍集中表现在贸易上。第十二王朝早期,两地的关系是通过不同路径的双边互动:黎凡特与埃及的联系是通过陆路来完成的,位于拜尼·哈桑的第3号坟墓中的壁画和来自于塞拉比特·艾尔·哈戴德采石场的铭文可以证明这一点;与此同时,出土于伊弗沙的陶器则反映了埃及与黎凡特南部的海上联系;孟菲斯铭文以及出土于达舒尔的克努霍特普坟墓铭文揭示出黎凡特北部地区更趋向于与埃及进行海上贸易。第十二王朝末期和第十三王朝时期,埃及与黎凡特南部的贸易通过出土于阿什克龙的印章和陶器得到了充分的揭示,而克努霍特普的达舒尔铭文则揭示了埃及与古王国时期的传统贸易伙伴巴比罗斯的联系,乃经过埃及第一中间期和第十二王朝早期的中断后,并于这一时期重新开启。
古代埃及;中王国时期;迦南;贸易
任何文明的发展都不是孤立的,都与其周边文明发生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古代埃及亦如此,在古代埃及文明发展演进中,埃及与其周边国家或地区始终保持着密切的交往,而迦南则是其主要交往对象之一。迦南,即黎凡特地区,迦南是古代埃及语称谓。在古代,迦南包括乌加里特、叙利亚南部地区、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地区、西奈半岛北部地区和塞浦路斯岛。*郭丹彤:《埃及与东地中海世界的交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10页。由此,埃及与迦南的交往实质上就是古代近东地区各国各地区间的交往。近东地区,虽然面积不大,但是由于各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领土纠纷和错综复杂的宗教问题,使得这一地区长期以来成为国际关系的焦点。因此,研究古代埃及与迦南的关系将有助于人们加深对当今近东政治格局形成的历史认识。
由于迦南经西奈半岛与埃及接壤,并且两地都位于地中海沿岸,因此,早在公元前4000年代,埃及就与迦南开始了或陆路或海路的贸易往来。*郭丹彤:《史前时期埃及与巴勒斯坦的关系》,《史学集刊》 2002年第4期,第58—62页。古王国时期(包括第三—八王朝,约公元前2686年—前2125年),正是迦南地区的青铜早期文化时期,此时的迦南地区城市文明蓬勃兴起,出现了诸如巴比罗斯等著名的港口城市,它们也便成为埃及在迦南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古王国结束后埃及进入政权分裂的第一中间期,而在迦南,青铜早期文化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两地的交往随之中断。中王国时期(包括第十一、十二和十三王朝,约公元前2055—前1650年),两地的交往再度开启。
囿于过往中王国时期两地关系的相关考古资料没有一个相对明确的年代勘定以及文献资料的相对欠缺,较之于以贸易为主导的古王国时期的两地关系以及埃及对迦南进行殖民化统治的新王国时期的两地关系而言,居于古王国和新王国之间的中王国时期的两地关系始终是学界最具争议的一个议题,而在这一时期迦南地区年代学的重建和社会性质的勘定上存在的难题进一步将这一问题复杂化。上一个世纪二十年代以来,埃及学者、近东学者以及圣经学者都曾对这一课题进行过讨论,总括起来,有这么几种观点: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表现在贸易和外交上,而战争,绝无仅有;*A.Gardiner,Egypt of the Pharaoh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J.M.Weinstein,“Egyptian Relations with Palestine in the Middle Kingdom”, BASOR 217 (1975),pp.1-16.埃及通过军事征服成为迦南的宗主国;*W.F.Albright,“Presidential Address: Palestine in the Earliest Historical Period”, JPOS 15 (1935),pp.193-234;W.F.Albright,“The Chronology of Middle Bronze I (Early Bronze-Middle Bronze)”, BASOR 168 (1962),pp.36-42;B.Mazar,The Middle Bronze Age in Palestine,IEJ 18(1968),pp.65-77;R.Giveon,The Impact of Egypt on Canaan Iconographical and Related Studies,OBO 20,Freiburg and Goe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it,1978.埃及确有武力征服,但却并没有实现政治控制;*G.Posener,“Syria and Palestine c.2160-1780 B.C.: Relations with Egypt”, CAH,3rd,vol.1,pt.2,pp.532-538;D.B.Redford,Egypt,Canaan,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p.80.与这一时期埃及对努比亚的系统有效的殖民化统治相比,埃及对迦南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政策。*S.L.Cohen,Canaanites Chronologies and Connections: The Relationship of Middle Bronze IIA Canaan to Middle Kingdom Egypt,Eisenbrauns: Winona Lake,2002,pp.137-139.最近,有学者将“港口势力模式”运用到对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关系的勘定上,这一观点着力于两地的海上贸易往来。*所谓“港口势力模式”是指埃及与迦南的联系以商业贸易为主,并以海路为主要贸易路线。由此,沿海的港口城市就成了埃及的主要贸易伙伴。参见L.E.Stager,“Port Power: the Organization of Maritime Trade and Hinterland Production”, in Studies in the Archaeology of Israel and Neighboring Lands: in Memory of Douglas L Esse,ed.S.R.Wolff,Chicago: Oriental Institute Press,2001.此外,经济学上的中心-边缘理论也被应用到埃及的对外关系上,并由此认为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与迦南的关系是中心国家与边缘地区的关系。*所谓“中心-边缘”理论由西方学者提出,用于表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关系的国际关系理论。将这一理论应用到古代世界国家或地区间的交往就是强盛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认为他们是世界的中心,而周边地区则是蛮荒之地,是为它们提供劳动力和纯原料的。于是,在处理与其周边地区关系时,他们往往从中心与边缘对立、边缘为中心服务的视角看待和处理问题。参见郭丹彤:《埃及与东地中海世界的交往》,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第20页。凡此种种,各执一词,莫衷一是。然而近年来的考古和文献资料的新发现,却使我们重构这一时期的两地关系成为可能。为此,本文拟使用这些新材料对这一论题进行探讨,以期较为真实地梳理出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关系的基本脉络。
在讨论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之前,首先要对青铜中期文化时期的迦南社会性质进行勘定。并且,任何埃及与迦南关系的讨论都必须建立在迦南地区青铜中期文化年代学构建的基础上。
一、两地年代学上的对应
大体说来,埃及中王国时期与迦南青铜中期文化时期基本上处于同一个时间维度中。然而,在迦南青铜中期文化年代学的构建上却存在着诸多难题,并首先表现在这一时期各分期的称谓勘定上。根据来自戴尔·贝特·米尔斯姆(Tell Beit Mirsim)的考古资料,奥布瑞特(Albright)将居于青铜早期文化与中期文化之间的文化称为青铜早期文化四期,即EBIV,后来又改称为青铜中期文化一期,即MBI。前一个术语揭示出这一时期继承了青铜早期文化的城市文化特征,*W.F.Albright,The Excavation of Tell Beit Mirsim 1A: The Bronze Age Pottery of the Fourth Campaign,AASOR 13,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33;W.F.Albright,The Excavation of Tell Beit Mirsim Vl.II: The Bronze Age,AASOR 17,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38.后一个术语则揭示了这一时期开启了青铜中期文化的新阶段。*P.Gerstenblith,“A Reassessment of the Beginning of the Middle Bronze Age in Syria-Palestine”, BASOR 237 (1980),p.2.如果这一过渡时期被命名为青铜早期文化四期(EBIV),那么,青铜中期文化便可以分为青铜中期文化一期、二期和三期,即MB Ⅰ、MB Ⅱ、和MB Ⅲ;*W.G.Dever,“New Vistas on the EB IV (“MB I”) Horizon in Syria-Palestine”, BASOR 237 (1980),pp.36,38-39,48-49.如果这一过渡时期被命名为青铜中期文化一期,那么,青铜中期文化就可以分为青铜中期文化二期A、二期B和二期C,即 MB IIA、MB IIB和MB IIC。与此同时,将青铜早期文化四期和青铜中期文化一期合并,即青铜早期文化四期/青铜中期文化一期,也颇为流行,这一称谓揭示了这一中间过渡阶段与青铜早期文化和青铜中期文化都有着密切的联系,而青铜中期文化也便相应地被划分两个阶段,即青铜中期文化二期A和青铜中期文化二期B/C,即MBIIA和MB IIB/C。*S.L.Cohen,Canaanites Chronologies and Connections: The Relationship of Middle Bronze IIA Canaan to Middle Kingdom Egypt,Eisenbrauns: Winona Lake,2002,p.11.
然而,这一过渡时期也可以被勘定为一个独立的阶段,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一时期在物质文化上与青铜早期文化没有必然的联系,同时它似乎与青铜中期文化也没有什么内在的关联。于是,青铜中间期文化时期,被用来指代青铜早期文化与中期文化的过渡期。如此,青铜中期文化,作为一个重新城市化的时期便被分成两个或三个阶段,即青铜中期文化一期和二期,即MB I和MBII,*D.M.Bonacossi,“The Northern Levant (Syria) during the Middle Bronze Age”, in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evant c.8000-332BCE,ed.by M.L.Steiner and A E.Killebre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414-433;H.Charaf,“The Northern Levant (Lebanon) during the Middle Bronze Age”, in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evant c.8000-332BCE,ed.by M.L.Steiner and A E.Killebre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434-450;S.L.Cohen,“The Southern Levant (CisJordan) during the Middle Bronze Age”, in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evant c.8000-332BCE,ed.by M.L.Steiner and A E.Killebre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451-464.或者青铜中期文化一期、二期和三期,即MBI、MBII和MBIII。*S.J.Bourke,“The Southern Levant (Transjordan) during the Middle Bronze Age”, in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evant c.8000-332BCE,ed.by M.L.Steiner and A E.Killebre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465-481.
关于青铜中期文化开始的日期及其阶段是关于青铜中期文化年代学的第二个争论。奥布瑞特坚持一个低年代表,即青铜中期文化一期的时间断限大约为公元前1800年—前1750/1700年;*W.F.Albright,“The Eighteenth Century Princes of Byblos and the Chronology of the Middle Bronze Age”, BASOR 176 (1964),p.41;W.F.Albright,“The Historical Framework of Palestinian Archaeology between 2100 and 1600(E.B.IV,M.B.I,M.B.IIA-B)”, BASOR 209 (1973),p.17.毕塔克(Bietak)则认为青铜中期文化一期应该从埃及的第十二王朝中期到第十三王朝时期,大约为公元前1750年—前1680年。*M.Bietak,“Problems of MBA Chronology: New Evidence from Egypt”,AJA 88 (1984),pp.471-85;M.Bietak,“Canaan and Egypt during the Middle Bronze Age”, BASOR 281 (1991),pp.27-72;D.Ben-Tor,“The Historical Implications of Middle Kingdom Scarabs Found in Palestine Bearing Private Names and Titles of Officials”, BASOR 294 (1994),pp.7-22;D.Ben-Tor,“The relations between Egypt and Palestine in the Middle Kingdom as Reflected by Contemporary Canaanite Scarabs”, IEJ 47 (1997),pp.162-189.与此相反,另一些学者则坚持较高的年代表。莫匝(Mazar)将这一时期的时间断限勘定为公元前2000/1950年—前1800年;*B.Mazar,“The Middle Bronze Age in Palestine”, IEJ 18(1968),pp.65-97;A.Mazar,Archaeology of the Land of the Bible,10,000-586B.C.E.,New York: Doubleday,1990.靠恩(Cohen)则给出了一个相对较低的日期:公元前1950/1925年—前1730 年,*S.L.Cohen,Canaanites Chronologies and Connections: The Relationship of Middle Bronze IIA Canaan to Middle Kingdom Egypt,Eisenbrauns: Winona Lake,2002,pp.11-14;S.L.Cohen,“The Southern Levant (CisJordan) during the Middle Bronze Age”, in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evant c.8000-332BCE,ed.by M.L.Steiner and A E.Killebre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451.M.Bietak,Relative and Absolute Chronology of the Middle Bronze Age: Comments on the Present State of Research”, in The Middle Bronze Age in the Levant: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BIIA Ceramic Materials,Vienna,24th-26th of January 2001,ed.by M.Bietak,Wien: Verlag Der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2002,p.41.而开尼恩(Kenyon)将这一时期开始的时间勘定为公元前1900年。*K.M.Kenyon,Amorites and Canaanites,the Schweich Lectures of the British Academy,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35.
由于学界在青铜中期文化年代学上的勘定难以达成共识,本文将结合上述勘定,同时参照《牛津黎凡特考古手册》*A.A.Burke,“Introduction to the Levant during the Middle Bronze Ag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evant c.8000-332BCE,ed.by M.L.Steiner and A E.Killebre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pp.403-413.,对这一时期年代学进行如下勘定,即青铜中期文化开始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900年,从青铜中期文化一期到二期过渡的时间大约为公元前1700年。如此,青铜中期文化一期的时间断限大约为公元前1900年—前1700年,青铜中期文化二期的时间断限大约为公元前1700年—前1600年,青铜中期文化三期的时间断限大约为公元前1600年—前1530年。
关于埃及中王国时期的年代学,即从第十一王朝中期开始直至第十三王朝结束,也存在着高和低两个年代表的分野,这是因为两个年代表所使用的发生在第十二王朝国王森沃斯瑞特三世统治第七年天狼星观测数据来自不同的观测地点。*R.A.Parker,The Calendars of Ancient Egypt,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0;R.A.Parker,“The Sothic Dating of the Tewlfth and Eighteenth Dynasties”, in Studies in Honor of George R.Hughes,SAOC39,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76,pp.180-182;R.A.Parker,in The Legacy of Egypt,ed.by J.R.Harris,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R.Krauss,Sothis und Monddaten,HB 20,Hildesheim: Gerstenberg,1985,pp.136-163.克如斯(Krauss)认为其中的一个观测点应该在埃及南部城市埃利芬提尼(Elephentine),由此,森沃斯瑞特统治的第七年便是公元前1831年。将森沃斯瑞特二世的统治年数从19年缩短到6年,并将森沃斯瑞特三世的统治年数勘定为19年,克如斯为第十二王朝勘定了一个低年代表:公元前1937年—前1759年。*R.Krauss,Sothis und Monddaten,HB 20,Hildesheim: Gerstenberg,1985,p.207;J.Von Beckerath,“Bemerkungen Zum Turiner Konigspapyrus und zu den Dynstien der agyptischen Geschichte”, SAK 11 (1984),pp.49-57.然而观测点在底比斯的观点被学界普遍接受,于是,森沃斯瑞特三世统治的第七年便可勘定为公元前1872 年,一个高年代表便可得出:公元前1963年—前1786年。*K.A.Kitchen,“The basics of Egyptian Chronology in Relation to the Bronze Age”, in High,Middle,or Low? ed.by P.Aström,Gothenburg: Paul Aström,1987,p.43.目前,第十二王朝的一个跨度较短的高年代表被学界普遍认同,为此,本文将中王国时期的年代表勘定为公元前2055年—前1650年,其中第十一王朝的时间断限为公元前2055年—前1985年;第十二王朝的时间断限为公元前1985年—前1773年;第十三王朝的时间断限为公元前1773年—前1650年。*I.Shaw,ed.,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483.
如是,迦南地区的青铜中期一期文化与埃及的第十二王朝和第十三王朝的前期同处一个时期;而继承和发展了青铜中期一期文化的二期文化则与第十三王朝的后期相对应。青铜三期文化与第十五王朝处于同一个时期。*A.A.Burke,“Introduction to the Levant during the Middle Bronze Ag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Archaeology of the Levant c.8000-332BCE,ed.by M.L.Steiner and A E.Killebrew,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p.410.
通常,埃及的中王国时期与迦南的青铜中期一期文化(约公元前1900年—前1700年)和二期文化 (约公元前1700年—前1600年)相对应,而三期文化,由于与埃及的第十五王朝相对应,遂被剔除在本文所要研究的范畴之外。
二、埃及文献中的迦南社会经济状况
青铜早期文化时期迦南的城市文明已经得到学界的普遍认同,然而其后的青铜中期文化一期的迦南是继续了其早期的城市文明?还是被游牧民族统治着?对这一问题的回答直接影响着我们对迦南与埃及交往模式的构建。如果迦南是一个游牧社会,它又如何与文明程度甚高的埃及进行诸如贸易的正常交往?而两地正常贸易的存在与否又可对迦南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反证。由此,在探讨埃及与迦南关系之前对迦南社会经济状况进行勘定是必不可少的。由于迦南地区大多数考古遗址中的青铜中期考古层因为青铜后期的重新使用而使学者们不能对其进行准确勘定,故此,我们无法利用它们重建这一时期的迦南社会。然而,埃及语文献却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这样的埃及语文献首推《辛努西的故事》。
辛努西是第十二王朝时期服务于后宫的官吏。当他听闻埃及发生宫廷政变时,他正追随森沃斯瑞特一世(Senwosret I,约公元前1956年—前1911年)在三角洲西部地区与利比亚人作战。在这场宫廷政变中,森沃斯瑞特一世的父亲第十二王朝的第一位国王阿蒙奈姆海特一世(Amenemhet I,约公元前1976年—前1947年)被杀。很可能辛努西曾参与过这场宫廷政变的密谋,当他听到国王被杀的消息后便仓皇出逃。他穿越位于三角洲东北部的“统治者之墙”(“Walls of the Ruler”),前往巴比罗斯(Byblos),接着前往凯戴姆(Qedem),最后到达上瑞特努(Retjenu)。上瑞特努统治者将女儿许配给他,并赠予他一块叫做亚阿(Yaa)的领地。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当暮年来临之时,他的思乡之情油然而生。他要落叶归根,将尸骨埋葬在故乡的土地上。于是他便向当时的埃及国王森沃斯瑞特一世表达了他的心愿,国王应允了他的请求,邀请他返乡,并赐予他一块墓地。*关于这篇故事的译文,参见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下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80—898页。“统治者之墙”,军事防御工事名称。第十二王朝时期,为了防御亚洲人的入侵,埃及在三角洲东部边境地区修筑的军事防御工事;巴比罗斯,地名,古代腓尼基人的一个港口城市,位于近黎巴嫩境内,曾是地中海地区重要的港口城市,以其发达的造船技术与繁荣的海上贸易著称于古代地中海世界;凯戴姆,地名,根据这篇文献的记述,应该在黎巴嫩东部山区;上瑞特努,地名,即为现今的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

与此观点相反,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这个故事不足以证明这一时期迦南人的生活方式是游牧,因为游牧人口不可能种植葡萄、无花果和橄榄,他们也没有能力放牧大型牲畜。这篇故事所反映的瑞特努的人口不仅是定居的,而且一些小的城邦之间还不时地发生着战争。*G.W.Ahlström,The History of Ancient Palestine from the Palaeolithic Period to Alexander’s Conquest.Sheffield: JSOT,1993,p.169.因此,故事中青铜中期文化一期的迦南社会体系无疑是城邦制。瑞特努由一位君主统治,辛努西的领地遍布黎凡特的各种农作物,居于其边界的游牧民族不时侵扰着这个组织机构严密的国家。辛努西是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的长官,他曾领导了与其邻邦的战争。辛努西与瑞特努大力士之间的决斗是组织严密的社会生活的反映,这个社会绝非是游牧的。对王室帐篷和国王活动的描述与第十八王朝国王图特摩斯三世年鉴的描述别无二致,而第十八王朝统治时期的迦南,毫无疑问,正处于城市文明高度发达的青铜后期文化时期。事实上,《辛努西的故事》的作者是为了强化他的主人公在瑞特努的成就以及当时埃及在地中海世界的霸权,而故意不谈迦南地区的城市、王宫和神庙。*A.F.Rainey,“The World of Sinuhe”, IOS 2 (1972),pp.370-408;A.F.Rainey,“Remarks on Donald Redford’s Egypt,Canaan,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 BASOR 295 (1994),pp.81-85.
由于《辛努西的故事》是一部文学作品,因此在使用它重构历史事件时,学者们对其不同的理解必然导致不同的甚至相左的历史叙述,并且文学作品自身的可信度也无法与历史文献相提并论。为此,我们将通过诅咒铭文对当时迦南的社会经济状况进行更接近于历史真实的还原。
诅咒铭文即为通过仪式摧毁敌人的咒语文献。通常,人们把敌对国家和种族的名字写在陶罐和小雕像上,并在仪式上由诵读者在将其上刻写的敌对国的名字以及咒语诵读出来后粉碎或烧毁。由此,当埃及的武力无法直接消灭那些潜在的敌人时,这些敌人不仅是外国人也有那些图谋反叛的埃及人,通过魔法消灭他们无疑使埃及人在精神上得到了慰藉。诅咒针对的是人,不是国家或地区,所以文献中的地名仅仅是为了勘定埃及人所要诅咒的对象。诅咒铭文最早出现于古王国时期,中王国时期的诅咒文献主要有三批,它们都是由多篇零散的文献组成。
第一批文献因发现于努比亚的米尔吉萨而被称之为米尔吉萨诅咒铭文,这批文献共计175块碎片和3座小雕像,时间断限大约为公元前1900年—前1850年。*这批文献由坡塞纳(Posener)于1966年出版。参见G.Posener,“Les texts d’envoutement de Mirgissa”, Syria 43 (1966),pp.277-287。米尔吉萨(Mirgissa)要塞兴建于阿蒙奈姆海特二世或森沃斯瑞特二世统治时期,重建于森沃斯瑞特三世统治时期。如此,这批文献的时间不能早于公元前19世纪前半叶,大致在森沃斯瑞特三世统治早期。参见Ld 4 (1982),pp.144-145。与辛努西的故事描述的情形相似,这批文献反映了迦南青铜早期文化四期的末期和青铜中期文化一期的早期时期的迦南地区,一个从城市文化到游牧文化的过渡期。第二批文献发现于底比斯,因现存于柏林博物馆而被称之为柏林诅咒铭文,这批文献现存289块残片,时间大约在森沃斯瑞特三世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870年—前1831年)或阿蒙奈姆海特三世统治的早期(约公元前1831年—前1786年)。*这批文献由塞斯(Sethe)发表于1926年。参见K.Sethe,Die chtung feindlicher fürsten,Völker und Dinge auf altägyptischen Tongefasscherben des Mittleren Reiches,Berlin: Abhandlungen der preuss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Phil.-Hist.Klasse,No.5,1926。关于这批文献的日期,参见T.L Thompson,The Historicity of the Patriarchal Narratives,Berlin: Walter de Gruyter,1974,pp.98-113.第三批文献来自萨卡拉,因现存于布鲁塞尔而被称之为布鲁塞尔诅咒铭文,这批文献由小雕像组成,时间大约为公元前十八世纪前半叶。*这批文献由坡塞纳发表于1940年。参见G.Posener,Princes et pays d’Asie et de Nubie,Brussels: Fondation Egyptologique Rrine Élisabeth,1940.
根据柏林文献,我们可以得到诅咒文献的基本书写样式:一、统治者的名字列表,每个统治者都标注了他的统治区域,即“某某地的统治者某某某,以及与他在一起的所有追随者”;二、一个总结性的句子:“某某地的所有亚洲人,一个地名列表”;三、第二个总结性句子列举了所要诅咒的对象:“他们的人、他们的追随者、他们的同盟者、他们的支持者【……】”,并伴有修饰性句子:“【……】意欲反叛的,意欲谋划的,意欲战斗的,意欲谈及战斗的【……】”。*这里引证的诅咒文献相关译文皆为作者自译。
米尔吉萨诅咒铭文和柏林诅咒铭文要比布鲁塞尔诅咒铭文早二十年或四十年,在地名数量和排列以及人名和地名之间的关系上前两批与后一批有所不同:首先,从米尔吉萨-柏林文献到布鲁塞尔文献地名的数量呈递增趋势;第二,在前两批诅咒文献中,一个地名有两位或三位统治者,可是在布鲁塞尔文献中则是一个地名一个统治者;第三,在前两个诅咒文献中地名并没有按照地理方位进行排序,而在布鲁塞尔文献中所有的地名都是按照地理方位排序的。
由此,米尔吉萨-柏林文献与布鲁塞尔文献之间的差异反映了迦南地区社会经济组织的变化。前两批文献中出现的地名多为地区,而非城镇,例如“西阿帕海岸/地区”。在这两批文献中,迦南是一个农业社会,城镇数量不仅少而且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微小;两位或三位统治者统治着一个地域是部落制度的基本表现。而在布鲁塞尔文献里,被列举出来的地域往往都是城镇,并按照地理方位排序。布鲁塞尔文献所记录的地理范围与前两个文献的记录大体相同,但是布鲁塞尔文献中的迦南地区的居民却是定居的,而一个地域一个统治者则反映了城市化的政权组织形式。
上文提到的诅咒文献书写版本中我们所开列的第二个总结性句子记录了各种名衔。这些名衔揭示了一个小的不成熟的社会组织机构。在前两批文献中,一个“强有力的人”或者一个“武士”这样的称谓揭示了一种部落组织的存在,而在布鲁塞尔文献中,“市民”和“收获者”这样的称谓则反映了一种定居的农业经济形式。
由此可知,青铜中期文化一期的早期,也即埃及的第十二王朝前半期,迦南地区社会经济以游牧为主,到青铜中期文化一期的中后期,也即埃及的第十二王朝后半期和第十三王朝的早期,迦南的社会经济开始过渡到以定居为主的城市文明阶段,城市重新兴起。迦南与包括埃及在内的周边国家或地区的交往日益密切,对外贸易繁荣。另一方面,迦南与埃及等周边国家或地区的密切交往也进一步加速了迦南地区城市化进程。
三、考古资料中的两地关系
迦南社会城市文明重新兴起后便开始了与埃及的交往,并被充分地反映在考古和文献资料中。先就考古资料而言,发现于迦南的雕像和护身符是我们构建埃及与迦南关系的首选考古资料,这些文物都带有第十二王朝和第十三王朝国王名字,其中较有佐证价值的是发现于米吉都*考古遗址名,位于巴勒斯坦地区,现今在以色列境内。的图特霍特普雕像。现存雕像残缺,大约24厘米高,17厘米长,13.5厘米宽,黑色闪长岩质地。图特霍特普呈坐姿。其基座的左侧有四列铭文,右侧又有四列铭文,雕像背部中轴线上有一列铭文。图特霍特普是野兔州州长和赫尔摩坡利斯城托特神庙的高级祭司,他的坟墓铭文告诉我们,他阿蒙奈姆海特二世统治时期的王宫中长大,直到森沃斯瑞特二世统治时期他仍活跃在埃及的政治舞台。*J.A.Wilson,“The Egyptian Middle Kingdom at Megiddo”, AJSL 63 (1941),pp.225-236;G.W.Ahlström,The History of Ancient Palestine from the Palaeolithic Period to Alexander’s Conquest,Sheffield: JSOT,1993,p.166,n.1,2;Y.Yadin,“Megiddo”, in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Holy Land,vol.III.ed.by M.Avi-Yonah and E.Stern,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1977,pp.830-856.这位埃及政府官员的雕像出土于米吉都表明他生活于此。有证据显示,图特霍特普是森沃特瑞斯三世政治改革的幸存者。在这场波及全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许多旧有的政府高级官员被剥夺了权利,甚至招致杀身之祸。*I.Shaw,ed.,Oxford History of Ancient Egypt,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p.167.据此,图特霍特普出现在米吉都不是以埃及政府官员的身份,事实上,他是一名政治逃亡者。他为自己建造雕像表达了他对故土的思念之情。正如辛努西,他也在迦南获得了很高的社会地位。*W.A.Ward,“Egypt and the East Mediterranean in the Early second Millennium B.C”, Or.NS 30 (1961),pp.38-44.
大量的带有国王和官员名字的埃及护身符出土于迦南地区,但是由于它们的功用和日期至今无法勘定而不足以作为阐释两地关系的直接证据。最近,出土于阿什克龙的47枚护身符和陶器的功能和日期得到了勘定,这批文物的制作日期在阿蒙奈姆海特三世(约公元前1831年—前1786年)统治结束之后。*L.E.Stager,“The MB IIA Ceramic Sequence at Tel Ashkel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Port power’ Model of Trade”, in The Middle Bronze Age in the Levant: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BIIA Ceramic Materials,Vienna,24th-26th of January 2001,ed.by M.Bietak,Wien: Verlag Der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2002,pp.353-362;I.E.Stager,“Tel Ashkelon”,in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Holy Land 5 (2008) (Supplementary volume),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2008,1578-1586.目前,只有几枚护身符发表,*O.Keel,Corpus der Stempelsiegel-Amulette aus Palästina/Israel,OBO 13,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1997,pp.714-715,no.68;L.E.Stager,“The MB IIA Ceramic Sequence at Tel Ashkelon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the ‘Port power’ Model of Trade”, in The Middle Bronze Age in the Levant: Proceedings of an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MBIIA Ceramic Materials,Vienna,24th-26th of January 2001,ed.by M.Bietak,Wien: Verlag Der Osterreichischen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2002,pp.353-362,fig.2;I.E.Stager,“Tel Ashkelon”, in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Holy Land 5 (2008) (Supplementary volume),Jerusalem: Israel Exploration Society,2008,1578,1581.它们是我们构建迦南青铜中期文化和埃及中王国年代学上的对应的重要证据。
一只保存完好的出土于伊弗沙(Ifshar)*考古遗址名,位于巴勒斯坦地区,现今在以色列境内。的埃及陶罐有准确的时间勘定,它制作于公元前十九世纪前半叶,与阿蒙奈姆海特二世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911年—前1877年),森沃斯瑞特二世(约公元前1877年—1870年)和三世(约公元前1870年—前1831年)统治时期处于同一个时期。*S.M.Paley and Y.Porath,“Hefer,Tel”, in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Holy Land,ed.by E.Stern,Jerusalem: The Israel Exploration Soceity & Carta,1993,pp.609-614.此外,在伊弗沙还出土了一大批产自埃及北部孟菲斯地区的陶器,另外一些则产自埃及南部地区。*E.S.Marcus,Y.Porath,R.Schiestl,A.Seiler and S.M.Paley,The Middle Kingdom Egyptian Pottery from Middle Bronze Age IIA Tell Ifshar”, in Egypt and the Levant, XVIII (2008),ed.by M.Bietak,p.205.出土于伊弗沙的陶器揭示了青铜中期文化一期时期埃及与黎凡特南部的海上贸易。
另一方面,发现于埃及的考古文物也有助于我们重构埃及与迦南的关系,并以位于拜尼·哈桑*地名,位于埃及中部地区。的克努姆霍特普二世的3号坟墓壁画为主要代表。克努姆霍特普二世是森沃斯瑞特二世统治时期的“东部沙漠总管”。壁画的解说词记述了一支由37名亚洲人组成的商队前往埃及,但是壁画只展示了其中的15人,他们由王室书吏奈菲尔霍特普(Neferhotep)带领。这位书吏手上的纸草卷写着:“在陛下、荷鲁斯、两土地之主、上下埃及之王森沃斯瑞特二世统治的第六年,一支亚洲的商队由地方王子克努姆霍特普带领,他们携带着眼影涂料,总计37人。”跟随着克努姆霍特普的是王室书吏“狩猎者总管”罕提(Khety),在他后面的就是那队亚洲人,他们的首领伊布沙(Ibsha)走在前面。这群亚洲人的上方是一行铭文:“37名亚洲人带着眼影涂料来到埃及。”与此同时,壁画还描绘了亚洲人首领牵着一只山羊,另一个亚洲人则牵着一只羚羊,紧跟其后的两头驴驮着一些物品。*P.E.Newberry,Beni Hasan,vol.I,London: Kegan Paul,Trench,Trübner,1893,pp.30-31,pls.28.
然而,无论是绘画还是铭文都没有指明这群亚洲人来到埃及的目的。但是根据壁画描绘的场景和壁画解说词我们可以推测,这时的埃及与迦南之间存在着官方贸易往来。
除了这幅壁画及其铭文,出土于埃及三角洲东部地区泰尔·戴尔·达巴(Tell el-Dab’a)*考古遗址名,即古代埃及语文献中的阿瓦利斯(Avaris)。该城兴建于第十二王朝时期,是当时亚洲人的主要聚居地,到希克索斯王朝统治时期,这座城市成为埃及的首都。的陶器也是我们研究两地关系的主要考古资料。这些陶器大部分从黎凡特北部地区进口,其余的则进口自黎凡特南部,其时间大致为第十二王朝末期和第十三王朝时期,从而揭示出这一时期埃及与黎凡特北部地区广泛的海上贸易,与此同时,埃及与黎凡特南部地区的联系却十分有限。*A.Cohen-Weinberger and Y.Goren,“Levantine-Egyptian Interactions during the 12th to the 15th Dynasties based on the Petrography of the Canaanite Pottery from Tell el-Dab’a”, in Egypt and the Levant, XIV (2004),ed.by M.Bietak,pp.69-100.
四、埃及文献中的两地关系
与考古资料相比,中王国时期的埃及文献在构建两地关系时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奈菲尔提预言》在描绘第一中间期的混乱局面时提到了亚洲人的入侵,并且一位名叫阿蒙尼(也即第十二王朝国王阿蒙奈姆海特一世)的来自南方的国王将修筑防御亚洲人入侵的“统治者之墙”。*关于这篇文献的译文,参见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下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826—832页。《阿蒙奈姆海特一世的教谕》中阿蒙奈姆海特一世在教导他即将继任王位的儿子时说道:“我征服努比亚,我俘获迈扎伊人(Medjay),我迫使亚洲人像狗一样逃走。”*关于这篇文献的译文,参见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下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776—779页。迈扎伊, 即为努比亚的一个部落。尽管这两篇文献都提及了亚洲人以混乱制造者的身份出现在埃及社会,但却并没有直接提及两地的关系。而在《辛努西的故事》里两地的关系被勘定为“他(第十二王朝国王森沃斯瑞特一世)将征服南方的土地,可是他却并不关注北方。”由此,第十二王朝时期埃及对迦南的政策似乎不是军事征服,而是军事防御。
出土于西奈半岛,特别是出土于塞拉比特·艾尔·哈戴德采石场(Serabit el-Khadêd)的文献对两地关系也有所揭示。目前我们在塞拉比特·艾尔·哈戴德的哈托尔神庙发现了400余块文献残片,它们中的大多数是石碑,另一些文献刻写在石块,石板和雕像上。*I.Beit-Arieh,“Serabit el-Khadêd”, in The New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s in the Holy Land,ed.by E.Stern,Jerusalem: The Israel Exploration Soceity,1993,pp.1337-1338.这些文献在对埃及人的采矿活动进行详细记述的同时也对埃及人和亚洲人在采矿上的合作进行了描绘,表明至少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两地是和平共处的。
然而,也有文献对埃及的军事行动进行了描述,奈苏蒙图(Nesumontu)铭文便是其中的一篇。奈苏蒙图,远征军首领,在阿蒙奈姆海特一世统治的第二十四年和森沃斯瑞特一世统治的第四年率领埃及军队征伐贝都因人和亚洲人。*这篇文献的译文为作者自译。因为这一文献的纪年方式采用双王制,因此,它也是第十二王朝的第一位国王阿蒙霍特普一世与第二位国王森沃斯瑞特一世共治的主要证据。然而令人遗憾的是,铭文并没有明确指出发生战争的具体地方,据此,这应该是一次前往迦南和东部沙漠地区的带有惩罚性质的突袭。
另外一篇内容类似的文献是森沃斯瑞特三世统治时期的索白克胡(Sobekkhu)铭文。这篇铭文记述了索白克胡,一名军事将领的最为荣光的事迹就是曾在晒海姆(Shechem)击败亚洲人。*关于这篇文献的译文,参见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中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44—546页。晒海姆,地名,现代考古遗址是位于巴勒斯坦境内的泰尔·艾尔·巴拉塔(Tell el Balata)。与奈苏蒙图铭文相同,这次军事行动也是一次带有惩罚性质的突袭,从而揭示出森沃斯瑞特三世统治时期埃及并没有对迦南进行有效的统治。
与上述两篇文献相比,阿蒙奈姆海特二世的孟菲斯铭文更具史料价值,它是我们重建第十二王朝时期埃及与其周边国家或地区关系的主要文献之一。这篇铭文是迄今所知唯一一篇埃及第十二王朝时期的王室年鉴,现存两个版本,皆出土于第十九王朝国王拉美西斯二世(Ramessis II,约公元前1279-前1213)统治时期的孟菲斯普塔(Ptah)神庙。篇幅较短的那篇出土于本世纪初,刻写在红色花岗岩石碑上。该石碑高125厘米;宽137厘米;厚58厘米,共12列铭文,现存于开罗博物馆,编号为SCHISM 3864。1906年,皮特里(Petrie)对这篇铭文进行了复制整理。*F.Petrie,Memphis I,BSAE 14th year,1908,London: School of Archaeology in Egypt,1909,pl.V.而篇幅较长的那篇则被发现于本世纪70年代初,同样,它也被刻写在红色花岗岩石碑上。该石碑长188厘米;宽25厘米;厚58厘米,共41列铭文。与小块石碑相同,它也现存于开罗博物馆,编号为SCHISM 3701。法拉格(Farag)首次对这篇铭文进行了复制整理。*Sami Farag,“Une Inscription Memphite de la XIIe Dynastie”, RdÉ 32 (1980),pp.75-82,pls.3-5.后来,马莱克(Málek)和魁克(Quirke)对其进行了再次整理。*J.Málek and S.Quirke,“Memphis,1991: Epigraphy”, JEA 78 (1992),pp.13-18.由于大小两块石碑在第十九王朝时期分别被重新用做拉美西斯二世的两座巨型雕像的底座,因此,学者们最初勘定它们应属于拉美西斯二世统治时期。然而,尽管铭文本身并没有为我们留下任何具体的时间,但从其所记述的事件全部发生于第十二王朝的国王阿蒙奈姆海特二世统治时期上看,这篇铭文的时间应为阿蒙奈姆海特二世统治时期(约公元前1901年-前1886年)。
根据这篇文献的记载,第十二王朝时期埃及与其周边国家或有着密切的贸易往来:
(他)派遣一支远征军到罕图什(Hanty-sh,今黎巴嫩)。(列7)*关于这篇文献的译文,参见郭丹彤:《古代埃及象形文字文献译注》,上卷,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41—54页
(他)派往罕图什城的贸易使团乘坐两艘船返回来了。他们带回16761/2德本*古代埃及重量单位。中王国时期,德本有大小之分:1大德本=27.3克,用于称铜;1小德本=13.6克,用于称青铜、黄金、白银、铅、香和无花果以及其他东西。白银、4882德本青铜、15965德本铜、1410德本铅、13块大理石、16588德本金刚砂、39556德本抛光沙子、1块玄武岩成的下碾石、6块(手推磨)碾石、5块坚硬的粗粒玄武岩、白色和黑色的石头、4块锤打石、1枚亚洲金银质地的印章、【……】2箱【……】石英【……】、5/8赫卡特*古代埃及容量单位,1赫卡特=5升。毛芮嘎油(moringa)、【……】663/8赫卡特油、271袋(?)提筛坡斯树果(tishepes)、7罐香料、922罐香、81/2赫卡特特耐特姆树果(tenetem)、553/4赫卡特胡荽果、4赫卡特克苏树果(kesu)、1/4赫卡特枪伤草药、3+x(?)小无花果树、73棵无花果树、65名亚洲人、2面镶嵌着黄金和象牙的青铜镜子、16把镶嵌着黄金、白银和象牙的铜短剑、21把镶嵌着象牙的铜短剑、4袋沙贝特植物(shabet)、197袋贝昊植物(behaw)、x袋筛弗筛弗特植物(shefsheft)、【……】231根松木。 (列18-21)
该文献还记述了埃及对西奈的贸易活动:
(他)派往绿松石山的远征军返回来了,他们带回了1413/32赫卡特绿松石、8700“两”化石、5570“两”比阿基阿(bia-kia)矿物、6赫卡特研磨了的矿物、2613/16赫卡特的盐胶、109/16赫卡特泡碱、8只海星、41袋乳香、93/4赫卡特白银、10头公牛、3只小野山羊、1张豹子皮、尼罗河刺槐制成的一座神龛、15枚印章。(列13-14)
依据上述文献,除了绿松石,出自西奈的货物并不产自西奈,表明此时的西奈有一个贸易亚洲物品的国际贸易市场。*A.Gardiner,“The Tomb of a Much-Travelled Theban Official”, JEA 4 (1917),p.28ff.第十一王朝时期,由于埃及没有加入近东贸易圈,埃及人只好从西奈获取他们所需的物品。第十二王朝时期,这一国际贸易市场依然存在于西奈。
这篇文献也提及了来自亚洲的贡赋:
人们俯首而来。亚洲统治者的子女,他们带来了220德本白银。(列12)

这里的塔姆帕乌人是没有任何暴力倾向的贸易者。*H.Goedicke,“Egyptian Military Actions in ‘Asia’ in the Middle Kingdom”, RdÉ 42 (1991),p.91.至于塔姆帕乌这一地名,它应该位于现今的图尼普(Tunip)。*M.V.P.de Fidanza,“The Tmp3w People in the Amenemhet II’s Annals”, GM 167 (1998),pp.89-94.
此外,该文献对埃及的军事行动有所记述:
(他)派遣一支由步兵指挥官率领的远征军去摧毁亚洲城市,伊瓦伊(Iway)。(列8)
(他)派往摧毁伊瓦伊和伊阿席(Iasy)这两个城市的步兵返回来了。从这两个亚洲城市带回了战俘1554名、铜和木制品:10把斧子、33把镰刀、12把短剑、41/4(?)把锯子、79把小刀、1把凿子、4把剃刀、330、2把五勾鱼叉、45件武器、36杆标枪、3个秤盘、60个车轮、646德本铜片、125德本铜块、青铜制品:30杆矛和26杆标枪、1杆铜和木材制成的矛、3德本共计38件黄金制成的头饰和耳饰;8件木材和白银制品成的带有圆环的权杖、58德本紫水晶、11/4德本哈斯乌德(haswud)石、1734德本绿色石头、4个象牙调色板、54件亚洲物品、1顶轿子、13付车的连杆、8根辐条、375德本铅。(列16-18)
根据上述文献,埃及与黎巴嫩和西奈都有密切的贸易往来。由于该文献明确记录了埃及与上述两个地方的贸易活动,那么居于它们之间的巴勒斯坦地区是否也与埃及有着同样的贸易或军事冲突呢?为此,我们需要对文献中出现的两个地名伊瓦伊(Iway)和伊阿席(Iasy)进行勘定,这是两个被埃及摧毁的带有围墙的城市。据文献记载,来自这次战争的战利品清单中包含有亚洲俘虏,据此我们推断,这两座城市应该位于黎凡特地区。*S.L.Cohen,Canaanites Chronologies and Connections: The Relationship of Middle Bronze IIA Canaan to Middle Kingdom Egypt,Eisenbrauns: Winona Lake,2002,p.44.由此表明,中王国时期的埃及国王们对迦南地区确有关注。然而如果将第一个地名伊瓦伊勘定为小亚沿岸的乌拉(Ura),*W.Helck,“Ein Ausgreifen Des Mittleren Reiches in Den Zypriotischen Raum?”, GM 109 (1989),pp.7-30;E.S.Marcus,“Amenemhet II and the Sea: Maritime Aspects of the Mit Rahina (Memphis) Inscription”, Egypt and the Levant, XVII (2007),ed.by M.Bietak,p.144.第二个地名伊阿席勘定为阿拉什亚(Alashiya),也即塞浦路斯(Cyprus),*W.Helck,“Ein Ausgreifen Des Mittleren Reiches in Den Zypriotischen Raum?”, GM 109 (1989),pp.7-30;D.B.Redford,Egypt,Canaan,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2,n.47;J.F.Quack,“kftaw and I3sy,” Egypt and the Levant,VI (1995),ed.by M.Bietak,pp.75-81;E.S.Marcus,“Amenemhet II and the Sea: Maritime Aspects of the Mit Rahina (Memphis) Inscription”, Egypt and the Levant, XVII (2007),ed.by M.Bietak,pp.146-148.这又揭示出阿蒙奈姆海特二世统治时期埃及与黎凡特北部地区保持着海上贸易往来,这可以从这句“(他)派往罕图什城(即黎巴嫩)的贸易使团乘坐两艘船返回来了”的文献中得到印证。
然而,无论这两座城市位于何处,从贸易品清单和战利品清单来看,这一时期的埃及与迦南的贸易联系以及前者对后者的军事行动都十分有限。这些物品中的一些我们无法对它们做准确的勘定,尽管其他的物品广泛应用于埃及社会,但是数量并不大。贯穿于古代埃及始终,埃及人对银都有很大的需求,但是该文献在记述对外贸易时只提及两次银,它们的数量分别是1676 1/2德本和9 3/4 德本,这表明埃及的对外贸易规模并不大。并且银还缺失于埃及的战利品清单中,同时战利品中的其他物品的数量也不是很大,表明埃及军事行动的经济目的也很有限。
此外,揭示两地关系的重要文献还有克努姆霍特普三世的位于达舒尔(Dashur)的坟墓铭文。克努姆霍特三世,前文引证过的克努姆霍特普二世的儿子,是一位负责埃及与东部邻居贸易的官员。他的政治生涯从森沃斯瑞特二世统治的第一年一直持续到阿蒙奈姆海特三世统治时期。现存的这批文献零散且破损严重,有几百片之多,最近出土的几块石板残片为我们整理出一篇完整的文献提供了可能。*关于这篇文献的译文,除了专门标注外,其他译文均参见J.P.Allen,“The Historical Inscription of Khnumhotep at Dahshur: Preliminary Report”, BASOR 352 (2008),pp.29-30.达舒尔,地名,位于开罗以南,尼罗河西岸。
该文献在称呼巴比罗斯的统治者时没有使用最为常见的指代“统治者”的埃及语单词hq3,而是用了M3ky,一个指代“国王”的塞姆语单词,并且这个词汇的定符是跪着的双臂被反绑在身后的人,揭示出此时的埃及与巴比罗斯是敌对的,并且森沃斯瑞特二世统治时期巴比罗斯的统治者是一位“国王”,而不是“地方王子”(h3ty-’),这是埃及对属国统治者的称谓。到阿蒙奈姆海特三世统治时期埃及语文献开始称巴比罗斯统治者为“地方王子”,*K.S.B.Ryholt,The Political Situation in Egypt during the Second Intermediate Period,c.1800-1550 B.C.,Carsten Niebuhr Institute Publications 20,Copenhagen: Carsten Niebuhr institute of Near Eastern Studies,University of Copenhagen,1997,pp.86-90.表明这一时期,巴比罗斯重新归顺于埃及:
海上远征军首领【来到巴比罗斯】“国王”的住所。(1D4-2A2)
普塔神的王室祭品:一份由面包、啤酒、牲畜和家禽组成的祈祷祭品,为贵族、高级官员、王室印玺掌管者和国王唯一辅佐者以及国王最信任的人的卡(即灵魂),为他在弹压亚洲人荡平贝都因人时的战绩,王室总管克努姆霍特普,荣耀的拥有者。(2H)
中王国早期,埃及在迦南的贸易伙伴是乌拉匝(Ullaza)*地名,位于叙利亚地区的港口城市。,而非巴比罗斯:
人们到达瑞特努获取【乌拉匝】这个港口城市的雪松。(1C2-3)
而后不久,埃及就与巴比罗斯重建了贸易联系:
【……】船只返航【……】他们曾向北前往巴比罗斯。(ON4-5)
巴比罗斯还曾与乌拉匝有过小规模的军事冲突,这次冲突由巴比罗斯统治者的儿子挑起,埃及站在了乌拉匝一边:
【……】来自乌拉匝。然后巴比罗斯“国王”【……】与100名亚洲人一起,他们将被赠予【……】。(2P8-10)
人们前往黎巴嫩。他们在乌拉匝看到巴比罗斯统治者之子与那100名亚洲人,他们正制订计划,准备与乌拉匝统治者开战。(3A5-B5)
一次穿过三角洲东部运河前往黎巴嫩的远征也被记录在文献中。如果这次远征发生于森沃斯瑞特三世统治时期,那么它很有可能与前文提及的索白克胡石碑中记述的那次远征为同一次:
【……】前往黎巴嫩【……】乌拉匝,沿着【……】那里,为了穿过运河,前往亚洲人的土地,前往战场。【……】(3D2-4)*J.de Morgan,Fouilles à Dahchour,Vol.I: Mars-juin,1894,Vienna: Holzhausen,1895.
要之,达舒尔铭文为我们进一步勘定阿蒙奈姆海特二世统治时期埃及与黎巴嫩、叙利亚和塞浦路斯的或贸易或战争的联系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正如这一国王统治时期的孟菲斯铭文所揭示的埃及与迦南的海上贸易联系,这篇文献揭示了阿蒙奈姆海特二世统治时期埃及与黎凡特北部地区的海上贸易和军事冲突。*E.S.Marcus,“Amenemhet II and the Sea: Maritime Aspects of the Mit Rahina (Memphis) Inscription”, Egypt and the Levant, XVII (2007),ed.by M.Bietak,pp.175-176;E.S.Marcus,Tel Nami: A Study of a Middle Bronze Age IIA Period Coastal Settlement,MA.Thesis,University of Haifa,1991.直到到第十二王朝末期,埃及与巴比罗斯的联系才重新建立起来。
结 论
根据上述埃及文献以及出土于迦南和埃及两地的考古资料,尽管奈苏蒙图石碑、索白克胡石碑和孟菲斯铭文记录了埃及在迦南的军事行动,但是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仍集中表现在贸易上。第十二王朝早期,两地的关系是通过不同路径的双边互动:黎凡特与埃及的联系是通过陆路来完成的,位于拜尼·哈桑的第3号坟墓中的壁画和来自于塞拉比特·艾尔·哈戴德采石场的铭文可以证明这一点;与此同时,出土于伊弗沙的陶器则反映了埃及与黎凡特南部的海上联系;孟菲斯铭文以及出土于达舒尔的克努霍特普坟墓铭文揭示出黎凡特北部地区更趋向于与埃及进行海上贸易。第十二王朝末期和第十三王朝时期,埃及与黎凡特南部的贸易通过出土于阿什克龙的印章和陶器得到了充分的揭示,而克努霍特普的达舒尔铭文则揭示了埃及与古王国时期的传统贸易伙伴巴比罗斯的联系,乃经过埃及第一中间期和第十二王朝早期的中断后,并于这一时期重新开启。自此,埃及与迦南的或陆路或海路的贸易联系全面展开。中王国结束后埃及进入历史上的第一个异族政权希克索斯王朝统治时期,此时的迦南值青铜中期文化三期阶段,由于希克索斯人本就来自迦南地区,因此,这一时期的埃及与迦南的联系越发的密切。到埃及新王国时期,此时的迦南已进入铁器时代,两地之间的交往不仅仅体现在贸易上,更突出地体现在外交和战争上,直至埃及将迦南几乎所有的土地纳入了自己的版图。
据此,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与迦南的交往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古王国时期的两地交往,更为新王国时期更大规模更多途径的双向往来奠定了基础,成为古代埃及对外交往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责任编辑:冯雅)
2016-05-13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新王国时期古代埃及经济文献整理研究”(编号:13BSS008)。
郭丹彤(1968-),女,吉林德惠人,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
A
1674-6201(2016)02-006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