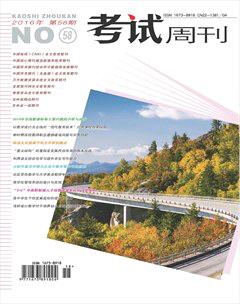中学教材中的又一悲剧形象
马潘婕
摘 要: 师陀小说《说书人》中的主人公,也就是说书人,是一个足以令我们为之动容的悲剧形象。他的悲剧源于时代,特殊的时代背景和战乱环境使他注定是一个不被那个时代、那个社会接纳的孤独者。作者采用独特的局限型叙事手法,讲述情节质朴简单、人物和情感却震撼人心的故事。说书人形象之所以伟大,不仅仅在于他自身所具有的精神品质,更在于其背后丰富的文化内涵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深深震撼着我们。
关键词: 《说书人》 生命形象 文化底蕴
《说书人》出自苏教版高中语文必修二,是2014年教材篇目调整新增的一篇文章。这篇课文选自师陀的小说集《果园城记》——我国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沦陷区乡土小说代表作品之一。《说书人》这篇文章原来的副标题是“果园城记之十一”。《果园城记》里的作品旨在从文化层面上挖掘中国乡村生存状态,揭示民族劣根性,从文化层面对人的生存状态进行审视。写于抗战时期的《果园城记》就是这样一部夹杂着作者浓厚乡土情结的作品。在《果园城记》的序言里,师陀如此评价:“我有意把这小城写成中国一切小城的代表,他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见解、有情感、有寿命,像一个活的人。”①读罢《说书人》,能够被其所包含的生命形象、文化底蕴深深震撼,而心中涌现的情感更是五味杂陈。
一、说书人——他是一类人中独特的那一个
文中在对说书人的形象刻画过程中,数词的应用信手拈来,尤其是“一”这个数。比如第一段写道:“他有一把折扇——黑色的扇面已经不见了,一块惊堂木——又叫作醒木,一个收钱用的小笸箩,这便是他的一切。”说书人所拥有的仅仅是这几样说书道具,而且每样只有一个,扇子连“黑色的扇面都不见了”都没有换新的,可见其生活的窘迫。除了生活困窘外,“一”在某种程度上也表现出他的孤独。他没有孩子,没有家庭,死后也被埋到永远不会有人来祭扫的乱葬岗。除此之外,更有他人对其不解和对其职业的蔑视。说书人的一生,陪伴他的是他的说书道具和听众们。可是,在他为了说书呕心沥血、身体都垮了之时,“他的老听客慢慢减少了”,老人逐渐死去;孩子逐渐长大,有了大人的责任,无暇再去听书了。他死的时候是如此孤单,没有亲人,也没有听众,抬灵柩的人对他除了鄙夷外,再无其他。就这样一位朴实、坚韧的民间艺人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挂念他的人——如文中的“我”的内心会有无限悲伤涌动,但对于其他人而言,他的离开并不是稀奇的事,也压根不会在意。
文中有一句话颇具深意——“说书人,一个世人特准的说谎家”。说谎本是一个贬义词,在这里却变成了褒义,还是“世人特许的”说谎家。说白了,是世人需要这份职业,需要这份职业带来的乐趣,说明说书人的存在对于世人的价值。但是尽管是世人特许的说谎家,尽管他的技艺得到认可,他依旧是贫苦社会的底层。说书人的困窘是贯穿在整部小说中的,坚持着说书直到死去,生活却从来都没有得到真正改善。比如第五段:“时光于是悄悄地过去……说书人所有的仍旧是那把破折扇,那块惊堂木,那个收钱用的小笸箩。”“渐渐的他比先前更黄更瘦;他的长衫变成了灰绿色;他咳嗽,并且嗜血。”物质生活条件越来越差,身体越来越差,死亡对于他而言是一种必然。尽管小说淡化了对其死亡情景的描述,读者还是能够体会到他的死是多么凄凉。
对于说书人,每位读者或许都会产生一种悲悯的情怀。文中说,这是一种贱业。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像说书人这样的人,他的命运似乎是注定的。他努力说书,努力给听众带来乐趣,却难以养活自己,连死都那么悲凉。无论如何,只要作为说书人这样的技艺人,他就无法左右自己的命运。就像说书人生活的这个小城一样,平静得经不起一丝波澜,不管外面的世界如何变动,每天的生活像排练了一样,有条不紊地上演。但是,这个小城背后的东西太过厚重,总有些扑朔迷离看不透的深邃,有着说不出的压抑。这应该是依托于这片土地上面浓厚的文化底蕴和民族气息的另一种体现,使得果园城这片神奇的土地富有生命力的张力,足以震撼到人的心灵,引起人们意识深处的情感共鸣。
二、局限型叙事手法的巧妙运用
师陀的《说书人》采用的是局限性叙事视角,将叙事者直接与文中的主人公“我”合二为一。不仅采用的是人物的内聚焦透视,所选用的第一人称作为叙事者更使得整篇小说颇具特色。文中有一个叙事主人公“我”贯穿全文,“我”并非小城中的人,而是一个外来者,小说就是用“我”的视角带领读者回顾那个年代,走进那座小城,走向说书人。整部小说的情节作为一种意识流,在“我”的回忆中进行着。师陀曾说:“我的短篇小说有一部分像散文,我的散文往往像小说,我自己称之为四不像。”首先,对于师陀的这句自我评价,其小说散文诗一般的语言风格这里不再多加赘述。在叙事形式上,不同于站在“上帝的视角”那种全知型叙事风格,这种局限型的叙述方式使得叙事主人公视角可以在小城中任意移动,可以瞬间拉开,也可以自由靠近,在限定时空中行云流水般地任意穿梭。
在那个年代,当京派和海派作家在进行激烈论战的时候,师陀却以另一种姿态游离于激战之外。尽管很长一段时间内,师陀在现代文学史上可谓默默无闻,然而他的叙述风格就像他的性格一样,孤独又热忱,所以终究能被挖掘和欣赏。师陀在小说中用“我”的口吻讲述说书人的故事,殊不知他自己也是一位说书人。有人说:“在《果园城记》中,作家淡化了痛苦,节制了愤怒,以写实沉静的外衣包裹火样的情感,以沉思冥想阻挽即将喷薄而出的热情,以时间的延宕来经营形式的美丽。”②阅读《说书人》,我们似乎能感觉到平缓的文字下的力量,说书人的命运在作者笔下是那样一种“自然而然”的结果,但是又是被时代所迫、不公平的命运结果。一位优秀的说书人大概就是这样,既不能在说书过程中流露出刻意情感表达,又要透过文字将想要抒发的情感巧妙地传达出去,让听众或是读者为之触动。
小说的叙述顺序是比较常见的正叙,从“第一次”见说书人到“时光悄悄过去”,再到“最后一次”到小城来。一共是三见说书人,但是和一般小说不同的是,每一次“见”后,作者都采用了大量笔墨议论抒情。从开始对于说书这个职业的思考,到对于说书人境遇的思考,再到对说书人死亡的思考。通过阅读,我们可以得知“我”仅仅见过说书人三次,那么“我”对于说书人、说书场景、说书内容的回忆可能都带有一定虚构的成分。相对于一般小说重点在情节叙述上,《说书人》则增加了许多其他议论、抒情的成分。局限性叙事手法,使得小说的叙述者“我”所经历的事件、所产生的感悟和思考,同样可以影响读者对于这篇小说的理解深度。读着读着,自己都仿佛成了文中那个“我”,目睹了说书人的一生,进而咀嚼了说书人的命运、品读说书人的悲哀,把对说书人的情感传达了出去。
三、在教材中的地位、价值
苏教版必修二第二单元的单元主题是“珍爱生命”,在这个主题的基础上又分为两个部分,“向死而生”和“陨落与升华”。《说书人》出自“陨落与升华”部分,且为一篇自读课文。“陨落与升华”,对于说书人的命运,倒也是很好的概括。和上一篇《最后的常春藤叶》中的老贝尔曼相比,说书人似乎更令人感到悲哀。令人感到悲哀惋惜的不仅是说书人的凄惨人生,更有小城中其他民众的麻木和看客心理。对于看客的描述,鲁迅在小说里为我们呈现了很多,师陀的这篇小说也是。《说书人》所呈现的已经不仅仅是个人命运的问题,而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命运问题。那些麻木的人,他们仿佛都与正常的人性相背离,忘记人与人之间最美好的情感,忘却人性中的善良。原因大概有两点:一是贫苦,二是愚昧落后。小说如此构思,这刚好印证师陀想要把果园城塑造成一个社会的缩影的初衷。这篇小说的叙述本是朴实委婉的,但是其文字后面所蕴含的力量却是震撼的。致力于师陀及其作品研究的刘增杰曾这样评价:“作者以其朴实又热烈的情感,浓郁的抒情笔调,流畅又富有诗意的语言,向读者介绍了一个又一个凄凉又亲切的社会。”③当凄凉遇到亲切,便产生一个个说书人这样的形象。说书人能带给我们这么大震撼的原因,除了其身世凄凉、在于其蕴含的精神文化内涵外,还有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他是一个令人感到亲切的形象。他对于文中的叙述者“我”来说,是亲切的,是熟悉又喜爱的。所以当这样一个人最终凄凉死去的时候,“我”的内心无比痛苦,读者的内心往往也是。
课文导读的主题是“陨落与升华”。说书人的死意味着生命的陨落,为何又说是一种升华呢?因为死亡也不能掩饰说书人这个形象及其背后的情感、文化和精神所散发的光芒,他的经历、精神留下来,留在像“我”这样的听众的心里。“他说武松在景阳冈打虎,说李逵从酒楼上消下去,说十字坡跟快活林,大名府与扈家庄”。“他说‘封神,说‘隋唐,说‘七侠五义和‘精忠传”。说书人,本来就是文化的缩影,他精通历史小说和神话故事,用一种惟妙惟肖的方式讲述给观众。他以自己的文化积累,给小城的人创造了一个精神世界。临死前几天还在说书,他对于说书的坚持令人敬佩和感动。
师陀笔下的说书人,是中学教材中的又一悲剧符号。作者师陀采用独特叙事手法塑造这一形象,更凸显了其独特性。尤其是这一形象背后的文化内涵,需要结合师陀的创作背景和小说的历史背景进行挖掘。
注释:
①师陀.果园城记.序[M].上海:上海出版公司,1946.
②王欣.乡土中国的“诗与思”——重读师陀的《果园城记》[J].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
③刘增杰.师陀资料研究[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2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