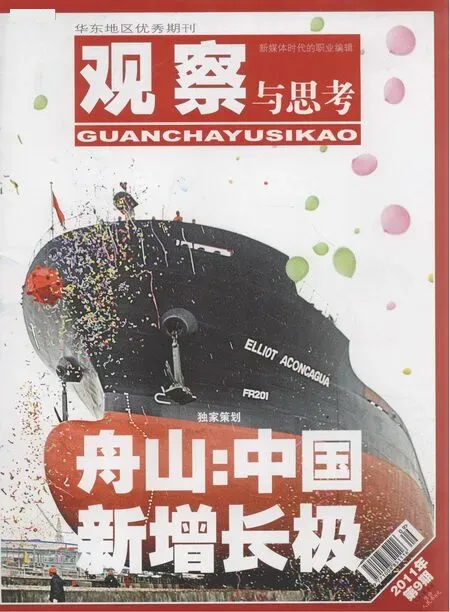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何以可能?
董 石 桃
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何以可能?
董 石 桃
提 要: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所以可能,首先体现在关于人的本质、人的异化和人的解放的科学认识;其次体现在历史、社会和经济的方法论支撑;最后体现在应然和实然、普遍和特殊、个人和社会辩证统一的实践论特色。
马克思主义 人权哲学 认识论 方法论 实践论
作者董石桃,男,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政治学博士,公共管理学博士后,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湘潭 411105)。
在人权哲学的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做出了独特的贡献,“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对人权的批判和理论贡献已成为一种基本原则”①[美]科斯塔斯·杜兹纳:《人权的终结》,郭春发译,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页。,但是如何可能?学界对这一问题还缺乏深入探讨。面对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的人权思想遗产,人们常常问:是否存在一种“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如果有,它与其他人权哲学相比,有什么独特性?对此问题值得进行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的认识论基础
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之所以可能,首先在于其具有独特的认识论基础,主要包含如下三个方面:
(一)人的本质
人权的观念是对人的本质认识的折射,不同的人权哲学反映着对人的本质的不同解释和规范,关于人的本质的不同认识是人权哲学基本分水岭。自然主义的天赋人权观把人的本质理解为绝对理性,并将这种理性视为社会历史发展的根本尺度,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个人主义本位的人权哲学。这种人权哲学认为人权是上帝或造物主赋予的,人们按照自然法则所享有的与生俱来的权利。他们认为,人的属性根源于自然状态,人的本质是孤立的,彼此之间是没有什么社会联系的,而自由平等的人权就源于人的理性,或者说是“自私利己”或“趋利避害”的本质性,“天赋人权”就是以个人为本位的利己主义的权利,资产阶级人权哲学的基础就是这种抽象人性论。马克思则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任何一种所谓人权都没有超出利己主义的人,……即作为封闭于自身、私人利益,私人任性,同时脱离社会整体的个性的人。”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9、18页。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反对这种脱离社会关系的,抽象的人性论。马克思人权哲学认识论的首要根基及独特性在于对人的本质的独创性理解,即从社会关系的总和方面去考察人,把人看成是“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看成是和物质生活条件互相联系的活动着的人。马克思说:“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39、18页。这是马克思主义对人的本质的最科学、最深刻的说明。在马克思看来,人们从事改造自然界的生产实践必须同自然界发生关系,但人们要从事物质生产还必须同社会其他人发生关系,从而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人的本质就是在这种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形成的。社会是人的社会,而人是社会的人,人和社会密不可分。而人权问题是人的本质的根本体现,人的本质又是在现实社会关系中形成的,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决定了人权本质上就是人们之间结成的一种深层次社会关系。
(二)人的异化
人的社会关系本质决定了人权的社会性本质,社会关系性质及其合理性程度决定了人权的性质及其合理性程度。社会关系的基础是人们在生产劳动过程中结成的社会联系与相关规范,这种劳动关系如果合理,它将促进人权的发展及实现,反之,如果作为人权及人的发展手段的劳动关系变成了目的,则将成为人权发展和实现的障碍,造成“人的异化”。由于劳动是社会关系的根本与基础,“劳动异化”则是“人的异化”的根本环节。马克思通过对社会的经济分析,揭示了“劳动异化”的四大奥秘:其一,劳动产品作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劳动者相对立。“工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的产品的力量和数量越大,他就越贫穷,工人创造的商品越多,他就越变成廉价的商品。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273页。其二是工人与劳动过程的异化,劳动的实现以工人失去现实性为代价。劳动本来是人的本质,是人对自身的肯定,但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变成压迫工人的异己力量,成为“被迫的强制劳动”。其三是劳动者同自己类本质相对立。异化劳动颠倒了类和个体的关系,它使“生活变成维持个人生活的手段”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67、273页。。使人的“本质变成仅仅维持自己生存的手段”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6页。。其四是人与他人的异化,即由于所有者与生产者的分离,工人和资产者的关系就变成相对立的关系。马克思通过批判哲学揭示了人的异化现实,展示了西方社会关系的不合理与扭曲,不仅无助于反而有碍于人的本质及权利的实现。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将这种异化劳动关系制度化,发展成为国家的法律关系,从而固化了既有的不平等的关系,加剧了人的异化。在这里,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即脱离了人的本质和共同体的利己主义的人的权利”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437页。。这种人权是与人权所应有的道德目的相背离的,造成理想和现实的严重脱离。杜兹纳也指出:“西方人权,从理论上讲,国家为了实现普遍的善,实际上它只提升了资产阶级的狭隘阶级利益及其在文明社会的统治地位……人权是革命的主要意识形态。这些权利属于抽象的普遍人,然而在实践中人权促进了资本主义非常具体的人及自私、贪婪的人的利益。”①[美]科斯塔斯·杜兹纳:《人权的终结》,郭春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69-170页。在近代西方制度中,所谓人权只是资本所有者基于私有制享有的特权,“人权本身就是特权,而私有制就是垄断”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229页。。“平等归结为法律面前的资产阶级的平等;被宣布为最主要人权之一的是资产阶级的所有权”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20页。。马克思“人的异化”理论实质上是对西方近代人权制度“对实现人权理想的手段或标榜实现人权理想的手段的批判,而不是对人权本身的批判,即对手段的批判,而不是对目的批判”④夏勇:《人权的概念——权利的历史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175、175页。。马克思正是通过这一全面彻底批判,从“破”的角度奠定了其人权哲学的重要“人学”理论基础。
(三) 人的解放
对旧手段的批判,意味着对新手段的寻求。“人的异化”理论意味着马克思对整个近代西方社会制度自我进化、自我改善可能性的否定判断。“具体讲,就是否认近代资本主义私有制促进和保障人权理想实现的可能性,否认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民主和法制促进和保障人权理想实现的可能性。”⑤夏勇:《人权的概念——权利的历史哲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74-175、175页。既然“异化”的社会关系,使人成为非人,那么克服异化的社会关系就是人权发展的应有之义,而“人的解放”就是克服“人的异化”的根本方向。“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的根本价值目标。在马克思看来,人权是有待扬弃的历史性权利,其社会理想的核心是“人类的解放”,即实现每个人自由全面的发展。“人类解放”是对人的异化的克服和扬弃,将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身,人的解放是“人的类特性”的成就与复归,人的这种类特性就是人的“创造生命的生活”活动及“自然自觉的活动”,而“人的类特性”就是“人的解放”的前提和根据,“只有当人认识到自身‘固有的力量’是社会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起来,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以政治力量的形式同自身分离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的解放才能完成”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6页。。人类解放本质上就是国家和市民社会二元对立的克服,是人的存在的二重化的消除,也是人权与公民权分离的消除。当一种社会制度虽然从抽象意义上承认人们类特性意义上的权利诉求,但在现实上又无法满足和实现这种诉求时,那就应该谋求建立新的社会关系及社会制度,在马克思那里,就是建立一种能够克服私有制的缺陷,扬弃劳动的异化,树立人的尊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社会制度,这种新型的社会制度就是共产主义制度。值得指出的是,共产主义作为一种理想的社会制度,只是一种手段而不是目的,正如资本主义制度之于狭隘的利己主义是手段而非目的一样。马克思认为,“共产主义作为‘否定之否定’的肯定,因而是人类解放和自我复归的历史发展的第二阶段的必要的真实因素。共产主义是最近将来的必然形式和能动原理,但是共产主义并非人类发展的目的——而是人类社会的形成”⑦转引自:《马克思“英译本补遗”》,弗·梅林:《马克思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592页。。作为人类解放的条件和手段,共产主义代表马克思主义对实现人权合理社会制度的探求,其目的在于解决资本主义所无法解决的矛盾,实现真正的人类、自由、平等、安全和幸福,实现真正的人权。
二、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的方法论特征
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之所以可能,还在于其科学的方法论特征,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将历史视角贯穿于人权分析的全过程
历史分析法是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的重要方法论特征。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具有历史性,都是从历史中产生的,是一定历史的结果。“单个人的历史决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5页。以平等、自由、民主为基本内容的人权也是历史地发展的。首先,从人权的产生来看,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马克思指出,“‘人权’不是天赋的,而是历史地产生的。而‘批判’关于人权是不可能说出比黑格尔更有批判性的言论的”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46页。。这其中最有力的证明就是作为人权发展的理论根基——平等正义的观念就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罗马法发展以前,除了原始社会自发公社中公社成员之间的自发平等权利外,平等的观念很少存在。作为以私有制的基础的法律的最完备形式——罗马法,确认了自由民的私人平等,但是自由民和奴隶之间的对立和不平等还是普遍存在。到了中世纪,基督教发展出一种平等观念,这种平等观念只承认一切人的一种平等,即原罪的平等,这同它曾经作为奴隶和被压迫者的宗教的性质是完全适合的。到了十八世纪,资产阶级将平等观念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原则加以传播,这种天赋平等的观念就忽视了平等观念产生和形成的全部以往历史。马克思认为:“现实的人过去和现在如何行动,都始终取决于他们所处的历史条件。”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60页。作为人权理论基础的平等观念并不是自古以来就作为真理而存在的,而是历史性地形成的,且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具有不同的内容。其次,历史分析法也是剖析资产阶级人权产生和发展的科学工具,资产阶级把自由、平等的权利宣布为人权,作为其革命口号与政治纲领并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并不根源于资产阶级的特殊利益,而是根源于近代商品经济发展及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历史要求。资本主义阶段,商品经济的发展要求在市场交换中资本家和工人都应当是享有自由、平等的人权的人,才可以有效地保证商品经济的正常发展。总之,资产阶级人权的产生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到特定历史阶段的产物,而不是所谓天赋的产物,而资本主义人权的性质也是具有特定历史阶段的特征。
(二)将社会关系作为人权分析的主线
如前所述,马克思确认人的本质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所谓人权,无非是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中的人的权利。因而,对社会关系本身进行具体的分析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的重要使命,社会分析法也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的具体分析方法。马克思认为:“人是最名副其实的政治动物,不仅是一种合群的动物,而且只有在社会中才能独立的动物。”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84页。据此,马克思把人权分解成三个相互联系的方面,即人,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以及具体的权利内容。有学者指出:“马克思并没有把眼光单纯置于人权的权利内容上,而是紧紧抓住了作为总和而又必然反映社会关系基础物质的具体的人,以及为社会关系所决定的人与人之间现实的权利关系来展开他的人权理论。”⑤朱锋:《马克思人权理论论要》,《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2期。社会关系分析方法使马克思超越了以往所有的资产阶级启蒙学者,能够比他们看得更远、更清晰、更准确。在马克思看来,人权中所指的“人”,不是抽象的人,而是市民社会的成员;人,不是指人的自然属性,而是指人的社会属性或人的市民社会属性。马克思指出,“所谓人权无非是市民社会的成员的权利”,而“市民社会的成员,就是政治国家的基础、前提。国家通过人权予以承认的”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5页。。马克思之所以强调运用社会分析方法来分析人权关系中具体现实的人,原因在于资产阶级天赋人权观将人定义没有任何差别的自然人,就割裂和抛弃了人权的社会关系性,也否认了人权和人的时代特征,也就无法科学把握人的具体的权利行为。马克思运用社会方法确认了人权的社会性本质:首先,权利关系是人的社会关系的表现形式。“政治国家的建立和市民社会分解为独立的个体——这些个体的关系通过法制表现出来。”②《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5、45页。资本主义的人权关系本质上是“私人”之间关系的具体体现。其次,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关系是现实权利关系的基础。只有物质关系是平等的、自由的,人与人之间的权利关系才是平等和直接自由的。由此推之,人权关系的状况只有从社会关系分析中才能真正把握。最后,人权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并不直接取决于法权关系及其具体内容的调整,而是取决于人和人之间的经济所有制的调整。资本主义法权关系并不能真正告诉我们西方国家人权现实的答案,真正的答案需要运用社会分析方法从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才能寻求到。
(三)将经济因素作为人权分析的决定性要素
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并不是抽象的思辨或玄想,而是紧贴人民的生活世界分析人权的本质及发展, “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47页。。经济生活事关人们生存和发展的根本,经济分析方法因而成为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探究的重要方法。马克思认为:“法的关系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18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概括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页。马克思运用经济分析法剖析资本主义经济现象和经济规律,彻底批判了资本主义人权的虚伪性,确认资本的内在属性即要求形式上的平等和自由,“资本是天生的平等派,就是说,它要求在一切生产领域内剥削的条件都是平等的,把这当作自己的天赋人权”⑤《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7、338页。人权赋予资本家以自由和不可剥夺的权利,是资本的要求。而当资本进入流通领域中,则更需要人权和自由来保障资本家对工人剩余的不平等占有,“平等地剥夺劳动力,是资本的首要人权”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57、338页。另外,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作为交换价值的一般等价物,人权表现为资本主义货币运动的必然要求。在资本主义流通领域同样是“人权和自由”的经济规定领域。流通中的商品普遍体现了人们一般劳动的凝结,流通的商品本身没有特权,它只有按价值衡量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每个人都按自己选定的价值尺度自由地买和卖。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如果说经济形式,交换,确立了主体之间的全面平等,那么内容即促使人们去进行交换的物质材料,即确立了自由”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99页。。此外,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一个根本规定是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成为商品既是自由人权的社会要求的经济结果,又是自由人权的经济决定因素。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时代的特点是工人有使自己的劳动力成为商品的自由,这既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本质要求,又是资本运行的必要条件。总之,正是运用经济分析方法,马克思完成了对资本主义人权的科学的辩证的批判。他一方面承认资本主义社会中确有“公正,自由”的人权制度;另一方面又深刻阐明了这种自由和人权的虚伪性和内在矛盾,从而为以后西方人权理论的发展带来完全新的气象。
三、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的实践论特色
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之所以可能,还在于其独有的实践论特色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一)应然和实然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在实践途径上首先体现在理想和现实的统一。如前所述,马克思对近代西方人权理论及人权制度作过许多透彻的批判。有学者据此认为马克思是蔑视和否定人权概念本身,至少是不提倡人权的,因此在马克思的理论中其实并不存在一种人权哲学。这种观点无疑是不正确的,原因在于他们未能区分人权概念包含理想与现实双重维度,马克思从现实维度对资本主义人权的虚伪性、狭隘性进行了透彻地、无情地批判,但从一般性的理想上,马克思批判的是实存的人权制度或者实存的标榜人权的制度,而不是批判应然人权的要求。马克思人权哲学在实践方式上,其实是试图实现人权理想和现实的辩证统一,即通过对实存人权缺陷的改进不断地接近“人的解放”的人权理想。因此,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中存在着一个理想的维度。正如夏勇所言:“马克思认为近代西方的人权制度有虚伪性、狭隘性,这本身就已表明马克思心中有一个不与之对照的理想的、合理的人权概念,若不求真责实,何以抨击虚伪与偏狭?所以,将马克思关于人权的实然判断当做马克思的人权概念,就像将马克思关于国家和法法律,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这一实然判断当作应然判断一样,是十分危险的。”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3页。否定马克思人权哲学的应然维度,或者将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的应然维度和实然维度相混淆,将出现一系列的偏差,比如有学者根据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实存人权的批判,确认马克思反对人权概念本身,甚至据此提出,“人权无非就是西方那一套”就是佐证。马克思对于整个人类大多数人的苦难怀有强烈的道德使命感,对于底层人民的苦难有着深切的怜悯,马克思的理想就是克服一切人的异化,实际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性的复归。这就应该要承认和保障人们的共同权益和要求,应该要保护人类的基本共同利益即人权。这是马克思人权哲学的应然维度和主体论。另一方面,马克思对人权问题的思考,又是从现实的人活动及其社会关系出发的,即马克思人权哲学有一个实然的维度。马克思认为在现实维度上,无产阶级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的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③。人们只有逐渐依据现实的条件,慢慢通过人的完全恢复来恢复自己。而且,现实人权的实现必然有较为丰富的物质条件为前提。
(二)普遍和特殊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认为,人权是普遍性和特殊性的辩证统一。“人权的普遍性”是人权主体、内容和价值目标的普遍性。从主体上看,人权是一个只要是人就具有的权利,这里的“人是指全人类”;从内容上看,人权的形式是普遍的,它既包括生存权、政治权,也包括经济权、社会文化权,还包括发展权;从价值目标上看,人权的理想是普遍的,人权作为所有国家共同努力促其实现的目标是普遍的,人权在当今世界得到了普遍的承认。马克思对人权普遍性有着深层次的确证,即人权作为权利的最一般形式,是区别于优先权、特惠权等特殊形式的权利。人权是每个人作为社会成员享有的最低限度的,使其成为人而不是非人的权利,以此从人权的判断标准来看,讲人权就只能撇开人性其他一切方面,再不把它当作什么,只是把他当作人。马克思指出,“就它的本性来讲,只在于使用同一尺度;但是不同等的个人(而如果他们不是不同等的,他们就不成其为不同的个人)要用同一尺度去计量,就只有从同一个角度去看待他们,从一个特定的方面去对待他们”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4页。。
另一方面,人权普遍性并不排斥人权的特殊性。任何人权的概念及内容,以及人权思想本身都具有历史的特殊性、特定性和多样性。从哲学上看,人权的普遍性要通过具体的特殊性才能表达出来。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权特殊性的含义是指人权的民族、国情、实现途径的特殊性。人权民族性是指各民族由于社会制度、内外环境、文化传统等具体情况不同,因而对人权的理解及保护措施也不同。人权的国家性,指各个国家总是根据各自国家不同的政治、经济等条件,在各自国家不同的历史、宗教和文化背景下,形成自己的人权观念,制定适合各自国情的人权政策和人权制度,由此也就形成了不同的人权模式。人权在实践途径上,只有考虑各个国家民族人权发展的具体情况,一切从实际出发,避免一刀切,才能使人权的普遍原则得到真正的、切实的贯彻,人权的法律和政策才能确有实效。因此,人权的全面发展必须把人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二者不能偏颇。
(三)个人和社会的辩证统一
马克思认为,从人权的主体来看,个人是首要的主体,“人首先是个人的存在”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十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20页。。人权在现实上体现为对个人基本需要的满足,这种需要是每一个个体的本性。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也就是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就是,人类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一切东西。个人的需要是人类的自身存在的必然性,人权的具体实现需要将个人的要求纳入保障范围,否则人权就是一句空话。马克思在 《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到:“任何情况下,个人总是从自己出发的”,但“由于他们彼此不需要发任何联系这个意义上来说他们不是统一的,由于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以及他们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关系”。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514页。需要是社会关系产生前提和动力,离开具体个人的需要,人权也就失去存在的前提。因此,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成员的履行责任时,必须以满足个体的基本需要为前提,以社会集体名义压制个人的正当需要,必将导致社会的分裂,也将摧毁人权的基础本身。但是马克思主义人权哲学对个人人权的强调和自由主义对个人人权强调不同,自由主义个人人权强调独立于他们的意志,甚至是独立于他们的社会关系之外的自由,个人被看作是他自身和能力的所有者。马克思强调人权对于个体利益和尊严的保护并不是个人独立能够完成的,必须要通过社会关系的途径。马克思强调,任何一个单个的个人仅凭自己是无法,也是根本不可能获得满足其自身需要的。“需要”本身并不能保证人类自身的存在和发展,维持和发展人类自身的必要条件是“需要的满足”,而“需要的满足”本质上就是人们通过一定的途径获取所欲求的对象,满足需要的途径问题把从事生产和结成社会关系提上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日程。换句话说,个人的需要离开社会本身就不可能实现,因此人权的实践离不开特定的社会关系,作为人权主体的个人或集体,只能在现实的社会关系中去先履行义务和享受权利,而人权保障也必须仰赖法律制度和司法救济,以及其他社会资源,引导社会救济等社会手段才能实现。
责任编辑:吕小雅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研究”(15KS066)、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中国特色协商民主过程中的公民有序参与研究”(15A191)、湖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公民资格发展和扩大农民有序政治参与研究”(11YBA295)、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湘潭大学毛泽东中心开放课题“国家建设视域中的毛泽东政治协商思想研究”(14MY09)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