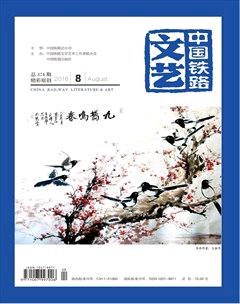王石榴
郑文臻
王石榴是我姥姥,我从未见过。母亲说她的名字叫王世珍,小姨说她的名字叫王石榴。两人都各持一词,我更愿意她叫做王石榴,一个更女人化的名字。
有关王石榴的信息,我都是从母亲或者小姨那里的片言只语里获得。她的出身是一个谜,但有几点是可以确定的。首先她是礼县人,这一点确定无疑,因为她从外地被带到本地,到死没有改变家乡的口音,多个人可以佐证她确属西和礼县一代的口音。其次她属牛,至于是生于1913年的癸丑牛年,还是1901年的辛丑牛年是存疑的。最后一点是她从自己的出生地被姥爷村里当兵的人带到了村里,从此再也没有踏上故乡的土地。母亲说她和姥爷吵架的时候,总要赌气带上孩子说回娘家去。可那个年代,可怜姥姥走出家门,浑然不知礼县的方位,走出半天,最后无奈返家。我觉得姥爷与姥姥吵架后,肯定是有恃无恐,稳坐钓鱼台,要走随你。娶一个不知道娘家方向的老婆,对那时的男人来说,的确是庆幸的,省了不少麻烦事。从姥爷家到礼县县城时下的公路距离约150多公里,不过是两个小时的车程,可在上个世纪交通基本靠腿的条件下,姥姥一辈子没能走到娘家。姥爷家没有人为这个可怜的女人去打听一下娘家人的信息。那个年代,王石榴娘家人在女儿被拐之后,也不知道打听过她的下落没有。丢失一个女孩子,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家人短时间的伤心之后,也许永远地忘却了这个世界上有个王石榴的亲人。于是母亲她们兄弟姐妹就没有了姥姥舅舅这样一层亲戚关系。
王石榴其人,母亲和小姨,以及舅舅均说是出身大家闺秀,家族是当时礼县城有名的王府,家道殷实。据说王石榴给她的孩子们讲述娘家的富有时,总要谈到王府门前高高的铁旗杆,还有石狮子和拴马石。这是旧时富豪和官宦人家大门的标准配置,除此之外,没有透漏更多的信息,比如自己的父母和兄弟姐妹。根据母亲的讲述,王石榴明事达理,可在厨艺、纺织、针线活方面是比较差的,至于地里的农活更是常落于人后,于是在旧时的大家庭里,常遭叔伯妯娌们的白眼,抬不起头来。而正是这些不如人的地方,把自己的女儿教得相当出色,母亲在年幼时就崭露头角,小小年纪厨艺、纺织、针线活样样不差,而且超出家里的年长的婶娘们。从这点看,王石榴倒是有点像没落的名门闺秀。小姨说王石榴样子长得极像她,由此判断她浓眉大眼睛,面大额阔,头发浓密,体态偏胖,个子偏矮。她缠过的脚,短而粗,像棒槌,不是标准的三寸金莲。王石榴做的另一件伟大的事,就是在自己的大女儿,我的母亲脚上成功地完成了自己未能实现的夙愿,把母亲的脚缠裹成标准的三寸金莲。
母亲是1937年生人,其时距辛亥革命已经26年,那一年日本人发动了“七七”事变全面侵华。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天水县就成立天足会,提倡妇女放足。旧时缠足的年龄大多是四五岁,按照这样的时间推算,母亲裹脚差不多是在1942年左右,差不多政府提倡妇女放足已经近30年。其时,尽管是偏僻封闭的农村,好多同龄的女孩子已经不再缠足。但王石榴仍然为自己的第一个女儿裹脚,足见裹脚这一封建习俗在她脑海中根深蒂固,同时也自己对未能实现的理想的执着。王石榴并不理会时代的潮流,一味按照传统的封建习俗,以及自己的审美观点调教和塑造自己的女儿。也许她认为,女孩子缠足和现在的母亲强迫孩子学跳舞、弹钢琴一样重要,事关孩子未来的前途和发展。母亲的骨子里反叛意识很强,据说在裹脚这件事上,让王石榴颇费周折。能让母亲最终就范,我从心底里对王石榴的能力、毅力和决心佩服,她终究不是一般的农村女人。王石榴的努力,成功地留下了裹足这一中国封建陋习最后的活标本,母亲估计成了中国最后一代裹足的女人之一。在北京的大街上,母亲的三寸金莲往往会招致众人围观,弄得她很不好意思。她特不愿意别人拍照,于是上街的时候总穿宽长的裤子,遮住小脚。这与王石榴当初的想法大相径庭,她当年费尽心机把女儿的脚裹成标准的三寸金莲,是让刻意让人观看的,是要炫耀的。其标准的配置应该是用一条带子把裤腿扎起来,更显得小巧,走起路来尽显女人摇曳的姿态。王石榴未能与时俱进,坑苦了母亲一辈子。一双小脚和别人的大脚一样,走过了人生崎岖的路程,比别人遭受了格外的疼痛和磨难。
关于王石榴的生年,就得从她是怎样从礼县辗转到姥爷他们村里说起。老人们一致的说法是当年白狼造反的时候,村里当兵的人从礼县带来的。据说白狼匪兵攻破礼县县城之后屠城,王府家眷尽数被杀,百姓惨遭屠戮,县城街道血流成河,王石榴属苟全性命,在战乱中被姥爷他们村里当兵的带到村里。姥爷并不是王石榴首任丈夫,她的第一个丈夫死后,正赶上姥爷丧妻。姥爷比姥姥大十岁,丧偶之后均未留下子女,小寡妇和老鳏夫在村里人撮合下组建了新的家庭,于是就有了后来曲曲折折的故事。
关于本地流传的白狼造反,其实就是史书记载的“白朗起义”。白朗河南宝丰人,1913年在家乡率众起义,转战于豫皖鄂交界地区。1914年1月攻破豫陕交界的紫荆关进入陕西,一路横扫关中十三州县,由陇县进入甘肃。先后在陇南地区活动两个月,大致在4月下旬至6月中旬,先后攻克陇南十三个州县,两破秦州,击毙天水总兵马国仁。一度攻陷礼县县城,所到之处烧杀掠抢,尤其打劫官家和绅富之财物。白朗叛军进入陇南以后勾结当地土匪,以“劫富济贫”为名,大肆焚掠奸淫,惨无人道。老一辈人所说的白狼匪兵礼县屠城应该就是发生在1914年5月左右的。据此王石榴应该是1914年从礼县被带回村里。
但是,如果说王石榴是1914年带回村里的,按照小姨的说法,她去世的时候为48岁,其时小姨为11岁。小姨是1950年生人,这一点确凿无疑,由此王石榴卒于1961年,大概是9月份,这样她应该是1913年出生的癸丑牛。那么1914年的王石榴只是个1岁的孩子,在兵匪横行的年代,那个当兵的能把一个1岁的孩子带回家抚养,他们抢劫的除了财物,基本就是成年妇女或者成熟了的黄花闺女,因此按理不可能。另外一个1岁大的孩子,在一个新的环境长大,不可能学成异于本地的礼县口音。
那么,王石榴会不会是1901年的辛丑牛呢?1914年她13岁,正好符合兵匪抢劫的对象,13岁的孩子,基本可形成稳定的家乡口音。但这种假设仍然从另一个侧面被推翻。如果这种假设成立,那么王石榴卒年为60岁,而不是48岁。她去世的那一年,小姨为11岁,小舅差不多八九岁。那么她生小舅的年龄应该是52岁左右。这不可能,在当年缺吃少穿、营养极度不良的情况下,绝不可能有这样的高龄产妇。退回到她是1913年出生的癸丑牛,那么生最后一个孩子差不多也到40岁左右,这有可能,但也是算当时少有的高龄产妇。
据此考证,如果王石榴确属牛,那么她应该是1913年的癸丑牛。其二,她到姥爷家村里绝对不是1914年。
但是,王石榴被带到村里,和兵乱有关应该是没有问题的。因为过去一个村没有几个识字的人,有老皇历的人家不多,忘记年份比较常见,记年的方法多以肖生,人们往往说马年、虎年发生了什么事。另外就是和那年发生的大事相关联,兵乱和自然灾害应该在人们的记忆中留下很深的印记,至于政治事件,农村人并不关心。因此,“兵乱年间被带回村里”应该是比较可靠的信息。民国年间的礼县兵乱,除了1914年的白朗匪兵攻陷县城之外,查阅史料发现,民国十九年(1930年)9月5日,受蒋介石支持的马廷贤礼县屠城,是礼县历史上空前之惨劫。事件的由头是1930年3月蒋与冯、阎、桂之间的中原大战爆发后,蒋介石为动摇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联军的甘肃大后方,花重金收卖了“黑虎吸冯军”的头目之一马廷贤,并委任其为“讨逆军十五路总指挥”,牵制和削弱冯、阎联军力量,扰乱联军后方。马廷贤乘机抢占地盘,扩张势力,到处攻城掠地。5月6日(农历四月初八)马廷贤由静宁南下攻占天水县城,烧杀淫掠,两小时惨杀无辜3000多人。天水被占后,陇南十五县不战而降。礼县县长马绍棠假意投降,暗中加紧筹集粮食,扩充民团,整修城防,准备武力抗拒。农历六月十七日,马廷贤派兵包围了县城,围城二十余日后,马军暗挖地道,以三口棺材炸药,炸塌城墙,守城攻陷。疯狂的马军进城逢人便杀,遇物就抢,妇女被侮辱者亦不计其数。屠杀持续一天一夜,城内8000余人中有7200多人被杀。马绍棠率部死守巷战,终因寡不敌众,惨败溃散,马绍棠被俘后押解至天水被杀。
这段历史在民间流传颇广,陇南天水一代的老年人都听说过。王石榴是不是在此次兵患中作为战利品被带回村里来的。只能是我的假设了。因为这一年王石榴年方十七,青春正值当年,正是这群匪兵优先抢劫的对象。而对于战事离家不远,目睹马廷贤匪兵惨无人道的横行,良心尚存的某个当兵的来说,带着妙龄女子远离是非之地,遁回家乡,既保全了她的性命,做了一件积德行善的大好事,又能白白捡一个媳妇,实在是两全其美的抉择,何乐而不为?而对于王石榴而言,苟全性命于乱世,就算走运,她还能怎么样呢?只能任人摆布了。因此我猜测大概是1930年6月王石榴被带回了村里。
另一个旁证是,母亲生于1937年,其实王石榴已经是24岁,到这个村里的时间已达7年之久。据说在生母亲之前,她生过两三个孩子,都不幸夭折。那时,对于一个女人来说,养不成孩子,没有人追究当时的生育条件和医疗卫生因素,往往怪罪于女人本身。而那时姥爷家兄弟三人,每年出生的孩子尽数夭折,亟需一男半女延续香火。王石榴屡屡养不活孩子,备受歧视。据传被赶出家门,和姥爷寄居在家里柴园的破房里。奇迹终于发生了,母亲的出生并成活,让这个好久没有孩子叫声的家庭万分惊喜,重新把他们迎回到家里,母亲成了家里的掌上明珠,而此后王石榴一发不可收拾,连续生了多个孩子,最终成活两男三女,也算有福气的了。我要说的是,从来到村里,7年的时间,从17岁到24岁,基本与结婚、丧偶、再结婚、生两三个孩子夭折的时间吻合。
如果上述推论是正确的,那么如何解释他们屡屡提到白狼叛乱时进村的说法呢?我觉得也许1914年白朗礼县屠城,年仅1岁的王石榴幸运逃脱,这个年幼的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屡屡被提及这段悲惨的经历,记在自己的脑海里。白朗叛军和自己的身世密切联系在一起,她的成长经历也许并不是在条件优越的王府。只是大人们告诉如果不是白朗反叛,她应该生活在家道显赫而富裕的王府。当第二次兵乱再次打破她的生活,她被带到一个陌生的环境,除了那个早逝的先夫,周围没有人知道她的过去。她在向自己的子女讲自己过去的故事的时候,刻意炫耀自己是所谓“王府”后裔的显赫,其实是转述大人们对她过去的一种假设,让自己的孩子有一种优越感罢了。而她说的“王府门前高高的铁旗杆,还有石狮子和拴马石”,是那个兵乱中自幼失去家人的女孩,对家人和自己家族的有关联的唯一记印了。
王石榴虽然说自己是王府的人,但从未向子女透漏自己的父母亲和兄弟姐妹的有关信息,只是笼统地描述为家大,人很多。这有违常理,女人对自己的娘家是记忆是深刻的,而远离,对于远离乡土的女人,更是如此。这种概念的模糊,也许印证了她的成长并非是王府,而是别人的转述。至于她从1岁到17岁是怎么成长的,没有更多的信息了。这种信息的缺失,可能不是她的健忘和失忆,也从侧面印证王石榴并愿不提及自己的过去。由此可以想象她并不是很如意。
另一种谬传的可能是王石榴告诉母亲和小姨的是自己生于白朗叛乱之时,另一次兵乱的时候被带到村里。是母亲和小姨她们听错了,把两个事件混为一谈,以讹传讹,最后形成“白狼兵乱时带回村里”的说法,一直口口相传。
关于王石榴的出身我只能考证到这里了。1914年白朗在陇南地区横扫各县市,礼县并不是重点,史料记载不多。而马廷贤制造1930年惨案,死者十之八九。死者没入历史的长河,生者苟全性命,而今已经基本作古。成千上万的罹难者和他们的家庭,是上个世纪社会动乱中极其平常的事情,见惯不怪。倘若要在历史长河中,细窥那一朵细小的浪花,并复原放大,难度可想而知,于是我决定就此打住。王石榴,你到底在心里埋藏了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已经并不重要。在丙申初春,有个您的子孙突发奇想,乱猜一通。倘若有冒犯您的地方,请您原谅我的冒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