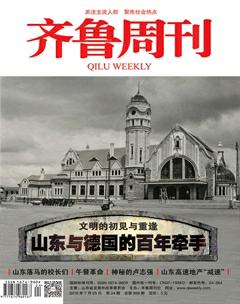午餐的革命
荆棘
一日三餐,已经成为我们普遍接受的饮食规律。俄罗斯有句谚语:“自己吃早餐,和朋友一起享用午餐,把晚餐留给敌人。”实际上是在告诉人们一日三餐怎么吃才健康。今年三月,央视《百家讲坛》主讲人马未都发表了题为《两顿》的博客,颠覆性提出了“一日两餐”的生活理念,并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针锋相对的争论。
在消费主义快感盛行的现代社会,当脂肪、高血压……这些从前未闻、现在却无所回避的“富贵病”出现,“一日两餐”不仅意味着更为适应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社会思潮的松动,同时被赋予了“节制”的文化意义——人们对待食物和欲望的态度可谓天差地别,当节制不再成为令人称道的美德,在大处看,这是关系到人们安身立命的终极问题。
三餐演变史
“我们现在每天三顿饭,上班的人早餐紧张,午餐条件不好的就凑合,晚餐自己做的话还累人,总之,对上班族来说,三顿饭都不尽如人意。”无论是出于健康和适应现代社会节奏的考虑,还是被推上“被告席”的“一日三餐论”,马未都“一日两餐”论首先从饮食文化的角度给我们留下了追根溯源的空间。
为什么每天要在相对固定的时间点吃三顿饭,其实不像我们所设想的那样理所当然。
在原始的狩猎生活中,由于食物的产量多寡难以预料,他们的饮食也全无规律,有时能一天吃多顿到极饱,但另一些时候则一整天不进食也没关系。因此,规律性地进食,本身就是“从混沌到有序”的一种文明化规训过程。所以孔子在《论语》中才要强调“不时不食”。
最初,一日两餐似乎是相当普遍的情形。据考,中国上古便是如此,“商代人为两餐制,一餐是在上午进之,约当今7-9点间,称为‘大食,一餐在下午,约当今15-17点间,称为‘小食,两餐就食时间约定俗成,又被纳为时辰专名。”
迟至两宋时人们普遍“每天仅早晚两餐,官员士人概不例外”,现在人们常说的“三餐”,当时却说“二膳”,即使贵为宰相,每天也只早晚各一餐,中午通常是不吃饭的。《夷坚丁志》卷一七载打油诗:“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
直至明代,常人仍多习惯两餐。明初洪武年间,宫中饮食相当俭朴,即使御膳,也只是在奉先殿日进二膳。根据清宫档案所藏乾隆南巡的膳单,乾隆帝每天只吃两顿正餐,分别叫“早膳”和“晚膳”。这种情况在近代中国仍极为普遍。从西北到东北、江淮等各地,其例不胜枚举,有不少地方甚至至今如此。
这种两餐制下的时间安排也颇为不同。从各种记载看,在两餐制的时代,早上九十点吃早餐、下午四五点吃晚餐较为普遍,但也有例外,成语“旰食宵衣”便以天黑后吃饭来称谀帝王勤劳政事。
由两餐而演化为如今习见的一日三餐,最早或见于古埃及。古埃及普通人本早晚各一顿,但富裕者逐渐在下午加一餐。在食物供应匮乏的时代,能多吃一餐,本身即是经济状况较好、乃至社会地位优越的表现。金字塔铭文记载有法老号称“五餐”,朝鲜李朝时国王也一日五餐。
上层人物每日多餐,在中国历史上亦然:汉代时最高统治者每日四餐,贵族三餐,而平民只两餐,可见向三餐的演变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侧面。三餐制的演化定型,最初可能见于明代江南较富裕地区,相关记载表明,“明代江南人家,朝夕亭午,每天均以三餐为足。此外,又有上下午中间的点心。”(陈宝良:《明代社会生活史》)。随着一日三餐的逐步形成,三餐的内容本身也固定化了。如《红楼梦》从五十回等处看,午饭已渐渐地从非正式的点心,变成了重要的正餐,而原本重要的早上第一餐,反而渐渐地非正式化了。
但另一方面,“多餐”自然而然与某种特权、贪婪、浪费等负面形象联系起来,翁贝托·艾柯在《倒退的年代》一书中曾说:“我甚至仍记得当年法西斯政府要求包括我在内的学童高喊‘上帝降祸给英国鬼的口号,因为他们是‘一天吃五餐的民族,所以犯了七大罪之一的贪吃罪,是不配和刻苦耐劳又节俭成性的意大利人相提并论的。”
“早午餐”里的社会思潮:各种开胃派和荤腥,对人是一种折磨
两餐制其实是一种普遍的世界性情形。古代近东、希腊、印度的普通人一般也只吃两顿。早上劳作,正式吃饭一般要到“晌午”。在Uruk供神享用的供物每日有四餐,分小餐大餐,早晚各二。供神的食物为一日两餐,是当时美索不达米亚常见的做法。柏拉图在《理想国》中说,在前往叙拉古时,他想知道的是,在“幸福被看作一天吃两顿饱饭,晚上从不一个人睡觉”的地方,年轻人懂得节制和公正吗?
1895年,《打猎者周刊》(Hunter Weekly)里,英国作家盖伊·贝林格在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brunch(早午餐)”这个词。他在文章中说:
“为何不用一种新的、由茶或咖啡开启的午间饮食来替代我们每周日教会活动后那个提早开始的晚餐呢,后者往往是各种开胃派和荤腥,对人是一种折磨……有了早午餐,周日上午不用早起,这会让周六晚上喝得酩酊大醉的人感到轻松很多。”
贝林格的这一呼吁明显体现出当时社会思潮的松动,也就是说,个人的生活体验被更大程度地接受了,那种古老刻板的规律作息被逐渐打破。1939年,《纽约时报》刊文宣称周日就是“一日两餐”,即早午餐和晚餐。而到了60年代,早午餐在更大范围内风靡,以至于出现了很多教人烹制早午餐的美食手册。90年代的时候,美国人在周六也开始吃早午餐,而早午餐也成为了一种生活方式,不再成为专属于周日的一种“特殊活动”。
还是在《打猎者周刊》的那篇文章中,贝林格说:“早午餐是令人开心的存在。它给人们的交流提供条件。它让你心情愉悦,让你对自己和周围人感到满意,它可以一扫忧愁,驱除一周的纷乱烦忧。”
虽然这段话可能会让人感觉神化了早午餐,但饮食并不只是几次吞咽就能表达的,吃一餐饭还包括你吃饭的时间、地点和一起享用美食的人。饮食常常是一件社会化的活动,它与人际交流和社会变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1980年,美国历史学家卡尔·德格勒(Carl Degler)在谈到美国早午餐文化时提到:“在150年前城市化和工业化刚刚发展起来的时候,周日的晚餐变得格外重要,因为那是一家人一周内唯一有机会聚在一起吃饭的时间”。因此也可以想见,后来逐渐取代周日晚餐的早午餐对于已经逐渐完成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美国社会也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因为早午餐,家人才有机会聚起来,这甚至可以被视为一项家庭活动。
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越来越多女性走上了工作岗位。工作日没有时间为家人烹制丰盛的早餐,职业女性们于是在周末和家人一起准备早午餐,享受休闲时光。因此,早午餐也可以被认为是女性社会地位逐渐提高的产物,有各种社会进步的烙印,被视为一种新式的生活方式。
“一日两餐”:
当节制不再成为一种美德
现代社会,越来越多人不再关注“吃”本身,而是顾着吃一顿饭带来的种种衍生物,这就包括背景音乐、气氛、社交等等。
在肖恩·米考利夫的著作《早午餐的问题》中,早午餐俨然被上升到了反映阶级身份和自我认同等等问题的高度。米考利夫认为,早上和中午界限的模糊实际上也是工作和生活之间界限模糊的反映。用早午餐的时间和朋友或者客户“交流感情”这件事在主流价值观的关照下看起来很合情合理,是一种“这个人很会管理和利用自己闲暇时间”的做法,是一种“政治正确”的做法。
但有多少人注意到,这本身实际上是一个非常疲惫不放松的过程?又有多少人其实想说,“去死吧礼节,去死吧社交!我只想自己带着,瘫在家里。我已经够累的了!”
也正因为此,马未都在《两顿》中如是说:如果吃两顿,上午10点上班,下午4点下班,两头吃饭时间都宽裕,对身体也好,符合早吃饱、晚吃早的养生理念。每天6小时上班效率高,精力集中,不间断就不浪费时间,晚上还能拉动社会消费,第二天晚起会儿也无碍,想想吃两顿真是好处多多。
的确,更多时候,或许早中饭存在的本身也恰恰是因为人们太累了,周末连睁眼都变成了一件费力气的事儿——什么“富裕阶层的生活方式”都滚开吧,吃早午餐根本就是因为一大早爬不起来,而一睁眼已迟到千年。
从健康角度,日本医学博士渡边正也曾大力提倡“一日两餐”的健康理念。他认为,早上起来身体中还残有前一天的多余水分及毒素、废物等,因此早上与其补充食物,不如以排泄为先; 内脏功能在上午最为活跃,新陈代谢,清洁肠道,排除废物等,所以这个时间段补充食物、吃东西,反而会给内脏增加负担。
放弃早餐,经常断食治疗法,由此,肠道环境得以有效清洁,自然治愈能力得到明显提高。作者认为,这才是获得健康的基础,是所谓获得健康的常识。
如孔子所说,情欲和食欲是最基本的欲望。但他之后的中国古人对欲望的态度不怎么友善,传到朱熹那里就成了“存天理、灭人欲”,这和西方基督教对待欲望的态度几乎完全一致。在苏格拉底看来,唯有节制,也就是忍受快感的过度膨胀,才能让人们体会到一种值得回味的快感:只有在饿了的时候才去吃东西,胃口成了饮食中的调味品,而其他时候的进食都是破坏节制原则。从小处看,这关系到人们是不是能够长久地享受快感而不感到厌倦,而在大处看,这是关系到人们安身立命的终极问题。
在柏拉图的体系里,饮食、性、软弱、睡眠等等都是人在追求德行高尚之路上的绊脚石。而在消费主义盛行的现代社会,我们确实已经和古希腊人的理想相去甚远。节制不再是令人称道的美德,消费社会希望他的理想对象成为一所工厂,24小时生产出尽可能短的、容易满足的欲望。
从前身体是欲望和道德斗争的战场,如今身体成为欲望表演的场所。而身体需要满足的基本条件是健康,这样才能维持欲望的运转:当脂肪和高血压这些从前未闻、现在却无所回避的“富贵病”出现了,身体在这时能做的是维持感官的能力——在此过程中,代表节制的“一日两餐”制能从另外的角度审视自己的处境。